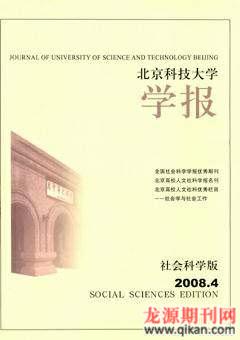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宋 琳
〔摘要〕女性主义自提出“科学—性别”研究(science-gender system)以来,涉入到科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其中尤以科学史的研究成果显著,但是其中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使以女性主义视角切入中国科学史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当我们以女性主义理论来展开本土化探索时,在理论建设、方法研究、内容选择等方面应如何实践,文章尝试着提出作者的一点建议。
〔关键词〕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科学史;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4-0164-04
一
女性主义认识论作为世界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学术派生物,一经产生就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女性主义借用“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涉入历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但是进入科学领域则相对较晚,正如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伊夫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Keller)所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女权主义理论——我把这一称呼看作是集体性努力的结果——的著作开始出现在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中——虽然还未曾出现在任何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学科中。”[1](63)但是随后,即出现了凯勒所期待的“科学—性别(science-gender system)研究,并而迅速成为一个理论研究热点。
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在批判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父权制统治,而这种批判之所以较晚地指向了科学,是因为科学历来被看作是客观公正、价值无涉的,所以科学领域是不存在什么不公正的现象的,面对科学界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科学分层中的性别差异,人们历来心安理得,只是轻描淡写地以“女性不适合搞科学研究工作”一带而过,但是女性主义却认为我们传统上对科学的认识只是一种神话,是掩盖在客观、公正假面具之下的一种性别关系的强权政治。
女性主义提出了建立在科学与性别双重建构之上的“科学与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科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男权主义,科学的性别化倾向不仅表现在科学的性别分层和男性权威的结构,而且表现在科学的整个思想框架、方法论准则和价值体系的男性化标准和规则中,女性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所谓客观的、普遍的、价值中立的科学公认标准实际上是男性中心文化设计的一种神话。与科学的建构性相呼应的是性别的建构性,女性主义创建了社会性别的核心概念,并首次对“sex”与“gender”做了区分,指出生理性别(sex)是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证实的男性或女性,而社会性别(gender)则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正如西蒙·德·波伏娃在其女性主义名著《第二性》中曾指出:“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明确指出,造成两性不平等的根源是社会文化因素,因此是可以改变的,要想改变两性的不平等就必须把女性问题置于两性关系的结构中去研究。女性主义的“科学—性别”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融合。正如凯勒指出,“性别和科学都是社会建构的范畴,这是对社会性别与科学进行反思的两大前提。”[2](4)
二
女性主义自将性别与科学联系在一起,就进入到与科学相关的诸多研究领域,其中在科学史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正如凯勒认为,女性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研究学科的图景——某些学科的改变要比其他学科显著得多:最引人注目的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科学哲学,至少目前还不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几乎没有改变;只有科学史的某些领域发生了变化。”[1](63)科学史作为对科学研究的一级学科,当女性主义理论随着后现代思潮冲击着科学技术元勘的诸多领域时,首先在科学史获得突破也是较自然的事。
今天,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解读科学史在欧美文化传统中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然而有关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却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席宾格尔在1988年谈到:“我们还没有关于中国古典科学的社会文化性别的研究。”随后到了90年代的时候,开始有学者从社会性别视角介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诸如美国学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对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和建筑技术史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科学技术史专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对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研究,台湾学者傅大为对中国台湾地区近代妇科史的研究等。我们发现在这有限的研究工作中,从参与研究的学者来看,几乎都是海外学者,而中国大陆本土的研究者介入的很少;从研究的时间段看,仅有的工作也仅限于古代,而对晚近和现代的科技史还没有涉足;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是从技术的发展来分析其中隐含的性别权力关系,而诸如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女性生存状态、重大科技事件中的性别差异等问题还没有涉及,并深入地展开。鉴于西方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已初具规模,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域,而从性别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科技史还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章梅芳博士曾说,在中国“以妇女与科技的历史研究为例,利用女性主义理论展开本土化的案例研究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 [3](237)它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成为一片值得开垦的沃土,在于“‘性别是一种关系过程,各种社会发展均在这一视角下得到反映。它不仅仅是一种指代妇女的新名词,而且是一种分析方法,改变着全部旧的观念。用性别范畴分析中国,不仅仅是将这种分析纳入中国研究而已,还将彻底改变人们过去对中国的全部看法。” [4](2)从性别的角度切入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不但可以为我们解构中国科技发展史中所隐藏的性别权力关系,而且还可以解构一种制度,解构一个国家、解构一个民族,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父权制”在中国存在的独特形式。
三
“社会性别”是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它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虽然世界范围内,女性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中存在着相似性,但是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社会性别”应该是有国界的。女性主义学者贝尔·胡克斯认为,社会性别理论建立在一个共有的和本质化了的社会性别的假设之上,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5]她反对把所有的妇女都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分类,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以同样的方式和程度被边缘化。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把这一理论移植到我国时,如何分析该现象的中国特色,这成为问题的关键。人类历史中不存在单一的社会世界和不变的性别关系,因此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中加以分析和考察。作为科学史的本土化研究,我们更应该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特定文化中的性别关系,二是中国具体科学语境下的性别关系。
一方面应把握好中国文化中性别关系所表现的独特方式。在历史上,性别问题一直是隐而不现的,或者叫做视而不见的,但是“不现”或“不见”的程度和情况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却是不同的。首先,当我们用产生于西方文化中“社会性别”理论应用于解释中国科技史时,要注意文化的多元性所带来的不同。一位女性学者曾说,在中国“歧视妇女的意识是观念性的(认识上的),不是信仰性的(与宗教无关);是历史性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奏效),不是本质性的(与创世说无关)。中国历史上没有女权(在社会上),但有母权(在家族中)。有轻视妇女的历史,但没有仇视妇女和诋毁女性的运动。因此,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7]这位学者从总体上概括了中国性别关系的特点。在中国的性别对抗中历来是缺少暴力和激烈的冲突的,正是在这种比较温和的性别关系中,使研究者在深入研究性别问题时缺少了更能引起话题的“关键事件”,更多的性别权力问题是潜藏在日常生活中,隐而不现的。同时,这种温和的性别关系也决定了中国女性的进步只能是渐进的,而且她的进步是缺少主体性的,女性的命运更多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因为中国女性的进步历来都是由男性倡导和发起的,每当中国处于危难的时刻,如近代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新中国建立初期,男性倡导男女平等是号召男女共同来承担救国的大任。所以借鉴和利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来研究中国科技史,我们必须着重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本质、性别关系的特殊规定,并把社会性别维度纳入民族、阶级等范畴做综合研究。其次,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制”形式自西周建立起来以后,也经历了种种的变革,因此,我们应有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分析“父权制”的成因和演变,才能更全面地把握中国文化中性别关系的特征。
一方面应把握好中国科学发展中的性别关系。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应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即古代科技史和近代以来的科技史。只所以这样分,源于这两个阶段的科技发展历史境况的不同。古代科技史可以说是中国原汁原味的东西,是根治于中国文化土壤中萌生出来的,明显地带有中国文化的烙印,而近代以来的科技史则是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移植过程,是在与西方科学反复冲撞中,一个艰难的学习和创造过程。当我们用性别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科技史是,应该明确这种阶段性。在中国,直到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科学技术虽然已逐渐成为一种支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还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真正的科学共同体并没有形成,科学和技术是散落在士大夫阶层和民间工匠中的,这时科学和技术领域中性别地位的差距是与在更大的社会中所持有的社会地位差别遥相呼应的。到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移植的成功,中国开始走向了建制化的道路,这时候中国科技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则体现了西方科学中性别霸权的复制与中国原有父权制的一种交融。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与清末民初开始的留学科技人员陆续回国分不开的,这群后来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界精英的群体中绝大部分都是男性,如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81名,其中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53名,无一女性院士;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次聘任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共172名,林巧稚成为唯一的女性学部委员。中国近代以来科学的社会建构,无论是从科学人员构成,还是科学发展所选择的领域等诸多方面都带有男性中心主义的色彩。当我们对科技史进行性别分析时不能脱离科学所在不同阶段的历史背景,只有在历史的脉络中才能把握科技女性的命运。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研究中国科技史,要同时注意中国文化进程中和科技发展中的性别特征,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是如何促成了中国科技领域中独特的性别关系,从而揭示出中国特有文化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中国科学女性,这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科学的发展,揭示科学女性在科学界中如何被边缘化的秘密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中国科技史的道路才刚刚开始,我们应该如何展开中国科技史的本土化研究,应该遵循什么,应该关注什么,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该着重考虑: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我们要着力进行社会性别理论的本土化建设。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从事中国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基础。对科学史编史理论的选择和创新是决定科学史研究能够走多远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科学史研究中,理论研究与事实展开就好比树根与树干的关系,只有树根扎得越深,树干才能枝繁叶茂,这种关系对于一个新的领域来说尤为重要。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对中国科学史领域的学者来说,更是一片没有开发的处女地,“欲要善其工,必先利其器”,要想开发这片沃土,必须在坚持文化的多元性,坚持不同文化中女性的特殊经验和特定的性别权力关系的前提下,构建本土化社会性别理论,这是完成科学史本土化研究的理论前提。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要寻求针对边缘人群研究的有效手段。女性群体一直以来在科学史上都是被边缘化的人群,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如何让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研究工作至关重要。以往中国学者针对女性的研究多采用数据统计、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但本人的经验认为这些方法局限性很大,数据统计、问卷调查往往是在结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推测,难以表现女性自身的主观经验;深度访谈也往往由于女性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在很短的接触中无法让她们表述出自己内心深切的感受(中国人的性格决定人们并不喜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访谈结果因而也并不很成功。人类学方法作为一种对一个特定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的有效研究手段,不失为一种对科学女性进行研究的好方法,可以深入到实验室中、深入到科学家群体中,从她们的日常生活、言谈举止中去认识她们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科学思想。同时,我们可以借助于语言学、修辞学的研究成果来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我们应进一步挖掘和寻找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域。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者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已经形成几个相对集中的研究域,诸如,在研究群体上,她们往往选择诺贝尔奖女性得主这些杰出科学女性,或生物学、物理学等这些较具有性别特征领域的科学女性;在时间段上,她们往往选择一些在西方科学史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如近代科学产生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等等。她们的研究视角为我们进行本土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应结合科学发展的历史进一步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域,如中国独特的中医领域中女性的研究、科学史上被遗忘了的女性研究,以及中国近代科学本土化实践过程中性别关系的构建研究等等,只有使对女性处境的认识深入到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历史、特定的文化中去,才能很好地完成本土化实践工作。
总而言之,在进行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中,我们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特有的文化特色、科学观念和社会性别的特殊性,在充分考虑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和独特性。
五
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对科学领域中杰出女性的研究,它不是完全的以女性为研究主体和研究目标,它是两性共同参与的、既包括对女性也包括对男性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旨在揭露隐藏在性别之中的权力关系。女性主义科学史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批判史,它直指科学客观性的伪善、直指科学领域中性别不平等现象存在的深刻原因。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批判功能,所以对于以下的问题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首先,如果漠视科学界中“女性缺席”的现象形成一种惯性,就会严重地挫伤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造成严重的人才流失。因为无论是从生物学角度,还是科学史上女性科学家的工作都说明女性并不是天生就不适合科学研究工作,而是另有原因。美国女医学物理学家罗莎琳·苏斯曼·雅洛若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奖是指出,“要解决当今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世界决不能浪费它一半人口的才能”[6](136);其次,缺少、排挤女性参与的科学是不全面、不健康的科学。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父权制”、“男性化”特征已经暴露出它诸多的弊端,这源于对科学的建立是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而相反女性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体验世界,以不同的价值取向来理解科学,只有当科学的发展涵盖全人类(包括女性)的经验和价值,科学才能全面、健康地发展;再次,科学领域中的“女性缺席”更需要我们深思什么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在科学领域中,性别平等不能是也不应是“男女都一样”,而应当是承认性别差异、充分尊重性别差异基础之上的平等,使女性获得在科学领域中的生存和发展权。
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读女性的昨天,更是为了女性的明天。“从社会性别角度切进中国,在中国研究中是一种革新。它突破了民族、国家革命、战争乃至家族、家庭、婚姻这一类社会范畴和传统设置的批判尺度以‘女人的名义推举一系列‘人的问题,使得一整部中国史因此焕然一新。”[7](175)以史为鉴,正是从科学史的角度分析,使我们来看当今存在于我国科技界中的性别分层现象,来把握中国现在科技界中的“父权制”的存在形式和存在的原因,而使“父权制”的问题不再困惑明天的女性。
〔参考文献〕
[1]伊夫琳·福克斯·凯勒. “性别与科学”的起源、历史与政治——出自第一人称的表述[A]. 希拉·贾撒诺夫等编. 科学技术论手册[C]. 盛晓明等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
[2]Evelyn Fox Keller.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M].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3]章梅芳、刘兵. 妇女与科技研究综述[A]. 刘伯红主编.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01-2005)[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 性别与中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5]金一虹. 社会性别理论:新视角、新思维方式与新的分析范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评介[J]. 妇女研究论丛,1999.
[6]郑艳秋、朱幼文编著. 科学女人——10位荣获诺贝尔奖科学家小传[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7]李小江. 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李晓光)
On Localization of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rom Feminism Angle
SONG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Since feminism proposes the science-gender system, it has reached to many scientific fields, among which the scientific history has made obvious achieverments. However, the studie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are comparatively weak, which makes it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from the angle of feminism. The present author tries to give some suggestions on theory construction, method study, and content choice.
Key words: feminism; social gender; history of science; loc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