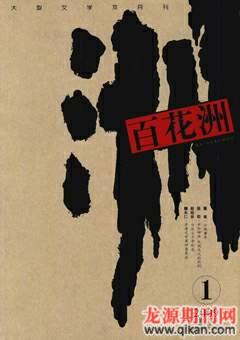茅盾文学奖评委笔谈
2008年10月底,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落下帷幕,经过层层评选,最终有四部作品获奖。对于这一评选结果,文学界和各种社会舆论众说纷纭,这也许并不奇怪。一方面,当今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不同,当然就会有不同的认识看法;另一方面,文学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不像物质产品那样,可以确定某些具体客观的量化指标用来进行检验评比,以区分高下优劣,对文学则只能依据评判者某种整体性的审美判断。因此,我们也许不能简单地说,获奖作品就是最好最优秀的作品,而未能获奖的作品就更低一等。我以为,对于文学来说,恰恰适合套用那句广告词,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作为本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参与者,笔者有机会集中阅读了近一时期比较优秀的一批小说作品,我的整体感受是:一方面,这批作品的差异其实是很大的,这里主要指的是,比如题材的差异,有写现实题材的,也有写历史题材的;有写乡村生活的,也有写都市与机关生活的;有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也有写军旅生活的等等。再如写法上的差异,有的是朴素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有的是传奇式的叙事手法,也有的是荒诞象征性的写法等等。还有文学风格上的差异,有的温情朴实细腻,有的波澜壮阔磅礴大气,也有的婉转多讽充满反讽意味等等。如此题材风格多样差异巨大的作品,要放到一起来进行比较评选,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另一方面,从艺术创造和审美价值来看,其实又未必相差多么悬殊,无论获奖还是未获奖的作品,应当说都各有其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这里笔者仅就其中的部分作品,简要谈谈自己的阅读理解与审美感受。
首先从几部获奖作品谈起。贾平凹的《秦腔》是一部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小说,也是一部具有独特贾氏风格的作品。贾平凹作为我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其创作成就以及在文学界的影响是世所公认的。他的小说创作始终以其所生活的三秦大地为根柢,尤其是乡土题材的写作,从上世纪80年代的“商州系列”作品,到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长篇小说《浮躁》;从90年代的《高老庄》到如今的《秦腔》,都无不根源于他家乡的乡土生活,无不反映了陕南的地域风情和文化习俗。作者对这种乡土生活极为熟悉,几十年对家乡变迁的关注与牵挂,使他对这种生活烂熟于心,有人批评其为“坐家”,即坐在家里胡编乱造地写作,是不太实事求是也不太公平的,至少《秦腔》这类作品不是这样。而且他的小说语言与叙写方式,也都是地道乡土化具有独特贾氏风格特色的,几乎是不可重复、不可模仿的,仅此而言,在当代作家中也并不多见。《秦腔》所叙写的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乡土生活,是陕南某地一个叫清风街的村镇(以作者家乡棣花街为原型)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可以说是“一地鸡毛”式的,庸常、琐碎甚至无聊,多是家长里短、家族矛盾与邻里纠纷。即便是比较大的事件,也不过是果园承包与土地置换带来的利益纷争,强征农田税费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主要人物白雪与夏风的情感婚姻纠葛,等等。然而正是在这种波澜不惊的平静叙写中,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现代变革中的乡村图景。从表面上看,农村土地承包各家各户自主经营,乡民的生活自由、散漫而平静,然而背后却悄然萌动着各种矛盾冲突;在看似简单的乡村现实关系中,混杂着现实利益的纷争与观念情感的裂变,交织着人们的期盼、躁动、迷惘与焦虑不安。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乡村变革显然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带来了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与生产力的解放,乡村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更具有活力,乡民们也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而另一方面,几乎每个家庭与个人,都无不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和关注半径,传统亲情、乡情等朴素价值观念逐渐崩解,现实关系显得松散而缺乏凝聚力,人变得自私、冷漠、平庸而缺少理解宽容等等。正如作者所说,如今的乡村,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向前拥着走;旧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无所适从。这无疑隐含着当下乡村生活的某种深刻矛盾乃至危机。小说以冷峻的笔法,写出了当下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极富于生活质感;同时也寄寓了作者对乡村变革的前景与乡亲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忧思。小说完全是自然主义式的还原生活写作,没有典型化的提炼概括,也没有线状推进的中心化事件情节,人物故事的叙写呈网状结构,也恰好契合了生活之网的本真形态;小说语言是地道的贾氏风格,朴拙而极富秦的韵味;写作方式是一种密实的流年式叙写,有些絮絮叨叨、鸡零狗碎,初读时也许不太容易读进去,但如果有相当的耐心读进去,还是别有趣味和意蕴的。当然,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小说中有些细节和场景描写比较夸张失实,显得有些俗,其中描写“我”(引生)的自残、自虐、自慰等等,本意也许在于写“我”对白雪情感的纯洁与纯真,然而却给人以残酷丑陋之感,反倒显得低俗了。
同样是写当下的乡村生活,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则是全然不同的写作风格,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注重对生活现实的提炼概括,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结构的严密性,注重题材意义的开掘及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因而更具有可读性。小说以农村现代变革为时代背景,以一个村庄(楚王庄)为典型环境,展开对中原乡村生活全景式的描写,主线则是写主人公楚暖暖一家的生活命运及其悲欢离合的故事,从而融入对农村现代变革的合理性与荒诞性,以及关于人性与权力、资本等悖论性关系的深刻思考。乡村姑娘暖暖以其在城市务工的经历及其所获得的现代观念,回到乡村力图主宰自己的命运,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她不顾村主任家族的要挟逼婚和家人的反对,自己做主嫁给了贫穷弱势的青年农民旷开田。她本以为靠自身的老实本分和勤劳奋斗就可以过上安稳殷实的生活,没想到他们的命运并未逃脱村主任詹石磴的权力掌控,权力的魔棍轻轻一点,暖暖一家就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走投无路之际,她不得不含屈忍辱以自己的肉体和人格尊严与詹石磴进行交换。这种屈辱刻骨铭心,也更激发了她自立自强发家致富昂然做人的意志力量。暖暖凭自己的智慧和眼光,通过经营特色旅游和家庭旅馆迅速发家致富,然后用心计扳倒了詹石磴,让丈夫旷开田竞选当上了村主任。为了带领乡亲们共同富裕,她领头办起了村里的旅游公司,引进了商人薛传薪的资金和项目,产业如滚雪球般迅速扩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让暖暖始料未及,旅游公司扩张强占土地严重侵犯村民权益,村里姑娘进入旅游公司当服务员却变成变相卖淫,当了村主任的旷开田变得比前任詹石磴更蛮横霸道,欺男霸女为所欲为,公然声称要做楚王庄的“王”。面对这一切,暖暖气愤难抑伤心欲绝,极力进行干预和抗争,但在资本与权力结合形成的魔力面前,她又一次成为失败者,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事业陷入困境。然而她仍不甘心于在现实面前屈服,仍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暖暖的人生命运令人扼腕叹息,充满悲情与悲怆,却让我们看到一种人格精神的柔韧与刚强。小说一方面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农村变革的生活现实及其内在矛盾,充满生活气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显示出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小说不是那种“还原式”写作,而是有对生活现实的深刻领悟与表达,提供了比生活题材和人物故事本身更多的东西,具有相当的审美超越性,可以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比如,关于人的命运、人性与权力、资本的悖论性关系。当初暖暖一家的不幸是由于既无权也无钱受人欺侮,因此他们含屈忍辱拼命挣钱发家致富,费尽心机竞选夺权出人头地,以求主宰自己的命运扬眉吐气。然而当这一切都如愿实现,金钱权力都拥有的时候,却又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重新陷入悲剧性的命运之中。这似乎寓示着,缺乏权力和金钱难免会陷入屈辱的生活境遇和不幸的命运,但即便拥有了权力和金钱也并不能保障拥有幸福生活,一切都有可能走向反面,坚守做人的道德良知和理想信念,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再如,关于当代中国农村变革的方向、出路何在?“非农”产业化是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吗?商人薛传薪给楚王庄带来了资金和项目,发展起了旅游产业,他以救世主的口气说是来“拯救”农村的,然而资本的侵占和掠夺却给楚王庄带来了新的苦难和灾难。还有,只有少数人奋斗创业成功,而没有形成乡村共同富裕的机制,特别是农村民主体制改革还没有得到切实推进,村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就不可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不合理的现实。暖暖的命运遭遇和旷开田的蜕变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启示。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叙写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族人的生存状况及百年沧桑的史诗性作品。小说通过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生动叙写了这个弱小民族带有原始野性的生存状况。他们历来以部落群居的方式生活在茫茫原始森林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与驯鹿、马、羊等动物相依为命,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原始宗教信仰。与现代文明社会相比,他们的人际关系相对单纯,情感淳朴,当然也自有其矛盾冲突和爱恨情仇。这部小说没有像许多民族题材的作品那样,刻意构织民族冲突或部落间的纷争,在激烈的冲突争斗乃至战争场景中讲述故事描写人物,表现某种民族精神;它甚至都没有什么中心事件和情节主线,也没有大起大落的矛盾冲突。它向读者展现的是鄂温克族一个家族部落的日常生活,他们所遭遇的自然灾害与生死别离的种种苦难,他们的爱情、亲情与人间真情,他们的欢欣、痛苦与忧伤,从而写出了这个民族勤劳智慧、坚忍不拔而富有血性的民族精神,写出了一种原始性的人性的淳朴、善良、忠诚、宽容,让人感受到这种生活的纯净美好和人性的温暖动人。然而他们所遇到的现实困境是,随着现代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推进,森林被不断砍伐,自然生态遭到破坏,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将不复存在,他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也将难乎为继,他们不得不离开世代相守的家园接受和适应新的生活。现代的城镇化生活虽然有许多诱人之处,然而像“我”这样老一辈的鄂温克族人却依然对古老的生活方式充满怀恋,依然坚守在日渐破败的森林家园里;新一代的鄂温克族人虽然更为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也更容易接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然而他们也依然难以割舍这种民族情感。“我”的孙女依莲娜是鄂温克族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作为北京美院毕业的画家,无疑更多受到大都市生活及现代文明的洗礼,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她更加眷顾自己民族家庭清新温暖的生活,终于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森林部落家园,试图用画笔记下大自然的神奇美丽和这个民族最后的生活图景,不料却意外失足葬身在这美丽如画的土地上。在这些描写中,可以说寓含了对土著式少数民族生存命运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现代文明进程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深刻反思。这种人文价值的反思,甚至可以说具有全人类性的普泛意义。小说文笔优美,叙事和场景描写饱含诗情画意,温暖动人,让人读后难以释怀。
麦家的《暗算》也许称得上是一部奇异性的小说。首先是人物故事的奇异性,小说讲述的是秘密情报部门的传奇故事,具有相当的神秘性和吸引力,以前很少见到此类题材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题材写作领域。其次是故事讲述方式的奇异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题材的独特性决定了故事讲述方式的独特性,它没有采用一般现实主义小说的叙写方式,而是采用传奇性的写法,运用精巧独特的构思,丰富奇异的想象,诡异多变的叙述手法,把故事讲得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和神秘感,使其获得了极大的可读性。当然,题材和写法的奇异性并不足以决定小说的内在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小说对人物命运遭际描写,心灵情感与内心世界的展现,对人的生命意义价值的探求与关怀。小说里写到的那些特殊人物,如神奇的听风者瞎子阿炳,天才的解码者黄依依,在刀尖上行走的捕风者老A们,都是一些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物。他们担负着神秘而重大的特殊使命,他们的一切也同时被一种神秘而巨大的力量支配着,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个人命运将是悲剧性的。他们只能生活在离群索居封闭的神秘世界里,身负特殊使命,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拥有常人那样的个人化生活,他们的一切都是受限制的,必须无条件服从所担负的使命的,甚至随时面临苦难和牺牲;而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当然也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有情欲的躁动和爱情的渴望,有各种生活之欲和儿女情长。由此构成的巨大冲突对于他们无疑是极为严酷的考验,在这种冲突中表现出来的人物的心灵世界也许更真实可感,其人格精神甚至比战场上的英雄主义更令人震撼和感佩。应当说,这部小说及其改编的电视剧之所以受到读者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不仅因为好看,更有其中寓含的精神品格及其审美意蕴带给我们的那份震惊和感动。当然,从长篇小说结构的整体性而言,这部作品还是有所不足的。
除上述几部获奖作品外,还有一些作品也被普遍看好,得到较高的评价。
范小青的《女同志》是一部描写当代官场生活的小说,题材贴近生活,也具有相当的敏感性,但作品的艺术处理还是比较得当的。小说描写了一群党政干部特别是女干部的官场人生,寄寓了作者对这种官场生活、官场人生的认识感叹和讽喻。官场似乎有一种巨大而无形的规则和逻辑,进入这种生活圈,人的命运及其人生轨迹都将在无形中被支配。在这种生活形态中,有的人如作品中写到的聂小妹等,能无师自通特别适应;而像小说主人公万丽这样原本比较单纯善良心软的女性,初入官场便感到很不适应一片茫然,后来在同学加情人的康季平的鼓励和引导下逐步适应,但她原有的那种温柔真诚的本性却逐渐失去了。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类人物的生活状态,并且通过描写万丽在官场生活中的被动适应转为主动追逐,她内心的矛盾困惑、犹疑彷徨等等,也隐含了作者对官场逻辑与生活逻辑、为官之道与为人之德、身在官场身不由己与独善其身人格独立等等矛盾关系的思考,非常富有启示意义。也许作者是为了写出万丽单纯真诚的本性,便安排了一个通晓官场逻辑和秘密信息、深谙为官之道的康季平作为她的“启蒙导师”,然而作为一个普通大学教师的康季平何以具这样大的能量,他与万丽的恩恩怨怨何以是这样一种发展走向,却显得有些不合逻辑和缺乏现实依据。
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分上、下部,总计近九十万字,体量巨大场景宏阔,也可谓一部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小说叙写了大别山区天门口镇从20世纪初到“文革”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演变,整个儿差不多就是一部暴力斗争的历史,其中交织着各种矛盾与仇恨,包括家族的、阶级的、民族的、政党及其各种派系的,还有各种人物之间复杂的爱恨情仇,所有这些矛盾斗争交织在一起,便在天门口镇半个多世纪里不断上演恩怨仇杀的活剧。而这一切恩怨仇杀几乎都根源于各种欲望,如权势、地位、财富、情爱、肉欲等等,有时为了一个女人,或为了一件雪狐皮大衣,便可以导致无休止的占有与争斗,有些还是在公平、正义、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然而暴力带来的还是暴力,仇恨引发的还是仇恨,冤冤相报,没有终极。于是就引出小说中人物雪柠提出的问题:谁是最先被历史所杀的?谁最后被历史所杀?穿插整部小说情节的说书讲史,讲述了盘古开天地以来的一部中国历史,也就是在暴力杀戮中朝代更迭的历史。而在天门口镇上演的这场暴力仇杀,既是在中国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又是这部中国历史的现实延续与注释。由此而引人深思的是,怎样才能走出这种历史的悖论性循环怪圈?怎样才能化解乃至避免这样的暴力仇杀?小说设置了梅外婆及其所教育成长的雪柠等人物来昭示这样一种价值理念:冤仇无边,唯仁爱、理解、宽容是岸,爱是人一生中最不容易做的一件事;仇恨别人,在世上没有好日子过;要让人成为人的福音。小说以公平、正义、仁爱、宽容、悲悯等作为价值内核,应当说是积极和富有启示意义的。只不过,从整体上看,这种价值理念在小说情节中的贯注与昭示,还是显得薄弱了一些。
杨黎光的《园青坊老宅》以我国改革开放后城市改革发展为背景,叙写了一幢老宅里发生的充满神秘悬念的故事。在这幢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徽式老宅里,如麻雀窝般住着十多户人家几十口人,各自过着甜酸苦涩滋味各不相同的日常生活。当传言老宅将要在城市改造中被拆迁时,突然闹起了“狐仙”,家家户户各色人等既充满期待又惶恐不安,老宅里上演了“七十二家房客”般的悲喜剧。小说以比较严肃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将全景式的当下生活描写与历史文化的纵深探掘相交织,从表层结构看,展现了老宅里一群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生活样态、人情世态、人生百态,构成一幅全景式的生活图画;而从深层结构来看,循着老宅及各户人家的真实而琐碎的生活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则可透视数百年的历史变迁,几代人的命运沉浮,各色人等性格、心理形成的历史渊源。作品写出了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底蕴深厚;同时也写出了众多普通人的人情世态,包括人性的弱点和隐秘灰暗的一面,更有人性的善良淳朴、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彼此宽容理解等等,审美意蕴丰厚,题旨深邃。作者的本意也许不在于写改革开放的宏大主题,但通过叙写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细浪潜流,同样能折射出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其审美价值取向是比较积极与凸显亮色的。小说构思巧妙,以“狐仙”悬念引导情节发展和串联人物故事,增强了作品结构的整体性,也强化了小说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杨志军的《藏獒》也是一部广受读者欢迎和好评的作品。它以西藏解放初期汉族干部入藏开展民族工作为背景,展开了各种矛盾关系的描写,其中包括不同藏族部落之间的恩怨仇杀,藏人与汉人之间的历史积怨与现实隔膜,藏传佛教内部矛盾及其与藏族部落间的复杂关系,依附于不同人群而形成的藏獒群体的内部冲突及其相互较量,还有藏獒与草原狼群你死我活的惨烈厮杀,等等。各种矛盾冲突复杂交织,场景壮阔,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一些藏獒搏杀场面写得惊心动魄生动传神,非常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在上述复杂交织的矛盾冲突中,小说突出了藏獒活动的主线,精心塑造藏獒艺术形象。作者有意将藏獒有声有色的活动放到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与人群间的矛盾冲突交织起来叙写,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是使这个以动物为主体的故事获得更为广阔深厚的社会历史内涵;二是凸显思想主题,深化对人性的思考感悟。藏獒的天性是忠诚勇敢,为了主人的安全,它对狼群等野兽的攻击厮杀毫不犹豫,面临再大的危险也无所畏惧在所不惜;可是当它们介入人群间的矛盾冲突,却常常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按其天性它只能对主人忠诚服从,以主人的意志为意志,以主人的是非善恶为是非善恶,无条件执行主人的指令;然而藏獒的特异之处又在于,它以一种几乎是天然的智慧与直觉判断来分辨好人与坏人、善意与恶意,从而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当它实在搞不懂人群之间那些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和反复无常的矛盾纠葛时,它便只能以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以自己的本能心智来理解判断,而正是这种几乎是本能直觉的判断选择,恰恰是去芜存真,切近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本真意义。藏獒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纯真与忠诚、善解人意、嫉恶向善等品性,恰恰是最切近“人性”的东西;而人类那些为权势野心和掠夺占有为目的的纷争搏杀,反倒是一种近乎“狼性”的东西。作品中极写“父亲”与藏獒的生死之缘,也许正昭示着这种摒弃“狼性”而回归“人性”审美价值取向,畅快淋漓的阅读体验与心灵震撼之后,却也引人深思。
此外,还有范稳《水乳大地》、红柯《乌尔禾》、王刚《英格力士》、肖克凡《机器》等作品也都各有其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值得一读。
赖大仁,男,1954年生,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曾任第三、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著有《文学批评形态论》、《当代文学及其文论:何往与何为》、《当代文艺学论稿》、《魂归何处——贾平凹论》等。
组稿编辑姚雪雪
实习编辑 韩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