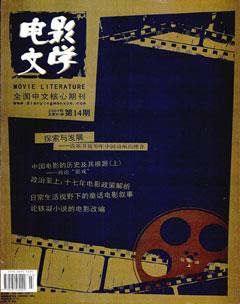中国电影的历史及其根源(上)
钟大丰
十年前,我曾以《论“影戏”》为题谈过自己对中国初期电影的电影观念及其银幕体现的看法。其实。我以为不仅初期中国电影是如此。几十年来在中国电影中占主流地位的电影主张大都是与其一脉相承的。几年来,不少人对以“影戏”来归纳中国电影的一些历史现象的看法提出了批评。虽然多数批评并未直接针对我的几篇有关文章,但我以为,围绕“影戏”的观点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澄清的。本文想以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对电影艺术风格的影响为重点,对“影戏”再做一些阐述。为了表述的相对完整,本文中不得不提到我以前几篇关于“影戏”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这难免使文中一些段落有老调重弹之感,望读者见谅。
皮影戏不能产生电影,电影诞生于新媒体、新文化
“电影是什么?”这是一个与电影本身一样久远的古老问题。近百年来,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它实际上一直萦绕在每一个醉心于电影的人的脑际。这是获得电影观众的基础,更是人们从事一切电影创作和批评活动的基础。我试图从“影戏”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电影的历史,就是企图从中国电影历史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观和电影观入手,寻找左右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较深层次的根源。
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仅仅着眼于电影本身,事实上是很难真正认识它的。近百年来,人们之所以对“电影是什么?”这一命题纠缠不清,正是因为电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对象。它是传播媒介和交流方式,是艺术,是意识形态,也是商业文化。由于人们的文化背景和生存环境的不同。电影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会有所不同,人们对电影的认识、把握的方式、角度和结果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人们的电影观正是由此建立和因此而修正。同时,由此建立起的电影观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着电影在生活中的位置和人们的生活环境。电影的发展正是从这种观念与环境相互造就的过程中派生出了绚丽多彩的历史图景。
电影诞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这不仅由于它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近代科技基础上的技术发明,而且还在于它的存在深刻地依赖于发达的商业文化市场。虽然电影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于中国早在近千年前便有的皮影戏就已经具备了电影技术原理的雏形,然而电影终于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因为在旧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电影得以产生的机制。
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摄影家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第一次售票放映电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多数电影史学者都把这一天看做电影发明阶段的结束,看做是电影时代到来的标志。这一次划时代的电影放映,不仅标志着一种新媒介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商业文化的奠基。在这之前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记录和再现活动的影像。从技术上讲,卢米埃尔兄弟做的实际上只是在众多科学家长期的技术探索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他们把以前只能在“电影视镜”的窥视孔中一个人独自观看的影像投射到了银幕上,供许多人同时观看。然而,这一改变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新的观看方法创造出一种新的传播和交流方式,也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电影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技术媒介,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便构成了—个难以截然分开的整体。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发展道路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历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影戏”的观点的提出也是企图从这种联系出发去认识中国电影的艺术特征。
人们说电影是20世纪的艺术。这不仅因为电影是在这个世纪中崛起的一种艺术样式,还由于它是那样巨大地影响着这个世纪中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在中国也是如此。电影虽然不是出自中国人的发明,但它一旦在中国扎下根来,便很快与中国文化与社会融为一体。它在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中汲取营养,根据中国社会和时代的现实需要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电影在20世纪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是中国人学习和消化这一外来的新媒介,创造一门富于中国特色的新艺术的历史,也是这一新媒介造就中国现代历史的过程。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影戏”成为中国电影历史不衰的传统
周恩来早年在一篇关于戏剧的文章中曾这样表述他的艺术观。他说:
故世界者,实振兴无限兴趣之大剧场,而衣冠优孟,袍笏登场,又为世界舞台中一小剧场耳。但推微及广,剧场中之成败若斯,世界之优劣亦判。言语通常,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事既不外大道,副以背景而情益肖:词多出乎雅俗,辅以音韵而调益幽。以此而感昏聩,昏聩明;化愚顽,愚顽格。社会事业经愚众阻挠而不克行者,假之于是:政令之发而不遵者,晓之以是道。行之一夕,期之永久:纵之影响后世,横之感化令人。夫而后民智开,民德进,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列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
这段话很典型地反映了许多中国艺术家对艺术,特别是对像电影这种大众艺术的看法和期望。它使人想到在中国的旧式舞台上常常持着一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的对联。人们不仅希望这块“小天地”能反映大世界,而且希望它能通过影响和教育观众而达到改造大世界的目的。由此也在艺术方面提出了主题严肃、题材可信、环境真实、情节清晰动人、艺术语言通俗易懂、境界蕴涵幽远、雅俗共赏等一系列追求。同时人们也看到,只有“副以背景”“辅以音韵”,即佐之以艺术创造,才能真正有效地达到艺术的社会功能效果。中国电影近一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正是一代一代艺术家们在复杂的时代变革中努力实现这一追求的历史过程。这种追求的结果就形成了“影戏”这一历史不衰的电影思维和艺术风格的传统。
“影戏”本来是指中国古代的皮影戏,后来被人们借用来称呼电影。虽然这个名字渐渐被“电影”所取代,然而作为一个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却并没有很快地消亡。作为一个电影的美学和历史现象,“影戏”具有丰富的内涵。
“影戏”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创作风格,而首先应被看做是一种看待和把握电影的思想方法。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影戏”是由双层结构的框架构成。它的核心是一种从功能目的论出发的电影叙事本体论,在外层则是一个带有浓厚戏剧化色彩的技巧体系。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影戏”随着电影的发展不断丰富着自己的表现手段,其外在形式不断地发展变化着,逐渐形成一套以叙事蒙太奇为主要特征的时空体系。但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它的结构则相对稳定地保存了下来,表现出了极为旺盛的生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影戏”决不仅仅是从候曜的《影戏剧本作法》一本书中总结出来,也不必认为候曜的书就是中国传统电影理论的标尺或典范。它不过是第一只被解剖的麻雀而已。而且“影戏”对主流电影倾向的一种归纳,无疑不能完全涵盖中国所有的电影现象。但是它
作为电影观念对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和体现的范围之广,又是其他电影主张和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影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和如此深广地影响中国电影,也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的。
功能目的成为中国电影的强心剂,决定了它必然的艺术道路
有人说电影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电影的语言是世界性的。这话并不错。但由此得出民族电影就不会有其独特的电影思维和表现方式,而只能是体现在其所表达的民族生活的内容方面的结论似乎就显得有些片面了。电影没有诞生于中国。却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电影的整个生存环境都在对中国电影的面貌产生着影响。它不仅影响着中国电影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同样影响着中国影人对电影的认识,影响着中国电影的艺术道路的选择。
电影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种独特的记录和传播媒介。这使得电影比起其他艺术来,更容易与社会生活建立起联系来。当电影传人中国,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之后,很快就与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着20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从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中,透视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变革的面貌,也折射出中国人民在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心态的影子。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由其栖息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着,其发展道路也被打上了社会和时代的深刻烙印。这烙印不仅仅表现在我们以往所注意到的它能反映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方式。成为历史的窗口和文化的镜子的一面,更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影人的电影艺术思维方法和中国电影的艺术风格。人们为什么拍电影,给什么人看。期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一切又怎能不影响人们的艺术方法和艺术言语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影戏”的认识也需要从中国电影发展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人们对电影所具备的功能的期望开始。
电影来到世间时,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转化,带着极大的野心和欲望贪婪地向全世界扩张的时期,电影也随着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侵略的足迹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包括刚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的中国。而电影诞生至今的一百年,又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转向后殖民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无论是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和意识形态载体,还是作为一种艺术样式,都处于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权威话语的笼罩之下。在第一世界权威话语的笼罩下挣扎的第三世界电影,实际上都是在无可避免地沿用权威话语,但又不甘于受其控制、并努力挣脱其控制的困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电影也不例外。
面对舶来的电影,一边认真地学习,一边顽强地抵抗,寻求中国电影的个性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出现了根本性的改观,但中国至今仍然是—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这使得中国电影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第三世界文化的色彩。经济的落后、综合国力的相对薄弱使中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难逃受到发达国家的文化倾销的命运。这也迫使国人产生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努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这造就了一种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卑感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文化心态。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电影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作为一门新的外来艺术的电影,外来的影响一直强烈地作用于中国电影。而中国电影工作者则带着一种矛盾的心理面对这种影响。他们一边认真地学习,一边又顽强地抵抗。中国的民族电影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从最初的电影放映开始,电影就成为外国人在中国赚钱的工具。然而,电影的输入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其结果却比人们开始想象的远为复杂得多。在旧中国的电影市场之中,以好莱坞电影为主的西方电影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大部分西方电影虽曾被逐出中国的电影市场,但另一个电影大国苏联却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电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电影市场又开始逐步向世界开放,西方和港台地区商业电影再一次大量涌入,近一个世纪中国电影几乎一直是在向外国电影学习和与之较量的过程中发展过来的。外国电影在中国传播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和意识形态,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激励着中国人为创造自己的民族电影而努力。在中国电影的发展中,“民族化”一直是人们关注和追求的一个重点,这当中不仅包含了艺术家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情感和信念,也渗透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地位的渴望和追求。当然这种“民族”的电影并不能直接从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产生,它不可避免地必须从对西方电影大国的艺术经验的学习和借鉴起步。我们从候曜的《影戏剧本作法》到陈鲤庭的《电影轨范》等中国早年的电影理论著作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从理论体系到论证方式各个方面的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学习并不等于照搬,他们无疑做出了自己基于民族的文化和需要的创造,加进了中国人对电影的认识和思考。事实上,根据中国社会、文化和电影市场的需要选择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并对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中国的国情,这是一代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们不懈努力的共同方向。“影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必然性的结果。人们对电影的理解不同,所做出的探索也会有所不同。可是最终又不得不服从于历史的抉择。从这里,我们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电影作为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化中的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方式,正形象地隐喻着第三世界在创造独立的民族新文化的过程中的这种文化困境。
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好莱坞作为权威的电影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统摄和制约着所有民族电影的表达。几乎所有的民族电影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我们在认识特定的民族电影对象的时候,更需要的是探讨它对好莱坞的理解方式及学习借鉴的具体角度和侧重点,特别是人们做出这一具体选择的内在动因。“影戏”的提出正是试图寻找这种内在的动因。
有的同志认为,“影戏”的主张并非什么独创,其实不过是一些早期影人对好莱坞的模仿而已。如果说关于“影戏”的观点仅仅是从候曜的《影戏剧本作法》一书中得到的,这种批评似乎还有些道理,但事实并不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的旁证,可以得知候曜所写的不过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普遍性的认识而已。说实话,相比之下候曜还是比较注重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的。虽然,在候曜的论述中的确有许多东西是直接抄自西方的戏剧理论和早期好莱坞的技巧经验的,但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他为何选择了这些。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候曜所处的时候(《影戏剧本作法》出版于1926年)好莱坞还处于默片时期,影片的情节性和戏剧性虽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进入有声之后的鼎盛时
期还无法同日而语。而在这时,好莱坞的戏剧式电影的技巧理论也刚处于萌芽阶段,其成熟更是迟至30年代中期的事。其实,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远非如我们30年前闭目塞听,不仅好莱坞电影为人们所知,印象派、立体派等先锋派电影主张、德国的表现主义和室内剧电影,以及爱森斯坦甚至维尔托夫都曾有所介绍。人们对好莱坞那一套感兴趣,正是因为它适合于他们对电影的理解。即便对于好莱坞,中国人也并非全盘接受。例如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等公认的代表作在初期中国影人看来便不如其后期作品成功,其原因正在于其对戏剧式叙事的超越。在这种选择的基础上,人们也不甘于简单地抄袭好莱坞,而是努力从自己对电影的认识出发探索电影创作的规律。与笔者在国外所见过的几种30年代初及此前的好莱坞早期技巧理论著作(包括候曜书后所列的参考书《How To Write for“Movies”》等)相比,候曜的书虽然篇幅不大,论述中却也不乏西方人所未及的独到之处。在这些不同之处中,最明显的大概可以说是企图超出技巧论而涉及电影的文化表现功能的部分了。这当中表现了中国人对电影的伦理道德意义的理解和认识,这也表现了人们期望通过戏剧性矛盾冲突来再现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的愿望。而正是这些部分最典型地反映了初期中国影人对电影的那种从功能到结构、从叙事到造型的认识方法。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电影的初期可以看到,此后30年代对苏联电影经验舍爱森斯坦取普多夫金的有选择介绍,“电影文学”概念的引入和与此相联系的经久不衰的关于戏剧性与文学性、诗电影与散文电影等等的争论。它们似乎都不应被看做对介绍对象的无知,而更应理解为选择性吸收和理解的结果。而做出选择的标准恰恰是与其是否能吻合于以戏剧性情节叙事为核心表达手段的电影观。
驱逐好莱坞,期待辉煌的民族新电影之降生
中国影人对待好莱坞电影的态度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一种面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权威话语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矛盾的文化心态。老一代中国电影艺术家,或者如孙瑜、张俊祥等直接接受过美国教育,或者如夏衍、袁牧之等曾整日坐在电影院中反复观摩学习,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好莱坞电影开始其电影启蒙的。但是在旧中国,那些“把这近代的色情文化和近代人的性的潜力,兑换为经济价值而博得巨利的”好莱坞商业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大肆泛滥,充分暴露了好莱坞电影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这又使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的艺术家都无法完全接受它。新中国建立之初将好莱坞电影逐出中国电影市场时,艺术家们曾由衷地为之欢欣鼓舞,期待着一个辉煌的民族新电影的诞生,然而新电影并不能从天而降,它只能从现有的电影观和电影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特有的政治环境下,人们不能再用好莱坞式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电影观,便转而求助于普多夫金和李渔。可是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的艺术样板仍是《吾土吾民》《魂断蓝桥》一类的好莱坞情节剧。但与此同时,人们出于一种抑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民族主义潜意识,对好莱坞电影经验的学习事实上也不可能全盘接受,而是以中国民族的通俗艺术经验为基础做出取舍的。
电影是一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结合物,它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拍电影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和资金等诸多方面的条件,需要一整套工业和经济体系作为基础和后盾,这一点是与某些物质生产部门比较接近,而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因此,电影不像绘画、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那样可以较少受到经济和物质条件的制约,创作者有更大的主动性。同时,由于影片的摄制需投入较大的资本,就需要尽快收回。这样也使电影的商业性比其他艺术门类表现得更加明显。电影传人中国的最初几十年,正值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日益加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不安。旧中国电影生产和创作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投机性,都使得中国电影无法具备强有力的经济技术基础。这使得中国电影难以致力于视觉奇观的营造,而只好更多地求助于叙事的戏剧性。这是“影戏”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动因。这样,“影戏”从中国民间传统的说唱艺术和戏曲曲艺等通俗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形成了一套相当有效的电影叙事经验。这些成了中国电影思想和艺术表达的基本手段,也造就了中国电影的基本艺术风貌。它不像好莱坞那样强调电影是用画画所讲的故事,而是在银幕画框里讲的故事。
另一方面,电影作为一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结合物,作为一种娱乐工业,使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独特的位嚣,从而也使它具备一种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特征。艺术本来是离社会经济基础比较远的意识形态方式,但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使电影的发展与社会和经济的条件及这些条件的变化有了比较紧密的联系。电影在艺术上的发展也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或群众的要求,如大危机后好莱坞影片的泛滥和战后新现实主义的兴起等都是如此。这在中国电影中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近现代的中国几乎一直处于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烈社会动荡之中,作为一种观众面极为广泛的艺术传播媒介,电影当然无法回避这一社会的现实,这使得中国电影与其所处的时代生活和社会历史条件之间表现出了特别直接和紧密的联系,这一点与许多外国电影相比显得尤为突出。社会历史的变革直接影响着中国电影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变革。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中国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中国电影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都是由历史的变革所催生的。反过来,电影作为一种广泛而具有影响力的艺术传播媒介又反作用于社会,不断参与着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进程的改写。这样,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中,几乎没有给纯粹的艺术实验留下任何位置,政治运动和艺术运动总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对此,我们以往常常首先看到的只是其作为政治运动的存在。事实上,从事特定的表现目的的创作,总是伴随着相应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方法的。如果说“影戏”在旧中国赢得主流地位还可以说是得益于初期电影创作队伍的文化背景及电影市场的一再空前未有的话,它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革命抒情正剧”和“文革”电影中以新的形式复活,则更明显地反映出对电影的政治功能要求在多大的程度上规定着艺术风格和艺术语言的运用。
政治、经济、艺术间的冲突,在于教化至上和政治读解
电影是艺术创作又是商品生产,是以物质形态体现的精神产品,它是商品、是艺术、又是意识形态。它具有多重的特性,不仅受社会历史和艺术规律的支配,又受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支配。这种多重作用和多重价值经常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中常常通过艺术家与制片人的矛盾表现出来,而在1949年以后的内地电影中则往往更明显地体现为政治、经济和艺术的不同目标间的冲突。而所有
这些冲突实际上都是艺术家对新的艺术观和电影观的探索与社会对电影的直接需要之间的矛盾的不同的体现方式。尽管艺术家们做出了勇敢的尝试,但较量的最终结果往往得要服从于市场、观众或政治目的的需要。“影戏”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较量过程中取得和巩固着其在中国电影中的主流地位的。所以,尽管我们的主要着眼点是在中国电影的艺术发展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电影的社会地位的这种复杂性,特别是中国电影作为一种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要准确地把握中国电影的艺术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电影是一种带有强烈商业倾向的文化工业,然而它又不是纯粹的商业。大多数中国的电影艺术家都不满于仅仅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而祈望能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观念不尽相同,有的也不尽正确,但他们在力图通过电影作品影响着人民对生活的认识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文以载道”的悠久传统,“文以载道”的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决定着万物从功能目的出发把握作品和创作的方法,它相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艺术家们的创作。艺术家们总是努力把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倾注到作品之中,希望能够以此影响和教育观众。中国早期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在他早年从事戏剧活动的时候曾讲过一段话很能代表中国人艺术观。他说:“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电影传人中国之后,面对着这个观众面极广的新媒介,人们更期望它能成为一种新的教化手段。从中国人自己开始拍摄电影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电影的这种社会教化的功能。
在中国电影的初创阶段,象郑正秋等早期影人的影片所表达的社会思想比起“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虽然逊色不少,但其创作态度却仍不失严肃。进入30年代之后,当电影与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时,中国电影那种强烈的社会意识便更突出地显示了出来。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们把摄影机对准充满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社会现实,用电影向人民呐喊,向敌人斗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强调了革命文艺作为“宣传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作用。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电影创作更是在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目标服务的。这一切都使中国电影的整个历史进程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间建立起了特别直接的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领域都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核心话题直接相关。
把电影看做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这不仅是艺术家的自身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艺术家们提}j{的要求。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国营电影体制的建立和全国性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络的形成,电影成了最广泛而有影响的传播手段。电影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地位和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还没有人直接否认电影是一门艺术,但实际上也没有人能把电影仅仅看做一门艺术了。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无法把电影首先看做是一门艺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电影艺术家,不管他的态度是由衷的认同,还是困惑的观望,抑或某种不满的宣泄,事实上都难以逃避其与时代的政治要求间的对话。与此同时,许多电影艺术家和影片的命运,也往往取决于其所处的时代对他们的政治解读方式。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把中国电影的社会政治内容与其艺术道路的取向截然分开。对电影在社会与文化之中的位置和意义的理解,很自然地也会影响到人们对电影的艺术风格和情趣的追求。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中,对艺术风格和情趣的追求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艺术问题,它总是与时代对于电影的宣传教育要求息息相关,也与艺术家对于自己的社会使命的理解密不可分。因此,电影在中国,从来就不是某个艺术家个性宣泄的工具。它如果不是某个特定时代或群体的意志的有目的的表达的话,至少也是他们的集体潜意识的流露。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武侠神怪片浪潮,30年代的软性电影之争,40年代对《小城之春》等影片的批评,50年代“革命抒情正剧”的创作高潮,“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戏”电影,70年代末电影新潮的兴起,80年代“第五代”电影的出现,直到商业大潮涌起后的都市喜剧等等,中国电影历史上许多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背后,实际上都是这种对电影的社会功能的理解在起着作用。所以,我们只有充分认识“社会教育”的艺术观对于中国电影艺术家的深刻影响。才有可能正确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规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