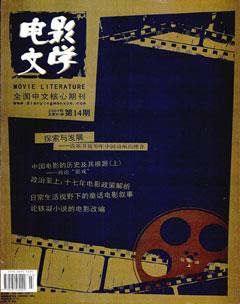日常生活视野下的童话电影叙事
俞春放
[摘要]在审美世俗化的今天,童话电影的诗性是否还存在,或者说童话电影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本文所要去面对的问题。从传统意义上讲,童话作为一种成长经验,是人生原始的理想冲动。指向于当下的形而上意义;而在当今的日常生活中,经典正在消解,价值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童话的意义呢——在一个不相信真情的年代,你如何去让自己相信也让别人相信真情?或者说童话发展的新格局在哪里?我们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童话作品,在对其诗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童话电影在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的乌托邦意义。
[关键词]
童话电影:诗性:乌托邦
一
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越来越在电影中寻找视听的震撼,从对DVD版本的苛刻要求到对具体一部影片光影音响的过分挑剔,无不说明着这个问题,全数字在现在往往成为一部动画片的一个刺激性的卖点。然而,在陶醉于技术带给我们的感官享受时,我们始终无法忘怀的是技术的另一重功能:诗性的叙事功能,而并非这个大众叙事时代的技术炫耀。
但问题是诗性在这个时代是否可能,它是否已成为我们一个遥远的历史梦幻?而执著于历史记忆的人是十分可笑的。另外,如果诗性仍有可能,那又怎样贯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才重新去观照那些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经典童话电影,而同时又到当下的动画影视中寻找经典的新发展,或者说在这个精英与大众、经典与通俗间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去发现诗性健康成长的轨迹。
不可否认,当前童话电影所面临的现实并没有像我们记忆的那样好。一方面当然是电影行业所面临的困境,这不在我们这篇文章论述的范围之内,暂且放一边不论。另一方面却是在接受上面的问题。我们总是会怀疑在现在这个时代坐到影院去津津有味地看这类电影是否显得过于天真烂漫。但这种怀疑本身却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余地。电影的意义何在?如果说因为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我们再也没法在这类电影当中找到生活的影子,那是否就意味着除寻找一时的快感之外,我们在电影当中只是去寻找跟我们生活一致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的标准。那么童话电影简直是如痴人说梦。王子和公主的故事中人们早就极为世故地看到了他们婚后的尖酸刻薄与庸俗不堪,公主和王子间那一吻的救赎在当代人的观念中根本就无法有太多的担当。但如果我们就是要在电影中看到尖酸刻薄与庸俗不堪,看到一地鸡毛的碎片,那电影还有什么意义?生活永远比电影更加丰富多彩,如果想要看到生活本来的样子,那么生活本身肯定比电影更值得看。而且既然已经成为电影,那肯定是从某个人的具体视点出发的,是他眼中的世界。所以想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生活原样,实际上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的是别样的世界,这就是一个“诗”的世界。所谓“诗”,实际上也即是“艺术”的一种雅称,这是一种以生命之“思”为核心的实体。反过来,作为电影这样一种实体,它所承担的,其实也就是这种生命之“思”。以日常生活为其外在的表现形态,而本质在于与世界的对话,对生命的言说。因此正像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中所提到的那样:“所谓真正的艺术都厌恶现实主义。”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关于“真”的把握的要点,在于“可能性”与“现实性”的不同。艺术中“真实”这一概念具有一种暧昧性和复调结构,艺术是实际的生活世界的符号化。童话电影中生活形态的纯粹性并不足以成为我们否认它在当下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因为它正是通过其纯粹性,来表达其生命之“思”。童话世界是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的另外一个世界,它具有不真实性。不真实性不在于其逃避生活,恰恰相反,正因为其对生活世界符号化的特点。才具有了直面世界时的深刻性。加缪说:“小说世界只是按照人的深刻愿望对现实世界进行的修改。”秘鲁作家略萨也说:“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同样是叙事艺术,如果我们把其中的“小说”置换成童话电影,其实也一样成立。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说,在童话电影中,诗性是可能的。诚然,日常生活日益碎片化、零散化,没有一个足以统领全体的价值标准,但这恰恰为诗性的追求提供了充实的依据。人要成其为人,总是因为有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有对于理想的向往,这种“不满”与“向往”,即成其为生命之思。
既然是一种生命之思,我们说,童话影视中。追求的乃是一种艺术之真,是一种内在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具有元叙事的味道,它可能看上去质朴简洁,但是它的行为和功能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范式。
在《灰姑娘》的故事中,仙杜丽娜的父亲自从娶了坏心的继母不久后便去世了,仙杜丽娜的命运也随着这噩运而改变了。直到皇宫送来了舞会的请帖,仙杜丽娜的命运才出现了转机。因为有了仙女的帮忙,她踏出了幸福的第一步。然而仅仅一只水晶鞋……她真的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吗?而梦想真的会成真吗?这个作品其实符合了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几种行为者根据各自所承担的功能的不同。构成了一个相互纠缠的复杂的叙事行为。仙杜丽娜对于幸福的追求形成基本的情节线索,她作为行动的主体者有一个明确的欲望对象,那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在故事结局看到的: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每个灰姑娘都只是暂落凡间的天使。这个在情节核心中是至关重要的欲望对象,与其说是受到仙杜丽娜具体生活中某一条件的触发。倒不如说是人的一种天性,一种来自内心的向往。主体行为的发出与作为对象的结果之间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于是就有仙女的帮助、王子的爱情以及父亲的去世、继母和姐姐的虐待这些辅助或者妨碍力量。辅助与妨碍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构成了基本的叙事情节。这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符码化,通过这种形式化了的生活展示,揭示了生活的基本内核。这是很多人都会去喜欢的童话故事,永远也忘不了,因为这个故事,他们的童年充满了梦幻,对世界热爱、好奇;在他们成年后,这个故事也永远是心灵中一抹不可掩藏的净土。但这个故事本身的意义倒不是在于王子与公主最终的相遇,如果那样,那就真是一出廉价的言情剧了。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明确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完美,人与人之间总是有那么多的隔膜,生活中会有坏人,好人也会受到暂时的委屈。灰姑娘也是受尽了继母和姐姐的虐待后,才有了美好的生活。因此对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生活都是美好的。活着。就是一个永远的童话。灰姑娘的生存状态,与其说是一次偶然性的自我满足,倒不如说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本质,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
因此,可以说,童话虽然表现出的是基于幼年的一种成长经验,但那种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其内核却是人生原始的理想冲动。指向于当下生存中的形而上意义。在《睡美人》中,美丽的公主不幸中了邪恶的诅咒,让她的手指被纺纱的轴车刺伤,变成了睡美人。勇敢的菲力普王子在三位仙子的协助下,面对重重困难,挑战邪恶力量,终于救醒了公主。而在《白雪公主》中,不幸吃下
毒苹果的白雪公主,先是得到七个小矮人的真诚帮助,使得陷害她的王后仓皇逃跑,在狂风暴雨中跌下山崖摔死:最后也是骑着白马赶来的王子,以爱情之吻使白雪公主死而复生。在第一层接受意义上这当然可以看做是一个爱情故事,爱情的力量可以解除所有邪恶的诅咒,对于爱情的向往本来就是人类基本的向往之一。正像白雪公主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神奇的许愿,我希望我所爱的人在今天出现。”“纯洁爱情会一生到老,永远快乐而幸福美好。”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想象,符合我们对于爱的向往。活着的意义有时候正在于我们是有想象的。如果没有对于未来的想象,庸常的生活中生命便会如中了邪恶的诅咒一样枯萎凋零。然而正如前面曾提到的那样。故事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符码化,它既有故事层面的意义,同时也有故事背后的意义。这些电影既是爱情的,同时又是爱情之外的。它们既承认了日常世界的欠缺,又显示了对这种欠缺的拯救。作为表现人类共同生命理想的最佳舞台的艺术,在上帝构造完毕的事实世界的基础上,依据人类自身的愿望;构建起了一个自由美好的可能世界。
无所不在的欠缺造成了人们内心的流浪感,他们需要去寻找一个心灵的栖息地,以对抗内心时刻存在的紧张状态。寻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救赎,表面看起来是一种外来力量的援助,但根本来讲却是一种自我的完善,是自我在历练中的成长。作为电影史上第一部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动画电影,并拿下“最佳主题曲”及“最佳原著音乐”两项大奖的《美女与野兽》也跟一般的童话电影一样,开始于一个魔法的诅咒,让自私又坏脾气的王子从此变成一头野兽!为解开咒语,野兽必须在被施魔法的玫瑰最后一片花瓣掉落前,设法以自己的爱心去赢得真正的爱情。这其实同样是一个以爱情之吻解除诅咒的故事模式,但它以更明确的方式告诉我们,在现实的欠缺中。能够拯救自己的根本力量其实在于自身。要得到救赎必须自己控制好,只有有了爱心,野兽才能重新变成王子。作为故事另一主体的“美女”——贝儿更具有典型意义。一方面,她是一个拯救者,在她走进被施魔法的城堡的第一时间起,他们就认识到她是能解开诅咒的那个女孩;另一方面,她也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对象,需要有非凡的爱情来使她走出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她显然不适合于她生活着的那个小镇,“人们的生活不该就这样”,“总觉得这里不适合我,没有人能和我对得上话”。她生活在想象中,在心灵的流浪中寻找自己合适的栖居地:“有些人看书是全靠想象的。”人总是处在找寻之中,只有拯救别人的同时才能拯救自己。拯救与被拯救。无非都是自己在这个日常生活状态中的一种自我完善。《风中奇缘》也表达着同样的意味,虽然不再是经典意义上的王子与公主。也没有在表面形式上的诅咒。当人们走上流浪之途时,也只有在拯救与被拯救的双向作用中,才能走向自我的完善。一个找着理想的青年碰上了一个不一样的忧郁少女,风把她的手送到了他手中。只是在这部电影中更加明确了一点:在找寻的过程中,你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时刻听从心灵的呼唤。朝着风的方向奔,用心聆听声音,风中的声音。周围有精灵存在,让声音指引人生的真谛。
正如儿童文学作品不单是给孩子看的一样。这些影片所展示的也不仅仅是孩子的世界。或者说它们给孩子展示的是成长中的启示,使孩子在成长中既懂得直面现实,又不失对于理想的坚持。对于成人来说,是不为世俗的平庸打磨,内心深处仍留着一方净土。我们当然相信这样的作品对于人性的关照,它们有的展示着成长之途如《狮子王》;有的告诉我们爱的纯朴和高贵如《海的女儿》;还有的是面对既定命运时的生存状态,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贫穷的命运和死亡的结局,都不能阻止她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希望的火柴。当然时代的审美风尚是在不断变换中的,趣味无可争辩,无所谓孰优孰劣。而且除了对人性的烛照这样形而上的关注之外,我们也会去关心俗世的生存状态。这类作品没有像上述作品一样有着明确的意义所指,它们的意义在于本文之中,在能指的游戏中呈现世俗的快乐。这却未尝不是对于人的一种真切关怀。比如《怪物史瑞克》。史瑞克是一个奇丑无比的绿色怪物,在旁人的眼睛中,他凶狠残暴,生性孤僻。独自一人在沼泽地里过着离群索居、安闲自得的生活。有一天,史瑞克的沼泽地里突然涌进大批的童话人物:七个小矮人、三只小猪、皮诺曹……史瑞克只有帮助法克大人救出公主,才可以要回沼泽地,回复往日的平静生活。于是史瑞克和他的惟一朋友——头喋喋不休的驴子长途跋涉,来到古堡,他们打败喷火龙,救出了公主。按照经典童话的原型,公主费欧娜坚信降临的将是英俊的王子,并且会给她以真爱的初吻。但眼前的怪物却令她失望不已。对经典的消解从一开始就初露端倪,习惯于经典阅读的人在这里却发现。猜得中开头,就是猜不中结尾。当真爱的初吻解除魔咒,公主恢复真实面目,恰恰不是期待中的美丽的一面。从表面上来看,这仍然是一个传统的童话故事。一个英雄,一个美丽的公主,还有一个可恶到极点的坏蛋。然而它与经典的童话也有不一样之处。英雄是一个丑陋的、脾气糟糕的怪物,公主也和以往的不同。结局也出乎人们的理想状态之外。这种更为日常的状态实际上是在讲述认同自己的故事。显示出植根于世俗的爱和幽默。显而易觅,这部电影形式意义大于故事内容,或者说电影所表达的内容是由文本结构传达出来的。它那世俗的爱和幽默通过拼贴人们所喜欢的经典童话而成,比如《皮诺曹》《小红帽》等等。可以说影片中幽默处处可见,是否能够发现它们就看你对童话故事知道得多少。影片只是将生活中的一些趣事集中在一起。用合适的演员,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演出了这个有趣的故事。
消解与拼贴并不是对经典的玷污,这仅仅是个时代的审美文化心态问题。如果说经典所关注的是一个彼岸世界的问题,那么类似《怪物史瑞克》这样的作品关注的是一个此岸世界的问题。王子虽然并不英俊。公主也并不美丽,但他们的爱情同样令人感动,他们日常的幸福让人备感温暖。影片对经典的戏谑,一方面剥掉了经典在形成体制化的审美之后的坚硬外壳,另一方面却也使人重温经典所带给人的温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重温时的那种会心一笑,那么日常生活叙事便充满了真正的平庸与琐碎。而叙事意义的缺失也在所难免了。如果说对彼岸世界的瞭望代表着坚强,那么对此岸世界的认同则是柔软所在。经典与大众叙事的和解使此岸与彼岸不再是两元对立的世界,而是处在彼此渗透之中,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不足以形成对人性的诗性关照。
三
因此在大众日常叙事成为主流的今天,此岸和彼岸共同守望的仍然是乌托邦。我们没有理由不信这个乌托邦世界对于人性的意义。蒂利然在《政治期望》中说:“为什么乌托邦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有的那种东西。”“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认同自己,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快乐,这该是童话电影的一种新发展。经典已经成为永恒,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不可重复性。而价值多元化和审美世俗化的当今时代,也不是经典的一元话语所能涵盖的。因此无论从创作还是接受的角度去讲。我们都应该对建立在日常叙事基础上的作品加以期许。在一个零散、琐碎、没有深度的时代,我们用什么去对抗日常的世俗与平庸?在一个不相信真情的年代,你如何去让自己相信也让别人相信真情?我想我还是用前面曾经讲到过的一句话来结束全文:活着,就是一个永远的童话。
注释:
①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第22页,三联书店。199i年版。
②加缪:《置身于苦难和阳光之间》,第17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③略萨:《谎言中的真实》,第7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蒂利然:《政治期望》,第2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