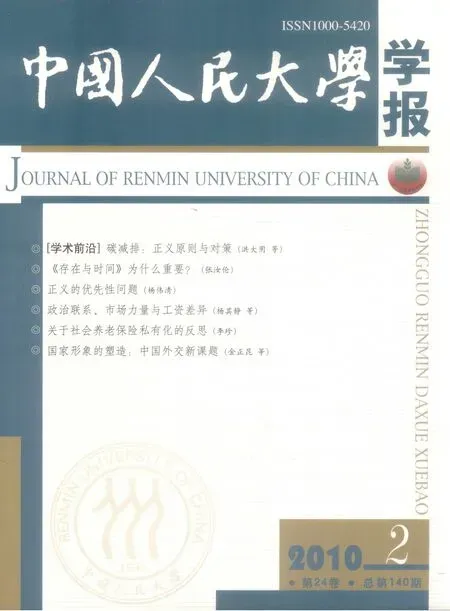正义的优先性问题
杨伟清
正义的优先性问题
杨伟清
正义的优先性指的是正义在人类价值体系或道德原则框架中的优先性地位。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论题。桑德尔不同意这一论题,并对这一论题提出了五种反驳意见。但他的批评意见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忽略了正义运作的诸多不同方式,忽略了正义在人类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
正义;优先性;罗尔斯;桑德尔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在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之于思想体系。一种理论不管多么雅致和简洁,如果不是真的,就必须被抛弃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如何高效和有序,如果不正义,就必须被改革或废除。”[1](P3)这一论断通常被称作是正义的优先性论题。正义的优先性论题指向的是正义作为一种价值或原则在价值体系或道德原则框架中的优先性地位。更具体地说,当其他价值或原则与正义发生冲突时,它们必须为正义让步,必须让正义的要求得到优先满足。
正义的优先性论题在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就批评者而言,哈佛大学政府管理系教授桑德尔可谓贡献良多。他的成名之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限度》就是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系统全面的批判。在这本著作中,桑德尔对正义的优先性论题给出了一系列反驳意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桑德尔的批评意见,并试图给出一种较为有力的回应。通过这一考察,我们希望可以有助于认识正义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正义在优良生活和优良社会建构中的作用。
一
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限度》这本著作中,桑德尔针对罗尔斯的正义优先性论题提出了以下一些批评意见:其一,正义无条件的优先性与罗尔斯关于正义环境的论述不相容,正义的环境只能支持一种有条件的优先性。其二,即便我们假定正义的优先性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层次上是成立的,这也不意味着它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共同体。在一些更为亲密和团结的合作体中,正义并不具有如此的优先性,甚至根本就无需正义规范。其三,正义的重要性程度是与正义环境的满足程度成比例的。布坎南将这一命题称作是相称性论题。[2](P877)其四,正义只是一种补救性的品德。如果有待正义补救的状况没有出现,那么,其他的品德就会占据优先性的地位。其五,正义的补救性特征使得我们无法断言正义的滋长必然意味着道德进步;如果正义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道德进步,那么,在某些情形下,正义就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恶德。[3](P30-34)
以上的这些批评意见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具体分析的时候,将会把某些论断合在一起进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桑德尔并非单纯地挑战正义的优先性,而是从根本上质疑正义的重要性和价值。
首先来看第一个批评意见,即正义的优先性是否与正义的环境相融合。正义的环境指的是使得正义美德和规范能够发挥作用的条件。①这里我们将主要遵循休谟对正义的环境的阐述。罗尔斯的阐述虽然稍微有别于休谟的阐述,但大体上是对休谟论述的概括,而且休谟的论述更为详细。这些条件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无论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都包括很多方面,但主要来说,主观条件指的是人们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客观条件则指的是外物的易转移以及它们比起人类的需要和欲望来显得稀少。[4](P534-536)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进一步修正了他的说法,将正义的条件更严格地概括为主客观方面的中等程度的匮乏。②这一修正是极为必要的,因为,他后来意识到,正义只有在一种中间的状态下才能发挥作用,无论是自然资源的极度丰富还是过分短缺,抑或是人们的极其利他或利己,都会使得正义难以发挥作用。休谟认为,只有在这些条件具备时,正义才会被想起并发挥作用。他认为,通过变换正义的主客观条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假如将大自然的馈赠和恩赐增加到足够充沛的程度,所有的人们根本无需任何勤奋和劳动,就能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就能过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式的生活,那么,在这样一种幸福的状态中,正义这一警戒性和防备性的品德就决不会被想起,相反,其他的社会性的德行如慈善和仁爱就会兴旺发达。[5](P35)同样,假如能够扩展人们的心灵,使其充满友谊和慷慨,假如人们能够像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关心同胞的利益,把他人当作另一个自我,那么,人类就将变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正义就会完全丧失其用途。
如果接受休谟关于正义的条件的论述,那么,正义看起来的确只是一种有条件的美德,无法享有无条件的优先性。桑德尔正是据此批判罗尔斯的正义的优先性主张。在他看来,如果正义的优先性要依赖于某些经验性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很难明白如何认肯其无条件的至上性。除非罗尔斯能够证明正义的条件在所有的社会中存在,而且其存在的程度足以确立正义总是优先于其他美德,否则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正义只有在特定的社会中才会具有优先性。罗尔斯不能单纯地认为我们的社会满足正义的条件,他必须为此提供相关的社会学的证明。[6](P30)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回应桑德尔的批判,一种指向桑德尔对正义优先性这一主张的理解,另一种则直接指向休谟关于正义条件的论述。
首先来看第一种方式。我们认为,桑德尔完全误解了罗尔斯有关正义优先性的主张。这一误解是建立在与康德道德理论比附的基础之上的。与康德不同,罗尔斯并不追求道德法则的绝对优先性和普遍性,也不认为道德法则甚至适用于人类之外的理性存在者。他的正义理论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社会之中,提供的是适宜于人类社会及其存在者的正义理论。正义的优先性是建立在正义环境的基础之上的,罗尔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罗尔斯的正义优先性主张能否成立,而在于正义的环境在当前社会中是否得到满足。罗尔斯的确没有对此给出经验性的证明,但我们真的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吗?人类社会的当前状况能够超脱正义环境的制约吗?我们认为,日常的经验和常识性的判断就足以确立问题的答案,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罗尔斯才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
第二种方式则是直接批评休谟对于正义条件和正义作用的理解。通过指出休谟正义观的缺陷,我们同时可以说明休谟的正义条件说的不完善。我们的目的在于阐明正义能够发挥作用的环境并不完全限于休谟所给出的正义的条件,而是也可能适用于其他一些情形。这一论述虽然无法确证正义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状况,无法确证正义的无条件的普适性,但却足以说明正义的重要性要远远超出了桑德尔的想象。③当然,这一阐述也意味着对休谟正义观念的批评。就罗尔斯接受休谟关于正义条件的论述来说,这一批评似乎也指向罗尔斯。但我们相信,如果着眼于罗尔斯的整体论述,他的著作完全可以消解这一批评。
休谟的正义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财产为中心的正义观,这可以从他所提出的三条正义法则看出来。这三条法则为稳定财物占有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以及履行许诺的法则。[7](P566)他认为,正义的主要作用在于确立人们的财产权,避免因财权不明晰所带来的纷争和混乱。“划定财产、稳定财物占有的协议,是确立人类社会的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件,而且在确定和遵守这个规则的合同成立之后,对于建立一种完善的和谐与协作来说,便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了。”[8](P532)休谟的正义观清楚地反映在他的正义条件说之中。他认为,假如外在的自然资源足够丰富,人人都富足有余,那么,划分财物和所有权就失去了意义,正义也就无用武之地。他以水和空气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同理,假如人们之间没有猜忌、没有隔阂、无分彼此,人们的心胸中流淌着无尽的慈善和慷慨,那么,所有权的区分就失去了意义。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完美的家庭情形中,所有权的区分根本不可能被想到,正义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观念。[9](P35-37)
财产的稀缺和争执的确是引发正义规范的重要来源,但休谟显然忽视了正义问题的其他向度。以正义的客观条件为例,我们可以反问休谟,在自然资源极度丰富的条件下,正义的观念是否就被放逐掉了?或者说,在财物纷争的情形被解决之后,就再无什么正义问题了?是否可以说所有的正义问题都可以还原为财物和资源的争夺?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即便在自然资源丰盈的条件下,我们也完全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形,有些人天生就有支配他人、统治他人的倾向和欲望,并非为了获取他人的资源,而是喜欢那种征服的感觉,喜欢有人能够完全隶属于自己,服从自己的威权,享受那种高高在上的滋味。这是不是一种不正义呢?在我们看来,大概很少有人认为,正义应该对此不管不顾。在现代社会中,很多问题都无关乎财物和资源的争夺问题,如某些宗教团体对自己后代的教育问题、少数文化的权利和自主性问题。如果对现代社会中正义问题的多样性保持敏感的话,很少有人会武断地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假象,都可以还原到最后的资源和财物问题上去。
再来看休谟的正义的主观条件。在休谟看来,假如人们之间的友谊和慷慨达到足够的高度,正义就将变得无用。也就是说,在一个普遍利他主义的社会里,正义就会被其他更为高尚的品德所取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休谟呢?最简单的回应方式是,一个普遍利他主义的社会只是一个虚构,当前的人类社会距离这一虚幻的社会过于遥远,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设想这一社会究竟是否需要正义。我们无法像休谟那样断言这个社会无需正义,而只能说它可能需要正义也可能不需要正义。如果根据当前的社会来测度这一理想社会,那么,它很有可能还是需要正义。我们只需追问一下,利他主义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否必然是一个和谐无间的社会?利他主义者在从事利他活动时是否跨越一定的边界,将自己变成家长主义者?利他主义者是否必然会对共同善的构想、对实现共同善的途径和方式达成一致的意见?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慈善与仁爱这些更高等级的利他主义情感自身是不自足的,因为假如这些情感关注的对象彼此冲突,它们就会变得茫然不知所措,因而就需要正义规范来调整和裁决这些情感的方向。[10](P190-192)就休谟所给出的婚姻例子来说,很多夫妇之间可能的确不存在关于财物的分割问题,因此,也不存在休谟所说的正义问题,但并非就完全不存在其他正义问题,如家务劳动的分配问题、孩子的抚育问题等,夫妇之间并非就不会发生任何冲突,并非不需要任何公平程序来裁决可能的冲突。
休谟正义观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完全是一种以财产为中心的正义观,简化了复杂的正义问题,忽略了正义的其他领域,尤其是没有关注到正义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即个体的平等权利与尊严问题。如果说正义理论真像德沃金所说的那样,旨在给予社会中的成员以平等的关照和尊重,那么,休谟的正义观就存在重大缺陷。
二
我们进入桑德尔的第二个批评意见。这一批评意见的内容是:即便我们假定正义的环境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能够满足,但它却不适用于其他一些中小型的共同体,像家庭、部落、邻里、城市、乡镇、大学、商贸协会、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诸多的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相似点是共同体成员或多或少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目标,呈现出亲密和团结的关系,正是这些特征使得正义的环境,尤其是主观的环境相对缺席。[11](P30-31)桑德尔据此认为,在这些团体中,正义并不具备罗尔斯所声称的那种优先性。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指明休谟关于正义环境论述的不足,在此要具体地进入正义所要处理的复杂问题以及正义所具有的多重作用。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桑德尔误解了罗尔斯的正义优先性主张。罗尔斯明确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他明确地区分了正义的不同主题,认为正义原则的制定必须参照这些主题的本性,没有普遍适用的正义原则。他认为,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有可能不适用于一些私密性的团体和小型的社会群体[12](P8),像桑德尔所列举的这些共同体。罗尔斯不认为他的差异原则可以直接运用于这些团体。因而,并非如桑德尔所指控的那样,罗尔斯倡导一种无区别的正义优先性。
即便罗尔斯没有这样的论述,我们还是可以阐明正义在这些中小型共同体中的优先性。这一阐述主要基于两点思考。这两点都植根于正义的独特作用。先看第一点。即便我们假定桑德尔所给出的共同体的确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共同体成员之间关系和睦,亲如兄弟姐妹,但我们仍要追问这一共同体是如何达成的,如何对待那些希望脱离这一共同体的人们。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第一种方式是具有共同目标和旨趣的人们相互吸引,彼此欣赏,最终走到了一起,确立一个旨在促进其共同事业的共同体。这一模式相容于正义原则,相容于个体的平等权利和自由,以自愿自主为基础。另外一种模式则是通过限制共同体成员的活动,限制他们的教育模式与精神世界来达成的。通过设置特定的教育课程,限定特定的活动场所,人们可以轻易地钳制其他人的思考和想象,使其认为他们所知道、所经历、所设想的就是生命的全部可能性,而无法知道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在一些宗教团体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现象是否要求正义的矫正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当今政治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理论能够断然否定正义在此问题上的相关性。
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争议性,我们不如换一个案例。以家庭为例。假定一个家庭中夫妇关系和睦,夫唱妇随,其乐融融。但实现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女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从家庭开始到学校再到整个社会,总是被教导要认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从属地位,要无条件地臣服于男性,无论是自己的父母还是自己的丈夫。虽然开始有可能感到挫折和痛苦,但鉴于整个社会的习俗和压力,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安于自己被设定的命运,正如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那样。进一步假定这个故事详细情节为,这个女性在婚后极其恭顺,侍奉自己的丈夫如同奴隶对待主人,勤勤恳恳地包揽一切家务,担负抚养孩子的全部重担。我们不禁又要问,这是正义的吗?显然,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这是亟须矫正的非正义。女性主义者可能会这样批评桑德尔:否认正义在私密性领域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充分暴露了桑德尔仍然固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这一不合时宜的区分,仍然忽视私人领域中大量的不正义现象。
为了进一步说明私密性团体中正义的优先性,我们可以再考察一下上面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假如特定共同体的某些成员想抛弃自己的既有成员身份,而加入到一个新的共同体之中,如若没有正义原则的保障,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当然会出现三种可能的后果:第一种是自由地脱离原有的共同体,去追求自己向往的新的生活;第二种则是该团体可能会为其成员脱离共同体设置极为苛刻的条件,如没收那些试图脱离共同体的成员的所有财产等,使得其代价过于高昂,以致不得不打消原先的念头,继续留在共同体内;第三种是这些成员可能会受到残酷的对待,甚至有可能被处死以警告那些试图效仿的人。无论在历史的案例还是在当今的某些团体实践中,我们都可以轻易地发现第二和第三种后果。这充分说明了,尽管在正义规范缺席的条件下,也有可能自然地产生一些道德的局面,如第一种可能后果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不能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必须为可能的非正义情形做好准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时刻稳固地确立正义原则。
以上的论述旨在表明,即便在一些具有共同目标和亲密关系的中小型共同体中,我们仍然需要确立正义的优先性。这是因为,总是有可能存在某些非正义的情形,我们不能抱侥幸心理,而是必须牢固地确立和维系正义的优先性。
这是我们论述的第一点。这一点着眼于正义在消除不正义方面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进入第二点。第二点相关于正义原则的另一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正义原则通常都会认肯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尽管内容上可能会有些出入,但都会同意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共同体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认肯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会助长个体的原子化趋势,会瓦解既存的共同体的纽带,并抑制一些更为崇高的共同体美德的兴盛。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个体运用权利的诸多方式。共同体主义者认为,当我们说个体拥有一项权利时,这就意味着个体又多了一项可以对抗他人的武器,又多了一个可以与他人分离开来的屏障。权利的确意味着要求得到保障的合理要求,但我们运用权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申认我们的权利,也可以搁置甚至放弃我们的权利,还可以让渡我们的权利。如果再辅之以我们做这些事情时的具体手段和方法,可以说,权利的运用就成为一项复杂的技艺了。[13](P523-527)
在运用权利的诸多方式中,权利的搁置与我们这里论述的正义的优先性相关性最大。首先来看权利与分外行为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分外行为体现出来的是高超卓越的美德,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行为,但如果不事先确立个体的稳固的权利,我们就难以识别这种分外行为,就有可能把它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受到激发和感染,各种高尚的社会美德如慷慨、仁慈、宽容以及友谊等就不会相应地滋长。但假如个体的权利已经得到明确的界定,那么,我们就会很轻易地识别那些放弃自己权利的分外行为者所透露出来的善意和高贵的精神,我们社会的整体道德局面可能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就一个共同体来说,如果其成员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有时能够主动搁置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对他人的合法要求,免除他人应该担负的义务,那么,这会极其有助于加强和稳固共同体的纽带。这种纽带与建立在威权和意识形态等基础上的纽带不同,它具有很高的道德品格,因而更为真实。必须注意的是,权利的搁置并不意味着权利的虚无,权利仍旧是在场的,权利的拥有者可以随时伸张其权利,因而权利的搁置无损于权利抑或涵盖权利的正义原则的优先性。
个体权利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对它们的不同运用通常会带来不同的关系后果。[14](P527)共同体主义者如桑德尔未能意识到个体权利的复杂结构和作用,因而才会轻率地认为,在一些私密性的共同体中,包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正义原则并不具有优先性。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私密性的团体中,正义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矫正可能出现的不正义情形,维系共同体的道德水准;另一个则是个体通过权利的搁置,可以滋长和强化共同体的纽带,培育和推动共同体美德的发展和兴盛。正义这两方面的作用足以支持罗尔斯的正义优先性主张,回应桑德尔的批评。
三
根据我们在回应桑德尔的前两个批评意见时所提出的诸多考虑,我们可以较容易地应答他的其他批评。下面具体展开之。
先来看他的相称性论题。这一论题指的是:正义的优先性程度是与正义环境满足的程度成比例的。由于正义环境的满足程度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等级,故而正义的优先性程度也应随之而变动不居,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确立正义的至高无上地位。这一论题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为经验心理性的解读,一为规范性的解读。就经验心理性的解读来说,这一论题可能是正确的,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人们在不同的场景下的内在心理感受。我们可以以“陌生社会”和“熟人社会”这两个概念说明这一点。根据我们的日常行为模式来看,在由陌生人构成的公共世界中,或在和陌生人打交道时,人们通常都保持足够的警惕,时刻关注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是否被侵犯,随时准备诉诸一切可能的手段为自己的权益抗争。相反,在由熟人构成的领域里,尤其在家庭这样的亲密团体中,我们通常会放心地把自己的事务交给对方去打理,即便出现了差错,也不会死死揪住不放,而是会谅解和宽容对方。正义和权利在此领域中很少被想起和被人诉求。如果再考虑到人们之间熟悉或陌生的程度也会有不同的等级,那么,的确,人们正义感受的迫切程度也会因之而异。
但如果从规范性的角度来解读这一论题,将其看做是否定正义的道德优先性,就大错特错了。这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说明。首先,正义所要处理的问题完全不限于休谟正义的环境所引发的问题,在很多不同的条件下,正义也会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也就是说,正义的应用领域已经超出了正义的环境所包容的内容。即便在正义的环境完全没有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可能还是需要正义的出场。其次,无论正义的环境满足的程度如何,正义的制度和规范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即便在一些私密性的共同体中,总是可以设想可能会存在一些非正义的情形需要去矫正,我们必须为可能的不幸做好制度和规范的准备,需要正义的原则去保证特定共同体的道德品格。第三,只有在确立正义原则的条件下,只有在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会有所谓的个体权利的搁置,人们也才会清楚地洞悉到他人权利搁置背后的善意,共同体的团结和纽带也才更有可能被加固。可以说,权利的确立和搁置能更好地阐释和界定其他社会性品德的含义和范围。总的来说,无论正义的环境满足的程度如何,都无损正义的优先性。其中的唯一差别在于:如果正义的环境充分满足了,那么,个体的正义感受可能会很强烈,正义就会出现在前台;相反,如果正义的环境未能充分实现,个体的正义感受就会淡薄,正义就会退居为背景还是幕后。但无论是前台还是幕后,正义都始终存在着,正义的优先性都没有被动摇。
显然,桑德尔要挑战的是正义的规范性意义上的优先性。就此而言,他并没有成功。我们猜测,他很可能是混淆了正义经验心理上的优先性与规范性意义上的优先性,以为只要击破前者就会粉碎后者,但这两者显然存在重大的差别,而且桑德尔也没有充分意识到正义规范性意义上的重要性。
我们再来看桑德尔的第四个论断:正义只是一种补救性的美德,它的道德作用在于补救恶化的道德状况,在道德状况优良的条件下,正义这一美德就会被其他互竞的美德如友善、仁慈、博爱所取代。[15](P32)桑德尔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正义的作用只是弥补性的;正义与其他美德是一种不相容的互竞的关系。
毋庸讳言,正义的确具有补救性的作用,它可以唤醒人们的正义感,矫正社会的不正义现象,修复恶化的道德秩序,但这并非正义的全部面相。以我们上面已经论述的一点为例,正义至少还可以赋予其他社会性的美德如仁慈和慷慨以含义,可以催生和滋长这些社会性的美德,巩固和强化共同体的纽带。不仅在道德恶化的时候需要正义,在道德秩序良好的时候,正义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就正义与其他美德的关系来说,它们之间也并非互竞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生互助的关系。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得到阐明。首先,就整个社会来说,正义是一种底线性的基础性的美德。如果一个社会无法稳固地确立一个合理的正义原则,无法稳固地保障所有个体的平等权利和自由,而是任由一部分社会成员剥削和压迫另一部分成员,听任社会的强势群体压制弱势群体,那么,这一社会从总体上来说很难是一个充满公民友谊和善意的社会,道德冷漠、道德愤恨很可能是其必然结果。相反,如果个体作为自由平等公民的地位受到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个体的尊严为整个社会制度所维系,那么,个体的友善、仁爱美德的增长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次,就仁慈和博爱等社会性德行来说,它们也需要正义规范的调节。因为,这些美德自身是不完善的,在很多冲突的情形下,这些德行显得很无力,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有时甚至完全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如我们常见的慈母和败家子的例子。
正如布坎南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当我们说正义是一种补救性的品德时,这就预设着我们接受了一种绝对和谐的理想,意味着我们不愿赋予多样性、分歧和冲突以任何积极的价值。[16](P877)但为何我们必定认为个体利益的冲突、个体善观念的歧异必定是道德状况恶化的标志呢?难道在绝对和谐和统一的社会中,其道德水准必然最为优良吗?答案显然很难确定。在自由条件下达成的多样性和冲突很可能是道德进步的重要表现。如果我们否弃那样一种极其绝对的道德和谐的理想,那么,将正义看做是弥补性品德的说法就是没有说服力的。
即便我们承认正义是一种补救性的品德,但由于有待正义补救的状况的普遍性(可能)存在,正义的优先性地位丝毫不会因此而受到削弱。
我们对桑德尔的第四个批评的回应也部分地适用于他的第五个批评,即正义的补救性特征使得我们无法断言正义的滋长必然意味着道德进步,在某些条件下,正义甚至是一种恶德而非美德。桑德尔认为,正义的滋长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通过矫正之前存在的不正义,这时的确意味着道德的进步;另外一种方式则无关乎之前的义与非义,它是通过改变之前存在的道德动机和道德倾向来实现的,如改变人们先前存在的自然仁爱和情感。就第二种方式来说,正义固然得到了滋长,但却无法保证它必然能修复之前的道德状况,必然能弥补更为高贵的美德的流失所带来的道德损失。[17](P32-34)这样一来,正义就并不必然是一种美德,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恶德。
桑德尔的第五个批评事实上包含了两个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都已经处理过。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道德进步的概念。第二个问题是正义的出现是否必然会改变人们先前的道德倾向和道德模式,正义是否必定与其他社会性的美德构成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先来看道德进步的概念。桑德尔事实上已经预设了一种道德进步的标准,即一个共同体的和谐程度越高,情感的纽带越紧密,共同利益的感觉越强烈,则该共同体的道德水准就越高。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多元善观念的分歧,充斥着多元的价值观,并且这些善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彼此冲突,它们对社会组织的安排和资源的分配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要求,那么,该社会的道德水准就值得商榷。应该如何看待桑德尔默认的这一道德进步标准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共同体和谐的手段如何。如果是通过正义的手段达成的,那么该共同体的道德水准的确很高,因为它将正义与共同体的价值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了。相反,如果是通过一些隐形和显性的强制性手段实现的,该共同体的道德水准是否值得艳羡就很不确定了。就多元价值的冲突来说,如果这种冲突远未达到分裂社会的程度,而只是确立个体平等权利和自由的自然后果,那么,我们也无法断然认为这是一种道德退步。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桑德尔倾向于认为正义的滋长会破坏和颠覆先前存在的一些和谐的共同体,会抑制与这些共同体相伴随的一些自然的高尚的美德。他试图以一个家庭内部关系的变迁为例说明这一点。我们以家庭关系a和家庭关系b来描述这种变化。在家庭关系a中,夫妇双方为自然的情感和慷慨的精神所激发,很少诉求个体的权利与公平的决策程序,公平份额和应得的观念也很少被想起,一切都是自然和自发的。随后,桑德尔又描述了家庭关系b:在这一新的家庭关系中,先前的自然性和情感让位于公平的要求和对权利的恪守,之前的慷慨精神也被一种明智的无例外的正直的脾性所取代。夫妇与孩子追求反思性的平衡,严格遵循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甚至努力实现稳定性与正当和善融合的条件。桑德尔让我们比较这两种家庭关系,并进一步追问两种家庭关系哪种更可欲,充分实现正义原则的家庭关系b究竟能否完全弥补家庭关系a中的道德品格和高尚美德。[18](P33)
桑德尔的意图很明显,他试图通过表明家庭关系b的不可欲性来证明正义优先性的缺陷。我们完全可以认同桑德尔的判断,即家庭关系b是一种极其糟糕的家庭图景,是常人完全无法忍受的家庭关系。但桑德尔如果想借这个案例批判正义的优先性,他至少还需证明家庭关系b是由于正义的滋长和介入而造成的。但他完全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甚至根本就无意做出论证。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的确存在着由于正义原则的确立,由于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高扬,家庭关系也受到了冲击,家庭关系经历了从a到b的变化。但这与正义的优先性有何关系呢?毕竟这是由于个体权利的误用造成的结果,是一些个体不知道何时伸张自己的权利、何时搁置自己的权利所引发的。正如科学技术一样,如果不恰当地运用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这与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何干呢?而且,家庭关系从a到b的变化的最大可能性原因是家庭关系a并不如桑德尔所设想的那样完美,而是早已潜存着一些积怨和不满,只是因为其成员还不知道生活的其他可能性,所以这些矛盾和冲突没有爆发出来。个体平等权利和自由的确立为这些成员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促使他们迅速地转向家庭关系b。但按照这种可能性,正义的优先性更是被证实了,因为我们要依赖它修正不正义现象。
根据我们日常的经验,如果真有一种家庭关系a存在,那么,它是不大可能会被正义原则的确立所搅扰和颠覆,否则现代社会中的大部分家庭关系都应该如家庭关系b那样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原因在于,个体有能力在运用权利时做出必要的区分,他们知道何时何处去伸张其权利,何时何处要适当地搁置其权利。如金里卡所说,正义并不取代爱和其他亲密的情感,正义只是要确保这种爱不会蜕变和沦落为支配和屈从关系。[19](P316)此外,根据我们之前的论述,正义与其他社会性美德是相容的关系,并非互竞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正义会成为一种恶德。
以上是我们针对正义优先性问题对桑德尔的回应。该回应旨在说明:正义的观念和制度是人类的重大成就之一,但同时也是一项相当脆弱的成就,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正义的诸多作用,为维系和实现正义而奋争,而不是轻易地就质疑正义的优先性,试图超越正义。
[1][10][12]John Rawls.A Theory of J ustice.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16]Allen Buchanan.“Assessing the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Liberalism”.Ethics,99.
[3][6][11][15][17][18]Michael 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 usti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4][7][8]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9]休谟:《道德原则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3][14]John Tomasi.“Individual Rights and Community Virtues”.Ethics,101.
[19]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
The Priority of Justice
YANG Wei-qing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The priority of justice means the primacy of justice relative to other values in the system of values or other principles in the framework of moral principles.InA Theory of J ustice,Rawls brings forward this thesis explicitly.Sandel does not agree with this thesis.He puts forward five kinds of objections.But his objections are not very convincing,because he overlooks the varieties of ways in which justice functions,and the peculiar status and important role justice has in the human society.
justice;priority;Rawls;Sandel
杨伟清: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 李 理)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争论及其演进”(22382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