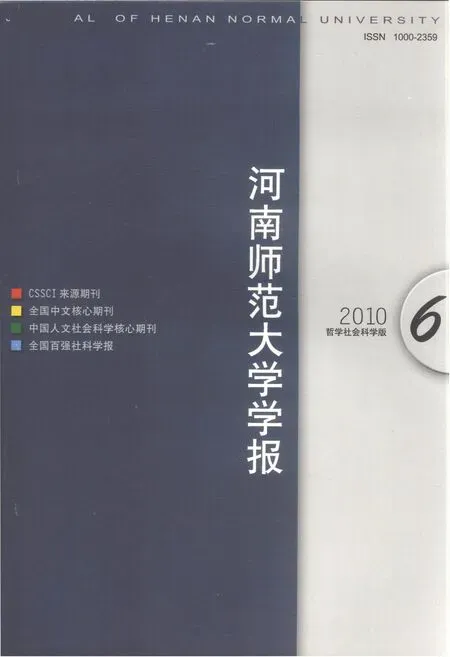论“痴”的审美与文化价值
——“文化语义学与魏晋文化研究”之一
刘志伟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论“痴”的审美与文化价值
——“文化语义学与魏晋文化研究”之一
刘志伟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本文尝试以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方法,探讨魏晋时代“痴”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通过把握“痴”与“早慧”文化、“痴”与审美“移情”及审美化生活方式追求、“痴”与“玄学”传统及文化病理等的内在联系,揭示“痴”所体现、折射的魏晋人格精神、浪漫气质、艺术情调、哲人深致、文化智能与“病”理色彩。魏晋时代对“痴”的审美与文化认知,许多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有益养分,深远、持久地滋润着民族文化精神,规范、影响着后世的理想人格塑造、文化艺术生活以及文学艺术创作。与西方“酒神”精神说和审美“移情”说等相比,“痴”具有更为深广多面、圆融互补的审美与文化价值蕴涵,而其语义指涉的感性、模糊与多趋向特征,也显示了中华思维模式的潜在缺陷。
“痴”;魏晋;审美;文化价值
一个大的文化与文学时代的出现,其突出标志之一就是:一批能够集中表现时代精神、风貌的文化语词的凸显。这些文化语词,有些是应时代之运而生的;有些是“旧瓶”而被装了“新酒”的;甚至,有些为人们所轻忽或不齿的语词,也因缘际会,被化腐朽为神奇,堂而皇之地频繁登台亮相了。如在魏晋文化与文学时代,“雅好慷慨”为建安文士所共同嗜好;呼唤、崇拜、反思“英雄”,是贯穿整个魏晋时代的重要文化现象;曹操等使“朝露”成为象征建安文士全新生命的特殊符号;曹植等甚至以“尘埃”张扬难以企及的时代才情;阮籍、刘伶特铸“大人先生”以象征魏晋之际文士的理想人格形象;魏晋风流人物对“虱”类语词的高频使用,则为中国文化史的奇观。魏晋时代,“痴”也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能够多方体现、折射魏晋审美与文化精神的重要文化语词。借助于全面考索“痴”的文化语义及其在魏晋时代的使用情况,本文试对以“痴”为名的魏晋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
一、大器晚成:“痴”与“早慧”交相辉映
先来考索“痴”的本义。
就语源看,今已难以确知“痴”字最早出现于何时,在先秦时代大约少见。《太平御览》所引《周书》逸文有“痴”:“太公望忽然曰:‘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大事不成。’”[1]2244《文子·守法》:“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贤者,痴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2]152《山海经·北山经》:“(人鱼)食之无痴疾。”《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说二》:“婴儿、痴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3]581但这些涉及“痴”的例句,还不能被确认一定就是先秦时代的。
西汉时期使用“痴”字则肯定无疑。如史游《急就篇》已将“痴”等明确归入“呆”类七病中,《淮南子·俶真篇》有“或通于神明,或不免于痴狂者何也”之问,班固《汉书·韦玄成传》记载韦玄成“阳为病狂”而被人指为有意“为狂痴”。东汉“痴”字较为多见,如王充《论衡》之《率性》记载“有痴狂之疾,歌啼于路”;《越绝书》之《计倪内经》言“惠种生圣,痴种生狂”;应劭《风俗通义》言蛮夷“外痴内黠”;郑玄注《周礼·秋官·司刺》“三赦曰蠢愚”言“蠢愚,生而痴马矣童昏者”;王符《潜夫论·边议》称“而痴儿马矣子,尚云不当救助,且待天时”;《三国志》注引《献帝春秋》记载,董卓找借口欲废汉献帝就谈到“人有少智,大或痴”等。
由前引例句看,在对“痴”的早期使用中,囿于人类对自身认识及科学水平较为低下,还不能明晰、准确区分“痴”与疾病的关系,有时或视“痴”为疾病,或将“痴狂”疾混同于“痴”,但已经关注、探讨“痴”与疾病的关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概括“癡”的本义:“痴,不慧也。从疒,疑声。”段玉裁注:“心部曰:‘慧者,獧也。’犬部曰:‘獧者,急也。’痴者,迟钝之意。故与慧正相反。此非疾病也,而亦疾病之类也。”[4]353扬雄《方言》:“痴,马矣也。”“马矣”意为呆傻。实际上,一方面,正如庾敳《意赋》所说,“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质所建”,“痴”具有非后天人为的因素;另一方面,“痴”虽有病态性成分,却与真正的疾病有着本质不同,它以个人心智的呆傻迟钝为其重要特征,是个人心智发育处于晚熟状态,或永远停留在较为低下的智力水准上的特定表现,适与“早慧”悖反。从这种意义上讲,“痴”就意味着连正常人都不如,极有可能终身难有出息,遑论大器晚成。
正因如此,在崇尚“早慧”文化的古代社会,“痴”经常被作为“早慧”的对立面,而为人们所轻视、嘲辱。汉末、魏晋时代,以文化高门为主体的门阀士族逐渐取得并巩固其政治统治权,受门阀士族主导,整个社会层面都高度重视对儿童智力的早期开发,对“早慧”文化的崇尚、褒扬风气,更是空前的。在专门记载魏晋风流人物言行的《世说新语》中,不但有《夙惠》专篇表彰陈纪与陈谌兄弟、何晏、司马绍、张玄之、顾敷、韩康伯、司马昌明、桓玄等的“早慧”事迹,其他篇中也随处可见这些人物以及对别的“早慧”者如徐稺、孔融及其二子、祢衡、曹植、曹冲、曹髦、杨修、王戎、范宣、钟毓、钟会、孙潜、孙放、谢尚、谢玄、谢道韫、谢灵运、王弼、卫玠、袁宏、王献之、祖纳、桓温、羊孚、戴逵、车胤、裴楷、裴秀、竹林七贤的后人等的记载。可以说,以“早慧”而为父兄、亲故、他人识赏,几乎就是直通魏晋风流人物的必由之路。故际身魏晋时代,如是常人而不“早慧”,或即便“早慧”而没有早被识赏,那就很有可能被视为不正常或“痴”了。如果被视为“痴”而终无特异表现,自然也就是通常所谓“痴”人,只能“痴”活一生而无足挂齿了。
但“早慧”却并非通往魏晋风流人物的唯一之路。因为“早慧”并不能确保人生必成大器。故单就语言本身而论,不去理会其中所包含的别有用心,则前引董卓“人有少智,大或痴”,以及《世说新语 ·言语》陈韪所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颇具真理意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大器晚成也为魏晋时代所普遍崇尚。一个值得予以高度重视的文化现象是:魏晋时代那些大器晚成型的风流人物,往往就曾被视为“痴”!经常的情形是:或原本就不“痴”,甚至是“早慧”的,但由于没有早被识赏的机遇,也会被误认为“痴”,这样的人物,一朝被人发现,就会大得盛名;或早期表现庸常甚至具有“痴”的表象,后来却有上乘表现为自己正名,这就正所谓大器晚成了。这些人物一旦成功,则曾被作为其人定性标志的“痴”,就有如美人之“痣”、月中微影,直接为其名士风范锦上添花、倍增光彩。比之于“早慧”名士,那些晚成名士的“痴”气、“迟钝”,不但不比“早慧”逊色,甚至如影随形相伴大器晚成,而与“早慧”交相辉映,饶具异量之美。故如果不能以“早慧”成名,“早痴”其实也可以成为通往魏晋风流人物的蹊径。只不过,“早慧”更强调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展现生命质量与价值的加速提升过程,“痴”慧更注重在不动声色中默默强化充实生命质量与价值的过程。这是“痴”也可以与“早慧”一样,作为表现、象征魏晋风流人物强烈生命意识与精神追求的特指“符号”的重要原因。
在有关魏晋风流人物的记载中,以“早痴”而晚得大名,是一种相当固定的惯用笔法。如《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早年也被“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5]1359;《晋书·皇甫谧传》记载,皇甫谧“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5]1409,后励志而终成大器等。至于最典型的例子,则要数王湛的“痴”名远扬。《世说新语·赏誉》记载:
王汝南(王湛)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精微。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懔然,心形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济虽俊爽,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去,叔送至门。济从骑有一马绝难乘,少能骑者。济聊问叔:“好骑乘不?”曰:“亦好尔。”济又使骑难乘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名骑无以过之。济益叹其难测,非复一事。既还,浑问济:“何以暂行累日?”济曰:“始得一叔。”浑问其故,济具叹述如此。浑曰:“何如我?”济曰:“济以上人。”武帝每见济,辄以湛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既而得叔后,武帝又问如前,济曰:“臣叔不痴。”称其实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于是显名,年二十八始宦。[6]234-235
刘孝标注又分别引邓粲《晋纪》“王湛字处冲,太原人。隐德,人莫之知,虽兄弟宗族亦以为痴。唯父昶异焉”和《晋阳秋》“济有人伦鉴识,其雅俗是非,少有优润。见湛,叹服其德宇。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湛闻之曰:‘欲以我处季孟之间乎?’”的说法予以补充。可见,王湛之“痴”著名当时,“虽兄弟宗族,亦以为痴”,甚至连皇帝都知其“痴”名。宜乎当侄儿王济早为风流人物,他还为“痴叔”。但是,一旦他以多能“弥日累夜”地折服自负“俊爽”的名士之侄,使其“懔然”,而“自视缺然”、愧叹“难测”,并追悔得“识”“家有名士”之晚,就以“早痴”胜过“早慧”而声名鹊起,俨然成为处于山涛、魏舒伯仲间的名士了。
王湛的为婚,也见出其非凡“痴”慧。《世说新语·贤媛》记载,王湛“自求郝普女”,连其父也“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可是,“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逐为王氏母仪”[6]371。在王湛已是名士后,“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人们这才明白:原来在其求婚“痴”相中,深藏着“难测”的远“识”!
有趣的是,被王济借以与其叔相比的山涛、魏舒,据《晋书》本传记载,二人都是在四十或四十多岁才步入仕途,又正好由魏舒接替山涛司徒之职,魏舒更是一位以“迟钝”近“痴”、大器晚成的人物,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
魏舒字阳元,任城人。幼孤,为外氏宁家所养。宁氏起宅,相者曰:“当出贵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谓应相也。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迟钝,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户长,我愿毕矣!”舒不以介意。身长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箸韦衣,入山泽,每猎大获。为后将军钟毓长史。毓与参佐射戏,舒长为坐画筹。后值朋人少,以舒充数。于是发无不中,加博措闲雅,殆尽其妙。毓叹谢之曰:“吾之不足尽卿,如此射矣!”转相国参军。晋王每朝罢,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累迁侍中、司徒。[6]234-235可见,以“痴”相十足而终成正果,在魏晋时代甚至是造就名士的传统。故王济在“发现”其叔时很容易就联想起魏舒来。再如《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罗友事迹:
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谢公曰:‘罗友讵减魏阳元。’”[6]404-405
“阳元”正是魏舒之字,而罗友被比之于魏舒,其事略同王湛。为什么在谈论大器晚成型的“痴”人时,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这些特定人物,以彼此事迹互比?这是否意味着:在魏晋时代,当人们形容“痴”类风流人物大器晚成的异量之美时,甚至还存在着为其所公认的人物原型参照模式?
王湛之孙王述颇有乃祖早“痴”遗风,则让我们见识了一脉相承的“痴”家门风。《世说新语·赏誉》记载,“王蓝田为人晚成,时人乃谓之痴。”《晋书·王述传》记载:
年三十,尚末知名,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既见,无他言,唯问以江东米价。述但张目不答。导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尝见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述正色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 !”导改容谢之。[5]1961
这些,简直就是王湛事迹的改写版。
正由于存在大量早“痴”而大器晚成的事例,为时人所喜闻乐道,并据以比较、品鉴、赏誉,甚至流风所及还影响到家族门风传承,这就使魏晋时代以“痴”来指称、赏鉴大器晚成者的异量之美,成为必然之事,也从而使“痴”能够与“早慧”双美并存、交相辉映。如果没有对大器晚成之“痴”的精心发现与赏鉴,魏晋时代“早慧”之“花”的独放,就未免失之孤寂、单调了。
二、“痴”与审美“移情”及审美化生活方式追求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最具浪漫气质和艺术情调,魏晋文士的日常生活与其文化艺术生活有着紧密关联。一方面,嵇康《释私论》中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代表了处于魏晋特殊时代文士普遍而强烈的心理欲求。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就是要求以审美态度看待人生,通过张扬自我人格和建构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以超越受魏晋特殊现实政治与伦理道德系统支配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魏晋风流人物往往以阮籍“礼岂为我辈设哉”和王戎“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生命实践方式,来实现对保洁存真的情感生活和审美理想的执著追求;也以追求和建构一种自然的适合心灵自由、精神解放的异态生活和生活秩序,来对抗阮籍《大人先生传》所指出的,为礼法之士刻意追求的充满矫饰诈伪的“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常态生活状态和秩序。由于“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使他在对象里寻回自我”,魏晋文士富于审美情趣的自我生活必然更多向文化艺术生活靠拢。另一方面,魏晋风流人物大多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艺术修养,甚至在某些专门方面造诣精深。故其文化艺术生活也必然对其自我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审美化的自我生活与其文化艺术生活的有机互动影响,既催生大量具有鲜明审美“移情”特征的文化行为,也容易形成一种被常人视之为“痴”的“痴”气人生样态。有四种被称为“痴”的情形,就值得予以充分关注:
其一,专注入神于所热爱之事,因“得意”“忘形”,或“得意”通“神”,被时人称之为“痴”。魏晋文士使其自我生活与文化艺术生活高度合一的现象,给人以深刻印象。《晋书·阮籍传》记载:
籍容貌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读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5]1359
阮籍的“任性不羁”、“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最能代表魏晋文士专注入神于所热爱之事,从而“得意”“忘形”的审美“移情”之“痴”。当阮籍有时“痴”迷于“书”或“山水”时,他就索性“闭户”而“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无论他封闭或开放自我,都往往处于半由意志半不由意志、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的审美观照之中,泯灭了时间的长短与空间的广狭界限;尤其当他“痴”迷于所嗜爱的“庄、老”、“酒”、“啸”、“琴”等文化艺术活动时,他更常常进入有如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与西方所谓审美“移情”境界,完全将自己外射、移置、感入于所热爱之事中,达到“无我”、“忘我”境界,“意”醉“神”迷,灵魂都已与之融合为一,不复知道身在何处,如何能够顾及他人存在!故他或静、或动、或哭、或笑、或叫、或闹,不觉眉飞色舞、足之蹈之、歌之舞之,一任自然,这就被“时人多谓为痴”。
因自我生活与绘画艺术冥合“通神”,大艺术家顾恺之被称为“痴绝”。《晋书·文苑传·顾恺之》几乎就是为一位“痴”其终身的画家写照:
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恒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每写起人形,妙绝于时,尝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又为谢鲲象,在石岩里,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图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辞。恺之曰:“明府正为眼耳,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仲堪乃从之……初,恺之在桓温府,常云:“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5]2405-2406
作为被谢安称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的绘画巨匠,顾恺之全“痴”于画。除了具有与阮籍相同的审美“移情”特点,在进行具体审美创造时,受其绘画审美想象与情感的驱使,顾恺之更注重有意扩大、加强、夸张其主观的审美认知:一是通过对“对象的人化”这种审美“移情”,刻意追求使不具生命的画作通“神”而“活”;二是通过对作为其绘画创作对象的特定个人的审美化“物化”,与设身处地的想象等审美“移情”,来创造“神明殊胜”的伟大作品;三是充分进行其他文化艺术门类与绘画的审美“移情”,使其成为绘画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故其画法、画思、画趣、画境、画论,处处通“神”,极尽痴黠灵妙之至极,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宜乎为时人目为画“痴”!
此外,如《晋书》本传所载的阮籍因“钟情”而送嫂归宁、而醉卧于酒家老板娘脚下、而前往并不相识的早逝少女坟前哭祭等,也是审美“移情”的典型事例。再如,《世说新语·惑溺》所记荀粲的因“痴”于“情”而冬月以其身体为妇取冰祛病,终于为“情”而死;同书《文学》所记王弼的“痴”想“梦”之玄理过苦而成疾;《晋书·袁山松传》所记张湛好于宅前种松柏,山松出游好让左右作挽歌,被人称为“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等,虽有违常情,同样也是嗜好至极才有的极端“移情”行为。至于《世说新语·术解》刘孝标注引《意林》所记载的,杜预称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他自己有《左传》癖等,虽不以“痴”见称,有些也未必具有审美意味,仍可列入具有“移情”特点的“痴”人事迹。
其二,“痴”于所热爱之事,表现出富有“痴”意的特异思维、思想、语言与行为举止。如顾恺之使其自我生活完全等同于艺术生活,总是以艺术眼光或思维看待现实生活,故经常被视为“痴”,《晋书》本传所记载的“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以及画人颊上三毫使其“神明殊胜”,置人画像于丘壑中等,都是显例。
再如《世说新语·方正》所记简文事迹:
王长史求东阳,抚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 ,真痴。”[6]186
简文之“痴”在于:王濛健康时不与“东阳”之职,而在其三十九岁临终时与之,已无实用。但其“哀叹”之“令”,确有对王濛深情补“过”之“痴”;而王濛沉着面对死亡,以“痴”、“真痴”咀嚼、赏叹如此具有审美意味的深情,也自有风度!
其三,魏晋时代普遍崇尚特异,特异之美也往往被称为“痴”。崇尚特异、张扬个性被视为“痴”,早在汉末已开风气。如《三国志·魏志·陶谦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记载:陶谦为司空张温所重,而谦“轻其行事”,曾于酒会上“众辱温”。后经人调解,陶谦答应道歉。见面则仰头谓温:“自谢朝廷,岂为公耶?”就被张温称为“痴病尚未除”。故梁章钜评价“恭祖(陶谦字)之痴病与元龙之豪气正可作对”[7]255。如此之“痴”,所表现的其实是一种骨鲠强项的士节之美。以嵇、阮为代表的魏晋文士“越名教而任自然”,极力张扬自我人格和建构审美化的自我生活,更倡导了普遍崇尚特异、张扬个性的魏晋文化风气。尽管他们的言行易被常人误解、礼法之士不与宽容,如伏义《与阮嗣宗书》就极力指斥阮籍这位礼法“公敌”:“而闻吾子乃长啸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拊腹大笑,腾目高视,形性侜张,动与世乖,抗风立候,篾若无人。”[8]547所指固有阮籍故为姿态以辱礼法之士的方面,许多正是被故意歪曲的阮籍之“痴”。实际上,阮籍之“痴”不但是其真情至性的自然流露,更展现了他以审美态度进入人生的丰神韵致。《晋书》对此有着恰切评价:“外坦荡而内醇至。”正因这样,阮籍等深刻影响了魏晋文化风气。魏晋风流人物展现与众不同的特异个性之美,许多就被视为“痴”美。如《世说新语·品藻》:
王中郎尝问刘长沙曰:“我何如苟子?”刘答曰:“卿才乃当不胜苟子,然会名处多。”王笑曰:“痴。”[6]290王坦之本希望刘奭能奉承自己,刘奭却直道真实。当坦之笑他不通人情,赏叹他性情真率,就以“痴”来形容刘奭,也表现自己的诙谐、风趣。再如《世说新语·简傲》:
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尝著白纶巾,肩舆径至扬州听事,见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蓝田曰:“非无此论,但晚令耳。”[6]414
谢万目无岳丈,直言其“痴”,故是真率狂豪;王述毫不计较,平心静气地解释自己“痴”名有自,然非真“痴”,则显示了平等、宽厚待婿风度。两“痴”相较,究竟谁是真“痴”?
其四,于所热爱之事达到通“神”境界,而在人生其他方面幼稚、迟钝,表现出偏能、偏弱的严重失衡、错位,亦被称为“痴”。魏晋文士自我生活与文化艺术生活的高度合一,往往造成其自我生活与文化艺术生活的失衡与错位,甚至会使自我生活完全混同于其艺术生活。最典型的仍是顾恺之。顾恺之使其自我生活完全等同于艺术生活,总是以艺术眼光或思维看待、错认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闹出种种笑话。如《晋书》本传记载,“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发其厨后,窃取画,而缄闭如旧以还之,绐云未开。恺之见封题如初,但失其画,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了无怪色”;“义熙初,为散骑常侍,与谢瞻连省,夜于月下长咏,瞻每遥赞之,恺之弥自力忘倦。瞻将眠,令人代己,恺之不觉有异,遂申旦而止”;“恺之矜伐过实,少年因相称誉以为戏弄”[5]2405等。可见,顾恺之因其艺术“痴”气的弥漫,在现实生活中也“痴”气十足,不通人情世故,生活能力低下,有时不免显得呆傻、幼稚、充满不切实际的荒唐妄想。
要之,魏晋风流人物的审美“移情”与对审美化生活方式的执著追求,因其不合或超越常态常情而迹近于“痴”,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与现实生活的严重失衡、错位,但就主要方面而言,其所表现的审美情韵与文化创造精神,具有重要审美与文化价植,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三、“痴”与“玄学”传统及文化病理
要全面探讨以“痴”为名的魏晋文化现象,还关涉其与“玄学”传统及文化病理等的关系问题。下面试分别予以简论。
先来讨论“痴”与“玄学”传统的关系。
实际上,在早期关于“痴”的语义使用中,人们虽没有直接谈论“痴”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但已对“痴”与思想智慧的深层关系有所关注。如前举《太平御览》所引《周书》逸文有关吕望谈论“痴”“狂”是“大智”“人师”成名成事的必备素质,特别《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详细描述、渲染帝王师范蠡的“痴”“醒”“狂”态,就都可视为人们对吕望、范蠡这类大智若愚型“痴”人的接受、认同。再如《三国志·魏志·管宁传》裴注引《傅子》记载,焦先以裸身、食秽、不言等怪异行为而被视为“痴狂人”,而他的许多颇具智慧的言行、义举和准确预见,又使人“颇疑其不痴”。裴注引皇甫谧《高士传》称其“见汉室衰乃自绝不言”,“虽上识不能尚也”,“自羲皇已来一人而已矣”。可知焦先这类人物,实际是隐于乱世的智者。而在魏晋时代,“玄”风大盛,《老》、《庄》、《易》成为时人崇尚、研读的“三玄”,对人们的意识思维与生活方式、行为举止有着深刻影响。魏晋时代许多以“痴”为名的文化行为,自然也不例外。
汉末、魏晋时代动荡,人心险恶,使“早慧”而锋芒毕露者往往难以善终,易招致杀身之祸或其他人生祸患,故时人每奉“易”“老”的处柔弱、示愚拙、行稳健,以求韬晦自保,这类行为,往往被视为“痴”。极端的例子,如《三国志·魏志·管宁传》裴注引《傅子》记载,石德林于汉末乱中,“遂痴愚不复识人”,外号“寒贫”,以“乞食”为生,后被发现“不痴”。其思想言谈举止,就与“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昼夜吟咏”密切相关。而“尤好庄、老”,并著有《通老论》、《通易论》、《达庄论》的阮籍,嵇康视之为“至慎”榜样,司马昭还称道其“至慎”乃“为官”的最高境界。阮籍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他对魏晋政局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对“三玄”有着精深的研究,故能以最强的自制力约束自我,臻于常人难以企及的“至慎”。其“傲然不羁,任性独得”,“喜怒不形于色”,“忽忘形骸”,显然与其“至慎”自保思想及“三玄”修为密切相关。
魏晋风流人物普遍崇尚、追求朴拙、厚重、深沉、稳健、大智若愚的人生涵养、功夫与境界,也受到《老》、《易》、《庄》“三玄”思想的深刻影响与熏陶。前举诸享有“痴”名的风流人物,不少就深受其影响,而表现出时代智者的气质、风度、情韵。尤可注意的是,魏晋时代不但盛行家族传习与浸淫《易》、《老》、《庄》“三玄”的文化传统,甚至还出现以“痴”为特色的家风传承。前所提及的王湛家族正是这样。王昶以精通“玄理”著名,其子王湛则以“玄学”修炼其“痴”,开家族“痴”风。《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邓粲《晋记》记载,当王湛父“昶丧,居墓次,兄子济往省湛,见床头有《周易》,谓湛曰:‘叔父用此何为?颇曾看不?’湛笑曰:‘体中佳时,脱复看耳。今日当与汝言。’因共谈《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济所未闻,叹不能测”[6]234。其子王承本传亦称其“清虚寡欲,无所修尚,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修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王承子王述本传称其“少孤”,“安贫守约,不求闻达。性沉静,每坐客驰辩,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述年三十,尚未出名,人或谓痴”,“既跻重位,每以克柔为用”,甚至能够面壁半日以忍受谢奕的极言詈骂。王导论王述“清贞简贵,不减祖父,但旷淡不如耳”。述子坦之“真率”又不及述,故述有“人言汝胜我,定不及也”的感叹。“论者以为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而祖不及孙,孙不及父”,恰以“痴”名之程度最深的王湛为最高,“痴”名第二的王述亚之。如此家族“痴”风,实际是以“玄学”精神培养一种高度人生涵养、功夫、境界,其所谓“迟钝”,其实是朴拙、厚重、渊茂、深沉、稳健,是大智若愚,其突出功效便是以冲淡谦退、沉静裕如等自保,并后发制人,取得更大的人生成功。
借助修习“玄学”来形成以“痴”为特色的家风传承,这在后世颇为罕见,也让我们联想更多是由家族生理遗传之“痴”。如三国时代虞翻《与某书》为其四岁小儿求妇,自嘲“蝦不生鲤子”,自称“老痴”;其《与弟书》谈为长子求婚,谓“虞家世法出痴子”,自述“有数头男,皆如奴仆,伯安虽痴,诸儿不及。观我所生,有儿无子。伯安三男,阿思似父,思其两弟,有似人也”。从《三国志·吴志·虞翻传》等所记有关事迹看,虞翻十一子中,第四子虞汜最有出息,另有数子也有声名,其言自有夸张与牢骚成分,但数代中皆有先天“不慧”的“痴”者,大约也是事实。故他为家族性之“痴”而焦虑、苦恼。虞翻家族这种更多具有家庭生理遗传性质之“痴”,与王湛家族以“玄学”为指导,提升、加强其文化理性与智慧品质,从而形成以“痴”为特色的家风,有质的不同,二者之间所蕴涵的文化与审美价值的高下,自然也不能相提并论。
接下来讨论“痴”与文化病理的关系。
首先,魏晋时代政局动荡,充满血腥与黑暗,毫无疑问属于非正常的病态时代,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必然会受此病态时代的影响,前举那些具有审美与文化价值之“痴”例,不少就由病态时代直接或间接催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病理特征。最为明显是,政治文化氛围的高度压抑,往往造就现实社会中貌似“痴憨”“痴呆”类人物。阮籍等的不遵“礼法”、好为“青白眼”等迹近“痴狂”、非理性的文化行为,是刻意蔑“法”破“礼”,或有意任其“性”“情”,完全受到理性意志的支配,更多韬光养晦、佯狂避世的主动选择,是其政治人生智慧的高度结晶,与真正的“痴狂”疾病,实有质的不同,但由于其产生于病态政治文化氛围中,故也具有特定的病态特征。
其次,受黑暗政局影响,人们对积极参与现实的热情消退,而对抽象之理论兴趣颇浓。在“三玄”理论的主导下,魏晋文士往往沉迷于谈“玄”论“道”之中,而轻忽对现实问题的关怀,这也是他们面对现实人生时,每每呈现出“痴”态的重要原因。由于普遍追求在思想层面摆脱现实的桎梏,“游心于玄”遂成为当时文士的自觉行为。在“葆真”“自然”的指导下,人们往往脱略形骸,追求目击道存的理想人生,表现出消极避世倾向。故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痴”气人生追求,实际放弃了个体生命的社会责任,客观上起到了纵容社会黑暗、腐朽势力的不良作用,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自有其不利的方面。
复次,受现实政治和“玄学”理论的双重影响,“立言”成为魏晋文化的主导追求方式。对审美化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的极端追求,导致“痴”与文学艺术创作联系紧密。就此而言,“痴”不仅仅成为一种文学艺术的创作状态,甚至也成为文士的现实生活的常态。这种“痴”态人生混淆现实和理想,虽然有利于创作,但就其表现而言,却不能不说有其病态成分。而且,对审美化生活方式的主动选择,虽易于产生高质量的传世之作,但就伟大作品的产生而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深刻思考毕竟也是其重要的创造源头。过于追求审美化的生活方式而轻忽现实社会生活,必然造成对文学源头的斫伤。
前面,我们讨论了“痴”与“玄学”传统及文化病理等的关系问题,而从更为全面、系统的文化眼光看,以“痴”为名的魏晋社会文化现象,往往相互胶着,实际呈现出更为复杂多面的情状:
首先,有些以“痴”著名的风流人物,也患有生理性或心理性“痴狂”疾病。如《世说新语·纰漏》记载,任育长早有声名,后因“失志”而致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失常,被王导视为“有情痴”;《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的罗友嗜于“乞食”之“痴”,明显属于心理变态行为;《世说新语·忿狷》记载王述吃“鸡子”不得,因此焦躁而举止“忿狷”失常,则由“五服散”之毒造成大脑指挥系统不灵,使动作反应迟钝所致。这些更多具有生理或心理病态的行为,也被时人目之以“痴”,却并不具有审美与文化价值。
其次,一些患有生理性“癫”“痴”病状的文化名人,也可能于其病状发作时伴生文化创作灵感。如《世说新语·轻诋》记载“王右军少时甚涩讷”,《晋书》本传云“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太平御览》引裴启《语林》记“王右军少重患,一二年辄发动,后答许掾诗,忽复恶中得二十字,云……既醒,左右诵之,读竟,乃叹曰:‘颠何预盛德事耶?’”[1]3280王羲之在“癫”病发作时,居然产生创作灵感,自可作为文学创作成功的特例,但就其行为本身而言,并非意识明确、理智清醒,与“痴狂”疾更近。
再次,“痴”也被使用于通常意义层面。如《世说新语·方正》记载,王述抱怨坦之“畏桓温面”,而许之以婚姻,违反门阀与“兵”不相通婚之规,“已复痴”;同书《纰漏》记载谢据上屋熏鼠,以其“痴”行成为时人笑柄,连其子谢朗也因不知情而戏笑“痴人有作此者”;《晋书·慕容超载记》引谚语“妍皮不裹痴骨”等;至于杨济《又与傅咸书》劝诫对“官事”过于执著、认真的傅咸,应该“痴了官事”,“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以游戏官场之“痴”为快慰,虽折射了魏晋时代对于“官事”所持的较普遍心态,但也是在通常意义上使用“痴”的。
可见,只有从有机整体层面,全面、系统研究“痴”与魏晋文化的关系,庶可避免认知及评价的模糊、偏颇、片面之弊。
四、余论
本文前三部分,主要通过全面考索“痴”的文化语义及其在魏晋时代的使用情况,揭示“痴”与“早慧”文化、“痴”与审美“移情”及审美化生活方式追求、“痴”与“玄学”传统及文化病理等的内在有机联系,认为“痴”在魏晋时代被用来指称大器晚成的异量之美,表现浑忘形骸、专注通“神”的审美境界与所谓“痴”气人生,指称朴拙、厚重、深沉、稳健、大智若愚的人生修养、功夫、境界,以及作为病态时代的病态之“花”等,多方体现、折射了魏晋文化智能、人格理想、浪漫气质、艺术情调、哲人深致与“病”理色彩,具有重要的审美与文化认知价值。此外,如下三点需要予以特别强调:
其一,魏晋之“痴”具有丰厚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并对魏晋时代的文化、文学艺术创作具有直接而强烈的影响。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痴”其实主要代表了魏晋艺术家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时的高度紧张、集中、凝练的精神状态,催生了不少精纯的文化艺术产品,如阮籍能够独悟“咏怀”,以音乐进入“达庄”境界,以目击道存创为《大人先生传》,顾恺之灵妙通神的绘画创作等,也可以说是“痴”的结晶。以“痴”的精神状态进入艺术创作者所专注、思考和体悟的精神界域,打破人与世界的天然隔阂,沉迷于作者所思考、体察、感知的对象,而达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齐一”的物我两忘之境,创造出卓然独立、风格独具、涵容广大的文学艺术作品,正是“痴”的力量的延续与作用的过程,也是“痴”的精神逐步挥发与弥散的过程。这一过程凝聚和保留于作者所留下的文化作品之中,而被后人所领会和感知。
其二,魏晋时代对“痴”的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认知,在相当程度上规范、影响了后世对有关“痴”的审美与文化价值意蕴的认知,有许多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有益养分,深远持久地滋润着民族文化精神,对于后世文士的理想人格塑造、文化艺术生活以及文学艺术创作,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我们从后世的大批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陶潜、张旭、李白、怀素、柳永、苏轼、米芾、王守仁、李贽、徐渭、袁宏道、汤显祖、金圣叹、傅山、朱耷、李渔、蒲松龄、郑燮等人身上,都能直接而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痴”的精神正是通过他们而得以绵延不绝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小说巨匠曹雪芹最得表现、折射魏晋风度、魏晋文化精神之“痴”的神髓,他自许“慕阮(籍)”,自述《红楼梦》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其全部人生的“辛酸泪”写出了一部巨大的“痴”人说“梦”书,可谓深得“三昧”至真。如“顽石”宝玉患有一种不可救药的“痴病”,“颦儿”黛玉几乎有着无处、无时不在之“痴”,至于其他众多人物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的“痴”相、“痴”态、“痴”情、“痴”精神、“痴”境界,都令我们想到魏晋之“痴”的方方面面。而《红楼梦》中所透露出的时代的病态与人物的病态特征,也与魏晋之“痴”所折射的文化与时代的病态倾向悄然相似。
其三,魏晋之“痴”与西方“酒神”精神说和审美“移情”说颇多相近之处。这说明,尽管时空条件不尽相同,人类的文化是共通的。这是各种异质文化能够对话、交流、融合的必要前提。但与西方“酒神”精神说和审美“移情”说相比较,“痴”具有更为宽广多面的、互补圆融的审美与文化价值蕴涵,为人们的解读与发挥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因为联想与想象的展开程度,有赖于意义的解释空间。而思维是否具有创造力,每取决于联想之有无及丰富与否。相对于现代实证科学的精确、明晰甚至单一,就思力的大气与文明开新的生命力而言,“痴”所显示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自有其优势方面。至于“痴”所表现的潜文化、潜美学命题的泛化,语义指涉的感性、模糊、混沌、多趋向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华民族思维模式的潜在缺陷。
[1]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王利器.文子疏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裴松之.三国志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严可均.全三国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I206.2
A
1000-2359(2010)06-0171-06
刘志伟(1962-),男,甘肃通渭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2010-08-20
[责任编辑 海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