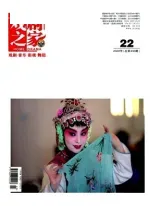浅谈汉族秧歌舞蹈与现代审美意识
□翁蓓俊
一、秧歌舞蹈的现代步伐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又能够敏锐地反映特定时代的审美意识。
过去,汉族秧歌的活动主要是在农村,而且各种组织与活动都带有浓郁的小农经济与封建宗教色彩。其组织形式是家长制的因袭,由族长或有威望的人充当会首,出面组织各项活动,活动的时间是依据农时,活动目的是顺其自然、祈天赐福、求安定与最低水平的温饱。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社会给舞蹈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舞蹈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具有突破性发展的里程。广泛流传在民间的秧歌舞蹈经过舞蹈艺术家的收集、整理,在编创一些具有代表性作品的同时,以一种舞蹈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教学的课堂,力图形成规范的民间舞蹈教学体系。其中优秀的舞蹈组合有《过街楼》、《逗蛐蛐》、《鬼扯腿》、《熬鸡汤》等。这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舞蹈组合,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民间舞传统组合”。的确,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有着经得起岁月考验的鲜明特征。如《过街楼》以传情为目的,通过每一个眼神和动作,将恋爱中姑娘的心理表述得淋漓尽致,却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这个教学的舞蹈组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训练价值。然而,这种“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却多少缺乏些现代意识,必然会在未来的发展中被突破。
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对艺术本质的认识是需要过程的,所以人们在返回人本身之前,首先扑向大自然的怀抱。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开始用舞蹈表现自然美,编导们创作出一系列模仿动物动态的舞蹈作品,如:《鹰》、《白鹤》、《金色小鹿》、《金蛇狂舞》等。但是,这类作品的创作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人们终于认识到,舞蹈应该表现人,表现人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系列以“讲故事”、描述情节为主的作品,并很快风靡全国的艺术舞台,如《月牙五更》、《看秧歌》、《元霄夜》等。这些作品可以说是让观众彻底“看懂”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存有一种喜欢“听故事”的审美欣赏习惯,经常以能否“看懂”来评价舞蹈作品的好坏,而此类作品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欣赏习惯。然而,“讲故事”的编舞手法,在对人的生活细节描绘的同时,掩盖了人的生命的内在律动。人的生命力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现——舞蹈艺术的最本质的韵味,依然沉默着。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的全面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解放。在国内人文主义思潮和国外“寻根热”的影响下,汉族秧歌舞蹈艺术创作开始了向本位文化“寻根”、向人自身回归的创作阶段。这是一个令人激动、振奋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张继刚的一系列舞蹈作品为代表。他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发现和感知着时代的脉搏与审美意识的转向。他突破以往“讲故事”的形式,开始用大色块、长线条结构舞蹈。在对中国这既有古代辉煌文明,又有近代落后挨打屈辱地位的历史,进行民族性与人性的透析,并以此为基础,在前人给后人的巨大遗产中,挖掘出熠熠生辉的精华,以宏扬民族精神和增强民族自信心。这些心灵的感悟,通过《黄土黄》、《俺从黄河来》、《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走西口》等作品加以表现,准确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可杀而不可辱的民族气概,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秧歌舞蹈的审美变化
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带来的审美欣赏方面的变化对秧歌舞蹈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产生这种影响的是西方芭蕾舞传入中国。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审美对圆形美的追求,人们的审美意识显然走向了多样化。在造型上不再以圆型线条为最美,而是追求棱角分明,开始喜欢长线条。
在舞蹈训练过程中,教师一再要求学生,将腿伸到最长,将手举到最高。舞蹈学生的选拔,对身体的结构比例,要求越来越高。下身比上身长15公分以上的学生更受欢迎,而且对女生身高的要求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芭蕾舞对汉族秧歌舞蹈最突出的影响是蹦脚面动作,这是加长线条的典型手段。即使中国戏曲,也受到了这种审美追求的影响,其程式化动作的线条也明显地有所加长,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秧歌舞蹈有其特定的风格,失去了这种风格就不再是秧歌舞蹈,但是一味因循守旧又会失去观众。所以,编导者为了创新,在不改变其主体风格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让观众耳目一新。这一现代意识上对艺术效果的追求,使编创者在创作过程中,改变了动作的单一性和重复性。一个动作元素,不再按照秧歌舞蹈的习惯那样,多遍重复,在舞台一点做四次,转到舞台六点再做四次;而是一个动作最多重复两次便开始转做其他动作。如果动作需要多次重复,在其中必然有所变化,或是加入对比性动作,或是对所使用的基本动作进行向度、力度、幅度上的调整,使动作发展的内在逻辑呈现出多种可能性,打破传统秧歌舞蹈动作变化的“可预期性”的美学原则,一反观众对动作变化的心理期待,从而使观众在观赏时感到变化莫测的新奇。
动作幅度的加大,是秧歌舞蹈现代意识的又一个鲜明表现。加大动作幅度的原因是为了增强秧歌舞蹈的表现力,使其更能适应现代舞蹈者的内心体验和意境追求。舞蹈是人类心灵的表达,原始秧歌舞蹈素材可以是创作的基础,它只是为创作者主观世界的表达而服务。当舞蹈创作向人回归的同时,必然引起秧歌舞蹈动作的某种程度的变形。它似乎不像原来的样子,失去了所谓“原汁原味”,但它更具有舞蹈特性,更具有艺术性,也更具有现代审美意识。比如《扇妞》这一作品,脚下重心的移动,除脚底滚步外,都要求动作加大幅度。脚底的“重心”移动,常常打破动作本身的原始规范,要求演员在能够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尽可能将动作做到最大程度,表现出现代人对自由的追求。这种加大幅度的动作,才能承受情感的迸发和内心生命之流的巨大冲力。“重心”一词与对“重心移动”的讲究,在中国民间舞蹈中是没有的,是从西方现代舞中借鉴的。西方现代舞与中国传统舞蹈的相融,无疑是秧歌舞蹈现代审美意识的一个突出表现。
秧歌舞蹈的现代性还表现在节奏变化上。节奏,是时间性的概念,对节奏的理解与运用并不是单纯的节拍运用,并非仅是3/4、2/4、4/4的概念。特别是现代音乐,从外形上,是没有节拍规律可寻的,在一般音乐里是由不同的节奏型来共同组成,同时,由不同节奏型时间上的各种差异、不和谐融汇成新的一种和谐状态。这种不平衡的和谐恰恰是现代音乐与古典音乐最根本的差别。现代音乐的内部结构呈现出的这种节奏型的立体交叉网,是人们处于信息爆炸时代,在思想、审美、情感、观念等意识形态的飞速变化下所产生的一种必然。人们不再以传统的是非对错来简单地评判一种事物的存在,尤其是思想意识层面的艺术。我们更不会再用“这个是不对的”来看待一个新的艺术现象。那种不和谐节奏型音乐的存在,好像是在对传统说:“在这个新的时代,让我们并存吧!”
秧歌舞蹈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叛逆者”,如《扇妞》这一舞蹈作品,在动作与节奏的安排处理上,就如同现代音乐与古典音乐两者节奏之间的碰撞,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扇妞》选用的还是传统的中国民乐,音乐的旋律还是民间小调式,节拍上,还保留原有的规整性,但在舞蹈中,动作节奏的使用上已打破了原有音乐中节奏的规整性,以舞蹈作品中二个八拍为一乐句来剖析:首先,同一乐句的二个八拍中,动作使用的节奏是无规律可寻的,先看第一个八拍:其中第二拍是动作的最大发力点,第五拍则是这一组动作的最低落点,余下的三拍却重新改变同前五拍不同时值的节奏。再来看第二个八拍:又以许多不同第一个八拍的处理方法来完成八拍的动作。其中第三拍的后半拍是动作的最大发力点,而把动作的最低点放在第七拍。从这二个八拍节奏的运用分析中人们看到,舞蹈作品不仅很好地使用了空拍和切分,而且改变了动作的连接变化,只在弱拍时变动的节奏结构被打破。其次,这种节奏的多重处理法使作品就动作而言打破了原有的课堂训练组合的规整性,加强了舞蹈动作变化的莫测性,这是现今新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现代意识较强的舞蹈编导,往往是先创作主干动作和作品结构,然后再配制音乐,让音乐只起背景和烘托气氛的作用。人们关注的不再是音乐的节奏,而是舞蹈本身的节奏。有些舞蹈动作甚至可以不合音乐节奏。这样一来,舞蹈可以摆脱音乐的限制,编创和表演过程就更加自由,更富于变化。对观众而言,会更注意舞蹈本身。
三、结论
随着世界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影响,世界文化在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作用下,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趋同性,这是一种客观趋势。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隔离和封闭,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拒绝与世界文化的交融,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中国汉民族的秧歌舞蹈正是在这种大趋势下,在迎接挑战和表现主体个性的过程中,向世人们呈现出自己的现代审美意识。这种现代审美意识,正是中国汉族秧歌舞蹈走向世界,与异域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前提。只有走向世界,拥有现代审美意识,才能最好地保持具有深层文化底蕴的中华传统,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我们每一个舞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