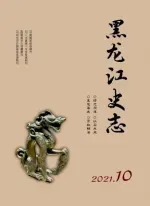浅析秦汉教育对中国后世的影响
赵长欣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浅析秦汉教育对中国后世的影响
赵长欣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些主要特点,都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秦代教育“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汉代教育则体现出大一统的特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经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模式以及教育思想的儒学化,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 教育 中国 后世 影响
秦汉时期的教育史,尽管只是中国悠久教育史的一个阶段,但由于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成型时期,几乎包含了封建社会教育的所有特征,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其对后世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文教政策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有崇尚法刑的传统。战国中期,商鞅变法,倡导刑名之学,提出设官置吏为天下师的主张,认为“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1)。韩非承袭了商鞅的思想,斥私学“乱上反世”,明确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并提,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2)。这样,“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作为与秦国基本国策相一致的文教政策,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实施法教、吏师制度的条件逐渐成熟。为了巩固商人地主的统治,镇压农民可能的反抗以及残余贵族可能的叛乱,于是,高压的强制促进统一的政令纷纷出台。在意识形态领域,秦始皇下令废除诸子百家,将法家思想作为官方的唯一意识形态。在崇尚法刑的社会背景下,秦代“以法为教”,禁私学“以吏为师”;法家以外的经典,均禁止传播;将百家争鸣的局面扼杀在独尊法家的屠刀之下,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先河。
秦代虽然只存在了15年,但秦代专制主义的的文教政策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更痛切断言:“两千年之政,秦政也”(3)。秦代专制主义的文教政策,均为后世帝王不同程度的加以承袭。尤其是后代对教育、读书人的控制,都可视为秦代文教政策的余孽。
不管怎样,秦代教育与其前的战国及其后的汉代均有所不同,它以稳固中央集权的统一为前提,将教育纳入到崇尚法刑的轨道上,不允许其他教育思想存在。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教育为封建统治服务,在秦代教育中已有充分的体现。
汉代是中央封建集权制度继续发展的时期。在文教政策上,汉代汲取了秦亡的教训,承袭秦制,但多有变通。大致说来,汉代的文教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杂霸”阶段,倚重黄老之学;二是“罢黜百家”阶段,独尊儒术。值得一提的是,秦汉同是“定于一尊”,但是汉代的“儒术独尊”远比秦代的“崇法尚刑”宽松。
汉代初年,如何确立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新政权面临的重大课题。卓越的思想家陆贾建议推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被高祖采纳。为了适应初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需要,黄老学派提倡重智、重学,对于恢复遭受秦朝严重破坏的文教事业,尽快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它提倡无为﹑放任,虽然使老百姓得到了修养生息,但同时也纵容了诸侯王的骄恣不法。七国之乱,宣告了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破产,促使一代英主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汉代的三大文教政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其首要目的在于借儒学独尊来保证政治的“大一统”。董仲舒在《对策三》中明确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4)。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用“独尊儒术”来统一思想,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而“兴太学,置明师”,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董仲舒认为,行教化必须兴办学校,通过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去推动教化,在《对策三》中他指出:“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5)。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要在京师兴办太学,将过去举贤养士的遗风,纳入到王权的控制之下。所以,太学的设置实际上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而“重选举,广取士”,养士与取士并重,是“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仍然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董仲舒是始作俑者。
儒家德治论的核心是“以教为本”,它从统治政策的高度论证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并以三纲五常这类道德规范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独尊儒术不仅是地主阶级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措施,也是对“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有力批判,从而将教育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地位。在这一政策的直接推动下,汉代设学校、广育人才,确立了我国封建官学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传统教育的发展。自此以后,教育逐渐被社会公认为“为政之首”,使我国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但是为了加强思想统治而独尊儒术,限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
二、太学的教学及管理模式和博士的设置
汉初官僚基本上来源于世袭,捐资及察举,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易造成官僚结构的混乱和官员素质的低下。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不仅把太学看作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也把它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及官僚选拔的基地。为了培养和造就大批人才,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设立了太学。汉代太学的兴办,得力于两个儒家学者,一个是董仲舒献策于前,一个是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后。汉代太学的教学与管理模式,严于择师的传统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汉代太学是我国古代第一所具有相对完备的规章制度,史实详尽可考的学校。自从汉代创立至清末,历代的最高学府大多被称为太学,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其次,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始于汉代的太学。汉武帝“罢黜百家”后,立“五经”博士,他们都是精通儒学的经师。而太学生学习一年,通过考核后就可以入仕的规定,使得政府直接控制了受教育者的政治前途,并就此确立了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两千年不变的性质——培养国家后备官僚。五经博士的设立和经学考试法的强化,使太学成为官僚体系的附属机构。
再者,汉代太学的考试制度使“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制度化。政府从太学中选择成绩较优的学生授予官职,以充实封建统治机构,比起“任人唯亲”的世卿世袭制度要好一些;可如此以来就把读书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读书做官”的狭小通道上,“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不利于思想和学术文化的发展。这种“读书做官”的教育目的论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
第四,汉代太学的教学以老师的讲授和学生的自学为主,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义是重要的教学形式。但是问难、讨论的内容是不能脱离儒家思想范围的。官方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和评判标准,使得教学过程中师生只注重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记诵,学生将各类儒家经典烂熟于心,成为进入官僚阶层的先决条件。它不仅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也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第五,汉代兴建太学善待天下之士,建构了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组成的“士—官僚”文官行政制度,成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支柱,对封建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秦汉设置博士,在中国教育史上亦有其意义。博士一职始见于战国时期。《宋书·百官志》:“六国往往有博士。”秦代沿袭六国之制。《史记》记载有(秦)“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之语,秦博士显然为闲职。秦代“以吏为师”,但吏不一定都为师,这些谙熟诗书的博士,可能会教授生徒。比如,曾经为汉高祖制定朝仪的叔孙通,本是秦博士,在降汉时,“从弟子百余人”(6),说明他在秦时就聚徒讲学。虽然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博士是秦代的教育官,但他们在文化教育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被视为古代文化的特殊载体。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是“国有疑事”仍应“掌承问对”,可见汉代博士是过问政治的。两汉挑选博士非常慎重严格,博士必须德才兼备,不仅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还必须具有足以胜任博士职责的专经训练和相当的教学经验。经过严格挑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儒宗学者。这对于后世学校尤其是太学的教师选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三、教育制度
汉代儒生根据《周礼》所载,对汉代的学制进行了具体规划。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官学又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官学。官学系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太学,为全国学校的典范;二是鸿都门学,为专门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三是专为皇室和外戚设置的宫邸学。地方官学有学、校、庠、序等。私学可分为经馆与书馆。由经师讲授专经的经馆,也称“精舍”、“精庐”,其程度相当于太学;书馆只教授读、写等基础知识,有启蒙教育的性质。
和官学相比,汉代私学有很多特点。私学由学者自办于民间,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学术色彩比较浓厚等,汉代私学教育可以说是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汉代官学系统中启蒙教育匮乏,私学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蒙童教育。官学讲经,以今文为限;而古文经,甚至黄老、道、法、刑名等学,均靠私学教育得以传播和发展。汉代私学还特别重视气节的培养,不少人不畏强权,不慕禄位,誓死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敢于批判社会现实,这种优良传统在后世书院教育中得到进一步发扬。汉代教育管理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劳赐,二是视学。劳赐是赐给师生实物或者酒肉,这是一种激励手段,用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视学是指皇帝亲临太学或者指定要员来太学视察,这就是后世视学制度产生的渊源。
汉代建立学校教育制度之始,官学即为国家选士的一个途径。汉代太学生完成学业之后,即可根据考试的等级名次获得相应的官职,而地方官学和私学出身的人,则通过郡国察举或者朝廷直接征召的途径做官。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国家通过考试录用的形式将选举权牢牢控制在了中央政府。
四、教育内容和方法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就成为读书人学习研究的主要对象。教育内容经历了由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到新“六艺”(即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演变,也就是由重视行为技能的训练到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汉代统治者用儒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也都以儒学为基本内容,儒家经学与古代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7);“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8);经籍的学习完全以读书为基础。书读得的多,读的好,不仅是学问的象征,也是获取功名利禄的必由之路。读书成为教育活动的最基本形式和方法,均肇始于汉代。
这种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读书为主的教育方法,自汉代至清末,未有改观。从西汉以来,对于这种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批评不绝于耳,西汉时大夫指责儒生“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9),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清代颜元指责官方正统教育是“率天下人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之人”(10)。
五、教育思想
秦汉时期的教育思想经过了由秦代以法为教、中经汉初黄老教育思想,再到武帝时独尊儒术,与当时政治的发展演变基本是合拍的。秦汉教育作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成型时期,其教育思想是颇为丰富的。
论及秦汉的教育思想,首推董仲舒。他不仅把培养和选拔人才结合起来,而且养士、选士均以儒家学说作为准绳,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儒家与仕途的紧密结合,从汉代开始。
董仲舒的“性三品”思想,不仅论证了他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也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同时,它也为最高皇权的神圣化,专制统治的绝对化和权力的永恒化找到了理论根据。
另外,董仲舒的重义轻利思想建立了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命题:“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封建教育本质上是道德教育,尽管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但是先秦儒家的思想以及董仲舒的重义轻利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代以来,反封建的思想家们,都把董仲舒的提议和汉武帝的决策视为封建专制思想的典型。但是,时过境迁,如果以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决策,我们也许会多一份“同情性理解”。与其“百家殊方”,“上亡以持一统”,使天下重回春秋战国的战乱局面,那么“罢黜百家”也许就是当时的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选择。从公元前124年设立太学开始,汉代的学制系统几经完备,一直为后世所沿用,直到清末,才基本上形成了新式教育制度,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它的渊源。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就成为了古代学校的唯一的必修课。尽管后来屡次遭到人们的抨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继承儒家文化的精华太少,汲取的糟粕太多,这是很让人痛心的问题。中国古代早就有重视教育的思想和优良传统,在当今这个世界,教育更是重中之重!所以,面对未来,我们任重道远,我们的教育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解决,否则,我们将难以更好的立足于世界的东方。
注释:
(1)《商君书·慎法》。
(2)《韩非子·五蠹》。
(3)《仁学》。
(4)(5)《汉书·董仲舒传》。
(6)《汉书·叔孙通传》。
(7)《潜夫论·赞学》。
(8)《朱文公文集》。
(9)《盐铁论》。
(10)《朱子语类评》。
[1]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2]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俞启定《先秦两汉儒家教育》齐鲁书社.
[4]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5]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
[6]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7]郑师渠龚书铎《中国文化通史秦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长欣,女,河南南阳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