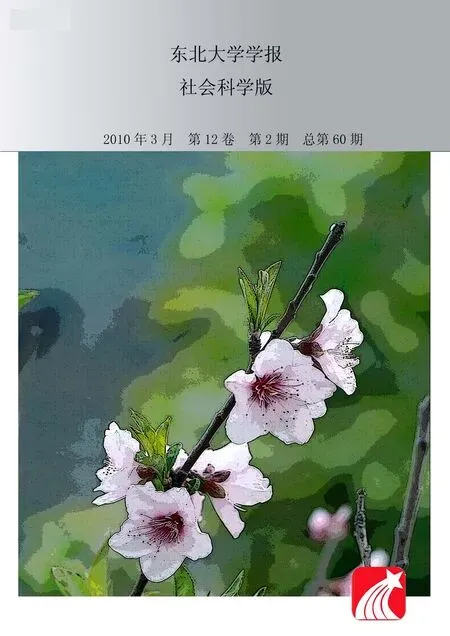划界与跨界:空间批评视阈下的《郊区佛爷》
尹 锐
(1.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2.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 1954 )是拉什迪(Salman Rushdie)之后英国文坛的又一位重要亚裔作家。恰尔兹(Peter Childs)在《当代小说家》(ContemporaryNovelists, 2005)中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国小说进行了梳理,选出12位杰出代表,库雷西的名字赫然在列。与拉什迪不同,库雷西出生于英国,父亲是巴基斯坦移民,母亲则是英国人。外国学者对他的研究开展较早,迄今至少已有摩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等人的4部专著问世,相关论文也经常见诸于各类文集或期刊。尽管以《郊区佛爷》(TheBuddhaofSuburbia,1990)为首的作品已在国内陆续出版,《外国文艺》、《译林》、《外国文学》等期刊也发表过相关的译介与评论,但目前库雷西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空间问题在库雷西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中直接以空间或地点名词为题的有:《郊区》(Outskirt, 1981)、《界线》(Borderline, 1981)、《我美丽的洗衣店》(MyBeautifulLaunderette,1985)、《郊区佛爷》、《我受不了伦敦》(LondonKillsMe, 1991);间接体现空间或以空间为隐喻的有《候鸟》(BirdsofPassage, 1983)、《萨米和罗西上床》(SammyandRosieGetLaid, 1988)、《亲密》(Intimacy, 1998)、《与我同眠》(SleepwithMe, 1999)、《身体》(TheBody, 2002)、《我的耳朵在他的心旁》(MyEaratHisHeart, 2004)。《郊区佛爷》原名为《我内心的街道》(TheStreetsofMyHeart)[1],经过这一改动后,小说的空间特色不仅得到了保留,而且显得愈发鲜明。纵观英美学界现有对于《郊区佛爷》的研究,从空间批评出发的较少且都集中于伦敦的描写上。显而易见的是,小说中的空间环境并非只是故事情节发生的地点或叙事的背景,它们应该被当做是社会文化、种族、阶级乃至性别的场域来看待,是具有多重意义的多维存在。本文试以“划界”与“跨界”为核心议题,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结合“另类空间”和“异托邦”的概念,以及后殖民文化研究的有关内容,对《郊区佛爷》中的空间问题进行解读。
一、 划界的郊区
《郊区佛爷》全书分为“郊区”和“城市”两部,这样的布局谋篇空间意味明显,两部分在形式上又形成了对照与并置。“郊区”指的是伦敦南郊,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二代移民,库雷西对郊区可谓又爱又恨。郊区一方面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写作素材;另一方面也给他的内心带来了耻辱和重压。他曾宣称:“我写作并成为作家,就是为了离开郊区。”[2]13库雷西为什么会对郊区怀有如此复杂的情愫呢?这与移民在郊区的境遇不无关联。大英帝国曾经幅员辽阔,殖民地遍及全球;二战后其政治、经济实力迅速萎缩,前殖民地纷纷独立。英政府因重建需要从南亚、西印度群岛等地引进大批劳工;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人民为躲避动乱和摆脱贫困纷纷投入殖民母国的怀抱,大批有色人种涌入以伦敦为首的大城市。多数移民实际上并未进入伦敦的中心,他们主要分布在大伦敦地区,包括泰晤士河以南的郊区。郊区位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处在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交汇之处,其空间与文化上的“间隙性”(in-betweenness)就是移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郊区在库雷西笔下是一个界线分明的场所,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白人权力的偏执与蛮横。白人女孩海伦的父亲直接对主人公克里姆说:“我们不欢迎黑鬼来我家”,“无论黑鬼干什么,我们都不喜欢。我们只和白人来往”[3]61。迈克·克朗认为,人们总是会创造有疆界的地域,并通过对这一排他性的领土的控制来定义和保卫自己[4]103。划界的郊区所展现的,正是帝国分崩离析后仍阴魂不散的白人优越感。以海伦父亲为代表的郊区居民死抱着白人中心论不放,将“黑皮肤”的移民排除在自己空间之外,他们对于有色人种的恐惧恰好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在库雷西看来,郊区文化“观念上的狭隘和对于不同事物的害怕”体现了英国的文化价值观,因为“英国主要是个郊区的国家”[2]170。的确,“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是借助包含道德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地理范畴来发挥影响的”[4]33,一道道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的界线让克里姆感到紧张疲倦,如小说数次提到的保暖“双层玻璃”一样,把郊区的人们隔绝开来,让他们始终处在猜忌与误解之中。
克里姆的家空间狭小而阴暗,因此他对白人中产阶级的家宅羡慕不已,“房子的草地上都有温室、大橡树和洒水器;人们在花园干园艺”,看着这些就像在看“一场演中产阶层的戏”[3]44。他这样描述自己和弟弟在姨妈家的感受:“我们走着,想象着我们住在这儿该是多么快乐。我们会怎样装修屋子,修整好花园,打打板球、羽毛球和乒乓球。”[3]44英国作家对花园的钟情,“部分地根源于他们的民族性”[5]。因此,花园往往被用以象征英国民族性中最本质的部分。克里姆对于白人家宅及花园的艳羡,就是源于他对于英国性(Englishness)的想象,是他内心渴望得到归属的表现。另一方面,从文化地理学上讲,“不同空间内的活动被赋予不同的地位和经济价值”[4]26,家宅作为文化地理景观的一部分,其所在区域、结构分布是受到地位、经济因素影响的。在郊区,家宅的划分代表着不同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花园则象征着社会地位与财富水平。克里姆家的居住条件并不是最差的,贫民区的情形更加触目惊心,放眼望去,尽是“即将成排倒下的维多利亚式房屋”,“洗好的衣物一排排胡乱晾在残垣断壁上”[3]65。从家宅层面上来看,郊区各阶层的划分似乎更加明显,人们按照肤色的深浅被安置到了不同的区域,住着等级不一的家宅。这样的划分方式既是空间的,又是种族与阶级的,三者紧密关联并互相影响。
二、 跨界的伦敦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另类空间》中使用了“异托邦”(heterotopias)的概念。他认为人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的空间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布满各种性质, 一个可能同样被幻觉所萦绕着的空间中”[6]。梅西(Doreen Massey)则在福柯基础之上提出了“另类空间观”与“权力几何学”,指出空间的本质充满权力与象征意义[7]。无论是“异托邦”、“另类空间观”,还是苏贾(Edward W. Soja)和巴巴(Homi Bhabha)的“第三空间”,都在强调空间的异质性,而想要获得这种不可预见的体验,就要跨越空间的界线,把不同的事物混在一起。《郊区佛爷》中的伦敦,就是这样一个“另类空间”。在这里,用以区分种族肤色的黑/白、表达阶级观念的上层/下层甚至包括男/女这样的二元对立全都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难以厘清、斑驳混杂、具有流动性和颠覆性的身份构建。
为了“继续一段进入伦敦的旅程”[3]151,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克里姆离开了死气沉沉的郊区,来到了五光十色的伦敦市区。对克里姆来说,“伦敦就像一所有五千个房间的大宅,每间都不一样;最刺激之处在于去发现它们是如何连通的,最后走遍所有房间”[3]187。“置身于一个如此明亮、快速和灿烂的地方”[3]186,他感到眩晕与茫然,不知该如何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从边缘地带来到帝国的中心,克里姆期待能够摆脱种种束缚与限制,在伦敦这个舞台上大展拳脚。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所面临的是如何演绎“地道”印度的难题。克里姆被选中在戏剧《丛林之书》中出演莫格利是因为他很“地道”。不仅如此,他还被要求发出“地道”的印度腔的英语。克里姆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有印度血统却从未到过印度;他了解接触印度,都是通过父亲和其他移民,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拿捏这种口音。导演对印度的一知半解和选择克里姆作为“地道”印度的代言人,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思想,也是白人权力在伦敦这个另类空间的直接体现。广义的身份包括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上层身份能带来“资源、自由、空间、舒适、时间”[8]。为了受人关注,克里姆不惜模仿乃至“伪装”成印度人,出卖并非地道的异国风情,他因此得到了大导演派克的青睐,获得了另一个出演有“黑人”背景角色的机会。在小说结尾处,他又将在反映堕胎与种族冲突的肥皂剧中出演一个印度店主的儿子。克里姆的演艺生涯,既是一种身份构建,也是一种空间构建。用李有成(Lee Yu-cheng)的话说,他是在为争取新的再现权,采用所谓“地道”的身份来“建构一个可以呈现社会问题的批判空间”,“在各种抗争对立的喧嚣当中,道地特质也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可供强势与弱势族群双方协商文化属性的交会场所”[9]。
鲍尔(John Clement Ball)指出,虽然《郊区佛爷》并非一部后现代小说,但其中展现的伦敦却具有后现代特色,从郊区到市中心的迁徙就是一场“进入后现代空间的旅行”[10]。的确,小说里的伦敦是一个“无深度”的空间,这样的空间里充斥着表演、模仿、含混与各种界线的消失。贩卖异国风情的并非只有克里姆一人,他的父亲哈龙靠着自己对东方哲学与佛教思想的肤浅了解,出没于白人的社交场所,为陷入精神危机的白人们排忧解难,成为了“郊区佛爷”。哈龙的情妇伊娃凭借自己超强的社交能力成功打入伦敦的文化界,并通过买卖房产发家致富。伊娃的儿子查理则依赖自己的音乐天赋和对潮流的模仿,一跃成了歌星“查理英雄”。在伦敦这个大都市里,他们都在实践着各种各样的越界行为,伦敦成为了他们的“新领地”,一个如游乐场般炫目变幻的场所。克里姆、哈龙、伊娃还有查理,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体验着这个跨界空间带来的非凡感受,或用自己的身体或用语言及其他天赋对伦敦空间进行探索。他们进入帝国的中心并重新界定其边界,使原有空间变得混杂,以此证明并强调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占领与拥有。不管是移民还是来自郊区的中下阶层,都渗透、融合到伦敦的城市空间构建之中,并逐渐改变其原有的文化属性与意义。
三、 “无界”的纽约
在小说的第十七章,克里姆随派克的剧团来到了纽约,开始了他短暂的异国之行。事实上,纽约在小说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作为伦敦的参照物出现,让克里姆和伦敦在空间上拉开距离。他在纽约得以认清派克、伊琳诺、查理等人的真实面目;也正是在纽约令他开始怀念起伦敦。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写道:“我越是善于把世界缩影化,我就越能占有世界。”[11]如果说伦敦代表的是老迈的帝国瓦解后,各色人等杂居混合、向多元文化迈进的城市空间的话,那么纽约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象征的就是欣欣向荣的年轻资本主义强国。克里姆身处中央公园附近的大饭店之中,从第109层俯瞰纽约,他和他的同伴们感到“紧张不安”,“作为英国乡下人,心怀愤慨且害怕受到资本主义的玷污”[3]357。纽约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城市的典范,那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连来自英国的伦敦人都感到恐惧,说明二战后西方各国财富与实力有了新的分配模式,新超级大国的地位已另有所属,暗示着西方世界的中心已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无论英国人是否心甘情愿,这已经成了不可争辩的事实。
美国是“摆脱了欧洲幽闭症的自由之邦”,是崇尚流动性的新大陆[4]107。与强调传统、讲究出身的欧洲社会不同,美国社会推崇的是个人奋斗与经济上的成功。与划界的郊区、充满各色跨界的伦敦形成对比,纽约简直就是个“无界”的空间。在纽约似乎没有人会在意克里姆的米色肤色,而在郊区他被贴上“黑鬼”的标签,在伦敦他被要求演绎“地道”的印度。查理则是最能享受纽约所给予的自由与成功的人。尽管他的音乐缺乏特色,来到纽约后更是失去了以前的对抗性,他还是靠自己的英伦特色走红,吸引了“那些最有闲钱的人”[3]363。查理习惯于在纽约操着伦敦口音,甚至用伦敦音来给俚语押韵。对此,克里姆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在贩卖英国风尚”[3]364。福柯认为,“异托邦”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空间,是想象和虚幻的领域。他以殖民地为例来阐明其特征:先是渗透和模糊的殖民化,随着商品、语言、宗教、人民、习俗的迁移,殖民也就发生了[12]。与郊区和伦敦相比,纽约这个前殖民地土地上矗立起来的大都会更有资格被称为“异托邦”。凭借着贩卖英伦风情,查理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这个充满幻象的“异托邦”。虽然查理并非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他代表着伦敦,因为他是从前帝国的中心进入纽约的。与来自印度的哈龙、第二代移民克里姆以贩卖异国风情的方式进入伦敦空间形成鲜明对比,查理行进的路线象征着大英帝国的衰败和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是一种权力倒置的结果。为了名声和金钱查理不惜过着违心的生活,甚至还讥笑克里姆比他更像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太道貌岸然、太过于狭隘。故作优雅的英国文化输给了现实势利的美国文化,这是对虚构的帝国的荣光的莫大讽刺,也是对白人所一直鼓吹的“英国性”的无情嘲弄。
克里姆在纽约重新审视了自己和英国间的关系,认清了查理的虚伪本质,最终选择了回国。重新回到伦敦后,他发现一切变得既熟悉又陌生,“老旧的东西被新东西取代,而新东西却很丑陋”[3]379。小说结尾,克里姆请亲朋好友在昂贵的餐馆吃饭。围坐在他们中间,他感慨良多:“我坐在我深爱的这座古老城市的中央,而它本身便坐落在一座小岛的最低处”[3]417。萨义德(Edward Said)曾说过:“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条件。”[13]纽约之行让克里姆发现自己是如此深爱着伦敦这座城市,点燃了他内心对于文化家园的渴望,而这样的家园应该是没有界线的家园。尽管现实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未来还有太多的不可预知,克里姆最后还是在伦敦找到了家的感觉。
四、 结 语
在《郊区佛爷》中我们看到了划界的郊区,跨界的伦敦,还有“无界”的纽约。库雷西所呈现的是三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无论是郊区的界线分明、贫富悬殊,还是伦敦的另类与后现代,抑或是充满幻象、自由的纽约,这些空间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空间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一种政治性的构建。库雷西在英国少数族裔文坛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他之前有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塞尔文(Samuel Selvon)、拉明(George Lamming)等人,在他之后有阿里(Monica Ali)、史密斯(Zadie Smith)等女作家。以空间批评的视角来看待以库雷西为首的第二代移民后裔作家,审视他们作品中出现的各种空间,探究他们是如何书写诸如“划界”、“跨界”的议题,解读这些作家在后帝国时代的空间策略,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参考文献:
[1]Kaleta K C. Hanif Kureishi: Postcolonial Storyteller[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8:63.
[2]Kureishi H. Dreaming and Scheming: Reflections on Writing and Politics[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2.
[3]哈尼夫·库雷西. 郊区佛爷[M]. 师康,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4]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宋惠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张箭飞. 解读英国浪漫主义----从一个结构性的意象“花园”开始[J]. 外国文学评论, 2003(1):100-109.

[7]Massey D. Politics and Space/Time[M]∥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3:154.
[8]兰·德波顿. 身份的焦虑[M]. 陈广兴,南国治,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5.
[9]Lee Y C. Exploiting the Authentic: Cultural Politics in Hanif Kureishi’s The Buddha of Suburbia[J]. Euramerca, 1996:26(3):1-19.
[10]Ball J C. Imagining London: Postcolonial Fi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Metropol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233.
[11]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163.
[12]尚杰. 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16(3):18-24.
[13]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0:331-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