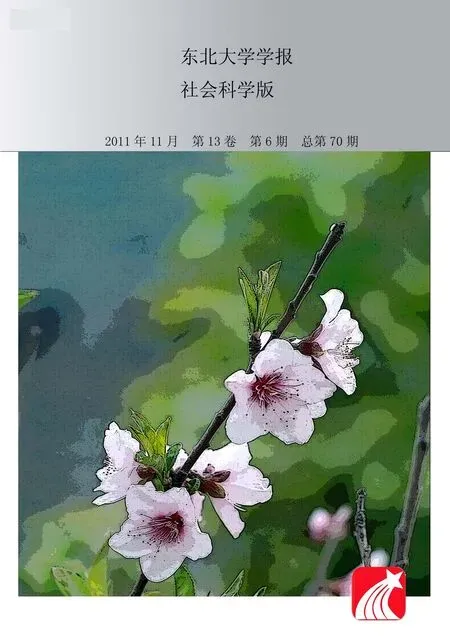哲学中的“语境”
----语境发展的三条路径及层面性分析
徐 杰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语境,顾名思义就是语言使用的环境。“语境是围绕我们所要理解的现象和为它的适当阐释提供方法的框架。”[1]49如马林诺夫斯基所举的例子:“我们到达村庄附近”(‘we arrive near the village’)这种表达非常清晰明白,而“we paddle in place”却只能在整个话语语境中来理解到底“in place”具体是什么地方[2]。在哲学中,将语境作为明确的范畴进行思考是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形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之前,哲学中并没有语境的思维。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论解释”篇中分析名词的意义时指出,名词必须放入与其他部分关联之中才具有意义,“所谓名词,我们是意指依据惯例的一种有意义的声音。它同时间无关,而且它的任何一部分要是离开了其他部分就没有意义了”[3]。对语言意义的研究一开始就是与语境联系在一起的。到中世纪哲学家那里,词语意义的考察会被放到不同命题背景中去。“语词不再作为与它们的语言上下文或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完全相分离的单位来研究。吸引着人们强烈兴趣的,毋宁说是语境本身。”[4]我们从三条主线来研究哲学中的语境:一是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境;二是语境主义流派中的语境思想;三是本体论角度的语境研究。
一、语境思维在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中的实践
对语言意义的思考,是当代西方哲学“意义----语境”框架下的语境思想研究的核心,并发展出了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和欧陆语言哲学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前者注重对语言意义和语言使用进行阐释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即一种知性思维;后者强调语言的非逻辑性、非工具性,尤其是语言对于人类生存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本体论意义。
1. 当代英美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学派)关注的“语内语境”
弗雷格是最早提出语境思想的哲学家,他认为只有当一个语词处于整个句子的语境中才具有意义。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认为“数”必须是在命题中,在与其他词语或物体的联系中才有意义,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数,也不存在抽象主观的数,只存在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的数的概念。数的意义是在和具体事物的联系中获取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句子的语境中的词才有意义,我们的问题成为:去界定有数词出现的语句的含义”[5]。弗雷格不是孤立地考察词项,而是遵循语境原则在包括这个词项的句子中来确定它的意义。在言说某个词语时,不是把词语当成他本身,而是把词语当成包含着它的原初背景来理解的。
日常语言哲学家如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丁、斯特劳森等和当代语用分析哲学家格莱斯、塞尔等,都认为对一个词语进行理解,必须将其置入更大的句子语境之中。他们普遍认为:第一,语言的意义或阐释比其本身或概念更重要;第二,对语言进行理解必须是出于更大或者更高级别的语境之中,无论是内部语篇语境还是外部社会文化语境,无论是心理认知语境还是客观语境;第三,对语言的意义进行探讨的基本条件是语言一定是在使用之中的语言,语言的意义在于用法,语言的用法取决于情景。从此之后,对语言意义的认识不再是过去的抽象的确定的终极观念了,而是转向处于语言具体使用过程中所存在着的动态的相对性了。
语境思想在后期维特根斯坦这里主要表现在“语言游戏说”和“意义即用法”这两个观点上:①针对前期“语言图象论”----试图建立一种与现实相区别的、理想的和封闭的语言观念,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认为语言的原始形式是和人类其他活动编织在一起的,语言并非独立于世界的一种抽象,而是从现实活动的具体情境中产生的,没有一种语言独立于语境而持有意义。②意义即用法。维特根斯坦指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6]。即语言的含义不在于其指称而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中也暗含了语境的思维。言语行为理论主要思想是“言就是行”、“说话就是做事”,即人们在说话时不只在说话,同时也在做事,是通过说话在做事。言语行为具有施为意义,也即是交往意义。交往意义受到说话人意图意向和语境的影响。“言语行为理论经常被称为支持的中心观点之一就是语境主义。”[7]奥斯丁指出:“说话的场合很重要,所使用的词在某种程度上要由它们被给定的或实际上已被在语言交际中说出的‘语境’来‘解释’。”[8]
2. 欧陆语言哲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存在本体论语境
在意义和语境的关系上,英美分析语言学派尤其是日常语言学派认为,意义主要是来自于人对语言的使用;语言的意义只能在语言使用之中的具体语境之下才具有一种相对的确定性;意义对语境具有一种依赖性,而语境对意义具有一种阐释性和限制性。在海德格尔看来,英美语言哲学先行设定了人、世界、语言、语境相互之间的一种分裂的关系,具有一种知性的认知思维,也就是说语言只是人认识世界的工具;意义是语言对世界的表达;语境也仅仅是语言内外,人的主观和世界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合成。这种将语言作为一种存在者的知性思维工具,并在生存中以知性的态度去寻求意义在语境之中所获得的确定性与明晰性。对意义、语境、语言的研究并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哲学思考和提问方式----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追问。就像传统形而上学关注存在者,而遮蔽了存在,使得对意义和语境的研究陷入一种源始性的脱落。
海德格尔从生存论角度来审视语言、意义和语境,给予了意义和语境以本体论性的地位。真正意义上的语境应该是从此在的生存性展开中构筑的语境。“倘若我们反过来使话语这种现象从原则上具有某种生存论环节的源始性和广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语言科学移植到存在论上更源始的基础之上。”[9]193海德格尔认为人总是生活在语言之中的,我们不能理解甚至想象语言外的世界,因为语言先在地为我们给出了世界。甚至我们言说世界都只能在语言的范围之内,“我们说话,并且从语言而来说话。我们所说的语言始终已经在我们之先了。我们只是一味地跟随语言而说”[10]。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语言自己言说,而不是人去言说。因此话语与此在的现身、领会在生存论意义上具有一样的源始性,此在在展开过程中,“可在解释中分环勾连的,更源始的可在话语中分环勾连。我们曾把这种可以加以分环勾连的东西称作意义。我们现在把话语的分环勾连中分成环节的东西本身称作含义整体。……如果话语是(此在)展开状态的源始生存论环节,那么话语也就一定从本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世界式的存在方式”[9]188。话语的环节----“话语的关于什么(话语所及的东西);话语之所云本身;传达和公布”[9]190----也就形成了意义的生存论语境,即此在对“在”的意义展开的源始语境。
以往的哲学具有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对知识的设定,还是对思维的探讨,乃至对真善美的哲学思考都会存在着一个终极的、永恒的、超越历史的本质倾向。在这种观念之中,对象具有了一种绝对性。而主体在对对象本质的探寻过程之中受到压制,只起到一种认识的作用,对事物本质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和作用。阐释学认为知识不是对象事物本质的镜像反映,也并非纯然客观的,知识是在对事物的理解过程中产生的,主体对事物的理解具有一种建构性。主体带着自己的历史语境参与到对事物的理解之中。在阐释过程之中,主体具有意向性,但是受到自身的主体语境的约束;被阐释对象具有自身的相对客观性和自主性,但是这种自主性是相对于理解主体的,语境会强迫文本向主体敞开自身,具有一种历史的开放性,产生无数的可能性;在语境和对象以及意义的生成过程之中,具有一种动态交互性和互相生成性。从而在时间上产生一种无限的可能性,呈现出一种未完成性;语境使得对对象的理解产生了一种相对性的倾向。
二、 语境主义哲学中的语境思想
由于哲学对语境的关注,语境的研究逐渐发展到哲学的各个派别,尤其是知识论,从而形成了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知识—语境”框架下的语境研究。知识论语境主义在知识论探讨中处于核心位置,索萨就说过:“语境主义从早期的‘相关选择论’到近期的重要出版物,主要是通过与怀疑主义的斗争,在知识论舞台上获得了核心的地位”[11]。语境主义是在奥斯丁的《他者思想》(OtherMinds)[12]和维特根斯坦的《关于确定性》(OnCertainty)[13]的思想中萌芽的,但是路易斯的《语言游戏中的记分》一文,真正将语境主义提到研究核心位置。现在活跃着的语境主义主要有路易斯(David Lewis)、科亨(Stewart Cohen)和蒂罗斯(Keith DeRose)等人所倡导的归因者(attributor)语境主义、乔恩霍桑(John Haw thorne)和斯坦利(Jason Stanley)的主体语境主义、瑞贝尔(Steven Rieber)的解释语境主义、巴克(Antonia Barke)的认知语境主义和格瑞克(John Greco)的德性语境主义等等。
语境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在试图运用语境思维对人类知识本身进行反思。语境主义的发展是伴随着与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论争而不断向前的。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从当代认识论到逻辑经验主义,人们都在为知识寻求一个普遍性基础,但是普遍性的知识论逐渐受到语境主义知识论的挑战。知识不是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普遍的和稳定的(即便是科学知识也不是对科学对象客观的反映),而是对具体语境下所呈现出的属性的描述。在语境主义者眼中并没有唯一的、绝对超越性的真理来统摄整个世界,“一个确定的有归属的知识句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不同的命题,这意味着存在有多种知识关系,而非一个”[14]。
在对知识的认知过程中,个体认知受到语境的影响:对事物的认知标准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即语境敏感性(语境主义承认认知的差异性,但不否认主体间通过语言达到互相的理解,即主体间性);同时作为语境主义知识观的社会维度,社会认知的语境强调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中处于形成之中的动态性知识,即知识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其真值性,而在于社会接受性。知识是在语境之中动态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语境对知识具有一种决定性,语境只是为知识提供一种可能性的场域,以达到主体之间开放的交互和理解。
三、 语境论的本体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哲学中的语境萌芽和发展,只是在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理解语境,知识论语境主义也主要是从认识论的层面揭示语境思维对人类世界知识的影响,而郭贵春等逐渐将语境研究推向了哲学本体。在郭贵春的语境本体论中,语境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本质:①语境是一种本体性的实在;②语境是人类思维和行为中的普遍性存在;③语境与世界对象普遍联系的动态性整体,它具有复杂的内在结构性[15]。
(1) 本体性
人对事物的观念涉及到意义的生成问题,因而语境对意义生产起着决定作用。但是这种语境不能是任意的语境,它是一种意义的顶级约定,具有不同主体之间的一致评价性。因此,起作用的语境一定是具有以本体论性为基础的约定性。“语境本体论性的实在性”和“约定性的相对性”,形成一种矛盾统一性。主体对实体本质的概括和认识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流变着的,即对事物不同的本体论态度是受到不同语境观的影响的。语境不同,对对象意义的界定就会存在很大不同。“语境本体论性的实在性”并非纯然形而上的,语境含有一种具体性:①时空上的具体性,保证对象时空转换中的指称和意义同一性。②语境可以是显在的也可以是隐在的,但是一定是存在着的。③语境中包含着偶然性和必然性,有序性和无序性的对立统一。同时语境的实在性还具有心理意向性的一维,因为意向性关涉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对象性就意味着实在性。
(2) 思维普遍性
语境化地思考是人类具有意识以来就具备的一种思维形式。库恩的“范式”、布迪厄的“场域”、心理学的“语意情景”和现象学的“视域”等都是语境论的学科化成就。语境论就是在这种具体运用过程中发现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语境思维。语境本质上具有一种整体性思维,并不将对象作为个体孤立,或者绝对地来看待,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语境的大整体之中去审视和判断。整体主义的思维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一直以不同的理论面貌出现,特别是分析哲学以来,整体主义就以一种方法论的姿态出现。同样地,语境论也一直更多地作为一种方法的形式指导着人们的思考或实践。与原子主义截然相反,整体主义强调整体性,但是其缺陷在于将事物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看做一种静态的组成关系。语境论具有整体主义思维,但是它更加强调在整合基础上的一种动态关系。
(3) 动态性和结构性
语境的动态性:“语境具有时间和定向行为,即指向过去(行为何时何地发生),指向现在(保持行为此在特点的条件),指向未来(可能性和尚未实现的结果)。”[16]语境具有一种结构性,而语境结构又是在不停的变化和发展中的,即罗蒂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随着语境结构的演进和变换,接纳新的因素,随着量的增大,展现出一个全新的语境。这种新旧语境之间的张力使得语境具有一种动态的平衡性。也就是说,语境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结构,一种确定语言环境意义的关系网。语境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对象被置入语境之中,便解构成关系。同时在再语境化过程中语境又是新旧交替的交结点。
四、 “语境”的层面性思考
语境从英美日常语言哲学和欧陆存在哲学走来,将知识论推向了语境主义,最后形成了语境作为本体的研究。三条路线分别从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角度分析语境,而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只有作为一个有机认知整体时,各自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会凸显出来。
从本体论上来看,语境是作为人类思考问题、认知对象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关系模式,具有一种本体论属性。语境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的语言语境到情景语境,社会文化语境的扩展。正如迪利(Dilley)所说,语境观念“从关于人们在语境中的所言、所行和所思,转变为了以语境为框架,对这些所言、所行和所思进行解释”[1]4。这样,语境就逐渐摆脱一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研究,走向一种对世界本质,对人类知识和孜孜以求的真理的深入思考。也就是说语境已经成为人类言语和思维的潜在规则,甚而具有一种本体性。主体通过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和建构,动态地创造和扩充着语境。同时语境反过来对主体的实践活动具有制约和阐释的功能,语境的差异性带来对对象本质认识的不同,决定着意义的生成。
从认识论上来看,语境具有与世界同构的样态。认识论的出发点就在于对主体和世界关系、对象的表征和对象之间关系的反思。在这种关系的认识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确定认识的对象是什么。第二,人的主体感觉和认知能否把握客观实在?第三,对象和主体之间交互影响的过程性是怎样的?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着认识论发展过程中的三种不同的范式形态:①本体范式的反思。从柏拉图的理式开始,后继的哲学家们重点关注着是否超然地存在着一种世界的本质或者永恒的理念,它能够成为真正的客观知识的根本性保证。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对永恒本质很难把握,不同的主体认知会产生不同的结论。②心智范式。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为转折点,逐渐关注外部对象如何存在于主体内在精神之中,主体对对象的表征与对象本身之间的差异性等。③语境范式。一切哲学问题不过是语言问题。“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在于人们所说的实在是什么。这一切表明, 实在依赖于语言。”[17]对主体心智的探讨转向了对语言意义、语言的本质和语言交流使用的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在这种关系中,语言对世界的指称性是否是唯一的和确定的又成为新的争论点。随着后期维特根斯坦等对语境的重视,我们发现语言并非抽象的永恒的形式,而是存在于使用中才具有意义。于是语境认识论范式逐渐兴起。“关于知识的主张是相对于言说语境的,……而且,对认识论结果的评价,也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来进行”[18]。
从方法论来看,语境问题的探讨具有普泛化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性质,从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当语境思维处于不同学科之间时,也存在个体特殊性,又具有一种理论术语的属性。语境思维渗透到各个学科之中,“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是相对于各种语境的, 无论物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和语言的, 都是随着语境而变化的”[19]。语境的方法论在实践上具有层面性:①语境的语言表征性层。语言对外部世界情状和主体思想精神世界具有表征性。②语境的个体活动层。知识在个体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语境中被还原。③语境的社会背景层。更广泛的,但受特定时空限制的语境。
总之,语境无论作为人类的一种终极追求,还是认知模式抑或学科理论研究,都充满着一种本体的、终极的追求。随着哲学思潮的三大转向: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阐释学转向(interpretive turn)和修辞学转向(rhetorical turn),哲学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着语言形式、语言意义和语言的使用,语境的研究更需要构建完备的理论体系,将三者融为一体,才能逐渐在实践之中发掘其语境本身的理论品性。
参考文献:
[1] Dilley R. The Problem of Context[M].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1999.
[2] Malinowski B. The Problems of Meanings in Primitive Language[M]∥Ogden C K, Richards A. The Meaning of Mean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23:307.
[3] 亚里士多德. 工具论[M]. 李匡武,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55.
[4] Kretzmann 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16.
[5] Frege G.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M]. New York: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0:73.
[6]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上海:三联书店, 1992:31.
[7] Schleusener J. Convention and the Context of Reading[J]. Critical Inquiry, 1980:699.
[8]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00.
[9]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10]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169.
[11] Sosa E. Skepticism and Contextualism[J]. Philosophical Issues, 2000(10):1.
[12] Austin J L. Other Minds[M]∥Austin J L, Geoffrey J O, Warnock J.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76-116.
[13] Wittgenstein L. On Certainty[J]. Oxford: Basil Black Blackwell, 1969:213-219.
[14] Preyer G, Peter G. Contextualism in Philosophy: Knowledge, Meaning, and Truth[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2.
[15] 郭贵春,成素梅. 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J]. 哲学动态, 2008(5):6.
[16] Pepper S. World Hypotheses: A Study in Evidence[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2:232.
[17] Quine W V. Existence[M]∥Yourgrau W, Breck A. Physics, Logics and Histor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70:94.
[18] Hookway C. Questions of Context[M]∥Christopher H. Proceeding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96:ⅹⅹ.
[19] Schlagel R H. Contextual Realism[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