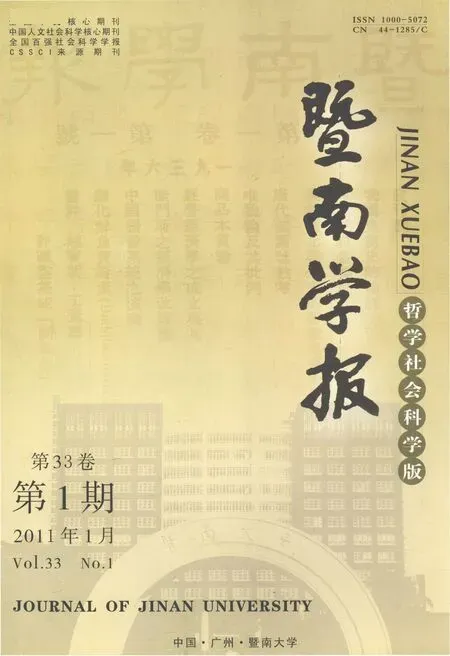纳博科夫对小说艺术本质存在的“无限还原”
赵 君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630)
纳博科夫对小说艺术本质存在的“无限还原”
赵 君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630)
颇具后现代颠覆与创新精神的纳博科夫将关于文学艺术的一切“先见”与“定见”悬置起来,对小说艺术的本质存在进行了无限度的“还原”:首先,消解外在“异质价值”对艺术作品本质存在的遮蔽,将艺术作品中并列而置的“真、善、美”标准简化为“美(内蕴真与善)”,即确立“美”(诗性)在艺术作品中的中心地位。第二,再一次“回溯”:对小说“诗性”的本源问题进行还原性思考,他察觉到了艺术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异质同构关系,从而有效消除传统摹仿论、唯美主义及现代文论中的某些理论缺陷,并从源头上保证小说艺术创新与发展的无限可能。纳氏艺术本质论不但为实验小说的大胆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小说艺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
纳博科夫;小说艺术本质;还原;诗性肌质;诗性本源
纳博科夫于1958年在美国出版的《洛丽塔》宣告了后现代文学的正式登台亮相。其实,《洛丽塔》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当流亡德国的青年纳博科夫趴在一张破沙发上完成他第一部小说作品开始,他就用一部部新奇的作品制成一颗颗重磅炮弹,向小说艺术的“常规”观念发难,将欧美权威评论家搅得寝食难安。
纵观几十年来纳博科夫作品的接受史与批评史,热闹非凡的纳博科夫研究表象后存在一个重大缺憾:长期忽略隐藏于纳博科夫那些具有多层次诗性艺术空间的“反小说”背后的美学动因,比如,作为后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纳博科夫对于小说艺术的本质存在问题的独特见解就被长期忽略。为此,系统梳理其颇具颠覆与创新精神的“后现代”小说艺术本质论,方能从原初意义上解读出纳博科夫既超越传统艺术本质论又超越包括唯美主义在内的现代某些文论的原始语境,并对纳氏艺术本质论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为后现代文学艺术的大胆实验与“合法”存在奠定坚固的理论基础——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艺术本质的还原——从“真、善、美”到“美(内蕴善与真)”的衍变
纳博科夫小说艺术本质论的基本理路是:不遗余力地试图将多年来强加于小说身上的小说观念悬置起来,努力剔除长期以来加诸在小说身上层层叠叠的遮蔽和覆盖物,以对小说艺术本身以及艺术本源的反思为根本出发点,系统地清算传统关于“伟大思想”对艺术造成的遮蔽与混乱,并一步步逼近艺术内在特性与本质特征。
纳博科夫注意到,当人们对小说所表现的思想性、社会性、道德性以及哲理性等“外在”效应津津乐道的时候,却将小说最为本质的存在——艺术与审美特性本身遗忘或边缘化了。因此,唤醒人们对小说艺术本身的麻木意识、让小说回到其最为元初的本真存在状态——艺术本身,成为纳氏艺术本质论的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
西方文论史上,文艺本质存在中“思”与“诗”的争斗从未停歇。就这个问题,纳博科夫与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之间就有过一场著名的论争。1939年7月,萨特发表了关于纳博科夫小说《绝望》的评论,指责纳博科夫“将自己降格为书写毫无意义的主题中去了。”[1]66-67明确地将纳氏作品归入“反小说”之列。
针对萨特的责难,纳博科夫奋起捍卫自己的美学追求,指出:“每一部原创性小说都是‘反小说’,因为它不仿效前人的文类和类型。”[2]173与此同时,纳博科夫在 1949 年4 月 24的《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点评刚刚在纽约出版的英文版萨特小说处女作《恶心》,责难小说在艺术方面的拙劣。
在纳博科夫看来,《恶心》在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完全是人们对其时髦哲学观念的一种好奇心所致,小说完全“淹没”在存在主义的观念形式之中,其表面紧张的艺术结构掩饰不了二流作家那里常见的毛病——散乱拙劣的艺术效果。纳博科夫对此讥讽道:“当一个作者将他自己空洞而随意性极强的哲学幻想强加在其虚构的无助的人物身上时,他若想要让这个戏法行之有效,就非得有超凡才华方可驾驭。当罗根丁认定世界是存在的,没有人会与他进行特别的争辩。但要完成艺术作品中的那个世界存在的重任,萨特显然是力有不逮。”[2]230
在纳博科夫看来,萨特在小说中推销自己的哲学观念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其文学人物成为其哲学观念的傀儡以后,萨特意在将自己的观念世界顺利地转化为艺术世界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对于纳博科夫来说,只有成功地创造出小说独立的艺术世界,才可以说文学艺术家完成了他们真正的使命。
从纳博科夫与萨特之间这段著名公案中,我们可以见到他们对于文艺本质论看法的扞格,即二人对文艺本质特征中“诗”(艺术)与“思”(思想教化)两个因素的各自偏向。
对于小说艺术本质存在的看法,纳博科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不盲从常识的“正常”指引,对任何“定论”与“真理”从不盲目接受,而要在经过自己充分思考与研究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有效判断。对艺术作品“真、善、美”关系的反思导引出纳博科夫对小说艺术本质存在的超越性思考。
纳博科夫清楚地看到,西方长期推崇的艺术作品中“真、善、美”三要素貌似并列而置,各要素的重要性似乎不分彼此而和谐统一,而事实上,它们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内在争斗从未停歇。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所谓的“真”与“善”内涵的模糊认识与盲目崇拜已经把“美”挤到了边缘上去,让本该是艺术本质存在的“美”在不知不觉中蜕变为“真”、“善”二要素事实上的附庸。
在一般人眼中,纳博科夫是反其道而行之,用“美”来压制另外二要素。如果真如此,纳博科夫也就回到了唯美主义的老路上去。其实,与唯美主义意欲斩断美与其余二因素的理论主张完全不同,在纳博科夫那里,艺术作品的三要素经过重新认识与整合,不但要确立“美”的中心地位,更要让三要素重新归于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与统一。
就什么是艺术作品的本质存在问题,纳博科夫在两个方面做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首先是要消除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思维定势,即,用异质性价值标准遮蔽文学最根本的本质存在——审美标准,也就是用思想内容(哲学思考、宗教颖悟、政治思想、道德说教、社会思潮、历史教训等)作为文学作品价值的根本判断标准;第二,旗帜鲜明地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即能给读者带来多少“审美狂喜”——确定为文学作品唯一的判断标准。需特别指出的是,纳博科夫还试图澄清人们对他“唯美”标准的误解,那就是坚持审美第一的标准并不因此就意味着要打压作品中思想内容的合理存在,只不过这种合理生存是以两个前提条件为基础的,其一,对艺术家天性本善的直觉信赖,其二,思想道德内容必须内蕴于艺术作品的内部结构和小说人物的天然禀性之中,否则就是对艺术的亵渎与损害。
由此可以看出,纳博科夫的艺术本质论遵循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轨迹,实现了从艺术作品的“真、善、美”到“美(内蕴善与真)”标准的衍变。
纳博科夫的“拨乱反正”工作并非易事,他的对立面是具有几千年高扬“理性”传统的西方文化价值系统,就艺术作品本身来说,受西方传统理性价值论显性与潜在的巨大影响,在人们的意识中,早已形成了一个对文学作品先验的、固有的价值判断观念:即,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成为作品是否“伟大”的标准之一,而且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理所当然”的主要标准。在人们对文学作品的习惯性接受中,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自然而然地一分为二,而且在作了一分为二的了断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往往主要集中在对“内容”的剖析和解读之上,“艺术形式”在不经意间成为对作品“伟大思想”进行解说的更为有利的有效补充。由此,一个关于艺术作品的怪异“公式”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文学内容≈伟大思想。
这种对艺术作品本质存在的长期遮蔽早已让人们神经麻木,而纳博科夫对此却奋起抗争,一生中宣称自己“像天才那样思考”的纳博科夫却似乎对“思想”有着强烈的反感,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对作品中人们钟情的“思想”尤其是“伟大思想”进行“抨击”。
纳博科夫以他独特的眼光将文学史上浩如烟海的小说作品进行重新检视,在他眼里,文学史上能够流传后世的作品已然不多,就连其中被冠以“文学杰作”的小说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纳博科夫并不受批评家乃至读者的喜爱程度和“公认”的判断标准的丝毫影响,而是以作品的艺术价值为唯一的判断标准。用他的标尺一量,他发现,除少量能“带给人们审美狂喜”、“符合艺术常规指数(好奇心、柔情、善意与迷狂)”的艺术品外,其余为数众多的都是“议题性垃圾或被某些人称为‘思想文学’的东西”,这些“思想文学”通常是一些“有议题的垃圾,它们自身覆盖着庞大臃肿的石膏体,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传了一代又一代”[3]333。
博科夫的“偏激”态度源于他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思想”的过度偏爱和忽略小说艺术本质存在问题的质疑。在他看来,读者的阅读习惯已经被作品的思想性牵引着严重偏离了方向:
那些浅薄与高级庸人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隐秘情结,即,一本书,如果说它伟大,一定得是论述伟大思想的。……他喜欢精彩故事里混合着社会评论香料,喜欢寻找作者那些与自己刚好吻合的思想和痛苦感受;他要求作者笔下至少要有一个人物是他的傀儡。[2]41
纳博科夫的这番话的确是有深刻的洞见性,文学史上,将文学作品视为“寓教于乐”、宣传政治主张、感悟人生哲理等绝妙的思想材料,已然成为“不言而喻”的共同认识。
纳博科夫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人们倾向于尊崇作品中的思想内容而非真正的艺术,然而思想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毫无意义的“石膏体”,或成为“搁浅在海滩上僵死的鲸鱼”,唯有艺术的万丈光焰才能照耀后世,作品中的艺术性才会成为作品免遭锈蚀和虫噬的最佳保护层。
在纳氏作品中,要按照我们对小说作品的“常规理解”去寻求小说常见的主题思想非常困难,小说主题的不确定性和对一般思想的反动正是纳博科夫小说的主题,其作品的多义性、无时间性、多重意蕴结构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体验巨大审美狂喜的广阔无垠的诗性空间,又让我们因为难以“准确”把握其“要旨”而真正地将阅读变成了一种痛苦的仪式。纳博科夫有些自得地告诉我们:“我将这些谜语的谜底留给学者型批评家去破解,留给知识苹果树上的夜莺去歌唱。客观地说,在我小说里我找不到所谓的中心思想,比如命运之类。”[2]117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找不到所谓的“中心思想”并非意味着纳博科夫作品就没有“思想”,没有道德是非观。那么,纳博科夫在自己的艺术实践活动中是如何妥善处理诗与思之间的关系的呢?纳博科夫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内蕴”,即:艺术作品是以“美(艺术性)”为中心的,但并非是说“思(善,真)”就不存在,只是“思”要内蕴于“美”中。在这里,纳博科夫将以往并列而置的“真、善、美”三要素演变成“美(蕴涵善与真)”,不但将传统的艺术作品的构成因素进行了全新的排列与组合,使其内在相互关系产生了质变,更避免了重蹈唯美主义只保留“美”而完全摒弃文学作品中另外两个重要元素的片面而武断的覆辙。他说:
我小说中可以追寻的思想是内蕴于我的小说人物,有可能有意识地带有缺陷。在我的回忆录中,可以引用的思想只是一些过往的景象、暗示、头脑中的海市蜃楼。它们就像热带鱼一样,如果把它们从其生活的热带海域的生存环境中打捞上来,它们就会失去色彩或爆炸。[2]147
纳博科夫用生动的比喻说明诗与思水乳交融的不可分离性。其实,在纳博科夫看来,争论艺术作品中的道德与否的问题并不重要,说它不重要并非是要将艺术作品“去道德化”,而是说这个问题并非艺术作品的中心问题。这基于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我们应该对艺术家天性的良知良能抱十足的信心,对人性之善应有直觉的信赖。人之善良本性比起那些摇摆不定、虚设假定的理想主义哲学更让人信服,是个人心中处于中心地位、最可以触手可及的东西。纳博科夫认为,像他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浪迹天涯的无数年轻梦想家,哪怕是身处最黑暗的时刻,在充满危险、苦痛、蒙尘乃至死亡威胁的日子里,他们都坚守着“这种非理性而神圣的信念”[4]373。那些对“善”失去了基本判断的恶人根本就不知艺术为何物。他说,真正的艺术家具有一颗未被污染、完整无暇的“艺术良心”,其内涵就是:“诗人(原文大写,笔者注)的内在使命感,他心中相生相依的真、善、美。”[5]347其二,从欣赏者角度来说,作品中哪怕表现的是人性的恶和癫狂并不会将读者引向歧途,这就像教堂中恶魔的塑像并不会影响信男善女们对崇拜与敬仰的对象选择一样。其三,纳博科夫始终认为,作家的职业目的并非在于改良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或像街头宣传家那样用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动人们寻觅到崇高的理想。尤其是,作家们在艺术上只能算得上二、三流的作品更是绝对达不到这样的高尚目的。
人们惊悚于他诸如此类对艺术作品中道德教化等异质价值问题的见解,对此,纳博科夫力图要让我们明白他真正的意思:“我从未企图否定内在地蕴涵于每一部杰作中艺术的道德力量。我真正想要否定的是那种人为的道德化,在我看来,无论其写作技巧是如何的高超,人为的道德化只会将作品的艺术性绞杀得干干净净,我会对此抗争到最后一滴墨水。”[6]56
纳博科夫认为,人为的道德化是艺术永远的敌人,他的“激进”观点可以说是对几千年来附着在文艺身上过于沉重的附加物的一种“拨乱反正”,纳博科夫试图将蒙蔽艺术明珠的千年积尘擦拭干净,让艺术之珠自身放射出熠熠的灵光。在其文学讲座中,纳博科夫更为全面而深刻阐述了他对文学本质特征与众不同的认识和思考:
长期以来,艺术被太多地当成传达思想——政治或道德方面——的工具,去影响、教诲、提高或启发诸如此类。我并不是想要说艺术不会对读者有提高和启示作用。而是说艺术会用自己特殊的方式产生这种作用,只有当艺术自己单一的目的始终保持良好、优异的本色,艺术达到艺术家创造出的完美状态,这种作用才会有效。一旦艺术这个唯一的真正的有价值的目的被忘却,一旦艺术被实用目的所取代,无论这个作品如何让人喜爱,艺术不但会失去其感觉和美感,还会失去它为之做出牺牲的目的:拙劣的艺术既不能予人教益也不能让人有所提高或得到启发。[7]111
由此可见,一方面,纳博科夫将“审美”置于作品的中心地位,艺术作品以艺术为唯一真正的目的,艺术家的唯一任务就是采用各种诗性手段努力达成艺术的完美,这一点是容不得半点怀疑的;另一方面,纳博科夫关于将思想道德教化内容“内蕴”于“艺术”的观点很好地澄清了人们将他的作品归入唯美主义行列、将他的艺术为中心的思想与唯美主义思想混为一谈的含混观念,因为纳博科夫并未武断地将作品的思想内容彻底摒弃,只是要求思想必须内蕴于艺术之中、从而成为艺术作品的自然组成部分。韦勒克对此的看法也颇为相似:“哲学,即思想意识内容,出现在恰如其分的语境中,似可提升艺术价值,因为它确证了几种重要的艺术价值:即复杂性与连贯性价值。”[8]123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纳博科夫对作品中“思想道德”诟病的真实意图和真实语境。
纳博科夫的“非思”的目的在于“扬诗”,在于将覆盖在小说身上层层叠叠的附加物清理干净,在于摒弃关于小说的“形式”VS“内容”、“道德”VS“不道德”、“形而上”VS“形而下”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小说的本质无限度地还原到其内在的诗性特征上去。
二、小说艺术中的诗性本源与诗性创造精神
经过一步一步行之有效的现象学还原工作,纳博科夫确立了“艺术性(诗性)”在艺术作品(包括小说)中的本质存在和中心地位,并最大限度地逼近了对于文学作品本质内涵的认定:艺术品最为基本的细胞组合结构是艺术品中的诗性肌质,在这种艺术品最为基本的构成中,诗性的密度与厚度决定了艺术品的高下,即它们决定了艺术品能否给人们带来“审美狂喜”和带来多少“审美狂喜”。接下来他就“诗性”的本源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还原性思考:他察觉到了艺术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异质同构关系,倡导艺术家保持与大自然的诗性创造相一致的诗性创造精神,从而有效消除传统摹仿论、唯美主义及现代文论中的某些理论缺陷。
凭借自己精细的科学研究活动和对大自然的无限深情,纳博科夫生发出自己独特的艺术本源论:显性的“此在世界”中蕴含着可以让艺术家通过个人意识的非理性灵感思维偶然一窥的非显性的“彼在世界”,这个“彼在世界”的构成方式与艺术作品中的“艺术审美的彼在世界”在构成方式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同一关系。因而,艺术作品中的诗性本质与现实世界的诗意存在两两相契,这正是纳博科夫的艺术本源论与他的艺术本质论的内在相通与契合。正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艺术本源与艺术本质的被打通,才彰显出其超越传统文论、同时也超越现代文论某些流派(如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等)的特质。在他那里,现实世界——艺术家——艺术世界三要素被彻底打通: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就是探索那个彼在世界的诗意存在,真正的艺术作品(“诗”)是通过采用理性语言构思的方式表征非理性神秘(诗性表现)的结果,艺术作品的根本存在方式是艺术本身,不是其他,而“诗性”品质正是艺术最根本、最具体的内在意蕴。
从他对大自然的深刻洞察中,纳博科夫不仅敏锐地察觉了艺术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异质同构关系,从而有效消除了传统摹仿论艺术与现实二元对立的紧张,而且,他从自然与现实的无穷意蕴中清楚地窥见到艺术与自然同一的诗性本质,也就是,用他的话说是“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愉悦。它们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都是玄机重重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9]125
这是他就艺术本质论问题所得出的著名的“纳氏美学定律”——艺术与自然在构成方式上同样无关厉害计较、都具有魔幻式的巫术与欺骗性质。
因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纳博科夫寻求的是与大自然欺骗本性相同的“艺术真实”。西方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再现说、表现说、艺术即形象说等都企图说明文学艺术的本质,然而,它们都未能超出认识论的哲学基础,长期以来,它们一直都在“反映”与“被反映”、“表现”与“被表现”等二元对立模式上打转,以完成“无限接近社会真实和生活真实”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设定目标。而纳博科夫却认为,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在构成性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之间没有界限。据此,我们可以看出,纳博科夫的文学本质论与传统文学本质论的根本差异在于:他旨在从本体论而不是认识论角度解决艺术本源的根本问题,他的主张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未经理性格式化的古希腊原始摹仿论的真义上去了。
从纳博科夫对“诗”所下的著名定义中,我们可以认清纳博科夫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论具有艺术哲学与艺术本身浑然而一的“元美学”特征。他说:“我所谓的‘诗’就是通过理性语言的构思表征非理性的神秘”[10]52。纳博科夫对艺术诗性的认识乃是他从自身对大自然的认识活动当中生发出来的,他与现代学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后者是在知识分类的鸽子分隔屋(纳博科夫语)中进行知识“理性”思考和逻辑化研究,与纳博科夫自身自觉地跨越科学、艺术与哲学的鸿沟而进行的“元学”感悟不能相提并论。在纳博科夫,对充满神秘诗性的大自然的研究正是人的诗性实践活动,而人的诗性创造活动正是对大自然诗性创造活动的最好摹仿。因而,科学创造与纯诗创造在本质构成上是一致的,像现代知识分类中将哲学、科学和艺术活生生地分离开来的做法是非常可笑的,因为,纯科学与纯诗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能给人提供一种妙不可言的“审美狂喜”。纳博科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非常生动地说明,科学活动与艺术活动一样,可以获得精神上至高无上的享受。蝴蝶研究的各个程序与过程就是体验艺术品创作与欣赏的过程,“精确绘制(蝴蝶)时那触觉上的喜悦、实验室暗房中静穆的天堂、对蝴蝶分类进行诗一般精确的描绘,这一切将艺术般的喜悦与震颤展现得淋漓尽致,新知识积累中的这种震颤(对门外汉来说没什么用处)赐给了其首创者。”[2]79
纳博科夫强调,艺术世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有自己的逻辑。“福楼拜的世界,如同其他大作家的世界一样,是一个虚幻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巧合。”[4]146这个观点似乎是英美新批评文论的回声。的确,纳博科夫的艺术本质论与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对艺术本质的认识有某些共通之处。他们都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都摒弃对文学那种道德伦理式研究、社会历史学研究、心理印象式研究的“外部研究”模式,都将文学的本质存在指向文学作品本身中的“文学性”和“诗性肌质”,然而,仔细分析他们各自的诗学话语的内在规定,其差异显然大于它们的叠合。
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还是英美新批评,他们提出的“文学性”或“架构-肌质”说等核心范畴的目的在于建构一门不依赖别的学科而独立存在的“文学学科”。然而遗憾的是,当形式主义将文学中与政治、经济、心理等与其他学科相关中的实体存在取消、将文学的存在归结为文学中的“文学性”时,突然发现“文学性”孤悬无依,只好将“文学性”推向纯语言学层面。而英美新批评也试图将文学批评“科学化”,他们试图确立文本本身的“本体”地位,让文本自身成为静止的、永恒可靠的研究对象。他们虽然也的确对诗歌中某些“诗性肌质”的认定(语境、复义、张力、想象、反讽等)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批评的理路与方式,然而他们的理论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伤害到了新批评派自身:他们试图以“意图迷误”斩断作品与其创造者之间的联系、以“感受迷误”斩断作品与欣赏者之间的联系,其结果不得不将诗降格为纯语义的分析。因而,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了语言研究的偏狭道路上去了。
而纳博科夫的文学本质论不但要确保审美(“诗性”)在文学作品中的独立与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并没有自我将死,相反,他尤其强调艺术作品的诗性本源和艺术作品中与大自然诗性世界一致的诗性精神。从他对“诗”的定义(“通过理性语言的构思表征非理性的神秘”)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强调了艺术作品诗性创造的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理性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一样,纳博科夫也看到了语言的重要性,然而,纳博科夫并不将文学的诗性与语言划等号,而是用了一个关键词“通过”,也就是,把语言当成文学达至“审美狂喜”的必要介质和手段。
第二,“构思”。纳博科夫并不否认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中的主导地位。他清楚地看到,正是通过艺术家的记忆和灵感思维,成功地将他眼中的“意向性现实”转化为同样充满诗性存在的艺术品。
第三,这是纳博科夫作品诗性创造中三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表征非理性的神秘”。它不但表明了艺术家诗性创造的最终目标,也是艺术品具有独立价值的诗性存在本质。在纳博科夫,“非理性的神秘”就是指“此在世界”中隐含着的“彼在世界”的真相,是人们通过原始诗性智慧对自然诗性的把握与认识。人与自然同构,与自然相通,注定了人对自然母胎的依恋,对原始鸿濛混一的怀念。没有被逻辑化,格式化的心灵,在神秘的精神历程中,建立起与现实之间的多重关系,实现个体生命情致的审美性超越。在此过程中,人的感觉、直觉乃至梦魇最接近事物的实质。“一个梦就是一次表演——那是在昏暗灯光下给有些懵里懵懂的观众表演的头脑中的戏剧片断……众演员、道具以及各种不同的布景都是做梦人从我们清醒时的生活中借用过来的……不时地,清醒的头脑会发现昨晚梦中的某种感觉模式;如果这种模式的造成了强烈的震撼,或者恰好与我们清醒时的内心最深处的激情相吻合,那么这个梦就可以被结合到一起和重复……”[11]176噩梦更是将焦虑的元素加诸于这种感觉模式。
纳博科夫认为,文学的本质就在于表现这些具有原初性、个体性以及事物特殊性的“非理性”“非显性”“非逻辑性”的原始诗性感觉,这正是他所青睐的艺术作品中蕴涵的“诗性精神”。这种原始诗性感觉类似于维柯所说的“诗性思维”。维柯认为:“诗既然创建了异教人类,一切艺术都只能起于诗,最初的诗人们都凭自然本性才成为诗人(而不是凭技艺)。”[12]104而荷马史诗中的智慧是一种世俗智慧,一种诗性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神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纳博科夫也认为,在神祗早已退休的今天,人们的这种神奇的诗性思维也严重蜕化,公共化、集体化思维逐渐取代了生动具体个性十足的个体思维,而艺术一旦触及“公共”“集体”“常识”等常规思维就会一无是处。只有像小孩第一次看马戏那瞪圆的眼睛、对生命原生态保持童心般的好奇、对感官印象的直觉记忆等诗性思维才是真正艺术的触须[4]382。
纳博科夫所谓的事物内在特质就是指艺术作品与自然世界具有同一关系的诗性表现。他强调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异质同构性、强调艺术作品中的诗性本源和恢复原始诗性思维的诗性精神构成了他艺术本质论的丰富内涵,充分体现出纳博科夫小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
三、纳博科夫小说诗性本质的理论意义
纳博科夫经过一步一步行之有效的现象学还原工作,最大限度地逼近了对于文学作品本质内涵的认定:文学最为本质的存在是其内在的诗性,也就是,艺术品最为基本的细胞组合结构是艺术品中的诗性肌质,在这种艺术品最为基本的构成中,诗性的密度与厚度决定了艺术品的高下,即它们决定了艺术品能否给人们带来“审美狂喜”和带来多少“审美狂喜”。因而,小说作品质量的高下的评判自然也就从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外部标准转移到了作品本身是否真正具备长久生命力的“诗性肌质”的内在标准。
纳博科夫这番“去蔽存真”的功夫与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真义的还原有着方法论上的惊人巧合。在海德格尔那里,“运思和作诗,以及思与诗的对话,乃是作为历史性此在的我们重返‘本真存在’、重返‘诗意地栖居’的‘返乡之路’”[13]38。同理,纳博科夫敏锐而准确地概括出现代与后现代文学最具特色的美学追求——小说的“纯诗”效果。对此,韦勒克的看法与纳博科夫异曲同工:“现代艺术-小说(《尤利西斯》等)寻求像诗歌即自我观照式建构自身。”[14]215就纳博科夫本人的作品来说,他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也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诗歌般“自我观照式建构自身”的特征。在纳博科夫看来,那些将小说大师们的作品以社会历史等外部视角加以解读、将他们的杰作阐释为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注定是不得要领。要检验一部作品是否具有长久生命力,主要的是看这部作品是否真正担当起了“诗”的职责,也就是小说是否具备了诗歌的诗性。虽然我们并不要求散文作品要具有诗歌作品那样的韵律与节奏,但并不妨碍其达到“纯诗”的艺术效果。就像纳博科夫称赞莎翁的和果戈理的戏剧作品为具有密厚诗性背景的梦幻作品一样,他也对福楼拜推崇备至,正是因为在小说史上,福楼拜是第一个成功地将小说艺术提升到与诗歌艺术同等高度的艺术大师。在其《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称福楼拜具有不同凡响的艺术大师风范,他非凡的艺术才华最能够体现在《包法利夫人》这部法国文学无以伦比的珍珠的作品上面。福楼拜居然可以依靠艺术神奇的魅力,将他构思出来的一个肮脏的世界,一个居住着骗子、市侩、庸人、恶棍以及一群喜怒无常的女人的世界成功地转化为一个富于完美诗意的艺术世界。这部诗意盎然的“最为浪漫的童话”在艺术风格上成功地“让散文担负起诗歌应该做的事情”[4]125。
纳博科夫的艺术本质论既超越了传统关于小说本质的流俗之见,高扬小说艺术中最根本的诗性特征,努力消除政治、社会等一切宏大叙事对艺术遮蔽的消极影响,同时又洞察出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空洞无物的内在实质。纳博科夫真正目的在于,辨明小说艺术的真正本质,让小说艺术发展真正回归本位。
其次,虽然纳博科夫的某些言论显得有些出格与偏激,但他对于小说艺术本质的大胆探索精神,尤其是不受任何固定思维与条条框框约束的独立创新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他关于艺术作品诗性本质与现实世界的诗意存在两两相契的学说,更是从源头上解决了后现代语境中艺术对现实关系的现实困境,从而全面超越了“文学枯竭论”文学艺术发展困局:对蝴蝶的研究越深入越是让纳氏对世界的具体性与复杂性有更清楚的认识,他看到了具体世界中潮涨潮落般连续不断的运动之流,事物中蕴含的不断深化、眼花缭乱、变化万端、层层递进的复杂特性。
他以为,既然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在构成方式上具有同一性,艺术世界中的带来审美狂喜的诗性与大自然蕴涵的无限诗性性质一致,现实世界的无穷意蕴也就成为艺术创造的初始与永不枯竭的宝库。
由此观之,纳氏小说艺术本质论不仅为后现代小说艺术的“合法存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障,而且为小说艺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更是给中国文学发展道路的多元化选择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参照物。
[1]Satire,Jean - Paul:La Meprise[M]∥In Europe,15 June,1939.Reprinted in Norman Page,ed.Nabokov,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1982.
[2]Nabokov,Vladimir.Strong Opinions[M].New York:McGraw -Hill Book Company,1973.
[3]Nabokov,Vladimir.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M]∥Nabokov.Lolita.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Nabokov,Vladimir.Lectures on Literatur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ch/Bruccoli Clark,1980.
[5]Nabokov,Vladimir.Unpublished Lecture Notes[M]∥Brian Boyd.Vladimir Nabokov:The American Ye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6]Nabokov,Vladimir.Selected Letters[M]. Dmitri Nabokov & M.J.Bruccoli,Ed.San Diego,New York,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ch/Bruccoli Clark,1989.
[7]Nabokov,Vladimir.Unpublished Lectures[M]∥Brian Boyd.Vladimir Nabokov:the American Ye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8]Wellek,Rene et al.Theory of Literature[M].New York:Penguin Books Ltd.1986.
[9]Nabokov,Vladimir.Speak,Memory[M].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6.
[10]Nabokov,Vladimir.Nikolai Gogol[M].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Corp.,1961.
[11]Nabokov,Vladimir.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M].New York,N.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Pub.,1981.
[12]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3]钟华.海德格尔诗学与《庄子》诗学思想之差异述略[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14] Wellek & 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M].New York:Penguin Books Ltd.1986.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I106.4
A
1000-5072(2011)01-0009-08
2010-05-21
赵 君(1964—),四川大竹人。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纳博科夫诗学问题考辨》(批准号:09BWW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