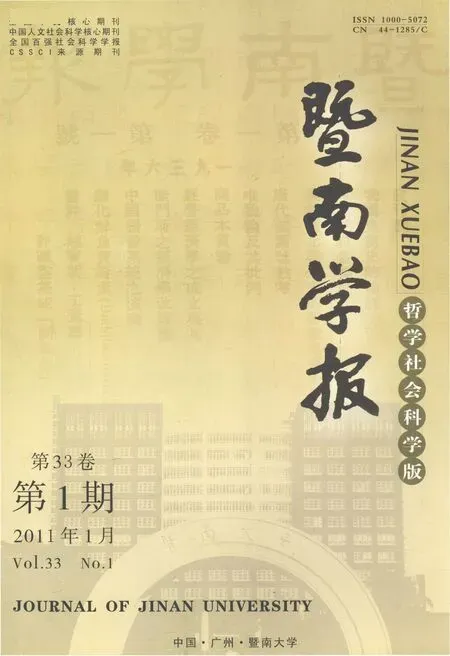“保护伞条款”与国际投资争端管辖权的确定
封 筠
(暨南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保护伞条款”与国际投资争端管辖权的确定
封 筠
(暨南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发展迅速。东道国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往往会在双边投资条约中,签订承诺保护外国投资者所有投资权利的“保护伞条款”。这一条款的创设,使得此后外国投资者能够以东道国违反与其签订的合同义务为由,通过“保护伞条款”将本属东道国国内管辖的合同争端,上升为东道国需担负国际责任的条约争端。ICSID对两个SGS案及相关系列案件的不同裁决,体现了国际仲裁庭对于“保护伞条款”在确定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管辖权中适用的态度—并无统一标准,个案区别对待的原则。因此,对于目前兼具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而言,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时,应给予“保护伞条款”以更多关注,以求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利益。
保护伞条款;双边投资条约(BIT);争端管辖权;ICSID
一、“保护伞条款”问题的提出
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更为迅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为了更多的吸引外资,在与外国投资者母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BIT)①自此处之后,下文中的“双边投资条约”均以英文的BIT表示。中,均会以用语不一的措辞,承诺将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所有投资权利,即在BIT中签订“保护伞条款”。该条款的存在,一方面有利于限制东道国的行政权力,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则使得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端管辖权的确定过程平生了一些不确定因素。早期国内学者对“保护伞条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性质及其对东道国主权的影响方面。而随着外国投资者通过依据“保护伞条款”将其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提交至ICSID的实践增多,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了对因“保护伞条款”而引起的合同违约与条约违约转换关系的研究。
现代国际投资实践中,东道国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发展本国经济,通常会在签订BIT的时候承诺缔约方将会遵守其对另一缔约方国民或公司所做出的任何承诺。这就是现代BIT中“保护伞条款”的主旨。“保护伞条款”是由特许合同中的稳定条款演变而来的。稳定条款的目的在于防止东道国利用主权权力逃脱通常由前政府所承诺,但继承政府却认为约束太大的某些义务。不过,如果认为该特许合同服从于国内法,后来的国内法就可以废除该合同中的稳定条款。因此,有学者认为,投资条约中的保护伞条款把合同稳定条款的意图和战略抬高到更高的条约义务的层次,这一义务并不会(或者更少)被国内法所否定[1]228。此前,东道国违反其与投资者间合同的行为并不会被视为是对国际法的违反,而仅被视为商业性质的违约。双方主要通过东道国国内救济的方式解决争端。自1959年首个“保护伞条款”出现以来,大量BIT都对“保护伞条款”以不同的措辞做出了规定。这些表述不一的“保护伞条款”就其本质而言,都存在着扩大东道国义务范围的倾向。2003年8月及2004年1月ICSID公布的两个SGS案件是有关“保护伞条款”与争端管辖权确定之关系的最早实践。这两个案件的申请方是同一家公司,被申请方是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两个不同的国家,提起仲裁的依据都是BIT中的“保护伞条款”,但是两个仲裁庭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裁决,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保护伞条款”问题的关注。
二、典型案例解析
SGS V·巴基斯坦
1995年,瑞士SGS公司与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由SGS对从某些国家向巴基斯坦出口的货物提供装运前检验服务。该合同的仲裁条款规定:当事方应该首先友好解决“涉及该合同的违反,终止或者无效的任何争端”;如果不能解决,则根据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地区仲裁法仲裁。合同执行两年后,巴基斯坦终止了装运前检验合同。SGS公司向瑞士法院起诉,认为巴基斯坦政府非法终止了装运前检验合同。瑞士法院最终以巴基斯坦享有主权豁免为由驳回了SGS的主张。在诉讼过程中,巴基斯坦政府援引装运前检验合同仲裁条款,请求巴基斯坦法院发布命令,要求当事方依据合同规定进行仲裁。SGS公司反对在巴基斯坦仲裁并向ICSID请求依据BIT仲裁①SGS.v Pakistan ICSID Case No.ARE/01/13。
2003年8月,ICSID仲裁庭裁定,其对有关违反条约的主张享有管辖权,但是对于有关违反合同的主张没有管辖权。仲裁庭的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仲裁庭认为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确立的解释原则,对瑞士-巴基斯坦BIT第11条②瑞士-巴基斯坦BIT第11条规定:“缔约方应持续保证其将履行与另一方投资者签订的有关投资方面的承诺。”进行解释,不能得出缔约双方具有将因违反与另一方投资者签订的合同义务,而必然构成对BIT中“保护伞条款”的违反,从而需要接受国际仲裁庭管辖的意图③SGS v.Pakistan ICSID Case No.ARE/01/13,para.165.;其次,仲裁庭认为,就众所接受的一般国际法角度而言,东道国违反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的合同的行为本身并不能代表东道国就一定违反了其与投资者母国签订的BIT。除非作为申请方的外国投资者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东道国违反合同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BIT④SGS v.Pakistan ICSID Case No.ARE/01/13,para.167.;第三,仲裁庭认为如果将瑞士-巴基斯坦BIT中的第11条作为“保护伞条款”执行将会带来以下不利后果:(1)这样的解释将无限扩大保护伞条款的适用范围;(2)这样的解释将会简化判断东道国是否违反BIT的标准;(3)这样的解释将使得外国投资者可以随意置其在合同中与东道国就争端解决方式达成的合意于不顾,而随意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⑤SGS v.Pakistan ICSID Case No.ARE/01/13,para.168.;第四,仲裁庭从条约的整体结构出发,认为瑞士与巴基斯坦如果想把第11条作为实体性问题的规范,就应将其放在第3条至第7条这样的实体条约之间,而不是将其放在代位条款与争端解决条款之间⑥SGS v.Pakistan ICSID Case No.ARE/01/13,para.170.。由此可见条款的具体位置也影响了其在整个BIT中的地位与作用。“保护伞条款”所规定的内容虽然从形式上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其实质仍是对相关实体权利的规定,所以应当将其与实体性条款放在一起。如果一个被当事一方认为是具有“保护伞条款”性质的条款并未放在这样的位置,那么其所代表的意义也就会在仲裁庭做出裁决的时候大打折扣。综合上述各方面情况,仲裁庭最终裁定其对SGS公司与巴基斯坦的合同争端不享有管辖权。这一裁决否定了投资者意图通过BIT中的“保护伞条款”将单纯的合同争端上升为条约争端的做法。
对此裁决,投资者母国提出了批评。一些西方学者也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首先,仲裁庭没有详细论述“保护伞条款”适用于违反合同事项为什么会使BIT中的实体规定变得多余。BIT中的实体性规定包括非歧视待遇、公正与公平待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自由转移以及征收保护等,而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的合同通常不会规定这些问题。对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合同性安排,“保护伞条款”使得投资者可以通过条约仲裁的方式寻求国际公正裁决,这并没有使得其他的义务变得多余。即使东道国没有违反投资合同,也可能构成征收或歧视;相应地,即使与投资者之间不存在投资合同,东道国也可能违反公正公平待遇义务,因此,仲裁庭所主张的“保护伞条款”适用于违反合同事项会导致其他条约义务变得多余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其次,仲裁庭对BIT实体义务的列举顺序过于重视。“保护伞条款”的位置处于争端解决条款之后这一事实应该表明,起草者没有把保护伞条款当作“次要性”规定,而是应该优先重视的规定[2]。
笔者认为,针对第一条批评意见,仲裁庭之所以裁定“保护伞条款”适用于违反合同事项会使BIT中的实体规定变得多余,是因为如果对保护伞条款的适用做出宽泛解释,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合同争端通过该条款自动上升成为条约争端,从而使东道国不得不接受相关国际仲裁庭的管辖。而其实与合同争端中很多问题相关的实体性规定,已经在BIT中得到了体现。投资者完全可以依据BIT中,东道国所承担的具体义务没有被其履行为由,提起仲裁申请,或者是采用类似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但如果投资者通过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保护伞条款”而可以任意将合同中的争端提交到相关国际仲裁庭,那么,对于BIT中已经存在的实体性权利义务的规定实质上是一种绕避。这些具体的实体性条款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争端仲裁申请的提起,就变为了依合同而定而非依条约而定,那么BIT完全可以只签订一个“保护伞条款”而抛开其他规定了具体权利义务的实体性条款。
针对第二条批评意见,从一个条款在条约中的具体位置判断其在条约中的作用,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人类在订立条约的时候,必定会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来安排各个条款的位置,一般都是实体性的规定在前,程序性的规定在后。但是实体性条款与程序性条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而无法证明在前的实体性条款就一定比在后的程序性条款重要。由裁决可知,仲裁庭认为:在瑞士-巴基斯坦BIT中具有实体性条款性质的“保护伞条款”被放在了程序性条款的位置,则可由此推知缔约双方对于该条款所代表的性质做出了新的界定,认为其更类似于程序性条款。因此,仲裁庭判定BIT中的该条款不具有实体性条款的作用与意义。这样的判断并没有不当之处,仲裁庭只是界定该“保护伞条款”不具有实体性条款的作用,但并未否定其作为一个有效BIT中重要条款的作用。
SGS V.菲律宾
2004年1月,在SGS v.巴基斯坦之案裁决做出不到半年的时间内,ICSID仲裁庭裁决的另一个SGS案件就得出了与前案完全相反的结果。SGS v.菲律宾一案涉及SGS公司与菲律宾政府之间的CISS合同,合同规定SGS公司为菲律宾政府提供进口货物装运前检验服务。在执行CISS合同期间(1992年3月到2000年3月),SGS为菲律宾政府提供检验服务的价值大约是6.86亿美元,而菲律宾政府大约支付了5.4亿美元。2002年4月26日,SGS公司向ICSID申请仲裁,主张菲律宾没有支付所欠款项,构成违反1999年生效的瑞士-菲律宾BIT,其根据之一就是瑞士-菲律宾BIT第10(2)条规定的保护伞条款,即“每一缔约方应当遵守其对另一缔约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具体投资所承诺的任何义务”。菲律宾政府于2002年11月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其理由之一是CISS合同第12条规定由当地法院拥有排他性管辖权:“本协议在所有方面应接受菲律宾法律规制并根据菲律宾法律加以解释。涉及本协议任一当事方义务的争端,应该在马加地或者马尼拉地区法院起诉。”①SGS v.Philippines ICSID Case No.ARB/02/6仲裁庭最终裁定,SGS可以通过BIT中的保护伞条款将基于合同的争端提交到ICSID仲裁庭,仲裁庭对该争端享有管辖权。
首先,仲裁庭认为,从瑞士—菲律宾BIT第10(2)款所规定内容的效用角度考虑,此BIT是为了促进和保护国家间的投资而签订的。依此BIT的序言可以看出缔约方旨在“为另一缔约方投资者创造并维持一个最佳的投资环境。”对于其所涵盖的投资活动的有关问题的不确定性做出解释是合乎条约意图的②SGS v.Philippines ICSID Case No.ARB/02/6,para115&116。在本案中,“保护伞条款”的措辞使用了强制性字眼“应当”与高度概括性字眼“任何义务”,而前一个SGS案中,缔约双方仅规定“任一缔约方应持续保证遵守所做出的承诺。”本案中的“保护伞条款”比前案中的“保护伞条款”更加明确的规定了东道国应当承担一切义务。因此,前案中仲裁庭对条约采用的严格解释方法不适宜用于本案中对条约的解释。
其次,仲裁庭认为从瑞士—巴基斯BIT第11条的字面意义理解,其并未包含“若东道国不遵守其与投资者间合同的义务必将招致国际法上责任”的意图。而瑞士—菲律宾BIT中的第10(2)款则明确包含了此种意图。仲裁庭在最终裁决中,明确了其对SGS公司基于合同提起的仲裁申请享有管辖权,但同时其也承认了SGS公司与菲律宾政府在合同中签订的有关争端解决法院选择条款的有效性,认为菲律宾当地法院对此合同争端享有管辖权,SGS公司应当首先将争端提交至合同中指定的菲律宾国内法院,只有当指定的菲律宾国内法院所做出判决不能使投资者满意,或是该法院没有做出公正判决时,SGS公司才可以再次向ICSID提起申请。对于此案的裁决结果,仲裁庭明确了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但也认可了东道国与投资者间合同中争端解决条款的有效性,且认为这种有效约定优先于仲裁庭的管辖权,因此,仲裁庭并没有对双方所争议的实体性问题做出裁决。
同样,一些西方学者对SGS v.菲律宾一案的仲裁结果也提出了质疑,认为仲裁庭既然裁定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那么为何又不对案件的实体争议做出裁定?“保护伞条款”试图在政府干涉投资合同的情况下,给投资者提供一种最简便的,直接的保护,使其再也不需用尽当地救济,不需经历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复杂程序,就可以获得争端的解决。[3]但是仲裁庭对第二个SGS案的裁决结果,实际上承认了东道国当地法院的优先管辖权,从而使得投资者仍然需要首先寻求当地救济。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达到“保护伞条款”预期的意图。然而,作为承认投资者与东道国间合同争端可以通过“保护伞条款”上升至相关国际仲裁庭管辖的第一案例,此案的结果已为今后“保护伞条款”在将合同争端上升至条约争端中广泛的适用奠定了基础。
Salini V.约旦与 Noble Ventures v.罗马尼亚之比较
在Salini v.约旦一案中,意大利投资者作为申请方,主张依意大利-约旦BIT中的第2条第(4)款,第2条第(5)款及第11条第(2)款所使用的措辞而言,已经构成了“保护伞条款”。其中第2条第(4)款及第2条第(5)款规定:“缔约各方应当在其领土内为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创造并维持一种良好的法律体制,包括遵守,善意履行对某一个具体投资者所做出的保证;缔约各方及其附属机构可以与作为另一缔约方国民的投资者约定有关投资者关注的具体投资方面的相关事宜。”第11条第(2)款规定:“如果东道国不能将这样的待遇付诸实施……并且投资者因此遭受了损失,那么投资者将被赋予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与前两个SGS案不同的是,该案的合同当事方是在约旦国内法上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地方政府,而并非东道国本身。仲裁庭在参照前两个SGS案例的裁决后,认为合同与条约的签订方完全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因此,条约与合同争端应当依照各自规定的不同方式加以解决,其对该案不具有管辖权。由条约措辞可知,意大利—约旦BIT中的第2条第(4)、(5)两款的规定着重强调的是东道国在为对方投资者提供良好法律环境的层面上负有严格义务,而非承诺承担一切保护义务。所以,仅从字面解释的角度也不能得出该条款具有“保护伞条款”的性质。因为传统的“保护伞条款”中没有区分法律或是非法律义务,而是将东道国需要承担的所有有关投资方面的义务,使用高度概括性的措辞统一纳入条款中。从严格意义上看,意大利—约旦BIT中包含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伞条款”。诸如此类的条款,我们只能称其为“履约保证条款”。这种条款只是缔约双方就某一个具体问题,或某一具体领域的问题所作的履约保证承诺。正如意大利—约旦BIT中约定的那样,东道国仅负有良好法律环境的创设与维护的义务。投资者可以对东道国没有履行其在“履约保证条款”中所承诺的义务而造成的违约行为提起仲裁,但这一仲裁是完全基于BIT的。这与投资者基于其与东道国签订的具体合同中的“履约保证条款”而提起的仲裁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涉及的是东道国对两国间条约的违反,招致的是国际法上的责任,应当依据国际法裁判;而后者涉及的是东道国对其与投资者个体间合同的违反,招致的是东道国国内法上的责任,应当依据东道国的国内法裁判。
与Salini v.约旦的裁决相反,在Noble Ventures v.罗马尼亚一案中,美国投资者对于其与罗马尼亚国家基金因合同产生的争端,依据美国—罗马尼亚BIT第Ⅱ(2)(c)款的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当遵守其做出的有关投资方面的所有承诺”,向ICSID提起了仲裁。而罗马尼亚政府认为,此条款的目的仅在于对东道国的国家主权做出一定的约束,使得其不得使用国家主权侵害具体投资活动中投资者所享有的权利。合同争端应当受罗马尼亚国内法而非国际法的管辖①Noble Ventures v.Romania ICSID Case No.ARB/01/11。仲裁庭在参考了美国—罗马尼亚BIT第Ⅱ(2)(c)款后,认为该条款中出现了“应当”﹑“与投资有关”﹑“所有”等强制性字眼,证明了该条款从本质上看,已经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伞条款”。因此,依据该条款的规定,作为罗马尼亚政府附属机构的罗马尼亚国家基金违反合同的行为应当视为是对美国—罗马尼亚BIT中“保护伞条款”的违反,是对BIT的违反,仲裁庭对此争端享有管辖权。
Salini v.约旦与 Noble Ventures v.罗马尼亚两个案件的审查过程都涉及了对申请者提出的BIT中“保护伞条款”性质的界定。两个案件的仲裁庭都是从条约文本的字面意思入手,结合缔约方签订条约的目的进行裁决,但却做出了不同的裁决结果。其中,对于缔约方签订双边条约的目的—“保护”和“促进”国际投资这一问题,两个条约缔约方的态度是一致的,使得案件产生完全不同结果的关键,则在于当事方所主张的“保护伞条款”使用的措辞不一样。前案条款中使用了限制性的,具体的措辞;后案条款中使用了概括性的,笼统的措辞。前案条款最终仅被认定为“履约保证条款”,而后案条款则被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伞条款”。这一点明确体现了ICSID仲裁庭在对外国投资者试图通过其母国与东道国签订的BIT中的“保护伞条款”将其与东道国间合同争端上升至国际管辖层面时,仲裁庭所奉行的抛开前例,个案分析的态度。
三、“保护伞条款”在争端管辖权确定中的双重性
现代BIT中“保护伞条款”的存在,体现了资本输入国在经济发展中对于资本的渴求,进而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做出特别承诺。资本输入国在与资本输出国签订BIT时,对于有关“保护伞条款”的措辞并无国际统一标准可循。正如前述案例分析中所言,约文不同的措辞正是形成案件不同裁决结果的关键。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的条约解释原则,在进行条约解释的时候,应当遵循条约的文本意思并要参考条约签订的目的。正是基于此种解释原则的规定,约文所使用的措辞就将决定其是否具有“保护伞条款”的性质。“保护伞条款”与“履约保证条款”的区别在于对东道国的义务做出了何种规定。如果缔约国在BIT中并没有说明“一国将履行其在有关投资方面做出的任何承诺”,而仅是约定其将在诸如“法律环境的改善”、“投资待遇的提高”等具体方面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么这样的条款从文本解释的角度出发,就不会被认定为“保护伞条款”。但是投资者同样可以通过“履约保证条款”将其与东道国间的争端提交至相关的国际仲裁庭。在此种情况下,投资者依据的完全是BIT中的“履约保证条款”。东道国的某些行为如果没有达到该条款规定的要求,那么其的确是违反了条约,负有国际法上的责任。这样的申请,将很容易得到相关国际仲裁庭的认可。但是“履约保证条款”中规定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相对而言比较单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满足对投资者给予全面保护的要求。而这种缺陷却能够被保护范围广泛的“保护伞条款”所弥补,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希望将其与东道国政府间的合同争端通过“保护伞条款”国际化。但是此种意愿在实践中并不会一帆风顺。
首先由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法律秩序不同。因此,国家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上所代表的意义和所承担的责任也就不同。在国内法中,国家既可以作为象征主权的公权力一方的代表者,也可以(大部分情况是在商业环境中)作为私权利一方的代表者。而在国际法中,国家只能是以主权权利的公权力者的身份承担责任与义务,其不具有私权利的性质[4]。那么在有“保护伞条款”存在的BIT中,东道国与投资者间的合同之争,就存在着被赋予双重性质的可能性。东道国没有遵守其与投资者在相关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就商业合同的本质而言,东道国的这种违反合同的行为应该受到相关国内法的管辖。如果违反合同行为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如没有按约定时间交款等)那么就更应当只接受东道国内国法律的管辖。但是“保护伞条款”的适用,使得东道国违反合同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违反了其在“保护伞条款”中做出的“遵守与投资相关的所有义务”的承诺。东道国的一个行为触发了对两种性质约定的违反。此时,对于东道国违反合同的行为,是属于行政性质的违反合同,还是商业性质的违反合同,应当加以区别对待。若国家利用掌握公权力的优势,利用行政手段侵害投资者的权利,则应认定其行为构成了对BIT中承诺义务的违反。此种情况下,投资者通过“保护伞条款”寻求相应的国际救济不啻为一种好的选择。因为“保护伞条款”存在的意图,就在于为了避免东道国运用国家权力通过国内立法,颁布行政命令等手段随意侵害作为弱势的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但是,如果东道国违反合同是由纯粹的商业行为引起的,那么投资者试图通过“保护伞条款”将争端国际化的做法就有待斟酌。毕竟双方因商业行为引发的争端,在东道国国内解决更为妥当。这符合东道国的国内法,也是对东道国司法主权的尊重。况且通常情况下,在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争端解决方式与管辖法院的选择,都是以东道国内国法律为标准的。这样的约定反映了作为当事双方订立合同时的合意,理应受到尊重。正如在Vivendi一案仲裁庭的裁决中指出的:“如果一个投资者希望将其与东道国的合同争端提交到国际仲裁庭,那么首先它应当遵守其在合同中所承担的义务。”①Vivendi,ICSID Case No.ARB/97/3很明显,仲裁庭认为投资者只有在首先履行了其在合同中承担的义务才有资格将其与东道国的合同争端提交至ICSID解决。而在Vivendi案中投资者所承担的一项重要合同义务就是需要用尽东道国的当地救济。
其次,相关国际仲裁庭在接受投资者通过“保护伞条款”诉东道国的合同争端时,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裁定合同中争端解决条款的效力。对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院,仲裁庭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在Aguas del Tunari一案中,仲裁庭认为投资者与东道国仅在合同中约定了管辖法院并不代表当事人放弃了其向相关国际仲裁庭提起仲裁申请的权利,除非当事方在合同中明确表明其放弃国际救济的权利。否则,合同中“管辖法院选择条款”本身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其就是当事方所选定的唯一有案件管辖权的法院[5]。但是,SGS v.菲律宾和Vivendi两个案件的仲裁结果表明,一个有效的“管辖法院选择条款”就可以排除其他法院或是相关国际仲裁庭对案件的第一管辖权。那么,对于投资者与东道国合同中的“管辖法院选择条款”的效力应当如何界定,该条款的存在是否能够完全排除其他法院与仲裁庭对案件的管辖?Aguas del Tunari一案的仲裁庭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法。该案仲裁庭通过两个独立的步骤来验证“管辖法院选择条款”可以有效排除相关国际仲裁庭基于条约对于争议享有的管辖权。第一,投资合同中的“管辖法院选择条款”必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ⅰ相同的争端当事方;ⅱ相同的争端问题;ⅲ“强制性义务冲突”第二,必须有投资者的明确表示,表示其在合同中约定了“管辖法院选择条款”的情况下,愿意放弃相关国际仲裁庭的管辖[5]。尽管此种方法明确了在何种情况下,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签订的合同中的“管辖法院选择条款”具有排他性效力,但是实践中,投资者与东道国签订“管辖法院选择条款”时并不会特意附加其是否愿意放弃相关国际仲裁庭管辖的表示。即使投资者在合同中做出这样的说明,也仅仅是针对其与东道国间对于合同争端解决方式的约定。在“保护伞条款”存在的情况下,投资者将可以直接就东道国违反其在BIT中该条款项下做出的承诺,提出对东道国的违约之诉,而东道国没有遵守合同的行为将成为投资者诉东道国违反双边条约的证据,而非如前述案件实践中将其作为起诉东道国的诉因。此种情况下,投资者仍然可以绕过其与东道国合同中的“管辖法院选择条款”,将本质上应为合同管辖的争端国际化。“保护伞条款”的存在为投资者提供了广泛的保护,但同时也使投资者动辄使用条约中约定的争端解决方式来解决合同争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争端解决的法律成本。
四、结语
BIT中的“保护伞条款”就像一把双刃剑,就限制国家利用公权力通过修改法律,或使用相关行政手段干涉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层面而言,“保护伞条款”的存在使得东道国在实行上述行为之前会考虑其可能承担的国际责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投资者的权利。但东道国为吸引更多外资做出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之后将要面临诸多的国际仲裁埋下了隐患。由于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司法系统公正性以及东道国内国法制的不信任,他们往往倾向于将与东道国间的争端提交到相关的国际仲裁庭。即使是在合同中规定了争端解决方式和管辖法院的情况下,投资者还是会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将争端解决国际化,而不论该争端在国内是否已经或者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保护伞条款”的存在无疑为投资者寻求此种争端解决国际化的方式提供了便利。然而,投资者与东道国间基于合同的争端,相关国际仲裁庭是否享有管辖权,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对于“保护伞条款”的措辞,其性质与效力的认定,合同中“管辖法院选择条款”性质与效力的认定等问题,不同仲裁庭可能会得出不同的仲裁结果。ICSID仲裁庭在审查相关争端时,采用了个案分析法。仲裁庭会参考先前相似案件的仲裁结果,但其将会更忠于本案的情况。尽管到目前为止,因“保护伞条款”提起的国际争端已为数不少,但在BIT实践中,该条款仍被广泛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条款的价值与作用。中国此前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入国,已签订了上百个BIT,但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以及各类鼓励对外投资政策的出台,本世纪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中国也将因此具有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身份。在此情势下,中国在签订或修改BIT的过程中,就需要对“保护伞条款”给予高度重视,切不可使用高度概括性的措辞,加重我国的义务,而应对“保护伞条款”的使用范围做出明文限制,将单纯的商事合同争端排除在外,并对其与合同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所可能产生的冲突进行协调,很好的利用这把双刃剑,使其为我国的国际投资活动更快更好发展做出贡献。
[1]陈安.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Christoph Schreuer,Travelling the BIT Route of Waiting Periods,Umbrella Clauses and Forks in the Road,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Trade[J].2004,(5).
[3]Thomas W.Waled,The“Umbrella”Claus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A comment on Original Intentions and Recent Cases,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Trade[J].2005,(6).
[4]Bjorn Kunoy,Singing in the Rain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Umbrella Clauses,The Journal of Investment& Trade[J].2006,(7).
[5]John P.Gaffney & James L.Loftis,The“Effective Ordinary Meaning”of BITs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reaty -Based Tribunals to Hear Contract Claims,The Journal of Investment& Trade[J].2007,(7)
[责任编辑 李晶晶 责任校对 王治国]
DF964
A
1000-5072(2011)01-0035-07
2010-12-07
封 筠(1982—),女,陕西咸阳人,暨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