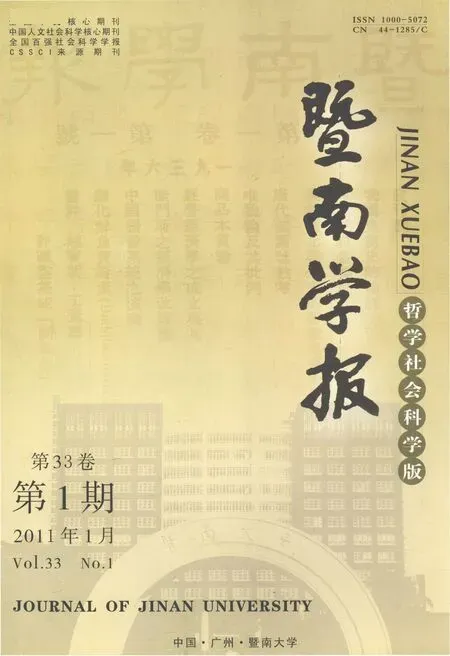数词非范畴化现象考察*
陈 勇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数词非范畴化现象考察*
陈 勇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通过句法分布、语义变化、语篇功能及范畴转移等方面考察,数词在非范畴化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句法分布特征的扩展;语义丧失、转指、抽象泛化;语义、语篇功能被强化。非范畴化的结果必然带来范畴转移,而以词汇化或语法化为手段在词汇层面所遗留的痕迹成了这种“转移”最有力的佐证。
数词;非范畴化;转移
一、引 言
数词在汉语词类系统中始终居于次要地位,与名、动、形等典型词类相比,在以往的研究中,其关注度并不高。以往对数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词的“归属”问题,如吕叔湘 朱德熙[1]、丁声树[2]、张志公[3]、朱德熙[4]等等;二是数词的分类,如吕叔湘[5]、王力[6]、朱德熙[4]等等;三是后期的研究多见于一些零散的个案分析,如邢福义[7]、冯雪梅[8]、舒志武[9]等等。这些研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数词在汉语词类系统中的地位,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都是以范畴的静态描写为基础,而对“数词”范畴内部的动态性关注不够,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鉴于此,本文将以非范畴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数词这个词类范畴,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数词句法特征的丧失与扩展;二是数词语义的丧失、转指、抽象泛化;三是数词在语篇功能上的扩展;四是功能扩展与范畴转移。
二、数词的范畴属性特征
根据范畴的属性特征(categoriality),一个原型意义上的数词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从语义上看,它具有“数量意义”,即数目义和次序义;从句法分布特征上看,它不单独充当句法成分[10][11],主要分布于定语位置(或称修饰语);语义功能上,它一般没有指代功能,“无论对名词还是动词都没有指代功能,都是普通的一种修饰性成分”[12]207,也不具有陈述功能;语篇功能上,其语篇能力较弱,更不具有篇章回指功能。
“非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指范畴成员在一定的条件下逐渐失去范畴属性特征的过程[13],据此,我们认为数词非范畴化的过程实际就是数词丧失范畴属性特征的过程,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句法分布特征的扩展,由“定语”位置扩展到“状语”、“主语”、“谓语”、“宾语”等位置,由“修饰语”扩展到“中心语”,且结构形式上存在一定的词汇化或语法化倾向,这些形式上的扩展实际是数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一种外在表现;二是语义的丧失、转指、或抽象泛化;三是语义、语篇功能被强化,即由“非指称、陈述功能”扩展出“指称、陈述功能”,由“非篇章回指功能”扩展出“篇章回指功能”,这些功能的扩展实际是数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表现。
三、句法分布特征的丧失与扩展
语言非范畴化在外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范畴某些典型的句法分布特征丧失,范畴之间的对立中性化”[13]。在汉语中,数词的句法特征单一,分布于定语位置,而在定语位置通常与量词配合使用。因此,我们认为数词的非范畴化主要表现为“去定语(或者修饰语)化”。通过实际考察,数词可在句中直接充当状语、主语、宾语等成分。
(一)数词充当状语
数词充当状语是数词非范畴化过程中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在句中可直接修饰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其本义不同程度丧失。如①本文所引例句未标明出处的均来自北大CCL语料库。:
(1)一打听,原来都是“候鸟型”新客人开办的。
(2)然而唯独没有正宗的茶类液体饮料商品问世,可谓“千呼万唤不出来”。
(3)开发区天津开发区秉持“循环经济”理念,正努力实现区内废物的“零”排放。
(4)尽管美国监管机构认为高盛犯有欺诈罪名,但他仍百分之百支持高盛集团。(《齐鲁晚报》2010-05-03)
(5)……我确定的是,我是百分之百干净的。(《齐鲁晚报》2010-5-4)
(6)……这么四平八稳的,我都要打瞌睡了。(《齐鲁晚报》2010-03-24)
数词做状语时,其计量意义受到磨损,其本义丧失,因此,不可被其他数词替换。如例(1)“一打听”不能说“二打听”或“三打听”,这里的“一”作为状语并非表示“一次”,而表“瞬时”。例(2)-(4)中的“千、万、零、百分之百”这些数词直接做状语,泛指动作强度的高低,其本义基本消失,也不具有可替换性。数词直修饰形容词,泛指“程度”的高低,其本义也丢失,如例(5)、(6)中“百分之百、四、八”这些数词表示“程度”,不再表数量意义。
这类非范畴化现象在词汇层面上也有一定遗留的痕迹(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收录为依据),如:“百出、四起、四散、四伏、四顾、多谢、多亏、三思、万恶、万全、万幸”。这些数词已经以状语性成分“并入(incorporation)”②“并入”指语义上独立的词进入另一个词的过程。[21]到了动词或形容词,其数词本义不同程度丧失,大部分已经词汇化,少部分虚化,如“多亏”是副词,“多”已经丧失了数量意义。
(二)数词充当主、宾语
数词充当主、宾语是数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另一种外在表现。如:
(7)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二,一是追风盘盲目追捧,二是……。(《京华时报》2003-6-20)
(8)他们就实行买一送一,甚至买一送二,亏损部分由县财政补贴。
例(7)中“二”充当“有”的宾语,实际表示“两种”,“一”充当主语,实际表示“第一种”。例(8)中“二”、“一”实际分别充当“买”、“送”的宾语,而二者也具有了指称意义。
来自词汇层面一些非范畴化的痕迹,如:“三不知、吆五喝六、接二连三、统一”。(以《现汉》收录为依据)。这些词中“三”与“五、六、二、三、一”分别以主、宾语形式融入了动词,其数词本义也不同程度丧失。这种非范畴化现象的痕迹还可见于一些惯用语中,如“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类结构中的“一、二”数词本义已丧失,并以宾语成分并入动词,整个结构的语义已经被重新整合,泛指“有什么说什么”。
(三)由修饰语变为中心语
在句法结构中,数词始终遵循着汉语的“修饰语+中心语”的普遍规则[12]。而数词由修饰语变为中心语,则是数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另一种外在表现。这种非范畴化现象可见于“名+数”这类形式,这种结构实际表示“名词修饰数词”。如:
(9)理由一,刘与被告签的合同是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南通市公证处公证的;理由二……。(《江南时报》2006-03-23)
(10)……事件单元里写的是一年多时间里发生的同类事件一、事件二、事件三。(《新闻战线》2003年第6期)
例(9)中“理由一、理由二”实际表示“理由的第一、二种”。例(10)中“事件一、事件二、事件三”,实际也是“事件”修饰“一、二、三”。在“名+数”这种结构中,我们认为是这些数词实际也具有了指称功能。
这种非范畴化现象被进一步证实还可见于“名+之+数”这种形式,“之”相当于“的”。如:
(11)成果之二是缅甸承办了首届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4国经济合作战略峰会。
例(11)“成果之二”实际表示“成果的第二个或第二种”,这类形式也可说成“成果二”。在这种结构中,数词实际也被赋予了指称功能,“二”实际指代“第二种/个(成果)”。
四、语义变化
语义变化是语言非范畴化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表现,主要表现为“语义抽象与泛化”[13]64,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语义的丧失或转指也能够带来范畴的转移,在语言中不乏一些以词尾或词缀形式存在的黏附语素,这些语素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语义,是非范畴化的产物。某种程度上来说,“转指”实际上就是“旧瓶装新酒”,即旧的形式被赋予新的意义,只不过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丧失”。因此,我们认为非范畴化过程中的语义变化实际表现为:语义的丧失、转指、抽象泛化。
(一)语义丧失
数词的本义经过长久的使用,受到磨损,以致丧失,我们认为这种磨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表层结构的磨损,即数词直接与其他词组合,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凝固词汇化,导致其数量意义丢失。如:
(14)南北朝时有斗鸡、打毯,唐朝时有秋千和拔河,甚至称清明为秋千节。
(15)邓曾告知,“左岸”出过一套“千纸鹤”系列丛书,在全国书市上创下了销量新纪录。
(16)杜拉拉没有花花肠子,没有八卦同事绯闻的嗜好……。(《齐鲁晚报》2010-04-16)
例(14)、(15)中“秋千”、“千纸鹤”这些词在产生之初,数词“千”都有一定的数量所指,但是历经长久的使用,其本义已经消失殆尽。“八卦”中的“八”原指“乾、坤、巽、兑、艮、震、离、坎”八种基本图形,而例(16)中“八”的数量意义完全消失,这里的“八卦”指“制造传播流言蜚语”[14]。
二是来自深层结构的磨损。有时,一些数词并不是来自表层数量结构,而来自深层的数量结构,它被“多重深层结构”过滤后,数量意义不断磨损,以致最终丧失。如:
(17)四川是个很美的地方。(自拟)
(18)六盘水市的各级领导更把希望工程看作是一座桥。
例(17)“四川”中的“四”原指“川峡四路”,即“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和夔州路”,四川是“川峡四路”缩略而得名,因此,“四”这个数词实际经历了两种结构的过滤:“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和夔州路”→“川峡四路”(缩略)→四川(词汇化)。所以,“四川”这个词不是说“四个川”。例(18)中“六盘水”取“六枝、盘县、水城”三个县字头而得名,“六盘水”中的“六”也已经非范畴化,其数量意义消失,“六”实际也经历了深层结构的长期磨损:六枝(初为一种数量组合)→ 六枝(专有名)→“六枝、盘县、水城”(缩略)→ 六盘水(词汇化)。
这类现象在汉语中还许多,如:“百姓、百灵鸟、三元里、九寨沟、九江、百色市、百事可乐、万金油、六安、八达岭、百合、六甲(怀孕)、千张(一种薄的豆腐干片)”等等。这些词中的“数词”语义已经不同程度丧失。
(二)语义转指
数词丧失本义的同时衍生出一种新的意义。Hopper& Traugott[15]125认为“较旧的意义一般是更为具体的,较新的意义往往是更为抽象的”。“转指”实际上是数词的外在形式被赋予新的、更为抽象的意义,而并非具体的数量意义,前后两者之间表现为一种“相关性”。如:
(19)1989年“六一”期间,这出剧应邀在北京演出,笔者随团去采访。
(20)说起来也怪,6月6日,按迷信说法,应该是“六六顺”的日子……。
(21)别看他哭,他心里在笑,笑广大群众是二百五,好哄。
(22)妻子疑惑地说:“那我刚才回家怎么听见儿子在他房间里说什么‘死三八’‘臭三八’,害得他没电视看。”(《京华时报》2004-10-22)
例(19)中的“六一”转指“儿童节”,它已经不具有数量意义,此类数词还有:“五一(国际劳动节)”、“ 十一(国庆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五四(青年节)”等等。例(20)中“六六”转指“顺利”的意思,汉语中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如“四”通过谐音转指“死”,“八”通过谐音转指“发达”。例(21)、(22)中的“二百五”、“三八”都是骂话,转指“傻、蠢”等意义,这些数词的本义实际已经丧失。
(三)语义抽象泛化
数词的计量功能受到磨损,其语义也不断弱化、抽象化,并泛指出新的意义。语义的抽象泛化实际是建立在旧意义上的一种抽象的泛指,是“概念细节逐渐减少到只剩下语义核的过程”[13]。郭攀[16]指出“较大的数目性表达形式,表示‘多’类状态义的频率较高……相反,较小的数目性表达形式,表示‘少’类状态义的频率较高……”。他还指出“任何一个数目皆可以独立或联缀等形式相对性地表‘多’或‘少’”。在汉语中,数词语义的抽象泛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泛指“多”义;二是泛指“少”义。
1.泛指“多”义。
数词“三”及其倍数“六”、“九”等都可以泛指“多”义,这一用法在汉语中较为常见。如:
(23)他们的非常戏剧化的生动故事,敢说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人民日报》2009-6-4)
(24)小老头道:“举一反三,孺子果然可教!”
(25)小酒馆里更是热闹,三教九流,在这里聚首碰头。
(26)杨先农想不通,责骂他六亲不认。
(27)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8)阿拉法特历经劫难,九死一生。
例(23)中“三天三夜”并非是三天加三夜的时间,而泛指时间久,是一种夸张说法。例(24)-(28)中的“三、六、九”都是泛指“多”义,其数词本义被抽象泛化。“举一反三”表示“从一件事情类推而知道许多事情”。“三教九流”实际泛指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六亲”泛指各个亲属。“六路”泛指周围,各个方面。“九死”表示经历的劫难多。
空间范畴下的一些数词诸如“四”、“八”等可泛指“多”义,表示“各”的意思。如:
(29)最后,起义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黄兴的威名却远扬四方。
(30)家徒四壁,八面来风,捉襟见肘,可他还请客……。
例(29)、(30)中的数词“四”、“八”被抽象泛指“各”的意思,“四周、四方、八面”实际表示各个方向。这类词还有“四周、八方、四野、四边、四围、四出、四处、四方、四近、四面、四外、四下里”等等。
“百、千、万”也可泛指“多”义[17]。如:
(31)看着14岁少年坐着轮椅渐渐远去,让我们百感交集。
(32)……只是这样一来,沈辰就不至于成为千夫所指了!
(33)他感到万念俱灰,甚至尝试过自杀。
例(31)-(32)中的“百、千、万”并非数词本义的用法,而是泛指“多”(或程度高)。再如“一落千丈、百叶窗”中的“千、百”也是泛指“多”义。
数词也可以联缀成一些格式泛指“多”义:“三…五…”这一格式泛指“次数多”,如“三番五次”、“三令五申”;“四…八…”泛指“多或程度高”义,如“四面八方”、“四平八稳”、“四通八达”、“四邻八乡”;“七…八…”泛指多或多而杂乱,如“七扭八歪、七拐八弯、七零八落、七嘴八舌、七拼八凑、七手八脚、七长八短、七上八下、七折八扣”;“千…百…”泛指“多或程度高”,如“千疮百孔、千锤百炼、千方百计、千奇百怪、千姿百态”;“千…万…”,泛指“多或程度高”,如“千变万化、千丝万缕、千家万户、千难万险、千真万确”。
2.泛指“少”义。
数词泛指“少”义,主要见于一些小数目的用法,通常是“一、二(两)、三、半”等。如:
(34)日后几番恶补,才对青花略知一二……。(《人民日报》2010-2-3)
(35)而他夫妻两地分居15年,其中的悲欢酸甜,又岂能三言两语道清。
(36)看起来,作案的歹徒对三新公司情况是一知半解。
例(34)中“一二”并非指数词“一”和“二”,在这里实际泛指“少”义。例(35)、(36)中的“三”、“两”、“一”、“半”也表示“少”的意思。
“两”这个数词可单独泛指“少”义,相当于“几”,与英语中的“a few”[18]301-312,如:
(37)a他喝了两杯酒就醉了。(引自蔡文)
b他没喝了两杯酒就醉了。(他没喝了几杯酒就醉了。)(同上)
例(37)a中“两”是实实在在的数词,这里可用“一、三”等其他数词替换,而例(37)b中“两”并非数词本义用法,而泛指“少”义,不能够被其他数词替换,但可被“几”替换,表达意义一样。
五、语篇功能的扩展
语言非范畴过程中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范畴成员“在语篇和信息组织上,发生功能扩展或转移”[13]64。数词并不能够指称现实的客观事物,它不具有指称意义(这一观点不同于逻辑语义学的指称论),其语篇能力较弱。因此,数词非范畴化过程中另一种内在的表现则是语篇功能的扩展。以下,有关数词语篇功能扩展,我们主要讨论这两种形式:“NP之一”和“NP+之+数词”。
(一)“NP之一”中数词“一”的回指功能
NP一般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从句法构造上看,数词“一”居于中心语位置,“NP”为修饰语,“NP之一”实际可表示“NP(中)的一个或一种”,处于中心语位置的数词实际具有了指称功能,且有具体所指,与另一种形式“NP+之+数词”相比,“NP之+一”一般不具有序列性,因此,数词“一”不具有可替换性。如:
(38)大兴安岭是我国东北部的著名山脉,也是我国最重要的林业基地之一。
例(38)中的“一”处于宾语位置,已经具有指称功能,且有具体所指,不可被其他数词“二、三、四”等替换。句中“一”实际可回指“大兴安岭”,因此,这里的数词“一”发生了非范畴化。
数词“一”以指称的形式出现在语篇结构中,是数词非范畴化的一种表现,同时,它具有了语篇回指能力。在语篇中,这类形式中“一”的回指功能还比较复杂。大致有以下类:
从“一”所回指的方向看,可分为前回指、后回指、双重回指。如:
(39)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军战将中年龄最高者之一 ,但他仍然老当益壮,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40)我上学早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长得高。
(41)他就是为维新变法而献身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杰出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先驱谭嗣同。
例(39)中的“一”有具体所指,前回指“朱德”,例(40)中的“一”也具体所指,回指“我长得高”,而例(41)中的“一”实际具有双重回指功能,“一”前回指“他”,同时又后回指“谭嗣同”。
从“一”的句法位置来看,可分为主语形式回指、定语形式回指、宾语形式回指。如:
(42)上海东方队的球迷那么想,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我在。
(43)三大肥料之一的磷肥,既能促进种子发芽生根,加速植物的生长……。
(44)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例(42)中“一”在句中处于“主语”位置上,以主语形式回指“有我在”,例(43)中的“一”则处于修饰语或定语位置上,以定语形式回指“磷肥”,例(44)中的“一”则是以宾语形式回指“林彪”。
从“一”回指距离的远近看,可分为近回指、远回指、超强回指。如:
(45)大统一理论的结论之一是预言质子要衰变,这与实验结果有矛盾。
(46)石墨是松软的、不透明的灰黑色细鳞片状的晶体,它同金刚石恰恰相反,是最软的矿物之一。
(47)蜘蛛的适应性也很强。有的能耐46℃的高温,有的能耐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这也是蜘蛛成为广布性种类的原因之一。
“一”与所回指的内容具有邻近关系,如例(45)“一”后紧接着“预言质子要衰变”。“一”有时与所回指的内容距离较远,但仍是句内回指,如例(46),“一”实际回指“石墨”,两者并非邻近关系,而是处于不同的分句之中。如果“一”与所回指的内容距离更远,则为一种超强回指,这种回指主要表现为一种跨语段回指,如例(47)中“一”回指“这”的同时,实际回指的是语段,即“有的能耐46℃的高温,有的能耐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
(二)“NP+之+数词”的数词回指功能
“NP+之+数词”中的“数词”除了表示一种顺序意义,同时也具有指称功能。从句法形式上看,“数词”仍处于中心语的位置,而“NP”是修饰语,且具有指称意义的“数词”也被赋予了较强的篇章回指功能。
(48)……他垮台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耐心。……原因之二是他在遏制那些威胁他的国家的稳定的人们时,还不够残酷无情。
例(48)中“一、二”实际指“第一种、第二种”,且分别回指“缺乏耐心”、“他在遏制那些……残酷无情”。“一、二”在句法结构中处于中心位置,而“原因”是修饰语,且二者具有指称功能。
有时,作为修饰语的NP显得并不重要,可以省略,这进一步证实“NP+之+数词”中“数词”的中心语地位,且它具有指称功能,这是数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功能迁移的一种外在表现。如:
(49)但放弃总是难于做到,原因之一是舍不得,之二是从反面证明为没有是同样不容易。
(50)两原则之一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之二反对单纯以生产关系为标准衡量发展水平,应当说是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例(49)中“之二”前承前省略了修饰语“原因”,例(50)中“之二”前承前省略了修饰语“两原则”。这些承前省略了修饰语的“之+数词”结构,某种程度上说,强化了其指称功能,同时也强化了语篇回指及衔接功能,而结构中的数词都有具体所指,表示“第一、二个/种”等等。
以上,我们主要讨论了两种形式中数词在语篇功能上表现出的较为明显的非范畴化特征,当然,这并不表示没有其他情形存在,只是这两类较为典型,也比较常用。“NP+之+一”与“NP+之+数词”中的数词在功能上发生迁移,两类结构中的数词处于中心语位置,具有指称功能的同时,又被赋予了较强的篇章回指及衔接功能,这成为我们研究数词非范畴化特征的较好的案例。
六、功能扩展与范畴转移
功能扩展实际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即“表义功能和句法功能”[13]148。数词的语义较为单一,在语义功能上一个原型意义上的“数词”不具有指称功能和陈述功能。因此,在非范畴化过程中,数词的内在表现实际是其语义功能的扩展,即由非指称、陈述功能扩展出指称、陈述功能。以下,我们先讨论数词在主、宾语位置上所获得的指称功能(也见第五小节中的相关论述)。
在“数词+是+……”一类“是”字小句中,数词已经占据了主语位置,它不单表示序列意义,实际已经获得指称功能。如:
(51)化学毒剂在战场上有3种散布方式,一是爆炸法;二是加热蒸发法;三是布洒法。
例(51)中“一、二、三”实际指称“第一、二、三种散布方式”,这从文中“有3种散布方式”可以看出,这些数词实际已具有了指称功能。
宾语位置的“数词”较多处于动词(或介词)之后,同样,也能获得指称功能。如:
(52)……原因有三:一是毛仁风常出国谈生意,一出去就是三两个月;二是他在北京有好多套别墅……。
(53)……但女足教练选来选去,只能二挑一。
(54)秋宝一周纪念的时候,这家热闹地排了一天的酒筵,客人也到了三四十……。
对比例(51),我们会发现,例(52)中的“有三”实际表示“有三种原因”,“三”是动词“有”的宾语,实际指称“三种原因”。例(53)“二挑一”实际表示“两个人中挑一个”,数词“二、一”也都具有了指称功能,例(54)中“三四十”充当宾语,实际指称“三四十人”。
这些来自主、宾语位置的数词所产生的范畴转移现象在汉语中并不是无迹可寻,除了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类形式外,再如“一是一、二是二”,表示“说话老实,不含糊”,这类结构中的数词发生了非范畴化,其原因实际是句法语义功能的扩展所致。
数词语义功能的另一种扩展途径则是由非陈述功能扩展出陈述功能。数词可直接做谓语,而充当谓语的数词实际也具有了陈述功能,这是数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表现。如:
(55)东西长六十六丈,南北宽二丈四尺,两栏宽二尺四寸,石栏一百四十,桥孔十有一,第六孔适当河之中流。
(56)罗切斯特先生已快四十啦,而她只有二十五岁。
(57)他今年已经三十五了,还没有结婚。(自拟句)
例(55)中“一百四十”直接做谓语,已经扩展出陈述功能,这里实际所指是“一百四十尺”。例(56)、(57)中数词的陈述功能更为明显,这些数词前面可出现副词“已、快、已经”等,后面也可出现语气助词“了、啦”等。
数词由非陈述功能扩展出陈述功能所产生的范畴转移主要表现为“数词谓词化(或动词化)”,也就是说,一些数词可能演变为动词或形容词,在汉语中这样的现象也存在,如“二百五、三八”等。其实,在英语中也不乏类似的情况:“eighty-six(无货供应)”、“nine to five(被正式雇用做办公室工作)”、“zero in(把……对准目标)”。[19]17-18有关数词句法功能的扩展,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数词直接做状语、谓语、主语、宾语等;由修饰语变为中心语。我们在第三小节中已作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句法功能的丧失与扩展是数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外在表现,而语义的变化以及语义、语篇功能的扩展则是数词非范畴化过程中的内在表现,这种“内”、“外”结合致使数词发生一定的范畴转移。
七、结语
对于数词,传统的研究多集中于一种静态的描写,如“分类”等等,本文并没有局限于这种静态的描写,而是以“动态”的观念重新审视了数词这个词类范畴,并获得了对数词的一种全新认识。在非范畴化过程中,我们认为数词所呈现出的特征可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特征,表现为句法分布特征的扩展,即由“定语”位置扩展到“状、主、谓、宾”等位置,由“修饰语”扩展到“中心语”。二是内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语义的丧失、转指或抽象泛化;语义、语篇功能被强化,即由“非指称、陈述功能”扩展出“指称、陈述功能”,由“非篇章回指功能”扩展出“篇章回指功能”。
这些非范畴化现象必然会以词汇化或语法化为手段在词汇层面沉淀一定的“遗留物”,而这种“遗留物”是研究过程中有力的证据。
[1]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北京:北京开明书店,1952.
[2]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4]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
[7]邢福义.现代汉语数量词系统中的“半”和“双”[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4):36 ~56.
[8]冯雪梅.数词“多”用法补义[J].襄樊学院学报,2000,(3).
[9]舒志武.数词“三”的文化意义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32~137.
[10]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1]张斌.简明现代汉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2]石毓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刘正光.语言非范畴化—语言范畴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4]李国正.古词新用说“八卦”[J].语文建设,2004,(Z1).
[15](美)鲍尔·J·霍伯尔、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著.梁银峰 译.语法化学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6]郭攀.汉语涉数问题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7]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8]蔡维天.“一、二、三”[J].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輯)[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9]张定兴.略谈英语数词动词化及其翻译[J].中国翻译,1995,(3):17 ~18.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1]Mark C.Baker.1987.Incorporati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责任编辑 范俊军 责任校对 吴奕锜]
H146
A
1000-5072(2011)01-0105-08
2010-11-17
陈 勇(1979—),男,湖南常德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
*本文承蒙彭小川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