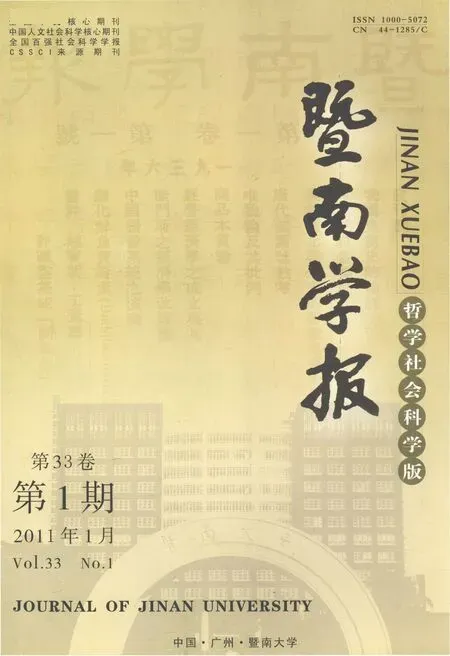何明华与基督徒学生活动之研究
吴 青
(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32)
何明华与基督徒学生活动之研究
吴 青
(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32)
何明华是香港圣公会第七任英籍会督,也是一位香港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华历时四十四年,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变迁。他与中国的渊源始于基督徒学生活动,该活动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
圣公会;何明华;基督徒学生活动
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1895 -1975)是香港圣公会第七任英籍会督,也是一位香港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于圣公会是英国国教,因此该会不同于一般的基督教会,在香港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过往的香港殖民政府一直依赖教会的协助进行统治,故昔日香港有两督,分别为香港总督和圣公会会督,他们在香港的殖民地模式管治中虽分工不同,但都对香港社会起到决策性作用。目前国内学界对圣公会会督何明华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的研究成果来自英美和香港。①国外的研究主要有英国学者David M.Paton的R.O.:The Life and Times of Bishop Ronald Hall of Hong Kong(Hong Kong: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 Hong Kong Diocesan Association,1985)、美国学者 Brown,Deborah A.的 Turmoil in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Rule:The Fate of the Territory and Its Anglican Church(San Francisco: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1993)、香港的专题研究有曾国华《何明华会督(1895-1975)对香港之社会及教育之贡献》(香港大学文学硕士论文,1993)、吴青《何明华及其与中国关系之研究(1922-1966)》(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论文,2008)等。前人对他的关注较多集中于何明华在香港的活动,相对忽略了他与中国的关系。实际上,何明华在中国历时四十四年(1922-1966),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新中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与中国的深厚渊源正是始于基督徒学生活动,该活动由英国传入中国,曾一度活跃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基督徒学生群体当中。本文主要阐述青年时代的何明华通过基督徒学生活动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历程,并总结基督徒学生活动失败的原因,反映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政治处境中的角色。
一、何明华其人
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于1895年7月22日,出生在英国一个传统的基督徒家庭。青年时代的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服役于法国战场。战争结束,他获赐陆军十字勋章。[1]随后相继在牛津大学布拉斯诺兹学院(Brasenose College)和古狄斯顿神学院(Cuddesdon Theological College)学习。1920年9月26日,何明华在纽卡素座堂被按立为会吏,第二年按立为牧师。在受圣职的同时,何明华还担任英国基督徒学生活动(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的干事。1922年4月,他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徒学生运动大会。通过这次会议,何明华认识了中国基督徒学运领袖顾子仁(T.Z.Koo)和青年会吴耀宗(Y.T.Wu)等人,并开始受中国朋友的影响,尝试从中国人的角度和立场去理解中国的政治。[2]1925年,他接受顾子仁的邀请,赴上海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这是他第二次来华。通过在华工作的经验(1925-1926),何明华对中国的认识和印象加深了,这也逐渐改变了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和圣公会牧师,对中国的态度与看法。1926年何明华回国后,开始担任纽卡素圣路加教堂的主任牧师。1932年10月,他在伦敦圣保罗座堂接受了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按立的圣礼后启程到香港,成为香港圣公会第七任会督。
何明华非常重视华人的自治,积极推动华人负责牧养工作。[3]三、四十年代,他在处理教务的同时,还担负了大量的社会紧急救济工作。特别是抗战时期,他在中国大后方积极从事传教及救灾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战后香港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何明华除了立即恢复因战争而中止的社会服务工作外,还创办了许多教育事业。在他的带领下,圣公会在香港有相对理想的发展,成为政府推广各项社会服务和教育事业的合作伙伴。[4]
何明华于1922年第一次来华,1925-26年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1932年开始担任圣公会香港及华南教区主教,直至1966年荣休返国(时年71岁),1975年在英国牛津逝世。他在中国的大半生岁月里建树良多,曾两次获国民政府颁发的荣誉奖章、接受英女皇授予的CMG勋衔等。但同时,何明华亦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教会领袖,1944年他破例按立李添嫒为全球圣公会第一位女牧师,该事件在全世界圣公宗体系内引起轩然大波;1956年,他受邀访问大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问中国的西方教会领袖之一。这些颇具勇气的行为,令何明华成为圣公会最受争议的会督之一。[5]
二、何明华与英国基督徒学生活动
基督徒学生活动(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以下简称 SCM)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889年10月15日在伦敦都城会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学生传教志愿者协会(Student Volunteer Missionary Union)。随着这一组织的发展,1893年又成立了校际基督徒协会(Inter-University Christian Union),1895年正式改名为基督徒学生活动(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6]该组织由渴求理解基督教信仰和追求基督徒生活方式的英国学生组成。SCM鼓励其成员突破种族和民族的限制,以献身的方式去重新认识和响应世界的需要。[7]此外,SCM在处理殖民主义(colonialism)与传教运动(missionary movement)二者间的张力与矛盾时,也表现出对西方传教运动的深刻反省。1895年8月17-1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简称WSCF)成立,该同盟秉持三个目标:1、团结全世界的基督徒学生活动和组织;2、收集全世界有关学生宗教事务的信息;3、促成以下的行为:a)带领学生成为将基督视为救主和上帝的信徒;b)深化学生的属灵生活;c)促进全世界的学生为拓展上帝国而努力。[8]后来顾子仁成为该组织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干事。
何明华于1919年加入基督徒学生活动,当时SCM提出了“世界处于危机之中,需要重新调整社会秩序和改变社会结构,为上帝国而战斗的口号。”[1]25值得注意的是,提倡调整社会秩序与改变社会结构,反映了当时基督徒学生已经开始认识到社会制度的弊端,他们期望打破当时的社会结构,追求世界的公平与正义。此外,SCM一个重要吸引力就在于它的海外事工部。该部门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学生赴海外宣教,并为准备赴海外宣教的学生提供相关的训练,其中包括为预备赴亚、非洲传教的学生培训当地的地理、历史等背景知识。何明华最初加入该运动的时候,威廉·裴顿(William Paton)①威廉·裴顿(William Bill Paton)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教士,他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的创办人之一。何明华在SCM的工作受其影响和带领,而他亦是何氏传记的作者裴大卫牧师(Rev.David Paton)的父亲。参David M.Paton,“The Life and Work of David M.Paton”,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 Judgment of God(Second Edition,1996),p.3.是海外事工部的负责人,但从1920年11月开始,何明华开始继任其职务,负责SCM的海外传教事工。1921年,英国有6万在校学生,其中1万人参加了SCM。不仅如此,SCM还有充足的资金,设有28个全职的工作人员,支持学生远赴海外传教。1921年,SCM在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学生领袖们从种族、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探讨了东西方的差距,并开始反省西方的优越感,他们勇于挑战西方的殖民心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弊端做了充分的揭露。他们还表达了对低下社会阶层的同情和关怀,积极提倡社会改革,希望亚非国家可以从西方的经济政治侵略中争取独立,重新构建一个新的世界。[9]
何明华在1921年的格拉斯哥会议上作了发言,他当时的演讲代表了基督徒学生开始对政治与国际事务高度关注,尤其关注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冲突中,东方屡屡受到不公正对待。他呼吁应该“正确对待东方的灵性”,“让基督教放弃帝国主义的做法”、“站在上帝的一边”,寻求属于基督教界的“政治的声音”。[10]青年时代的何明华不仅关心政治,还积极投入社会参与,他发起组织为社会贫穷人士服务的“流动炊事会”(soup kitchens),参与“房屋协会”(House Society)和“泰恩河社会服务协会”(Tyneside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等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11]努力结合基督教信仰与社会责任,以实践挑战和回应当时英国社会的需要。
英国的基督徒学生活动在长期的发展中,训练培养了一批具有坚定信仰的青年领袖。他们崇尚对公义的追求,对低下社会阶层的关怀;同时,该运动关注东西方的差距,勇于挑战西方传教运动中的殖民心理。后来这批青年领袖中的不少人成为教会中的领袖人物,如英国第九十八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汤朴(William Temple)①汤朴威廉(William Temple,1881-1944)是英国第98任坎特伯雷大主教(1942-1944)。他一生致力于教会合一运动及社会改革,认为教会应当关心社会问题,其代表作之一的《基督教与社会秩序》(Christianity&Social Order)集中反应了其社会改革的理想。、新加坡圣公会主教李安纳·威尔逊(Leonard Wilson)②李安纳·威尔逊(Leonard Wilson,1897-1970)曾在青年时代积极参与SCM,1941-1949年担任新加坡圣公会主教,1953-1969年任英国圣公会伯明翰主教(Bishop of Birmingham)。1941年新加坡被日占领后,威尔逊曾被投入狱中,备受折磨。他积极主张基督徒关注世界和平问题,反对侵略与战争。有关他的经历参Roy Mckay,John Leonard Wilson Confessor for the Faith(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3)。等,他们继承了SCM的精神,倡导社会改革,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其中,何明华就是这批青年领袖当中最为典型和突出的一位。
三、何明华与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
吴耀宗认为,“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这个词被提出来,是在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时候。[12]1926年,男女青年会及学生立志传道团在南京组织“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筹备委员会”,其宗旨为“本耶稣的精神,创造青年团契,建立健全人格,实行革命,谋民众生活的解放与发展”[13],目的就是创立一个统一、自主及不分宗派性别的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
1922年4月,何明华作为英国基督徒学生活动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SCF)第十一届大会。整个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副总干事顾子仁负责,何明华在这次会议上不仅认识了顾子仁,还认识了身为北京青年会学校部主任干事的吴耀宗。这次会议上,吴耀宗对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基督徒学生活动除了人数增加外,其他毫无成长。该运动缺乏领导作用,且远远落后。”[14]吴的批判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时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的问题所在,事实上,中国虽有600余位代表参加,但75%的代表不是来自大学,而是来自中学。相比之下,参会的海外代表均是在校大学生或是富有经验的学生干事。可见,当时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尽管人数众多,但十分年轻,缺乏有效的行政组织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何明华来自英国,SCM在英国已发展得非常成熟,作为WSCF宣教委员会的主席,何明华亦强调“今日传教的需求最主要是质量而非数量。”[15]
然而,正是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成为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线,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非基运动”。这场运动对于何明华个人产生巨大影响,使他意识到原来一直以来被西方社会认同的基督教,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却无法生根、以至于一个民族要凝聚全部力量来反对它。这场冲击给他带来的是——“重生”(rebirth)的概念,他开始接受顾子仁等中国朋友影响,用中国人的思想和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基督教。“非基运动”持续了5年之久,直到1927年才停止。在此期间,由于顾子仁的邀请,何明华不顾中国国内的紧张情势,于1925年五卅惨案后不久,来到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6]这段经验对何明华而言是特别重要的,1922年他第一次来华参加WCSF大会时,就已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所在。而顾子仁作为他最要好的中国朋友,1925年邀其来华工作,主要就是想借其英国基督徒学生活动的背景和经验来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基督徒学生活动。对何明华而言,五卅惨案导致的反英浪潮与非基运动对他的冲击与影响是永久性的。为此,他愿意再次来到中国,进入青年会工作,不仅为帮助中国发展基督徒学生活动,还期望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他到上海不久,就留意到中国基督徒学生们面临的困惑:[17]
我们来到上海刚好一个月……中国的基督教并没有受到政治动乱的严重影响,但仍有一种不安定感。长期接受的标准越来越成问题,那些过去受传教士影响至深的基督徒们现在越发迷茫,年轻的一代更觉得迷惑。他们发现那些深受国家主义影响的学生对他们表示出敌意,很难与之沟通。他们害怕与西方人交往,因为担心被误解为不爱国。
20世纪初,当英国基督徒学生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学生活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此时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却显得生机勃勃。是什么原因导致基督徒学生活动在中国的发展如此缓慢而脆弱?何明华对其中原因做了深入的阐述:[16]21
在学生工作方面,我的到来也是顾子仁结束此方面工作的开始,他采用英国模式运作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的构想使得他最终停止了在中国YMCA的工作。他非常明智地看到了在中国发起一种反叛运动将会比接受一套最终会失败的体系来得更加有害。选择就是屈服。YMCA将学生部门从属于城市工作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难道他们看不出对于中国而言,学生工作有多重要么?在英国,情况相反,YMCA之所以脆弱的原因是因为有独立的学生运动。
何明华认为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未能发展的原因是它没有从青年会中独立出来。顾子仁当时在中国负责全国青年协会学生部的工作,该主要工作就是将全国大专、高中里已成立的基督教学生团契结合起来,使他们彼此分享宗教经验,共同读经祷告、为主证道,并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这些工作就是一般俗称的基督徒学生活动。该组织并非与那时已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对立或抗衡,却是互相策勉砥砺,保持青年学生的超政治、超党派地位,勿被卷入党争或政争的漩涡。当然,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组织,其宗旨是“本耶稣的精神,创造青年团契,建立健全人格,谋民众生活的解放与发展”。[18]24-25这个宗旨显然切实适应当时中国的需求。然而,青年会的事工种类繁多,学生活动只属于其中一部分的工作。在青年会要顾及全盘各面的发展之下,学生部往往受到不少限制,特别是1924年,顾子仁赴英考察了英国基督徒学生活动之后,深深觉得中国青年会的学生活动,无论从组织上还是内容上,都有学习英国的必要,他认为应把青年会中的学生工作部门独立出来发展。为此顾子仁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邀请何明华来上海的青年会工作,期望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使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发展成为理想的状况。何明华1925-1926年在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的这一年经历,也是顾子仁极力想用英国模式建立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的尝试。而这件事未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当时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不支持学生部门从青年会独立出来,而顾子仁要全力实现推展他“基督徒学生活动”的理想,两人就此问题产生分歧,互不相让,最后顾子仁在1926年毅然辞去了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的工作,前往日内瓦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任职。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继续组织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的理想,一直持续到30年代。[19]
顾子仁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根据谢扶雅的解释:[18]29
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之鲜花怒放,而终功亏一篑,因素至为复杂。主要自然是当时外在的政治原因,尤其是中共青年团分子在一般学生界的插入与渗透为最不利创伤。而最后政府决定对日抗战,全国男女老幼总动员,学生请缨赴前线杀敌,在后方担任组训民众,救难抚伤;既然全民意志统一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大时代号召之下,自无特别基督教学运之可为。
另外一种解释来自当时中国基督徒学生领袖的耿元学:[18]100-101
当江文汉自美学成回沪,主持青年全国协会的学生事业,不愿见中国有一独立的基督徒学生活动。1937年春,青年会协会当局因国中政局复杂情形取消了我被指派在学运临时总会的执行干事。由是临时总会工作一时无法推行。
由此可见,谢扶雅和耿元学两人都指出当时日益紧迫的时局是造成基督徒学生活动失败的直接原因,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中共青年团与青年会的阻挠才是造成该活动无法开展的根本原因。1920年是青年会的转折时期,从此开始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及之后的50年代,青年会的一些领袖人物逐步接受共产主义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20]从 20年代始,中共逐渐开始渗透到青年会中,成为青年会的幕后领导者和实际掌权人。从青年会的立场来看,当然不希望“基督徒学生活动”这样的独立学生组织出现,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因此,从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独立失败,可以窥视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和掌控力。
作为顾子仁的朋友,何明华曾参与和支持他发展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能成功。在经历青年会为期一年的工作之后,他逐步意识到青年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并且感受到政治力量在基督徒学生中的影响;通过“非基运动”,他更意识到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情怀,而这些也成为他日后与中国互动关系中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基础。此时的何明华越来越能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他称“中国教会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女儿,而是我们的姊妹”。[1]4320世纪初的英国基督徒学生活动,影响了何明华的思想,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的经验,让何明华走进无数中国青年学生的心灵,也令他对东西方差异和信仰产生深刻认识与反省。
为何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没有能获得发展并难逃流产的命运?该活动在中国兴起的时间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时期,两者极力争取的对象都是中国的青年学生。基督徒学生活动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所继承的都是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理论,为什么一个遭到排斥而另一个却被中国接受?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两者都具有改革社会的理想,它们的关系是竞争的关系,而非阴谋的关系。作为相互竞争的理论观念,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着相同的试验,有着平等被接受的机会。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处境下,共产主义把握住了时代的机遇,将自己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捆绑在一起,从而更深入地觉察到、并紧握住中国社会政治的脉搏,也赢得亿万中国青年学生的心。正是中国这些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因素,导致了基督徒学生活动在中国的失败。
此外,我们也需审视和反省基督徒学生活动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殖民运动与传教运动,两者都在东西方权力不均衡的情况下来到中国,作为追求世界公平与正义的基督徒学生活动,在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沸腾的时代环境下,如何处理这个两难的悖论,相信也是当时基督徒学生活动在中国面临的困境所在。何明华作为SCM的宣教干事,他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21]
中国的报纸刊登了John Bull的一幅卡通漫画,充分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关注点:John Bull一只脚踏在潜水艇上,另一只踩在60磅的的平衡杵上,右手举着坦克,左手托着飞机。废气从他的鼻孔中排除,嘴巴里冒出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相信上帝”。当然只是讽刺,但是对于我们而言,确是挑战。
这是一幅典型的殖民主义与传教运动结合的漫画,透过这幅漫画,何明华深刻地表达出对西方殖民运动的不满。为了应对挑战,他认为“如果我们要使自己明白上帝的真理、祂的创造及祂创造的原本目的,我们就必须坦诚我们在行为与思想上的混乱。我们必须对现在这种流行于世的破坏和平的做法感到罪孽。”[21]8他还认为殖民主义是破坏上帝的旨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基督的家庭”[21]92才是上帝的计划。
结语
基督徒学生活动对何明华一生影响深远,他不仅认同该活动社会服务和社会改革的理想,还通过基督徒学生活动与中国产生深厚情感,将中国视为实践上帝爱与使命的场所。中国基督徒学生活动的失败,让何明华意识到基督教在与共产主义的竞争中,未能理解中国的处境,从而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基督教需要对自身进行反省。何明华的学运背景,是他不同于圣公会及其他宗教领袖的特别之处,也影响了他后半生对中国政治及共产主义的态度。由于基督徒学生活动的经历,他更深切地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与政治制度的方向。反思过去几百年来入华的西方传教士,何明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从中国的社会政治处境去理解中国,实践上帝在中国的旨意。20世纪20年代,何明华曾走进无数中国基督徒青年学生的心灵,分担20世纪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与基督徒学生活动的关系是一个涉及根源的重要问题。
[1]David M.Paton,R.O.The Life and Times of Bishop Ronald Hall of Hong Kong[M].Hong Kong: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 Hong Kong Diocesan Association,1985.
[2]Charles Henry Long.R.O.Hall[A].Gerald H.Anderso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C].New York:Macmillan Reference USA;London:Simon & Schuster and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1998,(275-276).
[3]R.O.Hall.The Bishop's Notes.Outpost[J]July 1933,(5-8).
[4]曾国华.何明华会督(1895-1975)对香港之社会及教育之贡献[M]香港:香港大学文学硕士论文,1993,(10).
[5]Brown,Deborah A.Turmoil in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Rule:The Fate of the Territory and Its Anglican Church[M].San Francisco: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1993:81 -110.
[6]Philip Potter&Thomas Wieser,Seeking and Serving the Truth: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the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eration[J].Geneva:WCC Publications,1997,(1 -11).
[7]“The Aim and Basis of the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Religion &Life in the College[J].London: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1921,(5).
[8]Philip Potter&Thomas Wieser,Seeingk and Serving the Truth: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the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eration[J].(11).
[9]“The Glasgow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Questions”,Religion &Life in the College[J].(13 -17).
[10]R.O.Hall.An Impression.Student Movement(Vol.23)[J].Glasgow 1921,(13 -16).
[11]Address by Bishop Gilbert Baker at the Memorial Post of Friday,2nd May 1975,“The Bishop's letter”,Outpost[J].Hong Kong Diocesan Association,(12).
[12]吴耀宗.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前瞻.天风[J]第109 期,(4).
[13]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委员会建议案.学生事业丛刊[J]第二卷第8号(1926年6月),(10).
[14]Y.T.Wu.The 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CR[J]54(Aug.1923),(468 -470).
[15]Studen World(July 1922).Philip Potter &Thomas Wieser,Seek and Serving the Truth: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the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eration[J].(73).
[16]R.O.Hall.T Z Koo.Chinese Christianity Speaks to the West[M]London:SGM Press LTD 1950,(20 -21).
[17]Nora& Ronald Hall,.YMCA.20 Museum Road Shanghai China Via Siberia,Dec 2nd 1925.
[18]谢扶雅.顾子仁与学运[M].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3.
[19]Jun Xing,.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1919-1937)[M].(203).
[20]顾长声.中国基督教简史[M].加州蒙特利公园市:长青文化,1999,(185).
[21]R.O.Hall.A Family in the Making[M].London:SCM,1925,(7).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吴奕锜]
K25
A
1000-5072(2011)01-0140-07
2009-12-10
吴 青(1979—),女,江苏南通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