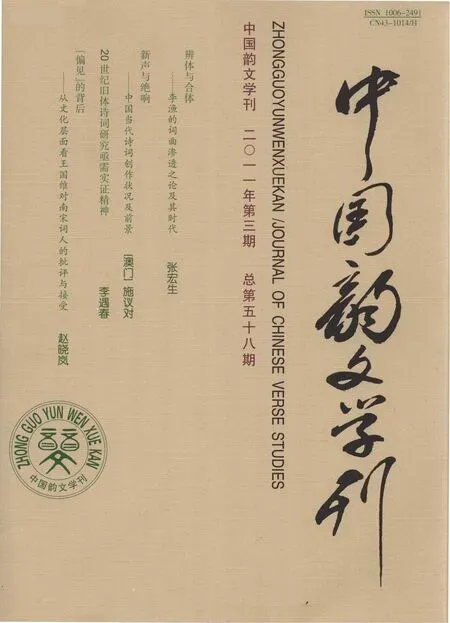李峤《楚望赋》并序的理论内涵与价值
刘伟生
(湖南工业大学 中文系,湖南 株洲 412007)
与杜审言、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的李峤(645~714)并不以赋名世,他留下的赋作仅《楚望赋》(并序)一篇,这仅有的赋作也谈不上有什么过人的构架、文采与气势,但其理论意义却不容忽视。钱锺书先生曾经广引诗文归结“登高望远,使人心悲”的普世情怀,认为李峤的《楚望赋》最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这种幽微曲折的心情。周祖诜《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也将《楚望赋序》收录其中。不过一般的赋史与文论史著作乃至李峤研究的专文都没有论及这篇原本不该忽略的作品,缘乎此,本文拟对此赋的理论内涵与价值作一全面的阐述。
一
《楚望赋》赋序开篇即说:“登高能赋,谓感物造端者也。”“造端”是开头、发端的意思,这里可指起兴。这一句话借“赋”义的阐释而嵌入“登高”与“感物”两个核心词语,实际上也包容了这篇赋及序理论内含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感物说与登临说。试分别加以阐发。
感物兴思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思想,现在我们都将这一理论贡献归功于《礼记·乐记》、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和钟嵘 《诗品序》等少数几篇文艺理论的专文。事实上感物兴思作为主客、心物关系的表现,是广泛地存在于写作主体的生命体验与创作心理当中的。即便是以描写为主要任务的赋体创作也是如此。在大多数的赋序里,赋家们总是念念不忘地加上“感而作赋”、“感而成兴”、“有所感遇”之类的话语:
……故兴志而作赋,并见命及,遂作赋曰。(魏·杨修《孔雀赋序》)
……于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于时秋也,故以秋兴命篇。(晋·潘岳《秋兴赋》)
……感万物之既改,瞻天地而伤怀,乃作赋以言情焉。(晋·陆云《岁暮赋序》)
……怅然有怀,感物兴思,遂赋之云尔,其辞曰。(刘宋·傅亮《感物赋序》)
……感恩怀旧,凄然而作。(梁·萧子范《直坊赋序》)
……感而成兴,遂作赋曰。(唐·宋璟《梅花赋序》)
不止是个体写作缘起的交待,有些赋序还对感物兴思的原理与过程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这些分析与描述也许不如理论专文那么集中而深刻,但它们都出自赋家之口,或者明显早于理论专文。如此看来,赋家如何理解感物兴思的过程,感物兴思的原理与赋体特征有何关系,赋体的存在对感物理论的出现有何影响之类的问题,就理所当然应成为我们探讨的对象。
按照叶嘉莹先生的观点,诗歌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不外“由物及心”、“由心及物”与“即物即心”三种,以之对应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则由物及心的是兴,由心及物的是比,即物即心的是赋。(参《迦陵论诗丛稿》中《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一文,及《汉魏六朝诗讲录》第一章第四节《诗歌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之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及 2000年)赋中用比的手法是较为少见的,从赋序来看,赋家对于感物兴思模式的概述,也大体不出由物及心与即物即心两类。由物及心指最初的触发点是物,是由外物触动内心,从而产生情思的过程。上举赋序,多属此类。“感物兴思”一语即出自傅亮的《感物赋序》,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中“诗人之兴,感物而作”一语虽指诗歌而非赋颂,却已开文论中“感物说”之先河,到潘尼《安石榴赋序》,就已自觉用于赋体创作心理的总结了: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是以属文之士或叙而赋之,盖感时而骋思,睹物而兴辞。
不过对这一过程的表达最为确切也最为详细的,还是李峤的《楚望赋序》:
序曰:登高能赋,谓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心由目畅,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是以骚人发兴于临水,柱史诠妙于登台,不其然欤?盖人禀性情,是生哀乐,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千里开年,且悲春目;一叶早落,足动秋襟。坦荡忘情,临大川而永息;忧喜在色,陟崇冈以累叹。故惜逝慜时,思深之怨也;摇情荡虑,望远之伤也:伤则感遥而悼近,怨则恋始而悲终。达节宏人,且犹轸念;苦心志士,其能遣怀?是知青山之上,每多惆怅之客;白蘋之野,斯见不平之人:良有以也。余少历艰虞,晚就推择,扬子《甘泉》之岁,潘生《秋兴》之年,曾无侍从之荣,顾有池笼之叹。而行藏莫寄,心迹罕并,岁月推迁,志事辽落,栖遑卑辱之地,窘束文墨之间:以此为心,心可知矣。县北有山者,即《禹贡》所谓岐东之荆也。岹峣高敞,可以远望,余薄领之暇,盖尝游斯。俯镜八川,周睇万里,悠悠失乡县,处处尽云烟,不知悲之所集也。岁聿云莫,游子多怀,援笔慨然,遂为赋云尔。
由于这篇序是结合登高望远必致伤感这一具体的感发形式来阐述感物兴思的现象与原因的,其内涵就更为丰富而深刻。
一是描述并总结感物兴思的现象。序以“千里开年,且悲春目;一叶早落,足动秋襟”来描述感物兴思的现象,大体同于陆机《文赋》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与《文心雕龙·物色》之“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就语法结构言,更近《文心》以物为主,以心为宾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易于突出外物作为最初触发点的身份。“情以物感”、“心由目畅”的总结也大体同于《物色》篇之“情以物迁”。这一层次主要是继承前人观点。赋作正文中也仿《文赋》“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方式描述了感物兴思的情状:
其始也,罔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怅乎若有待而不至也。悠悠扬扬,似出天壤而步云庄;逡逡巡巡,若失其守而忘其真,群感方兴,众念始并,既情招而思引,亦目受而心倾。浩兮漫兮,终逾远兮;肆兮流兮,宕不返兮。然后精回魄乱,神苶志否,忧愤总集,莫能自止。
若有所求,若有所待;似出天壤,似失其守;群感方兴,众念始并;浩漫无边,不知所归;忧愤总集,莫能自止。正与《文赋》一样使用了赋体擅长的铺陈方式。
二是分析感物兴思的原因。序云:“盖人禀性情,是生哀乐,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故惜逝慜时,思深之怨也;摇情荡虑,望远之伤也:伤则感遥而悼近,怨则恋始而悲终。”上文言情思是因外物而触发的,可外物为什么能够触动情思呢?答案是人有一颗敏感的心,能够在外物的触动下产生哀乐之情,感物兴思是一个心物交互的过程,望远必伤与思深必怨是一致的。这一观点当然也不是此序首创,《礼记·乐记》早已明确阐述过这一原理:“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P660)从纵向的角度来看,由“ 声”而“ 音”、由“ 音”而“乐”是一个音乐生成的过程。就心物之间的关系而言,“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音”由“ 心”生 ,而“ 心”因“物”动,艺术的生成,根源于“人心之感于物也”。这“物”便是客体,是外物的震撼激起了内心的波澜,从而引发外宣的冲动。即所谓“应感起物而动”[1](P667)。由此可见,《乐记》认为艺术的生成是因“ 物”动“ 心”,由“ 心”生“ 乐”的过程,是主观的“心”与客观的“物”交互感应的统一体。这是极富有辩证思维的论断。[2]《文心雕龙·明诗》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语亦本此而来。当然,这里讲的还只是感物兴思的过程,就内涵来讲,感物兴思的实质是同声相应,同类相从。骆宾王《萤火赋序》说:
余猥以明时,久遭幽絷,见一叶之已落,知四运之将终。凄然客之为心乎?悲哉!秋之为气也。光阴无几,时事如何?大块是劳生之机,小智非周身之务。嗟乎!绨袍非旧,白首如新。谁明公冶之非?孰辨臧仓之愬?是用中宵而作,达旦不暝。睹流萤之自明,哀覆盆之难照。夫类同而心异者,龙蹲归而宋树伐;质殊而声合者,鱼形出而吴石鸣。苟有会于精灵,夫何患于异类?况乘时而变,含气而生,虽造化之万殊,亦昆虫之一物。应节不愆,信也;与物不竞,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义也;临危不惧,勇也。事沿情而动兴,理因物而多怀,感而赋之,聊以自广云尔。
这篇序是悲秋之作,不过它反复强调“因物而多怀”实是“有会于精灵”,而所以能有会于异类,实是“质殊而声合”,也就是同声相应,“声”、“心”互文,也可说“同心相应”。在赋中作者再次强调了“同声相应”、“同类相从”的道理:“物有感而情动,迹或均而心异。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宋人林希逸的《孔雀赋序》近此:
夫离合聚散,悲欢怨怼之情,非必含灵而具识者有之,物亦与有焉,而怀怅恨以相感者,又非必有族类俦侣者也,物亦我,我亦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不同的是,林序更明确地指出:物亦有情。王勃《涧底寒松赋序》“盖物有类而合情,士因感而成兴。”则以更为简洁的语言概括了感物兴思的原理。
二
以上是直接言及感物兴思的内涵,此外是指出登山临水必致伤感的现象并解释其原因。序云:“骚人发兴于临水,柱史诠妙于登台”;“青山之上,每多惆怅之客;白蘋之野,斯见不平之人。”这是现象,赋体正文更主要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与概括,如“于是繁怀载纡,积虑未豁,生远情于地表,起遥恨于天末”;“愿寄言而靡托,思假翼而无因,徒极睇而尽思,终夭性而伤神。或复天高朔漠,气冷河关,汉塞鸿度,吴宫燕还,对落叶之驱寿,怨浮云之惨颜”等等,先说繁怀积虑,生情天地,再说将言已叹,无哀自伤,再说人事多戚,无忧不入,然后说极睇尽思如何夭性伤神,羁旅离愁如何因望至极。
那么登山临水易于感物造端(起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序文说:“夫情以物感,而心由目畅,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就理论言,心物对应,情以物感,心由目畅,所以只有登山临水才可触动情思、激发灵感。这里内含两个常识,一是心物直接对应,因为登高所见必然广泛,《毛诗正义·定之方中》曰:“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3](P113)二是心物间接对应,因为在旷漠的时空里,外物可以激发主体创造性的想象,正如《文赋》所言,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可以“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
接下来的一小段进一步申明登山临水可以触动情思的原因。哀乐本于人之性情,思深必怨,望远必伤。具体说一是感兴,二是因感兴而起的惜逝慜时,摇情荡虑。这里更进一步阐述了“感遥而悼近”,“恋始而悲终”的连动过程。然后说面对不同的自然景致,即使是“坦荡忘情”的“ 达节宏人”,也会流露出喜怒哀乐之情。末了再以事实说明青山之上,白蘋之野每多惆怅不平之人。这一段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感物而动的心理过程与特征予以了形象的描述。
但这一解释还很平常,不够深刻,所以他在赋里接着说:
惘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怅乎若有待而不至也。……故望之感人深矣,而人之激情至矣!必也念终怀始,感往悲来,沿未形而至造,思系无而生哀:此欢娱者所以易情而慨慷,达识者所以凝虑而徘徊者也。
登高之所以伤感是因为人皆有待有望,登高可以望远,可是远望还是得不到所望,所以慷慨伤悲。这“有求而不致,有待而不至”正道出了登山临水,使人心瘁神伤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一问题,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在广引古代诗文并充分肯定李峤的观点之后,又引西方浪漫主义理论中的“企慕”心理与“距离怅惘”之说来进行探讨,并因孔子上农山,喟然而叹“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之事而将其归之为“农山心境”。[4](P72)他甚至从文字的本源上寻找依据,说:“征之吾国文字,远瞻曰`望',希翼、期盼、仰慕并曰`望',愿不遂、志未足而怨尤亦曰`望',字义之多歧适足示事理之一贯尔”[5](P878)钱先生从心理的角度,以比较的眼光在“望”字上作出了充分的阐释,从他对这一问题的反复增订也可见了他谨严的态度与不懈的思考。
马元龙先生《登高望远,心瘁神伤——兼论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一文对登高望远使人伤感的问题作了专门的探讨,该文认为:“中国人渴求建功立业以期不朽的生命意识乃是这一情结的本质原因。但这种情结之所以在登高望远之际,才有更激烈的表现,乃是因为`高'、`远'本身所具备的两种对立的意味的催发,使登临者强烈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从而悲从中来,心瘁神伤。”[6]这样的解释深入到了生命意识的层面,也寻找到了“对立”的症结,不过反不如钱先生的解释通达。《楚望赋》中的有求与有待,固然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重点指向建功立业,又何尝不可更宽泛地理解为有为有待,按庄子的说法,真正的逍遥在于无为无待。其实人之自觉与生命之悲不过一念之转,都是人物、人人、人我对立的结果,人之自觉强调人物、人人、人我之间的对立,当自己不能成为外物、他人甚至自我的主宰时,自然悲从中来,所以老庄要齐生死、等祸福,忘形丧我。从这个意义上讲,登高临远是人生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大矛盾的突现。所以,登山临水,忧从中来的原因,一在自然生理的反应,二在社会纠纷的总集,三在终极问题的追寻。
最后不要忘了李赋对登高望远的感兴作用的归结:“故夫望之为体也,使人惨凄伊郁,惆怅不平,兴发思虑,震荡心灵。”
不管怎么说,李峤《楚望赋》对于登高望远使人伤感问题的描述与解释,与《文心雕龙·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的概略式交待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
就情感指向与渊源而言,登临说与屈、宋情怀不无联系。登山临水而致感伤,在《诗经》里就有出色的描写,如《周南·卷耳》、《魏风·陟岵》、《秦风·蒹葭》之类,但远不如屈、宋作品中那样集中而浓烈。屈原的作品大都是流放江湘的产物,整个就可以看作一个登山临水的意象系统。这里面既有理想中的“上下求索”(《离骚》),也有现实里的“容与不进 ”(《涉江》);既有神话中的“ 骋望佳期 ”(《湘夫人》),也有人世间的“横奔失路”(《惜诵》);既登昆仑之瑶圃(《涉江》)),也“临沅湘之玄渊”(《惜往日》)。不光有这许多山水的意象,还有作者自己的形象:“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这登山临水的意象系统涵蕴着屈原政治失意、理想落空的怨愤,岁月不居、年华易逝的苦恼,与思乡怀人、忧国忧民、孤独寂寞等种种感伤的情愫。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里说屈原的这些作品:“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7](P47)
屈原作品的这种哀怨感伤的风格,主要缘于他自己特立独行的操守,当“登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时,自然只能“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抽思》)当然也与他的经历遭遇有关。屈原的一生,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他的报国无门的不幸,表现在作品中,便是一腔怨愤。后人常借用屈原《九章·惜诵》“发愤以抒情”一语来说明屈原的创作动机。司马迁说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 《离骚》,盖自怨生也。”[8](P2482)在《报任安书》中他又举屈原为例,并以“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来解释“发愤著书”。从此“发愤著书”作为一个创作心理学命题,成为探究感伤类作品的重要依据。
不同于屈原“高驰而不顾”(《涉江》)的态度与雄奇瑰伟、哀怨感伤并存风格的是,宋玉将登临情感与意象集中在更为普适性、季节性的“伤春”、“悲秋”里。试看这些句子: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招魂》)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九辩》)
登高远望,使人心瘁。(《高唐赋》)
钱锺书先生说:“《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高唐赋》:`长吏隳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太息垂泪,登高远望,使人心瘁'。二节为吾国词章增辟意境,即张先《一丛花令》所谓有`伤高怀远几时穷'是也。……别有言凭高眺远、忧从中来者,亦成窠臼,而宋玉赋语实为之先。”[5](P875)
无论是创作的实践还是理论的归结,屈、宋都强化了登临作品的感伤情绪,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宋人韩元吉《虞美人·怀金华九日寄叶丞相》词云:“登临自古骚人事。”“骚人”是谁,这里当然是泛指古代文人,但它的始祖却是屈、宋。萧统说:“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文选序》)[9](P2)这个“ 骚人”指的是“ 楚人屈原”。胡应麟说:“`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形容秋景入画。`悲哉,秋之为气也!'`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模写秋意入神。皆千古言秋之祖。六代、唐人诗赋靡不自此出者。”(胡应麟《诗薮》)[10](P77、78)这“ 千古言秋之祖”是屈原 、宋玉 。在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谢朓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乎屈、宋的情怀。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杜甫的《登高》里,除了孤独与忧伤之外,更有屈、宋词句的踪影。出于屈原《河伯》的“南浦”后来成为送别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宋玉登临之举甚至也成了词中典故:“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柳永《戚氏》)。
因为屈宋是公认的感伤文学始祖,所以李峤《楚望赋》举的登临可致感伤的例子第一个就是“骚人发兴于临水”。值得注意的是对“柱史诠妙于登台 ”的理解。“ 柱史”是“柱下史”的省称,代指老子,这里讲的是《老子》第二十章的内容。前人多把这一章看作哲理诗,其实它更近于《离骚》式的抒情叙志类作品。大意说无论是受到赞扬还是反对,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都无所谓,但这只是主观态度,现实并非如此,所以他说别人所害怕的我不能不怕,别人都那样欢乐,就象参加盛大宴席、登台观赏春景一样,我却无知如小孩,所以狼狈如无家可归之人。众人都过着富余的生活,只有我被遗弃了一样,世人都这样明白清楚,只有我这样昏聩糊涂。这分明是一篇抒愤之作。其中的“荒兮,其未央哉!”很类似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充满着对前途渺茫的慨叹;而“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又与屈原的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何其相似。虽然字面相反,心境却一样,都在斥责世人的愚昧,悲叹自己的孤独,充满了不被理解的苦闷和愤世嫉俗的情绪。当然,初盛唐的李峤对辞赋的理解与要求不光是感伤情绪的表达,还有与时代文风一致的壮大气势。他的咏物诗《赋》篇说:“布义孙卿子,登高楚屈平。铜台初下笔,乐观正飞缨。乍有凌云势,时闻掷地声。造端长体物,无复大夫名。”在他看来,理想的辞赋要有“凌云势”和“掷地声”,这与陈子昂的“风骨”倡议是比较接近的。《楚望赋》中“霜尽川长,云平野阔,恨游襟之浩荡,愤羁怨之忉怛”的情绪,无疑也具有慷慨壮大的特点。
关于感物兴思的原因,上文提到同声相应,同类相从的原理,但因为同声相应的背后对应着的是心物交互、主客相融,所以文论家们又竭力在主客关系甚或天人关系上探求感物兴思的真谛。笔者无意于哲学的论证,只想谈谈赋体文学对感物兴思现象与理论的影响。在早先的诗歌里,已有诗人与外物的情感交流,但认识世界的有限与描写技巧的欠缺使这种交流无法全面而深入。屈、宋的楚辞如《山鬼》、《九辩》已自觉地运用外在景物来衬托主观情思,极大地发展了诗歌的比兴,不过骚体的形式更适于直接的抒情。汉大赋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它继承了宋玉《高唐》、《神女》体物的传统,将目光放置于广阔的客观世界,在刻苦钻研铺陈描写艺术的过程中,暂时抛开了个人的情思,或者将主观的意念深隐在虚设的客主问答里,而客观上它却极大地发展了形象思维的能力。问题正在于感物兴思的发展有赖于形象思维的支撑。尽管艺术形象既可以再现、拟想,也可以幻想虚构,但归根结底源于客观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主观的理念。查检《文选》的目录就会发现,《文心雕龙》中用以阐述感物兴思原理的“物色”篇名 ,收罗了 《风赋 》、 《秋兴赋 》、《雪赋 》、《月赋》等四篇赋体,可见“物色”一词的含义首在客观的自然景物。“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前提是“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文心雕龙·物色》)。美国的鲁道夫·阿恩海姆指出:
一棵垂柳之所以看上去是悲哀的,并不是因为它看上去像一个悲哀的人,而是因为垂柳枝条的形状、方向和柔软性本身就传递了一种被动下垂的表现性,那种将垂柳的结构与一个悲哀的人或悲哀的心理结构进行的比较,却是知觉到垂柳的表现性之后才进行的事情。[11](P624)
于感物兴思的原初形态而言,这话讲得在理。就理论形态本身而言,陆机的《文赋》被公认为是感物说的奠基者。可是这篇用赋体写成的理论著作中更引人注目的命题是“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一命题近师曹丕,其远祖却是《尚书》中的“诗言志”。在“缘情说”兴起之前,赋体体物的特征早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并形诸理论性的文字,到陆机所在魏晋已是诗赋并进的时代,并进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赋的诗化与诗的赋化。赋已从汉大赋总揽万殊的大题目中裂变出一些小题目来,由对阔大宇宙的铺陈回归到个人细腻感情的描写。诗则在吸取乐府新的体式与赋体描写的长处后复兴了。总言之,原初的比兴经由赋体形象思维的润泽充实后,伴随着写作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而逐步形成了相对自觉的感物意识与理论。这种意识与理论一经明确,又反过来促使作家关注外在的客观之物,自觉将笔墨伸向山水与田园。由于长期的实践与总结,感兴观在初盛唐非常盛行,几乎所有善于写诗的作家都把感兴视为创作活动的基础。
李峤历仕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数朝,官至宰相。地位极高,文华亦显,在当时以及后世都颇具影响力。他的一百二十首“杂咏”曾被日本列为平安时代传入的中国三大幼学启蒙书之一,他的这些诗歌“将唐初以来人们最关心的咏物、用典、词汇,对偶等常用技巧融为一体,以基本定型的五律表现出来,为初唐诗歌广为普及提供了现实依据。”[12]在李峤诗歌得到应有的肯定后,我们也不妨留意一下他的这篇《楚望赋》,因为它细致曲折而又综会性地描述与阐释了感物兴思及望远伤神的现象与原因,也展现了自六朝到隋唐诗赋及理论发展的轨迹,并为我们全面地了解李峤的文学贡献提供了诗歌以外的别样文献。
[1]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刘伟生.《礼记·乐记》“声”、“音”、“乐”辩 [J].船山学刊,2002(4).
[3]孔颖达.毛诗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钱钟书.管锥篇(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
[5]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马元龙.登高望远,心瘁神伤——兼论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4).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长沙:岳麓书社,1995.
[10]吴广平.楚辞全解[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1][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2]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J].文学遗产,19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