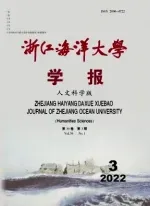陆九渊、吕祖谦关系探微
王法贵
(滁州学院思政部,安徽 滁州 239000)
陆九渊(1139-1193)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在南宋中期,他以“心即理”为核心构建其理论体系,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并集其大成的正统理学对垒而立,引起了思想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吕祖谦的协调下,陆九渊通过与朱熹等学者的讨论、辩难,在理论上逐步成熟和发展,后经由“甬上四学者”(特别是杨简)及白沙先生等的学脉传承,至王守仁而进一步发展成为影响中国明清以来数百年历史进程的主流哲学思潮。鉴于陆吕在中国思想史上据有独特的地位,本文试就其相互交往、理论共识作些探究。
一、陆吕交往考察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浙东“婺学”代表人物,因其郡望东莱,人称东莱先生,全祖望在其学案中称“吕学”,[1]3侯外庐等在《宋明理学史》中对其有专章介绍。[2]340-367
陆九渊第一次拜会吕祖谦,时间在乾道七年(1171)冬,地点是临安。双方年谱对此次会面均无所载,唯陆九渊《祭吕伯恭文》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辛卯之冬,行都幸会,仅一往复,揖让而退。既而以公,将与考试,不获朝夕,以吐肝肺。”陆九渊即将参加礼部春试,吕祖谦时任左宣教郎召试馆职,会面未能尽兴。吕、陆年谱未载其会面,或为疏漏,或因有所顾忌。今人杜海军《吕祖谦年谱》谓:“是冬,陆九渊以考试故到临安,二人初会。”①吕祖谦比陆九渊年长二岁,成名较早,二十七岁即举进士甲等,又中博学宏词科,三十三岁时任严州(今浙江建德)教授,与知州张栻相与论学,次年,被同召入朝,二人又与朱熹交游论学,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幼承家学,少时因读《论语》而内省,使性情复无暴怒,后诚如全祖望所评价的那样:“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1]2《宋史》本传谓“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这可能是令陆九渊慕名来会并引以为“幸”的重要因素。
据陆九渊年谱记载,第二年,陆九渊三十四岁,春试南宫,奏名时,尤延之袤知举,吕伯恭祖谦为考官。读其《易》卷,至“狎海上之鸥,游吕梁之水,可以谓之无心,不可以谓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见其过焉而溺矣。济溱洧之车,移河内之粟,可以谓之仁术,不可以为谓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见其浅焉而胶矣”。击节叹赏。又读《天地之性人为贵论》,至“呜呼!循顶至踵,皆父母之遗体,俯仰乎天地之间,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惧弗能,倘可以庶几于孟子之‘塞乎天地’,而与闻夫子‘人为贵’之说乎?”愈加叹赏。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内难出院,乃嘱尤公曰:“此卷超绝有学问者,必是江西陆子静文,此人断不可失也。”又并嘱考官赵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选。他日伯恭会先生曰:“未尝款承足下之教,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夏五月,廷对,赐同进士出身②。[3]486-487由上述可知,陆九渊考取功名,一方面是因有真才实学,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吕祖谦的慧眼识才,公正评判。后忆及此事,陆九渊不无深情地写道:“公素与我,不交一字,糊名誊书③,几千万纸。一见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镜,斯已奇矣。”[3]305
据王文政《吕氏年谱补编》记载:“乾道九年癸巳(1173),吕祖谦三十七岁,在明招山服父丧。期间问学诸生重新集结,前后多达300多人,曾讲《尚书》,因陆九渊、汪应辰等人之劝阻,讲学至年底。”[4]66陆九渊对吕公无疑是很珍重的,但是,他那淳直的性格与强烈的道义感,决定了他对任何人的珍重都不可能超越理性而不讲原则。针对吕祖谦居忧教授这种所谓有损“纯孝之心”的“君子之过”,陆九渊写出了一封至诚而又很不客气的信。信中先云吕祖谦“聪明笃厚,人人自以为不及,乐教导人,乐成人之美,近世鲜见。如某疏愚,所闻于朋友间,乃辱知为最深。苟有所怀,义不容默”,继而说“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妇之所与知,而大贤君子不能无蔽者。元献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忧。元献屈致教导诸生,文正孳孳 诲诱不倦,从之游者多有闻于时。窃闻执事者俨然在忧服之中,而户外之履亦满。伯夷柳下惠,孟子虽言其圣,至所愿学则孔子。文正虽近世大贤,至其居忧教授,岂大贤君子之所蔽乎?”[3]61然后直言,您是给我们做表率的人,怎么能有一个大贤君子所不应有的行为呢?“执事天资之美,学问之博,此事之不安于心,未契于理,要不待烦说博引而后喻。”信中还说,就我所知,您的朋友中,没有哪一个不因此而为您感到不安,而您的心中也必定很难过。您若知过而幡然改之,以此感发诸生,其教育意义是何等的重大啊!信末云:“舜闻善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过,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愿不惮改过,以全纯孝之心。不胜至愿。”[3]61-62受到陆九渊的善意批评,吕祖谦深为感动,“遂辞散所有问学诸生,而独居守墓潜学”。[4]66后来,陆九渊对此高度评价道:“惟公之生,度越流辈,前作见之,靡不异待。外朴如愚,中敏鲜俪,晦尝致侮,彰或招忌。纤芥不怀,惟以自治,侮者终敬,忌者终愧。远识宏量,英才伟器,孤骞无朋,独立谁配。”[3]305全祖望在《东莱学案·附录》中称赞吕祖谦为“亦善改过者”。[1]13
《吕氏年谱补编》载:“乾道九年癸巳(1173),吕祖谦三十七岁。……八月,陆九龄(子寿)与刘清之(子澄)来访。十月,陆九龄复访,与之同观《实录》,有《实录节》。”[4]66次年,陆九渊三十六岁,其年谱载:“三月赴部调官,过四明,游会稽,浃两旬,复至都下,授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五月二十六日,访吕伯恭于衢。伯恭与汪圣锡(汪应辰)书云:‘陆君相聚五六日,淳笃敬直,流辈中少见其比。’又与陈同甫(陈亮)书云:‘自三衢归,陆子静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笃实淳直,朋游间未易多得。’”[3]490吕祖谦还在此信中转达了陆九渊对陈亮的善意:“虽未相识,每见尊兄文字,开豁轩翥,甚欲得相聚。”吕祖谦“觉其意甚勤,非论文者也”。[3]490此前不久,吕祖谦在《答朱侍讲二十四》信中云:“抚州人士陆九龄子寿笃实孝友,兄弟皆有所立,旧所学稍偏,近过此相聚累日,亦甚有问道四方之意。”[5](第一册)416吕祖谦在学术圈积极推介陆氏兄弟,对陆学深表关切,至去世前,还应陆九渊之请,抱病志陆九龄墓,对陆学予以客观评说。吕祖谦于陆氏兄弟之情分,由此可见。其实,在取得赐同进士出身时,陆九渊就已“名振行都”,“在行都,诸贤从游”,“朝夕应酬问答,学者踵至,至不得寝者四十日”。“复斋与学者云:‘子静入浙,则有杨简敬仲、石崇昭应之、诸葛诚之、胡拱达才、高宗商应时、孙应朝季和从之游,其余不能悉数,皆亹亹笃学,尊信吾道,甚可喜也。’”[3]487-488陆九渊的名声引起了朱熹对陆学的兴趣和警觉。他首先提出陆氏兄弟“不知师谁,然也不问师传”[6]的问题,接着收到吕祖谦介绍陆氏兄弟的来信,即在《答吕伯恭三十六》信中称“陆子寿闻其名甚久,恨未识之,子澄云其议论颇宗无垢,不知今竟何也。”[7]82册746之后,适逢陆九渊访吕伯恭于衢,朱熹极为关注,在《答吕子约十五》、《答吕子约十七》中指出:“陆子静之贤闻之盖久,盖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又如何耳?”“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然恐其说方行,亦未必肯听此老生常谈,徒窃忧叹而已。”[7]83册402就在朱熹对陆学深表堪忧之际,张栻在《与朱元晦秘书三十》来信中说出了同样的感受:“若临川,其说方炽 ,此尤可虑者。”[8]基于上述背景,“吕伯恭约先生(陆九渊)与季兄复斋,会朱元晦诸公于信之鹅湖寺。……按吕成公谱:‘乙未四月,访朱文公于信之鹅湖寺,陆子静、子寿、刘子澄及江浙诸友皆会,留止旬日。’”[3]490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吴文丁《陆九渊年谱新编》记之为:“先生三十七岁。六月,‘鹅湖之会’在信州铅山大佛寺即鹅湖寺举行。参加者有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近百人。六月上旬开会。二陆吟诗,刺朱熹。休会。翌日,朱子考子静《易》经‘九卦之序’,满意。继续进行‘尊德性与道学问’及‘为学之方’的激烈辩论。六月八日,因故提前散会。”[9]据与会者朱亨道书云:“鹅湖论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此颇不合。”[3]491侯外庐等认为,鹅湖之会“触及理学思想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2]373尽管朱陆仍存异同,未能会归于一,但双方在会后不仅言路畅通,继续保持交流,而且态度相当友善,极显大家风范。六年后,淳熙八年(1181)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据朱熹《答吕伯恭九十四》[7]卷三十四信中介绍,期间,二人不仅一同泛舟,讲学,悼念南轩和复斋,同时还就两派学术分歧坦诚地交换过意见,朱甚至想约陆在方便的时候一同入浙会吕,以期深入讨论相关问题。不料这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吕祖谦竟“因为体肥而死,年纪不过四十五岁”。[10]
以吕祖谦这样一位天才突然如此的早死,的确是12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朱陆等纷纷长歌当哭,为位而祭。陆九渊在《祭吕伯恭文》中写道:“期此秋冬,以亲讲肄,庶几十驾,可以近理。有疑未决,有怀未既,讣音东来,心裂神碎。与二三子,恸哭萧寺,即拜一书,以慰令弟。惟是窀穸,祈厕未肂,继闻其期,不后日至。”陆九渊哭诉自己“蹑屩担簦,宵不能寐,所痛其来,棺藏帏蔽。谁谓及门,绋翣已迈,足趼塗泥,追之不逮。矫首苍茫,涕零如沛,不敏不武,将以谁罪?”[3]306祭文还通过对往事的追忆,表达对死者的崇敬与感激,同时也表达作者的深刻自省以及对吕公的深深愧疚:“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权,或以取戾。虽讼其非,每不自制,公赐良箴,始痛惩艾。问我如倾,告我如袐,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坠,竟勤公忧,抱以没地。鹅湖之集,已后一岁,辄复妄发,宛尔故态。公虽未言,意已独至,方将优游,以受砭剂。”“追惟曩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岂足酬义?”“我固罢驽,重以奔踶,惟不自休,强勉希冀。比年以来,日觉少异,更尝差多,观省加细。”[3]306吕祖谦生前曾通过《与陈同甫》、《与刑邦用》等书信,对陆九渊在鹅湖会上的某些过激言行,以及在学术上的欠开阔等问题,提出过中肯的批评,陆九渊对此一直心怀感激,并引以为教训。
失去了吕祖谦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人物,朱陆间的交流开始出现障碍,后来竟屡现危机。朱诋陆为狂禅,为告子,陆讥朱为支离,两家互相水火。尽管朱陆原本都不愿意因学术矛盾而殃及相互间的友情,但由于他们在争鸣中往往容易意气用事而又得不到有效的调解,加之两边门人的非理性行为,致使朱陆之间的矛盾日趋扩大化、复杂化,吕公“欲会归于一”的遗愿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二、陆吕心说分析
(一)独立不苟的陆氏心学
对于“理”的认识,在二程尤其是程颐那里,主要是讨论社会伦理,而至朱熹一辈,则广泛地涉及宇宙间的许多问题,但其核心仍然是道德伦理,重点是研究儒家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教人首先必须多多读书,然后方可认识“理”,达到“理”的境界。陆九渊觉得没必要把“理”说得那么复杂,把方法说得那么繁难,因为道德根源就在人“心”中,只须发明“本心”,即是合于“理”也,并非一定要泛观博览,多向外寻求知识,故为学工夫之根本在于“易简”,即在日常活动中,确保“本心之善”[3]162。
陆九渊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3]149以此为立论基础,论定“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3]423,又谓“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3]4-5,进而得出一个著名论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3]483此类语录,曾被斥之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例证。实际上,对这种思维不可以简单地诠释为宇宙在我心中,或万物皆依附我心而存在,而应当联系陆九渊三、四岁时就开始探寻“天地何所穷际”[3]481的成长经历,逻辑地理解为:“方寸”或“心”中所蕴含之“理”与宇宙万物之“理”是同一的,因为“宇宙不曾限隔人”,[3]401人与“理”具有圆通性和无限隔性,所以有是心则有是理,有是心则有宇宙万物;如此,“心”、“物”关系似乎成了派生关系,然而,如此派生并非实体意义上的由我心之存在派生出宇宙万物之存在,而是通过人所特有的主体意识及其“满心而发”的活动,在“理”之意义上与宇宙万物打通,从而实现我心中之“理”与宇宙万物之“理”的交融契合,“至当归一”,“不容有二”。在这样的语境下,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也就呈现了鲜明的个性特色,即激扬人的主体意识,强调充分发挥人的潜在心能,号召人们:“收拾精神,自作主宰”[3]445。他认为“仁义者,人之本心也”[3]9,“本心非外烁”[3]51,“此心之良,人所固有”[3]64,“人所均有”[3]67,这就是说,“本心”之善,是与生俱来的,且无论圣贤或是平民百姓,莫不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九渊喜谈孟轲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11]378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人因受气禀、物欲、形势、习俗及俗论邪说等方面因素的干扰,致使“本心”放失,最终不能成为像尧舜那样心地明盛而纯善的人。有鉴于此,陆九渊提倡“存养”工夫,开创“发明本心”之学。这种有别于程朱派“格物穷理”的心学理论,令人耳目一新,颇受一部分学者的欢迎。有象山学者代表评价说:“先生之讲学也,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此心耳。其教人为学,端绪在此,故闻者感动”。[3]502在立学过程中,陆九渊通过与朱熹的鹅湖之争,更加重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累言“先立乎其大者”[3]400,更加自觉地坚持价值理性的优先地位和引领作用。尤为可贵的是,陆九渊所奉行的尊德性教育,并非强制性地用天理窒息人欲、以道心钳制人心,“而是以‘明心’(‘立心’)为根本”,[2]561即以人所固有、均有之心作为人生价值与意义之源,通过“存心、养心、求放心”,[3]64使人心得以明盛,纯善得以发扬,道德主体得以坚挺,人的自觉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如此,“某若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3]447这种教育理念,本质上是对人者尊严与价值的赞美,凝结着对天下苍生的终极关怀。
(二)自成体系的吕学“心”论
陆九渊在《祭吕伯恭文》[3]305-306中这样称颂吕公的道德文章:“玉在山辉,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繄人是寄。……属思纡徐,摛辞绮丽,少日文章,固其余事。颜曾其学,伊吕其志,久而益专,穷而益厉。约偏持平,弃疵养粹,玩心黄中,处身白贲,停澄衍溢,不见涯涘。岂伊人豪,无乃国瑞”,“《诗》《传》之集,大事之记,先儒是裨,《麟》《经》是嗣。杜门养痾,素业不废”。关于两家的学术联系,陆九渊写道:“先兄复斋,比一二岁,两获从欸,言符心契”,“道同志合,惟公不二”。从文献考察来看,吕公不仅有令陆氏肃然起敬的道德文章,更重要的是的确还有一系列与陆学“道同志合”的理学思想,而且极具研究价值。
和陆九渊一样,吕祖谦虽深受佛学影响,但一向以儒学为宗,主要提倡“治心养性”、“正心诚意”等学说,注重强调“心”的作用。他说“命者,正理也”,[2]345认为“天命”乃“天理”,又认为“天命”与“人心”相通,故谓“圣人之心,即天之心;圣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也。……此心此理,盖纯乎天也”。[5]第三册62又说“心犹帝,性犹天,本然者谓之性,主宰者谓之心”。[2]347这样,吕祖谦运用天人无间、合而为一的观点,将“心”、“性”同“天”、“帝”联结起来,进而又将“理”与“心”言之为“纯乎天”且无异于“天”者。如此,则“心”、“性”、“理”、“天”的内涵被联通起来而变身为同一的范畴。吕祖谦由此而进一步提出“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2]347,并得出“心即道”的论断。显然,所谓“心即道”实质上就是“心即理”的同义语。吕祖谦之所谓“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与陆九渊之所谓“道未有外乎其心者”[3]228的看法是相通的。在陆九渊著述中,“心”、“理”、“道”等一贯是被作为同一概念使用,虽有时变换为“太极”、“性”等别称,甚至间或与其他伦常概念一并混用,但本义唯一,不容有二,这就是“心即理”也,也就是吕祖谦之所谓“心即道”也。吕陆强调“心即道”,“心即理”,探讨天道与人道、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统一,追求和谐圆满的心灵美境,充分显示了一代思想家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辨证思考。
吕祖谦得出“心即道”的论断后,顺着这一路经继续思索,结果得出了和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3]483颇为近似的判断:“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2]347他还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11]302之说为依据,称“圣人备万物于一身”[2]347,认为“圣人”之心与宇宙万物是相通的,故看重“圣人之心”的地位与作用,特在《东莱博议》等著述中不厌其烦地予以强调。吕祖谦在本体论上与陆氏不谋而合的方面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时,往往把代表“天理”的“圣人”之“心”与普通人之“心”联系起来立论,如他指出:“人言之发,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2]349无论是“心即道”论,还是“心即天”论或“心即神”论,吕学都在一定程度上比较鲜明地凸现了这一特色。
吕学“心”论与陆氏心学之“道同志合”,还体现在认识论方面,如:吕祖谦的“反求诸己”论与陆九渊的“切己自反”说;吕祖谦的善恶伦理观与陆九渊的道德修养说,等等。从学脉上看,这些理论都主要源自于孟子的性善论与“良知良能”说;从主观愿望上看,他们都把医治人心作为医国治世的药方;从其它方面来看,二学的确各具特色,自成一体,但归根结底,就其本质而言,则恰如全祖望所说:“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1]3
陆吕之间,因仰慕或欣赏对方而建立起深厚友谊,又因敢于批评并善于对待批评而使友谊之树常青,这种珍重友谊、更珍重道义原则的品格,至今仍不乏启迪作用,可视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难能可贵的现代性的文化基因。
吕陆之交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发现并成就了一代心学大师陆九渊,南宋理学因为有陆学的独树一帜而大放异彩。后学认为,宋乾淳之后,学派主要分为朱学、吕学、陆学,朱学主张格物致知,陆学主张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可见,吕祖谦之辈在南宋思想学术领域拥有不可或缺的独特地位。罗素曾经说过:“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的10余人抽出,恐局面将全变。”[12]7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一说:“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如何?”[12]7笔者之愚意以为,南宋思想界,若缺一吕祖谦,恐将难有那般异彩纷呈的景象。
陆吕理论的共识,突出地体现在“人”学旨趣上。两位思想家着眼于心,立足于人,以现实的人为起点和归宿,以人性或人的本质为重要范畴,从各自的学术视角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人之所以能认识并能影响宇宙间万事万物,关键在于人人都有一颗天赋神奇的“心”在支配着人的一切思维与行为;人们必须好好地存养此心,使之能正常地发挥主宰作用,以确保人们的一切思想行为完全符合正义和常理。这种理论的特殊吸引力,在于它系统地抽象发展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典型地凸显了客观世界中人的主体地位及其重要作用。
注释:
①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2页。
②赐同进士出身,属第三甲。《陆九渊年谱》载:“先生既奏,名声振行都,廷对考官意其必慷慨极言天下事,欲取置首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问之,先生曰:‘见君之初,岂敢过直。’识者称其得事君之体云。”
③“糊名誊书”等。糊名,就是将考卷上考生姓名、籍贯等内容反转折叠密封,以防止考官作弊。誊书,就是考生交卷后,监考官先行糊名,然后送誊录院,再由书吏将考卷抄成副本交付考官批阅。与糊名誊书相关联的还有锁院制度,即为防止干扰考选,考官一经任命,即入贡院而与外界隔绝,至评卷结束才能出院。有人认为吕此前见过陆的乡试《易》卷,故“一见吾文,知非他士。”缺乏依据。详见吴文丁:《陆九渊全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1]续修四库全书.宋元学案:第51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钟哲点校.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王文政.吕祖谦与浙东明招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吕祖谦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6]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11:2969.
[7]朱熹.晦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8]张栻.南轩先生文集:卷三十[M].华氏剑光书屋,淸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本.
[9]吴文丁.陆九渊全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429.
[10]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5.
[1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2]孙响城.象山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