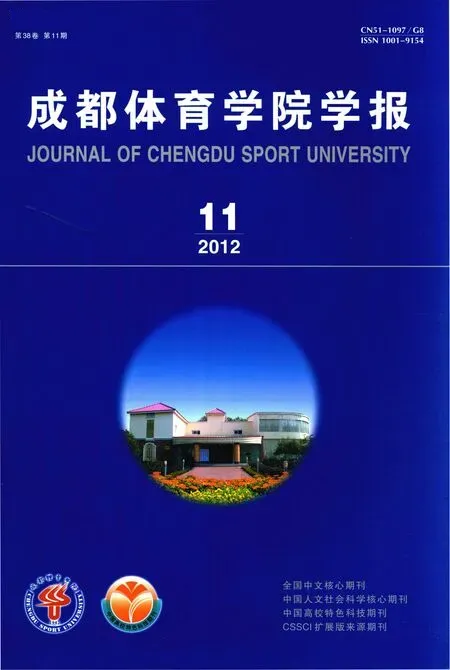一个屋檐下的体育法——体育法方法论的路径选择与思考
吕 伟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体育法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价值日益升温。近年来,法学界和体育学界人士(以下称体育学派和法学派)都开始将视角投入这一场域之内。在这一场域内,两大学派法学方法论的不同导致了相互之间的学术分野,而在这一学术分野之内,所使用的方法,所阐述的价值和理念,归根到底是体育法哲学方法论的问题。在此阐明一点,无论法学派研究的体育法,亦或是体育学派研究的体育法,大家都是一个屋檐下的体育法,这也是本文阐述的前提性条件,两个学派从不同的法哲学立场出发,探讨体育法的学科任务、内容、对象等基础理论问题,两者互为前提、互相借鉴,最终处于一个体育法的屋檐之下。
法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既然其如此之重要,那么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大颇具代表性法学家的学术进路,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可能会给予我们启示与思考。
美国著名法学家卡多佐大法官采用列举方式阐述法哲学,“其认为法哲学应当告诉我们法律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成长以及它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更具体地讲,是讲述关于法律的产生、发展、目的和功能的学说。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被创制出来的?在法被创制出来之后,它又是如何发展的?当法官无先例可供选择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是什么原则指导他对处理案件的原则进行选择?是什么力量迫使法官必须遵循先例以及法官所追寻的法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法哲学的问题。”[1]卡氏认为给法哲学下一个抽象的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完整或是不精确的,所以其采用列举式的方法探讨法哲学的问题。在追寻法哲学问题中,法律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成长以及它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更具体地讲,是讲述关于法律的产生、发展、目的和功能的学说,是核心要义所在。卡氏从经验事实出发,以问题为中心,以实证主义哲学构成其主导法哲学思想。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法律进行思考,即涉及价值的思考,是作为文化事实的法律思考,它构成了法律科学的本质;评价价值的思考,是作为文化价值的法律思考,法哲学通过它得以体现;最后,超越价值的法律思考,是本质的或者无本质的空洞性思考,这是法律宗教哲学的一项任务。”[2]拉氏认为法律作为人类的立法实践,只有从其价值理念出发,才能得以被真正理解和遵守,法律就概念而言,首先应是先验的,它不是法律科学的结果,而是法律科学的工具,它不是对经验法律现象之偶然性的体现,而是对法律思想的必然性范畴,正义,合目的性与安定性构成其内在规定性。
纵观两个学派,英美法系以问题为中心,从经验实证出发,关注法律在实践中运用和实施的状况,关心的是社会中的法律。其方法是从经验到理论,申言之,其是从个别到一般进行归纳,在归纳之后再进行演绎。大陆法系以“逻辑”为中心,从概念出发,强调运用逻辑方法对法律文本进行研究,关注法律条文的逻辑结构。其方法是从理论到实践,就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过程,先演绎再归纳。
以上两位法学巨匠的学术研究进路,或多或少代表了当今世界法学方法论进路的方向。这样的学术路径多少与其法学传统研究模式有关系。两个学派的研究进路都具有其相对合理性和价值性,都对体育法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有莫大的指引和帮助作用。同时,两派的法学方法论进路也为体育法方法论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参照,通过这个参照我们能够检视当下我国体育法学界学术研究的现实问题,并能指引我们做出正确的路径选择。
对于本文来说,需要将二者作为“参照”和“指引”,以此来检视和指引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路。就此而言,本文将探寻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原理,称之为体育法方法论的厚度,将研究路径的方法论分析,称之为向度,而将不同向度内进行的推演,称之为体育法方法论的逻辑推演。
1 法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1.1 法学派——“部门法问题中心”下的向度研究
法学派研究体育法多以规范分析为路径,以三段论(大前提—规范、小前提—事实、结论)的逻辑推演进行所谓的法规范分析,这样的研究被界定为规范法学下的方法论研究,其诸多流派中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麦考密克等人构建的分析法学奠定了规范法分析的根基。其中,以凯尔森的最为极端、最为“纯粹”。其理论核心最具特色的是“提出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理解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3]概言之,凯尔森的纯粹法以法规范为前提,是从规范到规范的分析,仅在规范内部进行逻辑循环论证,是一个封闭、自洽的内部循环论证构造。
我国法律体系自清末民初学习借鉴大陆法系成文法以来,基本的法律体系框架属于大陆法系一派,而大陆成文法系学术研究注重概念的界定,逻辑的推演,从法条出发,逐一对法条进行解释,力图构筑逻辑严谨,体系完整,内容自洽的法体系。以我国法的体系为例,“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律部门、民事法律部门、行政法法律部门、经济法法律部门、社会法法律部门、刑法法律部门、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法律部门。”[4]同时,在这些部门法之下还可以根据调整内容的不同再具体进行划分。
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较多受到这种研究路径的影响,诸多学者以成文法学术路径构建体育法的学科体系,一系列典型代表著作开始形成,例如董小龙、郭春玲《体育法学》、张厚福《体育法理》、闫旭峰《体育法学与法理基础》、韩勇《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张扬《体育法学概论》、汤卫东《体育法学》等著作。其中董著与韩著参照部门法的法律体系划分模式进行体育法体系构筑,张厚福等四位学者以传统的“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三分法为路径,以体育分类理论划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并依照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的逻辑结构进行路径研究。
董著与张著为代表的两种体系模式,虽然在分类框架下存在不同,但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并无实质差异,都是采以“逻辑”为中心的法规范分析为进路。受此进路影响,我国学术论文的撰写也多采用用此种模式,例如周青山《体育法的概念与范围》、童宪明《体育法学的学科研究》等论文。
1.1.1 部门法与三分法模式的比较分析
对比两种模式,笔者认为以部门法问题中心为进路划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进路,但相较而言,体育理论三分法的“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模式(以下称三分法)则更为有利于学科体系的定位与发展。原因有三:
第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文本来看,体育法立法设置为七章五十六条(现为五十五条),其主体结构是以体育分类理论进行的法条归类。因此,以三分法的模式研究体育法,相较之下更为符合体育法研究的文本逻辑。再者,关于相关配套立法的研究,也多采用体育三分法为中心进行的相关立法。我国体育法著名学者于善旭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中,对体育法的学科体系有过精深的论述,其提出“以《体育法》为核心,建立体育法规体系,并将体育法规体系划分为两个层次10个部门法规的内容结构。[5]
第二,从体育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看,体育部门基本是以三分法进行的行政机构划分,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其行政行为中,可能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问题,但其发生的领域仍在社会、学校、竞技这一场域之内,仍为该场域的主管机关负责协调处理。
第三,体育法是体育共同体的法,制定体育法的目的是为体育共同体服务。体育社会领域内的规范对体育共同体最为有效力,相对而言,三分法的领域划分是已然事实层面的问题,部门问题中心主义却是应然层面的理论构想。
从实践角度而言,“部门法问题中心”路径研究,是法学派围绕“法律定性”所设计的运行机制。申言之,是法官对于发生的案件,做法律性质的诊断,属于法律的“先决问题”,即属于民事、行政亦或是刑事哪一类的问题。经过定性后,再从事“找法”的工作。然而,法律定性的“先决问题”,仅仅是法官处理案件时遵循的逻辑推理和分类处理的思维进路,对于体育实践问题并无多大的实质意义。
反观“体育三分法”的路径研究,从形式来看其也为一种归类研究,但三分法是以领域属性为“先决问题”的研究路径,而不存在法律定性问题,其制度设计主旨在于体育实践问题的分类管理,所处理之问题即便存在法律适用的情形,其首先做的也是一种直接“找法”的工作,即从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领域找具体法律规定的思维路径。
就此而言,以体育领域问题为中心,无论从实然层面和应然层面,还是从实践操作角度而言,其都更为有利于体育法的学术研究。
1.1.2 “部门法”模式与“体育实践”模式的体系差异
就目前体育法的学术研究来看,利用法理论移植来观照体育实践问题之研究,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阶段。从1995年体育法颁布后,围绕体育法条文的法解释,到法学部门理论的全盘移植,被认为是体育法的实质所在。周青山在其博士论文《体育领域反歧视法律问题研究》中说到“我们要让体育法更像”法。[6]言下之意,现在的体育法还不能称作法,还缺少法学理论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可能指的就是上文所分析的“规范法学”方法论。周青山在其硕士论文《体育法的概念与范围》中,富有前瞻性的以“部门法问题”为中心,构建体育法研究的范畴,其主旨以体育与部门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展开问题研究[7]。简言之,如果体育领域内涉及到民事法律部门问题,就应适用民法及相关理论进行规范分析,对于体育特殊性的问题,可以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以此来丰富法学理论,但体育法涉及的民事问题,仅是特殊主体产生的民事问题,总体而言仍是民事问题,其他部门法问题以此类推。如按其构建的“体育实体法与程序法”模式,实践中起主要规范作用的体育规则,则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即否定体育规则的法意义,但实践中真正起到法规范作用的却又是这些体育规则,周著等于将体育规则排除在了“体育法”之外,但颇为有意思的是周著对于体育法的定义则采多元化、广义性的定义,由此来看周著划分的体育法体系与其定义的体育法概念实质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伪命题,其所讨论的体育法仅是国家制定之法,排除了体育规则的存在。
学者韩勇在其《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以“问题中心”为走向,对体育法的学术进路做出了富有建树的探讨,但该文的“问题中心”不是部门法问题中心,而是以“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例如书的构架“体育与侵权、知识产权、伤害、纠纷解决等”[8]。其进路恰好与周青山相反,韩勇以“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不以部门法为前提,探讨具体问题中可能会涉及某一部门领域的法律问题,但不对问题框定范围。
韩勇的“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的进路,同时在法律技术层面上解决了周青山构建的“体育实体法与程序法”命题困境,即体育规则的法律性问题。如果按照“部门法问题”中心的模式,其前提必然是部门法内的制定法,这样做的后果使许多真正起到规范体育秩序的“体育规则”无法涵盖在其之列。因为体育规则不具有法的形式特征,不能称其为法,所以自然也就排除在体育法之外。而韩勇以广义的体育法为前提,认为“体育法既包括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育法律规则,又包括体育各项目长期形成的规则(包括项目的竞赛规则、技术规则、管理规则、处罚规则);既包括成文的规则,又包括不成文的规则;既包括各国国内的体育规则,又包括国际体育规则;既包括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则,又包括依靠行业自律行使的规则”[9]。关于体育法的广义定义,学者郭树理在对体育规则与法律规则进行比较后,总结认为应采取广义、多元的“体育法”概念。其将体育法界定为“由体育运动的当事人自己创造的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体育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这类规则具有自治性、专业性、国际性、文化性、传统性以及非公力强制性的特点,但其中的一部分经过国家的体育立法程序,成为国家体育法律法规的一部分,则具有了公力强制力。”[10]
韩勇采用的大体育法的定义,涵摄基本的研究范畴,其不同于以“部门法”为前提的体育法研究进路。应该说,韩勇的大体育法是一个涵盖范围更广,涉及内容更全面的定义。就体育法的研究内容来看,狭义的制定法并非是体育法研究的主要内容所在,反观体育项目长期形成的规则,由于对体育领域的影响力和实际规范效力,其则才是实然意义上真正的“体育法”。“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以“规范-规则”的二元路径,很好的解决了体育规则的属性问题,更有利于体育法学的学科发展。
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荷兰ASEER国际体育法研究中心曾专门进行“Hague joint proposal on the definition of sports law”学术主题研讨会。对于体育法上的“法”,国际体育法学界从公法(public law)与私法(private law)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体育法的研究兼具公私两面性,公法部分涉及与国家和国际立法相关的部分,包括法律、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决定、习惯法、判例法等。私法部分涉及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规章、体育习惯、体育纪律处罚、体育仲裁等内容。[11]我国学者贾文彤也提出“我国体育法体系应该包括软法和硬法两大板块,它们按照法规范的公共性高低和刚性强弱顺序排列进行组合,实质上形成了一个谱系结构。[12]学者谭小勇、姜熙在《全球体育法引论》中也提出了法的多元创制催生全球体育法,并引证尤根·埃利希的“活法”来论证全球法的合理性。[13]
1.2 法学派——“普通法”判例问题中心下的向度研究
普通法是指发源于英格兰,由拥有高级裁判权的王室法院依据古老的地方习惯或是理性、自然公正、常理、公共政策等原则,通过“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在不同时期的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具备司法连贯性特征并在一定的司法共同体内普遍适用的各种原则、规则的总称。[14]其与大陆法的主要不同是大陆法主要是由大学教授完成的,“professor-made-law”(法学家法),而普通法则是从法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所作的一系列判决中不间断地抽出的“judge-made-law”(法官法)。[15]
体育法的方法论研究受到判例法问题中心的较大影响。以郭树理和黄世席两位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两位学者以“国际体育仲裁”研究为视角,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利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即将举办北京奥运会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法律实证研究。
郭树理在其著作《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比较法与国际法的视野》内,对一个个鲜活的司法案件进行解读和分析,不断归纳出体育法所具有的独特原则,以此在“体育实践”问题中涵盖体育法的研究内容和体系范围。[16]
黄世席在其著作《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中,对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多个代表性经典案例进行归纳分析,也对体育法的基本原则、体育法的学科性质等问题,从比较法的层面给予了一定的分析。[17]
两位学者的研究,具备一定的高度和水准,丰富和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他们的著作让我们了解到体育法的形成、成长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让我们清楚的在具体鲜活的案例里,了解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的仲裁员在无先例可供选择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是以什么原则指导其对处理案件的原则进行的选择,是什么力量迫使仲裁员必须遵循先例。
具体来看,两者的研究是从案件事实出发,以问题为中心,利用案例、判决书、统计数据、体育机构政策的改革和效果等事实进行分析,有别于大陆法系,从“法条”出发,以概念为前提,进行法体系内部逻辑的推演。相较部门法问题中心的大陆法研究路径,判例法问题中心的研究更具体、更真实,更有利于体育法的现实发展。
2 体育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体育学科是一个综合研究学科。其涉及到运动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学科的内容,也涉及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等人文社科的研究内容。体育法学作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使用法律的手段调整和规制体育,从法规范的严格意义上说,应从学校体育说起。如果从韩勇的大体育法来看,则从体育规则的起源就可以算起,但笔者这里主要拟从规范的法沿革算起。体育领域为何会出现使用法律作为调整的现象出现,而且直至今日已成为主要的手段,这与体育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
2.1 体育理念——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沿革
我们知道体育运动经历了几次大的发展。从顾拜旦到罗格为首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变迁,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体育,例如体育的军事说、教育说、社会说、娱乐健身说、文化说等体育理念的认识变化。我们对体育的本质认识逐渐发生着改变。有如学者熊欢所言,“可以说体育是从身体的运动到社会的运动之嬗变,在这一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体育,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所具备的功能论,还可以从体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体育是一种政治制度,体育是一种经济现象,体育是一种传媒方式,体育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体育是一种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等,所显示出的体育作用论。”[18]从功能论到作用论,折射体育的发展变迁。而对于体育法的研究来说,在体育法的本体“体育”的变化下,体育法的学科研究也从学校体育法令走向社会体育法令与竞技体育法令之场域变迁,体育功能的扩大使得体育法的研究主体和范围也扩大。
认识体育的本质,是认识和研究体育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因体育而生之法,而不是制定体育之法。现许多法学派研究学者,在未认清体育发展之本质时,便从先验之形而上开始以“法本位”构造体育法,规范体育法,这种不以体育问题为中心的“先验概念”主义研究,往往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因为,再完美的理论也是要为实践服务的,否则其永远也只是空洞的“教条”。当下我国体育法的尴尬境地,其本本的纸面法,鲜有落地转化为实践法的现状,可能就在于未能立足于实际问题,以至于被学界长期诟病。体育毕竟是一种身体社会实践活动,一切法律应来自体育实践活动的需要,这才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理念提出的真实要义,而不是概念之下的问题中心。
2.2 体育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体育法的发展在体育领域内,不能逾越一个藩篱,即体育法是体育所生之法。体育问题是体育法的前提所在,没有体育问题的法,就不是体育法,仅是臆造法。体育法应以体育问题为中心,构造体育法。体育现象是体育问题的征表,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对体育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是体育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体育学派学者研究的方法注重对现象、成因、对策的分析,喜欢对历史沿革、体育体制、成因、对策进行论证,但如此的研究,多少给人有缺乏理论逻辑分析的空洞性感觉。这种研究方法到最后,逐渐演变成了学者们倚重的价值、伦理、心理的应然分析,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体育学内常常有学者在论文中高频率地使用“应该”二字。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不可取,而是要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具体的经验观察和分析,实证研究主要依靠的就是经验分析,研究不能仅现象探讨,在现象背后更需要做的是本质的分析和理论的归纳。
法学研究也注重现象、成因等问题的探讨。例如从法学流派的研究来看,存在自然法学派、法社会学派、历史法学派等诸多学派的学术进路研究,这些研究为丰富和提升法学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围绕法的解释提供诸多有价值的素材,各派研究之间仅存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不同,但都是研究法的生成条件、法的起源、法的变迁、法的功能、目标。法学研究在注重现象、成因的分析下,更注重现象背后的理论构造,不论英美法系以“判例”为逻辑起点,亦或大陆法系以“法规范”的法条为起点的逻辑构造,两派都非常注重现象背后的理论构造。以纯粹法学派的凯尔森最为突出,其研究注重规范体系内逻辑自洽的推理,强调体系性的构建。从这点来看,其对体育法理论的未来研究,有较大的指引和借鉴价值。
3 一个屋檐下的学派对立之融合
综上所述,本文希望构筑一个独立学科的体育法,一个法学派与体育学派共处一个屋檐下的体育法。体育法合而不同,学派之争能使得学科理论研究深耕细作,能使理论研究更具深厚。今法学派内尤以刑法学渴望构筑学派对立,例如日本的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之争历时百年,为我国刑法学者所羡慕,有些学者甚至人为推动学派对立。美国法学家哈特与德沃金、德福林、富勒之间的论证,使得法律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的讨论,越辩越明,形成了一系列经典著作。
体育学派与法学派最大的不同是,它脱离了法律的框架,在法律之外,从社会、体制等其他方面观察、研究整体的体育现象,研究体育的法律制度。如果说法学派是在法律框架内研究体育法(规定之法),那么,体育学派则是站在法律框架则之外,从法律外部,研究体育法。法学派作为研究法规范的学科,它只能法学地研究体育法,这是由它的学科任务所决定的。然而,体育问题不只是法律上的问题,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首先是社会现象。因此,没有对体育社会的、成因的、体制的等多方面的研究,我们是不可能全面、理性地认识和把握体育问题的。两个学派应互为借鉴和倚重,体育学派为法学派提供“现象问题”素材,法学派为体育学派提供规范分析,两者互为前提。
“学科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成果和水平的标志。在学科的划分问题上,理论逻辑是次要的,社会需要和人类对社会知识积累而形成的学科是首要的,只要社会需要而又具备独立学科的资格,就应以独立学科对待。”[19]
体育学派与法学派的不同研究方法之间不存在价值上的判断之优劣。体育法研究中两派学科任务的不同,导致了两派学科的概念、对象、方法等基本内容的不同,但最终不妨碍二者都是一个屋檐下的体育法。
[1]孙文恺.社会学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0;156-157.
[2]拉德布鲁赫著.王朴译.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4.
[3]徐爱国.分析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0;66.
[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0;156-157.
[5]于善旭,张剑,石岩.建立以《体育法》为核心的我国体育法规体系的框架构想[J].中国体育科技,1999,35(1):3-10.
[6]周青山.体育领域反歧视法律问题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法学院,2011:4.
[7]周青山.体育法的概念和范围[D].湘潭:湘潭大学法学院,2007.
[8][9]韩勇.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1;2-20;9.
[10]郭树理.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比较法与国际法的视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45.
[11]荷兰ASSER国际体育法研究中心.体育法的定义[EB/OL].http://www.asser.nl/default.aspx?site_id=11&level1=13914&level2=13931&level3=&textid=39391,2012-05-10.
[12]贾文彤.再论我国体育法体系的建构—软法视角切入[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0,24(2):55.
[13]谭小勇,姜熙.全球体育法引论[J].体育科学,2011,31(11):77-79.
[14]王名扬.比较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1-19.
[15]大木雅夫著.比较法[M].范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2;118.
[16]郭树理.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比较法与国际法的视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
[17]黄世席.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9.
[18]熊欢.身体、社会与体育——西方社会理论视角下的体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7;2-20.
[19]王牧.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科际界限[J].中国法学,200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