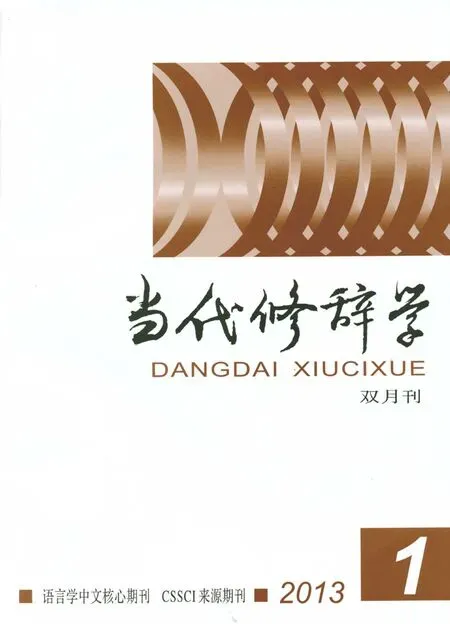语体风格的共性与个性
——试论“自己的样子”的语体风格学
丁金国
(烟台大学中文系,山东烟台264005)
提 要 陈望道先生曾提出语体风格研究应有“我们自己的样子”。沿着望老的提示,从与异样的对比中我们发现,汉语语体风格论异于西语的殊异性在于:语文以体制为先,理论形态上语体与风格相互依存,风格体系上阴阳对立,阐释手段为以象表义。现代语体风格论体系的建立,只有立足于自己固有的特质,吸取现代新理论、新方法来构建。其现代性的主要标记:在理论上,以语义为核心的结构原则必须进入体系之中;在具体操作上,成分的离析和量化微分析当是重要的实证性手段。
一、引 言
1965年9月20日陈望道先生在《关于修辞问题的谈话》中说:“我国研究风格,包括语文‘体裁’和表现‘体性’,是很早的,现在更是在研究,今后还要继续地深入研究。不过,我们的研究,有我们自己的样子,不一定是人家的那个样子。”(转引自陈光磊2010:3-4)这一段话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那就是:我国语体风格研究已经有“自己的样子”,并且今后的研究依然应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样子”只有在与异样的鉴衡中方能显示,本文试以屈折型的西语为参照系,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语际交流本质上要凭借语体而进行,其中信息交流固然是主项,然语体错位,必然累及信息的接送,其结果是伤损语际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研究语体的共同性,而是通过对共同性的参照,来寻找和发现汉语语体的特异性,以回应望老四十多年前“语体风格研究应有自己的样子”的召唤。2012年又是《修辞学发凡》问世八十周年,藉此作文以志纪念。
二、语际交流的通约性
1.以体为语的普遍性
统观人们对语言运用的研究,尽管时代不同、理论观点相异,但却一致认同——以语体为载体进行信息交流是不同语言间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说明,不同的语言及其运用规律,存在着通约性。正是这种语体的通约性,为语际交流开辟了天然的通道,使得操不同语言的个体,当其为着同一个话题进入特定功能域时,尽管各自语言不同,性情、爱好各异,但所言所论,都严格限定在话题的宗旨要求的语体范围内,极少有越“体”现象发生,这就是语体的通约性之谓。语际间之所以有此通约性,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生存空间的同一性所决定的思维规律的一致性所使然。
这种通约性可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一是从功能的视野进行观察,扫描不同语言,在语用中的语类存在状态;一是从表达的角度,即以语篇的表达方式为立足点,来审视语体文脉运行轨迹。西语的语体论就是建立在功能的基础之上,所谓功能语体,其分类依据就是言语运用的功能域(丁金国2004)。苏俄修辞学和西语文体论都据此对语体进行了划分。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俄的格沃兹节夫在《俄语修辞学概论》中就将俄语的语体分为日常谈话语体、公众事务语体、科学语体、政论语体和艺术语体。1977年科任娜在其《功能修辞学》中作了五分:科学语体、公文事务语体、政论语体、艺术语体和日常口语体。两相比较,完全一致。欧陆的西语文体论,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英人克里斯特尔和戴维《英语语体调查》(Longman出版社,1969)。该书将英语语体区分为会话语言、评论语言、宗教语言、报道语言、法律语言和科学语言六类。在“建议:进一步分析”一章中,又补充列出电视广告语言、文字广告语言、公众演讲语言、文字说明性语言、公共服务语言、口头法律语言、新闻访谈语言和科学语言等八种。与苏俄的分法显著区别是,克里斯托尔和戴维二人并没有将艺术语言单列出来予以分析,而只是在第三章中有所涉及。
国内外语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始,将西方的语体理论译为“文体学”并系统地引入,以英俄语文体著作为主,间有一两部德、法语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对语体的分类,都有新闻语体、广告语体、法律语体、科技语体、日常会话语体和文学语体的区分。汉语学界的功能语体研究,受苏俄影响较深,属舶来品。我国语文学界对这种引进的理论,目前还处在消化之中,仅是理论探讨,还没有进入语文教学和付诸言语实践。公正地说,功能语体所揭示和归纳的言语事实,是有道理的,也符合汉语的语用实际。但因其理论抽象程度过高,概括性太强,故至今仍是语言学家书斋里的功课。从表达角度来观察语体,我们将在下文专门论述。
2.表达选择的共同性
表达方式是语用者依据意念与质料性质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对表达的选择。应该说这种选择是无可逃避的,只要开口说话就要有表达方法,它是实现语体各项功能的主轴,是一切语篇的流动性意绪在时间轴上的展现方式,不同的展现方式决定着语体的性质及其之间的差异。如新闻语体主要表达方式是叙述,广告语体的主要方式是说明,论辩语体的主要方式是议论,抒情与描写主要出现在审美语体之中,等等。
表达作为流动性的意绪,国人称为“语脉”或“文脉”,西语则称为语类结构潜势①或宏观结构(张德禄、刘汝山2003:4)。所谓语类结构潜势,尽管提出者们对其解释语焉不详,然此一命题却颇具启迪性,我们认为表达即是外化了的结构潜势,正是这种语义结构潜势,制约着语篇表达方式的选择。可见,不同的表达规定着不同的语体。反过来说,不同的语体要求与之相匹配的表达结构。语篇的语脉运行,其表层的形式联结,传统上称为起承转合,西语则称为衔接与连贯。如果说语体与功能域之间的依存关系是外在因素对语体的制约,那么表达的选择性,则是语体的内在规则对语体的潜在规定。这种语体与表达方式的对应关系,汉语与西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即使在语言类型上与汉语、西语迥异的日语,也分立着叙述、说明、议论、描写等语体类型。通常表达方式计有记叙、说明、议论、描写和抒情等,我们认为对话应独立成为一种。如审美语体中的戏剧和小说,就是典型的对话体,还有新闻语体中的访谈,也具有对话性。它之所以能独立成体,其理由在于:(a)对话体在人们的言语生活中比例极高,是人际交流的主要形式;(b)对话体由口语转化为书面形式时,因其对原语境的模拟,因而使历时接受者,角色发生转化,从间接接受进入直接接受,这种身临其境的在场性,更利于跨时空的交流;(c)关键是其本身存在的形态结构所显示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异于其他五种,故确乎应单列一体。需要说明的是,这六类表达语体,在言语交际中的出现频率是不一样的,对话体出现频率最高,其次是叙述体。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在表达语体系统中地位上的差别。虽然它们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但存在着位差,其序位是:叙述→说明→论证→对话→描写→抒情。叙述是基础,它几乎可进入一切表达,或者说一切表达都是建立在叙述之上。任何语体中的表达方式,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以一种为主,其它辅之。
3.价值判断的相似性
所谓价值判断,既指对语篇的语用效果的审视,也指对附着于语体之上的风格形态的关注程度。尽管东西方对语体的风格形态在其各自的研究中所提出的范畴不同,但对语篇的语用效果进行评价,对语体层级性的认识却有着诸多的相似点。正是这些相似点确保了语际交流的顺畅。对于语体的风格形态,西语讲层次,汉语讲对立。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德米特里乌斯在谈到演讲体时,就区分出简朴、庄重、修饰和刚重,虽无层次意识,但有类型观念。到了古罗马时代,西塞罗首次提出三体论,即一切演讲体,均可依照所用的语料和论辩表达以及是否有证明力、取悦力和劝说力,划分为平白体、中间体和庄重体。其中,平白体不事修饰,以简练、纯朴、清晰见称;庄重体以雄辩的逻辑力、典重的语辞、铿锵的语势见著,中间体介于平白体和庄重体之间,重修饰,追求言辞的华美。20世纪中期,欧陆有人从语境的角度,将语体划分为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从语境出发,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功能域来判断语体的正式程度。因为任何一个言语事件,都毫无例外地包括下列六个要素:我是谁?对谁讲话?为何目的?在什么地方?讲什么?如何讲?这六个要素是对功能域的对象、目的、时间、内容、方式的进一步分解。其中的任一项,都可分出正式与非正式。1962年马丁·朱斯在《五只钟》(Monton&Co.,1962)中,将风格区分为五个等级:庄严体、正式体、咨议体、随意体、亲密体。前二者为正式体,后二者为非正式体,咨议体为中间体。朱斯的五分,实际上是西塞罗三分的扩展,将层次顺序由从低趋高颠转为由高趋低。就语用实践而言,还可七分、九分,以至无限。
国人对语体风格的评判,一向以二元对立的模式进行操作。从《易》的阳刚、阴柔中,获得灵感,悟释出语言运用中的阳刚系列与阴柔系列,并以此为两端,去寻找中间层的亿万品次。
品察西人的正式与非正式层级体系与国人的二元对立体系,我们惊异地发现:何其相似乃尔!就语用哲学而言,任何语体都存在着语体级差上的选择,正是这种级差性,为语言运用提供了形式多样可选的语体级别,使得语言运用丰富多彩。对于语体风格间的等级差,洪堡特在讨论各种语言的特征时曾说过,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由民族的集体财富逐渐转化为个人的属物。因之,语言精英们的语体便与大众的语体对立起来,其结果是使语言获得了双重语体。洪氏对这种对立的评价是:“只要文学语体与大众语体的对立保持着适当的关系,对立的双方就可以成为两个相互补充的源泉,向语言供输力量并确保语言的纯洁性。”(洪堡特2004:199)哲人的隽言睿语对我们的启示有三:(a)对立的语体并非对抗,而是互为补充,推动着社会语言生活的正常运行。可见,典雅语体与低俗语体的对立是语言干预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b)同一语体内部适度的级差存在,不仅标示着语言的存在状态,也展示着语言社会对语言运用的关注程度,语体级差的存在不单纯是语言运用问题,而是社会文化繁荣与发展的镜像。(c)语体的级差存在,就语言本体而言,既是其自身调节的重要机制,也是其发展的动力。
三、汉语语体风格论的特异性
1.语文以体制为先
在古典语体风格论发生之前,先民在其语文生活中,已显示出依“体”言谈的痕迹,《尚书》“典、谟、誓、诰、训、命”的六体勾勒,就是明证。《书》、《诗》分纂,《骚》、《赋》行世,诸子百家驳杂恣肆,虽无理论抽象,然却都有序不乱,显然在先哲的言语生活里,以“体制为先”的意识已在萌发之中。最早作理论概括的是宋倪正父,倪氏在其著述中明确提出:“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转引自吴讷1962:14)王应麟、王安石、王正德、张戒等都曾对倪氏的论述作过肯定性回应。洎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凡例”开篇就是“文辞以体制为先”。对“体制为先”的学理,明顾尔行在《刻文体明辨序》(见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又作了通俗透辟的阐释:“尝谓陶者尚型,冶者尚范,方者尚矩,圆者尚规,文章之有体也,此陶冶之型范,而方圆之规矩也。”迄今,语文“以体制为先”已从方家的理论主张,融化为语文生活的规则,遍及为大众的话语习惯。此点固然是普世通则,然有鉴于汉语的特异性和其语体类型的绝对多样性所致,故而“以体制为先”就自然成为汉语语体风格论特异性的第一要点。
2.语体与风格依存的理论形态
汉语的语体风格论,是在“体”、“体制”、“体性”的名义下萌生、生存、成长、孳乳的。“体制”相当于现代的语体,“体性”相当于风格,“体”二者兼而融之。汉语的语体风格论异于西语的是:从其发生伊始,就是在体制与体性相互依存的形态下发育、成长,尽管二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语体中隐显程度有别,但从未缺位。
这种体性合一的理论形态,宋陈骙认为始源于《左传》。陈氏在恣阅古籍讽诵考据随手而录的《文则》里,将散见于《左传》的体性意识提抉、梳理,“摘其英华,别为八体: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陈骙1985:27)。左氏的所谓体,充其量只能算是中国古代体制与体性共存关系的朦胧认识的反映,将其说成体性一体的滥觞,显然失当。将体性融为一体进行理论论述,最早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八体四格的提出,显示出语体风格理论上的自觉。晋初陆机在《文赋》中,将曹氏的八体四格,细化为十体十格:“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士衡较之子桓不仅仅是八化为十,更重要的是从二体共一格,剥离出一体一格,理论上无疑又前进了一步。逮及刘勰《文心雕龙》,则将体制与风格的辐辏关系进行了彻底剥离,析出二十一体八格。二十一体是: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囊括了24类)。八格(刘氏称为“八体”)是: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肯定有体必有格的前提下,否定了体与格的对应关系,体是体格是格,相关但不相应;一是提出了一格对多体的理论思想。八体(风格)对应的是几十种语体,这就意味着,一种风格可以在多种语体上显示出来。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刘氏首次提出,不同风格对修辞手段、表现方法和语言特点有着不同的选择,现代汉语的语体风格论,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来。唐宋以降,虽然语体与风格分而治之,但在以体为宗的著述里,从不缺少格调的述说(见陈骙《文则》、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而以论风格为专任的著述,也均以语体为机杼展开。自钟嵘《诗品》始,“品”为标记,专用于对特定语体的风格形态的评论。语体与风格分立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唐有《二十四诗品》(司空图),宋元以还,由诗品衍化出赋品、词品、文品、曲品、戏品和书画品等等不一而足。各品目虽标立有异,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没有超出表圣所圈定的品类,都是沿着《诗品》的思想及范畴,在阐发演绎的同时,围绕元范畴进行增删整合、繁衍孵化。
统观中国现代语体风格理论形态,其代表性的体系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为代表,一类是以王德春《语体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为标识②。前者既谈语体,也谈风格,在风格的名义下讨论语体,也就是说风格是上位,语体则是风格的下位,所谓语体风格之谓也;后者则只谈语体,不谈风格,将前者所论的风格,化作语言特征或语言运用系统概而论之。传统上语体与风格依存的理论形态,淡而化之为纯语言分析。应该说后者是典型意义上的现代语体论。
3.阴阳对立的风格体系
汉语传统语体风格论的第三个特征是阴阳对立。阴阳对立导源于《易》,即“一阴一阳谓之道”,“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并由此衍化出“阳刚”、“阴柔”。“阴阳刚柔”在《易传》中出现频率之高,是其他范畴或概念难以企及的。笔者初步统计,“阴”、“阳”、“刚”、“柔”共出现202次。天地始源于阴阳,阴阳生刚柔;人类始源于阴阳,阴阳规定着人性的刚柔。这种极性对立的哲学根基,使汉语风格论从一开始,就孕育在“阴”、“阳”、“刚”、“柔”的母体之中。但正式将阳刚、阴柔确定为风格论的元范畴,确是肇始于刘勰。刘氏在《文心》里,始以“刚柔”取代“阴阳”,以“刚柔”论述气质、文势及语体风格的关系。在语体风格研究史上,首次提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的对应系统。这种以“刚”、“柔”来提携八体(八格),开辟了汉语语体风格论的先河。自此以降,阳刚、阴柔就一直作为元范畴主导着汉语风格论的运行。洎清姚鼐,又将阳刚、阴柔对立互补体系,进一步发展为阴阳对转。姚氏(1985)认为绝不能“一有一绝无”,在阳刚阴柔对立两端之间,“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
刘勰所开创的阴阳、刚柔对立系统,在现代体系里继承和光大的是陈望道先生,陈氏在其《修辞学发凡》(大江书铺,1932)中,提出了四组八格(体):简约/繁丰、刚健/柔婉、平淡/绚烂、严谨/疏放。继望老之后,王之望在《文学风格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里确定五组十格,张德明在《语言风格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中提出八组十六格,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里立八组十六格,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中提出七组十四格,李心峰在其主编的《艺术类型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里分为六类十二格,郑荣馨在《语言表现风格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中计分为八组十六格,黎运汉在《汉语风格学》里提出了五组十格,周振甫在《文学风格例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提出了十一组二十二格。以此模式为理论者,还有郑颐寿、王焕运等。上述十一家体系,大都是在《文心》和《发凡》的基础上所作的增补。从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迄今为止的汉语风格论,在范畴的归类抽象中,无论是单项式还是复合式,都沿着刘勰四组八格的路走下来,遵循着阴阳对立互补的原则,从没出现过大的偏离。这一情势说明,《易》的哲学精髓,已经渗透于汉语风格论体系的内核,成为汉语风格论成长、发展的基石。
第二,汉语风格范畴的提取方式和存在状态,从古自今,表述方式有别,但对其存在状态的整体把握的原则未变。西方风格范畴的提取多基于模仿论,如日神精神、酒神精神、悲剧性、喜剧性、崇高、狂欢、古典型、浪漫型、感伤、怪诞、滑稽、诙谐、复调、象征、多声部等等,种类之多并不少于汉语。应该说汉语的风格范畴产生于主体内在体验,是一种评价式的抽象,这种基于直觉式的评断,与具体的审视对象的形态结构具有高度的同构性。而西语的风格论,则是基于对客体的理性判别和科学认知的客观描述,前者重在潜在力的暗示,后者则重在对客体的再现。虽然西语也有感悟式的表述,然远逊于汉语。
第三,上述所列的范畴体系,虽然存在着量上的差别,却都未离开《文心》路径,所列的共有范畴,在处理对立双方的转化,无论从理论上的认识,或是实践上的操作,都远未达到姚鼐的高度。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范畴类型的多少,而在于把握汉语风格论范畴的精髓。这就是:对立、互补、对转。找准对立双方,就有了体系运作的轴心;把握对立互补,就掌握了运行的能源;了解对转机制,就能够洞悉“品次亿万”的生成之源。
4.以象表义的阐释手段
汉语异于西语的第四点是,在对风格内涵的阐释上,与西方风格论的那种语言分析和逻辑推演相左,而是凭借主体的内在直觉,展示出特定范畴的模态。其所使用的基本表达方式是凭借隐喻性的描摹,来展示特定风格的体貌,所表述不是“是什么”,而是“象什么”。深谙“立象以尽义,系辞以尽言”三昧的是晚唐司空图,司空氏所确立的不仅是诗的品格,而是为汉语的古典风格论确立了体系性的构架。以实喻虚,以形摹神的表述方式,是《二十四诗品》在消化魏晋以来风格论精华的基础上熔炼出来。它发展了刘勰、钟嵘风格论的思想,进而以其超人的睿智和才华,集具象临摹风格形态之大成,臻为一种力主心灵感悟的审美体系。
以象表义的本质是隐喻。先民的原初思维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能是以自身为参照系对周围事物予以模仿或临摹。这种临摹的原始性体现在其认知过程对时空的绝对的依赖上,随着人类意识的发展,进而跨越到脱离时空的限定,推演到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直至达到符号化的程度,这就是隐喻的生成、发育、成长的过程。隐喻在语用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束定芳(2000)归纳为修辞、语言学、诗歌、认知、社会功能等五种功能。我们认为认知功能是隐喻的本质功能,因为任何一种功能的实现,都必须以认知为先导,才能得以实施。隐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话语策略,是人们在交际中为了解脱语言的“空缺和贫困”而采用的一种措施和手段,以便破解那些已活跃于思维里难以言状的东西。隐喻的过程就是通过对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征的比较,去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已知事物的某些特征去表达暂时还难以表达的概念。汉语传统风格范畴发展的历史也反复证明,我们的先人正是透过直觉经验所获取的物质图式,去构组起另一个新的图式,借以谈论内心感受的精神现象,从而达到把握和拥有未知领域的极终目标。这种具体的、形象的、物质的感受,并非完全是人类认知的原初形式,而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普遍规律,正是经过这一过程,才能够过渡到理性的境界,才可把不可知变为可知,从而使我们得以获取一个新生的概念结构。
一种语言采用何种话语方式来表现风格形态,是由这种语言结构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英人理查德兹在为李安宅的《意义学尝试集》(1933)作序时,从语义哲学的角度,阐释了话语方式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结构影响着使用该语言的社群的思想。中国的语言结构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其影响方式和内容当然异于西洋各语言之于西洋思想的。理查德兹的思想,与德国的洪堡特和美国的萨丕尔的理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为当今的话语研究,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依据我们的研究,汉语的无数事实都证明了哲人思想的睿智与深邃。
汉语之所以为汉语,不仅其静态体系异于西语,更重要的是其比类取象、以象喻义的运作机制突显于西语。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譬喻的论述不胜枚举。汉语之所以以象表义,是其先天的本性所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象喻同生共存。喻是汉语得以生存、发展的生命源,是其自身存在的根基,取消了象喻,就等于消解了汉语。北齐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文章篇》云:“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这是以象缀文的典范,从写作过程到文章的内容、形式及风格形态,都用象喻展示出来。汉语风格论发轫初始,就以象喻为体。曹丕《典论·论文》倡文气“清浊”,陆机《文赋》欲尽“辞达理举”之妙;逮至《文心》综成八体,经钟嵘到司空图,以象喻表述为宗的汉语风格论臻于定型。时至今日,任何谈论汉语风格的著述,离开了司空图所熔炼的“品”,就寸步难行。所以说,通过象喻来描述风格的范畴特征,既非异常,亦非“原始的印象式描述”,而是最正常不过的与生俱来的表达方式,这也正是汉语风格阐释异于西语风格表述的缘由所在。可见,观察一种语言的言语风格,离开了其存在的母体,则必定是水中捞月。既然汉语的风格范畴是通过象喻构建起来的,而要破解个中的奥妙,则非从象喻进入不可,只此一路,别无它径。中国古典风格论为什么长于以具体的物象和比喻来描摹抽象的理性概念,我想根源就在于此。
四、汉语语体风格论体系的构想
1.语体与风格的共生性
汉语语体风格论体系的构建,处理好语体与风格的关系,是关键性的环节,具有本体论意义。风格与语体既非同质异称因而可同义互换,也不是各自纯然独立的概念;而是相互关联,且各自又拥有殊异于对方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风格与语体比较,风格突显的是个体性,这种个体性特征不仅在语篇之间、表达个体之间显现着,甚至同一语篇主体在不同时空中的表达,都会存在着差异。但任何个体都是群体中的个体,都无法摆脱群体、公共的的约束。这就决定了任何风格,不管其个体特征如何鲜明,都无不深深地凝聚着历史、公共的印记,任何风格都是群体中的个体。而语体所突显的是社会性,任何一种语体,都是对具有共同特征的具体的、个别的语篇类的概括,是一种类型的抽象。而正是这种类的抽象,使其得以摆脱个体的主观羁勒,而臻为代表着特定语言的客观、群体面貌区别于其它语言的语体。语体具有可预测、可验证、可重复的物质性特征,而风格则是透过语体的物质性语言形态显现出来,由此也就决定了二者同生共现的天然性。从二者的依存关系中,我们可以感悟到,语体与风格属于语篇形态的两个不同层次,语体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现实可把握的语言实体和由语言实体所构成的叙述结构,而风格则是隐附在语体之上,借助于语体的物质标记得以显现。可见,风格对语体的伴随是绝对的,是人类语言运用中的普遍原则。言语行为中,不存在没有风格附着的语体结构,也不存在离开语体结构的风格,语体是第一性,风格是第二性,二者的紧密程度,是表与里、骨与肉的关系。
2.语体成分的决定作用
一种语体区别于另一种语体,起决定作用的是其构成成分。语体的构成成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性成分,一类是言语性成分。
语言性成分即由静态语言体系所提供的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等;言语性成分是语言被运用时,出现和发生的语言变异现象,这种变异可以小到一个词,大到句群、段落或篇章。言语性成分与语言性成分的根本区别是,言语成分必须凭借特定功能域作为存在的根基,是动态性的成分,随境而入,因域而变。言语性成分的提取,着眼于对语篇或话语整体,从形式和意义总体倾向上进行考察,进而概括出相关的语言成分。我们这里提炼出六大言语成分,即:体目标记、体脉结构、体材性质、韵律模型、表达方式和风格形态。(丁金国2009)
1)体目标记 体目标记是语体的“眼睛”,因此称为“体目”。体目与常识中的标题有联系,但不完全一致,因为有的语篇没有标题,所以标题作为语体构成成分的一个共有范畴,其概括力差,故我们弃标题而另立“体目”。
2)体脉结构 语体运行中体现秩序、和谐和平衡法则的是其体脉结构。体脉结构伴随着语体的定型而臻于规律化和规范化,自然是历时积淀的产物。不同的语体有着不同的构成成分和不同的结构方式,由此也就决定了语体体脉结构的多样性和各自的变化规律。体脉结构对于任何语体来讲,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封闭系统,是处在变化中相对稳定的状态。由于语体性质的差异,其稳定性也不同。
3)体材性质 体材不同于体裁,体裁是语篇的体式或格式。体材与题材、话题相关,就是指各种类型语体中所共含的质料而言。体材包括进入语体的人物、事件、场景、例证、数据,甚至图表、影像资料等。体材性质不同,常常引起语体性质的改变,二者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不同的语体对体材的容纳,具有类型上的选择和程度上的差别。
4)韵律模型 语篇运行其内为体脉结构所统摄,其外则表现于音律节奏。音律节奏在语用中类型化的结果,由韵律模型得以显现。可见韵律模型不是单纯的诗韵、格律,而是指语篇中的声、韵、调在语流中所形成的周期性变化的普遍规律。各种不同的韵律,在不同的语篇中表现各异,其存缺与分布关系,决定着语篇的韵律变化周期,因而形成不同的韵律模型。
5)表达方式 表达方式是语用者依据意念与质料性质对表述的选择。表达方式是语体普遍的构成要素之一,这是因为任何语篇都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行文说事所使然。由于言语交际中功能域的制约,因而使得交际语篇的表达方式自然也就各自有别。人们在长期的交际实践中,提炼出与语体性质相适应的表达方式为叙述、说明、论证、描写、抒情、对话等六种。语用中常是以一种为主,其它辅之。
6)风格形态 语体与风格的依存关系,我们已多次论述过,实际上语体与风格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一对一的对应,而是“一对多”或“多对一”。“一对多”指的是一种语体可容纳多种风格的语用事实而言,“多对一”是指不同的语体可以共显同一种风格形态的现象而言。
3.高低语体的对立机制
纵观语言运用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有序的社会,其社会语文形态中,始终存在着高雅语体与低俗语体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调节着言语社群的语言运用,而且也是语言发展演变的动力。我们认为在高低对立的双方之间,绝非是一空白地带,而是一个极为广阔、存在着形形色色、介于高低之间的中间语体带。这个中间带是个难以在量上进行精确提取的层次,是不可穷尽的区域,其上与高雅体构成对立,其下与俚俗体构成对立。这就意味着,同一语体内部,其雅俗度不是单一的,而存在着不同语用层次的级差。同一语体内部所存在的等级差,实际上是其雅俗度的差。
在一个有序的言语社群里,高低语体的级差对立,通常是处在相对稳定的形态,人们在交际时,都会“各就各位”,一般不会发生级差对立。然级差对立却又无时不在运动着,一般规律是低者尽量“高攀”,而高者为了某种需要,有时也有意识地“就低”(此为合作原则或礼貌原则所使然)。于是开始了量上微变的累积过程,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质变,产生高低语体的置换。“对立的双方就可以成为两个相互补充的源泉,向语言供输力量并确保语言的纯洁性。”(洪堡特2004:199)清人姚鼐(1985)在纵论语体风格的阳刚、阴柔时,认为在对立的两端之间,“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阴阳刚柔相生相济的结果,或向心演进,或离心对反,于是发生阴阳对转。阴阳对转应该说是一条很重要的语体演进规律,是语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4.实证性的微分析
现代语体风格论的现代性,笔者认为是:在理论上,以语义为核心的结构原则必须进入体系之中;在具体操作上,构成成分的离析和量化微分析当是重要的实证性手段。当然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汉语语体风格论传统的基础之上。
微分析的本质是形式分析,是将语体的形式结构,由高到低逐次进行微观的量化处理。其操作程序,首先是确定语体的结构类型,然后再对特定的类型逐次地进行语体标记提取。运用语料库技术对语体风格进行微处理,是基于真实、宏观、大数量的语言事实,搜索语言运用中语体的各种特征和标记,以概率统计为手段,辨析各种语体间的共同点和区别点。建库的关键是设计出一套足以覆盖特定语言系统的主要语体、可供计算机运算的语体标记体系,而且便于标注赋码。
为保证所提标记的信度和效度,我们认为在具体操作中,应遵循如下的原则:共时性、普遍性和层次性。共时性原则是就提取的语体标记所涵盖的时间跨度而言,必须把研究的目标锁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普遍性即代表性。对于语体标记的提取来讲,所提标记能否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关键在于所提标记在各类语体中的覆盖面,覆盖面大其解释力则大,覆盖面低则解释力必然小。层次性是就语体标记的内部体系而言,因为处在同一个体系中的各个单位,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严整有序的聚合。语体标记体系(汉语语体知识集)中的各个成分,不是处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是处在上下位关系中,每个上位层面,统辖着不同的下位层;而一个下位层面,又是后一个下位层面的上位层面。如此层层隶属,组成了一个有序的隶辖系统。在对语体标记的提取或构拟时,必须在分清主次、理顺层次的基础上,逐次进行。
五、结 语
汉语语体风格研究,新世纪以来出现一种倾向:试图避开语篇的风格,专注于话语的形式结构,以纯“语言学方法”取代行之有效的传统阐释,把风格排除在语体研究之外。殊不知语体与风格相关联恰是汉语语体风格论的主要特征,权衡一种学术的价值,尤其是对于人文性极强的语体风格学来讲,并不在于其现代“新”的含量,首先要虑及到汉语的特质,因为语体风格学是一门实用性、人文性极强的学问,离开了言语实践(尤其是语文教育),则毫无意义可言。汉语语法学被淡化或排除在义务教育的语文体系之外,就是很好的教训。走到这般境地,与其源自西语的语法体系,无法运用于汉语实践密切相关。对汉语的语体风格研究,如果仍照抄受制于结构规则制约的西语语体学,其发展前景也确乎令人担忧。从汉语语体风格论的特异性可看出,汉语异于西语的最显着特征是:论者始终把语体与风格关系,视作唇与齿,骨与肉的关系。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者的陈望道先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一直热望有“自己的样子”的语体风格论。“自己的样子”不仅是望老的理想追求,对我们也是一种警示!
注 释
①“语类结构潜势”理论最早是由哈桑(Hasan)提出的,后经毛翰(Mahan)和婉托拉(Ventola)等人的修正,在中国经由张德禄等的阐发,使其臻于完善。该理论认为语类与语境之间存在着配置关系,语类本身限定了语篇语义的大致范围。语篇的结构不是语法结构,而是一种语义结构,这种结构控制着语篇的结构运行。
②与黎运汉《汉语风格学》理论框架相似的有程祥徽(1985)、张德明(1989)、黎运汉(1990)、郑远汉(1990/1998)、王焕运(1993)等,与王德春《语体学》理论框架相似的有王德春(1987)、袁晖和李熙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