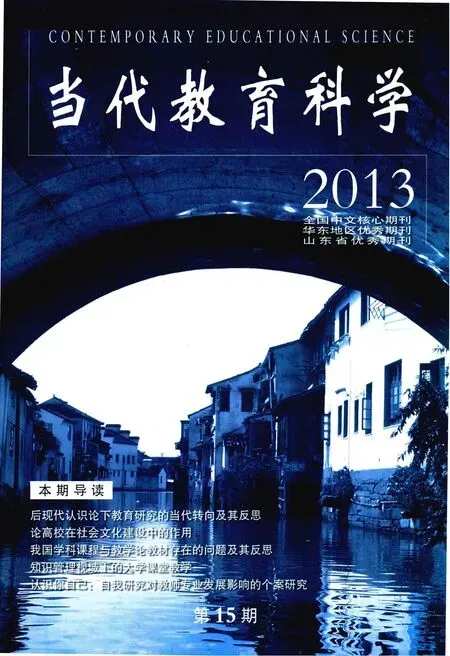试论“广义狭义式”德育概念界定的逻辑纰漏
●孙 玲 唐爱民
一
众所周知,在迄今为止的德育理论研究中,对于德育概念的界定,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都相当宽泛,所涉指的范畴高度发散,几乎侵占了所有有关的社会科学领地。概念泛化,边界模糊,内容驳杂,专业色彩淡薄,已司空见惯且危机德育学的学科生存与地位。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针对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庞杂、多元现象所引发的感触:“研究对象的漫无边际,研究视角的多种多样,使得这个学术群体缺乏一种总体上的学术认同感,同行之间没有同行的感觉。”[1]德育的确是一个涵义广泛、复杂的概念,但它绝不意味着任何事情,它有自身的内涵、价值范围和学科界限。德育理论由于对德育概念采取广狭式的模糊处理的态度,已使这一概念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德育所意指的内容已日趋多元,德育概念也正趋于多元论的理解中。“但多元论的观点很不确切,因为它既可以很好地适用于交叉着不同观点的有条理的对话,也可适用于杂乱碎片的不和谐的杂烩。我们怀疑——此刻我们所有的只有怀疑——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这种杂烩。”[2]过于宽泛的德育概念,必将流于对德育本质的肤浅把握,所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虚实篇》)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此早有断语:“德性是多样的,即使一个人试图集中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德性,但如果每一种德性都至少得到部分开发的话,那么把精力分散到如此广阔的领域,则必然会损害这一事业。”[3]德育概念因缺乏统一的可以明确说明的界定,而日益成为一种内涵模糊、外延扩展的词汇,成为一种“尊称”(奥康纳语)。
在一般的教育学著作和德育学著述中,提到德育,通常将其复杂的内涵作简单化的理解划分:广义的德育与狭义的德育。广义的德育,按几成共识的表述,就是把一切影响受教育者思想品质、政治品质、道德品质、心理品质和法制意识的活动通称为德育。“目前人们普遍把德育理解成包含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的一个广义的德育概念。”“德育,在我国已约定成俗为广义的大德育概念。”[4]问题是,这种“约定成俗”给德育理论带来了混乱,对德育实践的成效留下了隐患。这样的划定在概念的外延上作了开放式处理,德育的边界意识极为模糊;而在最广义的理解上,还把上述一切影响,不管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系统的还是无目的的、无计划的、零碎的影响统统称之为“广义的德育”。狭义的德育则专指道德品质教育,即只对受教育者道德品质产生影响的教育活动。这样的划定司空见惯。然而,这种广狭式处理,除了造成德育概念的进一步纷杂而外,并未解决德育本质涵义这一根本问题。德育理论的“自我意识”与学术规范盖因这种偷闲的、简单化的做法而几度弱化。我们体会,广狭式定义,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存在着难以言明的逻辑问题与现实危害。
二
德育概念的广狭式界定,至少存在如下五个方面的漏洞或危害。
首先,将德育作为一种广义的泛指,其概括力和一般性是相当有限的。因为,既然是广义的泛指,就给德育概念的开放式理解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为给德育添加更多的成份留下了口实。故而,德育的范围日益扩大,关涉领域日益庞杂,除却思想、政治、道德、法制、心理品质的教育而外,礼仪、劳动、军事等教育也悄悄并入德育的范围,而全然不顾道德品质教育与诸如此类的教育之实质区别。如此,德育理论不伦不类,德育实践难负其重,德育成效难遂人愿。广义的界定实在后患无穷。如有学者从德育哲学的角度,将德育所涵盖的内容泛分为政治、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教育(涵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和民主法制、情感情操、意志品质、审美意识、心理健康教育等等,并断言:这种认定“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随着德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德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5]且不说,这种巨细无遗、无所不包的德育将相互重叠和明显不属于德育的范畴硬扯进德育的归属中,是否会使德育走向“本真和深邃”(相反,走向的是混乱和肤浅);单从学科发展的逻辑变化看,学科的交叉互摄及德育含量的增加与德育社会化趋势,不应是以淡化德育的边界意识、模糊德育的固有范围为前提的;如果只是囿于泛泛的罗列,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流于空泛,疏于精密,乏于规范,甚至可能冒着窒息德育的生命、危及德育学的学科生存的危险,到头来,德育的研究仍难跳出人云亦云的泥淖,这种代价难以承受。
其次,与广义界定相对应,将德育作为一种狭义的特指,按说该切中了德育本质的要害,然因这是以广义界定为逻辑前提的必然引申,故也存在致命的硬伤:它依附于广义的界定,从属于广义的理解,不仅难以显示概念的统摄性与概念的规范性,而且也仅具理论描述意义。此外,尽人皆知的是,以狭义的界定为指称的陈述,除了“为概念而概念”之外,并无一贯的使用原则与打算,当关涉到德育理论的具体运用与分析时,先期的狭义界定又自觉不自觉地“广义化”了,狭义的理解仅成了某种点缀或虚饰。或者,相反的是,在概念界定时用广义狭义并列描述,可到了具体论述时不是变成了单一的广义,就是变成了单一的狭义。概念的使用缺乏彻底性。如在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中,论者认为德育之德乃指个体品德,“指人的个性品质中的德性,狭义指个体的道德品质,广义指‘思想品质’,包括思想品质、政治品质、道德品质。”[6]按此理解,德育自然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也即广义的德育。可是,在后续论证时,又认为“德育即育‘德’,德即德性或品德。”[7]如此,德育又成了狭义的指称,而在对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课程、德育方法进行论述时,则又是以广义德育为立论前提的。概念的内涵时大时小,全凭主观需要;转换之唐突,逻辑之混乱,十分明显。在另一本有影响的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在论及德育概念时,论者指出:“德育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对受教育者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影响,通过受教育者积极的认识、体验、身体力行,以形成他们的品德和自我修养能力的教育活动。”紧接着,论者以特有的语气着重指出:教育学上的德育与伦理学范畴的道德不同,它“是相对于智育和美育来划分的,它的范围广,包括培育学生一定的思想品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8]该定义的特色是,将品德形成的机制以抽象简约的形式反映在德育概念中,是很有创新的。然而,我们体会,该概念仍然在逻辑前提、外延边界上回到了传统的广狭式界定上,对品德形成机制的出色论述因立论前提的罅漏而不能为人全部接受。在表述完概念之后,论者话锋一转:“简而言之,德育就是教师有目的地培育学生品德的活动。”这与先前框定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影响”显然是不对称的,有抵牾的。在最好的理解上,至多是将思想、政治、道德影响视为提高学生品德的制约因素。而问题是:思想、政治、道德影响与品德是单向制约还是互为制衡?它们之间是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还是平行并列的关系? 道德影响与品德活动如何转换?这不能不使人产生疑虑。在“简而言之”之后,论者又回到了传统德育概念界定的老路上:“道德教育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道德教育,是指伦理学上的,即道德品质教育;广义的道德教育,则是指教育学上的德育,道德品质教育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9]这样迅速的摆动,使人缺乏思想准备,也让人摸不出头绪,存在着明显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矛盾。其实,这种窘境非此独有,而是非常普遍地存在的。显然,这种处理方式也存在诸多隐患。
再次,广狭式界定既不符合“内在的完备”,也基本未有“外在的证实”。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一种理论、一种概念指称,若要成为科学的,须符合两个标准:内在的完备和外在的证实。“内在的完备”指逻辑上的严密证明;“外在的证实”指经验的检验或证明。德育概念的广狭式界定在这两个方面均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说明。美国基督教伦理学家弗莱彻(Josph Fletcher)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道德探索中通常要遵循两条推理规则。一是‘内在一致性’规则,任何人对此均无异议——一个判断不应自相矛盾。另一个规则是‘外在一致性’(类推法)即在一种情况下适用的原则应当适用于一切类似情况。”[10]由此关照广狭式德育概念,便可明显觉察到,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界定在广义上存在继续添加成份的空间,在狭义上因论述中经常的前后不一而不能适用于一切情况,无论是在概念的内在规定性还是外在使用范围上均缺乏必要的一致性。
复次,广狭式处理因未能把握德育概念的本质,故对德育理论建设和实践运行带来了不少麻烦。正如法国哲学家居友(M.J.Guyau)所言:“纯科学的道德学不应当自命包罗万象,它并不需要扩大其统辖范围,而应当努力去解决自己份内的问题。”[11]广狭式处理,将会使德育理论的进展继续裹足不前,在不明了自己对象领域的情况下继续糊里糊涂地绕圈子,甚至连本应是份内的职责也因“广义”处置而一推了之。其实,在教育学界,已经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德育概念的广狭式处置所必然带来的理论上的前后冲突、自相矛盾和实践上的各行其是、无所适从。桑新民教授就曾专门指出:“什么是德育? 当前最流行的说法是:德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德育指道德品质教育,广义的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这种流行的德育观在理论上缺乏严格的依据与界说,尤其是没有正确揭示德育的实质及其与智育的区别与联系,在实践上则将德育与智育既混淆起来,又割裂开来,使德育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造成学生严重的逆反心理。”[12]这种认识是很深刻的。
最后,如前所述,广义的界定,把或然当作盖然,把个别视为一般,把偶然视为必然,把特殊的经验事实赋予本质的普遍意义,把联系放大至包容或并行的关系,犯了逻辑推演的常识性错误。广义的界定,实质上回答的是“什么是德育”的问题,即将现象、个别、属性视为德育的本质,至多是在现象、个别、属性之于德育的相互关系上把握德育内涵;而德育概念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德育是什么”,即从本质、一般、普遍意义上理解德育的内涵。也就是说,德育概念所关注的不是一种归属性判断,而是一种本质界定;不是一种现象描述,而是一种本质抽象。广义的界定不能做到这一点;它有取消德育的危险倾向。若继续容忍这种表述,必定给作为一个学科的德育学带来更严重的损害。
三
总而言之,对德育概念的广狭式解决方案,潜存着诸多难以圆说的困境。在理论上,广义的多元式界定以道德教育的分析来代替其他教育成份,逻辑漏洞颇大;在理论之于实践的影响上,狭义的界说又多以广义成份取代,实行的是诸育并施的策略,理论的规定成了多余的累赘。理论言语所否定的东西,在实践上却予以默认。这是不能达到德育理论所标榜的价值与目的的,德育学于是进而成了无关大碍的虚饰。的确,德育概念的多元规定与泛德育概念的流行已习以为常了。然习以为常并非真知,以习以为常为由便不去分析、研究它的本来面目,那是会阻碍我们达到真正的认识的。因此,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指出的,必须“扬弃那些固定的思想从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的东西”。[13]一如居友的思考:“当今的道德认识到,要它预先绝对控制全部人类生活,是有些勉为其难了。”[14]德育学必须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德育的本质,以免承担难以承担的任务,从而杜绝将理论研究变为“普遍闲谈”的倾向。由此,探索德育以一贯之的符合逻辑与学术要求的本体涵义,使德育学的理论建设从而使德育实践操作完善起来,便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那么,如何化解德育概念的广义狭义式界定所带来的问题与危害呢? 这需要诉诸德育本体论视野。我们以为,所谓德育乃是教育者依据教育对象品德生成的规律,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教育对象的品德并引导其外化为道德实践,以实现道德人格建构和道德境界提升的教育活动。质言之,就是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的教育。这种理解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狭义的德育”,而是——德育就是培育学生道德品质的教育。
[1][美]托马斯·库恩.金吾伦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总序.
[2][美]A.麦金太尔.龚群等译.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0.
[3][德]爱弥尔·涂尔干.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3.
[4]朱小蔓.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5.
[5]张澍军.德育哲学引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7.
[6][7]班华.现代德育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9,25.
[8][9]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330.
[10][美]约瑟夫·弗莱彻.程立显译.境遇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2.
[11][14][法]居友.余涌译.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9,138.
[12]桑新民,陈建翔.教育哲学对话[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53.
[13]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