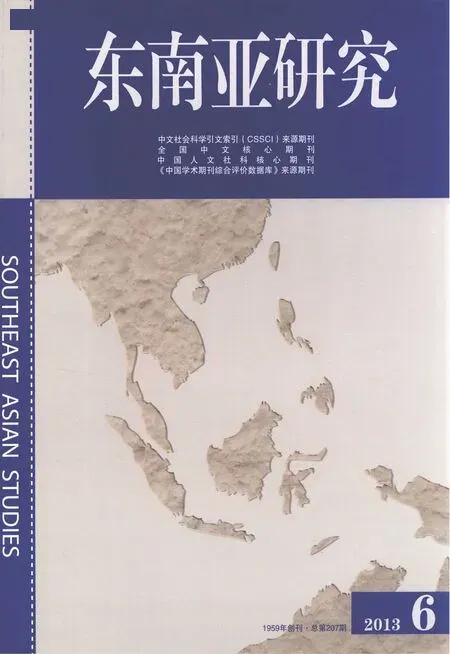会看户户诵雄文,价重蓬山求络绎*——纪念朱杰勤教授诞生一百周年
高伟浓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510630)
一 黄卷青灯忆髫龄:家教与学养
朱杰勤教授祖籍顺德,整整一个世纪前降生在广州一个华侨家庭。从一个“负不羁之才”的天分少年,成长为一个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大学者,冥冥中似乎早已昭示世人,他在逝世23年后成为广东“世纪学人”绝非偶然。
朱先生学术领域广博,毕生治学勤谨,笔耕不辍,著述丰硕,誉满学林。在其数十年的砚墨生涯中,著、译学术专著达20 余部,校订、主编书刊11 种,发表论文120 余篇,并曾担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中国编审委员会委员等多个社会职务。
朱先生前半生遭逢世变,家国多灾,转徙流离,学路殊艰,但一自步入黉门,便对学术矻矻以求,未尝废歇。要了解这位大学者的人生轨迹,有必要对他早年的成才之路做一简单疏理。不过,单靠现在稀少而散乱的资料,只能描绘出一幅他少年受教的蒙胧画面。
客观地说,少年杰勤所接受的,是普通的“家教”,而没有诗书礼乐之家拥有的显赫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朱少学是马来亚归侨,“读书不多,粗通文理,赋性慷慨,志大才疏”。回国后,在广州一家商店做雇员,收入微薄,仅供一家四口衣食,不过其思想甚是开明。朱先生后来回忆说, “家父少学先生早岁漫游南洋群岛,年近古稀,豪情如昔。”朱父交游广博,所结交的人中,名流不少,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康有为。笔者猜测,其与康氏的交往应只是一面之缘。不过,以康有为好为人师的禀性,很可能对朱父多有嘉勉。而对朱父来说,即使是一面之缘,也肯定使他益发滋长望子成龙的渴盼。
对少年杰勤来说,经商的父亲只是他的经济保护伞。但有三个人对他后来的成才作用至巨。一个是他母亲,一个是他伯父,还有一个则是他的业师罗隰甫。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母亲的角色早有定位:相夫时做贤妻,教子时做良母。朱母识字无多,督责儿辈读书上进,便是她与生俱来的最大责任。她对少年杰勤管教甚严,诫之勤奋读书,不贪便宜,不说谎话。朱先生终生治学不辍,待人礼让有加,处事耿直知性,与母亲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伯父曾经参加过科举,但落第了,那时杰勤还未降生。晚清的朱家,跟几乎所有的中国家庭一样,崇尚读书为仕。杰勤出生之年,已是民国第二个年头。时代虽已更替,但社会仍受传统浸染。科举不第的伯父对侄子进行系统的启蒙教育,给他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厚实根基。从伯父那里,少年杰勤习读过《三字经》、《千字文》、《成语考》、《唐诗三百首》。平心而论,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对传统经典的习诵,可锻铸人格,陶冶性情,让人终生受益。少年杰勤聪颖过人,记忆力好,文献理解能力惊人,更使他如虎添翼。
罗隰甫传授给少年杰勤的传统经典,已非那些少年启蒙之牍,而是《四书》、 《史记》、 《离骚》等高深层面的典籍。罗隰甫出身不凡,是张之洞创办的两广方言学堂出身的高材生,国学功深,教学有方。他对学生态度严峻,常常“扑作教刑”。笔者每每听到晚年的朱先生对业师赞颂有加,话语里充满着感恩与怀念。每有新生到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罗老师的故事。不过,少年杰勤并没得到“扑作教刑”的“待遇”。罗老师对他倒是一反常态的和蔼可亲。因为老师发现,杰勤读书虽不求甚解,但作文却是一次比一次长进,往往举一知三,触类旁通,孺子可教也。显然,是罗老师让他积垫了厚实的国文基础。
由是笔者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先生后来对自己学生的语文要求,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一般人不把遣词造句当回事,但朱先生将之看成是做学问的基础。针对时人文句不通的现象,他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要他做个中学语文教师,还是合格的。或许他已经看到了年轻学人基本功的欠缺,看到了现代教育的弊端: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来,几乎没有一刻时间属于自己,人成了机器,脑库里虽塞得满满,但知识堆放杂乱无章,人文类知识更是少得可怜。
朱先生的国文根基集中表现在他对古代音韵格律的精通。他的诗作常常独出心裁,其造诣之深,直追古人,且格律对仗,极是娴熟,平仄粘合,亦甚考究。若说韵脚,时以平声,时以仄声,均甚自如。他的诗作的一大特色是喜用入声韵,铿锵有力。朱先生留下两本诗集,一本是《微雨集》,另一本是《英诗采译》。前者用典准确精巧,对仗工整,遣词用韵堪称珠圆玉润,意蕴深厚;后者是英文古诗的译集,多采用中国古风体,读来了无“洋味”,恍如以中国古文直书而成。先生国文功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这两本诗集都是朱先生早年的作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中晚年却没发现有新的诗作问世,不能不让人深感惋惜。
朱先生的另一个优势是有机会接受了良好的英文语言教育。1927年,他转入一间私立英文学校。他学习英文跟学习国文一样游刃有余,三年之后,就已会写能译。实事求是地说,他的英文口语确实不好,口音极重,但他的翻译能力惊人,且对翻译有自己的一套专门论述。他信奉信、达、雅原则,主张以直译为主。有云,一个人的中英文水平往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从朱先生身上可得到印证。
约在英文学校毕业前后,朱家迭遭家变。先是其父经商失利,借贷度日。随之,母染沉疴,长年卧床。两弟又双双遽遇不幸,相继离世。先生时年十七,不得已辍学回家,在商店充杂役,但并未因此而弃学。工余,他就学于商务印书馆的函授学校,相继完成了中文、英文、数学、商科等专业课程,但他专趣于文史,常以零用钱上街沽书。然而,直到斯时,有超强读书天赋的朱杰勤还丝毫没有成为学者的奢望。他读书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找到一份维持家计的固定收入罢了。
晚年的朱先生每自提到陶渊明,倒不是因为好菊,而是喜欢他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朱先生常说,当年他对书无所不读,“与专业无关的杂书不知读了多少”。当代学者多喜欢走学问专精之路,一开始就“深挖洞”,却不屑于横向拓展。往往又文史分家,其专业与爱好非文即史,非史即文。朱先生显然不喜欢走这样的治学之路。他主张博通广识,而后由博返约。王国维有语曰“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朱先生将之作为治学方法,倍加推崇。因是,他的学问淹贯宏通,经史子集,每能兼融,又能诗能文,能著能译,大师风范,殊属名至实归。
1933年,朱杰勤的弱冠之年,也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和分水岭,他从非学术之野,踏入了学术的殿堂。这一年夏天,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招收史学研究生。朱先生自知非科班出身,更无本科学历,仍欲呈勇一试。好在研究生并非一定从本科生中招录,非本科生只要有专门著述,送审合格便可报考。朱杰勤的聪颖敏达这时派上了用场。他只花了半个月时间,便写下了《中国史学研究》一稿,洋洋洒洒8 万余字。主考官,也就是他后来的导师、章太炎的大弟子、著名南明史专家朱希祖批阅他的卷子时,点头赞许不已,感叹此乃可造之才,遂将其破格录取。其时失业失学的朱杰勤,就这样步入了大学的殿堂。天降大任于斯人矣。自此之后,他终生与学术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晚年的朱先生常回忆当年的入学经历。他谦称自己不过是个门外汉,却时来运转,走进黉门。他终生不忘朱希祖的知遇之恩。希祖逝世时,朱杰勤曾留下挽诗五首,其中一首云:“躐等贻讥我自知,差强人意是文辞。点头顿起怜才念,犹记沉吟阅卷时。”师徒之情深,跃然纸上。
步入大学殿堂之后,他在恩师指点下系统读史,每天循序点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勤奋不辍,深得传统历史学的严谨之功。但他文笔恣肆,意气纵横,又深谙大学者高屋建瓴之道,乃至日后数十年间,他酣游史海,饱览群籍,融通文史,学贯中西,著述等身,殊非偶然。尽管人生跌宕,他仍白昼提灯,矻矻以求,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累积跬步,终至千里。他用力之“勤”,成就之“杰”,同辈难以比肩。193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之后,得著名画家高剑父介绍,到广州美术学校讲授国画史。1937年夏,应中山大学之聘,回母校任教,主讲中国艺术史。
人生多有不幸事。1937年抗战爆发后,广州、香港相继沦陷,他的手稿、藏书、衣物俱付诸一炬。母亲也在颠沛流离中因病情加重而亡故。家仇国恨,使他走出书斋,为日后他的人生经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但“昔年种柳,摇落江沧”,先生家计本已窘迫,此时更是雪上加霜。1940年开始,他不得已辗转流迁。先是取道越南抵昆明,任职于云南中山大学(广州沦陷后迁此),后任职昆明巫家坝空军军官学校(任编译)。1942年,转入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侨委会在重庆合办的南洋研究所,任史地研究员兼主任。1943年到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任教,任印度史和泰缅史教授。1945年,应熊庆来校长之邀,到云南大学讲授世界古代史。1950年,调入云南军区司令部,在参议室主持东南亚研究工作。直到1952年,身穿军服、鬓有微霜的他,方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中山大学,开始了崭新的学术旅程。到1958年,方调入在广州重建的暨南大学,任历史系主任。 “文革”开始后,暨南大学被迫停办,朱先生先后到华南师范学院 (今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工作。1978年暨大复校后,才又回到暨大,主持历史系的工作。
早年人们就曾这样评价过朱先生的作品:“大气磅礴,沙泥俱下,较之屑碎撦挦之考据,有香象草虫之别矣。”笔者认为,这些已成公论的评价,缘因于他的“大器早成”:中大肄业第二年,他便以《秦汉美术史》一书录入日本的《中国名人大辞典》中。之后,撰成《王羲之评传》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 世纪40年代,又著成《龚定庵研究》一书。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传统历史学研究,其实看重的是微观研究。主要特点是,尽最大努力占有资料,包括文献、档案与考古等方面的资料。因之,一个细微的历史事实,往往经过反复考证。很多人只是将历史典籍看成是工具书,需要的时候才去按图索骥地翻检一下,取其所需。虽然人们也说在对史料钻研透彻的基础上进行结论的抽象,但往往只是蜻蜓点水。
朱先生做历史研究,可以说是“皓首穷经”、“韦编三绝”,他在传统历史学研究方面的功力更是炉火纯青。作为一代史学大家,特别是作为受过清代朴学影响的史学大家,朱先生在治史方面无疑深具探赜索隐、发微阐幽的功力。但人们往往忽略了朱先生在治宏观历史方面的“大气”。可以说,今天已无完整地通读二十四史之人,但对朱先生来说,通读完二十四史只是跬步之功。他的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论文,表面看没有多少注释,洋洋洒洒,但却是在通读原著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撰写出来的,蕴含着他对历史的真知灼见和透彻感悟。而在其背后,靠的是学富五车的学养和厚积薄发的底气。见过他的人,不难感受到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的才识。这就是朱先生的“大家风范”。
与朱先生有过交往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赞叹他著书立说方面那些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南方日报》记者李培从当事人那里采访到不少关于朱先生的佚事,兹举两例。
其一,朱先生的学生、中山大学年近九旬高龄的退休教授黄重言(也是笔者的硕士生导师)回忆说,1952年,朱先生在中山大学开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开设)。朱杰勤边述边著,第二年即挥就一本36 万字的讲义,1956年修改出版了《亚洲各国史》,达80 万字以上,内容包括中国周边14 个邻国。行内人都把融为一体地编纂多国历史视为畏途,但这对朱先生来说却是举手之劳。
其二,1958年,朱先生调入暨大。3年后,开设“中国古代史学史”一课,其时无教材,但他在半年内即写成一部30 万言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是解放后出版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论著。这部书,凝聚着他悠悠数十个寒暑中的读史心得。
笔者从旁观察,朱先生对太正规的教育似乎不是太看重。但对自学却有很高的评价,显然,科学的自学可以让人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当代中国有两位国学大师,即“北季南饶”——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和香港大学的饶宗颐。季羡林是朱先生的好朋友,有闪烁的科班教育和留学背景,是正统教育成才的典型;饶宗颐则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他少时即在家读书,十六七岁就读完了家里藏书阁的书,之后一步一步地走向大师之巅。窃以为,朱先生的成才之路,是介于这两位大师之间。
二 当时名士首推公:创举与盛誉
作为国内历史学的名家之一,朱先生的笔墨生涯将近60年,研究领域广及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世界史、亚洲史、东南亚史、美术史、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和华侨史等,当然各各之间多有串通。多少年的耕耘,使他在上述领域颇有建树,占尽风骚,誉满海内外,不少成果得到一些世界著名学者的推崇和引用。早在20 世纪40年代初,日本《中国名人辞典》即已刊载他的专辑。1989年,美国《国际杰出名人录》刊登了他的生平并向他颁发了证书。在晚年,朱先生更创造了学术事业的辉煌。
1978年,因“文化革命”而被取消了12年的暨南大学复校,朱先生迎来了学术生命的另一个高峰。在作为他人生归宿的“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他孜孜不倦,独辟蹊径,一手开创了两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研究,并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国内之风骚,执学科之牛耳,成为暨南大学标志性的学术制高点。在生命的最后数年,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穿行于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研究的学圃中。
平心而论,要在这个学圃中自如穿行并非易事。朱先生说过,研究中外关系史,学科知识面要广,起点高,难度大。研究者既要懂得中国历史,还要懂得相关的外国历史,两方面要能够对接。华侨华人研究也是如此。要开拓这样的学科领域,舍朱先生这样的大家莫属。朱先生造诣深厚,又得益于早年练就的西学功底,他“古籍洋书,并列案头”,每当涉及中西互证,总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曾说过, “作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博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这样才能谈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数十年的学术积垫,使他成为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研究的众望所归的开拓者。
1979年,在中国历史学会规划会议中,他就倡导成立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1981年,他创立了华侨研究所(后改称华侨华人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成立的同类研究机构,在很长时期内也是这个领域的最知名学术机构。
早在20 世纪60年代初期,朱先生就把两种中外关系史名著——德国汉学家夏德的著作《大秦国录》和利奇温著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译成中文。及至80年代,有《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中外关系史译丛》等成果结集出版。
20 世纪80年代,廖承志提出要开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这一重任,当之无愧地落到了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和朱先生身上。华侨华人研究肇始于民国时代,在广东,则以梁启超为标志性人物。可惜1949年以后中断了,改革开放后开始恢复。朱先生是新时期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暨南大学这个领域的奠基者。他的这一贡献,也奠定了暨南大学日后作为国内华侨华人研究重镇的历史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批重要著作。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数年,他投入巨大精力,主编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日本等国的国别华侨史(每个国家均有专人撰稿)。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后,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没有衔接下来,只是到了近年,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国别史的专著才基本完成。国别史是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基础工程,实际上,它的意义在今天更加凸显。
实事求是地说,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曾有越走越窄的趋势。若以二十四史作为基本素材,则其中记载中国与外国、中国与外面民族交往的材料是最少的,再做下去就难免出现粮草短缺现象。愚以为,在这方面,当代学者也要与时俱进,才能不断超越前人。实际上,中外关系史还有很多空地或薄弱地带可以耕耘。比如说,将眼光从国家的层面跳到地方的层面,研究某个省份、某个乡邑的对外交往史,就大有潜力可挖。又比如,可以从外文资料中发掘当地政权、当地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史。就研究的范围来说,中外关系史还可以扩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人文交往。此外,还可以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
朱先生十分重视人文交流方面的历史。这里所说的人文交流,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史、哲那一部分,包括经史子集、礼仪风俗等方面的对外传播。在朱先生的研究中,人文交往占了很大分量。例如,朱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化在境外的传播、对古代中外文人间的交往就很感兴趣,并写有专门的研究文章。
在朱先生的年代,华侨华人研究是以历史研究为主,当时关于华侨出国史的研究是主流。在这方面,首先是对中外文文献、档案的收集和整理。作为开拓者,朱先生当年只是打下了基础。我们今天纪念他在这个领域的业绩,没有必要将他的贡献无限拔高,恣意夸大。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朱先生的治学态度。事实上,到今天,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国际关系学、人口学等等,都被当作可用的学科手段相继引入到华侨华人的研究领域中来。但各种学科方法差异很大,不可能要求一个学者十八般武艺都样样精通。作为今天的华侨华人学者,除了自己专业的学科方法外,还应粗知其他某个或某些学科门类的研究手段。我们今天没有必要把朱先生等学者当年在华侨华人领域的贡献“神圣化”,把他们所提倡的学科手段和研究方法“教条化”和“凝固化”。反过来,今天采用各种学科手段进行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也不应对朱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就和研究方法妄加“矮化”。学科手段与研究方法各有长短,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最重要的是用得其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学科之间、学派之间、学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协同攻关,永远不会过时。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取得共赢,才能把华侨华人研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才是对朱先生所开拓的这一事业的最好继承。同时也应看到,直到今天,华侨华人研究仍然到处是“处女地”,基础研究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试图撇开基础研究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想法是幼稚的,不可取的,从长远来看也是无益于学科发展的。当然,在今天的华侨华人研究中,也应顾及国家需要和学术研究的均衡。
20 世纪80年代,朱先生还把晚年有限的光阴用在人才培养上。自1984年至1988年间,作为一个古稀老人,朱先生指导了两届共七八位博士生,为此他燃尽了心烛。作为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最早通过的博士生导师之一,他招录博士生比较密集,从一侧面反映出他对学科建设后继乏人的焦虑。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多有阐析,这里就不赘述了。
1988年,朱先生应国家教委之约,承诺撰写一部鸿篇巨制—— 《中外关系史》。他珍惜秒阴,废寝忘食,谢绝了大部分国内外会议邀请,忙于著书立说。实际上,这时他已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还出现过数次心绞痛,且腿疾加重,举步乏力,沉疴之状已很明显。但他似乎浑然不觉,日夜案牍劳形,不知倦怠,每周还坚持上课。现在回过头看,朱先生当时的潜意识中是不是隐隐有时日无多之感?在笔者的记忆中,他当时似乎非常反感谈及健康之事。一次,笔者给他带去一幅非常精美的挂历,但因为画上有他认为的“不吉”之语,便婉然谢绝了。笔者感觉到,他所以对自己的健康十分敏感,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精力不济,没法完成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恢宏计划。1990年4月30日,笔者来到朱先生家中,请他写一个项目的推荐信。其时他还谈笑风生,勉励有加,孰料次日即突患心脏病住进医院。即便这样,个性耿介的他也未料到自己已悄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时他被安排挤在6人一间的简陋病房内,与生命做最后的抗争。他不配合医生治疗,拔掉插在身上的注射器,要回家去。9 天后,他在昏迷中溘然长逝,留下了许多未竟的遗愿。他燃尽了自己,却烛照前路,烛照后人。
三 遥想清操一往深:禀性与知交
与朱先生有过交往者,都知道他把自己的住处称做“旷远楼”。一个老旧的镜框,里面一张发黄残破的宣纸,裱着这三个苍劲的仿宋字。其意境不难明白:“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与之闲止。”品位之高尚,气度之辽阔,似淼淼回音,清幽旷远。
子曰,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又曰,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两千多年来,已成为士人信奉的为人法则。因为, “狂者”,必“志极高而行不掩”,敢作敢为;“狷者”,则“知未及而守有余”,可以清高自守。不过,笔者听过晚年朱先生对“狂狷”二字的理解。他说士人“狂”未尝不是好事,而为人“狷”则不可为。晚年的朱先生笃学嗜茶好静慈祥,有时虽然发火,但其性格已有别于青少年之时。不过从他身上,依稀仍可感悟到早年的桀骜不驯。中国文人多有屈原的抱负、气质与情怀。依笔者愚见,朱先生身上就充满着三闾大夫的因子,特别在他的青年时代,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那时他就像一个“野性难驯的书呆子”。
还在六七岁时,父亲就把儿子送往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育会学艺,却因好勇斗狠而被禁止习武。如果没有此事,说不定多少年后世上就多了一个武林高手而少了一个学术大家。时也运也,孰能逆料?不过,习武人耿直的个性,却溶进了朱先生的血液里,伴随着他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朱先生秉性耿介,然襟怀坦荡,待人以诚,遇事直言,肝胆相照。对此,先生也坦然不讳。1949年,先生有诗曰《六月二十七日奉父书内有共军我甚表同情等语读毕而作》,原注中自云: “余尚忆二十年前,吾父语母曰:‘此子刚愎自用,志大才疏,如不经十次以上之大挫折,使其反省,痛改积习,前途殆无希望。’吾母亦怃然视余点首,今果应其言矣。又吾父每次来渝,辄以骄盈为戒。陶渊明有责子诗,引以为喻。”先生自示严父之语,多有自谦之意,然其宽广胸襟,亦跃然纸上矣。
朱先生在中大修业满后,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曾经介绍他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授国画史,却因与学生一同反对校长而去职。但这只是他与东家或上司之间长长的“书剑恩怨录”的开端。日后在香港报馆,他因编译之事与社长发生争执;在中大,与文学院院长发生抵牾;在昆明军官学校,与上级意见不合;在重庆南洋研究所,反感主持人结党营私。这一次次冲突,他皆以去职了结。而一次次去职,长则年余,短则十日。总的来说,给人的印象是,朱杰勤年少清狂,心高气傲,难以合群。其中内情如何,今已无从细加考证。笔者这里所录,也只是“人云亦云”。但笔者相信,他的一次次去职,并不全是个人意气,应看到笼罩在他身上的,是难能可贵的耿介率直。
这种耿介率直之气,如果表现在国家与民族大义上,就会变为一股浩然正气。作为中国半殖民地的过来人,他对祖国的命运感受尤深。还在少年时,朱杰勤有一次在粤海关检查征税,一言不合,便遭把持关税的洋人一个掌掴。这一经历,他终生不忘,成为他日后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原动力。在笔者的记忆中,朱先生每说及此事,总是慷慨激昂。
20 世纪40年代末,朱先生供职于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他仗义执言,愤怒地谴责政府的腐败与独裁。解放前夕,国民党驻守云南的卢汉将军起义,时有义勇自卫队阻击来犯的国民党残部。在昆明保卫战的人群中,出现了唯一一位教授,他叫朱杰勤。
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学人,朱先生具有两方面最基本的素质。其一是本人的修养,兼通古今中外,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其二就是社会良知。朱先生的修养和品位极高,与人在一起时,他喜谈学问,谈经史子集,每每引经据典,虽然地方口音极重,但在座者无不沉醉其中,就像流连在一个传统文化的兰圃里。晚年的朱先生,在待人接物中每每一派蔼蔼古风,待我等晚辈,也时时处处展现其谦和厚道之情。每当授课之日,我等至其宅,先生总是早早沏茶以候,俾人如沐春风。
朱先生一辈子忠于学术,甘为人梯,是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晚清学人龚自珍的第一“粉丝”。在学脉上,他融合古今,在学识上,他汇通中西。不管是为学为师,他都“学不厌,教不倦”。笔者看到,晚年的他个性突出,只存傲骨却无媚骨,一派谦谦君子的风度。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同行间,他从不轻易出相轻之语。他与人交往多用书信,有信必回,字虽抖斜但苍劲有力,行文传统且规范,礼语、谦语和敬语的使用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他笃信“学问为本”,“学术持身”,他的崇高地位和人望绝非靠行政职位的支撑。当然,他那个时代尚有堪称“古朴”的学术机制。学者是靠一步一个脚印地先做好自己的学问,然后才通过同行阅读他的作品,通过同类作品之间的比较来认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
古往今来文人间的交往,已经形成一套人皆心仪的“法则”:“君子之交淡如水”,“一片冰心在玉壶”。朱先生的朋友、知交不在少数。他最为神交的至友,多有未曾谋面者。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与冯承钧的神交。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圈中,冯承钧教授堪称大家。因南北之隔,朱先生与之从未谋面。1946年冯承钧不幸去世时,朱先生曾写《悼冯承钧先生》长诗悼之,情深意切,恍若故人。诗中亦吟及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深刻见解。先生另撰有悼念冯承钧之文(见《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文后附此诗。《悼冯承钧先生》俱用入声韵,属朱诗中之佼佼者,也是他的最得意诗作,晚年屡被提及。其时先生曾将此诗寄达著名历史学前辈陈垣教授,甚得夸赞。兹录之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读者从中或可窥见先生之学识与为人矣。
昔者有道守四夷,舟车所至及蛮貊。
礼称外语设官司,西北东南言莫隔。
汉世永元通大秦,文化交流赖重译。
音形虽别义则同,法云谓译犹如易。
玄奘义净天竺回,新翻经本殊充斥。
译场八备五不翻,体例谨严见梵册。
从此翻译奇才多,宋元继唐专馆辟。
明清一代盛通商,番舶联翩来叩驿。
海客丛中杂教徒,来华布道兼游历。
耶稣会士艺不凡,西法流传藉其力。
汉学欧洲法国纯,沙畹诸儒足矜式。
二三豪俊识时宜,艺术吸收由外域。
不耻相师或出洋,旧学新知随所择。
清末复设同文馆,训练专才延外客。
彼习华文我西书,借鉴沟通无畛域。
译界严林早擅名,至今人尚称贤硕。
一时创始难为精,居上后来如薪积。
异军特起有冯君,汉口世家名奕奕。
从师比国在晚清,习律巴黎匪朝夕。
欲明法制考源流,惟从历史求痕迹。
回国遂成史地家,不倦披寻人笑癖。
法人汉学各名篇,系统翻成几半百。
直译精翔意尽披,补注校雠词竟核。
研究西域与南洋,佛学方言多创获。
解惑析疑奠万哗,察往知来显幽绩。
暮年痼疾厄斯人,举动艰难需扶掖。
药炉侍者总随身,铅椠图书时狼籍。
矻矻穷年志不移,正学昌明资改革。
稍尝宦况便抽身,远志难酬常跼蹐。
抗战军兴滞北平,八年陷虏愁交迫。
万方多难贱儒冠,五车莫补非长策。
典衣换米入穷途,失业还遭丧明戚。
重操旧业摊皋比,扶病垂垂形槁瘠。
去秋光复我神州,方期从此辞劳剧。
今年忽患肾脏炎,撒手仲春在床箦。
入世艰虞六十年,一逝竟如驹过隙。
巨星遽陨译林摧,遗稿箧中仍数尺。
家徒四壁与遗孤,隙光斜照麻衣白。
我与君无一面缘,一在岭南一朔北。
造诣悬殊所学同,每读君书心莫逆。
也曾著论表微忱,但恨学荒难为役。
会看户户诵雄文,价重蓬山求络绎。
残膏剩馥沾靡穷,岂徒当世受其益?
来岁扁舟吊旧京,郁郁芸香贤者宅。
侧身天地苦蹉跎,禀性愚顽祈感格。
君虽淡泊身后名,我愿滂沱君子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