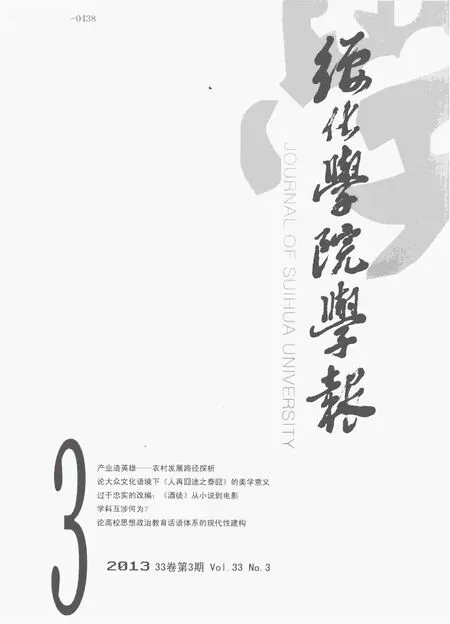“追寻”原型的后现代重构:品钦《V.》的存在主义解读
宋泽楠
(广西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3)
一、原型批评理论
原型批评起源于20世纪人类学家们理清人类原始文明源流和互生关系的努力,发展于心理学家们探究人类共核思维的成就。早在20世纪初叶,“以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剑桥人类学派就深入探讨了意识崇拜、巫术、神话与人类原始文明之间的源流关系;恩斯特·卡西尔则提出原始初民以隐喻思维认识世界,证明了神话、巫术和诗(文学)同源;”(朱,2005:162)
著名心理学家C.G荣格在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中首次提出“原型”这一概念。荣格认为,在个人无意识之外,存在着集体的、普遍的、非个人的并被所有个体心理所识别的集体无意识,而原型就是集体无意识所承载的内容,(Jung,1999:42-43) 是某个具体文化中频繁出现的或者被所有文化所共同享有的意象和模式。默里将之比喻为“种族的记忆”。
罗索普·弗莱把荣格的原型理论以及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运用到文学批评中,由此开创和引领了一个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原型批评。“在批评实践中,原型批评试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朱,2005:162)弗莱认为这些反复出现的基本形式是衍生于神话故事,蕴含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神话原型。
二、《V.》中“追寻”原型的后现代重构
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分析归纳了多种文学意象并把它们与四季相对应。其中在论及The Mythos of Summer:Romance(夏天的主题:浪漫)时,他把“追寻”模式的叙事结构视为最为完整的浪漫形式(Frye,2000:187)。 而另一位著名的原型批评家约瑟夫·坎贝尔甚至认为,“追寻”模式是人类文化中几乎所有神话故事的情节原型,它界定和囊括了人类社会的大半个文学史。弗莱和坎贝尔将“追寻”原型在结构上划分为三个部分:冒险的征程、艰辛的战斗以及最终的胜利。
作为一本复杂而晦涩的小说,《V.》的情节错综复杂而似乎杂乱无章。然而细细查看我们不难发现:“寻找V的章节同那写主要描写 ‘全病帮’的章节交替呈现。这两股叙事流在文本中频繁交融并最终在第十六章汇合。”(Pearce,1981:20)基于这两股叙事流,文本的信息建构主要围绕四个向度铺开并形成四个文本信息群: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人、德国人在非洲和亚洲岛国的存在图谱,当下美国社会中“全病帮”们的生活图景,文本营构的追寻变体以及经验读者所熟知的 “追寻”神话原型。其中,当下美国社会生活图景围绕“全病帮”展开,而其他三个文本信息群则是由追寻V这一股叙事流营构和释放。
小说中,斯坦希尔对V的追寻是从发现父亲遗留的杂志上的一句话时开始,“隐藏在V的背后和内里的东西超出了我们任何人的猜想”。(叶,2003,54)①斯坦西尔穿越美国来到马耳他收集线索并核实推测。他收集到了诸多线索,这些线索主要围绕德国、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非洲和亚洲岛国的殖民斗争和间谍活动而展开,期间涉及维多利亚女皇(斯坦西尔正是出生在维多利亚女王死去的1901年),老斯坦西尔以及戈多尔芬的特工间谍活动,非洲的蒙多根天电事件以及维苏事件,马耳他的坏神父等。斯坦西尔在追寻V的过程中探索并否定了一系列可能的推测,最终未能探究出V背后的意义指涉。
对“全病帮”的描述主要是写实性地呈现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围绕两个维度铺开:反叛的艺术、酒和性的狂欢。一方面,他们活动的主要范围是酒吧。通常,“普鲁费恩、安杰尔、和杰罗尼莫在河滨公园看完姑娘后便马上离开公园去找酒喝”(40)。这一情节是代表性的,概括了“全病帮”基于性和酒两个向度上的生活建构。另一方面,他们对后现代艺术有一种特殊的痴迷,如斯费亚是一位小号手,斯拉伯喜欢用各种流派的手法来画丹麦酪酥饼,肖克是一个奇异的人体模特。
尽管对V的追寻和关于“全病帮”的描述几乎平分了文本的所有话语空间,而斯坦西尔身份是双重的,既是一个反时间的追寻者,亦是一位“全病帮的新来者”(112)。同时,“全病帮”其他成员通过不同的方式同追寻过程及过程中的事件发生关联。如葆拉是马耳他人,间谍戈多尔芬是舍里梅克在军队崇拜的英雄,而舍里梅克又是“全病帮”成员埃斯特的整容医生。基于此,文本关于“全病帮”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追寻情节的辅助和支持,而主人公斯坦希尔对V的追寻则建构了文本故事展开的平台和情节发展的基本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V.》中的“追寻”模式同“追寻”原型传统模式存在以下差异,详见表1:
品钦对“追寻”原型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将传统模式的基本结构戏仿为线索搜集旅程、线索验证以及不确定的结局。事实上,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范畴,因此,“追寻”原型的后现代重构真正地嵌入了后现代的思想内核。除了结构层面的调整,品钦还巧妙地在线索以及与追寻相关的情节中增添了对“全病帮”生活的直接描述。他们熟悉或沉迷于反叛艺术,或糜烂于酒和性的狂欢。当然,结构和情节两方面的调整使“追寻”变体充满了新的象征寓意和现实特征。

表 1.“追寻”原型与《V.》中的“追寻”变体
三、《V.》的存在主义意义
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文明在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和生存图谱下产生的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存在主义主要指以法国哲学家萨特为代表的哲学思潮,广义的存在主义则指以存在为哲学基本问题并集中思考这一问题的哲学思潮”(朱,2005:131)。 然而,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存在主义,它们都共享以下几个基本概念:自由选择、焦虑、荒诞以及虚无。
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存在先于本质。这意味着,人的本质是在以时间为基本度量的存在中通过自身的自由选择不断建构的。然而,在社会框架下,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自由选择必然受到他人、社会、法律和社会道义等外生力量和契约制度的制约、干扰或阻碍。换言之,任何自由选择都必然意味着反抗并因此产生焦虑。而在加缪的哲学中,荒诞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基本生存处境。他认为,荒诞不在于人,亦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存。虽然现代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但是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存在方式,都无法逃离自我以及容纳自我的世界,因而也就无法规避存在的荒诞境遇以及由此而生的失望、放逐感和焦虑。
《V.》中的存在主义主要蕴含于两大方面:结构重构后的存在主义隐喻以及情节层面的存在主义色彩。具体包括意义的主观性、存在的狂欢化与荒、存在的虚无以及存在主义隐喻四个方面。
(一)渎神性和意义的主观性
作为“全病帮”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费恩(Profane)的英文意思就是“渎神的”。渎神不仅是对神的亵渎,而且主要是对以上帝为中心的价值建构进行漫画式的背叛。小说中,“全病帮”的存在方式具有明显的渎神性。他们或痴迷于艺术,或沉醉于酒和性的狂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对传统道德的彻底背叛,更是对以《圣经》为蓝本的教义价值取向的粗暴践踏。作为垮掉的一代人,他们熟悉并受到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皮格·博丁喜欢读“一部名叫《信奉存在主义的警察局长》的先锋派西部小说”(318),并常推荐给普鲁费恩们读。事实上,他们是在日常行为中实践加缪的渎神性解禁话语:重要的不是赎罪,而是与原罪共存。
此外,文章的其他线索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这一主题。追寻初期,列车长沃尔德夫认为,仅仅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许多宣扬上帝权威的故事,如诺亚关于洪水的警告、红海海水的分开,其实并不是上帝的干预,而是源自于偶然的命运。而与《圣经》齐名的《古兰经》在小说中也被认为是荒谬和毫无意义的,“如果这本书仅是对沙漠二十二年倾听的结果,那真是天大的笑话。沙漠没有嗓子。如果《古兰经》毫无意义,那么伊斯兰教也毫无意义。于是安拉就只是一个故事,他的天堂仅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了。”(90-91)
最为滑稽的是维罗妮卡这一线索,线索中,维罗妮卡是一只小雌鼠,同一名在黑暗肮脏的纽约下水管道内向老鼠布道的神父菲尔林有着不合常情的关系。在菲尔林的日记中,维罗妮卡以V的名字出现,她会在晚上来到他的身边听他布道,并“带回显示他要使她皈依基督的愿望的东西”(134)。这应该是小说中最具有想象性的渎神情节之一,该故事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和突兀的漫画效果嘲讽和亵渎了了人类数千年的坚定信念和神圣信仰。
应该说,后现代小说中的渎神更多地是为了宣示价值体系的主观性,从而让当下存在的人们能够摆头意识的束缚,进行自由选择。萨特亦曾言,“在哲学领域内,哲学思想不断诞生,又不断消亡;哲学体系不断被建构,然后又不断坍塌”(Adams&Searle,2006:1176)。 萨特用哲学的思辨表明:人类在历史中寻觅人生价值的过程是一个创造价值观念和不断否定创造的主观过程。在历史中,“存在的人总是被人为的传统价值所牵引并人为地创造束缚后人的价值体系。人们捍卫这些价值体系的努力以及废黜这些价值体系的抗争填充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宋,2007:92)。而站在任意一个历史远点,这些行为显得苍白而荒诞。
(二)狂欢化和荒诞
狂欢是“全病帮”存在图景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酒和性的狂欢。小说中,酒吧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中之一是一个名为“水手之墓”的酒吧。他们常常在次聚会,因为每一个发薪日晚上的八点至九点是酒吧的“吸奶时间”(Suck Hour),期间250多名水手会争抢7个用海绵橡胶定制的巨乳状啤酒龙头。
在蒙多根天电线索中,一个名为“福帕尔的围困聚会”也具有相同的狂欢质性。故事发生在1922年的非洲,由于发生战乱,福帕尔庄园内的人决定撤毁木桥、封住门窗,“让他们去打他们的仗,在这儿我们将举行狂欢节”(262)。庄园内食物充足,在音乐的遮蔽下上演着一幕幕性爱的狂欢并弥漫着偷窥的快感。庄园外则是怒号的杀戮和叛乱的贫困。两相对比,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人性丑恶的道德评判,而是在一个更为宏观的画面上揭示人类整体意义上的深层荒谬。
此外,品钦的创作期待视野之一就是把斯坦西尔描述成一个荒诞的小丑形象:V.作为一头模糊不清的狩猎对象,像公鹿、雌马或者兔子一样被追逐,又向一种老式的、古怪的或被禁止的性快乐形式一样被追逐。斯坦西尔小丑般地跟在她后面蹦跳雀跃,身上铃儿叮当作响,他的手挥舞着木制的玩具赶牛棒。这不是娱人,而只是自娱。(《V.》第 64 页)
这种“自娱”性的寻求在普鲁费恩的眼里是一种“猜疑病”,他认为“斯坦西尔像他的父亲一样对于瓦莱塔私下里患有一种猜疑病”(446)。而心理牙医生艾根瓦吕则从心理学和牙科的双重视野分析斯坦西尔对V的追寻,认为这是一种“矛盾态度”和“异牙构造”(279)。 无论是“自娱”、“猜疑病”还是“异牙构造”,都表明斯坦西尔对V的寻求在他者看来是一种不可理解和毫无意义的荒谬行为。
(三)存在的虚无
“全病帮”们的存在方式同加缪的另一个理念——“不求生活的更好,只求生活的更多”也极为相似。蕾切尔对他们的总结一语中的:“这帮人只有经验,没有生活,亦不会创造”(356)。这种在反传统的向度上扩充人格的生存方式,从本质上讲,起源于企图摆脱传统约束下沉重而又无意义的价值束缚,是一种体验式的唯乐主义。如果说受传统道德约束而无法自由选择的存在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那么全病帮们自由选择的、“与原罪共存”的存在方式在无限度地放纵人的自然本能时彻底放逐了人类的既得文明,有一种昆德拉思想中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显得更加无意义和更加荒诞。因为在解构和背离一切价值后,他们发现自己被掏空了。这是一种虚无和病态的存在方式,正如温森姆自我反省时所说,“对所有我们这帮人有一个词,那就是‘病了’……我们中你指不出一个人可称为健康”(412-413)。
(四)重构“追寻”原型的存在主义隐喻
在“追寻”原型的传统模式中,其遵循的基本结构为征程→战斗→胜利。战斗的艰辛和最终的胜利象征着基于正义的不懈努力总会有回报,是对存在主体主观能动性和行为效用的肯定,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有付出就有收获”的人生哲学。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成功抵达上帝期许之地。这不仅肯定了基于正义的努力总会有回报,而且也昭示了充满正义并向往美好的人也会最终得到超自然力的帮助。其实,在“追寻”原型的传统模式中,超自然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伊阿宋追寻金羊毛故事中的神药,贝奥武甫的铠甲等等。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基本人生定位和基于两个向度的意义诉求。其一为凡世间的自我努力和自我规约;其二是对超自然力的臣服。自我努力、正义的价值取向和对神的虔诚是当时人们最为主要的价值标准。
而与此截然相反,在《V.》中,斯坦西尔的寻求主要体现在试图揭示大写字母“V”背后意义的不断努力。其具体过程是对一系列和V相关的线索进行推测、证实和否定。小说中,V同姓名以V开头的人相关,从维多利亚·雷恩、维罗尼卡小鼠到维拉·梅罗文和维罗尼卡·罗加兹,再到马耳他的坏神父,新的人物不断出现,旧的人物不断被否定和消失。新的推测只是对上一个推测的否定并即将被下一个推测所否定,而由此形成的线索链在有限的文本框架下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或没有结局的方式结局。
从隐喻维度来看,不确定或许象征着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没有终极意义:一切皆有可能,一切也皆不可能。在无意义的人生中,人的一切努力和抗争显得徒劳而荒诞。萨特对哲学思想的经典概括亦可以用来描述坦西尔对V的寻求:新的线索不断诞生,又不断消亡;希望不断产生,然后又不断坍塌。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坦西尔同不停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是相似的。“斯坦西尔关于V的每一条新线索付出的努力以及最终的排除线索对应了西西弗斯每一次推石上山和最后自然力命定的石头滚落山谷。 ”(宋,2007:92)加缪曾用西西弗斯的神话作为自己一本散文的书名。很显然,加缪把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神话看作是人类的荒诞原型意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别在各自不同领域内独立思考加缪和品钦实现了相同的认知突破和思想同构:加缪借用神话故事和神话人物来揭示人类荒诞处境的原型意象,而品钦则通过在自己的文本内创造文学人物和营构文学事件对存在主义思想进行呼应。他们在同一个时代中,相互独立地完成了思想的相同转向和同质突破,并因此独立而又共同地酝酿了那个时代的文化。
四、结语
“追寻”作为内核性的神话原型和最为古老的文学母题,其意义指涉是放射性的,其可能的阐释边界随着人类想象力的延伸和存在种类的拓展而不断外溢扩容。品钦对追寻原型在结构和情节层面的后现代重构产生了新的“追寻”变体并由此建构和蕴含了新的文本意义。从“追寻”变体的情节层面来看,渎神性的故事情节宣示了价值的主观性,“全病帮”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后现代生活的存在主义转向。从“追寻”变体的宏观结构来看,不确定性结局以隐喻的方式对情节层面存在主义进行印证和强化,从而实现了内容与结构在意义建构上的统一。当然,“追寻”变体的后现代重构使品钦在文本内外构筑了历史和此在的话语互动,这一话语互动揭示了战后美国社会存在方式的存在主义转向。
[1]Adams,H.&Searle,L.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3rd edition)[C].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
[2]Frye,N.Anatomy of Criticism.[M].Princeton&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3]Jung,C.G.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4]Pearce,R.CriticalEssays on Thomas Pynchon [C].Boston,Massachusetts:G.K.Hall&Co.1981.
[5]宋泽楠.论狂欢化视野下的《V.》[J].绥化学院学报,2007(2).
[6][美]托马斯·品钦.叶华年,译《V.》[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7]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