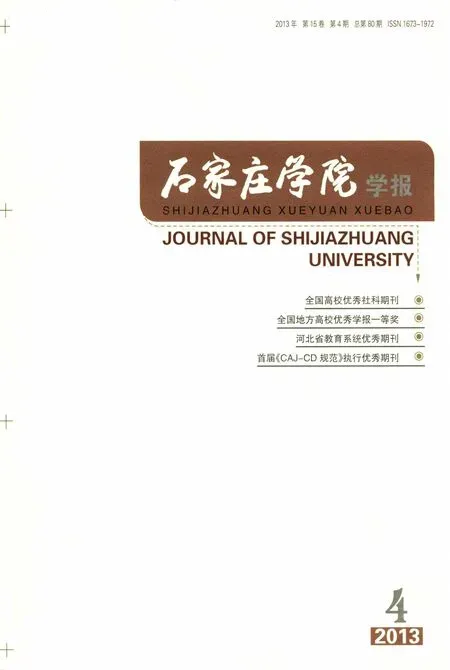《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订误
尹 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汉字古音手册》由郭锡良先生编著,北京大学1986年出版,收录秦汉以前古籍中的常用字7 479个,构拟古音节8 011个,[1]1是学习和研究汉语音韵学的重要工具书。书中对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都有较详细的音值构拟。以现代北京音的韵母为目进行编排,每一韵母下,又依音节和声调的不同排列汉字,而同音节同声调的汉字又依中古音的不同分条排列,中古音相同而上古音不同亦分条排列,这样,汉字的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变化便清晰可见;于每一条中,标明上古韵部、声母、中古反切、音韵地位,以及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构拟。此书大大便利了使用者查检古音的需要。
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增订本。增订本把“凡东汉以前有用例的字都收了”[1]24,又把大约两百个左右“东汉以后才有用例的后起字删去”[1]24,使得此书中的上古音体系更为纯洁。同时也对初版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进行更订,完善了不少。但由于排校或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失误仍有很多,难免影响读者的学习与研究。
本文以《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以下简称《手册》)中的古音系统为本,对《手册》的失误进行订正。我们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上古音的构拟,各家对上古音的构拟差异颇大,这里不作评论。既然是在本书的基础上订误,则暂遵从郭氏体系。郭氏在《例言》中转录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对上古韵部采用等呼的观点,我们引用如下:

这表明郭氏《手册》也采用了此种观点。但书中并未对上古音系发展到中古音系的过程中,上古韵部等呼与中古韵等呼的对应关系作详细论述,所以,书中出现的涉及到此类问题的上古音错漏时,便不易察觉。因此,笔者首先对《手册》所收录的全部字条进行了归纳,总结出《手册》本身所体现的上古各韵部等呼和中古各韵等呼的对应的规律①笔者将在下文中只对涉及到的部分对应规律予以指出。,在此过程中,也就找出了此类不合对应规律的失误。笔者就是以《手册》的古音体系为本,进行订正。古韵部的分类、古音的音值构拟和标示、争议字的上古音归属等问题,悉依郭氏。
本文订误的版本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8月第1版,201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参考的《广韵》有钜宋本、泽存堂本、周祖谟校本和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
一、上古音“等”之误
(1)30 页:

上古音拟作三等,误。案:郭氏对铎部的构拟,与王力相同,包括开一、合一、开二、合二、开三、合三、开四。其中,开三长入到《广韵》中归入御韵,如“庶”字;开四长入到《广韵》归祃韵开三,如“谢”“榭”等字。《广韵》中“柘”组字的反切是“之夜切”,属祃韵开三。祃韵开三的字,一部分来自上古鱼部开四,如“卸”“泻”“舍”等字;一部分字来自铎部开四长入,如“借”“谢”等字。《手册》将“柘”组字归入上古铎部长入,但不应拟为三等,应为开四长入。
(2)78 页:

拟作三等,误。依郭氏古音体系,铎部开三短入字在《广韵》中归入药韵开三,铎部开四短入字归入梗摄开三,隻属昔韵开三,亦即梗摄开三,故上古当为开四短入,应拟作。
(3)81 页:

91页:

同上例,拟作三等,误。炙拓、释均属梗摄开三,上古音均当为开四,应分别拟作。
(4)91 页:

拟为开四,误。案:脂部包括开二、开三、合三、开四,脂部开三主要归入《广韵》脂韵类(即包括脂旨至三韵)开三,脂部合三主要归入脂韵类合三,脂部开四主要归入齐韵类开四。嗜属于至韵开三,则上古应归脂部开三,应拟为。 《手册》115 页耆组字(脂韵开三)拟为脂部开三[ɡǐei]亦可为证。
(5)104 页:

拟为开三,误。翳组字音於计切,中古属开口四等字,故上古音为脂部开四,应拟作。
(6)135 页:

拟为开四,误。案:质部包括开二、开三、合三、开四、合四。其中,质部开三长入归入《广韵》至韵开三,如“四”“自”等;开四长入主要归入霁韵开四,如“计”“闭”等。《广韵》“鼻”音毗至切,属至韵开三。因此上古音为质部开三长入。应拟作。
(7)138 页:

同上例,“痹畀”属至韵开三。上古音当为质部开三长入。 应拟为[pǐēt]。
(8)139 页:

上古音误拟。案:对于物部的等呼分类,郭氏和王力不同。王力将物部分为开一、合一、开三、合三[2]107,郭锡良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增补了合二、开四、合四[1]9。物部开三短入到《广韵》归入迄韵,如“迄”“讫”;物部开三长入归入未韵开三,如“既”“气”;物部开四长入主要归入《广韵》至韵开三,如“寐”“魅”“暨”。鄪费(古地名)音“兵媚切”,属至韵开三,故上古音为开四长入。应拟为。《手册》既错拟为三等,又错拟为短入。
(9)225 页:

上古音拟为三等,误。案:依郭氏古音体系,微部四等开合俱全[1]9。上古微部合三归入《广韵》微韵类合三,如“非”;微部合四归入《广韵》脂韵类合三,如“衰”。夔组字在《广韵》中属脂韵合三,上古音当属微部合四,应拟为。
(10)269 页:

拟为三等,误。案:宵部包括开一、开二、开三、开四,演变情况比较整齐,分别归入《广韵》效摄开一、开二、开三、开四。“镣”组字在《广韵》中音“力弔切”,属效摄四等,故上古音当为开四,应拟作[liau]。
(11)270 页:

拟为三等,误。案:药部包括开一、开二、开三、开四,其中,长入字到《广韵》中分别归入效摄开一、开二、开三、开四。“尥”反切为“力弔切”,属开四,故上古当为开四长入,应拟作。
(12)374 页:

上古拟音误,应为合口四等。案:王力《汉语史稿》文部包括开一、合一、开二、开三、合三、开四、合四,郭氏在此基础上增补合二。具体字归属也有不同。详如《手册·例言》所说:“文部将《广韵》谆韵的字全归合口四等,而以仙韵的舌齿字代替谆韵的舌齿字与文韵的喉唇字相配,列为合口三等。”[1]9当然,郭的意思不是说 《广韵》谆韵的字上古全部属于文部,如“匀”“荀”等字属于真部合三,而是说《广韵》谆韵中属于上古文部的字全都属于文部的合口四等。依郭氏古音体系,文部合三的舌齿字归入《广韵》仙韵类,如“川”,喉唇字归入文韵类,如“云”;文部合四归入谆韵类,如“准”。“尹”在《广韵》中属准韵,故上古音当属合口四等,应拟为。
(13)432 页:

这两组都是上古音的等拟错了。案:依郭氏古音体系,阳部开合四等俱全。其中,阳部开三归入《广韵》阳韵类,如“强”“想”;阳部开四归入《广韵》庚韵类,如“迎”“影”。显然,这两组字在中古都是庚韵字,故上古为阳部开四,应拟作[iɑ耷]。
二、长入误拟为短入
郭氏认为上古的长入声的字到中古变为去声,构拟上古音时,他在长入字的主要元音上面加“-”,短入字的主要元音上加“ˇ”。
(1)33 页:

“厕(厕所)”中古已经变为去声,上古音应该是长入,《手册》拟为短入,误。应为。
(2)87 页:

(3)133 页:

“戾”组字音郎计切,属霁韵开四去声。上古当为质部开四长入。应拟作[liēt]。
(4)233 页:

“芮”组字在《广韵》中是祭合三去声,故上古音当属长入,应拟为。
三、“开合”之误
(1)210 页:

标为开口,误。案:《韵镜》第五图标明“羸”是合口三等,而支韵来母开三则是位于第四图的 “离”字。[3]34-37开合口误,则拟音亦随之误。应改为:

(2)449 页:

453页:

以上两组上古音标注为合口,误。王力《汉语史稿》东部包括开一、开二、合三,《手册(增订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开口三等,《例言》说:“东部增补了开口三等……如充衤充崧。”[1]9东部开三的字到《广韵》归入东韵,而东部合三的字则归入锺韵。《例言》中既已举出这些例字,拟音却与之相悖,岂非疏忽之至?
四、“反切”之误
(1)40 页:

案:《广韵》钜宋本、泽存堂本、唐韵、周祖谟校本磨小韵反切均为“摸卧切”。《手册》误把“摸”字作“模”字。
(2)359 页:

反切误。钜宋本、泽存堂本、敦煌本王韵、唐韵“袨”组字均作“黄练切”,王三作“玄绚反”,但均不作“黄绚反”。《手册》失据。虽然黄练切的反切下字“练”是开口,被切字是合口,但我们知道,被切字的开合有时是可以通过切上字表现的,如《手册》179页“域,雨逼切”,被切字是合三,切下字是开三,被切字的等呼是由切上字表现的。
(3)430 页:

《广韵》泽存堂本、钜宋本、周祖谟校本皆作“敷空切”。这也是被切字的等呼由切上字表现的例子。余迺永说:“豐乃三等字,此用一等之空字作切,乃其上字用三等之‘敷’也。”[4]27解释得不无道理。但切二、王三作“敷隆切”,郭氏可能是据王三所改,亦属有据。
五、起别义作用的“又音”漏收
《广韵》的很大一部分又音是起别义的作用。这些又音表示的意义有的已经消失,但有的依旧常用。《手册》对常用的别义又音有的收录,有的却没有收录。例如:
(1)67 页:

其中的“喋”字,《广韵》三见,分别是“徒协切”“丁惬切”“丈甲切”。 释义各别,“徒协切”注为“便语”,如喋喋不休;“丁惬切”注为“血流貌”,如喋血;“丈甲切”注为“啑喋,凫雁食也”。第三种用法现在已经不常见了,不收也无碍。第二种用法虽然口语不常用,但书面语还是较常用的,而《手册》只录了第一种读音,应该别列一项,注明各音词义,并标示相应的上古音。
(2)91 页:

“视”字在《广韵》旨至两韵并收,“常利切”注为“看视”,“承矢切”注为“比也,瞻也,效也”。 可知,中古“视”字读上声和读去声意义有别,读上声有比较、效法的意思,读去声则专表“看见”义。既有区别意义的又音,别立一项为佳。《手册》只收上声一项,失之。
《手册》收录的起别义作用的又音中,有个别释义失误,如:
(3)136 页:

142页:

《广韵》“辟”字有三种读音:房益切,释为“便辟,又法也……”;必益切,释为 “……君也,亦除也……”;另有芳辟切,义同同小韵的“僻”字,同小韵的“僻”释为“误也,邪僻也”。《集韵》“辟”字反切用字不同,但切出来的各音与《广韵》相同,并且音义对应关系也完全一样。《手册》释义欠妥。“法”义应注在“房益切”下,而“必益切”应释为“君主”。 另外,“打开”是对“房益切”的“闢”字的释义,“闢”简化后与“辟”合为一字,但《手册》用的是繁体字,所以,释义必须严格。
六、今音标注欠妥
(1)93 页:

案:“雌”是次清平声字,如果遵循普通话的语音演变规律,确实应该变为阴平调,但普通话的事实是归入了阳平调,《现代汉语词典》也注为阳平。语音演变规律也只是从客观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排除有不合规律的例外。还是依客观事实,将雌字注作阳平较为妥善。
(2)121 页:

普通话读作阴平xī。
(3)219 页:

普通话读作阴平wēi。

(4)336 页:鲇组字音“奴兼切”。“鲇”和“拈”应该是同音的,但普通话两字声调已变得不同,鲇归阳平,拈归阴平,《现代汉语词典》也将“拈”注为阴平。故鲇组字分两个条目为妥。
七、“拟音符号”之误
(1)205 页:

(2)223 页:

从危得声的字属于支部,郭氏支部拟为e,拟音应为[ɡǐwe]。
(3)224 页:

这三组字拟音都没有标长短入符号。三组在《广韵》中都归入止摄合口三等去声,因此上古都是长入声。 应分别拟为。

(4)226 页:kuì去声“溃”“愦”“聩”“嘳”组、“蒉”组、“归”等六组字皆属物部长入,但音标都没有标示长入符号,疏忽所致。
(5)241 页:

(6)254 页:

两组字韵腹误标。郭氏将幽部音值拟为藜u,所以,上两组字拟音当分别作。
(7)308 页:
tān 滩(涒滩)……

韵腹误标。《手册》元部一等音值是an,如“坛”组字拟为[dan],“半”组字拟为[puan]。郭先生古音体系中,ɑn与an不构成对立音位,所以这是小问题,但前后保持一致为佳。此处当拟作[t‘an]。
(8)447 页:

八、“韵部或韵摄”之误

(1)213 页:归入“微”部,失之。案: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表二“己声”入第一部(基本等同于王力古韵二十九部的之职二部),《手册》中也体现了凡从“己”得声的字都在之部,故知“配”组字在上古应属之部。改为之部,也正与后边的上古拟音相合。
(2)420 页:

韵摄误注。应为梗摄。这个疏漏李无未先生在1993年就已经指出。[5]
九、缺拟上古音“又音”项
(1)20 页:

案:《广韵》中“刷”字有两种读音,分属于二等和三等,《手册》既然都予收录,却只构拟了合口三等的上古音,不妥。 应再列上古又音[蘩o觍t],使《广韵》又音有源可溯。
(2)196 页:

案:“蓋”字《广韵》三收:泰韵“古太切”、盍韵“胡臘切”、盍韵“古盍切”。“古太切”蓋字注曰:“覆也,掩也……”[5]380;“胡臘切”蓋字注曰:“苫盖。 ”[5]536看来此两种读音意义无别。“古盍切”蓋字注曰:“姓也。”[5]537-538基于这个用法较少见,《手册》没有录。但前两种读音既然都予录入,则不可只拟一个上古音,应对两种读音都溯源。
十、排版失误
例如:461页部首目录中,二画“入”至“刀(刂)”的八个部首对应的页码数都是465,实际这八个检字部首都在466页。
[1]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 (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李新魁.韵镜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5]李无未.汉字古音手册订误举例 [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1):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