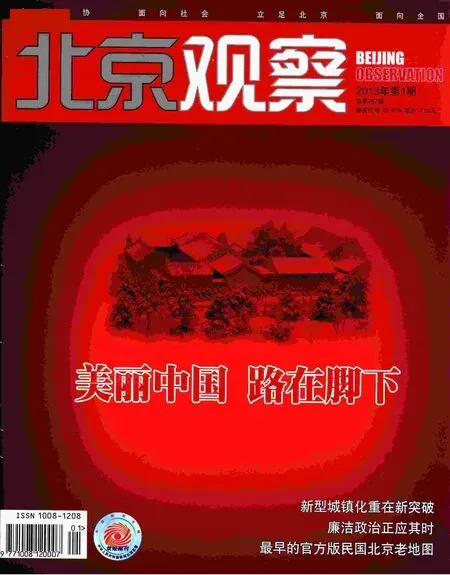赵志强留住一把打开历史的钥匙
文/本刊记者 郭 隆
作为一个锡伯族人,儿时的赵志强便从父辈人那里听到过有关乾隆年间,4000多锡伯族军民穿越大漠草原,翻越冰天雪地的阿尔泰山,最后到达新疆伊犁的西迁传说。
说起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东归传奇”,世人耳熟能详,但对于同样悲壮的一段“西迁壮举”则是鲜为人知的。
248年前的1764年阴历四月十八日,一批锡伯族军民从故乡沈阳(当时叫盛京)出发,告别世居的故土和骨肉同胞,踏上了万里西迁的漫漫征途。在历经严寒困顿、路途坎坷等种种艰辛后,这支锡伯族部落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二十二日,先后抵达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地区,开始了平息叛乱、为国戍边的民族壮举。
将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民族大迁徙故事探究、考证出来的,是一位执著而痴情的民族学者,一个用近乎顽强的民族精神,将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段历史串联起来,颇具传奇色彩的人。他就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赵志强。
“文革”后的第一批满文人才
1975年,“文革”尚未结束,当时的青年人也少有选择未来学习或工作的机会。而出生于新疆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小伙赵志强,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说起与满语结缘,我实在是很幸运的”,赵志强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会说满语、写满文的人日渐稀少,而一旦满语文人才断档,就意味清朝皇家的200余万件满文档案无人解读。为此,北京故宫博物院遵照周总理批示,开办了满文干部培训班,特准从北京、新疆、黑龙江等地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21名学员学习满文。通过考试的赵志强被顺利录取,自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和工作航标。
在北京故宫内阁大堂的大殿里,赵志强和他的同学们开始了艰苦的学习生活。“满文和锡伯文的很多字同形同音,基本上,锡伯语完整地把满语保留了下来。”赵志强说,从小熟练掌握锡伯语言,使他当时在学习满文时比其他一些学员要快些。尽管如此,锡伯语与满语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特别是他们掌握的口语与清朝官文书中的书面语差异更大,需要一个一个地记单词,逐字逐句地去领会。小本子记了一本又一本,卡片写完一张又一张。清晨和晚饭后,故宫西华门旁的内护城河边,每天都能看到赵志强背单词的身影。
经过三年的专业学习后,赵志强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从事满文档案整理、翻译、研究工作,埋头于浩如烟海的清代文献资料中,常年的实践,使他对馆内文献了如指掌一般。不久前,赵志强为查找一份资料来到离开多年的档案馆,当工作人员一番查找后歉疚地告知所需资料短缺时,赵志强凭借多年记忆,准确无误地提示给对方资料所存的位置,果然一份文献便被取了出来,这样的功夫令包括同行同事在内的所有在场人员佩服不已。
工厂内的残损木板
作为一个锡伯族人,儿时的赵志强便从父辈人那里听到过有关乾隆年间,4000多锡伯族军民穿越大漠草原,翻越冰天雪地的阿尔泰山,最后到达新疆伊犁的西迁传说。老人们讲的是否是真实发生的故事?自己的故乡到底在哪里?族人们为何要背井离乡远涉万里?一连串巨大的疑问很早就撞击着赵志强触摸民族历史的使命感。而今,掌握了满文,又能接触到故宫保存的珍贵清代历史档案,他最想弄清楚的就是自己民族、自己祖先的历史。
因为研究锡伯族史不是赵志强的本职工作,所以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干。每天晚饭后,他就埋在浩如烟海的清代满文档案里查找史料。没有复印设备,就手抄,一本本的笔记记了几十本。俗话说,阅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赵志强知道,传说中被抽调的锡伯人,出发前曾在沈阳的锡伯家庙集合,祭祖告别。是不是真有一个家庙?200多年后它是否依然存在?带着探索和敬意,赵志强和他的同事、老乡吴元丰第一次到沈阳太平寺寻找史迹。
“当时的家庙已成为一个工厂,找来找去看不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赵志强颇有感慨地回忆说。他在工厂外拍照的行为引起了一位工人师傅的注意,当得知赵志强是来寻找锡伯族史迹的,工人师傅便向他说起厂内机器下压有一块刻着字的木板。专业的敏感让赵志强十分小心地从机器下把残损的木板抬出来,除去上面的油泥后,“锡伯家庙”四个大字虽有残损却仍可辨认。“经考证,这就是太平寺大殿内的木匾!”提及此事,赵志强至今仍是一脸兴奋。如今,这块木匾就悬挂在修葺后的锡伯家庙殿内。
赵志强十分注重对细微史料的考证,多次到东北、内蒙古、新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特别是对锡伯族的西迁,更是收集了百余万字的历史档案资料。他先后出版了锡伯文版和汉文版的《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他与同事合作发表的《锡伯族西迁概述》利用大量鲜为人知的满文原始档案史料,经过严谨的研究和考证,对锡伯族西迁的历史原因和行进路线进行了严密考证;他与同事以锡伯文合著的《锡伯族迁徙考记》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因为国内外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人会用锡伯文或满文写著作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斯达理将此书译成德文,在欧洲发行。
70万字专著破解“旧清语”
近年来,从《明亡清兴六十年》到《前清秘史》,与清朝历史相关的讲座、纪录片接连热播。“除了对历史故事本身的兴趣之外,对于一个少数民族为什么能统治中国达200多年,‘康乾盛世’如何使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都是人们的兴趣所在”,赵志强说,探究这些问题就必须掌握大量的满文原始档案,对满洲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发挥自己精通满语文的优势,结合人们关注的清史热点,赵志强逐步将研究方向转向清代政治制度。在查阅了大量的满文档案资料,经过分析考证后,赵志强发现了清代的很多决策是集思广益的结果。“清代中期的决策机构里不仅集中了一批满洲族人才,还有蒙古族、汉族等各民族的优秀人才。所做的决策基本是符合客观的,符合当时国情的,这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结合研究成果,赵志强出版了《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一书。书中探讨了清代中央决策的办法、政策产生的背景、过程和效果,理清了清代从入关之前的议政处,到雍正朝的军机处,还有九卿会议等机构在中央决策机制中的地位和关系。
研究满洲文化与历史,满语是所必须的重要工具。而在多年的学习、研究过程中,赵志强发现,由于满语文自身的演化过程,也给满洲文化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
有一年赵志强和同事去辽宁省档案馆查资料,遇到一位研究人员向他们请教关于一句老满文的翻译问题。原文大意是:一个人不舒服,干硬的东西吃不了,也就喝点稀的东西。这句话是用老满文写的,如果按照皇太极改革后的新满文来翻译,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成了‘也就喝点尿’。赵志强对研究人员解释了这是老满文里面特有的一种表述方法,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喝点稀的东西”。
这件事对赵志强的触动很大,促使他对老满文进行研究。赵志强说:“皇太极时期,朝廷对老满文进行了改进,增加了‘圈点’,形成了‘新满文’,到了乾隆时期,很多人都不认识老满文了。”对此,赵志强经过20多年的潜心钻研,出版了一本近70万字的专著——《旧清语研究》。现在国内外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如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台湾中正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教学老满文的时候,都把这本书当作工具书使用。
一次使用满语的彻夜长谈
1991年,赵志强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他的满语专长不仅在业务上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也成为联络北京满族学者、拓展满族民间研究的纽带和桥梁。实业家陈丽华、皇族后裔毓瞻、启骧等都先后成为他情感上的朋友、事业上的同志。这种关系的建立不仅加强了民族内部之间的交流,也为满语民间资料搜集、强化满语社会影响、推动满语学术研究等带来积极的效果。
即使在满学所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赵志强还是与以前一样,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满文满语研究方面,发表了《清初军国议政与满洲贵族》、《清朝兴衰与皇子教育》等近三十篇的满文满语学术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都配合了时下的民主施政建设、教育体制探索、反腐倡廉机制等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让人们看到了满文满语新的价值和前景。
在当今社会,如果提到某人致力于满语研究,似乎总给人以“过去式”的感觉。而赵志强能够全身心的致力于满语研究近30年,除了本身的职业要求外,更源于心底的一股情感的力量。
一次,赵志强来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满族村考察。作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在这里尚有为数不多的几位精通满语的老人,孟老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当他听到赵志强纯熟、地道的一口满语,当即将他视作知音,不仅让到家如宾朋故交般地款待,还施以地主淳朴、至尊礼节,让老伴借住他处、腾出炕头,与赵志强用满语彻夜长谈。是什么力量使得并不同族且年龄殊异的二人近若父子家人?共同的民族语言在这里产生了神奇的效应。也正是这种效应,坚定了赵志强守护民族语言、探究民族文化的决心。“抢救满文,就是为了留住一把打开历史的钥匙”,赵志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