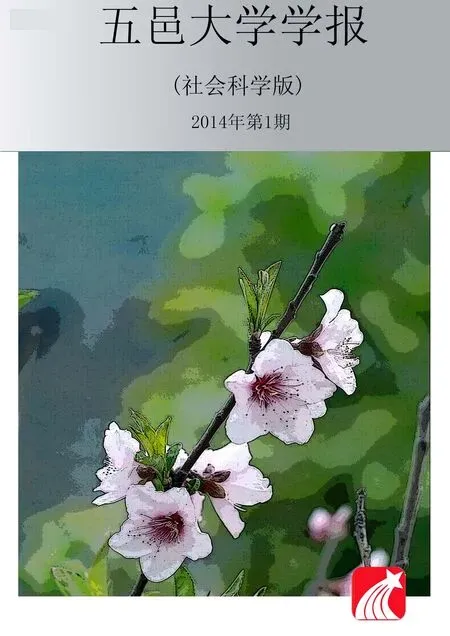略论梁启超的“破坏”思想
席志武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一、破坏主义是梁氏思想之关键
台湾学者黄克武先生在《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中,曾就辛亥革命前后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与文化传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援用美国学者墨子刻(ThomasA.Metzger)的“转化—调适”分析架构,将其概括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一是强调渐进变革的“调适”(accommodativeapproach),二是强调激烈变革的“转化”(transformativeapproch)。在黄看来,梁启超的思想即属于调适思想的典范。这里且不论梁氏思想是否能用“调适”所能概括,也无意对梁氏思想所发生的前后转变做具体评说,但从梁本人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所作的自我评价来看,“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1],即可看出梁对自己早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有着自觉的供认。黄克武认为梁启超是“调适主义者”,自然有他的依据,但就历史的实际情形来看,梁之所以成为“舆论界之骄子”,产生“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巨大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早年鼓吹“革命”和大力提倡“破坏主义”。
1934年,郭湛波完成《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初稿①,随即请胡适等前辈对此指导。据郭“再版自序”的说明,该著初稿论及梁任公时,只写了梁晚年的思想(由此可见郭、胡两代人对于梁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认识——笔者注)。胡适对此提出修改意见,认为梁的影响主要在其创办《新民丛报》时代之“新民”学说,倡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自由等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大。[2]胡适提给郭的此番意见十分富有深意,它不仅决定了梁在郭著“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也可看出胡适在时隔30多年后依然对梁的激进思想念念不忘。这或许正是梁启超影响“五四”精神的一个最佳注脚。而胡适直接论及梁启超的内容,在《五十年来之文学》(1922)、《四十自述》(1933)中都有明确体现,兹不赘述。需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所发生的这些历史回响,都可归结到梁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所大力提倡的“破坏主义”。
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梁究竟是不是“调适主义者”实际上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破坏主义”和“新民”学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时代,并直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激烈变革”的思想资源。而仅以“调适”一词来概括梁氏思想,显然仍值得商榷。诚然,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复杂的迂回流变,梁也自认“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这说明,梁氏思想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按照其实际情形来作出合乎事实与逻辑的描述。
梁启超的“破坏”思想可谓是清末民初最具蛊惑力和冲击力的时代话语,然而吊诡的是,1948至1978年间,国内学界对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梁后期的改良与保皇思想作政治性批判,认为梁是政治上落后和思想上反动的典型。1978年后的研究虽充分肯定梁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历史价值,并对此作了全方位展开,但都极少对梁的“破坏”思想作深入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仅见蔡开松《梁启超“破坏主义”思想透视》(《求索》1988年第6期)一文。由此观之,对梁启超“破坏主义”思想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开掘空间。对“破坏主义”进行研究,对于理解梁启超的整体思想及其历史影响,有着重要的指示意义。
二、破坏与爱国
梁启超正式提出“破坏主义”口号是1899年,这是他遭遇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第二年。此时梁借道日文开始接触到大量西方资产阶级著作,这些“畴昔所未见之籍”使得梁氏“思想为之一变”。他一改维新变法时期温和渐进的改良主张(即黄克武所谓的“调适”),大力倡导“破坏主义”,在《自由书》中即明确表示要“务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3]52。并且认为,只有“破坏主义”才是拯时救弊的重要方略,才能使中国走向进步之途。透过梁的具体论述,不难看出梁氏“破坏”思想的形成受到日本明治文化的直接刺激,同时也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学说密切相关。梁启超的思想博杂无定,一如他自评的“务广而荒”、“太无成见”,[1]然而不论何时何地,梁氏始终都坚持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探索。他的所有言论和行动,无不是围绕着“忧国”与“爱国”而发。对此,梁亦有着情真意切的陈述:“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谁欤踊者?吾歌矣,谁欤和者?”[3]87正是因为对国家深沉的忧与爱,所以在面对糟糕的社会现实时,梁才觉得如此紧迫和急切,以至于忙不迭地鼓吹“破坏主义”、宣扬革命。
1900年,遭遇“庚子勤王”的失败后,中国又发生义和团运动、满清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占领紫禁城等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刺痛着有志之士的爱国神经,同时加深了梁启超对于晚清政府与愚陋民众的认识,在梁看来,“今日之中国,又积数百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距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4]50梁认为,中国积痼太深,已非“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所可以维持,必须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进行一场彻底的大变革方可救国救种、保国保种。于此而言,“破坏主义”可谓当时挽救时局独一无二之法门。那么,破坏什么?现存的旧制度和旧文化都是梁要进行政治革新和民众启蒙的最大阻碍。
首先是政治革新。政治革新所针对的是一个“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社会之所以积弱患贫,受尽外族欺压凌辱,其根源即在于延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政制度,因此需要“破碎而齑粉之”[5],建立一个“政体之最良”的“君主立宪制”[4]1。早在1896年,他对此就作了深刻揭露:“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6]正是由于一种起于自私的“防弊之心”,以国家为一姓之私产,所以罪大恶极的如秦始皇、元太祖、明太祖等“民贼”们呕心沥血,遍布罗网,精心搭建起一整套精而且密的防弊之法,“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4]28,这种愚民、柔民、涣民政策使得民众斫丧元气,变得愚陋怯懦并自居为奴隶,甘心受治于专制之下。故人人自主之权归诸一人,天下之利归诸一姓。梁因此说:“我国蚩蚩四亿之众,数千年受制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而犹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7]76梁于此可谓对中国的积弱根源做了一个系统梳理,即是中国积弱全在于专制独裁的君权政体。“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8]90,“天下坏伦常毁天性灭人道破秩序之毒物,未有甚于专制政体”[8]98。独夫专制使得中国失去了文明进化之资格,使得广大国民不知有民权,使得西太后党之政府守旧自大,使得中国任人宰割利权尽丧,使得外国之逼迫日益加重。既如此,梁明确标示出他的破坏主张,“今欲举秦汉以来积敝,摧陷而廓清之,以举自强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9]民权之议是梁氏对抗君权专制的一把利刃,同时也是革除清廷诸多旧弊的法宝。
其次是民众启蒙。民众启蒙所要指向的是“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梁启超曾指出,人才乏绝、百举俱废,是中国所以讲求新法三十年而一无所成的根本原因。那么有着四万万之众的中国何以人才如此匮乏?这就必然要触及到传统思想文化的改造问题。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认为要想国家自强,必须废科举、立学堂、译西书、开报馆等,并且认为这些都是开民智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然而这些开明主张,在当时的“蒙翳固陋窒闭之中国”,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奋力抵抗。他们以维护孔学圣教为旗号,指责梁氏推崇异学、乖悖伦常、背戾圣教等,是“乘外患入侵之日,倡言乱政,以启戎心”[10]之举。这使得梁对孔教的看法略有改观,他在《新民说》中说:“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11]59-60正因为孔教屡屡被人作为抗拒维新变法和束缚国民思想的凭藉,所以梁干脆一改维护孔教之义,认为孔教不必保,也不可保,因为保教会妨碍思想自由,[8]55而思想不自由,开民智就成了空谈。之后梁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为自己申辩道:“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12]278梁最后表示,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但是,透过梁启超的言论看,他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破坏”,并没有如对待君主专制那般干脆利断,相反,还一直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这就决定了梁氏所谓的“新思想”,并非完全地舍弃旧学,而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革新、对西方文化进行采补和汲取的基础上,是一种中西文化会通的理想。正如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中所说的,中华文明“迎娶”欧美文明,“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13]此“宁馨儿”既是梁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破坏”后以期达到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对民众进行启蒙所欲实现的目标。
1899至1903年间,梁启超在他的相关著论中不止一次地盛赞过“破坏主义”,认为这是医治“积数千年之沉疴”中国的最佳策略,同时也认为这是疗救四百兆身患痼疾的民众的灵丹妙药。在梁看来,惟有打破传统限制民权的独夫专制,惟有粉碎原来窒息民智的腐败学说,才能使国民成为“新民”,才能使国家走上进步之途。由此可知,梁氏的“破坏主义”,破坏的正是禁锢人的制度和文化,是要打破死气沉沉的思想局面。梁氏从民众角度来对国家实行改造的策略,有着深刻的民本思想,同时又昭示了其深在的“新民”底色。就此而言,梁氏直接给“五四”时期的那批“新青年”们提供了从“改造国民性”出发的救国范式。
三、破坏与新民
梁启超的“破坏”言论,无不是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不论是前期的大力提倡,还是之后的全然放弃,都反映出他对于时局的清醒认识,其出发点都在爱国。但国乃积民而成,所以应该从国民素质上下功夫。“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11]1。“新民”也就成为梁此时“破坏”思想的应有之义,这也被认为是“第一急务”,救亡图存之根本。何谓“新民”?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专设一节做了详尽阐述:“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1]5这句话中,实际上已经潜藏有一种固已存在的“旧民”现象,一个从“旧民”到“新民”的破“旧”立“新”的转变过程,并涉及到了一个“新民”所应具备的品格素养问题。
首先来说一说“旧民”现象。梁启超应该是他那个年代最了解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对民族深沉的爱,不仅表现为浓烈的爱国情怀,同时也体现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批判上。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一文中,梁从六方面揭露了“旧民”身上所存在的诸种缺陷:一曰奴性。他认为国民秉奴隶性者最多,从居上流的高官权势者到乡曲小民,“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吾民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甘居奴隶,且以此为荣。二曰愚昧。梁氏认为,国民之智慧关乎国脑,是国家富强的根本。然堂堂中国,“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且全国之官吏与民庶皆愚昧之人,“未有通常之智慧”。三曰为我。爱己利己是人之本然,但毫无利群之心则一己之利也将不保。中国群力薄弱是因为“为我”之心太深,以致国家难以自存于竞争世界。四曰好伪。梁指出,今日之中国人,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皆以伪之一字行之。民无信不立,举国之人持一伪字以相往来,定难立于天地间。五曰怯懦。中国民俗向来柔弱,然处今日生存竞争最剧最烈百虎眈视万鬼环瞰之世界,“无勇”之害不仅损及民权,国权也将消亡。梁因此说,为国民者不可以无勇,并提倡“尚武之精神”和“中国魂”,此乃“民力”之体现。六曰无动。针对国人如木偶、如枯骨的“无动”现状,梁提出要打破这一死气沉沉的局面,“动者万有之根原”,人应该富于冒险进取精神,而不是安于现状,以不动为至善。[4]18-28
其次,如何破“旧”立新,实现从“旧民”到“新民”的的转变呢?毫无疑问,上述梁启超所分析的六种国民缺陷都是要破除的,这不仅是“新民”的重要内容,更是“破坏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戊戌变法时期,新起的维新派就注意到国民愚弱的社会现实,于是大力提倡要从国民入手,实现救亡目标。其中最具代表性、且对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是严复的《原强》(1895)一文。具体到“新民”内容,严复就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梁的“新民”思想,几乎都是围绕着严氏此义所做的发挥和推进。具体而言:“鼓民力”方面,梁强调要从生理上对中国人种进行改造,如强健体魄、讲究卫生、禁食鸦片、禁戒缠足、禁止早婚等,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倡以一种尚武精神来塑造“中国魂”,这种“中国魂”即以爱国心和自爱心和合而成的“兵魂”。为进一步激发民力,梁还创作了《中国之武士道》(1904)一书,认为吾族乃“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以此激励同胞发扬国人之武士道精神,涤荡文弱之风。“开民智”方面,梁将开民智视作国家自强的第一要务,是兴民权和立国权的前提。他认为开智的根本在于教育,并提出了废科举、立学堂、兴学会、立师范、立女学、立幼学、译西书、开报馆等一系列主张。另外,梁提出开民智要与开绅智、开官智并启,尤其应以开官智为起点,因为“官贪则不能望之以爱民,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7]45。“新民德”方面,梁极力提倡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来对传统封建伦理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大力输入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群治思想、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进取冒险精神等等,以重塑国民道德。这些新的道德观念也即要将原来的乡民、臣民、部民改造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
最后是“新民”所应具备的品格素养问题。如果说从“旧民”到“新民”过程所体现的是“破坏主义”的“破”的内涵,那么这里则关乎到“破坏主义”的“立”的意义。很显然,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针对国民道德所存在的缺憾树立了诸多新的道德观念,可以归结为“公德”与“私德”两方面。梁氏说,道德无外乎公私二者:“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11]12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在《新民说》中立专节论述的,包括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义务、自由自治、竞争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等思想在内,无不属于公德范畴。而且事实上,已有论者将上述内容归结到“公德”条目下做了具体分析。②不难发现,梁在前期所论列的这些公德条目,无不以利群固群善群为旨归,服务于他的“群治”理想,而这也恰恰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所最缺的,“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11]12因此才有必要“采补其所本无”来进行革新。梁认为,只有发明了“诸德之源”的公德,新道德才会出现,“新民”也才会到来。需指出的是,梁提倡公德从来就没想过要把它与私德对立起来,为防止此种现象,梁在1905年又专门论述私德的意义。他开篇即说:“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11]118并且申明:“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11]119梁认为,私德是传统文化中最为偏重的道德,那么如何“淬厉”这种本有之道德,他提出了三个进德修身的要领,即正本、慎独、谨小。梁这种处理传统“旧”道德的方式,恰恰又印证了他最初所提出的“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由此,梁氏“新民”所具备的“新道德”,即可说是西方道德与传统道德的相互补充,也即公德和私德的融合。这个客观事实说明,梁氏的“新民”思想自始至终都完整地落实了他“破坏主义”的策略:随破坏随建设。
四、结语
梁启超一生思想,表现出如其师康有为所责难的“流质易变”的特征。梁的“破坏”主张从萌芽到明确提出,再到自美洲游历归来后(1903年)的完全放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流变过程。这种流变本身包孕着梁对时局时刻保持的警惕。早在1896年,梁通过《变法通议》极力批评秕政,要求从民众的素质出发(“兴人才”),对现有社会制度(“变官制”)进行改造。这是梁氏思想的最初出发点,它直接预示了后来“破坏主义”主张的根本旨趣:“兴人才”意味着新民,“变官制”意味着打破君主专制。梁的这一观念在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时期,以及后来流亡海外的《清议报》时期,都得到了深入贯彻。
显而易见,梁提出破坏主张所针对的就是顽固守旧派,他们是当时社会前进的最大阻碍。对于流亡时期的梁启超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摧倒旧物(包括旧制度和旧文化)的“破坏主义”更能契合他的心境与处境了。然而,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新党的棼乱和腐败日益暴露,民众的无知与怯懦也愈加明显。梁深感破坏后可能造成“流弊无穷”的后果,旋即决定放弃“破坏主义”,“乃益不复敢倡革义矣”[12]214。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破坏思想之流变,既使得他不同于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同时又与后来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区分了开来。康有为“太有成见”,终其一生都奉行保皇的改良主义,要求以和平手段推行君主立宪;而孙中山等革命派则要求以激烈手段推翻满清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共和。梁启超则时常徘徊于二者之间。这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潮对于人心的深刻影响,同时又体现出梁对于国家现状与前途命运的独立思考。梁最后选择放弃“破坏主义”,并与革命派发生激烈论战,说明了他对待破坏主义的审慎态度。但与此同时,他对于时代的影响力也渐渐被激进的革命派所遮蔽,并最终成为了革命派的主要批判对象。
总之,梁启超的“破坏”思想始终都浸透着他本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深沉思考,同时又包孕着一种对于旧制度和旧文化的改造方略,以及对未来新时代新景象的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的“破坏主义”是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里最富于鼓动性和穿透力的政治口号,甚至影响到中国后来漫长的革命岁月。
注释:
①该书初版于1935年,由北平大北书局出版。受胡适、冯友兰等人的意见影响,郭湛波不仅丰富了对于近代诸思想家的具体论述,而且在1936年再版时将书名更为《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
②详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六章。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9.
[2]郭湛波.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
[3]梁启超.自由书[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2.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64.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96.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13.
[10]苏舆.翼教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24.
[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