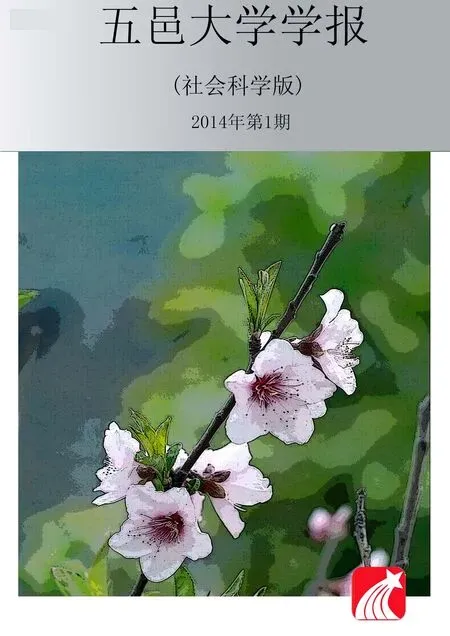中国近代翻译创新先驱伍光建
邓世还
(中央戏剧学院 戏剧文学系,北京 100009)
伍光建(1866—1943),原名光鉴,字昭,笔名君朔、于晋,广东新会人。他一生译著甚多,所译哲学、历史、文学书籍等共130余种、近1亿字。伍光建虽然译作丰富,却从未对自己的翻译经验作过片言只字的总结,只在对子女日常教育中,谈到过一些经验与方法。复旦大学伍蠡甫教授(伍光建三子)在《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中,记载了伍光建涉及翻译问题的谈话。我们今天只能依据这份记载以及当时作家、学者对伍光建译作的评价,来探讨他的翻译经验。以下主要从翻译方法、主体修养以及翻译与创作的关系三方面做一些研究探讨。
一、翻译方法的独创性
中国文化翻译历史悠久,多为宗教经书典籍。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就是一位佛经翻译大师。到近代,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留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翻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著作,翻译事业兴盛一时。但因为文化修养、外文水平的局限,以及译书经验的不足,很多对于西书中译的客观规律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误译、文辞不通、辞不达意等问题不少。所以到清末,大翻译家严复就提出了“信、达、雅”三原则。这是最初对西书中译试图作出客观规律总结的法则。
到上世纪20年代,身为作家、文艺评论家也是翻译家的茅盾,对西书中译方法做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到1937年,已写了近10篇专论文章。仅于1934年《文学》第2卷第3号就发表了3篇谈翻译的文章,将当时五花八门的翻译方法归纳为“直译”、“顺译”、“歪译”(以林抒为代表)、“意译”四类。同时,他对哪一类也归不进去的伍光建独创的“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写了《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和《〈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两篇文章,对伍译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两篇文章在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发现了伍译方法的独特性及其规律,将之总结为“节译法”或“删译法”。茅盾根据《侠隐记》(即《三个火枪手》)的译法,提出伍氏译法的两大特点:
第一,对原作从结构角度作出删削。茅盾指出:伍译本“第一,删削了一些不很碍及全文故事的结构的小小的子句,把复合句拉直,成为平行的几个子句”[1],而且是“有删削而无增添,很合于大众阅读的节本原则,不像林纾似的删的地方尽管删,自己增加的地方又大胆的增加;第二,是译者的白话文简洁明快,不是旧小说里的白话;第三,是紧张的地方还它个紧张,幽默地方还它个幽默,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办到的;而这一点使译本人人爱读”[1]。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谓的“有删削而无增添”,是在忠实于原作本意基础上的“删削”,而没有译者自己主观意念的“增添”。这就体现了“信”的原则。因此,尽管有所“删削”而无碍原作本意的传达。二是为什么要在“结构”上做些“删削”?茅盾的理解是:“我以为他是根据他所见当时的读者的程度而定下的。……因为他料想读者看不懂太累赘的欧化句法。”[1]他又举出小说主人公达特安出场时形象刻画的一段文字:“你想象他是一个十八世纪的堂吉珂德吧,一个没有他的胸甲,他的铁铠,他的肋甲的堂吉珂德吧。”伍译简化为只留下第一句话“此人年纪约十八岁”。为什么删去那些形容词?“因为他料想那时的读者不认识那位大名鼎鼎的堂吉珂德”。在伍译之前,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虽然在西方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可是小说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一般读者还不知道这位大人物。所以茅盾特别提醒读者、批评家:“我们应该原谅他在二十年前这种为读者着想的苦心。”[1]“为读者着想”,这就是伍光建独创这种前所未有的翻译方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一位大翻译家,心中永远想着读者,他翻译是给广大读者看的(不像他的老师严复译书是给“读古书的人”看的),他的翻译事业是为读者服务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第二,从人物刻画的角度作出节略与缩小。茅盾总结出伍译的另一个特点是“小段的节略和大段的缩小”,而这种“缩小”“对于原文的‘动作发展’方面没有什么改削;换句话说,他所缩去的部分都是描写景物的,至于写到动作发展的,他几乎是尽量保持着”[1]。“最精彩的动作描写,最能表现出人物个性的描写,他往往是几于直译。”[1]通过对《孤女飘零记》(即《简·爱》)的研究,茅盾总结出伍氏翻译法的三原则:“一,他并不是所谓‘意译’的,在很多地方,他是很忠实的‘直译者’。不过他用他的尖利的眼光判断出书中那些部分是表现人物性格的,那些部分不是的,于是当译到后者时,他往往加以缩小或节略。二,景物的描写和心理的描写,他往往加以缩小。三,和结构及人物个性无多大关系的文句、议论,乃至西洋典故,他也往往加以删削。这三个原则,从《侠隐记》到《孤女飘零记》是一贯的,这三个原则,使得伍先生的译本尽管是删节本,然而原作的主要人物的面目依然能够保持;甚至有时译本比原作还要简洁明快,便于一般读者——例如《侠隐记》。”[2]最后,茅盾说:“伍先生的译作,我几乎全部读过;我常常觉得伍译在人物个性方面总是好的。又在紧张的动作方面也总是好的。而对话部分,尤其常有传神之笔。主张直译的我,对于伍先生那样的节译,也是十分钦佩的”[2]。从上面的总结,可以看出茅盾对伍先生创新译法是多么重视,审视分析得多么细致深入。结合茅盾的评价和伍译的实践,可以发现伍译方法有两个独到之处。首先是伍氏那“尖利的眼光”——审美判断力。这审美判断力的准确锐利,来自他极高的文学素养,以及对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比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对话的“神来之笔”、人物动作的紧张性等,在翻译中是极难的课题,因之尤其见功夫。其次,在“尖利的眼光”的审视下,伍氏对那些无关情节发展、人物性格的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的部分,他常常是“加以缩小或节略”,而对那些和结构及人物个性无多大关联的文句、议论、西洋典故,则是加以“删削”。翻译时不同的处理,可见先生掌握分寸之确当。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之后,就使得作品的人物个性更加鲜明,永远处于行动之中,在动态中展示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推动了情节发展,使结构更紧凑明快。由于译作人物个性鲜活、生动,故事性强,引人入胜,伍译达到“人人爱读”的效果。这就是伍氏删译法或节译法的艺术魅力,是他创新译法的成功,它深刻地解释了伍光建所说“懂多少不一定就译出多少”的深刻含义。
除茅盾的总结外,伍光建翻译的独创性还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伍光建很好地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符合读者审美习惯。伍光建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饱学之士,深谙中国古典哲学家著作高度凝练简洁的笔法,加之他在英国留学以及对欧美多国访问期间对西方社会习俗、文化传统与艺术理念有广泛接触与深刻研究,这些学识修养就决定了他有可能对西方文学名著走出一条自己的西书中译的路。
中国古典小说都是以讲故事(情节的发展、起伏、延伸等)为结构方法,刻画人物性格多以人物的行为、举止、言谈(对话)等外部动作(含蓄地显示内在的品格、行为动机、情感等)为表现手法,尽量少写长篇议论、写景、抒情式的散文,以免冲淡主体(人物)、延缓节奏,如果文字又不精彩,难免读来寡味无趣。写人物内心活动、情感起伏跌宕、心理意念等等,也常常只有简短的几笔或以一首短诗、一阕小令来衬托。举几个个古典小说中的例子。如《红楼梦》林黛玉的《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诉尽内心深处的凄凉、伤痛和自己洁身如玉、坚贞高傲的品质。又如薛宝钗的《临江仙》,词中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显示了人物外表淡泊娴静、内心向往富贵荣华的隐秘情志。在“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一回,林黛玉与史湘云的联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不仅表现了人物的伤感情绪,而且对应了结海棠诗社时繁花似锦、诗兴盎然的盛况,曾几何时已是“联诗悲寂寞”,贾府盛极而衰了!再如《水浒》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英雄落难,天也欺人。林冲发配受尽折磨,来到山神庙时,“正是寒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到酒店沽酒,“那雪正下得紧”;在酒店喝罢酒,“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从“卷下一天大雪”到“正下得紧”再到“越下越紧”,仅一个“紧”字,步步加强语势,尽显雪势的猛烈。又用小草屋被雪压倒、火种熄灭等细节,突显了风雪之肆虐,茫茫雪野孤伶伶独行,令人对满怀悲愤而又身陷险境的主人公又将面临怎样的遭遇充满同情与担忧。多么精练的笔法,却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这样的艺术手法在优秀的古典名著中不胜枚举。伍光建正是汲取了优秀的古典文化精髓的滋养,将之化入文思笔墨之中,从而启发了他悟出西方文学名著中译的新路,使欧化句法变为民族化的语言,使译文更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做到“人人爱读”。
第二,伍光建的翻译方法具有前瞻性。伍光建不仅见多识广,而且具有洞察社会发展趋向的远见卓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要求文化载体表现新的文化内容,取代陈腐僵化的文字形式,宣扬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伍氏先生深知旧的文字形式必须随着文化内容的更新而变更,以适应新文化的需要。为寻找适应新内容的新形式,他独创以白话文翻译西方文学、哲学、史学名著,将先进的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青年——未来的社会文化主体。由于顺应社会前进的步伐,符合了时代精神,他的译作受到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伍译的巨大成功,早于白话文运动(1917年由胡适发起)至少10年,因此有学者称赞先生是“前瞻式”白话文翻译。茅盾说:“伍先生的白话译文,既不同于中国旧小说(远之如‘三言’‘二拍’,近之如‘官场现形记’等)的文字,也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白话文,它别具一格,朴素又风趣。”[3]胡适1918年在北大演讲时说:“我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伍光建笔名)所译为第一。君朔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别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作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抒百倍。”[4]致曾朴信中又说:“近几十年中译小说的人,我以为昭扆先生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严谨而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他。”[5]寒光则赞美伍氏的译文“都是百炼的精钢,胜过林抒百倍!”[6]叶公超则称赞伍译《诡姻缘》是“读者修来的福气!”[7]
伍光建独创的白话文翻译法将欧化语言转化为民族化语言,既符合时代的要求,也符合是读者的审美习惯,在新文化运动中为推动新文学的深入、普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二、翻译者的主体修养
如何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伍光建认为:“写好散文是锻炼译笔的基本功。”[8]4“写文章先从叙事入手,不急于描绘、抒情,久而久之自然干净利落而又有神采。”[8]4他进一步推荐多读古人、前人或外国人的书(当然都是经典作品),认为其对文章和译笔都有好处,至少不致拖沓、零乱、呆板。这里说了三层意思:首先是以写好散文来锻炼译笔,然后是文笔“干净利落”,最后还应有“神采”。而“神采”乃是文字的点睛之笔。仍以伍光建所译《简·爱》为例。茅盾举出第一章开头一段两种译本的不同:在冬季阴冷的午餐后与里德太太一家散步时简·爱的感受。伍译的“薄暮寒光中散步回来”,比另一个译本“在阴冷的黄昏回家”,“读起来就多些韵味”[2]。这“韵味”就是译笔的“神采”,它来自译者的文学修养、敏锐的感受和文字的锻炼(“炼字炼句”)。由此可见,现代口语译文的风格,也有文野、粗细、雅俗之分,生动流畅与晦暗生涩之分,译者只满足于字面的通顺,还是要求更高的富有“传神之笔”?这正是译本的文学价值和译者的思想修养、文化境界之所在。
在当下,翻译者已不可能大量研读古人、前人的经典之作,但还是应尽可能多读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的文学作品,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提高精神境界。所谓“功夫在诗外”,透过译笔,就能看出译者的文化素养和译文质量。
伍光建在谈到自己译书的选题曾说:“自己喜爱的,例如:把世故人情摸得很透,写来逼真;描摹真情至性,肝胆照人,倒不一定情节曲折,甚至离奇;笔墨细致,刻画入微,却不是大人物、大问题。”[8]5-6这个“标准”,在《侠隐记》、《简·爱》以及其他许多为他以白话文首先翻译介绍过来的文学名著那里得到了印证。这些观点,对今天也仍有启示意义。伍光建还提醒译者:“了解西洋,介绍西洋,不等于盲目崇拜,也要让读者看到西方社会那些肮脏东西。”[9]可见他对西方社会观察深刻、识见超前,对今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伍光建对文化交流的预见性和社会责任感,令人敬佩!
三、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人将翻译与创作比喻为“媒婆与处女”,当然很多翻译家都不以为然。伍光建认为:“翻译和创作犹如模仿和创新,并非决然两码事,而是相因为用。”[8]6他认为茅盾和曾朴的文笔甚佳,外文又好,可以翻译与创作并举,两方面都有好处,尤其对茅盾专事创作而丢掉翻译甚感可惜。
那么,如何理解伍光建的观点?翻译作品是通过译者的理解而艺术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风格,犹如艺术上的二度创作,其功力相当于文学创新。茅盾深谙翻译与创作之“难”:“大文学家创造一个角色出来,不仅有其特殊的思想和行动,亦有其特殊的口吻。一个角色前后口吻一致,这是作家的事,也就是翻译家的事!作家描写人生,欲使甲乙丙丁四位人物的口吻各自不同,还不是很难的;而欲使甲的口吻始终是甲的口吻,却不容易。翻译时便也一般。”[10]“真正精妙的翻译,其可宝贵,实不在创作之下;而真正精妙的翻译,其艰难实倍于创作。”[10]“要将一个作家的风格翻译出来,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需要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除信、达之外,还要有文采。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的创造性,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面貌,这是对文学翻译的最高要求。”[11]这是真正的“二度创作”,而且“其艰难实倍于创作”。当时的文化界对《侠隐记》译文的评价是:“用白话文,忠于原文,而生动乃同创作,人物豪爽,如读耐庵水浒。”这个评价,精辟地说明了伍光建译文“二度创作”、“相因为用”的重大特点:不仅“生动乃同原作“,而且是将欧化风格转变为民族化的文学风格。这一精论已经足够说明,伍光建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新时代赋予的文学革新因素相融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文学天赋,创造性地用他特有的白话文来“节译”或“删译”西方文学名著,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翻译风格在当时横空出世,独数一帜,具有有特定历史时期珍贵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如果说优秀作品鲜明的艺术风格犹如作家的“印章”,那么伍光建独特的译文风格就是他的“印章”。
仍然借用茅盾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1)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研究文学的人。(2)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了解新思想的人。(3)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有些创作天才的人。”[12]这不就是对翻译巨匠伍光建最准确的评价么!
参考文献:
[1]茅盾.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J].文学,1934,2(3).
[2]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J].译文,1937,2(5).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4.
[4]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86.
[5]胡适 胡适译短篇小说[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195-196.
[6]寒光.林琴南[M].上海:中华书局,1935:28.
[7]叶公超.诡姻缘·序[M].上海:新月书店,1929:4.
[8]伍蠡甫: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9]李净昉.步严复后尘的翻译家:伍光建名字不应被遗忘[EB/OL].[2010-09-16].http://www.china-
news.com/cul/2010/09-16/2538053.shtml.
[10]茅盾.“媒婆”与“处女”[J].文学,1934,2(3).
[11]茅盾.茅盾译文选集·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2]茅盾.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J].小说月报,19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