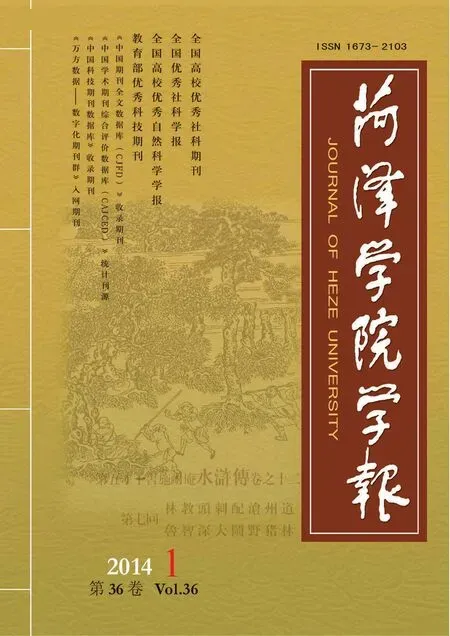程善之《残水浒》对水浒空白结构的发现与弥合*
孙 琳
(菏泽学院学前教育系,山东菏泽274015)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翘楚之作,它从问世之初便为诸多读者和专家学者所瞩目,尤其是在明清之际,金圣叹将其作为第五才子书加以修改和评点,更是推到了经典的位置。到了晚清民初,在众学者的推崇下,《水浒传》又一次作为经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晚清民初梁启勋(曼殊)在《小说丛话》中认为:“《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共认矣。然于二者之中评先后,吾固甲《水浒》而乙《红楼》也。”[1](P415-416)燕南尚生在《新评水浒传叙》中提到:“《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1](P391)最具代表性的是胡适提出了“四大名著”的说法:“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2]
在民国时期,小说创作成为时髦,“一部小说一旦畅销,小说家便趋之若鹜,竞相仿效。一位作家一旦成名,成为畅销作家,便常常按照市场的需求,连篇累牍,不断炮制作品。李定夷创作生涯不到10年,却创作了长篇小说40 多种。李涵秋在短短的15年内,就创作了1000 多万字的小说。”[3](P316)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既出名又畅销的经典之作《水浒传》,为人喜闻乐道,而其文本本身的召唤结构尤其是金圣叹腰斩之后剩余的空白,引起很多文人进行续作的兴趣。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水浒传》续书有十多部之多,像《新水浒》、《水浒新传》、《水浒外传》、《水浒别传》、《水浒中传》、《古本水浒》等,都站在时代的角度对水浒故事有一定的阐发,而其中在结构方面深具特色的是程善之的《残水浒》。
一、《残水浒》对水浒空白结构的发现
程善之(1880—1942),名庆余,祖籍安徽歙县,是同盟会会员和南社成员。他生于扬州,天资聪颖,在家庭的书香氛围中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少年时即意气纵横,早负才名。清末时于扬州府中学任教,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常有不满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言论,成为清朝地方官吏的严密侦查对象。在1913年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之役中,曾任孙中山秘书,后倡导成立扬州学生会,声援北京五四学生运动。历任《中华民报》和《新江苏报》编辑,发表大量时评和诗文。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力主抗日,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革命性思想和经历贯穿程善之一生,但另一方面,对于革命失败和民族危难的深刻体认也使程善之心情郁闷,对于国内军阀混战、有闲阶层醉生梦死等现象甚感失望,因此推崇佛道思想。
《残水浒》署名“一粟”1933年在《新江苏报》连载,后于同年10月出版单行本。该作从金批本70回卢俊义惊梦起,共分16 回,相对于其他水浒续作,篇幅相对较短,但结构完整,其结局又应对正史中宋江等36 人为张叔夜所擒的记载。《水浒传》作为长篇著作,在人物描写、情节安排方面限于时代和各方面原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缺疏部分。作者这些或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结构,给人以联想的余地,《残水浒》即紧紧抓住原作前70 回中的矛盾和不合情理之处,从人物经历的角度发掘性格的另一面,补上若干合理情节,将看似强盛至极的梁山泊从内部瓦解。而整书人物除张叔夜之外并没有增添,情节也基本上顺遂前70 回而行,仅就创意和结构而言在水浒续作中应属比较上乘的。正如秋风在《残水浒小引》中所言:“一粟之才,不及施耐庵;《残水浒》之文采,不及《水浒》,此无庸讳者。然而吾以为善读《水浒》者,莫如一粟。盖能利用前《水浒》之疵病,而一一翘而出之也。”[2](序2)《残水浒》确实准确地找出了《水浒传》中的空白点。
梁山泊好汉有108 人之多,《水浒传》从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人各一面的描写,但这么多人之齐上梁山尤其是还能安居其位却显得有点突兀。有些人物如官兵上山仅仅因为宋江虚情假意地跪拜、让位,有的人物仅仅因为一句“义气深重”或“星宿下凡”就甘心待在梁山,尤其是在排座次之后,难道真的没人能看出所谓天降石碣的人为性来吗?这应该算是水浒描写中的一种召唤结构,给人以联想的空间,但并不告知读者此后的结局,这正是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只留70 回却可令此书流传更广的聪明所在。《残水浒》的谋篇布局即源于108 人每人不同的想法与追求无法完全弥合所产生的矛盾。《残水浒》书名中的“残”字,一方面是指对水浒的接续,另外也寓分裂、破残、解散之意。马幼垣认为,《残水浒》“洞悉梁山集团人际关系之绝不可能长期和睦共处”[4](P228),“把重点放在梁山人马的派系冲突、私人恩怨,和其他内部矛盾,是民国水浒续书不可多得之作”[4](P186)。
《水浒传》一成书,扈三娘形象便备受争议。正如其绰号“一丈青”,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指的是“一丈青张横”,应指身材高大、肤色较深,而在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中题浪子燕青云:“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此处“一丈青”与大行春色联系起来,并指的是浪子燕青,则令人备感疑惑,到底是指某人,还是指春色无限?这两处至少说明《水浒传》中出现一丈青并非无因,而跟王矮虎搭配起来看,此处一丈青与矮应为对立,构成一种俏妻呆汉的特殊效果。在《水浒传》中,扈三娘身材修长、面目姣好,且一身武艺,却被宋江乱点鸳鸯谱嫁给了身材矮小、本领低微,最关键的是还贪财好色的王英,给读者留下了一个空白:二人的婚姻会幸福吗?此外,扈三娘在《水浒传》中一家老小除哥哥扈成外都被李逵杀掉,连自小长大的庄子都被抢光、烧光,这样的灭门大仇她知道吗?她心里难道没有什么想法吗?此外类似情况的还有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人,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但不是被官府,却是被他们每日里号称“义气深重”的兄弟们所逼迫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空白,留待后人去补充。
如果结合历史来看《水浒传》,会发现水浒故事的背景是大宋宣和年间国内奸党擅权、国外辽金虎视眈眈,而且跟北宋灭亡的靖康之耻隔的时间非常之近。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梁山众人的国家观念却没有得以凸显,仅仅靠征辽成功的那种意淫描写是无法迎合众读者的期待心理的。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很多情况无形中与《水浒传》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开放结构。
此外,对于晁盖与宋江的矛盾、董平杀人父娶其女的不义、石碣何来等问题在《残水浒》中也一一挑开点明,尤其是还创造性地对柴进这个大周子孙的心理进行了深入剖析,且用种种独特的方法将问题一一解决,弥合了《水浒传》中的空白。当然在续书的写作中,重点表达的还是程善之个人的某些想法,比如他对国家内忧外患的关注,对匪患横行的厌恶,对女性自主的期望与赞赏等。在《残水浒》中处处浸染着程善之本身所具有的因果循环思想,这也是他弥合《水浒传》空白所用的主要思想和契入口。
二、《残水浒》对水浒空白结构的弥合
程善之跟佛道的结缘在其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生母终生信佛茹素,另外在其自传性著作《倦云忆语》中提及他的表兄汪乐川善导引之术,年七十,犹有婴儿之色[5](P54),表兄汪仲伊自负遁甲奇门,七十余犹纳妾生子[5](P60),友人陈馨来、陈孝起等也皆好佛[5](P62),其三叔擅道家导引及画策驱蚊之术[5](P99)等。在这样的深厚的文化氛围中,程善之对佛道思想的接受也就顺理成章了。尤其是在1890年至1893年他的三兄、二兄、五兄、四嫂接连离世,1906年左右心爱的姬人孙氏紫云的早逝,更是加深了敏感聪慧的程善之对浮生若梦的思考。
在弥合《水浒传》空白结构方面,《残水浒》作为善读水浒者之作,很好地发掘了可供展开的情节因由,做到了与《水浒传》的前后呼应,并且掺加进了作者本身特有的佛道因果思想。如在《水浒传》中扈三娘被李逵灭门作为前因,扈三娘不但丝毫没有报仇的意图和表示,还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人才卑劣的矮脚虎王英,在此之后扈三娘基本上罹患了失语之症,只是在冲锋陷阵时一展身手,连成句的话都不再说一句,在因果观念看来,是为大缺憾。程善之在《残水浒》中设计了扈三娘杀李逵报仇的情节,并且当着宋江众人的面直承其事且质问众人:“当初公明哥哥三打祝家庄时候,我扈家因为小妹的缘故,特地讲和。那时公明哥哥将令,明明白白说,敢有动扈家一草一木者斩。……我扈家正为这个缘故,不加防备。不料这黑厮逞着兵势,杀进庄来,把我父亲、母亲和一门良贱,杀个罄尽……事后,公明哥哥也不曾加责罚。连丈夫王英也奉公明哥哥将令,不敢泄漏分毫……小妹虽然是报父母之仇,可是依着公明哥哥将令,这黑厮不是早就该杀吗?”[6](P72-73),原本失语之人一下子说了那么多话,而且开口都称“公明哥哥”,闭口即提“将令”,有理有据,不但令宋江只能脸色发青、干翻眼珠,连与宋江关系一向不错的朱仝都力挺扈三娘:“真正女英雄!我朱仝枉然为人,大半世怀恨在心,几次不好发作。贤妹,你真好气概!好胆量!我朱仝真正惭愧死!”[6](P73-74)在《水浒传》中天杀星李逵虽为人天真,但滥杀无辜,是为可憎,所谓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残水浒》落得个身首异处也算是因果循环,迎合了读者的部分期待视野。此外,像秦明祭奠亲人、程小姐毒夫报仇、林冲杀高俅父子等情节,也一一对应于《水浒传》中有因而无果之处,令读者心情大畅。程善之对于水浒人物经历和性格的把握也丝丝入扣,像卢俊义之上梁山的不甘,所谓“军官团”成员的内心挣扎与反抗等,都以一定的因果关系加以阐发,并直接促成了梁山的瓦解。
其次,在弥合《水浒传》显见空白的同时,程善之还结合当时的时代特点,将自己对于国事的关注加入其间。梁山事业兴盛之时,正值北宋末年,民不聊生,在小说中提到奸党弄权误国、四大寇为首的盗贼遍地,外有辽金的时常侵扰和觊觎,国土面积比秦唐之时缩水甚多;而程善之所处的清末民国时期,很多方面与之相似,在民国初年其作的《清代割地谈》中他痛陈国土丧失的悲痛之感,再加之当时“九一八”事变对国内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程善之将对亲日分子的憎恶加在了宋江身上。而《残水浒》中,程善之延续了金圣叹独恶宋江的观点,不但刻画了宋江的“假”,甚至增添了宋江企图投金的情节,这一点与《水浒传》的“忠义”观正好背道而驰,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作者忧心国家、痛斥汉奸的文学表达。在《残水浒》中,宋江同时脚踏两条船,派乐和走奸臣蔡京的门路,又派段景住、皇甫端走大金的门路,可以说这两条路都不是正途:蔡京的门路被栾廷玉和扈成设计堵死,而投靠大金的门路,在宋江看来,“只今接洽完备,将来大金进了中原,我们便是首功[6](P133)”,汉奸的无耻嘴脸表露无遗,作者借关胜之手刀劈了为卖国奔走的“卖国贼”金毛犬段景住,义正辞严地对众宣称:“我们梁山泊旗号是‘忠义’二字,须容不得石敬瑭、毛延寿一流人物。”[6](P134)这不但是关胜的心里话,更是身处民国的程善之对那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汉奸行径的极力控诉。国家危难之际,众多梁山好汉以卢俊义、林冲、武松、鲁智深为代表都投靠了种经略相公以报效国家,而宋江面对分崩离析的梁山局面,不得不领着一部分效忠于他的头领共36 人逃出水泊,但最终被张叔夜所擒,这样的结局与历史上的记载相吻合,也恰是程善之弥合《水浒传》疏漏的集中体现。
再次,程善之常年执掌教职,与新思想、新文化接触较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下,人性解放尤其是妇女的解放成为众多作家关注和表现的主题。像欧阳予倩在1927年发表的话剧《潘金莲》一改其淫妇形象,赋予其追求爱情、蔑视封建礼教的现代观念,并深入人物内心探讨人性问题。在程善之的《倦云忆语》中,他借鉴了《浮生六记》中对家人尤其是对心爱女子的爱恋之情,更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尊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及的女弟子许幼钦,不但聪慧超人,且为人“刚急”,“正直无私曲”,并“余私意中原女权不振久矣,郁极思伸,其在斯乎!”[5](P83)可惜的是此人因病早逝令人叹息。在《残水浒》中,程善之不但深刻揭示了不同出身、不同经历的好汉们不同的人生追求,令梁山为之分裂解体,更重要的是还一改《水浒传》里对女性的贬低和漠视,大倡女权,不但给了扈三娘独立报仇的机会和话语权,更给了弱女子程小姐强烈的现代女权意识。《水浒传》里程小姐只是作为招降董平的一个引子存在,风流双枪将董平贪图程小姐的美色而献城投降,且第一时间里抢到程小姐并杀了她的一家老小,这样的仇恨不弱于扈三娘,而程小姐报仇举动的激烈程度更是远远超过扈三娘对李逵的枭首。程小姐本来怀了董平的骨血,只因“自己要儿孙,就不该害人的父母;杀了人的父母,还要替你养儿孙,天下有这等便宜事”[6](P98),便自撞桌角而落胎,这样的烈女子不能不说已经深具现代独立意识。程小姐先是绝了董平的后,又下毒于董平,发出振聋发聩的女性独立宣言:“休道妇人失了身,就不得不受人牢笼。须知失身不是失节,失身是没有力量,失节是没有志气。没有力量,是无可如何的,志气不改,总有一天,复仇的机缘到手。没有志气,跟贼党,替贼效力,那才是下等人,才算失节呢!”[6](P100)这样的表达不但令饱受压迫尤其是在《水浒传》中饱受压抑的女性张目,更是令众多男子汉汗颜,宋江背后即有人愤然长叹:“真正烈女,羞杀我们也!”[6](P101)宋江不敢回头看到底是谁发出此叹,相信当时的不少读者也不敢深究。这样的举动,这样的话语以现代性的思维和语言弥合了《水浒传》对女性的压抑之憾,也表现了水浒续书独特的时代价值。
三、小结:程善之的爱国与因果思想
《残水浒》作为续书,整书弥散着程善之个人独特的爱国与因果思想,而这又是在作者深入探究《水浒传》疏漏的基础上的时代之作,既有对水浒空白结构的发现,又有个人志意的表达,更重要的是时代性在作品的展现,可谓是续书中的精华之作。在程善之的很多其他作品中也都体现出对国事的关注和佛道因果思想。如在《自杀》中,整篇小说都是叙述人自问自答,没有小说中常见的情节和环境描写,最终认为“世界无一不秽”,故只能自杀;在《机关枪》中则写到某中国军队的副官和军需等人为了私人利益向日本人购买劣质机关枪,在试枪的靶场上百般掩饰,事成后又与日本人同往妓院花天酒地;在《健儿语》中,描写一位革命者为建立民国甘洒热血,但革命暂时成功后他不甘与投机者同流合污而穷困潦倒,因生计无着仗刀去抢当铺,被官府杀害。在很多作品中,程善之都体现了对于革命不成功的失落感,满纸间渗透着一种宿命感。
王钝银在《小说丛刊》“序”中称赞程善之的小说做得好,说他“怀抱非常之才,郁郁不得志,乃本其生平所阅历名山大川人情世故——托于文章,激昂慷慨,褒贬劝惩,以抒写其胸中蕴积之气,而补救人心,启发知识之功,亦于是乎收焉。是岂寻常所谓小说家者所能望其功业哉”[3](P316)。此评价恰能指出程善之《残水浒》的创作出发点和杰出之处。当然《残水浒》并非完美之作,一来篇幅较短,仅仅16回就结束了水浒一百单八人的各自归宿,情节方面未免过于简略,跳跃性过大,给人以简单武断之嫌;此外对人物的刻画无法与《水浒传》相媲美,且人物性格尤其是宋江、吴用等人给人变化太大,在投金一事上不太合理,当然站在特殊时代背景上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借小说表达对卖国者的憎恶;还有就是语言方面,一些现代性过强的词汇像“军官团”、“委员”等,虽然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事实,但与整体风格有些不太协调。总体而言,《残水浒》作为《水浒传》的续书,结构独特,情节完整,深刻指出了水浒中的某些空白点,能够帮忙人们更好地理解《水浒传》,另一方面作为程善之本人的愤世之作,也很好地表现了他的爱国与因果思想,是一部难得的水浒续作。
[1]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G].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2]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J].新青年,1917,3(4).
[3]陈伯海,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幼垣.水浒论衡[M].三联书店,2007.
[5]程善之.倦云忆语[M].文艺小丛书社,1933.
[6]程善之.残水浒[M].新江苏日报,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