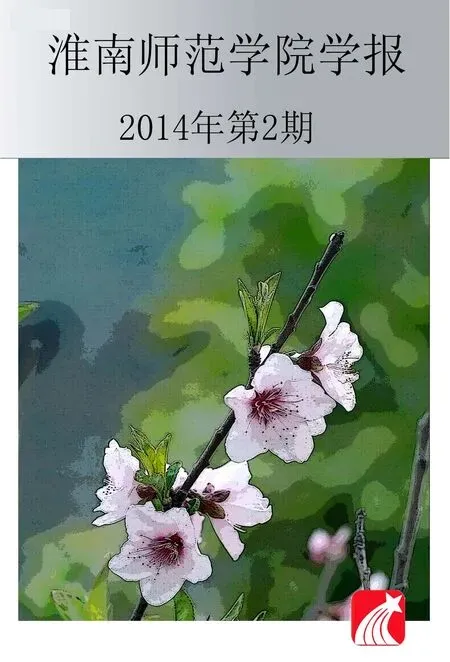论黄梅戏中舞蹈语汇的来源
陆娟
(安徽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黄梅戏是全国的五大剧种之一,她起源于100多年前安徽省安庆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时间若再往前推,可以追溯到在地理位置上与安庆搭界的湖北黄梅地区的采茶调。采茶调并不是黄梅戏,但可以说,采茶调应该算是黄梅戏的长辈。采茶调流入安徽地区以后,与安徽本地的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遂产生了黄梅戏。
在中国的20世纪50~60年代,黄梅戏如初长成的乡野二八少女,淳朴、热情、真诚、自然,乡村气息浓厚,从而广受城乡人们的欢迎,在那个时代,黄梅戏着实火了一把,在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的舞台上,黄梅戏如浪潮般席卷了人们的视野,《夫妻双双把家还》、《谁料皇榜中状元》、《对花》这样的经典黄梅戏唱段,到现在人们还是耳熟能详,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能哼上一两句。
黄梅戏影响力之所以这么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优美、婉转的唱腔,但除此之外,舞蹈表演也为黄梅戏的精彩表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研究黄梅戏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黄梅戏中的舞蹈主要由安徽以及相邻的湖北、江西当地的民间舞蹈,京剧、昆曲等其他种类的戏曲中的一些舞蹈,以及新创舞蹈三部分组成。
黄梅戏舞蹈虽然尚未自成体系,但她在黄梅戏中起着很重要的衬托作用,是黄梅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深入挖掘黄梅戏舞蹈语汇的来源,总结黄梅戏舞蹈的特点,为研究安徽省戏曲舞蹈提供参考借鉴的资料。
一、民间歌舞
在黄梅戏剧作家陆洪非先生的 《黄梅戏源流》中介绍,黄梅戏的雏形,是黄梅采茶调与多种民家艺术形式相结合产生的,有歌,有舞,有情节甚至有对话的小型节目。①陆洪非:《黄梅戏源流》,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1页。湖北的黄梅县是个面水背山的地方,历史上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尤以水灾为重。据黄梅县志载,明清时期,黄梅地区就发生过数十次水灾,水灾一来,乡民们就民不聊生,四处逃散,灾民们有的会唱一些采茶调,以此谋生,便将采茶调带出了家乡,完成了采茶调向外传播的过程。但这时候的采茶调还只是一种民歌小调,并不是戏曲,其他民间艺术形式的加入促进了采茶调向黄梅戏转变的过程。
在灾民们外出卖唱谋生的过程中,除了以板击拍清唱,还利用“道情”、“花鼓”、“连厢”、“罗汉桩”、“送傩神”、“莲花落”等民间艺术,充实演出内容。比如黄梅戏的传统表演中吸收了“打花鼓”和“花鼓灯”的舞蹈身段,演员常用的“手巾花”、“扇子花”与花鼓灯的某些小花场中舞弄手巾、扇子的手势、身段如出一辙。
陆洪非先生曾经说过:“黄梅戏中的舞,主要就是黄梅戏在形成之前就保存于民间的推车、高跷、跑马、旱船、花篮、采茶等等之中的民间舞蹈。”虽然这句话并不完全准确,但是至少在黄梅戏形成初期,情况是如此。这些民间舞蹈在“两小戏”、“三小戏”阶段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载歌载舞、轻松活泼的黄梅小戏如《闹花灯》、《打猪草》等常演不衰,长期受到观众们的欢迎,成为黄梅戏表演风格的典范。但是出现本戏以后,这些民间舞蹈即吸收消融在台步、身段之中,即使有按原样保存下来的,也只是作为一种调剂气氛的穿插,不再起到主要作用,用以衬托黄梅戏的表演。②比如,在《无事生非》的第一场,李侯府张灯结彩迎接唐侯大将军凯旋归来,四个小姑娘站在四个小伙的肩头,高高放下彩绸,还在台上绕场一周,是用花鼓灯的站肩渲染喜庆热闹的气氛,新颖而得体。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黄梅戏中的民间舞蹈部分形成于黄梅戏之前,在黄梅戏的形成初期,尤其是在两小戏、三小戏阶段,给了黄梅戏较大的支持。在这个阶段,黄梅戏自身的舞蹈语言还相对单一,除了一些可以直接拿来用的民间舞蹈之外,表演唱的演员会根据相应情节辅以对应的动作、身段和表情,但这样的辅助动作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舞性,只不过是让演员们看起来不那么呆板而已。稍微复杂一点有一种叫做“杨花摆柳”的表演形式,也就是演员在扭动身躯的同时舞动手巾帕。这些黄梅戏发展早期出现的、相对随意的舞蹈动作,就是黄梅戏舞蹈的最初形态。而到了黄梅戏出现本戏之后,民间舞蹈的部分就逐渐减少了,至少,在表演中不会随便什么舞蹈都拿来使用,而是有选择地使用,并且在使用时经过加工、改造,以能融入剧情为主,这体现了随着黄梅戏艺术的发展,对其中舞蹈内容已经有了一定的要求,对民间舞蹈的依赖也较前期减少。相对应的,在这个时期,黄梅戏老艺人开始有意识地向其他较为成熟的剧种吸收舞蹈语言。
二、其他剧种的舞蹈语言
戏曲艺术通常需要通过唱、念、做、打(在黄梅戏中主要是舞)等手段来表现,缺少了任何一样,都会削弱整体表现力。自黄梅戏诞生之后,随着她的演出形式由简单到复杂,演出角色由少到多,演出范围由乡村到城市,黄梅戏中从民间歌舞中直接移植过来的舞蹈就不够用了,因此,早期的黄梅戏艺人开始有意识地向其它较为成熟的剧种学习、借鉴包括舞蹈在内的表演方式,从而拓展黄梅戏的表现手段,最后形成黄梅戏所特有的唱、念、做、舞相结合的表演方式。
对黄梅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有青阳腔、徽调、京剧、昆曲等。在剧目、唱腔、表演、服装等方面,黄梅戏都从其他剧种中广泛吸收营养。此外,黄梅戏表演行当体系方面,随着黄梅戏本戏演出逐渐增多,在参照青阳腔和徽调等大剧种的前提下,早期的黄梅戏老艺人对生、旦、丑为基础的角色行当进行扩展、细化,从而大大提高了黄梅戏的表现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黄梅戏的不断发展,她开始逐渐向京剧靠拢,除了学习京剧精细的角色分工,更吸收了大量的京剧古典舞蹈身段融入黄梅戏中。在黄梅戏中直接来自于京剧的舞蹈动作有:云手、台步、云步、跪步、卧鱼、整冠、理髯、整鬓、抖袖、翻袖、扬袖、吊毛、抢背、打背躬等等。由于戏曲表演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这些程式化舞蹈语言融入黄梅戏中并不是太难。但是各剧种之间的表演又存在着一定差异性,因此,在借动作的同时,老艺人们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比如,在成功塑造《天仙配》中的董永角色后,王少舫有一段话能让我们看见他们在将京剧舞蹈语言黄梅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董永不能归到武生行里去。小生行的台步是书生走的,不能用。像话剧那样,又不甘心。我想来个‘创造’吧!把小生的四方步改一改,一般的四方步要亮靴底,董永哪有那个闲工夫,不亮了,四方步慢慢吞吞的,文绉绉的,我就让他来快点,粗犷一点……我想把他演得的像个农民,不仅在台步上,一些细小的动作我也尽量去模仿农民。”①王少舫:《我演董永》,《中国电影》1956年第3期。由这个小的细节可以看出,黄梅戏这个植根于乡土的戏曲,有别于京剧、昆曲等,她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那就是浓浓的乡土气息,比较贴近群众生活,如果把董永演绎得像的书生或者是公子,七仙女演绎的像个大家闺秀,那就缺少了黄梅戏特有的味道,那也就不是黄梅戏了。所以说,黄梅戏舞蹈的特点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而如果想让舞蹈动作和谐地融入黄梅戏表演,也必须掌握这样的特点,要相对真实地演,不能太阳春白雪,也不是一定要下里巴人,而是要贴近生活,真实地反映农村生活。
在向其他兄弟剧种学习方面,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老艺术家的名字,那就是严凤英同志。严凤英是黄梅戏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成功演绎了几乎所有黄梅戏的经典作品 《小辞店》、《何氏劝姑》、《蓝桥会》、《夫妻观灯》、《打金枝》、《借罗衣》、《天仙配》、《打猪草》、《牛郎织女》、《女驸马》等,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有有关黄梅戏表演的知识,她都是边演、边学、边悟出来的,她天资聪颖,学戏一学就会,还很勤奋,只要是她认为有用的东西,都会虚心请教,甚至向自己的学生请教。但是她命运不济,没有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最终只能在唱尽人间悲欢之后香消玉殒。但她的学戏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梅戏的成长过程,她曾经的辉煌,也正好是黄梅戏的辉煌时期,通过她的学习、感悟,也促进了黄梅戏的个性化形成,
在陆洪非先生的《黄梅戏源流》中提到:“严凤英像辛勤的蜜蜂一样,除了向本剧种的老艺人学习,还不断从兄弟剧种的艺术家身上吸取养分。”严凤英不仅深入揣摩学习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表演,还向粤剧演员红线女学习她“干净、大方”的身段,但她也强调“决不让观众感到仅仅是些优美的身段和舞台上活动,而是人物的思想在舞台上冲击,发出灿烂的火花”,严凤英十分肯定歌唱和舞蹈身段在表演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更加强调人物的思想,认为如果没有人物的思想,则技术就会没有生命。表演也就失去了意义。可见,严凤英的表演之所以能那么动人,除了因为她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更在于她是一个能够用心、用思想去表演的人。
严凤英还曾经向北方昆曲的著名演员白云生学习昆曲身段基本功,特别是在指法方面。她还向一个叫张慧的老师学习昆曲《思凡》中小尼姑舞云帚的片段,还有《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剑舞,为她在日后的黄梅戏表演中积累了一定经验。严凤英还“向范瑞娟学习她扮演梁山伯的潇洒、文雅的小生身段和台步,向金彩凤学习她在《盘夫索夫》中扮演严兰贞的感情处理和水袖运用。”严凤英不仅向自己的同事、朋友学习,还曾经向自己的徒弟学习。比如,她曾向自己的徒弟王毓琴学习朝鲜舞蹈,向田玉莲学习扇子功,向徐自友学习川剧舞蹈身段等。②陆洪非:《黄梅戏源流》,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06页。在这里我们一方面是看见了严凤英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黄梅戏在像严凤英这样老艺人的努力下,吸收了众多其他戏曲艺术的表演方式,可谓是博采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当然,在严凤英的表演生涯中,最重要的还是她在黄梅戏创新方面所做的贡献,在舞蹈方面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在黄梅戏舞蹈的发展过程中,艺人们主观希望能提高表演水平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黄梅戏艺术的发展,正是通过他们忘我的学习和创新,才使得黄梅戏表演形式更加丰富,从而给黄梅戏艺术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财富。同时,由于黄梅戏是一个新生剧种,所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并且由于它的乡土风格,决定了它几乎没有太多的约束和规范,也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很多其他剧种的舞蹈程式化动作,在黄梅戏中都可以尝试使用,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适当加以改造以适应当时、当地观众的需要,从而达到丰富黄梅戏表现手法的目的。
三、自创性舞蹈语言
在《天仙配》的《路遇》一场中,严凤英在表演一个村姑化的仙女时,也采用了她自己独创的表演方法,变斯文秀气的表演为泼辣、大胆但又不失少女风范的表演方式,真实地表现了一个既有点野性、又很纯真的少女形象。
黄梅戏虽然脱胎于民间歌舞,吸取中国其他剧种的营养得以成长,但是并没有丧失掉自己的个性。相反,她就像一个穷苦出生的孩子,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却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创性的舞蹈语言体系。
黄梅戏早期的表演,没有一套固定的程式,舞台上的行动,除了演员们辅助性的扭动身体或者舞动手帕,各种舞蹈表演主要依靠对生活的模拟。各个行当的演员,平时都得留心相对应人物的观摩。由于尊重生活,各种人物演来都比较生动、活泼。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早期黄梅戏演员大多都是穷苦人家出生,所以,在黄梅戏里,不论是天上仙女,还是闺阁小姐,无一例外都带有农村姑娘的味道。同样,黄梅戏舞台上的秀才们也大都带有农民的气质。演员对人们熟悉的、生活中常见的动作,总是留心观察,仔细揣摩,经过提炼后搬上舞台。除开门、关门、上楼、下楼外,还有推车、行船、担水、纺纱等等一些来自生活的动作,又是戏中经常用的着的,一经搬上舞台,往往为观众认可,也就被同行接受,推广流传。如果说每个剧种都有表演程式,那么这些来自于生活的推车、行船、担水、纺纱都可以算是黄梅戏的表演程式。
比如,在《推车赶会》中,集中表现了推独轮小车的过程,并使之舞蹈化了。其他戏中遇到推车时也选用其中某些动作。如《罗帕记》中神仙变的车夫送陈赛金逃难,也是旦坐在独轮小车上,丑推着车跟在后面,二人就着锣鼓点子一推、一晃地向前行进。再比如挑水,演员在表演挑着空桶的时候是什么形态,装满水的时候又是一种形态;去井边挑水是一种形态,去池塘边去挑水又是一种形态;到干净的河里打水是一种状态,到有水草的河边打水又是一种形态。
总之,黄梅戏老艺人通过把生活中的动作加以提炼就变成了舞台表演,甚至直接演变成舞蹈动作,尽管有些表演显得粗糙、杂乱,没有青阳腔、徽调和京剧那么精致,但是,因为直接来自于生活,所以也相当具有生命力,从而受到观众的欢迎,同时也形成了黄梅戏舞蹈语言的特点,那就是真实、不做作、朴实,不虚浮、笨拙却不失可爱之处。比起黄梅戏发展初期的仅仅扭动身体、舞动手帕而言,这是的舞蹈在黄梅戏表演中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四、其他
在黄梅戏中还有一部分内容为武打和杂技,但因为早期黄梅戏演员大都是半职业性的,因此缺少系统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尤其是有关身段、腰、腿、顶的真功夫。他们大都是跟着其他大剧种学习些花架子,即使是在打斗场合中,也是“好似儿童嬉戏,不要求强烈紧张,而强调轻松愉快,”①陆洪非:《黄梅戏源流》,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没有深厚扎实舞蹈基本功。归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早期黄梅戏缺少科班出身的演员,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黄梅戏本身并不追求高超的身体技能,观众们希望在戏中看到的是自己真实生活的反映,而不是太脱离生活的东西,黄梅戏的乡土气息决定了她更加看重生活的情趣,无论演出形式还是演出内容,都更加追求贴近生活,而不是单纯的炫技。
综上所述,黄梅戏舞蹈脱胎于民间歌舞,又广泛吸收了其他剧种的舞蹈语言,最重要的是黄梅戏根据自身的特点,提炼出了属于自己的舞蹈语言,在这几方面的作用下,最终形成了完整的黄梅戏舞蹈语言体系。
黄梅戏的舞蹈语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
首先,在黄梅戏小戏中,对民间歌舞的采用较为直接,基本以民间舞蹈的原貌为主,但在黄梅戏本戏中,民间舞蹈的比重降低,而且对于动作的选取要符合剧情的需要,基本以烘托气氛为主,同时能融入剧情的舞蹈性动作增加。
其次,在黄梅戏本戏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剧种的舞蹈动作,主要以古典舞舞蹈语言较多,不仅有身段、台步、指法、武功,还有各种道具舞。吸收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舞内容,也是黄梅戏成长为大剧种过程中一个必须的过程。
最后,在定位黄梅戏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有那些来自生活动作的提炼和创新。安庆地区地处安徽的南部,出于对农耕生活的需要,这里的农村多二层楼房建筑,山多、水多、竹子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特定的生活和劳作方式,生活和劳作方式又决定了特定的表演内容,那些开门、关门、上楼、下楼、推车、担水、纺纱,以至于表现的戏剧内容如《打猪草》、《夫妻观灯》等,都来自于当地特定环境所产生的情节,即使是《天仙配》、《牛郎织女》这样的剧情,也主要以农村生活为背景,演员在剧中的表演也离不开现实生活的体验。
黄梅戏之所以好听、好看,与黄梅戏表演艺术中充分融合了诸多舞蹈元素为其服务有很大关系,不管是民间歌舞、古典舞身段、自创性舞蹈动作、只要能适合表现的、符合黄梅戏特点的都可以拿来用,当然,黄梅戏舞蹈想要更长远、更好地发展,还要更多更深入地研究它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1]王少舫.我演董永[J].中国电影,1956,(3)
[2]安徽省艺术研究所.黄梅戏通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350
[3]陆洪非.黄梅戏源流[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406
[4]王长安.黄梅戏志[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5]《中国戏曲志.安徽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安徽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1993
——严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