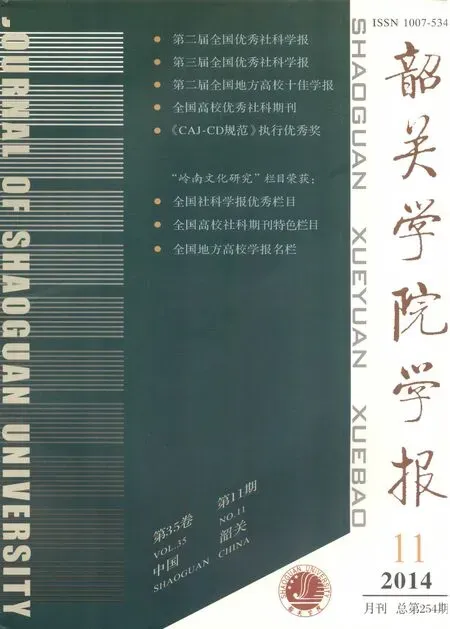读者批评视阈下的汉赋批评与理论
黄东坚,赖雪芳
读者批评视阈下的汉赋批评与理论
黄东坚,赖雪芳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汉代达到鼎盛时期,而从古至今的读者对汉赋有着褒贬不一的复杂态度,不同的汉赋作者对汉赋创作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主张。通过期待视野、召唤结构及隐含的读者等读者批评的视角,或许能够对存在较大分歧的汉赋批评与理论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把握。
汉赋批评与理论;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
相对于浩如烟海的古代诗话、词话等诗词批评,汉赋批评显得较为单薄,这既与几种文体所拥有的作品多寡有关,也与其受重视的程度有关。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几种主要韵文体诗、词、曲、赋中,赋可能是受重视程度较低的一种韵文体,而且由古至今的读者对其评价存在较大的差异。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读者批评理论,是一种以读者为主要关怀对象的批评理论,利用读者批评理论,能够更好地探析汉赋批评与理论中所存在的较大差异。
一、期待视野与汉赋批评
“期待视野”理论是德国理论家姚斯提出的,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与海德格尔及伽达默尔所共称的“理解视野”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一系列理论认为,读者在进行文本阐释时肯定带有“先见”,读者对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阅读的重点,决定对作品的褒贬态度和评价等一系列接受特征。期待视野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汉赋批评中的较大差异现象,汉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汉代就获得了无比尊崇的地位,其思想准则成为众多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行为标准,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就不免受到当时儒家强烈的诗教传统的影响。
汉赋作为文学艺术形式,自然要追求形式美、艺术美,但是受到当时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免也要对儒家的诗教传统回应一番,所以在汉赋作品中就会看到非常不协调的两部分被强扭在同一篇作品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其前部分大篇幅地铺陈赞美诸侯与天子游猎场地的广大与富饶,其中作者极尽铺陈与夸张之能事,极力渲染,堆积辞藻,篇幅宏大以致结构臃肿,“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1]88。而且赋作后面总喜欢加上一小段讽谏君王的话语,但那只不过是为了附和一下儒家的政教要求,与全文铺张夸饰的主要内容并不合拍。《天子游猎赋》在结尾部分借助虚拟人物亡是公之口说皇帝意识到自己的穷奢极欲并决心立志节俭: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乃解酒罢猎。[1]92
这些曲终奏雅的笔墨与整篇作品铺排扬厉的行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样的讽谏是通过文中的虚拟人物说出的,讽谏意识太过于隐晦,与直接讽谏或者以巧妙的委婉方式讽谏的方式相比,显得几乎没有讽谏的力度。相当部分汉赋作品缺乏思想性固然与汉赋的文体特征是分不开的,汉赋对景物注重客观描摹而不遗余力,极力搜求、罗列、刻画各种景物,必然影响作者对作品思想方面的顾及。
对于汉赋作品这种如上所言前后部分内容不协调的现象,秉持不同期待视野的读者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扬雄批评司马相如作赋不能达到讽谏的效果:“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2]3575
扬雄是一位笃信儒家诗教传统的辞赋家,他在《法言·吾子》篇中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3]49的著名论点,他赞赏“诗人之赋”的“丽以则”,否定“辞人之赋”的“丽以淫”,因此“诗人之赋”虽然“丽”却能坚守诗教“则”的传统。另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提到:“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2]1756
班固作为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是颇有经学造诣的学者,他向来是以正统的儒学卫道士自居。那么在他阅读汉赋的期待视野中,自然希望作品能够符合儒家的诗教要求。但是,在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中,显然其中的讽谏效果并没有达到儒家的要求,因此会受到班固的批评。相对于扬雄与班固对汉赋作品不符合诗教传统的的大力否定,司马迁与汉宣帝对汉赋的评价在今天看来是较为公允的。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对司马相如赋的评价是:“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4]3073司马迁在这段话里认为司马相如赋已然达到了儒家的讽谏要求,司马迁得出这样的阅读结论跟他的期待视野是分不开的,同为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不同,司马迁并不固守儒家的思想准则,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甚至是偏离儒家要求的,这在其创作的《史记》中有很多地方能够体现,他的这种倾向甚至还受到后来者班固的指责。正因为司马迁不固守儒家的条框要求,所以他对司马相如赋的讽谏要求也并不如班固那么严格。另外一位对汉赋有较为公允评价的批评者是西汉皇帝汉宣帝,《汉书·王褒传》里提到汉宣帝曾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2]2829汉宣帝作为帝王,在他的期待视野里首先是把辞赋当作娱乐工具来看待的,因为他不可能指望一些地位低下的辞赋家的赋作能够给他带来什么讽谏作用,所以说“以此虞说耳目”,但是他作为尊崇儒教的汉朝皇帝,想要赞美辞赋,就必须把辞赋与儒家要求联系起来,所以说辞赋“尚有仁义风谕”。
结合期待视野理论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汉赋批评理论里面的不同声音产生的原因,还可以为现代人更为完整地评价汉赋提供契机。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循环”理论指出:“部分须在整体上才能理解,整体也必须靠部分才能获得。正因为如此,后人的解释肯定要优于前人甚至作者本人,因为后人面对的整体更大。”[5]225的确,在前人汉赋批评的基础上,现代学界对汉赋的评价应该说是更为全面的。现代人对汉赋铺陈有加、讽谏不足特点的批评定然不会如班固、扬雄那样偏激,也不像司马迁、汉宣帝那样拐弯抹角的表示赞赏,因为现代人已不是生活在汉代那样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文化环境里,对汉赋的批评根本不需要以儒家思想为准则。再者,批评的重点已不再是汉赋的讽谏效果如何,而是它的艺术特色如何,或者它的题材、它关注社会的程度如何等等。前面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影响后面的读者,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品的接受经验被历代读者加深、发展、修正甚至推翻,但是无论如何,前人不同期待视野下的汉赋批评,都是后人加深汉赋批评的重要铺垫。在姚斯看来,每一个时代的读者之间存在着严密的历史联系:“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证实。”[6]25
二、召唤结构与汉赋批评
在中国古代各体文学中,相对于诗、词等,赋的受欢迎程度是略逊一筹,甚至作为赋体文学代表的汉赋更是屡遭指责,较多的指责包括:汉赋作为一种庙堂文学,多歌颂而少“风谕”,观赏性强而现实性弱,铺陈过多而导致结构呆板、臃肿,奇字僻字过多而难以阅读,题材较为单一况且因前后模仿沿袭过多而导致缺乏新意,等等。对于汉赋所处的这种尴尬地位,如果通过伊瑟尔的“召唤结构”加以分析,其中的原因似乎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伊瑟尔把文本中的“不定性”规定为它的召唤性……文本的“不定性”专指对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质疑,因此,伊瑟尔轻视消遣性、通俗性、说教性文学,因为这些文学形式对社会传统、道德规范多采取顺从的态度,从而削弱文本结构的召唤程度”[5]231。
首先,有很多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汉赋作品是可以定性为消遣性、说教性作品的,它的铺陈辞藻、刻意搜寻奇字僻字、忽视社会现实并导致层层相因的写作倾向完全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例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是为了献给汉武帝作为娱乐消遣作用的,况且其效果不佳的讽谏目的不仅不是对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质疑,反而是一种顺应,这样就会导致汉赋“不定点”的数量较少,审美效果减弱。但是,“召唤结构”仅仅是作为评判作品审美效果的一种测量标准,并不说明汉赋就缺少文学价值,毕竟汉赋还是作为汉代一代之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从汉赋文本中,可以看出汉赋对儒家诗教传统的逐步摆脱,转而对文学自身艺术特色的不断探索与追求。可以说,汉赋是中国文学逐渐走上自觉道路的重要发展阶段,而这正是汉赋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的体现。
三、隐含的读者与汉赋创作论
“隐含的读者”是伊瑟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预含使文学作品产生效果所必须的一切情感,这些情感不是由外部客观现实所造成,而是由文本所设置。因此隐含的读者观深深根植于文本结构之中,它表明一种构造,不可等同于实际读者”[5]232。
可以说,隐含的读者是作者创作过程中所预设的理想读者,是为了检验作品艺术效果的读者模型。既然隐含的读者是表明一种结构,而且“不是具体历史境况下的个体,而是一个超越历史的思考者,他的思维活动……不论何地都千篇一律”[5]235。显然,“隐含的读者”是要求理想中的读者能够对某一类型或者某一篇作品会做出相同或者相近的反应。其实,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如果是放在现实中,或许会有部分实际上的读者会达到这种状态,但是肯定不是全部。就好比如汉赋部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会提出他们的创作主张,其实他们的主张可以说就是他们创作中的一种构造,包含有隐含的读者在其中。首先,司马相如曾经说过:“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以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7]65按照他的理论,作赋就是在广泛的空间里,以华丽的词采尽情地铺排、罗列事物,客观描摹万象以使文章产生宏大的气势,这种主张只涉及到汉赋创作的艺术追求;其次扬雄所主张的“丽以则”是兼顾了汉赋创作的艺术追求及儒家的诗教传统;而班固在《两都赋并序》中主张辞赋创作要“兴废继绝,润色鸿业”[8]2,这种主张下的汉赋作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为了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以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的创作主张为例,可以看到其中都有“隐含的读者”的影子,他们都希望他们的主张可以转化为创作结构并得到读者的认可。但是事实上,当他们的理想读者转化为实际的读者之后,他们各自的主张都是仅仅得到部分实际读者的响应,况且他们各自所拥有的实际读者肯定是存在多寡的差别,这既与不同读者的不同期待视野有关,也与这些不同主张下所产生的不同类型的作品本身“召唤结构”的不同也有关系。
总而言之,以读者批评理论的视角来探析汉赋批评与理论,对于更加清晰地了解存在较大差异的汉赋批评与理论的原委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龚克昌.全汉赋评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8.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073.
[5]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姚斯.走向接受美学[M]//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5.
[7]成林.西京杂记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65.
[8]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
The Criticism and Theory on Han F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er Criticism
HUANG Dong-jian,LAI Xue-f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500,Yunnan,China)
Fu is an unique literature style in Chinese history,it reached its heyday in the Han Dynasty,but historically the reader has a complicated attitude mixed on Han fu and different authors of Han Fu also have their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bout the creation.Through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Calling Structure and Implied Reader and other Reader Criticism perspectives,perhaps we will have a more objective,comprehensive grasp to the different Han Fu criticism and theory.
criticism and theory on Han Fu;horizon ofexpectations;the calling structure;the implied reader
I206
A
1007-5348(2014)11-0029-03
(责任编辑:薄言)
2014-09-21
2014年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科研项目“汉赋动物意象研究”(2014YJY55)
黄东坚(1988-),男,广东湛江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