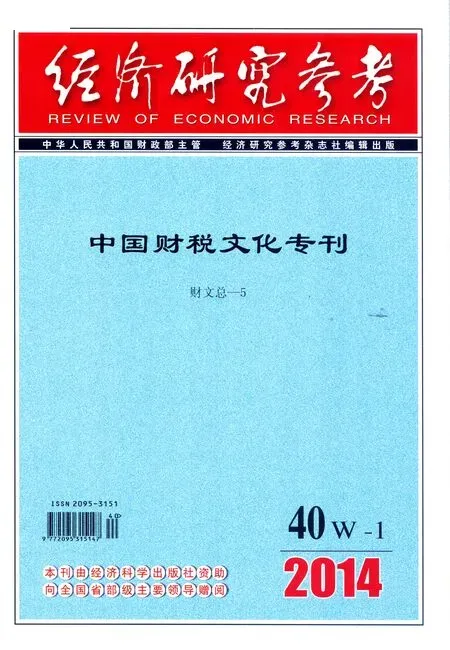分税制百年考
西南财经大学 付志宇
分税制百年考
西南财经大学 付志宇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至今弹指间已是二十年,个中曲折自不待言,然而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践已有百余年。本文从大历史角度,分析分税制的引入背景及实践过程,反思百年税制,从中得出分税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分税制;改革;历史
“折戟沉沙铁未销,试将磨洗认前朝。”分税制从一九九四年实行至今,弹指间已是二十年,个中曲折自不待言。但如将这一“礼制”置于中国的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观察,则远不止此时日。从形式要件看,最早可上溯到三代,《周礼》中的九赋九贡之礼明确了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贡纳机制,可视为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之雏形。中唐时期因藩镇割据形成的“留州、送使、上贡”体制则被《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认为是一种原始的分税制(本人十年前也曾撰文区别其与现代分税制之异同)。而真正意义的分税制乃是在晚清预备立宪时滥觞,北洋政府成立之初立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定型,全面抗战后调整的一系列学理争论与制度设计,前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质言之,分税制的引入乃是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作出的被动调整,是当时礼崩乐坏制度失范后国家“礼失而求诸野”的无奈之举。
晚清法务重臣沈家本对清季朝野学习西方制度的风气有过精要论述:“方今中国,屡经变故,百事艰难。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财政制度在“治道”之列,自然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内容。1905年清政府预备立宪,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其中就包括财政制度。五大臣回国后于次年颁行《清理财政章程》,诏令京师及各省报送收支数据,用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不久清廷又派唐绍仪等人出国考察财政,对西方的分税制和预算制度专事研究,回国后提出清理财政六项措施。一九○八年宪政编查馆与资政院公布了预备立宪的筹备事项,其中有“订颁国家税地方税章程”条款。该内容引起众多舆论关注,这一方面是“师夷长技”的实用主义选择,另一方面也导致国人“以夷变夏”的情感失落。一九一○年度支部在基本清查各省财政收支的基础上奏请中央申饬各省督抚将“何项应入国税,何项应入地方税,详拟办法咨明度支部分别核定”。但在具体的地方税划分层级和范围问题上,各封疆大吏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后来编撰《清史稿》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建议“将国家地方两大部分划定,再就地方一部各按本省情况细为划分较为确当”,江苏巡抚程德全认为“现定税法似宜以行政纲目为标准,先分国家地方两级,地方税中只分官治自治两种”,两广总督张鸣岐则提出“有一级之行政即应有一级之税,分为省税、府厅州县税、城镇乡税三种”。也有人认为,财政体制应与行政体制相吻合,如河南巡抚宝棻强调要“视将来督抚所处地位以为断,欲解决地方税之等级,必以此为前提”,东三省总督锡良也指出应“俟官制颁布后划分较有节次”。地方态度莫衷一是,中央只能体意屈从。近代以来督抚肆意截留税收,度支部对各省地方税划分根本无力干预,只得“令其自行删节,督抚以为可加则加之,以为可减则减之,以为不可加不可减则不加不减之”。分税制从倡行到清帝退位数年间只限于中央与地方文牍往还,形同画饼。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江苏都督程德全即提出划分国地两税议案,得到各省支持。一九一二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专门设置调查委员会,派员分赴各地调查财政状况,厘定税目,以划清两税界限。一九一四年财政部正式颁布《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分税制正式建立,到今年正值百年。此次分税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厘定税目,改良税制,“整理财政之道,首在改良税制。改良税制之方,首在厘定两税。前清末季,中央征税悉委各省代征,国家财政之基础已不巩固。军兴以来,旧章既已破坏,新制尚待筹议,中央乏接济之财源,益陷于困难之域。故非厘定税目,则国家与地方之财政永无划清之日”。二是奠定基础,以臻完备,“预定赋税系统之雏形,为将来施行之基础,调和贫富,酌剂盈虚。创新税,即所以去恶税;改旧税,即所以废复税。数年之后,两税之界限,以划分而愈明;赋税之系统,以改正而益备。庶足追各国之成规,而进于完备之境”。北洋政府时期的分税制是一种相对集中的财政体制,其中田赋等十七项为中央税,商税等十九项为地方税。当时主要的税源基本上都收归中央,地方不过一些杂细税种,这种划分无疑带有传统的重内轻外体制特征。不过,与前清高度集权的体制相比,显然是一种历史进步。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划分国家和地方收支,实行地方自治。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开幕式上指出划分宗旨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重”,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会议议决国家税包括盐税、关税等十五项,地方税包括田赋、契税等十二项。将来的新税中所得税、遗产税属于国家税,营业税、土地税则归地方。国民政府首次分税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关系,为地方自治奠定了基础。但是独立税制实行不彻底,县一级财力不足成了三十年代中国地方自治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国民政府《财政年鉴》评价此次分税“地方财政之规模因以具备”,但“所谓地方财政系以省级为主体,县则附庸于省,殊无独立地位可言”。有鉴于此,一九三四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划分省县收支的五项原则,国家财政收支系统采用三级制,国家税包括关税、所得税、遗产税等税,省税包括营业税等税,县税包括土地税、房产税等税。从此,地方财政的范围扩大到县,县级财政成为一级独立系统。孙中山主张地方自治,以县为基,这次调整对于促进地方自治作用明显。国民政府赋税司长贾士毅评价其“自国地两税划分,县属事业日广,收支日增,于是县地方财政乃渐独立,亦遂有预算决算之制定,而县地方财政遂与省地方财政同居重要地位”。
全面抗战开始后,各省收入有限,只能新辟税源,尽逾常规。而县级财政也渐涉苛细,陷入混乱无序,财政收支系统改订已刻不容缓。一九四○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讨论并通过《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把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国家税收包括土地税、营业税、所得税、遗产税等税,自治税收则包括土地改良物税、屠宰税、牌照税、行为取缔税等税。此次调整将省级财政并入国家财政之中,便于中央统筹分配;县级财政得以独立,利于推进自治,各地有望实现均衡发展。马寅初肯定其“由于省级财政之归并于中央财政系统,原属地方之田赋与营业税,及契税收入列为中央收入之大宗,有助于抗战者至巨,确实收到相当成效”。但这种分税制属于战时财政政策,主要税收均归国家系统,地方自治系统收入与其庞大支出不相符合,带来地方征收苛杂之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再一次对分税制进行调整。一九四六年还都南京后旋即召开第四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修正的《财政收支系统法》,规定中央税包括关税、货物税、所得税、遗产税等税,省税包括营业税、土地税等税,县税包括土地改良物税、屠宰税、牌照税、筵席及娱乐税等税。正如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在大会发言时所云,“我国幅员辽阔,县市单位数以千计,承上启下,现行省制实居重要地位。省级财政宜即恢复,以收提纲挈领、臂指相使之效。此次改订财政收支系统,仍分三级,并将主要收入划归地方,以期地方建设事业得以充分发展”。此次调整解决了地方财权的分配问题,尤其是重建省级财政成为改制要点。当然,一九四六年分税制也存在其他方面的弊端,如税种按收入分成导致省县之间责任不明,省级收入缺乏。因此,国民政府随后又于一九四八年重新制定《国税省税县税划分办法》,就实行宪政后三级财政所适用的税种做了明确划分。但当时内战正炽,行政院无力推行该法案,国民政府时期的最后一次分税制改革只能胎死腹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这一体制奉苏联经济理论为圭臬,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三级制行政体制相对应,自身无功过可言。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在搞活放开的指挥棒下,财政体制不断进行调整,大多采用分灶吃饭的包干体制,地方分权日益强化,总体上呈现一种弱干强枝,弱内强外的局面。另一方面,部分已经学会“睁眼看世界”的决策者与学术先行者也开始反思苏联经济学理论僵化封闭的教条,吸收西方经济学说中对中国财政实践有所补益的成分。在财力艰难和理论贫瘠的双重压力下,中央政府终于下决心改弦更张,采用西方通行的分税制模式来集中当时已经散布于各地的财力。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实践,到目前能够得出实现既定目标的基本判断。中央收回财权意味着重新掌握主动权,可以运用财力调度和配置资源,真正做到对地方“如臂使指,莫不制从”。同时,近年来中央政府也运用增加的财力办成一些好事大事,铸就亲民爱民的良好印象。但是,此次时隔四十五年后重新推行的分税制与历史上的做法区别较大。首先,采用的制度载体不够成熟,过渡期的双轨制特征明显,当时迫于压力实行增量分成的税收返还机制,时至今日仍大量采用收入分成和专项转移支付作为对地方的非正式约束。其次,推进的程度范围不算彻底,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无税可分,各省自行其是,无规律可循,导致县级财力倒挂严重。最后,缺少相关配套制度,其他领域的改革迄今仍付阙如,极大制约了分税制的深入推进。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回顾中国自近代以来走过的百年分税史,几个政权为之做出过探索。虽说是非成败转头空,这些探索已成历史陈迹,但如果不能以之为鉴,又会历史重演。分税制与政权盛衰休戚相关,总结其成败兴替之道对时下进行的改革实践不无参考价值。我们要尊重分税制自身的运行规律,不以一时一事之得失为标准,也不以一人一代之利钝为转移。反思分税百年,可以得出以下判断:其一,分税制并非二十年前首创,历经长期演化发展。其二,分税制亦非自创,乃是西学为用之舶来品。其三,分税制乃一国行政之载体,应与政体若合符节。其四,分税制之要义在于规范分税行为,以期央地相谐,互不干涉。其五,分税制之症结在省以下之分税,尤以确保县级财力为难。认清这些基本规律,反观未来改革之关节,自然纲举而目张。一言蔽之,应把握中央集权之度,张弛有法;应规范税目独立之限,宽严有据;应考虑税负弹性之量,轻重适度;应注重培植远期之税,长短结合。“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相信只要认清方向,找准目标,分税制必能得以光大!
F812.2
A
2095-3151(2014)40-0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