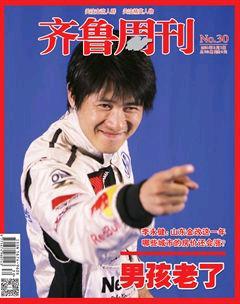从香港阅读世界:书展上的文化名流
吴越
7月16-22日,第25届香港书展举行。今年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越读越精彩”为主题,举办一连串文化活动。李敖、阎连科、白先勇、严歌苓、王家卫等名家登场,展开一场场盛大的文化交流。
每年7月,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便成为整个亚洲的文化中心。香港书展办到如今,之所以成为每年一度的亚洲文化盛事,与其文化和商业并重的理念不无关系。反观内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虽也有各种名目的书展逐渐成型,然而口碑和影响力都输香港书展远甚。
香港作家:
被割裂的“为世界写作”
香港书展第一天,2014“年度作家”董启章在明报上发表文章《给后代一个有文学的未来》。他写道:“我期待将来终于有一届书展年度作家,不须再回答‘为何环境这么恶劣还能写下去这样的问题。并且在被问及‘怎样才可以像你一样成为作家的时候,能毫不犹豫地告诉面前的年轻人:‘不用担心!你尽管去写吧!无论能不能成为作家,文学都会是你在这个地方活下去的理由之一。”
香港,董启章生活和写作的舞台。从1994年的《安卓珍尼》开始,到2005年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他虚构的“V城”故事成为旷世寓言。
书展主办方特设董启章专区,以“在世界写作,为世界而写”为题,从他的创作历程以及笔下文字,透视他心中的世界。
香港书展从2010年起设立年度作家,前四位年度作家分别是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出生于1967年的董启章是荣膺此殊荣最年轻的作家。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王德威说:“因为有了董启章,香港有了另类奇观。一切事物平添象征意义,变得不可思议起来。这是文学的力量。天工开物,从没有到有,从弹丸之地辐射大千世界。”
翻阅任何一部董启章的长篇小说,不论是一个男子的变形记,一群少男少女的青春期,还是一个作家的家族史与创作史,读者都很认同,董启章小说的结构设计之精密,犹如一个匠心独运的钟表师。比如《西西利亚》写一个年轻男性上班族爱上一尊服装店塑料模特儿,他给模特儿命名为西西利亚,由此开启一场绮丽的想象。在《安卓珍尼》中的蜥蜴之所以叫做安卓珍尼,象征着女主角对婚姻和两性关系的反省。《变身》的男主角林山,原就是一个每天走在中环的青年才俊,某天他在异地一觉醒来却变身成女人;《地图集》中,穿越到未来,一群狂热的地图学家,从一幅幅断简残篇,重构香港的街道、城市和生活面貌。
香港本土作家,除了董启章,还有黄碧云、钟晓阳。她们各自带来了新书《微喜重行》和《哀伤纪》。同为香港作家,两人的语言思维并不相同。黄碧云在写作时,采用的是“粤语思维”;而钟晓阳也许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采用的是“普通话思维”。
书展期间,黄碧云的《烈佬传》在第五届“红楼梦奖”上赢得“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的消息,她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香港作家。
当然,也有香港重量级作家参展,比如倪匡和他的《倪匡传:哈哈哈哈》。
阎连科与蒋方舟:
村庄里的中国与作家的困境
7月19日,最新一届卡夫卡文学奖得主阎连科亮相香港书展,做了一场名为“一个村庄里的文学与中国”的文学讲座。近些年阎连科在文学圈读者中口碑甚高,再加上受到不少国际性文学大奖关注,书展期间,成为颇受欢迎的内地作家。
阎连科说:“河南在中国的中心,中国在世界的中心,而我出生的那个村庄是在河南的中心,也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么了解这个村庄,就等如了解世界。”他形容那是一个永恒的村庄:“30多年前,村庄住了两千多人,现在也只七千多人,村里的人是不生不死的,因为大家都不报户口……”他说,村庄有人很有钱,拥有上亿身家:“30多年前,有人去上海买了一部桑塔纳轿车,一路从上海开回村庄的家门前,但突然一场暴雨,门前公路塌了,车从此离不开家门,成为景点。”
诸如此类荒诞十足的故事,阎连科讲了很多。“村庄很封闭,又很开放。有人开车把孩子撞死了,赔了三万块钱,他还气呼呼说被讹诈了,因为按常规来说,只需赔三千元。法律有时候几乎不存在。”阎连科说,但是有时候开放得令人瞠目结舌,“年轻男女结婚的时候,大部分都不打结婚证,未婚先孕很普遍。”
村庄成了阎连科的写作资源。他说:“我现在50多岁了,我已明白一个道理:我的幸运就是出生在这么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庄放大了就是中国,离开这个村庄,我几乎无法写作。”
作为阎连科最欣赏的年轻作家,蒋方舟也在书展上做了题为“大陆作家的奢侈与困境”的讲座。她指出,中国人口多,连带读者市场也特别大,“别的地方可能有2000人看书,相同比例下,我们随时就有2万人、5万人。”由于读者多,市场对各类型作品都包容,“写小说、写散文,以至网络不同形式发表,各种各样都会有人欣赏”。
不过,蒋方舟认为,空间大,挑战也不少,“否则拥有那么多的幸运,为何我们仍然不是处于创作上的丰年?”社会近年发生大量“奇人奇事”,一方面为作家带来创作灵感,另一方面却同时削弱了作品的可能性,“社会上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信手拈来一个例子,有父亲上网看色情片,竟然发现女儿当了主角,这些事件实在无法想像,生活有时仿佛比任何文学都更丰富、更真实、更具张力、更有戏剧性,也更令人痛苦。”
李敖父子和白先勇的历史观
台湾作家也是书展的重要“力量”。
7月16日,香港书展开幕第一天,21岁的李戡在书展首发近现代历史主题新书,80岁的父亲李敖现身与儿子同台演讲力撑。
“四年的时间,我从香港书展的观众变成演讲嘉宾。”李戡说。李敖谈起爱子的历史研究,也掩饰不住的自豪,“坦白说,在做历史研究方面,他虽然年轻,但他有我所没有的特色和优势。我做学问,肯下笨功夫,但我不是天才型的人,但是李戡是天才型的。”
书展第三天,台湾作家白先勇奉上两部新作,分别是《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和《牡丹情缘——白先勇的昆曲之旅》。
《牡丹情缘》讲述了白先勇数十年来传承昆曲的故事。10岁那年,他在上海欣赏过梅兰芳与俞振飞表演的昆曲选段《游园惊梦》,立刻被昆曲的优雅风格所吸引,从此与昆曲结缘。他的代表作小说集《台北人》中,就有与昆曲有关的短篇小说《游园惊梦》。他主持创作的青春版《牡丹亭》自2004年至今在世界各地上演两百余场,后来又打造了新版《玉簪记》。
回忆父亲的新书取名“止痛疗伤”,白先勇在书展的新书发布会上解释,是为了还原历史、填补空白,让人们了解真相,最终走出伤痛。
1952年,白先勇迁居台湾。当时有很多台湾人见到他都特意提及他父亲白崇禧,感恩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善念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当年15岁的白先勇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
香港书展现在被誉为“华人世界第一书展”,此次有来自31个国家及地区共570家参展商参与。游客方面,去年书展入场人流98万人次,今年达101万人次。
文化名人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书展的一个亮点。比如金宇澄与王家卫。
金宇澄以上海话书写的小说《繁花》,开篇借了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的结尾,而在小说问世一年后,王家卫也取得《繁花》的影视版权。
《繁花》令王家卫不但有兴趣拍成电影,甚至打算改编为电视剧,他认为若把书中对白变成普通话,“就像老舍的《茶馆》把京白去掉一样无法想象”。
对于语言味道,王家卫强调,“很多关于上海的小说,可能受到张爱玲影响,味道都是女性的,‘阴气太重。但金宇澄的《繁花》却充满男性荷尔蒙,有上海男人的性感。”王家卫特别提出小说开篇两句“上帝不响,一切全由我定。”其中“不响”二字充分表现出上海人的特色,“有时候上海人不讲话,心里却已经有了态度。”
对此,金宇澄解释,“不响”是地道的上海话,准确地说应该是“弗响”,即是“无语”的意思。
植根香港已100年的商务印书馆在市场需求和文化传承中找到了巧妙的平衡点。文化名人的号召力、雅俗兼容的图书种类、打折兼促销的定价策略,催生了每年7月香港阅读的“嘉年华”。有人说,每次到了书展季,香港人就会停一停脚步,买几本书,听几场讲座,这对于快节奏的香港至少是一种提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