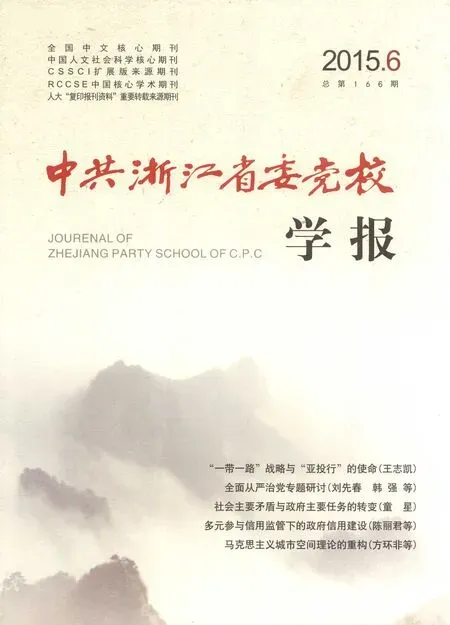党员忠诚意识的坚守与强化——来自苏共的启示
王 洁
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需要由大批忠诚的党员构成并积极地发挥作用。政党拥有其党员的忠诚,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会体现出来,反之,政党会因丧失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成为一盘散沙,甚至走向衰亡。苏共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拥有四十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苏共在1991年轰然倒塌时,将近两千万的党员竟然没有任何抗议和抵抗。如果说当时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政党精英们放弃了对党的认同,那么,一千多万的普通基层党员对党的认同、对党的忠诚又是如何流失的呢?深入地多视角地总结分析苏共党员的政治忠诚嬗变,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党员忠诚于党及其具体要求
孟德斯鸠把忠诚纳入政治品德的范畴中,认为要忠诚于责任,忠诚的客体是君主、国家和法律。随着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政治忠诚的内涵中更多地蕴含了价值层面上的公平、自由、民主等理念。如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对正义标准的忠诚。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乔西亚·罗伊斯在《忠的哲学》一书中将忠诚定义为一种社会行为,即“一个人对一种信念的自愿、实际、全心全意的奉献。”①Josiah Royce,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5:18.我国的学者有的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来理解忠诚,有的认为忠诚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忠诚的概念,而对党的政治忠诚的理解和界定则更少。本文倾向从政治伦理学角度看待党员的政治忠诚。所谓政治忠诚是指党员对政党性质、宗旨、地位、历史使命以及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对党的事业稳定的情感态度以及持久的责任行为。因此它是知、情、信、义、行的统一体,并且以认同为基础,建立在归属意识之上,以责任意识为核心,表现为内在的心理和外在的行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员忠诚于党首先要求信念坚定不动摇。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牢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共产党员不懈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只有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不动摇,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不迷茫,才能抵御形形色色的诱惑。其次,党员忠诚于党要求践行党的宗旨不懈怠。贯彻群众路线、践行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承诺。要忠诚于人民的利益,增强为民用权的意识和为民谋利的能力,以实现人民的幸福为己任,以执政为民为天职。再次,党员忠诚于党要求严明纪律不含糊。严守政治纪律,必须忠实地执行党的纲领、章程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严格执行组织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守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始终用纪律和原则来规范言行,不触碰纪律红线。因此,党员的政治忠诚应该体现为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为民服务的无私性和组织纪律的服从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①蔡世忠:《共产党员要不断增强党的观念》,http://www.ccdi.gov.cn/lt/llsy/llqy/201407/t20140709_45929.html.政治忠诚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尤为重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前车之鉴,更加凸显政治忠诚对于党的重要性。
二、苏共党员的忠诚危机及其成因
(一)思想路线的迷失造成了苏共党员的信仰危机
理论上的认同是政治忠诚的思想根基。苏共党员的忠诚来源于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认同,对党的奋斗目标的自觉认同。这种信念造就了党员们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他们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增强了他们在艰苦环境下建设美好家园的勇气和信心。而苏共执政过程中理论的僵化、混乱乃至迷失最终导致了党员的信仰危机,从而动摇了政治忠诚的根基。
列宁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促使理论的升华,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到民众广泛的精神认同,也造就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斯大林对确立和坚持列宁主义无疑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他又泛化、神化、工具化列宁主义,把科学的、生机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②季正矩:《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十个经验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党现在已经变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③牛安生:《苏共党章述评》,《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2期。公然抛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强调党组织成份的“全民性”,实质上否认了政党的阶级性原则,也从根本上否认了党的先进性和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新思维”的招牌下,名为对党进行自我革新,实则逐渐演变成为自我削弱、自我瓦解。从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到苏共二十八大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苏共已经慢慢偏离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渐行渐远。主要表现为:在党的奋斗目标方面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指导思想方面提倡多元化,追求“全人类价值优先”,认为思想库内应包括国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在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方面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舍弃了政治上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
这种思想和理论上的重大转变给全国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和活动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混乱局面。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引导,信仰迷失、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悲观失望、否定共产主义价值等现象在党员身上普遍存在,苏共变成了一支思想混杂、失去政治灵魂的队伍,一大批苏共党员退党、脱党,有入党意愿的人也锐减。
(二)高度集权体制下党内民主的缺失造成了苏共党员的归属危机
党内民主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党员对政党的忠诚度,也直接决定着政党组织的活力。在和平年代党员对党的政治认同和归属感主要通过在党内事务上的当家作主来形成。如果党员在政党组织中仅仅处于被管理、被驱使、被支配的地位,这样的党员在党内是没有尊严的,对于党组织也是没有归属感的。
列宁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实践中,体现出对民主政治的高度追求。在制度设计层面,通过建立和完善选举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监察制度、集体领导制度等力图确保党员政治权利的行使和党内权力的规范运行及制衡。而列宁本人也以身作则,有着高度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较好地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即使在严酷的环境下,列宁仍然强调在党内要广泛地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讨论,“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间接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①《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由于列宁的正确认识和身体力行,党内生活较为健康、正常、活跃,但是尚未形成良性的稳固的制度和机制,主要是靠列宁的威望和他本人的亲自带动。列宁逝世以后,苏共虽然在党内民主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认知和论断,但由于历史文化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往往停留在宣传层面,在实践中却逐步形成了个人专断的党内权力格局,党内民主流于空谈。按照苏共党章规定,制定党的政策、决定,要通过辩论,要保证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而斯大林时期特别是后期,党员意愿表达受到了打击和压制,政治高压使得大多数党员噤若寒蝉,因不同意见被视为“人民的敌人”遭到清洗更使得人人自危。尽管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开始揭露并批判暴力清洗的问题,但其本人和继任者并没有放弃对党内持异议者的打击,只是打击方式改头换面变成开除党籍、公职、管制劳动等。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按照个别领导的意志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党员的民主选举权徒有其表,走过场而已。更严重的是在苏共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形成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进一步加剧了党内集权。在党内监督方面,原先制度设计的党的代表大会的固定会期被取消,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地位下降,功能弱化甚至虚化。到70年代末期,基层党组织在国家决策和政治生活中已难起作用。在党内,“党的上层发生的事情,在通常情况下,不但一般的党员,就是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得而知”②[苏]罗亚·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贾连义、王器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与基层党员越来越远。这一切都使得基层党组织工作逐渐流于形式,缺乏实际内容,导致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政党的疏离,进而导致整个政党组织的衰败。戈尔巴乔夫则走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个人独断专行。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另一方面极端民主化。他认为党内民主缺失的根源在于民主集中制,解决的对策就是“民主化”和“分权化”,推行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于是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改变了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阐述。结果,无序的失控的党内民主导致派系林立、党内争斗和组织涣散,苏共由思想分歧转向组织分裂。
在这样一个党员缺乏主体地位的政党组织里,普通党员对直接关系党的命运的所有问题都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却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一切决定和指示,他们显然只会以消极的态度来应付事前他们毫不知情的决定或指示。长此以往,党员的政治冷漠逐渐取代了他们曾经的政治热情,疏离意识增加了,责任意识减少了,归属感丧失了,直至对党的命运不再关心。
(三)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造成了党员的信任危机
一个政党的领导阶层是该政党发展壮大乃至取得、巩固执政地位的中流砥柱。它在拥护贯彻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时必须体现出先进性和示范性,才能形成领导的有效性。因此政党中的关键少数是该政党形象的重要载体,其政治行为的道德表现深刻影响着政党的取向和去向。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苏共党内产生逐渐固化的官僚特权阶层。斯大林时期,创立了官职等级名录制度,党的特权现象开始蔓延,党内特权阶层开始萌芽。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各级干部享有不同的特权(汽车、高级住宅、别墅、休假券及医疗费补助、在特供商店购买物美价廉的紧缺商品等),而且领导特权逐渐制度化。享受着特殊待遇的不仅仅有党内要员,甚至他们的亲属、仆从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已、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①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赵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页。勃列日涅夫时期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官僚特权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这一时期特权阶层数量不断扩大,享有的特权越来越多,诸如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支权等,不一而足,以权谋私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就腐败案件的数量、规模以及社会影响看,勃列日涅夫时期堪称“空前绝后”,出现了珠宝钻石走私案、黑鱼子酱走私案、乌兹别克黑手党案、驸马案等等。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逐步演变为挂着红色招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势派”,②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页。已经严重影响了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据估计,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人员总数有50-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③王正泉:《官僚特权阶层: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人民论坛》,2007年第1期。
官僚特权阶层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它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群众,不是国家发展大计,而是自己个人的利益,自己的官位、自己的享受,自己的特权。特权阶层在人民面前高喊社会公正、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在行动上却鲸吞或蚕食人民的利益,滥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各种特权待遇,工作作风、生活作风腐化堕落。阿尔巴托夫在其著作中写道:“特权腐败不仅造成了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更加剧了社会分化,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④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苏共对人民的美好许诺与人民的所见所闻有天壤之别,群众接受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崇高道德要求在特权阶层的丑陋嘴脸面前黯然失色,苏共的执政合法性遭遇严重危机。
基层党员对社会主义、对领导阶层寄予厚望,但又因社会现实中长期存在大量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现象而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动摇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从而导致普通党员离心离德直至最终彻底抛弃执政党。一位叫索伦采夫的原苏共党员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我和同志们曾对党充满革命激情。但后来渐渐感到,这个党在失去它的活力。一方面,上层领导人高高在上,只知道布置许多繁杂的永远没有尽头的事务,却不知道该做些真实有益的工作。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这些人把争权夺利作为党的工作。请注意,这不是党的权利,而是他们个人的权利,是他们在党内的职务和排名。这是关系其物质利益和荣誉的事。另一方面,党员群众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他们似乎只限于进行繁琐的党内登记和向党组织的报告,而没有别的价值。”⑤黄苇町:《谁是苏共掘墓人》,《决策与信息》,2005年第1期。
(四)历史虚无主义瓦解了党员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造成了信心危机
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之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由于没有对其错误的事实、原因、根源等进行实事求是地必要的“切割”,没有在党内形成统一的决议,很容易被人利用来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时期党员的思想开始出现了重要变化,使得广大党员不再完全相信党的伟大,党的领袖的英明。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行的“公开性”改革,提出“不留历史空白点”、“批评无禁区”后,形成了对苏联和苏共历史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强大舆论洪流,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样。“在短短的时间内,清洗历史‘空白点’,变成了几乎将全部苏维埃历史涂成黑色。”⑥周尚文:《史学的困顿》,《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从批判、丑化、否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党的领袖人物到指向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列宁,从批判苏共执政的个别时期扩大到几乎整个苏共历史,从批判个别事件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各个领域。其中有真相,也有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及其历史人物的任意解释和刻意歪曲,把苏联社会描绘成兵营社会主义、粗陋社会主义和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最后否定苏共70年的执政历史。“不管在媒体上还是在日常交谈中,公开性没有带来对改革这一伟大事业的乐观和责任感,只带来了对现在和过去不断堆积的愤怒和冷言嘲讽,尤其是对领导人的政治辞令和允诺的不满。”①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在公开性引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下,苏共的威信迅速下降。历史虚无主义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使广大党员感到迷惘、无所适从,导致对整个社会制度的置疑,对整个国家前进方向的怀疑,这对广大基层党员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
信仰危机、归属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的不断累积,最终使得苏共广大党员的政党忠诚消磨殆尽,成为苏共衰亡这场葬礼上的冷漠看客。
习近平同志曾讲过: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②黄苇町:《执政党建设仍需“去苏联特色”》,《人民论坛》,2013年第24期。苏共党员政治忠诚的流失乃至苏共垮台给我们以警醒,如何提高广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度,如何使党员的忠诚意识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冲击下持久保持和强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要现实问题。
三、苏共党员忠诚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需以科学的理论来凝聚党员的忠诚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昨天的理论不放。”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列宁的这句话,鲜明地指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所以科学的理论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不断地通过理论创新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某些理论和话语既不能简单轻易地加以否定,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不可变更的教条,否则就会像苏共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从而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生命力。要力求最大限度地整合人民群众的基本价值取向,有鉴别性地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理论文化,正确看待并且谨慎处理好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与现实社会实践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从而完善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公众的要求,使党的理论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免疫力就会增强,能够塑造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以制度规范来增强党员的政治忠诚
建立在他律基础上的制度规范是强化共产党人忠诚意识的重要条件,客观上能规范和约束党员的思想和行为。
首先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党内民主是党的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就是用制度来保障党员权利、体现党员主体地位、尊重广大党员的意愿、统一共识来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反之,缺乏党内民主、丧失主体地位的党员就难以发挥工作的自主性、能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沦为党的工具,党员的政治忠诚无从保证,党组织的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十八大继续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就要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营造党内民主制度环境和党内和谐生态环境。
其次,要发挥党章规范党员行为的基础作用。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它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党的政治主张、整体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因此,党章成为衡量党员政治忠诚度的根本依据和标准。看一名共产党人是否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和人民,最根本的是看他在政治立场上、实际言行中是否真正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本质要求。同时,党章的刚性约束促使党员对党忠诚的硬规矩逐渐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行动。
再次,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选任干部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制度体现,也是其有效执政的组织保障。要规约公职人员的行为,保证政治忠诚,必须利用干部人事制度来作制度保障。要完善干部选拔制度,进一步提升干部选任过程的公开性、民主性和竞争性,提高干部选任过程的公信力。进一步完善竞争性选拔机制,要规范竞争性选拔的运行流程,并加以制度化和法治化。
(三)塑造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政治形象来引领党员的忠诚
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党的事业的中坚和骨干,作为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党员忠诚的引领者、实践者。假如党员领导干部都不忠诚,很难想象其他普通党员会忠诚。所以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把“忠诚作为第一政治品质”。习近平同志强调,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拥有为政清廉、勤勉尽责的官员会为执政党赢得更多的认同,它会激发干部“见贤思齐”的内生动力。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开篇之作。以反腐作为取信于民的的重要举措,对腐败“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强化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科学有效地防范与严惩腐败,重塑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政治形象,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赢得了党心民心。
建设领导干部良好的政治形象,对于增强中国共产党内部凝聚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党内广大普通党员来说,有利于加强对党组织的政治忠诚,加强党的组织基础。党的形象良好,对党员个体来说会有一种正的外部性,使他们身为组织成员而受益,他们也以身为一个伟大光荣的政党一员而感到骄傲,并愿意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党因此而更能凝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①王可园、齐卫平:《政党形象建设及其影响力》,《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四)纯洁党员队伍来保证党员忠诚
苏共亡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不是人越多越好,党员人数的增加与组织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政党功能的增强。相反地,如果让一些入党动机不纯、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人进入党内,只会加剧党组织凝聚力的涣散,给党的纪律带来冲击。列宁很早就指出:需要新党员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而不是壮观瞻,“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对庞大的政党组织中的党员忠诚的科学管理离不开党员队伍新陈代谢机制的构建,构筑扎实的入口机制和顺畅的出口机制是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已明确提出“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因此必须采取源头管理,严格积极分子队伍的培养、教育、训练和考察,确保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忠诚于党的人员进入党员队伍。但当前的重大问题恰恰不是入口机制存在多大漏洞,而是出口机制的阻塞。一些正式党员在党组织生活和工作中逐渐丧失了作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败坏了党的形象,如果不及时处理,极易在党内形成“破窗效应”,引发党员忠诚危机。所以亟需建立相应的评议机制,建立党员可进可退的组织机制,使那些虽然进入党内但又有悔意的成员能够体面地退出党组织,也可以经常性地主动将一些不符合党员要求和条件的党员清退出去。
19世纪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曾说过:历史是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现的值得注意的那些东西的记录。苏共党员的政治忠诚危机及其原因给了我们很多警示。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党员对党要忠诚的要求是一贯的,并且越是在长期执政的复杂条件下,越应当要坚守和强化党员的忠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