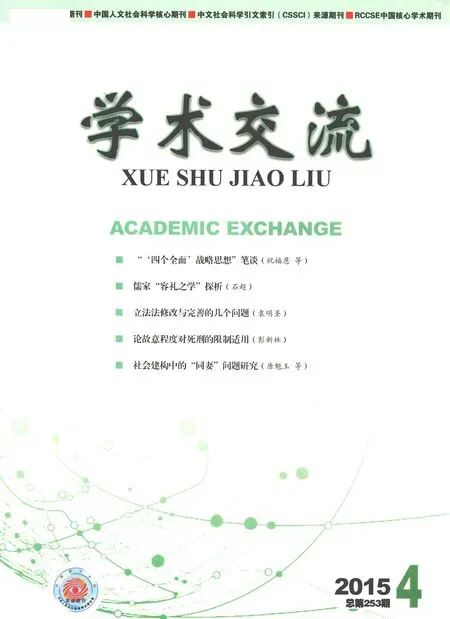“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平等与公正的论争及启示
王晓宁
(教育部社科中心文化美育研究处,北京 100080)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平等与公正的论争及启示
王晓宁
(教育部社科中心文化美育研究处,北京 100080)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平正义与以往各种社会形态下有产阶级所说的“公平正义”又有着质的不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平等与公正的争论,对于我们今天厘清社会主义的平等、公平、正义与以往阶级社会的平等、公平、正义的区别,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有启示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平等;公平;正义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探索中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日益和谐,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充分体现。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之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平正义与以往各种阶级社会的“公平正义”又有着质的不同。那么,马克思主义对待平等、公平、正义的态度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公平、正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曾有过一段激烈的争论。回顾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待平等与公正的态度的争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有启示意义的。
一、伍德的偏颇认知引发的争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诸多流派中的一支,因其成员都用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其理论工具而得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该学派内部掀起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待平等与公正的态度的争论,其导火索是伍德于1972年在《哲学与公共事务》杂志发表的《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
伍德在文章的开头即指出:当我们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读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时,直觉告诉我们这是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体系(制度)的刻画。然而,当我们深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就会立刻发现,在他们所有著作中既没有论证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意图,甚至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或不平等作出任何谴责。[1]244
伍德是这样论证他的观点的:首先,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主义的。他用马克思的理论有时被理解成“经济决定论”这一现象及法律、政治上层建筑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关系来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对马克思而言,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有机整体不是一个民族或政治国家,而是一种生产方式。……不仅仅人的需要、商业和交换方式及财产关系,而且人的政治生活、宗教、伦理和哲学思想,都是由人类的生产活动决定的。”[1]251其次,“公正”概念只有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才有意义。伍德在引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后得出了四个结论:1.马克思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谈论“公正”概念的。2.“公正”不是衡量人类活动、制度及其他社会生活的标准。3.马克思反对形式上的(抽象的)“公正”概念。4.对马克思而言,行为或制度的公正并不依赖于它们的结果,公正的行为和制度并不总是比不公正的行为和制度更让人幸福。因此,他得出结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特定的制度公正与否取决于它与其自身内在于其中的生产方式的关系,在一种生产方式中是公正的制度在另一种生产方式中则有可能是不公正的。”[1]259再次,剥削是公正的。根据上面的两个前提,伍德得出了这个在很多人看来不可理解的结论。他的理由是:第一,劳动力和资本的交换是平等(因而也是公正)的。依照等价交换原则雇用工人所付出劳动力的所有价值都已经通过工资形式得到了补偿。“资本家买了一件商品(劳动力),通过使用、剥削这件商品,他创造了比开始时更多的价值。”[1]262第二,没有剩余价值和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能存在的。一方面,劳动力同其他商品一样,只有被使用才会被人购买,它只有对于它的购买者有用时才能作为一件商品起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意识到没有剩余价值,他将没有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不仅是公正的,而且任何试图剥夺资本的努力都将是绝对的不公正。”[1]265
然而,又如何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剥削的批判呢?伍德认为,对这一问题的任何单一、简单的回答都是极其幼稚的,唯一明智的答案是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上具体的生产方式的全面理论来理解。伍德承认,马克思的确谴责过资本主义,而且这种谴责至少部分地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剥削的制度。但是,当我们把资本主义剥削视为“不公正”时,就意味着资本主义错在它的分配方式上。马克思对推翻资本主义生产的革命号召不是,也不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的批判的基础上。伍德进一步引述了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著名论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合理它才会终结,而不是相反。”“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的原因包含在他关于历史起源、组织机能,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未来预测的全面的理论中。”[1]281
伍德的文章发表六年之后,即1978年,胡萨米在《哲学与公共事务》杂志发表文章,对伍德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胡萨米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分配公正原则,即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并指出这两个公正原则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因此,关于资本主义公正问题,问题首先在于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否符合这两个原则。这就又牵涉到两个问题:马克思能否用无产阶级的或后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资本主义的分配?马克思是否或直接或含蓄地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资本主义的分配?
胡萨米认为,伦理社会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是政治、法律和道德观念还是国家等上层建筑,都受到了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和阶级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因此,阶级的代言人的道德观念不能孤立于历史发展和阶级利益而存在。尤其是在社会不稳定和变迁时期,上升阶级作为新社会的先驱,在同没落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往往用新社会的标准批判没落的社会。“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用无产阶级的公正标准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是合理的。”[2]34伍德对马克思的误读在于,他不理解如公正的观念等上层建筑的要素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只强调了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而忽略了阶级利益的影响。
胡萨米指出,无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用无产阶级的公正标准批判资本主义是合理的,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是这么做的。马克思的分配公正标准有两个,即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与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方式相比,按劳分配有两个优点:第一,通过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建立在平等权利原则的基础之上;第二,社会主义结束了阶级剥削。按劳分配的原则使社会主义的公正有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不同的个体在天赋的体力和智力方面也是不平等的,不同的个体也有不同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胡萨米认为,马克思所言的公正是建立在平等和自我价值实现基础上的公正,这两个公正原则通过废除私有制而消灭了剥削。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自由”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他们作为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在市场上与资本家“平等”交换,但是,“由于资本家和工人经济力量的不平等,劳动合同的自由、平等和等价交换变成了不自由、不平等和不等价交换。”[2]52因此,伍德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把马克思关于劳资交换的形式上的平等的论述误解成了一种关于劳资交换是平等而公正的论述。
胡萨米的文章发表之后,伍德又发表文章予以反驳,随后,柯亨、卢克斯等人也相继加入了这场论战,并产生了大批的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等理论成果。
二、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捍卫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源于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进而加深了两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不平等,是不公正的。这又包含了两层涵义:其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享受着不劳而获,劳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因此,资产阶级“平等”“公正”的口号因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具有局限性;其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的。
伍德正是在以上两个层面陷入了理论误区。首先,伍德不是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是从商品的生产领域,而仅仅从商品的交换领域或流通领域来论证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平等的,并由此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公正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经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流通领域的“平等”与生产领域的不平等进行了经典论述:“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3]168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剥削发生在生产领域而不是交换或流通领域,劳动力和资本表面上“平等”的交换,是建立在资本对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占有基础之上的。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条件下,由于经济力量的悬殊,想实现劳资双方真正的平等是不现实的。伍德仅仅从交换领域着眼,认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交换是依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显然是十分肤浅的。
其次,伍德机械地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漩涡。站在唯物主义观的视角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主张历史地评价特定的生产方式及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反对使用抽象的“平等”“公正”等概念,并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抽象的、超阶级的、普世的“平等”“公正”等概念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但是,伍德却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说明“公正”只有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才是有意义的,主张评价资本主义是否公正的标准只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并进而得出了“马克思批判正义”和“剥削公正”的结论。这显然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论证。人们只要按照伍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解推论下去,就不难发现,只要我们以特定时间的“特定的生产方式”为标准,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的剥削就都是公正、合理的了。这样,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等社会形态的更替就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了。显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上,伍德机械地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
相对于伍德,胡萨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认为“阶级的代言人的道德观念不能孤立于历史发展和阶级利益而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相反,在社会变迁时期,上升阶级总是会用新社会的价值观念同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是如此,社会主义者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亦是如此。胡萨米进而指出,事实上,无产阶级的代言人马克思也正是这么做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用“抢劫”“野蛮”“卑鄙”“可恶”等极富感情色彩的语词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和批判。马克思关于分配公正的标准,就是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这样,胡萨米就不仅证明了作为无产阶级代言人的马克思可以并且事实上确实是用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正标准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而且也指出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根源: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待平等与公正的态度的论战中,伍德、卢克斯等人坚持认为公正、权利及其他道德标准离开其所产生其中的特定生产方式是没有意义的,“对马克思来说,一项经济交易或经济制度公正与否取决于它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关系。一项经济交易如果与生产方式相协调,那它就是公正的;如果相矛盾,那它就是不公正的。”[4]268论战的另一方则用马克思的“抢劫”“掠夺”“侵占”“盗用”等语词抨击资本主义的事实来论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然而,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都难免走向“非此即彼”的理论极端。正如塞耶斯所说的那样,在这场论争中,“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道德价值被描绘成他思想中截然不同且逻辑上互相独立的两个方面。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被肢解成独立和互不关联的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它又被扭曲和篡改了。”“一方面,社会理论被描绘成价值无涉的社会学。……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被解释成为一种伦理观。”[5]68塞耶斯的评价是中肯的,他既反对伍德等人纯粹的相对主义,也对柯亨和诺曼·格拉斯的道德主义提出了批评[5]389,而是主张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理论,也是一种政治观;既是一种对历史的科学解释,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不仅如此,它还力图把这两个方面包含在一体化的理论见解中:不是把两者看作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两种因素,而是看作统一体中两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其道德和政治价值根本不相抵触。”[5]68
三、争论带来的思考与启示
这场争论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但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上的?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与资本主义的公平正义有什么区别?应该如何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这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待平等与公正的态度的争论,不管是伍德等人纯粹的相对主义,还是柯亨、格拉斯的道德主义,其实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争论不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科学解答了这一问题。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邓小平的这一番论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和政治立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批判深刻而犀利,这种批评从不避讳自己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政治立场。没有方法论的价值观,不管是早期的莫尔、康帕内拉,还是后来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都难免摆脱“空想”的命运;相反,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对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第二,社会主义平等与公正是对资本主义平等与公正的扬弃。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同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一样,都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革命作用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圈地运动、黑奴贸易和殖民掠夺等血腥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控诉,对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秘密进行了揭露。马克思曾愤怒地指出:“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3]298因此,资产阶级的“平等”“正义”等口号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虽然起过进步作用,但仍然摆脱不了其历史的局限性。恩格斯对此有深刻的论述:“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7]726
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是不争的事实,只是他们没有仅仅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正如胡萨米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显然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人类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标准。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以极大的客观性,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的历史进步意义作了肯定,另一方面也对其虚伪性和历史局限性提出了批评,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做了设想:私有制和阶级差别彻底消失,实现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平等的简单否定,而是对资本主义平等的扬弃,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言:“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8]195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平等批判的同时,是对更高级形式的平等即社会主义平等的追求,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平等”“公平”“正义”的批判抽象地说成是反对平等、公平、正义,这是根本错误的。
第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所有制基础。在伍德看来,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是依照平等交换原则进行的,因而也是公正的,所以,“任何试图剥夺资本的努力都将是绝对的不公正。”马克思早在《资本论》里就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因为资本家在市场上“依照平等交换的原则”所购买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剥削即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不是发生在流通领域而是生产领域。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流通分析后发现,资本既不能从流通中产生,也不得不从流通中产生,也就是说资本总公式存在矛盾。马克思经过研究发现,“劳动过程在只是再生产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并把它加到劳动对象上以后,还越过这一点继续下去……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3]183-184这就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开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面纱。可见,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不可能改变,因而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就暴露无遗,延伸至流通领域的所谓“平等交换”掩饰不了生产领域不平等的本质和无产者苦难的现实。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平等、正义等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们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仍然存在一些“不平等权利”,但这都是由于诸如个体劳动差异、家庭情况不同等原因造成的,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食利阶级的不劳而获有着质的区别。其原因就在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差别,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所谓“新思维”改革导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私有化改革,大批国有企业被贱卖,国家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被寡头垄断,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扩大,腐败问题日趋严重,社会经济秩序混乱不堪。这种状况在普京实施了大量国家干预政策之后才得以逐步改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社会日益和谐,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历史的发展已经雄辩地证明,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势必导致食利阶层的产生和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然无从谈起。
[1]Allen W 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2,1(3).
[2]Ziyad I Husami.Marx on Distributive Justice[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8,8(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Allen W Wood.Marx on Right and Justice:A Reply to Husami[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9,8(3).
[5][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M].鲁克俭,王来金,杨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余明全 程石磊〕
B089.1
A
1000-8284(2015)04-0053-05
2014-12-30
王晓宁(1984-),男,河南安阳人,副处长,助理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