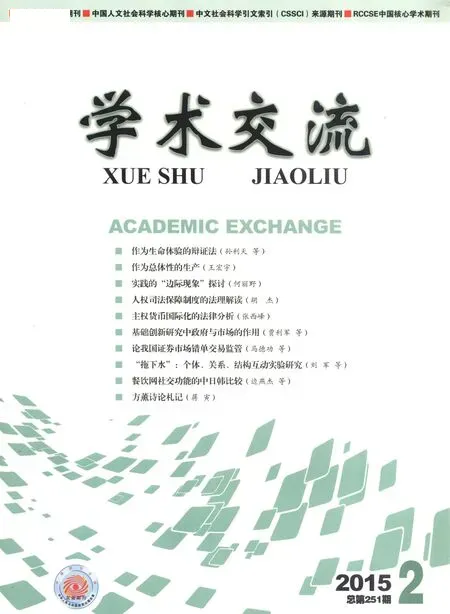柏拉图的灵魂学说及其现代意蕴
柏拉图的灵魂学说及其现代意蕴
王焱麒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生活报社,哈尔滨 150000)
[摘要]柏拉图通过死生互证法、“回忆说”论证法、构成分析论证法、反对“和谐说”的论证法、“相反相克”论证法来论证灵魂不朽,对后来的西方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关于灵魂的构成的灵魂能动说、等级说直接影响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理论;理性、激情、欲望三要素及其关系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人讨论灵魂、德性或人性问题时的标准性说法;灵魂回忆说是先验论哲学的最早表述;灵魂不朽说不仅是宗教神学的支柱性理论,也是伦理学倡导道德生活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柏拉图;灵魂不朽思想;精神实质;现代意蕴
[收稿日期]2014-11-13
[作者简介]王焱麒(1985-),女,黑龙江鸡西人,记者,硕士,从事宗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2-0026-05
一、柏拉图灵魂学说的思想来源
(一)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证来源
柏拉图对“灵魂不朽”的论证,是其灵魂论的最大主题。在《美诺篇》中,柏拉图首次提出“回忆说”,认为钻研和学习无非就是回忆。因为“灵魂是不死的”,它在以往的轮回之中“经历过一切”,所以能回忆起以前所知道的东西。柏拉图这里是用“灵魂不死”而推出“回忆说”,后来他在该篇对话中又用“回忆说”反推“灵魂不死”,他说:“如果事物的真相,也可直译为‘万物的真理’一直寓于灵魂之中,灵魂就是不会死的了。”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的对话中又相继使用了以下五种方式来论证灵魂不朽。
1.死生互证法
苏格拉底担心灵魂脱离肉体后将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他试图以此破除常人的担忧并论证:万物皆生于其对立面,因而,“活”生于“死”,“死”也生于“活”。所以得出结论:“死者的灵魂存在于某处,再从那里回到活。”也就是说,人死之后灵魂并未死,还活着,活在另外一个地方。但这种圆圈式的论证其实是把“死”“死者”和“生”“生者”等概念换来换去,不免自相矛盾。
2.“回忆说”论证法
“回忆说”的证明方法与《美诺篇》大致相同。但正如对话中的辛弥亚和格贝所言,它充其量也只能证明灵魂在生前就存在,还不能保证它在我们死后也继续存活。苏格拉底还是没有消除上面所提到的那种担忧。
3.构成分析论证法
柏拉图从分析灵魂的构成这一角度来论证,其大前提是组合物易于解体,非组合物则不会解体;小前提是不可见的灵魂属于非组合物之列,并且是“始终如一、毫无变化的”实体。所以,灵魂不会解体,灵魂在我们死后还将继续存活。柏拉图甚至认为:灵魂最像神圣的、齐一的、灵明的、不朽的、不可分解的、永恒不变的;而身体则最像人间的、非灵明的、多样的、会死的、可以分解的、不断变化的。柏拉图的魂身二元论,终于较为成功地证明了灵魂在人死后还能继续存活。
4.反对“和谐说”的论证法
《斐多篇》的对话中,辛弥亚以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类比魂身关系,格贝则以织工及其所织之衣的关系类比魂身关系。柏拉图则有意要把灵魂“和谐说”当作一种传统权威而加以批判。从理论层面,柏拉图拿起了“回忆说”这一武器,表明“灵魂在囚进身体之前必定已经在某处”,而“和谐说”则表明灵魂作为身体的一种性质,乃是“最后产生并且最先消灭的”[1]70;从事实层面,柏拉图利用反证法来进行,如果灵魂“和谐说”成立,就将推出“没有一个灵魂会有任何邪恶”“一切生物的灵魂全都同样好”的结论,“魂身交战”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但是,这些结论明显与事实相悖,所以反推出“和谐说”不能成立。
5.“相反相克”论证法
柏拉图后来又在《斐德罗篇》中,从运动角度提出了一个经典的论证,他首先区分两类事物,即“推动他物而又同时被他物推动着”和“自动者”,其中,前者终将“停止运动”“停止生命”,而自动者则不会“停止运动”,并且是“运动的第一原则”。“由于第一原则不是产生出来的,因此它一定是不可摧毁的”。而灵魂的“本质和定义”就恰好是“自动”,所以,灵魂也是“不可摧毁的”“不朽的”,它“既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
最后,柏拉图在《国家篇》中,从恶不能摧毁灵魂的角度再次论证灵魂不朽:即先给出善与恶的定义,认为“凡能带来毁灭和腐败的就是恶,凡能保存和带来益处的就是善。”[2]780其中,灵魂的恶包括不正义、无节制、胆怯和无知等等,但灵魂的恶与肉体的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加之,一个事物只能被它“先天的恶”或“自身的恶”所毁灭,而决不能被任何外来的恶所毁灭。[3]462所以,当身体之恶导致身体之死时,灵魂并不会因此而随之毁灭。但这只完成了论证的一半,因为按照柏拉图上述前提,我们似乎可以推出:灵魂尽管不能毁于外来之恶和身体之恶,却有可能毁于灵魂自身的恶,而柏拉图本人也承认了灵魂之恶的存在,灵魂最大的恶就是不正义。那么,不正义是否会“杀死”灵魂呢?柏拉图对此次的论证显得很勉强。他认为,不正义者不是死于他自己的不正义,而是死于别人对他的不正义所施加的惩罚。所以,灵魂自身的恶也不能杀死灵魂,既然任何邪恶都不能毁灭它,它必定是永恒存在的,必定是不朽的。这个论证其实也偷换了概念,本来后半部分柏拉图应该论证灵魂不会死于灵魂自身的恶,但他却转而论证不正义者不是死于其不正义,这种转换显然是不合法的。退一步说,即便承认这种转换的合法性,它也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不正义者正是由于其不正义才招致了别人对他的惩罚,所以,不正义者最终不是死于这种惩罚而是死于其不正义。
(二)对柏拉图灵魂归宿的理解
在对“灵魂不朽”作出充分论证之后,柏拉图惯于紧接着讲灵魂在人死后的归宿问题,他曾在《高尔吉亚篇》的523A-527E、《斐多篇》的113D-114D、《国家篇》的614B-621D等多个地方几乎以相同的神话故事的方式来讲,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强烈对比好灵魂和坏灵魂在人死后遭遇的天渊之别,来劝谕人们为善弃恶,做个正义的好人。灵魂死后归宿的问题又直接关乎灵魂“轮回说”,因为灵魂在死后受到的审判和相应报偿以灵魂的轮回为前提。
1.魂身关系
理解魂身关系前,先看柏拉图对于灵魂是如何分类的,他在不同的对话录中有不同的论述。例如在《蒂迈欧篇》中讲宇宙生成演化时,他基本将灵魂分为“宇宙灵魂”和“一般灵魂”、“神的灵魂”和“人的灵魂”,人的灵魂再细分为九个等级。除此之外,前面讲到灵魂具有善恶性和等级性,因此,灵魂也可以分为“至善灵魂”与“邪恶灵魂”。关于善恶灵魂以及九等灵魂的分类在此不过多赘述,仅简单讨论柏拉图对灵魂的分类。
关于魂身关系问题上,柏拉图在《斐多篇》论证灵魂不朽时,曾提出了一种极端的“魂身二元论”。他认为,肉体是各种不健康的情绪之源,因而干扰灵魂进行思考,是获取真知的障碍。柏拉图继承了他老师苏格拉底重灵魂轻肉体的看法,又多次强调灵魂是最初的本原,灵魂是先于一切形体和身体之类的东西。柏拉图唯一一次较为温和地看待魂身关系是在《蒂迈欧篇》88B-E处,他认为人有两种欲望,即身体上的食欲和神圣部位的求知欲。这两者若是不平衡的话,就将要么造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白面书生,要么造就粗暴无知的莽汉。医治之方就在于力求魂身平衡,即不做无视身体的灵魂运动,也不做无视灵魂的体力活动,这样才能“使两者各得其所”。
在《斐利布篇》,柏拉图还结合魂身关系来论述感觉、记忆、追忆,即“回忆说”中的“回忆”,以及欲望等问题。他认为感觉产生于“灵魂与身体形成了同一种情感并一起受感动的时候”;而记忆则是感觉的保存;追忆是指灵魂与身体一道经历的经验单独地在灵魂自身中再现。至于欲望,柏拉图认为,身体不可能感知欲望,因为“欲望并不属于身体”,欲望是灵魂“通过回忆而领悟到的”。所以,灵魂产生了一切冲动和欲望,灵魂确实是整个动物的决定性原则。这样,在感觉、记忆和追忆、欲望之间,柏拉图认为前两者皆为身体和灵魂所共有,后两者则基本上仅为灵魂所独有。从认识论及其所代表的知识的等级的角度来说,感觉和记忆还有其先后及高下之分,这直接影响了后来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等人的理论。
2.灵魂的构成
对于灵魂的构成,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认为灵魂包括进行思考和推理的“理性”和用以感受诸情绪的非理性的“欲望”,以及“激情”三个部分,它们“各起自己的作用,能够合在一起协调和谐,使灵魂能够主宰自己,秩序井然,这便是个人灵魂的正义与健康。如果它们相互争斗,都想争夺领导地位,便造成灵魂的不正义。”[2]780就三者关系而言,柏拉图认为,欲望从本性上说是“最为贪婪的”,所以必须由理性和激情来“监视”欲望。一旦欲望成为主宰,便造成“灵魂三部分之间的内战,相互争吵和相互干涉……于是就有了不正义、不节制、怯懦、愚昧无知”[4]425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更是以灵魂的马车和驭手来形象地比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把每个灵魂划分为三部分,两个部分像两匹马,第三部分像一位驭手。显然,这两匹马中的“良种骏马”代表理性,而另一匹与之相对的“杂种劣马”代表欲望,“驭手”则象征着激情。三者的关系就表现在驭手对于两匹马的驾驭之上,灵魂要想得见“真理的大草原”,就必须让驭手在良骏的帮助下制服劣马,从而在爱的激发下齐心协力,向着作为诸“理念”化身的被爱者飞奔。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强调所有的灵魂都要关注没有生命的东西,并在整个宇宙中穿行。由此灵魂被分为两种,即“完善的、羽翼丰满的”灵魂和“失去羽翼的”灵魂。前者“就在高天飞行,主宰全世界”,后者则一直下坠以至于“附着于凡俗的肉体”。到了《蒂迈欧篇》,柏拉图先是作出诸如“宇宙的灵魂”和其他一般意义上的灵魂之类的划分。此外,在《法篇》,柏拉图认为控制宇宙的灵魂的个数“至少不少于两个”,一个有益,一个有害:一个是指引宇宙走上正轨的“至善的灵魂”,一个是给宇宙运行带来“狂乱无序”的“邪恶的灵魂”。这里所反映出来的二元论明显带有恩培多克勒灵魂观的痕迹,柏拉图晚年在《法篇》中多次返回到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立场。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还专门提到了所谓灵魂的“上升”、“下降”及其“转向”。其中,“转向”意味着灵魂“转向真实的事物”,即“从变易的世界转向存在的世界”。正如“洞穴之喻”中那些被锁住脖子和脚踝的囚徒们必须努力挣脱身体上的束缚、转过头去、走出洞外,才能看见太阳及太阳照耀下万物的本来面目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也必须实现类似的转向,才能认清事物的真相,才能获得真知,而不至于被众说纷纭、淆乱人心的意见所惑。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只能来自恒常不变的存在的世界。
二、柏拉图灵魂观旳精神实质
柏拉图认为,只有进行真正属于可知世界的知识教育,才能让灵魂转向并得到净化,所以算术、几何、天文学等数理科学的教育十分有必要,它们能将灵魂引向追求实在的道路,从感知具体事物上升到感知抽象实在,达到对可知世界的认识。
(一)唯心主义灵魂认知
柏拉图的认识论建立在古希腊宗教神话有关灵魂不死和灵魂轮回等传统观念上,灵魂论实质上就是他唯心主义认识论的体现,在柏拉图看来,“我们的学习不过是回忆而已,回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定是从某个先前状态获得我们现在回忆起的东西。但是如果灵魂在进入人体之前不存在,这是不可能的。”[5]261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因融合了灵魂观而显得矛盾重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不是柏拉图所谓的“天赋”,而是来源于人的实践,正是实践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统一起来,认识的目的不是停留在追求柏拉图所推崇的精神理性,根本上是指导人的实践活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上升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这是认识发展的过程。具体说来,就是人通过感官在多种材料、经验的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之后获得感性认识,继而经过逻辑推理和分析综合抽象到理性认识,个人再将理性认识运用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这两种认识及其对象都是知识,一个是具体的感性知识,另一个则是抽象的理性知识,只不过认识的结果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符合客观实际的才是真理。柏拉图虽然承认可见世界感性认识的存在,也承认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由意见上升到知识的认识路线,但他基于唯心主义灵魂观,将认识的来源、对象和结果都看成是天赋先验的,把感性认识看成是不可靠的,理性认识是唯一的真知,它并不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无疑是不科学的。所以,柏拉图从传统的宗教神话灵魂观中走上了一条由意识到物质的认识路线,他将精神理性推崇到极致,将“理念”这一抽象的客观精神实体看作是世界的本原,由此产生了粗陋又矛盾重重的唯心主义认识论。[6]213
(二)心灵的终极关怀
柏拉图灵魂观是在继承苏格拉底对人的心灵关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格拉底赋予灵魂人格特征,十分强调我们要关心照顾自己的灵魂,追求灵魂的至纯至善。
他的最终哲学目的就是要通过道德说教,启迪净化人们的心灵,拯救人们逐渐堕落的道德和灵魂,使人们过上理性人的生活。苏格拉底对灵魂的关注和他的道德体系联系在一起,强调人的心灵关怀,追求心灵的和谐与宁静。柏拉图也不例外,虽然一定程度上,他的灵魂观是为其理念论、认识论、道德论、政治论等服务的,但其最终目的仍是希望城邦人民都能达到至善的正义生活。这必然需要每个人对自己的灵魂负责,认真去关怀心灵的和谐,努力去践行灵魂的净化。
从柏拉图关于灵魂与身体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灵魂的保护,防止肉体的疾病和不良情绪对灵魂的伤害。灵魂不仅先于肉体而存在,而且也优于肉体并统治肉体。柏拉图认为肉体具有双重的罪恶:它既是一种歪曲的媒介,像是隔着一层彩色玻璃那样地看得模糊不清;同时它又是人欲的根源,干扰我们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只有摆脱了肉体的愚蠢,心灵才能达到纯洁,这种褒扬灵魂而贬抑肉体的态度,体现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的心境:加强对心灵的关怀与保护,防止肉体对灵魂的侵害。
(三)唯心主义观念的哲学体系
柏拉图将先哲们灵魂观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发展到极致,一方面赋予灵魂唯心主义哲学色彩,使灵魂具有理性和认知能力,成为推动事物运动的主因;另一方面又赋予灵魂宗教神话色彩,将非理性因素与思辨哲学结合,这是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古希腊哲人所不能摆脱的哲学特征。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7]481从苏格拉底开始,哲人们开启了对人自身这个小宇宙的关注,灵魂观开始有了形而上的唯心主义色彩,灵魂开始作为一种精神实体与肉体分离。所以,自柏拉图起,古希腊哲学从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转入了唯心主义占主导的发展趋势,灵魂观也发生了质的转变。
柏拉图灵魂观既是其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开端和组成部分,也是其二元论唯心主义体系的依据。他的理念论和认识论都与灵魂观密切结合,相互联系,相互论证,共同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二元论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虽然他没有摆脱古希腊宗教神话传统,但其整体哲学不断进行着宗教外衣的剥离,同时其思辨哲学意味也不断加深。
三、柏拉图灵魂观的现代意蕴
(一)心灵哲学意蕴
柏拉图在对心灵问题的探索中十分褒扬灵魂(心灵)的作用。在心身关系问题上,他坚持认为灵魂先于肉体并优于肉体,肉体要接受灵魂的统治。柏拉图时期的身心关系问题主要是纯理性思辨的实体关系,虽然带有形而上学和先验论色彩,但无疑对后来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实体二元论心灵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给身心关系问题留下了广泛争论的余地。
科学主义心灵哲学在不否认传统心身关系问题的基础上,力图综合物理主义、系统论、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种分析方式对心身问题进行科学的理解与阐释。这种力图将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进行有机统一的方式,无疑使心灵哲学逐渐脱离纯思辨的甚至是无以言说的神秘色彩,表现出鲜明的科学实证色彩。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心身”问题逐渐集中到“心脑”问题上,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的发展与深入研究,甚至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心灵哲学的建构。
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是现代西方心灵哲学的源头,其关于灵魂的定义与特征、灵魂的构成与分类、灵魂与身体的关系等,在今天看来是对心灵问题比较粗糙的探索,但无疑对后来的心灵哲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心灵哲学本体论研究都离不开对上述问题的解读,虽然研究立场会大不一样,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及重点研究对象也有很大区别,但对“心”的本质、心身关系、心灵结构、心理现象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一直是心灵哲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
(二)人学意蕴
在关于人性和人的起源问题上,柏拉图以唯心主义理念论和灵魂论为基础,认为人具有社会性和先验性,人是造物主将灵魂放入躯体中形成的,理性灵魂是使人之为人的根本。关于人的属性与本质,他认为理性灵魂是使人之为人的根本,人的本质就是具有理性灵魂,人的属性就是具有精神属性。柏拉图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也与灵魂观分不开,他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对应国家这个放大了的个人分别相当于统治者、武士、生产者三个等级,每一等级有着各自的德性,即智慧、勇敢和节制,只有正义才能把这三个等级调和成符合善的理念的整体。因此,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每个人要做合乎自己本性的对维护社会正义有益的事情,合乎正义本分地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干涉别人,这样才能使国家达到“和谐”。关于人的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柏拉图将灵魂论与道德论和至善论统一起来,认为灵魂具有求真向善的本性,人的本质是灵魂,而灵魂属于心灵领域,当然受善的统摄,以善为最高的目标。通过德性和教育可以净化灵魂,使灵魂越来越接近真善美,所以,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对善理念的认知;人生的价值就是使人的理性本质得到实现和最大程度发挥,进入灵魂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三)死亡哲学意蕴
柏拉图的灵魂观和死亡观属于“死亡的诧异”阶段,此阶段的哲人主要侧重对死亡本质的思考,即对死亡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灵魂的可毁灭性与不可毁灭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生的自由等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柏拉图的整个灵魂理论就是他的死亡观。他对灵魂与身体关系的思考、对灵魂不朽的论证以及灵魂净化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对死亡终极性的思考,他相信灵魂独立于身体之外,相信灵魂不朽,同时也就相信灵魂可以轮回、人生可以轮回,因而死亡具有可逆性,死亡无需畏惧。
尽管如此柏拉图对灵魂与死亡的直面与思考启发着后人去不断地探索:我们该如何认识死亡?怎样的死亡观才是正确的?死亡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等一系列生死问题。随着人们对这一系列生死问题的追问,现代西方出现了众多死亡哲学理论,其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死亡哲学坚定的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考察人的生死问题。
柏拉图的灵魂观蕴涵着死亡哲学意义,其整个灵魂理论就是他死亡观的核心组成,是西方死亡哲学研究的重要源头,对马克思主义死亡哲学体系的建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之,无论是古老的柏拉图死亡观,还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死亡哲学,其发展道路都不平坦,真正的死亡哲学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是,他们理论中散发出的对人生意义、死亡本质和价值的执着追求,对真善美的渴望、对死亡的无所畏惧和对人生的真切关注,无不启迪着后人对生死问题的深入探究,照耀着继承者们走向更好的社会和更有价值的人生道路。
结论
柏拉图的心灵探索之旅,无论是对当时的城邦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他以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理论洞见,对灵魂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创新性的对灵魂进行定义,对灵魂的结构和分类进行阐释,对灵魂与身体的关系、灵魂不朽进行富于理性和神秘色彩的论证,对灵魂的功能与净化进行系统论述,就其理论深度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从他的学说中,可以找出对后来哲学研究有重大意义的相关主题,比如:灵魂、心灵、人生、死亡,等等。自然,柏拉图神秘的唯心主义灵魂观引来了多方的批评和诟病,可也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推动着人类对灵魂、心灵问题的深入探究。
现代新兴的心灵哲学、人学、死亡哲学的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灵魂理论虽然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人的心灵、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的深切关怀永远不会过时。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斐多篇[M].王晓朝,译.台北:左岸文化,2007.
[2]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M] .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6][古希腊]柏拉图.国家篇[M]. 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余明全程石磊〕
外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