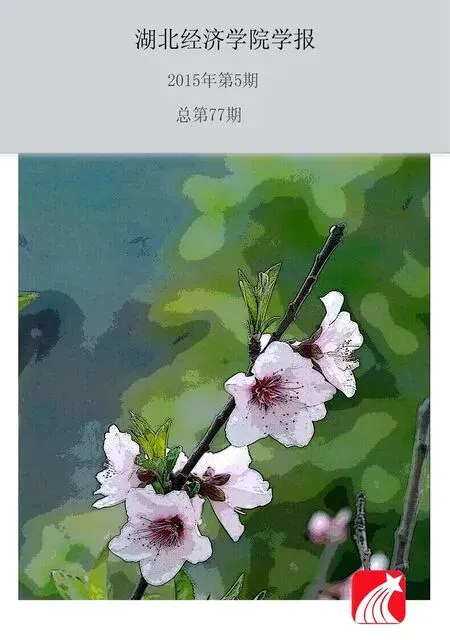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中介机制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分析
黄岭峻,唐雪梅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导论
截至2014年,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达2.74亿人。①随着农民工人数不断增加,农民工维权集体行动也不断攀升,这自然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广义的集体行动,是指“各种形式的、由一定群体参与的具备社会冲突属性的集群行为”。[1]狭义的集体行动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2](P2-6)本文采用狭义的集体行动概念,即指农民工 “由于各种利益被损害或被剥夺而引发的、旨在维护或索赔的利益表达过程”。[3]当前国内关于农民工集体行动研究的视角主要包括:利益与理性选择视角,公民权视角,怨恨、情感、剥夺感视角,其中,剥夺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因素,对集体行动有显著影响。
“剥夺”既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分为主观剥夺和客观剥夺,也可称为相对剥夺和绝对剥夺。“主观剥夺是指农民工主观感受到的不公平、不合理状况,客观剥夺则是指客观存在的对农民工不公正、不合理待遇的状况。”[4]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最早由斯托弗提出,[5]社会学家默顿强调相对剥夺感是个体由于某种参照系的对比而形成的剥夺感受。[6]与斯托弗和默顿不同,格尔认为相对剥夺感涉及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个人的价值期望两个层面,“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抗争的可能性越大。 ”[2](P78)总之,相对剥夺感或主观剥夺感是认知主体对不公正的客观环境以及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不符的一种主观认知结果,是由不平等和价值预期不一致给人带来的主观上的不悦感受。
Wright和Taylor研究证实长期的剥夺感易导致群体性事件。[7]相对剥夺感会引起社会冲突,继而破坏社会稳定。农民工进行的维权抗争是基于“外部压迫”的反应,而相对剥夺感直接带来外部压迫的主观感受,在这种状态下,相关利益者很容易参与到抗争行动中。参与者参与集体行动的强度取决于他们的主观动机强度,而这种主观动机很大部分取决于相对剥夺感的塑造,也就是他们自身已经形成了的被剥夺的主观认知。[8]因此,蔡禾教授等指出,在研究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时必须关注不满情绪、怨恨、剥夺感、认知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他们从不满走向愤怒,并最终采取行动的。[9]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会引发集体行动已经得到学界的证实。但它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以往关于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都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这仅仅揭示了影响因素和集体行动之间的单一关系,不易发现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本文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试图探究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影响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提出集体行动意向和城市生活适应在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和集体行动的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的假设,并进行证实,以便提前预防并有针对性地处理农民工集体行动事件。
二、农民工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中介效应假设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是他们在城市打工期间的主观感受。当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又极度渴望社会参与、市民权和发展权时,更易产生怨恨和剥夺感,进而产生集体行动意向,主观剥夺感强烈地激发着农民工的集体行动意向。意向和行动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这一问题一直是行动哲学的中心问题,塞尔认为:“不存在没有意向的行动,甚至不存在没有意向的无意向行动。”[10]“集体行动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它是由集体意向引起的。”[11]
基于上述理论与研究发现,可以假设主观剥夺感和集体行动意向均对集体行动有影响,并且主观剥夺感作为个体对社会不公平现状的一种主观感受,它要通过农民工集体行动意向的形成,继而影响他们实际的集体行动参与。而中介效应就是揭示事物之间的内部作用机制和相互影响过程。[12]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集体行动意向在主观剥夺感和集体行动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作用。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是他们对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社会关系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满意和习惯程度。”[13]如今,农民工客观遭受的以及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排斥是影响他们社会适应的最重要因素。由于工厂环境不能满足他们的主观需要,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一种低下水平,甚至产生“剥夺感”,这种心理剥夺感对他们造成了重大阻碍,降低了他们的城市生活适应水平。“主观剥夺感越强的农民工社会适应水平显著下降。”[14]
个人是“社会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要经历社会化的过程。“个人在社会中如果形成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按照社会要求来进行社会交往与行动。反之,他们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继而产生一些‘失范’行为。”[15]如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需求已经由以前的“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也就是说,城市生活越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求,他们就越容易产生一种对城市生活不满意的情绪体验,随着这种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会产生强烈的寻求自身权益得到保障、得到实现的倾向。当体制内手段不能满足这一行为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出极端反应,采取体制外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抗争”为主的集体行动过程实现他们利益诉求的释放。总之,“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与他们的集体行动参与呈显著负相关。”[16]剥夺感会引起农民工对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当这种不满积聚到一定程度,他们就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并改善现状。根据以上理论和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2.城市生活适应在主观剥夺感和集体行动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作用。
根据上述关系之间的假设,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图(见图 1)。

图1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城市生活适应、集体行动意向和集体行动间关系的假设模型
三、数据分析与描述
本文主要采用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的“珠三角农民工调查”中的相关数据。样本分别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州、东莞和中山9个珠三角大城市。各城市的样本数按人口普查与当地城市流动人口的比例分配,确保各城市至少有200个样本并限定单个企业的样本数不能超过3个。该数据最终收回有效问卷3086份,本研究中删除没有填写集体行动及意向的问卷7份,最终用于分析的问卷为3079份。
研究工具包括主观剥夺感量表、城市生活适应量表和参与集体行动的意向及参与过集体行动的情况。主观剥夺感量表由7个条目构成,包括5个选项,分别为:从来没有、偶尔有、经常有、总是有及说不清,“从来没有”到“总是有”依次赋值为 1~4。城市生活适应量表由7个条目构成,包括很差、差、一般、好、很好及说不清6个选项,“很差”到“很好”依次赋值为1~5。两个量表的相应条目见表3,所有“说不清”选项被处理成缺失值。参与“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集体行动的意向及具体的行为各由一个条目测量。集体行动意愿包括愿意、不愿意、不一定及说不清4个选项,其中选择“不愿意”赋值为0,其它情况均视为有集体行动意向,赋值为1。集体行动包括“没有”、“参加过”及“不记得了”三个选项,本文中将选择“参加过”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有孩子及换工经历。
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SPSS12.0完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采用Mplus7.0完成。连续性变量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分类变量用频数和构成比描述。是否参加过集体行动及有无集体行动意向的农民工间主观剥夺感、城市生活适应得分的差异分析采用t检验,由于量表中存在缺失数据,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的得分采用已填项目的均数表示。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量表的信度由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评价,Cronbach α>0.70认为达到可接受水平;[17]结构效度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价。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以潜在变量的形式进入模型中;是否参加过集体行动和有无集体行动意向均为二分类变量,以显变量形式进入模型中。四个拟合指数:卡方 (χ2)、比较拟合指数(CFI)、非规范拟合指数(TLI)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18]用于评价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由于卡方(χ2)值很容易受样本量的影响而膨胀,故不作为模型拟合优劣的评价指标。其余各指数达到以下标准时认为模型拟合较好:CFI>0.90、TLI>0.90、RMSEA<0.06。 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结构方程模型采用稳健加权最小二乘法(WLSMV)估计。对于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本文均报告标准化后的结果。P<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相关结果分析如下:
(一)样本的基本特征
3079名受访农民工中,以20~40岁的青壮年为主,占71.9%;年龄最小为15岁,最大63岁,平均(27±9)岁;男性 1637 人,占 53.2%;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一半 (51.2%); 未婚者居多 (55.1%);1274人(41.4%)有孩子;大部分人(75.1%)有更换工作的经历。参加过集体行动的有385人,占12.5%;2153人有参加集体行动的意向,占69.9%。详见表1。

表1 样本的基本特征(n=3079)
(二)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城市生活适应得分的差异分析
如表2所示,受访的农民工中,主观剥夺感平均得分为1.72,城市生活适应得分为3.11。与未参加过集体行动的农民工相比,参加过集体行动的农民工感受到的主观剥夺感更强(t=6.81,P<0.001),城市生活适应更差(t=-6.39,P<0.001)。同样,有参加集体行动意向的农民工比没有意向的农民工感受到更强的主观剥夺感(t=8.40,P<0.001),城市生活适应也更差(t=-5.87,P<0.001)。

表2 是否参加过集体行动及有无集体行动意向的农民工间主观剥夺感、城市生活适应得分的差异分析
(三)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评价
如表3所示,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 α分别为0.76和0.74,达到可接受水平。为了解两量表的结构效度,首先对两个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原始模型的拟合结果如下 :χ2=704.36,df=76,CFI=0.898,TLI=0.877,RMSEA=0.052,部分指标未达到可接受水平。基于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MI) 的提示及对测量条目的分析,允许两组测量误差共变(见图2)。模型修正后的拟合指数明显改善,分别为:χ2=415.16,df=74,CFI=0.944,TLI=0.932,RMSEA=0.039, 达到可接受水平。主观剥夺感量表各指标的因子载荷在0.36~0.61间(P<0.001);城市生活适应量表各指标的因子载荷在 0.36~0.63间(P<0.001)。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相关系数为-0.49,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由此可知,主观剥夺感和城市生活适应量表均为单一因子结构,信度和效度均较好。

图2 农民工主管剥夺感、城市生活适应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
由此,可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有孩子及换工经历作为协变量,对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城市生活适应、集体行动意向和集体行动拟合结构方程模型 (见图3),拟合指数如下:χ2=819.58,df=151,CFI=0.929,TLI=0.914,RMSEA=0.038,可见模型拟合良好。

图3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城市生活适应、集体行动意向和集体行动间控制协变量后的结构方程模型②
结构方程模型中各路径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及统计检验结果依次汇总在表4中。农民工感受到的主观剥夺感越强,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意向也更高,该路径的回归系数为0.26,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意向越高,其越有可能将意向付诸行动,更多地参与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集体行动,该路径的回归系数为 0.33,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另外,农民工感受到的主观剥夺感越低,其城市生活适应水平会更高,该路径的回归系数为-0.52,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水平越高,其参加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小,该路径的回归系数为-0.13,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总体而言,农民工感受到的主观剥夺感是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总效应为 0.23(P<0.001)(见表 5),即农民工感受到的主观剥夺感越强,其越可能参加集体行动。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和城市生活适应是农民工主观剥夺感与集体行动关系间的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7.9%和29.3%(见图3、表5)。

表4 结构方程模型中各路径标准化回归系数统计检验结果汇总表

表5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与集体行动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分解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主观剥夺感引起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和影响过程,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预防和解决农民工集体行动问题,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降低农民工主观剥夺感。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群体由于这个制度的限制,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城市边缘人”,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他们属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并且收入低;政治方面,由于在城市没有选民资格,回乡办理选民资格证成本又太高,所以,他们实际上成为了“政治边缘人”,丧失了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文化方面,部分城市居民存在对农民工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个别农民工的失范行为更加深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不满,两者难以融合。总之,由于户籍制度的分割,农民工群体无法平等地与城市居民享受社会资源,更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斥,这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主观剥夺感。因此,降低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就是要构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就业等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让农民工群体享受非歧视和无差别待遇。因此,政府应该积极探索并实践“积分入户”的户籍制度改革,当“积分”达到一定额度时,农民工就可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对于有意向实行身份转型的农民工,国家要逐步实现农村土地和农民工的分离,引导他们以农村宅基地、土地和住房置换城镇产权住房,逐步转换户口,从而与市民享有平等权益,降低剥夺感。
第二,建立健全利益表达和心理疏导机制,弱化农民工群体认同和集体行动意向,防止意向到行为的转化。农民工进城务工后,面临着社会不公平带来的剥夺感,这种剥夺感容易引发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继而衍生为集体行动的动力。如果农民工群体的不满情绪不能通过体制内合法的渠道表达,他们就倾向于采取体制外的方式来宣泄不满,并期望以此去改变现状,群体性事件就是不满的一种破坏性表达,这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政府部门首先应该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尽量让农民工的不满情绪通过合法渠道宣泄出来,真正发挥信访部门的实效性,缓解他们的积怨,弱化其集群认同,最终弱化他们集体行动参与意向。其次,建立农民工群体心理疏导机制也是必要的,农民工群体主观剥夺感的产生一部分来源于与其他群体的比较,特别是当他们与城市居民进行比较的时候,这种剥夺感更加强烈。因此,政府应该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状况选择合适的参照群体,并帮助他们正视现实,不能只关注于外部环境,还需关注自身,尽量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幸福感,从而摆脱困境;同时,引导他们对“公平”的正确认识,让他们意识到贡献大,则报酬多。企业要建立相应的企业文化,举办各种与农民工相关的主题活动,让农民工感受到心理关怀,改善他们的心理环境。最后,国家在制定具体社会政策的时候,要对农民工所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进行调查,弄清楚他们对政策的可接纳度,继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总之,要预防农民工集体行动,需要改善他们的心理环境,消除主观剥夺感,继而将集体行动意向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第三,提高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水平,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影响着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程度。因此,要让农民工在城市中有良好的生活体验,继而提升城市生活适应水平,首先,政府要着力为农民工构建友好公平的社会环境,要完善以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各种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要引导本地居民克服自身优越感和偏见,让他们真正认同、接纳农民工,使两者逐渐融合,逐步消除社会对农民工的各种排斥;相关管理部门要切实关注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实施积极的农民工管理政策,清除各种带有歧视性的规章制度,平等对待农民工和本地居民;其次,要保障农民工良好的工作环境。不少农民工由于知识水平不高,就业范围狭窄,进城后不得不依靠出卖体力和延长工作时间来换取工资。他们多从事高温、辐射、噪音等高危工作,恶劣的环境使不少农民工情绪低落,内心不平。如果自己的权益再得不到保障,就会进一步激发他们内心的抗争意识。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民工侵权行为的监督和惩处力度,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继而拓宽就业范围;企业要提高在农民工劳动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定期对从事高危工作的农民工进行健康体检,为他们购买工伤保险并提高他们的薪资和福利。通过采取以上措施,为农民工群体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提升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再次,农民工进城后一般在城乡结合部租房聚居,或者是工厂集体居住,这种共同聚居的环境就是社区,要加大对这些社区的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实现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平等的资源共享权;最后,政府要重点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当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实行的是属地管理,农民工在哪里参保就在哪里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异地就医需办理相应的手续后才能回参保地报销,这无疑增添了在农村参保的农民工医疗报销的难度。工资少导致了农民工不愿意甚至没有能力购买城镇医疗保险,有的企业也没为他们购买城镇医疗保险,农民工生病后,大多拖着,实在没办法,只得辞工回家。所以,政府要加强农民工城镇医疗参保力度,并实行异地医保结算制,使农民工看得起病,看得了病。总之,国家要从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医疗保障等方面着手,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活满意度,提高他们的城市生活适应,继而减少集体行动参与。
注 释:
①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5年4月29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网址为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② 箭头表示前一变量对箭头指向的变量的影响,数字表示标准化回归系数,即前一变量到箭头指向的变量的直接效应,正数表示影响方向为正向,负数表示影响方向为反向,数字的绝对值反应影响强度,绝对值越大则影响强度越大。
[1]Bert U.Breakdow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8,(24):215-238.
[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31-35.
[4]王晴锋.农民工集体行动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1-62.
[5]张艳.相对剥夺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70.
[6][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352-357.
[7]Wright,Taylor,Moghaddam.Responding to Membership in a Disadvantaged Group:From Acceptance to Collective Protes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0,(6):994-1003.
[8]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2):1-23.
[9]蔡禾,李超海,冯建华.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J].社会学研究,2009,(1): 139-161.
[10][美]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M].刘叶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9.
[11]季士强,任建霞.集体行动何以可能?——约翰·塞尔的行动哲学分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1):21-24.
[12]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13]杜萍,杨尚鸿.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因素探析[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12-120.
[14]景晓芬,马凤鸣.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J].南方人口,2012,(3):65-72.
[15]王康.社会学词典[M].济南:山东人民山版社,1988.352.
[16]李保臣,李德江.生活满意感、政府满意度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探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90-95.
[17]方积乾,孙振球.卫生统计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94-296.
[18]王孟成.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基础篇)[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9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