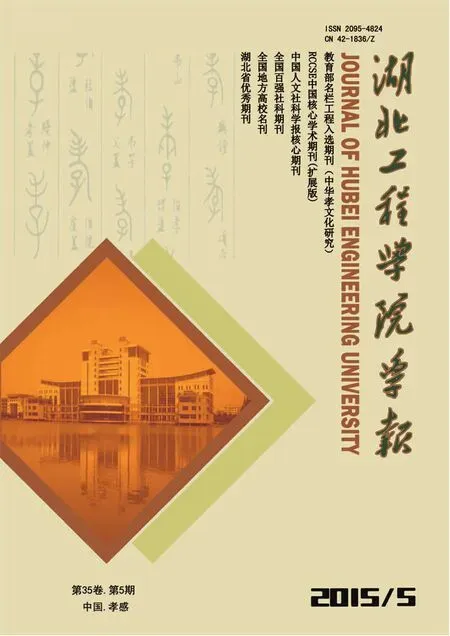论中国传统孝道对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整合及其历史经验
——以汉代公羊学孝道论及其影响下的孝行实践为中心的研究
王文东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100081)
论中国传统孝道对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整合及其历史经验
——以汉代公羊学孝道论及其影响下的孝行实践为中心的研究
王文东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100081)
中国传统孝道既是个人道德德性、社会伦理规范,也是一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仪等制度性要求,在学理上因兼含理论与实践、注重社会规范和制度建设而成主流社会道德体系之基本要素。汉代推重解释《春秋》大义的《公羊传》,公羊学因此成为一代显学,它不仅是儒家孝道论在当时的主要阐释者、发挥者,更是影响汉代法律制度、社会道德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春秋繁露》(董仲舒撰)、《白虎通义》(班固执笔)、《春秋公羊传解诂》(何休撰)构成汉代春秋公羊学发展之主脉,其对孝道的论说从以道论孝、以义申孝、以礼论孝、孝贯全体、以礼建孝、孝忠一体诸方面深化了先儒孝道论,成为汉代社会主流孝道论,亦是当时社会道德体系之主干。公羊学孝道论因其经学品性、官学地位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孝行实践,以孝断狱、春秋决狱作为司法原则推动了以“不孝入律”为中心的律法制度建设,促进了孝德与社会规范、制度的有效整合;以孝为德本、教化为先的道德观塑造了汉代崇德向善之时代精神,奠定了中国传统治道观之价值基础,其历史经验当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和伦理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传统孝道;汉代公羊学;德性;规范;制度
在汉代经学中,以推重并阐释孔子晚年所著《春秋》大义的《公羊传》成为一代显学。公羊学对孝道的论说一直是其各家讨论的重点。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孝为儒学之本,汉儒兴则孝道兴,更由于汉代孝道体现了其特殊的整合德性、规范和制度要求之功能。特别是传自先秦的汉代公羊学论理与治世兼重,把儒家春秋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居功至伟,其孝论由于经学品性、官学地位而深刻影响汉代治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深度整合而有效推动了汉代法律制度的建立,从而为当时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道德体系,我们不仅需要深入思考伦理理论如何体现道德生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使之具有丰富、切实、真实的内涵和强大的说服力,更应深入思考如何使伦理理论通过对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有效整合,促进社会系统的良性发展。孝道论对传统社会有建设与推动、异化与迟滞等多重复杂意义、价值、影响和作用。本文仅从正面立论,以汉代公羊学孝道论及其影响下的孝行实践为中心,分析传统孝道对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整合这一命题,期望对我们研究现代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和伦理理论提供某些值得思考和借鉴的经验。
一、汉代公羊学者对儒家孝道论的创造性阐释
汉代孝道承续先秦且在开邦立国之初已有勃兴之势,当时孔子七十子后学论孝之文逐步现世(如二戴《礼记》的编撰等),文帝时《孝经》和《论语》被立为经等,皆可为证。然而,创新孝道并使之具有经学品性而通达于政、学两界且影响社会实践,应首推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在现存《春秋繁露》及相关策论中阐述的今文公羊学思想为儒学独尊、立法更制起了关键作用,以统一经义为己任的《白虎通义》(班固执笔)是东汉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汉末何休穷数年之力著成《春秋公羊传解诂》则集汉代春秋公羊学之大成。西汉后期“《穀梁》之学大盛”[1]及王莽改制后兴起古文学,但公羊学以谶纬形式的持续存在使其基本思想在整个汉代有一贯发展之势。[2]因此认为汉代儒学演进中春秋公羊学一直居有主流地位[3],似乎不无道理。《春秋繁露》、《白虎通义》、《春秋公羊传解诂》构成汉代春秋公羊学发展主脉,其孝道论亦须以此为理论文本而得以理解。公羊学家在儒学孝道论之发展及父子之伦权威化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他们从独尊后的新儒学出发对孝道的阐述,学理新颖、独辟胜解,奠定了孝道在汉代社会道德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董仲舒及其后继者对孝道的阐释大要有四:
第一,以道论孝,即以天道哲学论证孝道之根据。董仲舒在不否认孔孟对孝之人情、人性之源肯定的前提下,以“孝”源于自然天道或源自天道对人的启示说,加强并拓展了孝道之所本的依据,如其言“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4](《春秋繁露·基义》,以下引本书只注篇名)即谓此意。阴阳五行是天道具体而微之显现,故以天道自然论孝可化为以阴阳五行释孝。河间献王与之论《孝经》关于“夫孝,天之经,地之义”的理解,董仲舒提出:“天有五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4](《五行对》)五行“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4](《五行之义》)。自然之理先于人伦之理,人伦之理先于政治之理,此谓公羊学思想之原则。董仲舒引申《孝经》以“天之经”论孝之说,为孝道寻找形上依据。如对“地之义”之论,其言:“忠臣之义子,孝子之行,取之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4](《五行对》)阴阳五行是自然界存在之构成者或基本要素,自然定然以阴阳五行有规律的运行、变化为转移;阴阳五行之序蕴涵人伦之序,是人伦关系之本,父子关系自然以此为据。五行相维相济、相生相须,父道蕴含于生者,子道反映于所生者,故父子关系内含生者与所生者之关系。如此内在联系之逻辑,自然昭示“孝”是人应守之基本法则。
以统一经义为旨的东汉白虎观会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对孝道根据之解释参考并发展了董仲舒的理论。班固根据会议主笔撰写的《白虎通义》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相糅合而强化君权制与父权制,其中云:“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伸,归功天地。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5]因循自然,取法天道,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理取法天地阴阳之道。“子顺父……法地顺天也。……金胜木,火欲为木害金。金者坚强难消,故母以逊体助火烧金,此自欲成子之义。”[5](《五行》)孝道源于自然天伦,五行规律更是昭示人伦之理,由此使孝道不仅有先秦人性论前提,更增加了天道论之依据。
第二,以义申孝,即从孝之“从义”方面提升孝道之伦理水准。孝之“从义”是先秦思想。如荀子云:“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6]汉儒训“义”为“宜”,如贾谊云:“行充其宜谓之义”[7];公孙弘云:“义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1]。“义”现代理解为正确的原则。[8]董仲舒认为孝是循“义”之行,即使情况特殊,如“辞父之命不为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5]也是合乎“义”的。《白虎通义》以父子相隐之道论述孝之“从义”原则,如云“父为子隐何法?木之藏火也。子为父隐何法?法水逃金也”[5]。此“义”首先在于自然之理,其次是人伦之则。子女为父母长辈复仇亦出于义,有则可循,如“子复仇何法?法木胜水,水胜火也”[5]。其根据仍在于复仇合于自然之理,因金若克木、火复其仇;火若消金、水雪其耻,土为火胜水、水为金克火、火为木克金,皆是此理,复仇乃天道使然。推而论之,“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之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5]。人子为父复仇是基于父子亲情自然之义,父母长辈因罪被杀而不能复仇则是基于律法之义。
第三,以礼论孝,即个人依礼践孝,社会以礼尽孝,国家以礼行孝。孝以礼为节度,汉儒普遍突出“德教”,同时推重尊礼守礼,离开礼制之约则孝难得其正。董仲舒的“以德善化民”与贾谊、申公的“以礼义治之”代表了德教的两种形式[2],大体上合乎先儒治道思想,而孝悌实为德教之落实。《白虎通义》多次引《孝经》及孔子之语,如:“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故有死道焉,以夺孝子之心焉,有生道焉,使人勿倍焉。”[5](《三教》)并循《孝经》、孔子、《礼记》之义法多次讨论丧制、葬制、庙制及服制,将孝道融入礼之差等身份制度予以申论,如“故《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子曰:……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傧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5](《礼乐》)。凡此都是申言个人和社会依礼践孝、以礼尽孝之重要与必要。
涉及相关伦理冲突尤其面对究竟如何践孝、尽孝之具体道德困境,公羊学更有详细探论。如论人子处理父母长辈可能发生之过错,《白虎通义》引《孝经》之“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谏诤》)语,以论证“谏诤”应善用理智以行权变:“子之谏父,法火以揉木也。……子谏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无毁伤也。”(《谏诤》)分析了“讽谏”(祸患未萌前规劝)、“顺谏”(言辞平和而不逆心地规劝)、“窥谏”(察言观色找准时机规劝)、“指谏”(就事论事地规劝)、“陷谏”(不顾危险直言相责地规劝)等不同义并提出“子谏父法”在于“法火揉直木”[5]。总之,一要“法火揉谏直木”即取法天道、依循自然之义,二要以高度的智慧行权善变,两者无疑都有助于更好地处理特殊境遇中子道与父道之实质冲突问题。《公羊传》云:“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桓公十一年)*本文引《公羊传》、《尚书》、《礼记》、《仪礼》、《周礼》等原文,皆出自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简体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相关引文只注书名、篇名。“权”与坚持原则甚至墨守成规之“经”、“常”相对,谓权衡轻重得失,因事制宜之权宜、权变或变通之计,公羊家在“谏诤”问题上要求善权变、守仁义,不许因墨守礼规而使父母虐杀、伤害子女而身陷不仁不义。如《白虎通义》引《孝经》人性价值论申说:“父煞其子当诛何?以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气而生也。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不得专也。”[5]此与《公羊传》之“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桓公十一年)相一致,公羊家坚持高度的原则性立场(“经”)不稍动摇,并从具体性意识、操作层面倡导行为的灵活与善变(“权”),要求行权有道、相互涵容,此乃崇尚权变、以礼行仁、以仁约礼之春秋学精神之反映。
国家层面以礼行孝体现为“孝”之规范与教化意义具有化育人性及管控、安定社会之效用。董仲舒在上书汉武帝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云:“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白虎通义》亦云:“人者,天之贵物也”(《三军》)。其中引《孝经》之“天地之性人为贵”一语时说明:人有欲利恶害之自然性,也有求义向善之道德性,王者治世重在启发人性之善端,以礼仪教化、圣贤示范、规章约束使人觉悟其为最贵者,自知其道德性而避免自然性。《白虎通义》又云:“安民然后富足,富足而后乐,乐而后众,乃多贤……内能正己,外能正人,内外行备,孝道乃生。”(《考黜》)此与作为内在德性的孝德在功能上是相合的,人子对父母之奉养、敬爱、忠顺、追念即是对道义之遵循。孝道以天道阴阳为依据以求取其规范与德性之整体功用,恰表明其对更具普遍性、有效性道德基础之探求。
第四,孝贯全体,即孝贯彻于天子至庶人等一切人,流行于个人终生乃至社会一切方面,渗透于亲子之外主要人伦关系。战国至秦汉时期孝道有普遍化与泛化之倾向,如《礼记》记曾子认为“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皆“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于亲……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祭义》)。《孝经》更有孝为“天经地义”及“孝通神明”之论,公羊学于此有承袭发展,如董仲舒认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春秋》之大义也”(《玉杯》)。“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家自为俗。”(《立元神》)“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悌也。……教化之功,不亦大乎。”(《为人者天》)此与《礼记》、《孝经》相关大旨相类,贵贱尊卑、自然生命、都市县邑无不以孝为要,故立国以德化为先,而德化以孝悌为重。
孝源自天道自然之必然性及人伦之普遍性使其成为安天下、化人性的必由之道,天与人、天子与百姓、君与臣相类于父与子,故孝当贯彻于万事万物与全体人伦。公羊学由此将原本主要是一种个体德性的孝道提升为内涵、地位发生很大变化的普遍之理,在来源、内涵、精神诸方面显示出与先秦孝道的殊异性。在来源问题上,孔孟明确阐明孝源于人类自然之善良性情或血缘亲子人伦,荀子认为孝源于修善弃恶、人道教化、礼仪修持,董仲舒则认为孝道源自天道自然,《白虎通义》进而主张孝道是王者发现天道所蕴含的人伦必然性;在内涵问题上,孔孟孝论基本上限人性人情、家族人道领域或推及具有相近相似关系的社会人伦领域,荀子将之作为对人道伦理之义的遵奉,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扩大到对来自五行阴阳自然天道之父、君及类似关系的敬信,《白虎通义》通过折中经义将之具体化为对君、父等人伦之道及社会体制的信服;在内在精神问题上,孔孟认为仁义忠顺、庄敬信诚、和悦温恭为孝之精神,荀子强调孝是合于普遍道义之准则,董仲舒则认为孝以内在于天道、人道之法则为自身价值追求,《白虎通义》认为孝当守天地之性、人伦之道、圣王及体制之教诫;在处理特殊道德冲突问题上,父母有可能发生过失时子女如何行孝,对父母长辈之孝与对家族相关成员之关系,对家族之孝与对社稷和君主之忠的关系等方面,孔孟以血缘为基础强调由家族本位扩展到社会本位,荀子倡言从道不从君且以社会为本位依循法则(礼),而董仲舒则希望以天道、自然人伦、政治伦理为序以协调家庭、社会、君主关系,《白虎通义》信奉君主圣人之教化、齐一于制度规范或律法。
春秋公羊学为西汉儒学立为官学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而为五经诠释之核心,它以孝道加强各诸侯王经由宗庙对朝廷之忠心,加之“事君不忠非孝也”此类观念对政统的推动力,以孝悌忠顺为家族精神纽带而使宗法社会趋于和平与稳定之力,促进了父权的扩大与强化,公羊学借此历史机遇极力整合儒家关于父权的权威性学说,将孝从个人道德德性上升到社会伦理规范、法令以及礼仪等制度纲常层面,俾使其具有强烈的伦理与政治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性。先秦礼学有父尊子卑、君尊臣卑、夫尊妇卑(此为“三纲”说之雏形)之萌芽,其中论定“父者,子之天也”(《仪礼·丧服传》)。汉初倡言礼治而一度居于主流的礼学孝论认同父权论,一是律法保护父权的绝对性、家长据家法惩办子女、据国法告发子女不孝而子女却不能,否则处以不孝罪。二是父权支配家庭财产,如言“父母在,不敢有其身……私其财”,“子妇无私货,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礼记·内则》)。三是父权主导子女婚姻、言行等,如子女无权决定婚姻是否缔结或废除,即使“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我者’,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同上)。子女“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曲礼上》)。董仲舒承先秦儒家孝论并以阳主阴从、父阳子阴为前提,论定父尊子卑、父主子从;《白虎通义》基于父权的至上性而提出子顺父命具有不可违逆性,如言“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孳无已也”(《三纲六纪》),父按法度教子而子自然受此教而不稍违逆,从而合于父权与父道之普遍性。父权确立于宗法制并代表其精神意志,孝道论以之为前提和基础同时又维护、提升此精神意志,以体现其现实性和实践性,于此可见汉代孝德在规范化、制度化方面确有大异于先秦孝道之处。
何休在古文春秋左传学兴起、今文春秋公羊学中衰之际穷神劳思注《孝经》、解诂《公羊传》,更表明东汉一代公羊学者仍在意于阐述、传布与弘扬孝道。何休不仅在其著《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直言“躬行孝道,以先天下”(桓公十四年),“罪莫大于不孝”(僖公二十四年),更是不吝笔墨对历史上不孝之人与事不遗余力地痛加贬斥。如何休注《春秋》记“冬,葬齐灵公”(襄公十九年)一事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无过。故夺臣子恩。明光代父从政,处诸侯之上,不孝也。”(襄公十九年)何休阐述不同性质之礼制更是全面渗透孝道思想,其要点有二:
第一,以“礼”建“孝”。何休述宗法之礼、内外朝礼、宗庙之礼、继承立储之礼,言之如:“礼,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族所以有宗者,为调族理亲疏,令昭穆亲疏各得其序也。……大宗无子则不绝,重本也。”(庄公二十四年)“礼,公族朝于内朝,亲亲也。虽有贵者,以齿,明父子也。……宗庙之中,以爵为位,崇德也。……丧纪以服之精粗为序,不夺人之亲也。”(宣公六年)“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隐公元年)此中论及“亲亲”、“尊尊”、“亲疏各得其序”、“明父子”之道,皆为述礼之言,隐含着“礼”对宗法、宗庙、继承制度同体一贯之维护与推重,意在表明对构成孝德基础与前提的宗法制度的肯定,孝德与规范、制度的深度结合更具现实性、必然性。如此述礼之文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使用次数甚多,如认为:“《春秋》正夫妇之始也。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和,君臣和则天下治。”(隐公二年)家之孝、国之忠为一体,而“礼”则是统一之道。因礼是立国之本、治道之源,故何休将构成家庭细胞的父子、夫妇关系作为行礼求治的逻辑始点。破坏亲子关系尤属不孝罪,依法严惩不贷,因此直言“无尊上、非圣人、不孝者,斩首枭之”(文公十六年),其对不孝者的论处体现了汉初以来公羊学的基本观念与精神,并承袭了秦法惩治不孝罪的态度与方式,倡言量刑极重至死刑,处置之重可见一斑。
第二,孝、忠一体。孝之实是“亲亲”,即以亲者为亲,亲亲以“孝”为核心;忠之实是“尊尊”,即以尊者为贵,尊尊以“忠”为本质。《礼记》认为“亲亲”、“尊尊”等为“人道之大者”(《丧服小记》),“不可得与民变革者”(《大传》)。《春秋公羊传解诂》云:“礼,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宣公元年)“王者得专杀。书者,恶失亲亲也。……称王子者,恶天子,重失亲亲。”(襄公三十年)亲子之伦是宗法之要素,而宗法则基于家、国一体,故视亲亲、尊尊为一体,由此使表“亲亲”之孝与表“尊尊”之忠联为一体,互为补充,两者于伦理秩序之功能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亲亲、尊尊之重要在于亲亲以行孝,尊尊以尽忠,孝、忠乃拨乱反正之匡世之道,两者一体并行可由微至著,循序渐进,起衰振敝,有重建伦理秩序之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功。此乃何休倡亲亲尊尊,推行孝道视作“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的真意。
综上所述,董仲舒在以道论孝、以义申孝、以礼论孝、孝贯全体诸方面都有较大的创新;《白虎通义》统一经义并集于君王礼法孝治;何休则强调以“礼”建“孝”、孝忠一体并行的重要,将礼制与君父本位之孝连为一体并依据社会要求以亲亲推进尊尊,以尊尊维护亲亲;公羊学孝道论比之先秦儒家孝道的理想主义(学理性)更属于现实主义(实际性),由此为其孝道论实现德性、规范与制度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以及最终的整合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二、公羊学孝道论影响下的孝行实践
汉代公羊家普遍认为刘汉作为暴秦的拨乱者,损益夏周礼法以定汉制;《春秋》为汉法之根本,《公羊传》为《春秋》之常典,孝亲则是春秋公羊学之核心价值。公羊学为一代显学,汉代社会伦理规范、制度层面“以孝论罪”的不孝法定主义及以孝断狱、春秋决狱发展为律法原则,皆与公羊学的推动密切相关。
汉代史家与公羊家的学统一脉相承,如司马迁曾从学于董仲舒,班固是《白虎通义》的撰写者等,其书所载孝案所在多有。今文公羊学孝道论理据俱实、诸说一体而深入人心,盖因汉代“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5],“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9],各阶层自觉实践孝道者层出不穷,而存心弘扬孝道,以孝博名者亦大有人在。《史记》记伍子胥报杀父兄之仇(《伍子胥列传》)。《汉书》载王尊闻美阳女子告假子不孝,遣吏收捕验问后取不孝子县磔著树,使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之(卷76《赵尹韩张两王传》)。强奸、鞭打后母皆属罪过极大的不孝行为,故王尊以不孝罪弃市为标准论处。元帝时东平思王宇“事太后,内不相得,太后上书言之,求守杜陵园”(卷80《宣元六王传》)。上层显贵因行孝而名声显赫者如翟方进,“身既富贵,而后母尚在,方进内行修饰,供养甚笃”(卷84《翟方进传》)。士人阶层更注意自身言行是否符合“孝”,《后汉书》所载著名孝子(女)有郑兴(《郑兴传》)、张奉才(《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周磐(同上)、公孙弘(《公孙弘传》)、鲍永(《鲍永传》)、樊修(《樊修传》)、韦彪(《韦彪传》)、陈纪(《陈纪传》)等等。庶人阶层行孝突出者亦有见诸于史籍,孝行内容直观且富有操作性、实践性和评判性,表现有如辛勤劳作、谨于奉养、维护父母尊严、顾虑父母安全、不置私产、依礼葬亲等,《后汉书》所载庶人孝子著名者如江革(《江革传》)、陈长(《陈长传》)、杨震(《杨震传》)、彭修(《独行列传》)、李充(同上)、范训(《范训传》),如此等等,难以尽数。
严惩不孝以维护父道,惩戒劝善为汉代德教之主题。宣帝地节四年奉行“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之论,免除“有大父母、父母丧者”之徭役,令“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1]此律解决了子孙尽孝与长辈犯法的矛盾。丞相薛宣因不孝而多次受弹劾,成帝诏书申斥云:“君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无闻焉。……罢归。”薛宣后又因贤再次任官,“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卷83《薛宣朱博传》)。薛宣最终坐免为庶人。兹分析三例,以详细讨论春秋公羊学孝道论影响下的孝行实践:
第一,刘爽弃市案。衡山王刘赐之子刘爽(衡山国太子)纠结于父子之伦,获罪弃市而亡。《史记》和《汉书》对其罪因说法不同,前者认为刘爽获罪是因父告不孝,后者则认为因告父犯律而被处死。前者说父告不孝当然要入罪,后者说因父谋反而将之告发,刘赐畏罪自杀,但刘爽亦获罪“不孝”。刘爽告父因违反孝亲之义自身也为国法不容,这无疑是儒家孝道亲亲守匿原则适用于当时司法的结果。公羊学提倡“父子相隐”,子告父母自然被处以刑罚。基于父子之伦,刘爽不仅不能告发其父,还要为其隐瞒。汉律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不追究责任,彰显了亲亲相守之隐匿原则。孔子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0],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引此语后说“崇父子之亲也”(文公十五年)。公羊学家将先儒孝道看作“治世之要务”,孝案的司法处理一般尊重并遵循《春秋》大义而对不守匿者苛以重罚,在此要区分伦理与道德:伦理是客观的关系及其协调的准则(公理性)、原则(普遍性)和规范(特殊针对性),道德则是个体主观意识及其法则。自然天伦是准则,人伦之理是原则,准则和原则的具体适用则通于规范。不孝的处罚依于违背公理性的伦理准则。父母长辈有过错一定程度上可得到法律的保护或宽恕,宣帝诏云:“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1]不为父母长辈隐罪反要受惩罚,为父母长辈报仇而杀人者常得到宽宥,反映出孝道观念对法律实施的实质影响。汉律处理亲亲相隐犯罪不仅考虑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为意图、动机和目的,也审时度势地做了制度考量,因为不施仁义、专任律法会破坏人道准则、天伦亲情。家、国固有的内在社会构成关系与自然人情的不可悖逆,是亲亲相隐得以生发的客观依据;而亲亲相隐作为孝道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司法方面缓和了法律的苛严,而且照应了人性之常情,顺从了儒道。
第二,陈母告子不孝案。仇览为蒲县亭长,陈元母告子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耻。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览乃亲到元家……因为节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9]。仇览深感教化之重,故有责任宣明孝行。如果援引前法,陈元必因不孝而获罪,仇览却认为陈元不应被苛以极刑重罪,其罪是教化未至之果,故需教民孝亲。盖因不教而杀谓之诛,以诛杀为治法殊不可取。民未感教化则难以立孝,立孝道之风必以德教为先而弃刑杀之责。《春秋》之道不违孝亲,仇览深谙于此。董仲舒云:“《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春秋繁露·竹林》)恪守表面大义而泥古不变难以达到真正的大义,因此司法者需要合理疏解与变通。
确定不孝之行要根据当事人心意予以断定,即判断者“原心”论行,据事洞察行为者动机。先秦时期,人们就非常重视“心”与“行”的关系。儒家是动机论者,重于以“心”论“行”且“心”、“行”一体,如孟子言:“心之官则思”[11],荀子言:“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12]。其以为心含有一种内在的自然生发之动力,是思维器官,具有主宰、发动人思考、行为的功能。公羊学者根据事实探索当事人主观心志、动机,判定其行为性质属恶或非恶,如果心术不正,故意为恶,即使是行为未遂,也要加以处罚。董仲舒言:“《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精华》)汉人于此多有发挥,如言“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1];“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为求生,非谓代死可以生也”[9];“《春秋》之义,原心定过,赦事诛意”(《霍传》)。公羊家桓宽总论道:“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13]“论心定罪”即“原心定过”,是依公羊学治狱的核心论点,“赦事”和“诛意”是其两种体现。“赦事”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本直者其论轻”,“诛意”即“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志邪者不待成”。此反映了公羊学宽厚和严厉之两面。司法者应重于以主观动机衡量过与非过或过之大小,而不以刑杀为教,如此以使情、理、法相通。
第三,赵娥因孝免罪案。赵氏为恶霸所害,其女赵娥志于复仇,潜备刀兵,历十余年而手刃仇人。[9]赵娥自知有违国法及杀人偿命之理,最终自首,而县治长官尹嘉为赵娥孝义感动,弃职欲与之同患难,共生死,赵娥终不肯离去。刺史、太守共表上而称其义烈,刊石之碑,显其门闾,为赵娥请愿免罪。依上述“原心”论行的原则,替父报仇公然违背律法,但本事原志,复仇亦合乎自然伦常。汉代律法此后在类似复仇的司法审判中对于行为者动机有着明确的要求和判定,而不将单纯的结果作为唯一考察点,依“《春秋》缘人情”(《俞序》)而全面考虑行为赖以产生的动机、目的。春秋决狱、原心论罪、以孝入律,在复仇案件审理中建立一种宽容的伦理制度。董仲舒言:“《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楚庄王》)。复仇案具有的判例性使司法者援引来处理了断他案,某种意义上古代仁治(“宥过无大,刑故无小”[14])与汉代礼治、德教思想是一致的。“汉时去古未远,论事者多傅以经义。”[15]“春秋决狱”以经义之微言大义为大原则、总指导,建立博士制度,通过经师的援经释义,指导审理法无明文论定的疑难案件,由此使经义条理经由经师阐释而产生立法与司法的双重效用与合理功能。
“春秋决狱”具体化了以孝论罪原则,不仅继承了惩治不孝之行的古学传统,而且又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尤其是“不孝入律”将父子之伦律法化更是对西周以来不孝论罪的全面实践。周公有“……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16]之语,将大恶与不孝不友对举;《周礼》有“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地官·大司徒》)之说,不孝作为犯罪曾为周人刑罚惩治的对象,此与当时重孝观念相一致。“不孝”盖指不遵亲亲尊尊之道,不事尊祖敬宗之职,毁坏人伦情理,破坏宗法关系,故为法律所禁。至秦仍有延续,秦曾立法对不孝之行施以惩罚,如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云:“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不当环,亟执勿失。”老者若以不孝之罪告发并请求(谒)予其子以制裁,则司法者可不经原手续(三环)直接捕捉犯罪嫌疑人。汉承秦制,张家山竹简云:“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弃市。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黥’指在脸上刺字;‘城旦舂’指劳役,男去修城池,女去舂米)”(《奏谳书》)[17]227;“教人不孝,黥为城旦舂”(《二年律令》)[17]139。以不孝为据来治罪量刑,此为“不孝入罪”律。春秋公羊学自战国至汉初传授系统完整,文、景之时开始影响朝政,武帝时成为法定正统学说,其倡孝治天下、引孝入律远接先周而近承孔门七十子后学,应是儒家思想与秦制的结合与创新。在一代显学影响之下,国家自上而下君相率先垂范重视孝悌,据《汉书》、《后汉书》所载西汉惠帝到东汉顺帝时举行全国性的孝悌奖励、旌表、赏赐达32次之多。反观另面,不孝之行、不孝罪及孝案亦较多[18-20],分析汉代史书、律法所载相关事实,当时惩治的不孝罪更见其对儒家公羊学孝道论的贯彻。不孝罪有如下数类:
第一,不养父母,侍奉不周。“孝”的基本要求是物质奉养,不奉养父母者依汉律将被弃市。西汉前期春秋学已流行,孝道逐渐纳入社会规范和制度框架,汉简反映的是汉初法律,自然与严于刑律以惩处违逆亲亲之道,防止平民不尽人伦义务、不事供养之责有关。将不事供养或侍奉双亲此类单纯的孝德作为治罪的法律依据,意味着孝德被制度化、法律化了。文帝时《孝经》被立为经,景帝时立治公羊学的胡毋生、董仲舒为博士。此时早已注重对长辈病时侍奉,文帝侍母“亲尝汤药”位列二十四孝,当时父母生病时不侍奉、不亲尝汤药皆属惩治行为,此类案例西汉中期前比较集中。《后汉书》载“汉中程文矩妻……有二男,而前妻四子。……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积,而穆姜慈爱温仁……及前妻长子兴遇疾困笃,母恻隐自然,亲调药膳,恩情笃密。兴疾久乃廖,于是呼三弟谓曰:继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识恩养,禽兽其心。……遂将三弟诣南郑狱,陈母之德,状己之过,乞就刑辟”(《程文矩妻传》)。此处不孝者愿就刑辟,可见惩处不孝者观念深远。
第二,殴辱长辈,打杀尊长。晚辈以暴力、凶器冒犯尊长肢体或生命尊严,比虐待常人情节恶劣,性质严重,自然当属不孝大罪。“子孙本以恭谨孝顺为主,所以对父母有不逊侵犯的行为皆为社会和法律所不容,不孝在法律上是极重大的罪,处罚极重。”[21]汉承秦律*秦墓竹简之《法律答问》曰:“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今殴高大父母,可(何)论?比大父母。”对殴祖父母、曾祖父母者,判“黥为城旦舂”之刑。,维护尊长权威,对有殴詈行为之人及事,不仅要考虑是否殴伤及伤之轻重以外,而且要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若以贱犯贵、以卑犯尊,则不稍迟缓而严刑惩罚。子女谩骂、殴打祖父母、父母等亲属受处死之罪。汉律对子女殴打祖父母者,所施处罚比秦律更重。妻子殴打、谩骂丈夫的祖父母和父母的,不仅因以阴犯阳、以卑犯尊,更以直接破坏人道亲亲之理而被处以极刑,殴打同辈年长者要被判处“耐为隶妾”的刑罚。可见,谋杀、杀伤父母、尊长者皆属大逆不道之罪,对谩骂、殴打父母之不孝罪的也有其他处罚。如殴打亲生父母及父母的兄弟姊妹,依法要判做司寇;若辱骂之极,猖狂无度,要罚金一斤。以尊犯卑者,如父母惩罚子女或主人惩治奴婢而致其死亡(期限内即二十日内),则判以死刑。这与贼杀非亲属成员(“贼杀人、斗而杀人,弃市”[17]137)之刑区别在于允许前者“赎死”。
第三,举告尊长,诬告父母。汉律对晚辈举告尊长、诬告父母,从晚辈身份、尊长年龄两方面作出限制,将其列入不孝之罪,以严刑处以“贼律”,此与公羊学的孝道论是一致的。汉律强力维护孝德,卑弱为尊长隐匿,特别是家庭关系中卑弱者须隐瞒尊长者的过错或犯罪行为,即向官府隐匿而不得告发。若卑幼告尊长,则官府不予受理;如父母告子不孝,不孝子要受严惩,经查属实将被弃市。人子杀伤祖父母和父母或者奴婢杀伤主人或主人父母、妻子,即使先到官府自首,也不能减免,最终要受惩处。凡此等等,反映了汉律维护孝道的决心。
第四,非议孝道,妄坏婚制。汉律不仅惩罚不孝,而且严惩非议孝道者,禁止“妻后母”并将之列入不孝罪。《史记》之《燕荆世家》、《樊郦滕灌列传》、《淮南衡山列传》,《汉书》之《王子侯表上》、《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蒯伍江息夫传》、《武五子传》、《霍光金日传》、《赵尹韩张两王传》、《匡张孔马传》、《薛宣朱博传》、《樊郦滕灌列传》、《外戚传上》、《王莽传下》以及《后汉书》之《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等,15处都有“妻后母”的明确案例。其中诛死或自杀的有9例,废或免的有3例,因奸事未发或风闻而未处置的有3例。排除奸事未发的,被诛比例更高,在各类不孝罪中处置最为严厉。
第五,不遵教令,居丧不谨。“守丧”、“居丧”或“守制”期间依制守礼、行礼尽哀,循丧葬礼仪,否则为不孝。居丧违礼受制裁的情况有四:一是闻父母亡匿不奔丧、不发丧。如陈汤在待朝廷分配录用期间,听父去世讯息而不回家奔丧,被检举为缺乏孝道而拘捕下狱,举荐者张勃亦被削减食邑二百户(《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二是服丧期间无悲哀之心,饮酒、不离妻妾或娶妻妾。如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即帝位,丞相扬敞等弹劾之,奏章列举其淫乱、不敬尊上,亲群小远功臣,丧期奔丧和居丧时不守礼等各种罪状达千条。扬敞等化用《孝经》“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之说,认为昌邑王悖逆人子之道,按汉初量刑标准应处以死刑,最终昌邑王称帝二十七日而被废。三是服丧生子。如陈蕃任豫章太守,“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遂致其罪”(《后汉书·陈蕃传》)。四是私奸服舍、作乐。如女甲夫去世,夜间守丧时与一男子在棺后房发生私情。次日,婆婆告发,甲被逮捕。廷尉以不孝定罪,因她是公士之妻,处以黥城旦舂(《奏谳书》案例二十一)。对妻子居夫丧奸与“居丧奸”的“不孝”罪之处置方法是一样的。居丧违礼的亲属仅仅限于父母、丈夫,限于子及妻。
第六,不遵法度,违立后制。“后子”作为他人嗣子须守为人后之礼,以子之礼孝事之。汉人重宗法继承,尊祖敬宗,立宗子以收族、序昭穆。宗子若无子,须立后为己之子。《公羊传》提出“为人后者为之子”(成公十五年),此论与今文礼学如出一辙,如《仪礼·丧服》云:“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同宗则可为之后。”“为人后者”因“受重”而继承所后者之宗庙祭祀权、爵位与财产等,故须像亲子一样为所后者服最重之斩衰服(三年)。“为人后者为之子”在西汉晚期至东汉都极受重视,是汉律立后之规定,要求“为人后者”须遵“为人后之谊”,违者即为不孝。《汉书·师丹传》、《后汉书》之《祭祀志》、《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等皆有关于“后子”如何守礼及相关讨论。将为人后之礼上升到律法高度自然是重视、实践、维护孝道之举。
第七,危殆宗庙,不守功业。汉人强调“孝子善述父志”(《汉书·粱商传》),“为人后嗣,守人功业”(《汉书·谷永传》)。守护宗庙、光宗耀祖、继志述事是秦汉以降社会孝论主题,如《孝经·感应章》云:“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云:“……以守宗庙,可谓孝矣”。公羊学承接此论普遍强调孝道在于不废先人之业而影响一代汉人,司马迁父子、刘歆父子、班固父兄妹皆为典型。名儒班固附阿窦氏,终因窦宪擅权受株连而冤死。其原因除班、窦家族有世交之谊外,还在于:其一,班固对守宗庙、继父志的深刻意识。班固曾祖父况举孝廉为郎,大伯祖父伯受儒学而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父班彪续写《史记后传》未成而亡。班固深感继宗族之业的重要而不惜攀附权臣,以求显亲扬名。其二,班固自觉尽忠孝为臣责,如他肯定汉赋抒下情、通讽谕、宣上德、扬忠孝,因此其赋歌功颂德者如《封燕然山铭》辞有“光祖宗之玄灵”之句,既颂窦氏之功,又明守孝之志。在汉人看来,危殆宗庙、不守功业则犯不孝之罪。
以上所列不孝罪类型大致可反映汉代公羊学孝道论影响下的孝行实践之概要。汉人重孝精神与春秋公羊学孝道论互为表里,道德要求人子在父母生前赡养、侍奉、敬重,不殴杀、不侮辱、不控告,死后居丧、祭祀、致哀以尽人礼,律法则通过查究不孝之过对不孝者予以惩罚,意在通过维护宗法制和父权制而成就公序良俗之社会。将孝道纳入律法范畴并形成严格的评判标准是汉代规范孝行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制度,其目的亦在于张扬做人之基、立国之本的孝道价值观,以律法的强制力来维护孝之价值,使其深植于民众思想、情感、行为之中而成公序良俗社会中的一善民,更使人真正自觉为万物中的最贵者。
三、基本历史经验
公羊学孝道论在汉承秦政之变中不仅体现出对先儒孝论的革故鼎新、发展重构之义,而且以影响一代孝行实践之力整合了德性(作为个人品性之孝德)、规范(作为社会伦理之孝行)与制度(作为律法原则之不孝入律),使思想道德、规范准则、社会制度三者有机结合且良性互动,成为贯穿社会道德体系运行机制的主线,使之以治国要道之力成为铸成名副其实之强汉的文化软实力。其经验主要有:
第一,“孝”在公羊学视野里既是国家政教大典的基础,也是德性、规范与制度建设的价值根源。孝论是贯穿整个今文学的原则要义,自然是治国大典与原则,正如经学是国家政教之大宪章,其基本特征如李源澄云:“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22]两汉通过五经博士制度确立今文学十四博士,而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以经学为“孔子法”,重“义”而不重其“制”,即根据经书中的义理来面对现实,将经义灵活引用到不同情形中,为现实提供价值依据。春秋公羊学者多为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之士,故皆能通经致用、不为腐儒,他们把对经义的精深理解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结合起来,阐述伦理、人伦优先,倡言人道、孝道为重,通经致用,重建纲常,以人伦之孝道为中心建构汉代社会律法体系和道德体系,纲举目张,抓住了国家政教、治道的实质与要害,值得深扣而细味之。
第二,以源于人情、人性的主观孝德与以伦常关系法则为主的客观孝行伦理规范相通,有利于内外一体、个人与社会合一地推行并实现孝道价值。春秋公羊学以经学追求现实性、恒常性、普遍性的立场对孝德进行阐述,使孝从德性为主转化成一种体现社会伦常客观必然性的实践理性法则,将孝由特定指向德性内涵转化为一种包容性很宽泛的社会伦理规范,从而将自然的行孝与外在的阻力之间的矛盾消解统一到内、外相合的社会规范系统,为规范系统转化为更具客观现实意义的律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这个转化过程突出人发现自知为天下贵的人性需求以及君王圣人在发现必然性中的地位,是人的自然性向道德性的提升、人伦发展及社会制度建构之要求而不纯粹是外在力引导的结果。董仲舒意识到人的向善本性及寻求规范后客观规则对于孝的恰当表现及实行有着重要意义,意识到聪明睿智的君王圣人具有示范作用;《白虎通义》将这种寻求归结到在现实性上以皇权为核心的一套制度体系的代言者君权及圣人。公羊学对孝道的这一论说逻辑说明孝作为德性,与规范与制度的结合在理论逻辑上有其必然性,他们关于“孝”的思想道德观点和理论系统作为汉代咨政论理之据,在一定意义上洞见到了人性需求、社会需要和道德发展的某些真理,客观上把孝德提升到了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地位,以孝为本建设纲常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令人可信的理论论证。
第三,孝德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维护了基本人伦道德底线。基本人伦道德底线包含了不可违逆的义务要求,孝德与法律制度的结合体现为“不孝入律”,其中有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双重倾向。汉代治道以孝道的维护为切入点使德与法恰当结合起来,某种意义上甚至使道德与律法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孝是无德,律法对不孝的惩处显然首先以不孝为罪过为前提,对违反孝德行为施以惩罚的本身表明孝德的法律化。可以说,对亲属间相犯之罪的处罚,循的是安定尊卑贵贱之序的道德法,这在社会道德体系建设中切中肯綮,抓住了人伦治理之本,有助于强化个人的基本道德义务,维护社会道德底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不孝入律”罪名多、范围广、惩罚力度大,立法、司法皆有体现。律法条文以及司法实践一度对不孝行为不分轻重、不分层次,一律严惩,由此反映出道德与律法相结合、相整合尚存在问题。当然,纵观汉代,对不孝罪的处罚遵循由严趋宽、由名察实的原则。对不孝罪处罚逐渐减轻,特别是随德化而非礼治的广泛推行,对犯不孝罪的处置由惩治逐渐改为教化改造,反映了在德、法关系之治道策略导向中德主法辅、以德为重的价值取向。
第四,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整合是一个需要诸多有效环节发挥作用的过程。从孝道体现的对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整合来看,道德教育、立法和司法、德与法的关系等是实现整合的重要环节。道德教育是孝德理论与现实制度整合的一个关键,统治者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政治上以孝德治国、教化孝道,制度、政策、措施上强调尊老敬老、旌表孝悌贞顺、孝廉选官、兴学设礼等等,都是实行道德教育、以孝德引导社会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在上者行为世范、以身作则,实践、推广孝德,带动、影响和感化社会下层民众,自上而下的教化与自下而上的推动相结合从而使孝道的实践具有普遍的效应与实质的影响。立法和司法通过律法将德性理论、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的相结合,以具有一定强制力的制度、政策、有效措施加以引导,使孝德的落实与向社会各层面的推广相得益彰,形成广泛持久的合力而能真正深入民心。今文公羊学总体上使孝道嵌入德与法之结合点的原则性看法对德性与制度关系的设置自然产生宏观调节作用,因此之故,主流社会以非强制性的道德化制度引导以及自上而下教化民众、收拾整肃人心,比单纯依靠博士制度、精英阶层之少数人的道德说教以及用律法强力、国家暴力控制、规范、影响人们的外在行为,更显长治久安之效果。以非强制性、合乎人心人情人性需要的国家教化,既不同于主观道德的个人化、理论化和理想化的自我塑形,又不同于律法具有的单纯强制性、惩罚性和外在性的他力成就,而是以多元因素及其调节作用的互补互通而共同造就。执政者如果偏重软性的、理想化的主观人为道德,则只能促进道德理论的研究、形式上的接受而难以对社会现实产生长期有效的实质作用。总之,道德教育、立法和司法、德与法的关系等环节使汉代德性、规范与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整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众自我觉醒、自我约束,树立起了国家制度结构所强调的道德感、羞耻心。
第五,孝德之品性、孝行之规范、不孝罪之律法制度是构成汉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因素,其所蕴含的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整合意义包蕴着道德体系建设的基本规律。社会道德体系是特定社会道德思想意识、规范系统及器物支持系统诸因素的有机整合系统。构成社会道德体系重要因素之一的基本道德理论及其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对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有效整合,往往是衡量社会道德体系是否达到良性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任何一种成熟而完善的、有影响的伦理理论,一般都善于依赖德性养成、规范要求和制度支撑诸因素以体现其存在的生命活力。德性养成使伦理理论的落实具有生长点,规范要求则使伦理理论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而为较多人所遵循,而制度支撑则使上述两者的有效实践有了充分的保障和坚实的支持。公羊学孝道论正是有见于德性、规范和制度之内在关联方式及本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道德生活的实然性、必然性并反映其规律性、应然性,在实践中最大程度地实现德性、规范与制度的结合,使之形成知行一体、虚实相生的系统,成为社会良性运行的保障。
第六,以孝为德本、教化为先的道德观在德性、规范和制度层面史无前例地落实了先儒“孝悌为仁之本”、“先德后罚”论,塑造了汉代崇德向善的时代精神,更奠定了中国传统治道观的价值基础。孝之德性、规范与制度诸层面是有机关联、整合发展之一体存在,这是汉代布衣君相社会取代秦之旧制而渐次创新转化且最终成就的一项文化杰作,其中蕴含着具有某种普遍性价值意义的、事关良性运行的社会道德体系之构成要素所具有的全局性、普遍性、整体性的知识、经验、智慧和德行。其核心有三:其一,论定孝是善行之开端,道德之根本,规范之重点,制度之基础,治道之关键,道德建设与社会治理之要首先在于以此开端、根本、重点、基础、关键为入口,提纲挈领,标本兼治,抓大作细,如此可能终得实效。其二,立足于孝德的养成以成就变化人性之教化,相比于其他治世手段而对民众更具普遍影响力和塑造性,因此而成就王道政治不移之理、不易之则、不变之道。其三,社会治道不仅以启发人的自觉性、发展人的道德性、建设人的社会性为要务,更应以全面的德政为基础,教化为先导,加之以具备严格规约性、惩戒性的规范和制度,最终形成切实可行、周密完善的系统准则体系。对此知识、经验、智慧和德行诸因素有机关联、动态运作、发展变化之形式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以系统性、综合性、整体性的眼光实质性地观照社会道德运行机制本身,更有助于我们以历史上人类善良意识、行为实践、准则体系等方面探寻一种直接关照个体、社会、国家诸方面内涵的治道结构,从而把普遍认同的善的理念落实于社会人心之业,落实于国家社会之道,以形成良知德性、公序良俗。正如“六艺”之原的《易》*刘歆云:“六艺之文……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班固《汉书·艺文志》卷30)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社会大系统的良性发展有赖于伦理理论对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有效整合。通过对孝之德性、规范与制度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考察,在揭示传统孝道对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整合这一命题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注重道德观念与社会基础存在之间、道德观念与现实之间可能的和必然的互动关系。
综括上论,汉代春秋公羊学被认为是五经诠释的核心,它不仅为儒学立为官学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而且其所提出的各种理念对于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孝道论由于公羊学的经学品性、官学地位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孝行实践,以孝断狱、春秋决狱作为司法原则推动了以“不孝入律”为中心的律法制度建设,促进了孝德与社会规范、制度的有效整合;以孝为德本、教化为先的道德观塑造了汉代崇德向善的时代精神,奠定了中国传统治道观的价值基础,其历史经验当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和伦理理论提供某些值得思考和借鉴的经验。
[1] 班固.汉书·儒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201-206.
[3] 汤一介.中国儒学史:两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60.
[4]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5] 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 王先谦.荀子集解·子道[M].北京:中华书局,1988:397.
[7] 贾谊.新书校注[M].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303.
[8] 赵俊.说“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5).
[9]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 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7.
[11] 杨伯俊.孟子译注·告子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4.
[12] 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M].北京:中华书局,1988:397.
[13] 桓宽.盐铁论·刑德:卷1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8.
[14] 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91.
[15] 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163.
[16] 孔颖达.尚书正义·周书·康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34.
[17]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8] 刘厚琴.汉代“不孝入律”研究[J].齐鲁学刊,2009(7):39-44.
[19] 刘厚琴.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D].山东大学,2006:15.
[20] 秦双星.传统社会和文化——以汉代孝亲案件为例的考论[J].社科纵横,2011(1):61-64.
[21]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9.
[22] 李源澄.经学通论[M]//林庆彰,蒋秋华.李源澄著作集(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6-7.
(责任编辑:祝春娥)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with Virtues,Norms,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Filial Piety by the Schools of the Biography of Gong Ya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ractice of the Filial Piety in the Han Dynasty
Wang Wen Dong
(SchoolofPhilosophyandReligion,Central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Beijing100081,China)
Chines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is not only a moral virtue and social ethics,but also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s such as decree and etiquettes, etc. under certa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Thus it has become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mainstream social moral system for its attention to social norm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Biography of Gong Yang in Han Dynasty is not only the main interpreter and elucidator of the theory of Confucian filial piety at that time,but also th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had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social morality in the Han Dynasty.ChunQiuFanLuby Dong Zhongshu,BaiHuTongYiwhich was written by Ban Gu andInterpretationofChqiuandBiographyofGongyangby He Xiu formed the main vei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ography of Gong Yang in Han Dynasty,which deepens the theory of filial piety of Pre-Qing Dynasty in the way of expounding filial piety with Tao,states filial piety with righteousness,analyzes and expands filial piety by propriety. And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are combined together,which makes it not only become the Han Dynasty's mainstream social filial piety theory,but also the main social moral system at that time. The theory of filial piety by the Schools of the Biography of Gong Yang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filial conduct at that time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s and official status. To adjudicate cases with the filial behavior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s the judicial principle promoted “inserting the rites into the laws” as the center of the law system construction,and also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filial piety with the social norms and system. In addition, the moral concept of the filial piety as the fundamental of morals and the enlightenment forme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such as the goodness and morals in Han Dynasty,laid the value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view of governance,and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might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social moral system and the research of ethical theory.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the Biography of Gong Yang in Han Dynasty; virtues;norms;system
2015-07-0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AZD008);中央民族大学社科项目(2015MDTD34C)
王文东(1970- ),男,甘肃张掖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B2
A
2095-4824(2015)05-0005-12
主持人语:
汉代独尊儒术,重视孝道,坚持“以孝治天下”,将《孝经》列入七经之中,公羊学派属于今文学派,其代表人物之一董仲舒对汉代思想和政治都发生了很大影响。王文东教授所撰《论中国传统孝道对德性、规范与制度的整合及其历史经验——以汉代公羊学孝道论及其影响下的孝行实践为中心的研究》对这一学派关于孝道的理论、实践及对汉代社会生活影响的诸方面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是一篇文献扎实、颇有新见的优秀论文。在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儒、佛两家在孝道问题上是既有对立又有融合,《儒、佛孝亲观理论依据之比较》一文对二者的孝亲观理论依据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近似与补充的关系,选题有意义,分析也较为深入。儒佛两家在孝道观上的融合不仅体现在形上根据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和艺术之中,佛经中产生的“目连救母倒悬”的故事在传统中国被大量改编为各种目连戏,甚至我们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也是受其影响而形成,《从目连戏看儒家孝亲思想对佛教文化之影响》一文选题独特,分析周密,其对目连戏的形成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有助于认识外来佛教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形成汉传佛教独特文化品格的现象,更有助于认识中华传统孝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影响力。《中华孝文化的历史嬗变与时代内涵》《中华孝道的内涵特征及伦理精神》两文都能把传统的孝文化与当今社会的孝道实践相结合,虽有泛泛而论之嫌,但也力求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