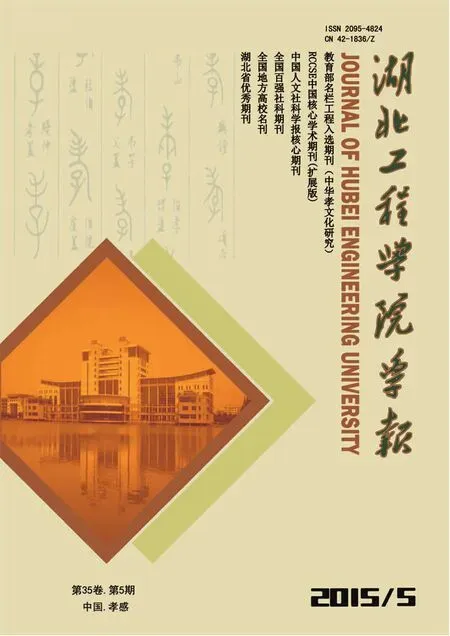儒、佛孝亲观理论依据之比较
刘昱均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100081)
儒、佛孝亲观理论依据之比较
刘昱均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100081)
儒家孝亲观与佛教孝亲观的相互融合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孝亲思想。对儒家孝亲观与佛教孝亲观的理论依据进行比较发现,无论儒家的祖先崇拜还是佛教的缘起论,儒家的人性论还是佛教的佛性论,儒家的仁爱论还是佛教的人生论,儒家的天道论抑或是佛教的业报因果论,它们之间更多的是理论依据差异基础上的近似与补充延伸关系。儒家孝亲观的理论依据于世间之道,展示为世间之孝,佛教孝亲观的理论依据于出世间之道,展示为出世间之大孝,二者之间表现为补充性延伸的关系,对引导现实中的孝亲、孝行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儒家孝亲观;佛教孝亲观;理论依据
中国传统孝亲观可谓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比较儒家孝亲观与佛教孝亲观理论依据之间的关系,更有利于促使中国传统孝亲观在现实层面的实践与发展。儒家孝亲观几经发展演变,核心地位无可替代。佛教虽然远自南亚而来,但自两汉传入中国,在原有佛教伦理基础之上,通过与本土传统思想的融合互通,形成了佛教在中国特有的孝亲观。本文欲通过对二者理论依据之比较,发挥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进而使整个社会能够重视孝道,个体能遵从孝道、践行孝道,达到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中国传统孝亲观在和睦家庭、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主导作用的目的,此乃本文写作之初衷。
一、祖先崇拜与缘起论
中华孝文化源远流长,“孝”作为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根基,它的起源,学界基本统一为:孝观念正式形成于周初,大兴于周代。[1]它是儒家孝亲观的理论来源及基础。加之佛教孝亲观,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孝亲思想。
1.儒家孝亲观源自祖先崇拜,佛教孝亲观源自规律发现。儒家“孝”的萌生与发展源自先秦初期先民的祖先崇拜。对死者的本能性敬畏及生存的种种需求,是崇拜的主要动因。先民们相信祖灵有神通,可以福佑子孙,也可以降临灾祸,所以子孙要敬祭祖先,以求家人平安,这些都带有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祖先崇拜是在鬼魂崇拜基础上,由生殖崇拜的传宗接代意识,加上图腾崇拜的氏族寻根意识和后起的男性家族观念,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远祖崇拜,主要是崇拜祖先的崇高人格和丰功伟绩,进而发展为圣贤崇拜。[2]
氏族社会后期,女性祖先崇拜被男性祖先崇拜取而代之。男性祖先崇拜对象往往是半人半神以人为主,或者氏族部落群体代表,或者有神奇的能力者,他们对中华文明创造皆有贡献。例如,《庄子·盗跖》与《韩非子·五蠹》中所说的“有巢氏”,《韩非子·五蠹》中所提“燧人氏”,《周易·系辞下》所说“伏羲氏”,以及神农氏、皇帝、炎帝太昊氏、少昊氏、颛顼、帝喾、陶唐氏帝尧、有虞氏帝尧等。这些男性远祖英雄,既是血统上的祖先,又是道德上的表率,还是政治上的领袖。近祖崇拜表现为对祖辈和父辈的丧葬祭祀,与现实生活十分切近,是祖先崇拜的重心所在。[2]114
佛教孝亲观以缘起论为理论依据。佛教认为,宇宙万物无不由缘而生,由缘而起。据《缘法经》记载,当问及缘起论是何人所创时,佛陀回答说:“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杂阿含经》卷一,第12经等)缘起法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不是圣人的臆造。不管佛陀出世与否,缘起法都永恒常在,佛陀只不过是彻悟这一法则而成正觉,依据自己的证悟为诸众生显示、讲说这一法则,佛陀是这一法则的发现者、解说者而非创造者。
何谓“缘起”,“缘”是结果所赖以生起的条件,“起”是生起的意思。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起,都是由相互之间关系决定的。佛教认为宇宙人生的种种现象皆在关系中存在,无独立的个体,会因关系的分离而消失。佛教常用“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来说明缘起的理论。也就是“诸法待缘而生,缘尽而灭”。缘起论的实质就是事物间的因果关系理论,缘起论主张世界万物无一不是由因缘和合而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互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互为因果的,都处在因果相续相连的关系之中。[3]114依据缘起的立场,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每个个别都是相互依赖的因子,而非独立的存在。[3]51佛教缘起理论将天下众生息息相连,为佛教孝亲观在理论上提供了佛法依据。由此可知,佛教孝亲关系就是与不同众生之间结下的因缘果报关系,范围之广,时间之久远无法计量。
2.孝亲观的补充与延伸:基于生活的祭祀活动与高于生活的佛陀尽孝。男性近祖崇拜是在父权制度发达和鬼神观念加深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中国最受重视,表现为男性家长丧葬的隆盛,丧仪的繁细,正是孔子所说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近祖崇拜源于对祖先德能的敬仰,对祖先留给后代财富的回报,对祖先的追思与继承,祭祀祖先便发展成弘扬孝道。《礼记·坊记》说:“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古代孝亲观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并大兴于周代,成为儒家孝亲观的理论基石。原因是自然界给了我们衣食,祖先给了我们生命,所以要报本达恩,方式便是敬天祭祖。《礼记》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郊特牲》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这是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观念。[2]
印度原始佛教“孝”的具体内涵,可以从释迦牟尼的实际行动中获知。乔达摩·悉达多为了了悟通达,不顾世俗情感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舍弃他显耀的皇室王子地位,放弃丰裕富足的物质生活,离家苦修,经过六年的苦行参悟,乔达摩·悉达多最终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4]35-42
成佛之后的释迦摩尼带领僧团返回王宫,为父亲及家人当面讲说了佛教的“四圣谛”、“十二因缘”、“八正道”教义,并为父王开示三皈依。在一个月之后,为了救度众生,佛陀赶回祗园精舍继续布道众比丘。当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佛陀再次返回迦毗罗卫国,拉着父亲的手,父子俩的手久久相握着,净饭王安详地走入另一个世界。佛陀亲自料理了父王的后世。[4]35-42至此,世尊尽了儿子所应尽的世间之孝。
佛陀在世间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佛教关于孝的理念与思想。其一,释迦牟尼认为在王宫整日陪着父亲不去修行悟道,不能算是对父亲的真孝,而离家寻道了悟成佛才能回报父亲,解决一切众生生老病死的苦恼,方是真孝;其二,当释迦牟尼成佛之后,又及时为父亲及王公贵族亲自说法,使父亲听闻佛法,了知生死,方便解脱,是对父亲之大孝;其三,父亲病危之时,佛陀久久握着父亲的手,既陪伴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刻,尽了世间的孝行,又把父亲亲手送到了另一个世界,尽了世间与出世间两方面的孝。由于释迦摩尼出世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记载,佛陀上升到忉利天为母说法,报答母恩,这是佛陀对母亲的孝。
3.孝亲关系的补充与延生:长幼有序与众生平等。《说文解字》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也。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5]这种观点把社会归结为家庭,把家庭归结为两性,把两性归结为自然,而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家族关系是古代社会的基础,祖先崇拜体现着古代家族社会的生活,是中国古代孝亲观萌生的根本原因。[2]47-57早期孝道表现为晚辈对长辈的敬畏、崇拜,用上下有别、长幼有序、层次明显来和谐家庭,稳定社会,更好地体现了尊顺之孝。这种基于家族社会的孝确实解决了现实生活的问题。[2]47-57
佛教孝亲观的众生平等之孝,首先把父亲视为与自己一样的众生,同时把父亲视作与其他种姓无二无别,即佛陀认为一切众生悉皆平等。佛陀在世时曾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这一点。据载,一天佛陀正在王宫里为王公贵族们说法,这时候来了当初送佛陀去修行的驭手首陀罗族人阐铎迦,他当即跪在佛陀的座前,请求皈依佛陀。智慧的佛陀没有马上答应阐铎迦的请求,而是暂让阐铎迦回避。然后佛陀向在场的王公贵族们说,一切众生在灵魂上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他是王宫贵族还是低等种姓,只要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都可以达到成佛涅槃的境界。佛陀的解说扫除了王宫贵族们身上的骄傲之气,从而对阐铎迦的皈依,不再提出任何异议。不久之后的一天,佛陀的姨母王妃和妻子耶输陀罗公主带着五百人的女性队伍来到祗园精舍请求皈依佛陀,成为女性出家者。起初佛陀没有同意,但后来这五百女众都皈依了佛陀,成为释迦摩尼僧团中第一批女性比丘尼。这再次体现了佛教对待众生的平等理念,当然令众生学佛同样是行善尽孝。[4]35-42佛教缘起理论的众生平等观表现在:
其一,一切众生皆父母。《戒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佛教的缘起论从内缘起把众生联系起来,众生因为贪、嗔、痴、慢、疑以及累积起来的烦恼习气造作了各种业因,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因缘果报,致使不同的众生都可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众生因在六道的留转而迷惑染污,无法记住曾经的父母。例如,今生是父母子女关系,此生了却前世因缘后,来生就不再是父母子女关系,会因缘分的深浅而成为其他角色的关系成员,而父母又是另外的男女众生了,这样循环往复,一生又一世,每一位众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六道中轮了多少回,于是有了无数的父母众生。此乃佛教所谓“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人皆我母”孝亲观的缘起根源。
其二,平等对待众生,孝敬众生父母更是成就佛道所需的福德资粮。《大智度论·卷九十五》指出:“若能自舍己乐,但为一切众生故行善法,是名上人。”佛教认为,教化众生行善、慈悲助人,发菩提心,救度苦难众生乃是成佛的途径。古人云:“百善孝为首,不孝父母,拜佛无益。”不孝父母,学佛或行作一切功德,皆无意义,可见孝顺父母为世间最大功德福田。
其三,平等孝敬众生父母,劝学佛法,了脱生死,以报亲恩。《佛说父母恩重经》中记载:“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是以寄托母胎十月,岁满月充,母子俱显生堕草上……饥时须食,非母不哺,渴时须饮,非母不乳……呜呼慈母,云何可报?”报答的方法,就是劝父母学佛,修善集福,命终之后出离六道,不再轮回,报恩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自度度他同时进行,皆大欢喜。
如此,佛教孝亲观就将儒家世间的行孝,进一步延伸到了往世、来生,扩大了行孝范围与行孝时限,为现实行孝大众提供了可信的理论依据。
二、人性论与佛性论
1.儒家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性论与佛教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论观点极为相似。儒家人性论的观点主要有:“人皆可以为尧舜。”[6]荀子说:“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可见,孟子与荀子都认为,人性无有差别,人性上的平等性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圣成贤。就成圣而言,古人认为只要遵守尧舜之道,“孝其所当孝,弟其所当弟”,也就是把孝顺父母,友善兄弟这样的规范行为做到了,就是圣贤之人了。[7]儒家关于人性的观点还有,孟子曰:“……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上》);“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人人有贵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等。当然,儒家还有其他有关人性的观点,例如,荀子认为人性“义利两有”,董仲舒认为人性“仁贪两有”等,但均未影响儒家上述关于人性论的普遍观点。
儒家人性论观点无论是“始出善,还是渐成善”,我们都可以发现,关于人性观点的终极态度都是“善”。例如,人有善端,求而得之;善始后天,积之成圣;性有善质,受教而成,性善恶混,修行成善。圣贤是儒家倡导的道德楷模,成就圣贤贯穿于儒家思想的始终。那么要成为圣贤就要从行孝开始,孝是基础,如果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成就圣贤无从谈起。关于这个问题,《孝经》明确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篇》)“孝”既是德的根本,又是德的彰显。教育从教孝开始,做人从行孝做起。一个人只有怀有对父母的感激孝顺之心,才有可能存有对外在人、事的感恩之心,才有可能成为圣贤之士,这也正是先王的至德要道。佛教也认为,只有做到儒家所倡导的这种真诚至孝,积善积德,才有可能成就佛果,孝是成佛的基础。[8]15
佛教关于人性论的基本观点就是佛性论的基本观点,也即佛教的人性论。佛教人性论关注什么是佛性,佛性是否众生皆有,即众生是否有成佛的可能性。[9]114-118据资料记载,佛性论问题应该形成于部派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时,发展于中期大乘佛教兴起时。[9]114-118中国佛教中佛性论观点认为:“佛身常住不灭,涅槃常乐我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一);东晋高僧竺道生主张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包括一阐提人在内;慧皎在《高僧传》中言:“阿阐提人皆得成佛”;禅宗慧能大师认为人的本心清净无染,真如本性,也就是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主张佛性平等,因迷与悟产生差别。慧能大师在《坛经》中言:“菩提波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随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遇悟即成智”,“……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修行定成佛”,“人有两种,法无不一。迷悟有殊,见有迟疾……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天台宗湛然大师进一步提出“无情有性”说[9]124-142。可见,佛教人性论观点认为,一切众生皆有无二无别平等的佛性。
至此,佛性论为佛教孝亲观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其一,既然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与佛陀无二无别的自性本心,那么善待众生,就是善待未来佛,孝敬父母就是供养未来佛。其二,既然众生佛性平等,成就众生本真佛果,也是修行佛弟子本然所为,内涵孝道在其中。第三,既然众生本性清净无染,那自不用分别心对待,应当将众生与父母同等看待。第四,既然无情有性,那么善待周围一切事、物也不无道理,自然延伸到了对众生的孝。
2.儒家与佛教均重视孝道,倡导发自内心的恭敬行孝。 儒家把孝的重要性与天地相比拟。例如,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我们知道日月星辰亘古恒常照耀大地,大地承载万物无始无终,不分丑陋贵贱,高低好坏,无限包容,孔子正是用天地的无私付出来比拟行孝也应像天地之恒常一样善事父母,像天地之恒常一样无条件,无终始。正因为人的此种德行,所以与天地合称为三才。
佛教重视孝道可以从佛教众多关于孝亲的经典中获证。代表性经典有:《佛说孝子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说孟兰盆经》、《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杂宝藏经》、《六度集经》、《大般若经》、《大涅盘经》、《百喻经》、《百缘经》等。其中《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就详细地讲述了父母对子女的恩德,经中记载,父母对子女有如下十种恩德:“父母祈求生子和呵护胎儿、临产受苦、生子忘忧、咽苦吐甘、推干就湿、乳哺养育、洗灌不尽、为造恶业、远行忆念等。”然而,父母对子女的恩情,子女毕其一生也未必可以报答。
发自内心的恭敬行孝,始终是儒家孝亲观所倡导的。《孝经》有具体表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纪孝行章》)又如,《论语》记载,子游问孝,孔夫子讲:“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可见,只有发自内心的恭敬供养父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
佛弟子虽然出家,但往往能生大愿,发菩提心,生生世世修无上善法,慈悲救度众生父母。佛弟子修行善法救度众生的愿行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文珠法师云:“众生因为历劫深恩,既非财物可报;更非尽一生的时间,或尽一生的力量可以成办。必须发愿,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广修六度四摄,广行诸佛无量道法。以财布施,解救众生,生活困苦;以法布施,解除众生,精神饥渴;普令多生曾为父母眷属的一切众生,知因识果,止恶修善,敬信三宝,同发菩提心,共度生死海,同登涅槃岸,彻底离苦得乐,乃尽孝道,才是报恩。”[10]可见,佛教是在重视孝道的基础上修无上善法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
3.儒家与佛教均以报本还恩之本性作为孝亲观的理论依据,但佛教又补充并延升了这一范围。儒家“人性善”论为人有报答父母恩德之本能提供可靠理论依据。例如,《孝经》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又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篇》)儒家认为,保护好自己是尽孝首先要做到的,然后,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取得社会和国家的认同与荣誉,以此来荣耀父母,使父母英名显扬,即儒家倡导的终极孝道。以上皆为儒家报本还恩之孝的外在表现。儒家提倡的仁德孝子,范仲淹可为典范,小时候范仲淹因为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另嫁,受到朱家人的鄙视,当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毅然决然别母求学,住进一个破旧的寺院苦读五载,衣不解带,每日断齑画粥,最终功成名就。他饮水思源,知恩报恩,将母亲接回家奉养,使父母名声显扬。
当然,儒家的孝也有层次性,正如“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篇》)。儒家孝道的三个层次表现为,在家要对父母尽孝,出外要为大众、社会服务,称为事君,终其一生将这样的行为发扬光大,视为至孝。可见,儒家也将行孝的范围从家庭扩展到社会。
佛教孝亲观不仅事奉父母,更是劝说父母学佛解脱,不仅报答现世父母恩,更报答众生父母恩。佛教认为,人们生活在世间,有四重恩德需要报答,即三宝恩、国家恩、父母恩、众生恩。三宝恩指佛、法、僧三宝之恩,能以正法利乐众生,令人远离苦因,得安乐果,永别烦恼,长养慧命,恩同再造,名三宝恩;国家恩是指执掌政令,保卫民生,维持秩序,使人生命财产获得保障,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皆有恩于人民,人皆应该知恩图报,遵守法令,辅助仁政,以促进社会繁荣,国家富强;佛教基于众生三世六道生死流转之理,故一切众生,可能是自己多生多世的父母眷属,关系密切,相互有恩,所以要报父母恩;人不能离群独居,彼此之间,必需互相依赖,互惠互助,被称为众生恩。实际上,佛教报本还恩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父母众生,更扩展到三宝、国家。可见,儒家虽也将孝的范围扩展开来,但与佛教之孝相比局限性比较明显。
三、仁爱论与人生论
儒家的仁爱论与佛教的人生论共同将“孝”从小范围的“孝亲”推向更大范围的“孝德”,不仅如此,佛教还将孝延伸到了世间之外一切众生。“仁”在中国传统儒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仁最早出现在《国语》中,“为仁者,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一》)。可见,仁的含义就是对父母双亲之爱。[11]103-105“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为人即是行仁,就是实践,仁的实践以孝悌为根本,就是对父母双亲的爱,对兄弟的悌。孔子继承了春秋时期仁的观念,明确指明了仁与孝悌之间的关系。孔子给仁赋予丰富的道德内涵。仁包括了“克己、孝悌、自爱”,还包括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及规范,仁被儒家视为全德。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这一思想在当时已经成为儒家的共识,仁是爱人的德行,超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爱之情,但在实践上以孝悌为起点。[11]103-105孔夫子对颜回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并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大家都能这么做,天下自然归于仁了。[11]103-105儒家仁的另一层内涵是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据此,仁爱的内涵已经完全扩大,扩展到了对大众的爱。
佛教通过对生命万物无常变化的分析,将人生观引向解脱,认为人生在世应该在孝敬父母的同时,更要劝导父母学佛,了脱生死。正如古大德莲池大师所言:“人子于父母,服劳奉养,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显之,大孝也;以念佛法门,俾得生净土,大孝之大孝也。”[12]佛教的这种有层次的孝道将儒家世间之孝扩展开来,延伸出去。佛教人生论指引众生行孝出离,最典型的孝亲代表就是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地藏王菩萨在过去生中曾轮转为不同角色,长者子、婆罗门女、光目女、国王等身份,均发大愿力来报母恩。地藏王菩萨在长者子一世时,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佛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于是长者子发愿:“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为婆罗门女时,为救度母亲,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为光目女时,因母堕入恶道,啼泪号泣而白空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毕十三岁,更无重罪,及历恶道。十方诸佛慈哀愍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及斯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华目如来像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饿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竟,我然后方成正等正觉。”地藏菩萨累生累世以来,为了度脱母亲,发大重愿,孝心深入三界六道,至诚至深。因此,佛教人生论基础上的孝亲观比儒家仁爱论基础上的孝亲观更加深远宏大,将世间之孝推广到了出世间的范围。
四、天道论与业报因果论
儒家天道论把天道与人道相联系来善导大众,与佛教业报因果论用善恶果报引导大众弃恶向善极为相似,孝顺父母得大回报。史书记载,周朝取代殷商后意识到,天道、天命不是恒常的,如果统治者不爱民,天道就会取消其合法性,所以周初的统治者开始有了“敬德保民”的责任与忧患意识,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论语》记载,对“天道”有了敬畏之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可见,周代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德性的重要,于是天子敬德,赐民以德,还意识到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行德,获得上天的护佑,延长来之不易的统治地位。周代重视德行,应该也是周代孝行大兴其道的原因吧。所以孔夫子非常重视仁德,正如孔夫子所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孟子用仁义礼智这种人自然生成的善端来引导人们向善。孟子认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也,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衣食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人如果能行四善端,就足以奉养父母,这是孟子天道论的观点,即善有善果。荀子曰:“一要明天人之分;二要循天行有常,三要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荀子认为,弄明白这种天命自然规律至关重要,只有掌握并遵循这种规律,人才能从中受益。例如,恭敬孝养父母之事是子女必须遵守的规律,这样人才有主动掌握命运的机会,儒家天道论的善恶观亦显而易见,因果规律藏于其中。
实际上,《孝经》所述“三才者,天地人”(《孝经·三才章》),正是倡导人应该效法天,行无我无私之道。人与天、地合称三才,一方面表明人与天地同等重要,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人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能像天地一样无私付出,就会与天地同在,得生光芒,益处无限。所以,结果好坏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行为,人能善待父母,就得上天恩泽,不善待父母就不得上天护卫,道理就在其中。善恶自行,结果自造,正是因果律的自然体现。
佛教有关业因和业果的学说发展出了“因果报应”与“六道轮回”学说。“业”原来的意思是造作,泛指有情众生的一切身心活动,即内心的思维活动和由内心思维活动所引起的一切意志、语言、行为等。佛教认为,有情众生的内心思维活动以及随之而起的言语和行为,必定会引起一定的业力。这种业力不会随众生行为的结束而终止,而是随着缘的成熟而产生,这就是业报因果论,善的业力产生善的果报,恶的业力产生恶的果报。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有因必有果,任何事物背后都有某种决定此事物非彼事物的必然原因存在,因果规律普遍存在。佛教基于这种因果规律,认为孝敬、恭顺父母就是行善法,因缘成熟,自然得善果,相反如果不孝父母行恶法,将来必定得恶果。
明白因果规律之后,人们就会主动遵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道德。行孝,报答父母之恩,循天地本然之意,自然得善报。例如,汉文帝行纯孝,大家都推举他作皇帝,就是孝道感召的善果;又比如,大舜本是一个平民百姓,因为将孝行做到了极致,尧帝把位置禅让给了他。[8]86正所谓“人以善感,天以福应。人以恶感,天以灾应”[8]79。可见,儒家天道论与佛教业报因果论共同将尽孝视为善行,种善因,必将获得善果。
综上关于儒、佛孝亲观理论依据之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在构筑中国传统孝亲思想上虽有差异,但更多的是近似与一致。无论儒家人性论还是佛教佛性论都使人们明白,行孝乃人之本性所然,纵使大小不同,范围不一,但只要恭敬行孝就是正当;无论儒家仁爱论还是佛教人生论都将这种孝亲观念推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人间处处皆是爱,了脱生死扩展爱。天道论与业报因果律共同揭示了遵守善恶规律的重要性,也是人获得主动性的关键所在,孝之者,德必积之,财必随之。正如《中庸》所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中庸·十七章》)可见,孝乃德之始,德乃善之基,得乃善之果。
概而言之,儒家与佛教孝亲观在理论依据上虽有差异,但二者更多的相似与佛教对儒家孝亲观的延伸性补充,为中国传统孝亲思想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为孝亲观的践行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一方面,儒家与佛教在世间孝亲理论上极为相似,另一方面,佛教为儒家未曾涉及的出世间之孝予以相应的补充,二者共同筑起了中华孝亲思想的理论大厦。通过对二者理论依据的相互比较,可以促使中华孝亲观在新时期发挥更加积极的教育、指导作用,使得中华文化精髓——孝亲观这一人类精神文明得到合理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家庭和谐、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需要。只要人类存在,这种报本还恩的孝亲观念就不能丢弃,因为为人子女心怀孝道、珍视孝道、践行孝道是人性使然,时代必然。
[1]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
[2]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 黄复彩.佛教的故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5] 李新璐.周易[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193-194.
[6] 李新璐.中华国学经典编读丛书·孟子[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200.
[7] 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3.
[8] 钟茂森.钟博士简讲《孝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9] 业露华.中国佛教伦理思想[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0] 文珠法师.无尽的孝道——地藏菩萨[EB/OL].(2014-12-02)[2015-07-10].http://www.365ag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79.
[11] 陈来.仁学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2]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EB/OL].(2011-08-25)[2015-07-10].http://www.xuefo.net/nr/article9/85222.html.2011/8/25 7:36.
(责任编辑:祝春娥)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Basis of Confucian Filial Piety and that of Buddhist Filial Piety
Liu Yujun
(SchoolofPhilosophyandReligion,Central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Beijing100081,China)
The 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 filial view with the Buddhist filial view have form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ideolog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made comparisons of the theoretical bases between the Confucian filial view and the Buddhist filial view and found that between them there was more approximate and complementary extension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differences with regard to the Confucian ancestor worship and the Buddhist origin theory, the Confucian view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Buddha Aaron,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and the Buddhist view of life, the Confucian natural law and the Buddhist karma causal theory. The Confucian filial view depends on the way of the world to show the world's filial piety whil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Buddhist filial view is from out of the world’ s way to show out of the world's great filial piety. The two have a complimentary extension relationship and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guiding and fulfilling filial piety.
Confucian filial piety; Buddhist filial pie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2015-08-15
刘昱均(1974- ),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B823.1
A
2095-4824(2015)05-00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