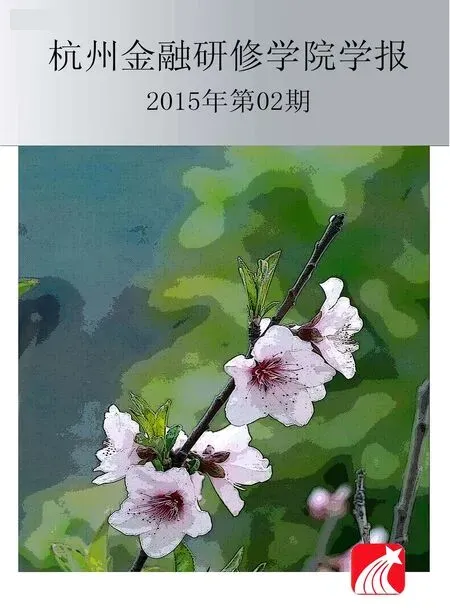国道318六十年祭
陈寅生

2014年的12月2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是318国道川藏线建成通车60周年。我家老爷子曾与这条路结下不解之缘。为了纪念他逝世两年去年我第三次进藏,特意在318国道川、藏、滇交界的巴塘县转悠了好一阵子,选在河谷区那一段的公路边,焚香三炷祭拜了当年的那些英灵,追思感悟当年他老人家川藏公路的情结。当时就觉得玛尼堆上悬挂着的翻飞呼啸的经幡,呼啦呼啦呼啦的越来越响,仿佛把老人家和筑路官兵们的英魂都召唤回来了……
1950年初,成立不久的共和国虽然还笼罩在一片欢庆的气氛中。但是在祖国的西南一隅,彼时尚未解放的西藏的政治情形十分复杂。据史料记载,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当时也在焦急中等待着内地的消息。却接到西藏葛厦(西藏原地方政府)的通知,要求他在两个星期之内,带领所有人员离开西藏。理由是国民党走到哪里,共产党就会追到哪里……陈锡璋意识到事情不那么简单,想向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汇报,却发现驻藏机构、住宅都被藏兵把守了,发电机也被拆卸一空,电台已经无法开启。拉萨城里连做裁缝的汉人都被勒令离开。这就是发生在拉萨轰动一时的驱赶汉人、密谋独立事件。
解放西藏,实现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成为新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毛主席接连做出了“进藏宜早不宜迟”“解放并营救西藏”的指示。党中央明确了进军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去完成。以刘伯承、邓小平为领导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的最终决定是:进军西藏的前期任务交给解放军二野十八军担当。
二郎山英雄情长
我们如今驱车行进的318国道川藏公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交通图上只不过是一根若有若无的虚线,那时对茶马古道了解的人还不多,肯定不会像现在的驴友们那么稔熟,那时的路况充其量就是骡马踩踏出的一条羊肠小道而已。要想实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军西藏,就必须建设一条从四川进入西藏的公路。二郎山是千里川藏线上第一道险关,被人们称为“天堑”。它海拔高度3213米,在川藏线上突兀横亘。大半年冰雪、暴雨、浓雾连连;常年滑坡、崩塌、泥石流不断。当地曾经有“车过二郎山,如进鬼门关,就算不翻车,也要冻三天”的谚语。
如果说二郎山是“川藏路的咽喉”,那么雅安的飞仙关镇则为“川藏路的口腔”。我们先后瞻仰了浓缩着川藏路的历史的“一桥一路”。当年修建二郎山公路,就必须在青衣江上建立起一座桥梁。1950年9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国家交通部公路局决议,在芦山河和青衣江的交汇处修建一座吊桥。该桥是川藏公路的第一座桥,为了抢时间、保进藏历时8个月就竣工通车了,作为二郎山公路的“要塞”,刘伯承为它提写了“飞仙关桥”。七十年代之前它一直被我国道桥专家引以为豪。
而如今在我们车轮下的川藏线,大道如砥的雅康公路段,当时的修建艰苦程度更为艰苦。作为施工难度最甚的雅安至马尼干戈路段其中的一部分,工程于1950年4月开工,由于任务紧迫十八军采取了沿旧路“先通后善”的方法,参加修路的部队没有建筑机械设备,士兵们脱掉身上单薄的棉衣,身上捆绑着绳子,一人扶錾,一人挥锤艰苦奋战了86天。就修通了雅康公路。没有筑路设备,完全依靠人力,按现在的眼光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那是一段与死神抗争的日子。用绳索拴着身子在悬崖上开路,在冰河上架桥。帕龙天险段万仞绝壁上,仍然依稀可见当年将士们用来攀岩凿路的铆钉和木桩。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解放军用了4年时间,修通了长达2000公里的川藏公路,付出了4963名战士军官生命的代价。在雅安双河乡我见过了当年的老战士柯大爷,他曾经跟随十八军筑路进藏。“我不满十八岁就参加了十八军筑路部队,前后有七八年在筑路养路。”他说。周遭经历过雨水冲刷的山路虽然泥泞异常,却把葱茏的灌木“洗涤”得郁郁苍苍。半山腰某处松柏掩映下,有十几座墓碑静静地矗立着。那是修建“二郎山”公路的烈士墓群。据老人回忆,那时的修路工程极为艰苦,一路杂草丛生,接连阴雨不断。病疫肆虐之下,部队患病的官兵达到了三分之一多。他们与天斗、与地斗,每天挖山不止坚持修路。“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的歌声唱响在工地上。
二郎山隧道获得了“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然而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年代,每天4000余辆汽车的通过,使它显得力不从心了。为了实施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四川省将雅康高速公路项目提上了议事日程。二郎山新隧道起于新沟乡蓝坝坪,规划在门坎河左岸设新沟停车区,在堡子上设置泸定服务区,路线长度约18.5公里,其中二郎山隧道长13.4公里。新二郎山隧道被视作川藏线的“咽喉”,集中了各种地质难题有待破解。2012年8月筑路队伍甫一进场,就遭遇到软弱破碎带的障碍,既有瓦斯、又有大量涌水极易塌方。设计部门与施工队伍制订了科学方案,稳扎稳打施工,步步向前推进。隧道终于成功穿越了3条断层破碎带。雅康高速公路计划2017年建成通车,届时从成都前往康定将由目前的6个小时缩短在3小时以内。
经过了尚未启用的泸定服务区来到了泸定桥边。它的桥亭是一座藏式的白塔建筑,亭内有一座呈四方梭形的石碑,碑上镌刻着《康定情歌》、《二郎山之歌》、《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三首歌曲。318公路在无数人的努力下,还将持续得到改善,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路。
老爷子的318情结
1951年10月爷爷作为十八军侦察参谋,随先遣队率先挺进西藏。车辚辚,马萧萧,铁流滚滚,剑指高原开进拉萨。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藏军区,以十八军进藏部队组成军区机关进驻拉萨(归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那一年你爷爷还不满三十岁。”这是奶奶告诉我的。以下这段历史摘自于爷爷的回忆录。
1951年10月7日晴
司令部开大会传达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的出访在苏联的毛主席电报:“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管理西藏,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刘伯承司令对时任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承诺是,任由他从二野所有部队挑选三个主力师,组成3万人的进藏部队。邓小平政委意见是让二野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和最强的军长进藏。原先我十八军的任务是去天府之国的川南,张国华当时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然而在经过思考之后张国华下决心:“我还是带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吧。”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一定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带进西藏。
由于历史上国民党南京政府只是派官员驻在拉萨,但并不驻军。行政事务由西藏政府自行治理。新中国成立前后,西藏上层贵族的分裂者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西藏一直受到外国势力的渗透与影响。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司曹、代理司伦的是鲁康娃。张国华军长拜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又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拜见鲁康娃。鲁康娃自持二品官阶,不但没有出门迎接,甚至见了张军长都没有站起来,非常傲慢地说:“你就是张国华吗?你们在昌都是打了胜仗的,现在进到拉萨了。但是以后如果饿着肚子再跑回去,那要比打败仗还要难受啊!”鲁康娃的态度反动嚣张,原因就是我军后勤给养跟不上。
1951年11月28日雪
解放军进军西藏,除了要在政治上要站稳脚跟外,从经济上就是要解决部队的吃饭。这个问题在先遣部队行军途中已经出现了,并且曾经几度陷于粮荒,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抵达甘孜,队伍粮荒持续一个多月,到昌都缺粮就更加严重了,每人每天只能供给半斤粮食的定量。解决给养的前提是交通应该通畅。十八军全共9个团,1个前出到达拉萨,1个前出到太昭、工布江达。而将主要兵力的7个团全部扑在了修路工程上。西藏是当时全国唯一没有公路的省份,内地的公路通到雅安往西就中断了。因为后方补给路线长,茶马古道的骡马运输,已经影响进军西藏的战略实施,为了不影响和平进军西藏的计划,部队行军多背粮食。除了枪支、弹药背包就是粮食。为什么说进藏艰苦?就是因为负重行远,爬山涉水,爬雪山过草地。这种情况下,修通道路成为迫在眉睫日显重要的任务。
1952年9月27日阴
十八军有个团的副政委刘结挺写信给张国华和谭冠三,提出“因身体不好,不愿进藏”。张国华气得对着政委谭冠三说:“想不到他这样坏!我这一辈子不想再见到他!”谭冠三也有点失去了政委的沉稳,把他给我捆起来!我到哪儿就用马把他驮到哪儿!”事件过去之后他们决定,进藏是件光荣的任务,不能让有些人败坏了名声。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西藏,那位副政委就地转退到了地方……
1954年12月25日,经过了将近四年的卓绝奋斗,川藏(当时又称康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时建成通车了。当时建成的康藏公路的维护管理工作,直属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十八军司令部。爷爷做为甘雅(甘孜雅安)工程处的军务参谋,主要任务按照政委谭冠三的命令,为公路日常维护组建一支亦兵亦工的准军事队伍,公路每前进10公里就设立一个道班,留下三、五名战士,就像古时的驿站那样。他们一边修路,一边剿匪。除了配备必要枪支弹药,还人手配备一辆独轮车,四川人叫它架架车,独轮车曾经是行军的“战马”,在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道路上,军队与民工的粮食被服、枪支弹药全靠架架车驮运。它们留在了川藏线后,就成了战士们手里的筑路用具。每当雨雪天气过后,或是运输车队经过,需要对砂石路面进行保养,独轮车就成了主要的运输机械。虽然爷爷有过挺进大别山,打淮海、进南京等经历,可是在他晚年的回忆里,最忘不掉的还是独轮板车,弥留之际他听到的也是越来越清晰吱嘎、吱嘎的车轮声声。
每留下了一个道班房,就有战友留下来和部队告别。爷爷作为的联络人,和战友们保持着联系。他们当中很多人在那里结婚、生子、终老,一辈子留在了318国道。此行在理塘县的团结村,没想到早餐的“团结包子”让我寻访十八军老战士如愿以偿。当年进藏修路的时候,村民们为欢迎部队发动大家做包子,可是几千人的到来,普通的包子费工费时解决不了需要。老乡们就将包子做得尽可能的大,一个包子就可以供应几个人甚至更多的战士。如今吃“团结包子”已经成了巴塘当地的风俗,有重要的客人或者亲人从远方来到,家里的主妇就会做“团结包子”给客人吃。
有幸见到了老战士的遗孀,大娘说家里的“团结包子”刚刚吃完,劝我在巴塘多留一天,让她女儿做“团结包子”款待我们。我问大娘现在的“团结包子”好吃,还是过去的“团结包子”好吃,老人呵呵一阵笑声:“当然是现在的好吃,现在的包子里是肉,过去的‘团结包子’主要是素菜。”看得出让老人最开心的不光是肉馅儿的“团结包子”,而是能和女儿一家人其乐融融。在种满桃、李、葡萄和各种花卉的院落里,她的大部分的时间除了看书,下棋,就是河边去刨窑洞储红薯,而从来不去打麻将。
沿线的成都部队各兵站,都是当地的学校、医院组成共建单位,在搞好军民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同时,帮助常年在川藏线跑运输的汽车兵解决一些问题。大娘家有三个女儿,除了最小的女儿照顾他的起居外,其他的孩子都在政府部门退休了,其中一个孙子是拉萨的公务员。
去甘孜县看看是奶奶的要求。她说老爷子晚年不止一次提起过,那里有一位牺牲的女兵,曾经说好了是要与爷爷结婚的……我特意去瞻仰了窑洞群遗址。县城外广袤草原视野开阔,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景,想必当年的景色和现在一样。可憾景是人非,不知当年他们是否在这里约会过啊。向左边前行约一公里,不远处可以看见半山坡上上下有两三层“窑洞”。十八军官兵60年前就住在这里,抢修甘孜机场,“窑洞”就是官兵们的营地。当年抢修机场任务紧急条件艰苦,不可能先建住房再建机场,只能挖几孔窑洞晚上休息,但是四川土质不像陕北,一天晚上大雨,窑洞顶盖突然垮塌,住在顶层窑洞的九位女战士全部被埋,她们的年龄都只有20多岁。
现在的甘孜县“十八军窑洞群遗址”已经成为了该县红色旅游景点,有当年的照片记录了甘孜机场是怎样建成的,4000公尺的跑道像玉带一样铺在蓝天白云下。在飞机跑道负重检查验收时,十八军邀请了藏区各方代表乘飞机绕甘孜县城飞行三圈。指挥塔、办公室、食堂、招待所等附属建筑的白铁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一个甲子六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川藏路在不断地改建修缮,从砂石路到柏油路,难以计数的车与人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数以千万吨计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进藏区。柯大爷“十字镐头架架车,劈山涉水去修路”的歌声还在耳畔回响。
2014年的6月虽然已经进入了初夏。可是这个时候的川西藏北还没有初夏的茂盛。路边水塘里白杨和垂柳写满的还是金黄色的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