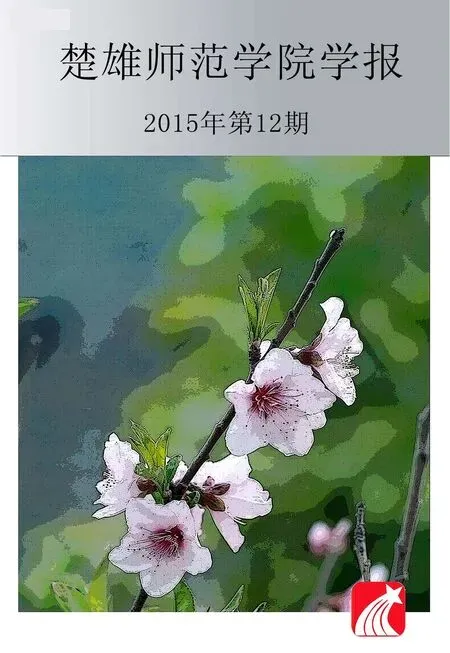源于叟与昆的两元彝族对比研究
唐楚臣,马建荣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楚雄675000;楚雄师范学院,云南 楚雄675000)
一、以叟为基础的彝族分布
彝族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支系庞杂,和多民族杂处,彝族的起源较为复杂,彝族的起源是多元的。叟与昆是彝族起源时的基础,以叟和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是彝族起源时不同的两元。
西汉时期的叟与昆都是彝族先民,叟与昆都是羌与濮融合形成的民族。古蜀人的主体民族为羌与濮,古蜀人遗散南中称之为“叟”。“昆”即昆明,昆也是羌与濮融合形成的民族,但他们是在金沙江两岸融合的结果。方国瑜先生说:“《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南中夷人的两大支系,曰昆、曰叟,昆在洱海区,叟在滇池区。”[1](P35)昆与叟虽然习性相近,经常同处一地,分布在南中广阔的大地上。但昆的主要分布在洱海地区,叟的主要分布在滇池以东地区。滇王归顺汉朝后,汉在滇池地区推行双轨制:虚设滇王,实行郡县。随着郡县制的加强,虚设的滇王不见记载,滇王印也陪葬于滇王墓中,这就抑制了滇池地区叟的进一步发展。而滇池东边另一个叟人聚居区则发展形成了彝族的第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央政权颁发的“汉叟夷长”印即为标志。
彝族形成的另一元是洱海地区,唐贞元时期,洱海地区就有自称为罗罗的彝族先民,罗罗当以昆为基础发展形成的彝族先民。罗罗发展至金沙江北岸成为落兰部,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 年)中央王朝在落兰部设罗罗斯宣慰司,标志着彝族另一元的形成。
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的最初地为朱提,以朱提为核心,彝族向各个方向发展壮大,这在彝族文化中的反映就是六祖分支。蜀王杜宇失位“复位不能”,“隐西山焉”。杜宇即彝族始祖笃慕,西山即洛尼白,笃慕在洛尼白娶了三仙女成亲,生下了六祖:慕阿切、慕阿枯、慕阿热、慕阿额、慕阿克、慕阿齐。笃慕在洛尼白主持了“六祖分支”,六祖即彝族最初的武、乍、糯、恒、布、默六支系,六支系从洛尼白向外发展。笃慕为始祖,这是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的文化标志,六支系的分布大体能反映出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分布状况。
关于六祖,滇川黔彝文典籍多有记载,贵州有《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四川凉山有《勒俄特依》;云南有《夷僰榷濮》、 《赊窦榷濮》等。三星堆古城水淹,杜宇失国,“隐西山焉”,这是公元前的事,而彝文成书为明清,其间有两千年的跨度,故六祖典籍在传抄中多有出入讹误。易谋远先生在《彝族史要》中对其比对研究,认为:
“彝族六祖”即笃慕的六个儿子,分居各地,向西南发展……长房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向“楚吐以南”发展成为武、乍两个支系,分布于滇西、滇中、滇南一带,是当地彝族及其他彝语支的一些民族(如哈尼族)之祖……次房生子慕雅热、慕雅卧,分布在“洛博以北”,发展为糯、恒两个支系,在云南昭通和川西、川南一带,为今昭通、凉山和四川盐源、古蔺等地彝族之祖……幺房生子慕克克、慕齐齐,向“实液中部”发展,为布、默两个支系,为今云南会泽、宣威、曲靖、镇雄和贵州毕节、六盘水、兴义、安顺等地区以及广西隆林等地彝族之祖。[2](P315)
六祖迁徙不定,但上面所述,大体反映了彝族六祖迁徙后分布的情况,也大体反映出以叟为基础的彝族分布的状况:川西、川南、滇中、滇南、滇东、滇北和贵州毕节、六盘水、兴义、安顺等地区以及广西隆林等地。
《夷僰榷濮》、《赊窦榷濮》的地名大都为彝语古地名,难于翻译,翻译者朱琚元先生认为六祖迁徙走向为:
武、乍向南方(滇南、滇西南),
尼、恒向北方(川西南),
布、默沿江走(滇、黔境金沙江南侧)。[3]
这和易谋远先生所述基本一致。彝族六祖史以口传和古彝文形式在滇川黔彝族民间广泛流传,以彝文形式流传的有多种版本。学术界普遍认为川、黔彝族是从云南,特别是朱提向外发展形成的。慕雅切为武部,慕雅考为乍部,慕雅热为糯部,慕雅卧为恒部,慕克克为布部,慕齐齐为默部。经笃慕主持,六个部落向各处发展,在发展中不断融合其他地区民族,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按彝文献记载,武、乍二部在云南作了大范围的迁徙,最后进入成都。糯部则进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建昌、雷波、黄郎、波卜一带,结合当地民族,最后发展成为“曲涅”彝族。恒部在迁徙过程中,和濮人融合,分为三支,一支定居昭通,发展成为乌蒙部彝族;一支经贵州毕节迁到四川省叙永、古蔺一带,发展成为“扯勒部”彝族;一支进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沿美姑河北上到达凉山腹地,发展成为“古侯部”彝族。布部和濮人融合壮大成为“德布部”向四方发展,东南路进入贵州普安,北路达贵州威宁,其后裔发展成为乌撒土司。黔部分散到贵州各地,发展成为“德施部”,德施部后裔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四大土司:云南东川阿于歹土司、云南镇雄芒部土司、贵州水西土司、贵州普安土司。留居洛尼白的布部后来发展成为南诏三十七部中的罗婺部、洪农禄券部、掌鸠法块部。据罗婺谱系追根,罗婺部部长阿而是慕克克第四十八代孙。六祖分支所到之地进而成为六祖后裔发展之地,这些地方大体为彝族主源以叟为基础的彝族分布之地,大体为滇川黔桂彝族现在分布,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操北部方言、东部方言、南部方言、东南部方言的彝族为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而滇西并非六祖迁徙所到之地。
二、以昆为基础的彝族分布
上述六祖中的武、乍曾迁徙到滇西,乍支的一部分迁到滇西洱海地区,他们却未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成分,变成了汉族。 《六祖乍寻源》说:
武野吐朵,乍嫡六子母。
乍迁西方去,兴起汉文化。建庙如积云,塑偶如红岩,
乍变汉去了,汉一样繁衍。[4](P299)
对此《彝族源流》也有反映: “乍氏六支人,塑俑多如云,偶像如人群。制鼓悬钟,在点苍雅卧 (今大理点苍山一带),与罗纪一般。”[5](P54-55)笃慕主持六祖分支是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事,那时洱海地区尚无汉族。上述彝文典籍所说的“汉”当是对后期彝族的另一元,即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的描写:不祭笃慕而祭佛的另外一种人群。乍是否变成为汉,不得而知,但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排外情绪:一方面洱海地区彝族和自己在语言、文化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另一方面洱海地区彝族却并不以笃慕为始祖,他们以沙壹为女始祖,以英雄祖先细奴逻为始祖。这令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十分困惑,把他们解释为变化为汉族,也有说变为白族的。的确,这是一种很好的解释方法,用后面的文化来叙说前面的事,这是民间文化常见的一种手法。乍的一支即便到达洱海地区也当融入当地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先民中了。
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虽以沙壹为女始祖,以细奴逻为英雄始祖,但祭祀经典无文字,仅以口头流传,这很容易变异和淡化。这种文化标记离南诏发祥地巍山越远就越淡薄,但与之相近的另一种文化标记尚还清晰。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丧葬祭祀时,由毕摩诵指路经,为亡人指路,指引祖魂回到祖先的发祥地。澜沧江以东滇西大理、楚雄、玉溪、临沧、普洱操西部方言彝族和操中部方言彝族在指引祖魂回到祖先的发祥地时,皆指向西方或大理方向。有的具体指向巍山、点苍山。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受佛教影响较大,还有的将祖魂引向同一方向的佛教圣地鸡足山。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70%以上操中部方言,而大理州彝族大部分操西部方言。《梅葛》是流传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支系罗罗的一部彝族史诗,云南人民出版社过去出版的《梅葛》整理者删去了指路部分,姜荣文收集整理的《蜻蛉梅葛》中丧葬指路说亡魂最终送到大理:“看见弥渡红岩,弥渡红岩坐,看见大理鸡足山,鬼王天府。到了此地,一级神王,二级祖老,服从安排,令行不违。”[6](P80)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大黑山彝族支系罗罗的丧葬祭辞说:
指路向何方?到大理普棚,
到永北街头,大理普棚地,
屯兵驻扎地,永北街街头,
熬纸卖纸地,已然去世者,
不去也得去,那是你居地,
那是你住所,教路至那地,
指路向那方。[7](P410)
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桂花乡依博拉罗罗彝村毕摩殷茂林是远近有名的毕摩,但不识彝文,也无彝书,他的祭祀经文皆为心记。当地祭祖要三天三夜,当地彝话称为“备别”。祭祖这天,毕摩主持祭仪,为三年内逝世的亡灵超度、指路、让亡灵归祖安灵,从而保佑子孙平安、吉祥。祭祖十分隆重,复杂,耗资极大,民间说“死人不吃饭,家产分一半。”祭祀分家祭和野祭两种,由数名毕摩分别主持。殷毕摩为亡灵指路是这样的: “汉族照书念,罗罗靠心授,下面我为你,指给方位,指给地名,教给路线,你心要记住。” 《指路经》从依博拉彝村亡人家开始,经百草岭、大姚城区南街、姚安县、祥云县、弥渡县,最后,将祖魂指引到大理鸡足山。
到达鬼地大理,到达亡府鸡足。(“鸡足”即宾川县内佛教名山鸡足山。)
大理是鬼府,鸡足是阴曹。
鬼地看见了,亡府看见了。[8](P255)
按彝族宗教祖魂当送往祖先发祥地,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以哀牢九隆为祖源,以南诏发祥地巍山为祖地。巍山彝族腊鲁(罗罗的另一种汉字记音)是清楚的。外地的罗罗最初也当清楚明白,但因没有文字记载的经书,毕摩全靠口传心授,渐渐发生变异,但有一点还是记住了,即祖地在大理方向。受佛教的影响,把大理境内的佛教名山鸡足山当成阴曹鬼府,把祖魂送到鸡足山也成了罗罗支系的一种常用的为祖魂指路所向。
丽江地区彝族为四川凉山迁入的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澜沧江以东滇西大理、楚雄、玉溪、临沧、普洱操西部方言、中部方言彝族为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
三、两元彝族的异同
和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相比,处于“蛮荒之地”、僻远之乡的洱海地区的彝族先民千年来处于相对隔绝的发展之中。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和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都是彝族,两元民族的基本要素完全相同、一致,这是根本的,是基础的,但许多细致的东西却有差异。两元彝族在两千年的发展中互相交融,互相影响,但那种从根上带来的文化观念差别还是能看得到。对两元彝族文化观念上的同异进行探索是彝学研究的第一次,这有助于加深对彝族族源多元的理解和认识。
(一)始祖崇拜
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有一个文化观念,即认为自己是始祖笃慕的后裔,在祭祀时均要追溯到始祖笃慕。三星堆古城被水毁大约在公元前600 年,也即末代杜宇王渡过金沙江“隐西山焉”之时。彝文发现较早,成书却为明末,最初的经文、系谱当来自口头传承。民间口传文化都有整合、变化现象。如六祖史版本很多,有母系六祖,父系六祖之说;有前六祖,后六祖之说;有七祖;有十祖之说。 《彝汉教典》则记为益博、诗德、根英、尼能、俄莫、神硕六部落。尽管我们不能把口传史和史实等同,但六祖的迁徙和彝族的迁徙基本是一致的,四川、贵州彝族主要部分是从云南迁徙过去的。这就有了四川、贵州彝族和云南东部、北部、南部、中部彝族一般均以笃慕为始祖的文化特征。
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其根源自洱海地区,现分布于云南西部和云南中部的一部分。南诏王室明确以沙壹为始祖。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并不以母系为族祖,特别进入父权制后,更无法坚持这种观念。故西部彝族和中部的部分彝族祖先崇拜时,对沙壹始祖观念较为模糊。在各种祭祀诵经时,仅诵“哀牢”二字;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文化观念中明确的始祖则是细奴逻,南诏王细奴逻是这一元彝族中的英雄。
始祖的不同说明在文化观念中,两元彝族的血缘是不同的。其实,两元彝族都是羌与濮融合的结果。
(二)宗教
两元彝族宗教都以原始宗教为基础,其特点是万物有灵,以物为神。原始宗教行为的主体当为氏族、部落时期的原始民族,其宗教的巫师是毕摩和苏尼。毕摩的功能以诵经祭神为主,苏尼的功能以跳舞驱鬼为主。
两元彝族宗教性质形式基本一致,若认真细分,两元彝族宗教还是有不少差异。南诏不仅推行儒学,在宗教上也积极推行佛教、道教,故滇西的寺庙中常常有彝族的土主和佛教的观音、道教的老君同处一堂的情景。甚至细奴逻的发祥地巍山,对细奴逻由农夫变为王也有佛佑和道佑两种说法。《云南通志·杂志·观音七化》、元《白古通记》、民国《蒙化志稿·沿革志》皆说细奴逻在巍山为农,得观音显化为南诏王,南诏寺庙多有观音显化细奴逻的描绘。而巍宝山青霞观《重修巍宝山青霞观碑记》则说:“九隆小子细奴逻自哀牢避难蒙舍,娶妇曰蒙欻,耕于山麓。”遇一老人乞食,妇善待。老人以杖击耜十三,曰: “汝家富贵子孙,相承有如此数。”这成就了南诏十三代为王之善业。此后,在细奴逻显化之所建了这座道观青霞观。巍山县城北10 公里处庙街区有一古祠为古石祠,内供一石和圣母九天娘娘。传说这石和九天娘娘皆和细奴逻继承张乐进求王位有关。石崇拜是当地原始宗教的产物,九天娘娘是道教产物。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在改土归流前只崇信毕摩教,就是现在,佛教、道教的色彩也不浓厚。
两元彝族的灵魂观也有差异,受南诏影响,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只有一魂观念,此魂经诵经指引,亡灵回到祖先发祥地后便送往阴间。而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则认为,人死后有三魂:头魂、脚魂、心魂,三魂离体,则人死亡。人死后,头魂守祖灵,脚魂守坟地,心魂经毕摩诵经指路,沿着祖先的迁徙路线,一站又一站,最后回到祖先发祥之地。
两元彝族毕摩做法事时装束也有差别,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毕摩做法事时戴竹胎黑羊毛毡笠,笠边吊鹰爪,披黑披毡,毕摩传承为家传。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毕摩做法事时也有戴黑毡笠的,弥渡县、南华县彝族支系罗罗传统毕摩帽为高筒形卷边白羊毛高筒毡帽,帽檐吊鹰爪。三十年代,马学良先生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县住在凤土司家,从事彝族文化研究很长时间,他当时看到的毕摩帽也是黑、白两种。[9](P282)祭经是毕摩祭祀的主要工具,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毕摩都有古彝文经书,毕摩的传承是家传,因为毕摩家才有毕摩神,毕摩神不是学习能得到的。毕摩的传承方式以抄写经书为主要形式,其经典较为稳定。经书内容十分广泛,毕摩一般传经不传书,其书在毕摩去世时随尸火化。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毕摩没有彝文经书,毕摩传承不一定家传,更普遍的是师传,其传承方式是用彝话口头背诵经典,其经典的变异性较大。
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基本没有偶像崇拜,唯一一点木质祖灵略成人形,但藏诸山洞,不仅不与外人见面,就是家人也轻易不能见面,更不用说直接崇拜了。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有偶像崇拜,南诏十三王为十三个土主,立有不少神像,各地土主神均立有土主神像。一些地方以佛教的摩诃迦逻即大黑天神为土主,立有三头六臂,黑面的“咪司”土主。南诏丰佑时在石宝山刻有大量佛像,其中有三窟刻南诏统治者雕像,一室雕细奴逻,一室雕阁罗凤,一室雕异牟寻。彝族土主庙中往往不仅有土主神像,还有佛教、道教神像。各村寨彝族都有土主庙和山神,土主的功能是保佑村寨平安、庄稼丰收;山神的功能则为牛羊兴旺、狩猎顺利。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没有土主神,只有山神,山神没有神像,是一棵经巫师选定的树,山神的功能是全能的,既保佑村寨平安、庄稼丰收,也保佑牛羊兴旺、狩猎顺利。
彝族宗教的核心是祖先崇拜,滇、川、黔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以笃慕为始祖,称之为阿普笃慕,将始祖笃慕的故地朱提或六祖分支的洛尼白视为重要的祖地。祭祀时必不可少的经典为《指路经》,它指导着亡灵从死亡地一站一站地送往祖地,从《指路经》中,人们可以追寻到彝族的迁徙发展过程。
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同样以祖先崇拜为宗教核心,其女始祖为沙壹,龙为父系始祖。进入父系制后,人们在追溯始祖时,均以父系始祖为祖,但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父系始祖却是神话中的龙,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云南西部和中部一部分彝族祭祀时均用彝话,经典有《请毕摩经》、《洗尸经》、《装棺经》、《忆魂经》、《招灵经》、《开路经》等,《开路经》内容为驱鬼开路和为祖灵指路两方面内容,指路内容不多,祖地含糊,经文开头一般都有两个字:“哀牢”,这是对哀牢九降祖地的朦胧记忆。人们一般均把魂送往巍山、西方、大理点苍山、鸡足山。不过,对始祖祖地我们还是能隐约地看到。南诏认为自己是九隆之后,这源于《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九隆神话中的哀牢夷女始祖沙壹:“南中昆明祖之。”而洱海地区彝族是以昆明为核心发展形成的。巍宝山的巡山殿就是南诏宗族最大的祠庙,至今一直是巍宝山附近彝族的祖祠。
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最为明确的始祖是英雄人物细奴逻,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进殿祀祖,人们都把细奴逻当作始祖崇拜。至今,分散各地的彝族罗罗人仍然在祭祖或为亡人教路时把蒙化巍宝山作为祖源地来祭祀。因为没有用文字传承的经文传承,祭祀时不能像以笃慕为彝族始祖一样有明确的祖先谱系和迁徙路线。但在经文中还是能看到始祖的影子。“南诏土主庙祭祖大典上,毕摩摇响法铃,一声‘哀牢——米洒,米嘛洒,哈抓彩嘎啦。’(彝语意:哀牢——知道名字的,不知道名字的,南诏王、王子、王妃全部恭请来。)令全场人下跪诵经的庄严,让人深感敬畏和神秘。”每段经文开始,均要大叫一声“哀牢”,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人都无法解释“哀牢”为何意,人们解释,“哀牢”是人们心中最牵卦的一个人。[10](P63)
在传统文化方面,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用族内婚制保护自己的民族性,在改土归流前对外来文化是排斥的;而以昆明为基础的彝族对外来文化则是包容的,南诏主动吸收白蛮、汉族文化和儒、释、道文化。南诏大量任用外族官员,郑回为汉人,任嶲州西泸县令,为异牟寻所俘,因其才能被异牟寻任命为清平官,“事皆咨之”。郑回是南诏兴盛和南诏归唐的大功臣。
(三)火葬
彝族在古代普遍实行火葬,两元彝族传统葬俗都是火葬。 《太平御览》卷五五六说:“建宁郡葬夷,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燔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劳贺作乐。若遇风,烟气旁邪,尔乃悲哭。”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记载:“罗罗,即乌蛮也……酋长死,以虎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自顺元(今贵阳)、曲靖、乌蒙(今昭通)、乌撒(今威宁)、越巂(今西昌)皆此类也。”再看洱海地区的西部彝族,《蛮书·蛮夷风俗》说: “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惟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洱海地区行火葬盛两耳之风仅见于唐时,洱海地区彝族现行土葬,只有少量地区仍行火葬。传统火葬无墓,骨灰随风扬弃,这就是南诏十三王至今未发现一座王墓的原因。明清以后,云南、贵州一些彝族开始实行土葬,但至今四川大、小凉山和云南宁蒗小凉山、元谋小凉山、洱海地区的一些彝族仍保留火葬习俗。彝族的火葬习俗是古羌人火葬的继承,火葬是古羌人的一种传统的葬俗,《吕氏春秋·义赏篇》:“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
两元彝族都用竹制作祖灵“玛都”,并将“玛都”放置于屋内墙洞中节庆时祭祀,以求祖先神灵护佑儿孙后代。祖灵由毕摩制作,具体制作时各地又有差异。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一般只设“玛都”祭祀,而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一般在“玛都”上方还绘制历代祖先的画像供奉。
(四)语言
两元彝族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分布在中国西南的广大土地上,传统经济都是山地农耕经济为主,畜牧经济为辅。两元彝族语言相同,都是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彝语词汇丰富,表达准确,修辞方法较多,讲究音韵,极富特色。两元彝族语言虽然都是彝语,却有方言和次方言的差别。彝族之所以有共同的语言和彝族的族源分不开,两元彝族都是羌和濮融合的结果,这种相同的语言文献称之为“左言”,由于融合的时间、地点不同,语言的形成发展就出现了差异。叟和昆明在形成彝族的长远过程中不断和当地许多民族相融合,加之分布不同,交往不多,这就有了方言的不同。彝语分六大方言,五个次方言,二十四个土语,十九个次土语。
北部方言主要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自称诺苏和聂苏的彝族支系使用。北部方言又分为北部次方言和南部次方言。
东部方言主要为云南武定县、禄劝县、寻甸县、贵州威宁县自称纳苏、聂苏的彝族支系使用。东部方言又可分为黔西北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和南部次方言和盘县次方言。
南部方言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的彝语为代表,操南部方言的彝族主要分布于普洱、玉溪、红河、文山等地州的彝族,约占彝族总人口的20%。南部方言中又分为石屏土语、元阳土语和峨山土语。
东南部方言以昆明市宜良县、石林县的彝语为代表,主要为云南中部自称撒尼和阿细的彝族支系使用,约占彝族人口的6%。东南部方言中又分为撒尼土语、阿细土语、阿哲土语。
西部方言以云南巍山县彝语为代表,使用这种方言的主要是自称罗罗的彝族支系,约占彝族人口的6%。西部方言又可分为西山土语和东山土语。
中部方言以云南大姚县彝族为代表,使用这种方言的主要是自称罗罗和俚濮的彝族支系,约占彝族人口的8%。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70%以上使用彝语中部方言,中部方言又分为罗罗土语和俚濮土语。
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识别时,自报支系多达四十多个,识别后合并为十三个支系,1957年楚雄专区曾对境内彝族的十三个支系的语言做过调查,并以罗罗濮为基础,将其余支系的语言与之进行对比,其结果如下:
与阿车语对比,282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211 个,占74.86%;
与车苏语对比,282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155 个,占55%;
与罗武语对比,282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214 个,占75.89%;
与山苏语对比,282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221 个,占78.4%;
与俚濮语对比,271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253 个,占93.36%;
与密岔语对比,247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206 个,占83.4%;
与水田彝语对比,29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23 个,占86.4%;
与格苏濮语对比,250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216 个,占86.4%;
与纳苏语对比,169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131 个,占85.4%;
与纳罗语对比,121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92 个,占76%;
与撒尼语对比,89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76 个,占85.4%;
与诺苏语对比,96 个词语中,相同相近者51 个,占53.1%。[11](P85)
彝语虽有方言次方言、土语的区别,但却是同一种语言,其同源词一般达到39%,其声调相同,一般有三四个声调。
古蜀人的特点是“椎髻左衽左言”,具体怎么是“左言”,文献未言。而在古蜀人的后裔彝族中,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两元彝族语言在语法结构上共同表现为:第一,基本词序相同,都是“主语——宾语——谓语”结构,这和汉语完全不同。如汉语说:“我吃饭”彝语则为“我饭吃”。汉语“你上山”彝语则为“你山上”。第二,动宾倒装,如汉语说:“走路”彝语则为“路走”。汉语“骑马”彝语则为“马骑”。第三,修饰词或形容词放在被修饰的名词后面,如汉语说:“蓝蓝的天空”。彝语则说为:“天空蓝蓝的”。汉语说:“红红的火”彝语则为:“火红红的”。两元彝族语言中这种语法上的这三个共同表现被文献称之为“左言”。从古蜀人的“左言”到彝族的“左言”,其中间过度者为叟,是叟把古蜀人的“左言”带到了南中,最终发展成为彝族的语言。
(五)文字
古蜀人是有文字的,四川郫县出土的青铜剑上的一排文字即为一证。2000 年7 月29 日四川省委办公厅在成都商业街一个地下室发现了17 具巨大的船棺葬,这是中国第一次把船棺葬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这17 具船棺葬是蜀王开明氏的最终归所。开明氏船棺是二次葬的结果,船棺均用巨大楠木从中间剖开,刳凿制作而成,棺内只有残骨。开明船棺葬墓地虽遭遇过盗墓贼的洗劫,还是出土了不少陶器、漆器、竹木器、青铜器。其中,铜编钟和漆艺高超的大件几案等非常人用品,这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不是普通人家的用品,它们是宫廷用品,是蜀王用品。成都商业街出土的17 具开明氏船棺每一具船棺棺头上都有文字。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认为古蜀人是有文字的,他在《有关古史的十个解读》中说:“成都商业街出土的船棺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巴蜀符号……在主要的船棺上都刻有巴蜀符号,可能是蜀王或贵族的名号,这些符号肯定是文字。另外,在成都以北新都王陵出土的印章上也有这样的符号。这种巴蜀文字是现在世界上存在很少的无法释读的文字之一。”[12](P40)
有没有这种可能,叟是蜀人,蜀有高度发展的文明,叟来到云南,带来了古蜀文字,在蜀文字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彝族文字,故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有文字。关于彝文的形成有多种说法,有汉代形成说,也有唐代形成说。文献记载有“爨文”、“爨书”、“韪书”、“罗罗文”、“倮文”、“夷文”等,为和改革后的彝文相区别,俗称老彝文。现存彝文典籍十分丰富,皆为明清以后。彝文均为毕摩手写,师徒相传。由于各个毕摩手写习惯不同,造成彝文异体字特多,彝文约8 万多个字,常用字约两千字。有部分明显有象形、指事、会意特点。彝文书写用毛笔,分主笔和副笔,先写主笔,后写副笔,从左至右直行书写。
昆为南迁的游牧羌和濮在洱海地区融合的结果,昆长期在民间发展,没有能够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南诏时期,这一元彝族先民虽然有了政权,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但还是没能产生自己的文字。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南诏以汉字为官方文字。南诏一方面从外面请汉文教师教习南诏子弟,另一方面把自己子弟送到成都学习。南诏王室及南诏上层汉文功底都很好,南诏王懂汉文,有的还能写很好的汉文诗歌,南诏诸王、群臣写作的汉文诗很多。对于南诏的文学,徐嘉瑞先生有这样的评价:“南诏诗歌、散文、骈文虽记载缺乏,然就现存文献征之,无论诗歌、散文、均已发展至高度,其完满成熟,与中原文化相差无几。” 《说郛》卷十七《玉溪编事》载南诏王隆舜和清平官赵叔达曾于东都善阐避风台唱和诗,隆舜十二月十六日星回节唱和诗道:
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腾越,
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
自我居震旦,(原注:天子为震旦。)翊卫类夔契;
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
不觉岁月暮,感激星回节;
元昶同一心, (原注:谓朕曰元,谓卿曰昶。)子孙堪贻厥。
昆与叟同居一地,叟有文字,昆也会受叟的影响,但在南诏政策的干预下,以昆为基础形成的这一元彝族始终未能产生出自己的文字。巍山县垅圩图山曾出土有字瓦,许多人认为其字是蒙舍诏时期的彝文。据说巍山境内还出土一面铜镜,上面有十个彝文,其意为“早上不能睡懒觉,要早起干活,否则要饿肚子。”。笔者曾到垅圩图山实地考察,山头树木密佈,只找到两小堆瓦砾,未能找到有字瓦。巍山现存的有字瓦字迹不太清晰,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彝文专家朱琚元先生认为瓦上确有文字,但这种文字更像是梵文,梵文在南诏佛教中十分流行。南诏文物中多有梵文,例如大姚白塔。大姚白塔建于唐天宝五年 (公元746年)高18.4 米,最大直径6.2 米,上部呈圆锥形,中部为八角柱,塔体白色。白塔通体覆盖砖刻梵文经典。如此说成立,则说明垅圩图山的建筑当为南诏势力强大后的作品,其有字瓦为梵文的可能性更大。据说山上曾出土一方铜印,印文为汉文“蒙”字,南诏王皮逻阁时被唐王朝赐名“蒙归义”,这更增加了山上建筑并非蒙舍诏时的作品,更增强了其建筑为南诏强大后所建的可能性。也许,以后会组织发掘作出正确的结论。但无论南诏早期有无彝文均不能影响南诏仅使用汉文的结论,也不影响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并无文字的事实。
南诏另一主体民族白族有文字,但这种文字也是汉字广泛流行的结果,白文是对汉字的一种改造。
(六)父子连名制
两元彝族传统命名方式都继承了古羌人的父子连名制,文献对南诏统计者蒙氏的世系多有所载,但互有出入。 《新唐书》记载为:“舍龙、独逻(又作细奴逻)、罗盛炎、炎阁、盛逻皮、皮逻阁、阁罗凤、凤伽异、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丰佑、酋龙、法、舜化”。
南诏王室谱系虽有出入,但足可证实南诏王室以父子连名制为其命名。今巍山彝族仍认南诏王室为自己的祖先,一些彝族家谱有的直接与南诏王室世系相连,如刘尧汉先生的《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中公布的张兴癸、杞彩顺、杞绍兴三人家谱。他们都是近百年的人物,都源自巍山彝族支系罗罗人,他们的家谱都和南诏王室相连接。滇、川、黔彝族民间皆用文字或口头相传牢记家谱,并以家谱作为鉴定血缘关系或亲戚的证据。
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民间有口头或彝文手抄系谱,《四川凉山彝族社会调查综合报告》说整个凉山的黑彝都认为他们出自古侯、曲涅为古侯系各支中的一支,本支至此绝,后面由曲涅系沙马家继承。)

无论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或者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均以父子连名制命名,这种命名方式是从根里即羌人那里带来的。古羌人的命名方式即父子连名制,即儿子的名字必有一字与父名相同,这种命名方式见于《后汉书·西羌传》所载,其世系为:

(七)舞蹈
两元彝族传统舞蹈一大特点是连臂跺脚,上半身包括手臂一般无动作,只用腿、脚变化来表达感情,特点是把个体和整体连成一体,一起起伏,一起移动。众多人围成一圈向下猛跺,踢倒山,跺碎石,显示出力量和狂放无羁的激情。滇、川、黔两元彝族歌舞的基本形式便是这种携手连臂的圆圈跺脚舞,和傣族的轻柔曼妙、藏族的狂放挥洒完全不同,联袂跺脚源于古羌人,古羌人的发祥地甘青马家窑出土陶器常见图案就是这种联袂跺脚舞。联袂跺脚舞是古代游牧经济的产物,上身着坚硬的披毡,不便行动,双脚猛跺能在释放感情中御寒。
(八)婚姻
彝族以同宗为同血缘,皆行同宗不婚。彝族视同宗结婚为禽兽行为,违者即便同宗性恋,也要受到同族长者的严厉处罚,重者烧死,轻者赶出村外。彝族普遍保存着姑舅表优先婚的习俗。婚姻的民族性是客观存在的,因受语言、习俗、宗教、环境的影响,少数民族一般在婚姻中均以同一民族为婚姻界线。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婚姻界限为民族内婚,黑彝不仅实行族内婚,还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则有所不同,南诏王室为了政治需要,主动和不同民族的首领通婚,南诏通过联姻方式来稳固不同部落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南诏突破了严格的族内婚界线,不仅与乌蛮通婚,也与白蛮和汉族通婚。南诏早在统一六诏立国之前就以联姻方式和白蛮张乐进求结成政治联盟。 《蛮书》卷四载,阁罗凤迁西爨白蛮二十余万户到滇西后,“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振……今与南诏为婚姻之家。”又载:“独绵蛮者,乌蛮裔也……异牟寻母,独绵蛮之女也。牟寻之姑,嫁独绵蛮;独绵蛮之女,为牟寻妻。”前述南诏与爨氏通婚,也与滇东北及北部的乌蛮联姻。《新唐书·南蛮传》也说:南诏时期滇东北至黔西北一带乌蛮形成七部,“乌蛮与南诏世为婚姻。”南诏通过联姻方式建立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从而确认和巩固了南诏王室的主体地位。受此影响,这一元彝族通婚民族界限并不重要。“有些地方彝族通婚不分民族界限,只要对方能尊重自己的民族习惯,即可通婚,不受歧视。”[13](P212)
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楚雄彝族自治州东接滇池地区,西连洱海地区,汉时是滇池地区叟和洱海地区昆的交汇点。唐代,楚雄州的禄丰县为两爨分界点,禄丰以东为东爨,禄丰以西为西爨。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两元彝族的交汇处,州内彝族六大方言都有人使用。使用东部方言的武定彝族支系罗婺传统婚姻习俗即遵循以叟为基础的婚姻习俗;州内彝族支系罗罗、俚濮则遵循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的婚姻习俗。
(九)体质
对彝族还有另一种两分法。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二《曲靖府》说: “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说:“倮罗,本卢鹿,而讹为今称。在大定府有黑、白二种,黑者为大姓,又名乌蛮。其俗尚鬼,故又名罗鬼。”乾隆《镇雄州志》卷五《种人》说:“罗罗,以黑白二种。分贵贱,其黑陇氏(土官家族)之支脉;白种乃其异姓臣庶也。”一些学者将两种彝族分为贵贱的不同,黑纯白杂。
更多的学者则看到两种彝族体质上的不同,例如,冯汉骥先生20 世纪30 年代和美国人希洛克所著《彝族起源史》说:“在现代倮罗中,黑白两个群体是有体质上的差别的。黑倮罗体格高大,有人说比欧洲人还高些。他们有鹰钩鼻,隆起的鼻脊,与蒙古利亚型是十分不同的。白倮罗与蒙古利亚人种更接近。”[14]以上所说将罗罗分为黑白二种,黑罗罗为西方人种,白罗罗为蒙古利亚人种是从体质人类学来研究彝族族源的。有的认为彝族源于雅利安人种,有的认为彝族源于伊朗人种,有的认为彝族源于印度人种,有的认为彝族源自斯基泰人种,种种说法都以推测为主,尚未进入科学研究。
这种体质上的差异其实在两元彝族中是存在的,以罗罗支系和诺苏支系为例;罗罗支系属于以昆为基础形成的彝族,而诺苏支系属于以叟为基础形成的彝族。从外观感觉,诺苏支系彝族个高、脸长、眉弓高、肤黑,即文献所说“肤黑、深目、体长、牙白。”罗罗支系彝族一般个矮、脸圆、眉弓平、肤白。
“黑彝”是彝族形成的另一元么?他们和昌都地区卡若类型新石器文化有什么联系呢?任乃强先生认为彝族为东徙的珞巴人的后裔。[15](P136)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清楚地说明川西羌族数千年来在中国西疆边境内外生存奋斗,他们挣扎于中原王朝与吐蕃、西夏、南诏的战争之间。为了生存有的变为汉,有的变为藏,有的变为夷。“在此地带的南端,过去被称作‘夷’的人群,其后裔如今被识别为‘彝族’,成为660万彝族最北边的一部分。”[16](P4173-174)王先生的研究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其一,这一带羌人界线模糊,他们有的自认为自己属于“蕃”(即藏),而有的史家记载时也有将他们划入蕃的。其二,羌与濮为彝族之源,这一部分羌是最后融入彝族中的羌人。凉山彝族中羌的成分较其他地区彝族更新鲜也更多一些。任先生的推测在体质和地理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当为众多探索之路中较好的一条。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两元彝族并无共同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没有共同的祖先血缘。两元彝族族源的一致,保证了他们文化观念和心理素质的一致,起决定作用的是从唐代以来,两元彝族先民互相认同是同一个族类。
[1]方国瑜. 彝族史稿[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2]易谋远. 彝族史要[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彝文翻译朱琚元,张兴. 彝族六祖史·太阳金姑娘与月亮银儿子[M].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3.
[4]彝族创世志·谱牒志(一) [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
[5] 彝族源流 (第十七——二十 卷)[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6]姜荣文收集整理. 蜻蛉梅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7]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丧葬祭辞·姚安彝族口碑文献(第五十三卷)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8]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祭祖经·大姚彝族口碑文献(第七十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9]马学良. 彝族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腊罗圣地[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11]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志[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
[12]李学勤. 文物中的古文明·有关古史的十个解读[M]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3]楚雄彝族人口[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14]冯汉骥,希洛克. 彝族起源史[J].凉山民族研究,1997 年年刊.
[15]任乃强. 羌族源流探索[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16]王明珂.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