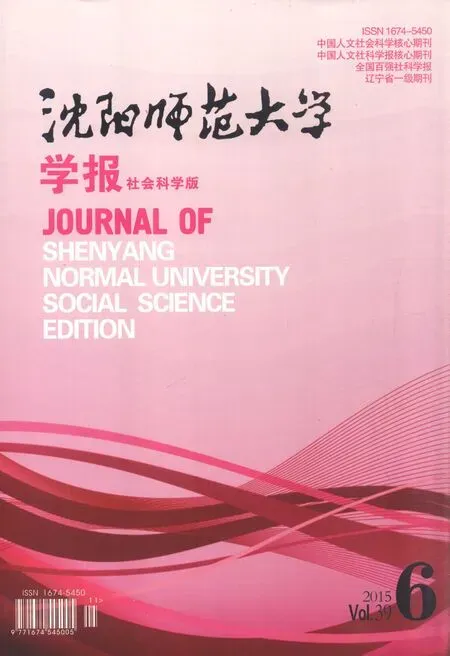《额尔古纳河右岸》研究综述
于巍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43)
《额尔古纳河右岸》研究综述
于巍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43)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的一部描写我国原始游牧民族鄂温克族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历史的长篇小说。自发表时就因其深沉的思想、内容的独特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与研究。通过对自发表至今关于文本的主题、文化、人物、艺术特征、及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形成的代表性观点进行梳理介绍,并在总结整理的基础上形成一些自己的认识与观点。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研究综述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发表在2005年《收获》6期,当时对它的评论文章仅有五六篇左右;2008年该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掀起了阅读狂潮,研究者专门著文研究,散见于各类报纸期刊上的专题论文已达百篇;到2006年,则出现了多角度研究该小说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本文拟对《额尔古纳河右岸》发表以来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学说进行梳理,并进行一定的评说。
一、关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题研究
《额尔古纳河右岸》有着多元化的主题,而且这些主题意蕴也是世界性的共同话题,它关系到人类文化学、生态学的问题。作者通过对“瑕瑜互见的原璞世界”[1]的书写,表达的是“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张扬”①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
(一)民族消亡的挽歌与家园回望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从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等因素的角度出发,分别在1959年和1965年两次安排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定居,但是鄂温克人依然过着半游猎的山上山下的二元结构生活,而在2003年政府安排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进行了第三次定居,然而部分饲养驯鹿的猎民们在定居后不久,又重返森林”[2]。迟子建在追逐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落时,用了“悲凉”二字来形容她当时的心情。现代人仿佛总是习惯于改变甚至于消除一些古老的生存方式,先把它们定性为“落后”的“、落伍”的、应被“淘汰”的,随即加以无情地鞭挞试图连根拔起,想把现代人心目中的文明生活强加在他们身上,居高临下地肆意摆布他们的生活。在这里笔者认为,没有哪一类文明是落后的,文明亦没有新旧之分,只要它符合、满足当时、当地人们的生存状况,那么这种文明就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
一个始终坚持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原本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古老民族,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既不是因为大自然收回了馈赠,也不是因为日、俄铁蹄的无情践踏,而是现代文明以温情依依的方式让他们与延续千年的传统挥手告别。即便他们被“请”进现代文明,但依旧是处于现代文明的边缘位置,内心是不自由的、无所适从的,可是又无力逃脱,也很难走近主流。即便有一天类似鄂温克族这样的古老民族真正地走入到了现代文明的核心地带,其民族特性、民族性格大抵也就在走入的过程中消亡殆尽。孙俊杰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性面前的命运处境也是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命运的一面镜子,在现代性这个具有绝对话语权的中心面前,它们都处在他者、弱者的地位,经历了被改造、被转换、不断流散的过程。”[4]迟子建笔下鄂温克族的命运也许是其他一些民族正在上演的或即将上演的悲剧的写照,它只是时代洪流下的缩影,折射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和传统文化的隐忧。
(二)生态意识主题
“生态批评”由美国学者威廉姆·鲁克尔特于1978年首次提出。其内涵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切丽尔·博格斯·格劳特菲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5]现代科技文明的迅猛发展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物资源的锐减,这些都对地球上物种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这种现实的沉重压力引发了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深刻思索与反省,作家们想以关注生态的文艺作品来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自身肩负的生态责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典范。但是迟子建被称为一个“潜在的生态文学作家”[6],原因是在她的小说中并没有十分刻意地凸显生态环境的价值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与冲突,而是把自然环境的艰难诡谲作为族群生存的大背景。即便是写鄂温克民族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裹挟下不得不做出退让时,迟子建也不延宕在人与环境的思考上,而是高瞻远瞩于对鄂温克族历史、文化、命运的思考上:“我其实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与无奈”[7]。
小说中鄂温克人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生态文化、生态观念。首先,自然是永恒而独立存在的敬畏象征,鄂温克人与自然形成相互融合的整体。王霄羽认为“大自然在她的文本中并不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或是人物精神与情感的象征存在,而是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在她的文本中,大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尊严和魅力随处可见,它们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成为了读者驻足欣赏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8]。在小说构筑的文本世界中,鄂温克民族生活的自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的系统,山水的巍峨秀美,风云的轻盈妖娆,树木的葱茏郁郁,生物的灵动生息,都依依因循着自身的存在轨迹,不受外在人世间千变万化的干扰和影响。族人生活在自然之中,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与自然和谐共处,接受着自然慷慨的馈赠,互相兴发,互相照应,从而形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右岸》深情地描写了鄂温克人与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须臾难离的关系,自然的一草一木都与他们的生命、血肉融合在一起,他们生活在自然之中,衣食住行均来自于自然。在作者笔下,与人类生命的短暂相比,自然又呈现出了“永恒”的品格。原本鲜活的生命此时犹如深秋的落叶般片片飘零,生命脆弱得会被神灵不经意间取走,最终又重新回归到自然的怀抱,仿佛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无论生与死,自然都是人类的归属。
除此之外,小说还展示了鄂温克人对自然的崇拜与守护以及外来现代文明对于生态的破坏。鄂温克人狩猎时不杀幼崽,在猎堪达罕时不许大声说话,不许往水中吐痰;吃熊肉时要做风葬仪式,萨满总要唱一首祭熊的歌;烧火只烧被雷电击中失去生命力的、干枯的树枝,他们怀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而现代文明的贸然闯入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是迟子建最为心痛的。伐木工人大批进驻兴安岭,连绵不断的伐木声吵醒了原本鄂温克人平静的生活。在1998年初春因两名林业工人吸烟乱仍烟头而引发的火灾令额尔古纳河和兴安岭蒙受灾难,妮浩萨满祈雨浇灭大火拯救家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迟子建从鄂温克人的视角出发,以文学为载体真实地再现了鄂温克族人面对生态遭破坏时的震惊和受到的精神伤痛。
曾繁仁的《生态美学视域中的迟子建小说》从生态美学视域阐释了小说独特的回望视角和美学特征;洪艳的《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生态批评解读》、胡书庆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生态思想》从小说文本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阐释作品中作家所持的生态观念,以及作品呈现的文化意蕴;李科文的《对大自然的生命感悟——读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则从文本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入手,探寻作家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之意。
二、关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研究
《右岸》中对于鄂温克族的民族传统即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的刻画是研究者们的另一个关注点。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罗皓文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文化主题研究》、郭梦贝的《迟子建的少数民族书写》、张紫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民俗描写》、谢林娜的《鄂温克文化的文学呈现》、张向东、罗文政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文化元素探微》、修磊的《论迟子建小说的萨满文化因素——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曾娟的《浅析〈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文化》等,以及刘春玲所著的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满——通古斯文化视域下的迟子建小说研究”的一系列文章。
《额尔古纳河右岸》所描述的是我国最后也是绝无仅有的依靠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的民族——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鄂温克族人世代生活在丰饶茂密的大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之中,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使他们只能完全依赖自然而生存,狩猎、采集、饲养驯鹿这些原始的方法就成了维持生存的不二法门。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可以发现,这种看似简单原始的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地域民族色彩,却又无处不彰显着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生命智慧。书中有许多纪录片似的鄂温克人独特生活方式的场景描写,把他们衣食住行的民俗传统影像般地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萨满教产生于狩猎时代,是一种以“万物有灵”为哲学理想的古老的宗教。“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魂崇拜以及巫术等,构成其基本内容”[9]。谢林娜在论文中归纳出《右岸》中鄂温克萨满的神圣职能包括占卜、治病、祈禳和超度亡灵;张向东、罗文政则侧重分析萨满的产生与功能、萨满文化中的崇拜与禁忌、以及迟子建给予萨满文化的肯定;曾娟认为萨满教影响了迟子建的创作个性心理和深层传统文化积淀,迟子建的死亡观是萨满灵魂观念的升华;刘春玲则在系列论文中详细论述了满——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招魂、超自然能力、禁忌文化的探究等。
关于作品中展现的萨满的神力,迟子建在与周景雷的谈话中说:“我在收集这部长篇资料的时候,知道了很多萨满的故事,他们身上确实有神力,这种神力用唯物主义史观是解释不清楚的,我塑造这样的人物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因为故事本身就是一段连着一段的传奇,我写萨满时内心洋溢着一股激情,我觉得萨满就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化身,这也契合我骨子里的东西,萨满通过歌舞与灵魂沟通,那种喜悦和悲苦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我所能够体会到的。”[10]
三、关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人物形象研究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人物在复杂的氏族关系中挣扎,整个乌力楞的族人基本上都是有血亲关系的,没有谁独立于氏族之外,他们在演绎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在深深地影响和诠释着他人的生命。研究者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右岸》中的女性形象和鄂温克族新生代青年的形象。
(一)女性形象
《右岸》中作者着重展现了以达玛拉、妮浩和伊莲娜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人物。这些女性生命中都有无法形容的痛苦与悲伤,而那些破坏幸福和生命的力量却是人无法抗拒的,这同时也是人类本身的一种巨大不幸,这最大的痛苦在本质上是“我们自己的命运也难免的复杂关系和我们自己也可能干出来的行为带来的”[11]。
对于女性形象的整体研究,作者认为唐晋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和深刻性。他认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不可能专为这些女性个体树碑立传,对她们的形象进行精雕细刻,但往往是廖廖数笔,已让她们栩栩如生。”[12]并提出,这些女性都是“为爱而苦”的女性:“达玛拉是为爱情而苦,妮浩是为亲情而苦,伊莲娜是为民族深情而苦。”[12]这些女性只是为爱牺牲自我的典型,她们其实代表了鄂温克女性的整体形象品格。小说中还有着众多饱受亲情、爱情和民族深情折磨的女性,这无疑展现了以她们为代表的鄂温克民族善良醇厚、敬畏生命、甘于奉献的美好品格。
而对于伊莲娜,向林认为她是“作者意志的符号”[13]。伊莲娜是这个部落所出的第一位大学生,她的艺术原型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第一位走出山林的女大学生、传奇女画家柳芭。她在城市或者林中,事业、爱情、生活的不满足和空虚寂寞都使得她想逃离。但无论逃到哪里她也无法心生幸福,因为种种欲望她无法摆脱,同时也无法否定自己的生命意志。“伊莲娜内心的矛盾,正是作者迟子建自身内心的矛盾,伊莲娜则是作者这种矛盾情感的替代符号。”[13]
(二)鄂温克族新生代青年的形象
按照鄂温克族新生代青年在文化嬗变中做出不同抉择的标准,刘春玲把他们分成四种类型:“堕落型、徘徊型、坚守型、进取型。”[14]“堕落型”的代表是索玛和沙合力。他们出生并生活在山林中,之后下山到定居点去接受教育。在学校接触到新鲜的现代文明后,两人选择了堕落,意志消沉、酗酒、放纵等。“徘徊型”的代表是上文提到的伊莲娜。她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徘徊摇摆,最终在额尔古纳河岸边孤独忧郁地死去。“坚守型”以玛克辛姆为代表,“他虽然最终随部族下山,但是仍然采取只说鄂温克语的极端方式来顽强地固守着已浸入骨髓的鄂温克族传统文化”[14]。而“进取型”的西班在不断思考、摸索着,力图在坚守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探索。例如西班造字就是要将鄂温克族美丽的语言永远记录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除此之外还有对伊芙琳、达玛拉、杰芙琳娜、马伊堪的归类研究,探讨他们生活的悲苦与困境。
四、艺术特色研究
《右岸》是一部独具魅力的小说,许多研究者在总结它的总体风格时大都使用了“苍凉”“温情”“浪漫”“诗意”等词,这也与笔者的想法不谋而合。
一些研究者选择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而且均把着眼点放在叙事视角上。孙苏认为“作家选取了一个独特的人物取代作者承担起了叙事主人公的角色”[15]。田秘总结出《右岸》叙事视角的多样变化,如“第一人称叙事的双重女性视角、儿童叙事视角、民间叙事视角”[16]。其中,笔者更倾向于张沛的《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叙事视角的设置》,他更加细致深入地分析了“我”的叙事视角的多重功用,“这种视角使‘我’与听者之间维持了一种对等的姿态;‘我’的设置使作者在身份认同方面得以解围;‘我’的身份使有关的思考与追忆展开,由此成就了作品的布局”[17]。
也有论著从文本学角度分析小说语言的独特性,“敢于在如此长篇的小说中,完全采用散文化的描写性语言方式,不能不说这表露了作家的勇气和自信”。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纪佳音、岳静的论文,文中着重分析了《右岸》的色彩美,比较新颖的是对小说中的色彩的词做了较为精确的量化统计,并由统计数字推出结论,“经过统计,《额尔古纳河右岸》共使用颜色词426个。其中,中性色系颜色词最多,有205个(白色134个,黑色43个,灰色28个),暖色系颜色词135个(红色74个,黄色47个,紫色14个),冷色系颜色词86个(蓝色39个,绿色27个,褐色13个,青色7个)”[18],这种创新性的方式和思维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五、《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比较研究
许多研究者运用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将《右岸》与萧红的《呼兰河传》相比,从鄂温克民族的书写方面把迟子建与乌热尔图做比较。
(一)与《呼兰河传》的比较
萧红与迟子建同是东北女性作家,这片广袤而富饶的黑土地给了她们独一无二的童真与神性想象。1942年,萧红在香港写下了长情凄婉的《呼兰河传》,二十一世纪初,迟子建完成了气势恢宏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文学创作使她们跨过60年的时空阻隔在心灵与想象中缓缓汇合。张贝思认为,萧红与迟子建都是在汲取着故乡的养料,同时也把故乡作为自己的精神、灵魂慰藉:“‘奔向你’的回归乡土故园的呼喊,成全了她们。成全了她们的童话和神话。”[19]也指出《呼兰河传》与《额尔古纳河右岸》才是真正的女性化的作品,无时无刻不呈现出母性的宽广胸怀和大地般的养育恩泽。
(二)迟子建与乌热尔图的比较
随着对《右岸》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迟子建与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做比较,如郭彦妮的《论乌热尔图与迟子建的鄂温克族书写》、李娜的《鄂温克民族生活的再现——乌热尔图小说与〈额尔古纳河右岸〉比较研究》、李旺的《书写鄂温克——乌热尔图、迟子建比较论》《民族、代际、性别与鄂温克书写一乌热尔图、迟子建比较论》、邓经武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地域书写与种族代言》等。
乌热尔图是生活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鄂温克族本土作家,对鄂温克族的书写是他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并在1981年、1982年、1983年连续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代表作品有《一个猎人的恳求》《鹿,我的小白鹿呵》《玛鲁呀,玛鲁》《悔恨了的慈母》《缀着露珠的清晨》等。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也是在写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但是二者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大都来自两位作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经历、经验和由不同性别而产生的不同写作风格、审美观念。
首先,两位作家创作文本和话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文性。“从文本语言上看,迟子建继承了乌热尔图作品中用汉语拼写鄂温克语以突显民族特色的方式,如安达,希榜柱,撮罗子,乌力榜,乌娜吉,新马榜等。从文本构建上看,迟子建小说中的某些情节设置也带有乌热尔图小说中的某些痕迹。”[20]其次,研究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右岸》缺乏乌热尔图那样那样独特、鲜明、真实的民族心理烙印。李旺认为:“对于携带着本民族生活记忆的乌热尔图来说,写作的过程意味着民族意识自觉并不断加强的过程,而对于有着在鄂温克、鄂伦春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聚居地带生活经验的汉族作家迟子建来说,鄂温克与鄂伦春的故事属于童年见闻”[21],除此之外“当把童年见闻转换成一种叙述的时候,作家借重了记忆中的鄂伦春、鄂温克气息,这种气息应该是氤氲的一团,不像乌热尔图的民族记忆那样清晰可识,更像是听来的故事”[21]。同时邓经武指出“迟子建其实只是一个代言人,她是在替鄂温克人讲述一个故事,并且努力地进入鄂温克人的精神语境,作家(迟子建)的个人经历、既定观念和想象性因素,在阐释鄂温克人的生存形态尤其是心理活动时,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偏差”[22]。在这里作者认为,这种“不深刻”是由于迟子建没有像乌热尔图那样从小受鄂温克族传统文明的熏陶,对于鄂温克族文化意蕴的理解没有深入骨髓而发出力透纸背的力量,但是她对于少数民族、边地民族生存、文化的关怀无疑体现了她的包容与认同,具有多元文化的认识价值,是跨民族书写的成功案例。
最后,从人物塑造角度讲,乌热尔图塑造了鄂温克族的男性群像,不管是猎人、还是萨满,在他的系列小说中都充斥着强烈的男性原始刚劲。《右岸》中刻画的主要人物形象多是女性,而且女性形象的刻画远比男性形象要圆润、饱满得多。
[1]安殿荣.鄂温克族书面文学中的民族记忆[J].中国民族,2006(4):15-17.
[2]褚桂平.鄂温克家园失落的比较研究—以迟子建和乌热尔图为例[D].广州:暨南大学,2011:16-20.
[3]刘中顼.民族文化的纪念碑志与族群生态的时代涅梁——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6):99.[4]孙俊杰.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意识[J].名作欣赏,2012(7):26.
[5]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2000:5.
[6]史元明.新时期生态文学研究——以徐刚,苇岸,迟子建为个案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7:18-31.
[7]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艺术广角,2006(2):34.
[8]王霄羽.《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人与自然[D].兰州:兰州大学,2011:30-31.
[9]张向东,罗文政.《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文化元素探微[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675.
[10]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J].当代作家评论,2006(4):43.
[11]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53.
[12]唐晋先.为爱而苦终无悔——《额尔古纳河右岸》女性形象分析[J].作家杂志,2011(4):4.
[13]向林.论《额尔古纳河的右岸》中女性人物的悲剧性[J].大众文艺,2012(1):153.
[14]刘春玲.文化嬗变下的人性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新生代青年形象的解读[J].大连大学学报,2012(5):27.
[15]孙苏.与心灵的美丽邂逅:《额尔古纳河右岸》艺术观照[J].学术交流,2010(9):168.
[16]田秘.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特色[J].安徽文学,2010(10):67.
[17]张沛.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叙事视角的设置[J].北方文学,2011(3):27.
[18]纪佳音,岳静.《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色彩美[J].文学艺术,2013(8):81.
[19]张贝思.从呼兰河到额尔古纳——萧红与迟子建之间的故事[J].作家,2009(24):1.
[20]李娜.鄂温克民族生活的再现——乌热尔图小说与《右岸》比较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23-28.
[21]李旺.书写鄂温克——乌热尔图、迟子建比较论[J].扬子江评论,2012(4):76.
[22]邓经武.《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地域书写与种族代言[J].当代文坛,2012(6):95.
【责任编辑 詹丽】
I106.4
A
1674-5450(2015)06-0101-05
2015-04-18
内蒙古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NMDSS1414)
于巍,女,河北唐山人,内蒙古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