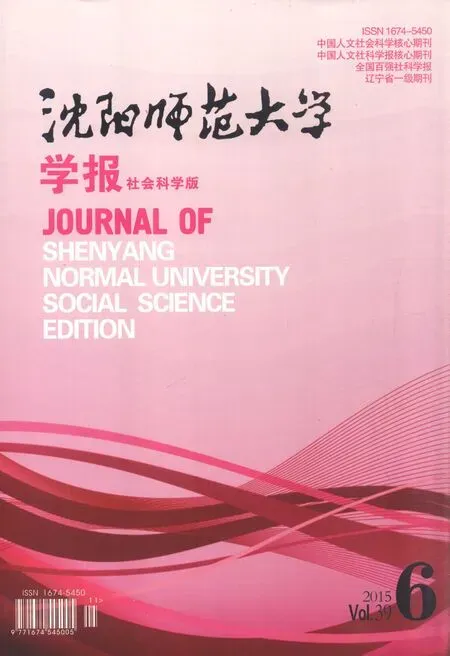荷尔德林浪漫主义诗学思想中的“返乡”情结
姜峰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819)
荷尔德林浪漫主义诗学思想中的“返乡”情结
姜峰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819)
作为德国18世纪末著名的抒情诗人之一,荷尔德林为浪漫主义诗学思想中注入了一种独特的“返乡”情结。在这样的诗意语境中,诗人对于德意志民族性的思考从故乡的怀念升华成祖国精神的建构。在他后期的诗歌创作中,他将对于地理意义上故乡的赞美转变成为精神层面上祖国的歌颂,在表达浪漫主义者对于无限美好事物追求的同时,也诠释着对于重振民族精神的渴望。
浪漫主义诗学;返乡;民族精神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说:“人们的哲学思想的类型,是由其所处的命运决定的。”作为一名德国哲学家,他的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于以往德国哲学家理论内涵的一种概括。作为与费希特同时代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荷尔德林的诗学思想中不可避免地表达着他对于所处时代的精神感悟。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的思想中,往往表现出一种对于无限而美好事物的渴望,在这种德国浪漫主义语境中,荷尔德林又融入了某种特殊的“返乡”情结。这种“返乡”宣告的并不仅仅是打破地域的界限、对故土的渴望,而是被升华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归家”。对这种“归家”情结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打破地域之界限和分离之狭隘,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中,对这种极具浪漫主义精神的哲学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的审视和挖掘,从而从全新的角度探寻西方浪漫主义思想之追求。
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浪漫之思
18世纪的德国是一个由三百多个大小公国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政治联邦。虽然席卷欧洲的启蒙思想为德国带来了理性的广泛传播,但由于30年战争的影响,德国的资本主义进程相当缓慢。同时,由于保守的“路德派”再次复苏,封建和宗教势力也随之复苏,而各地公国和诸侯的专制统治进一步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的复苏,并进一步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进程。恩格斯曾经把18世纪的德国称为封建的“奥吉亚斯牛圈”[1]。席卷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在德国却逐渐退化成为一种虚幻的理念,而没有最大限度地付诸现实。德国的众多知识分子可以在理念上表现得非常浪漫,然而却总是与现实表现出一种距离感。“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毅力,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勇气”,“推翻旧的政府,重建帝国”[2]。所以,18世纪的德国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度,而不是战士和行动的国度”[3]。拥护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只是局限于探讨知识、人文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甚至是民族主义,却忽略了启蒙的广泛意义与民族精神”[4]。然而这种局限却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复兴,体现出很多进步的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超越当时德国日渐僵化的工具理性的束缚,借助于自由之思和审美等手段,寻找超越“有限性”的可能性。
而由于路德派保守势力的再次上台,也使德国启蒙思想相比于欧洲其他国家更多地与宗教思想交织在一起,一些启蒙学者试图调和宗教思想与启蒙理性间的矛盾性因素,试图使宗教与科学以一种调和而非对立的样态存在,从而使德国启蒙思想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与自我更新,从而使当时的某些哲学理论在哲学的基督教与基督教的哲学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摇摆不定与德国古典哲学日益强化的思辨性相结合,体现出一种与同时代英法哲学思想异质性的特征,这也加速了当时德国神秘主义思想的形成,这一特点为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形成增加了某些特殊的历史元素。
同时,任何事物都很难独立存在,他们都在对立的斗争中存在和发展。作为一场兴起于欧洲大陆并席卷世界的思想运动,启蒙也有其对立面的存在,即“反启蒙”。而启蒙思想也是在与这些对立思想的争鸣中逐渐寻求一种合理化的展开。这种反启蒙的思潮中不仅仅包括维护旧权威的保守派,还包括一些具有启蒙精神的进步学者,他们立足于长远的历史性视野,跳出启蒙理性的规定性来对启蒙提出质疑。“反启蒙”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德国启蒙时代理性的样态,让启蒙理性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中展现出丰富的内涵,其中既包括理性绝对化的主张,也包括把理性与范围的限定结合定义,同时也有学者主张理性与其他要素的融合[5]。赫尔德(Herder)等一批浪漫主义思想家从法国的卢梭哪里吸收了自然主义和情感主义思想,他们反对将理性和知识绝对化,既反对对于宗教的迷信蒙昧,也驳斥理性至上的绝对化。他们认为在倡导理性的同时,不应该忽视人类的情感要素和想象力,否则理性和逻辑就会变成一种人为的约束。浪漫主义者们借由对于启蒙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诠释着浪漫主义的诉求。
二、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中的“思乡”与“返乡”
在启蒙运动的时代语境下,德国的浪漫主义哲学思想逐渐形成。“当资产阶级日益卸下往日的伪装……启蒙精神失去了曾经鼓舞人心的精彩,激情转化为狂躁,自由更改为专制,革命演变为恐怖,理性的极度扩张弥盖了情感与艺术存留的空间。”[6]为了找回情感与艺术存留的空间,浪漫主义者开始反思启蒙理性光辉背后的局限,他们继承了启蒙的批判精神与怀疑态度,并将这种始终保持着对外向度的批判和怀疑精神指向了“理性”本身。启蒙者凭借其“华丽的诺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变成了令人失望的讽刺画[7],政治理想的搁浅导致人们转而投身于文学艺术领域,国家统一理想蜕变成为一种重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诉求,德国浪漫主义思想逐渐与文学和艺术等形式交织,使“理性”施加在创造力之上的毁灭性理想在文学和艺术的空间中逐渐被驱逐。
同时,一些浪漫主义者也希望借助古希腊文学与艺术的荣光帮助人们充实日渐消退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涵。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积极投身到柏拉图全集德语译本的计划和翻译中,虽然后期施莱格尔并没有参与具体的翻译工作,但他发表了多部阐释柏拉图思想的著作。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译本更是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与时代意义,对当时的德国来说彰显着“伟大的希腊哲学的全面复兴”,也使“德意志民族首次拥有了柏拉图思想中宝贵的精神财富”[8]。他们开创了一种“浪漫的柏拉图诠释范式”[9],这种诠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因循着德国浪漫哲学与文学相互交融的样态,把文学理论分析的视角引入到柏拉图的哲学文本之中。即必须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理解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内涵,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理念打破了当时对于古希腊哲学纯粹义理式和逻辑式的理解框架,为哲学的思维范式注入了浪漫精神的内涵,哲学家同时也具有了艺术家的气质[10]。由此,人们开始从全新的视角理解柏拉图思想中的哲学内涵。“反讽”“对话体”、文学、语言学和哲学在浪漫主义的语境内达到了新的融合。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内,哲学彰显着自己浪漫的气质,诉说着自由的精神。而德国浪漫主义的自由彰显的是突破理性的有限制约,向着无限的精神境界前进。由于“无限不可穷尽,我们永不能贴近它,我们总在追求却难以满足,因此我们患上了思乡病”[11]106。这种思乡不是传统地域和生活情感层面对于故土的思念,而是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思想归宿的全新诠释,诺瓦利斯借小说主人公的话语将自己的思想归宿概括为:“总是在回家的路上,寻找我父亲的老宅。”[12]而这种浪漫主义的“思乡”情结从另一个层面上诠释着人类表达天性和体现自身创造力的“向往”[11]107。这种向往缘起于一种浪漫主义观点,“人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就是表达自己的天性。表达人的天性就是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虽然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不可表达的,但必须尝试表达”[11]107。
三、荷尔德林诗学思想中的“返乡”
作为一种产生于德国浪漫时代的诗学思想,荷尔德林的诗学思想表现出一种与当时并存的优秀思想的交融性,受到同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荷尔德林早期思想体现出的更多的是对思辨思维的赞颂。当时,正值康德的三大批判相继出版,批判哲学体系逐渐成形的时期,康德的思想犹如一阵飓风,在哲学领域内掀起“哥白尼式革命”的同时,也吹进了如一潭死水的图宾根神学院,为这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任务的闭塞的学院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希望,这些也深深地影响着荷尔德林。他在1799年写给他的兄弟的信件中高度赞扬了哲学为当时的德意志民族所施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高度地赞扬了康德哲学思想的作用,他在信中说:对于我来说,“康德就是我们的民族的摩西,将我们从衰退的古希腊引入了他那片自由但又浑然物外的思辨沙漠之中,聆听他从圣山上带来的福音(生机勃勃的律法)”[13]。
“按照西方哲学的初始逻辑及其内在惯性的演进路线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的早期路线图的总体概貌是确立本体的内在优先性原则,按照这种原则的思维路向就是在意识论和概念论以及二元论的根基上勾画出对本体的建造和固化。”[14]康德的哲学观点可以说是沿着这种思维脉络的指向逐渐延展的。然而,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很快认识到自己体内的创作激情与德国古典哲学那种系统化的理性之光无法融合,发出感叹“哲学是一位暴君,与其说我臣服于他,不如说我容忍其专横”[15]。但这种容忍没有抑制其追求与批判精神,在与老师费希特进行了充分交流之后,荷尔德林于1795年完成了著作《判断与存在》,在这部宣告其未来诗学思想走向的重要著作中,荷尔德林试图跨越康德和费希特的界限,从而完成自己的诗学诉求。如果说康德的理论起点是“人为自然立法”,而费希特的出发点是“自我与非我的相互设定”,那么荷尔德林的《判断与存在》则是希望通过“存在”寻找主客体的同一。费希特认为“绝对自我”能够“自己规定自己”,所以一切存在都以“自我”与“非我”的同一性为前提。然而在荷尔德林看来,自己规定自己则是以“分离”为前提,只有“自我”和“非我”分离之后,才有可能将二者置于具有同一性的观察视角当中,所以“我是我”作为一种判断则是以“分离”为前提的,而判断(Urteil)与区分(Urteilung)当时德语中的确具有同义性。那么由于“自我”和“非我”分离而导致的主客体的分裂,只能通过“存在”得到同一性的表达,即只有主客体同一的地方我们才能谈论存在。
当康德和费希特希望从主体性的内部寻求主客体的统一时,荷尔德林则尝试着通过“存在”的回归来克服主客体的分裂,而这种回归也将德国浪漫主义的“思乡”之情发展成为一种“返乡”之思。这是一种递进式的变化,彰显的是浪漫主义者对于完美之诉求的飞跃。这种飞跃将哲学的理论探讨和诗歌的艺术创作融为一体,使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哲学在诗歌中得到更加具体化的体现。在荷尔德林的后期诗歌中,他已经慢慢放弃了对于地理意义上故乡的赞美,转而在精神层面为祖国高唱赞歌,这已经不是针对浪漫主义“自由”之思的歌颂,而是将“自由”之思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结合,在哲学与文学的纠缠中实现了德意志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复兴。而具体到诗歌创作中,体现出的是通过与“自我”同源的“非我”式词汇的创造。在诗歌中,与“祖国”(Vaterland,德语直译为“父国”)一词相对,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母地”(die Mutter Erde),用来表示地理层面的故乡,而“祖国”/“父国”则成为政治、道德、文化等层面的精神建构,从此,浪漫主义者对于德意志民族性的思考从地理故乡的怀念升华成为祖国精神的建构,从对于希腊文化的满腔热爱升华为一种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具体实现。
[1]恩格斯.诗歌与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C]//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4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633.
[3]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565.
[4]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一卷[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81.
[5]O’Flaherty J C.The Quarrel of reason with Itself.Essays on Hamann,Michaelis,Lessing,Nietzsche[M].Columbia:Camden House,1988:149.
[6]刘聪.通往“蓝花”深处——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4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607.
[8]Szlezák TA.Friedrich Schleiermacherund dasPlatonbild des19. und 20.Jahrhunderts[C]//Protestantismusund deutsche Literatur(Münchener Theologische Forschungen,Bd.2)Gö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2004:125-144.
[9]先刚.施莱格尔的浪漫式柏拉图诠释及其相关问题[C]//北大德国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5.
[10]Schleiermacher,F.Über die Philosophie Platos[M].Hamburg:FELIXMEINERVERLAG,1996:28.
[11]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吕梁,洪丽娟,孙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2]Novalis.Schriften:Die Werke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s[M]. Stuttgart:W.Kohlhammer,1960:325.
[13]Hölderlin F,Schmidt J,Grätz K.SämtlicheWerke und Briefe in dreiBnden[M].Stuttgart: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1994:331.
[14]陆杰荣.论形而上学与哲学境界的内在关联[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2):109-112.
[15]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M].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78.
【责任编辑 赵颖】
B516.39
A
1674-5450(2015)06-0109-03
2015-09-10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20023);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ZX055)
姜峰,男,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讲师,辽宁大学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
——关于荷尔德林的诗《在可爱的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