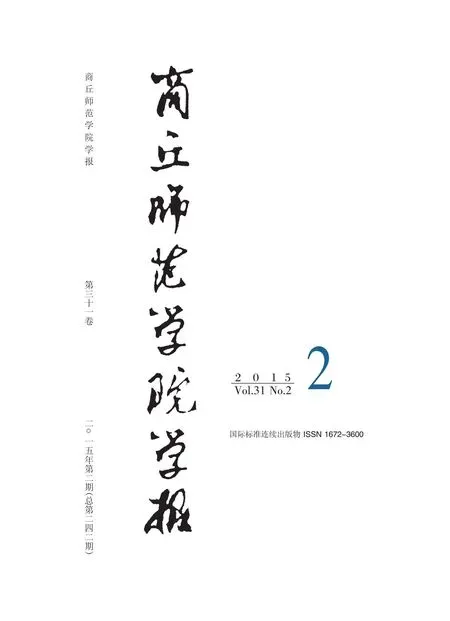乘物游心,无为大用
——曹宗璠《南华泚笔》研究
周 鹏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乘物游心,无为大用
——曹宗璠《南华泚笔》研究
周 鹏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庄佛互释是一种古老的学术现象,历代佛道学者均对这一路学术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明末清初学者曹宗璠著《南华泚笔》一书,延续了这种古老的手法。他以《华严经》为宗解释《南华经》,用《华严》“三界唯心”说在本体层面连通了佛学与庄子,并超越“色心不二”的见性境界,提出欲改造“世界”,根本在于把个人的觉悟与众生的因果结合起来,从而深刻揭示出佛道两家“无用之用”的化世大用。
曹宗璠;《南华泚笔》;乘物游心;色心不二
庄佛互释是一种古老的学术现象,自从佛法东来,便一直藉助着老庄玄理传播着天竺的妙义,道家学者亦以佛家的般若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大道的玄门。晋代支道林、唐代成玄英、宋代林希逸、明代释德清,均为这一路学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延至明末清初,遂有曹宗璠。
曹宗璠,字汝珍,号惕咸,金坛人,生卒年不详。明崇祯四年进士,崇祯七年任封丘县令。清顺治十八年,受通海案牵连,几乎被杀。著作有《麈余》、《故琴心》、《南华泚笔》等。
《南华泚笔》[1]二卷,前有康熙二十九年储士《南华泚笔序》、康熙三年《南华泚笔自序》。据书中有关文字推测,此书当成于曹氏康熙三年撰写自序之前。宗璠去世后,由子孙付梓于储士康熙二十九年撰写序言之时。
本书体例颇为驳杂,大都为短论性质。作者自云:“余幼喜看《南华》,为其思径窅渺,开文章鸟道耳。既而策名仕籍,遽罹厂珰之难,觅食四方,于东莱道间遇秦中头佗,口授坎离秘诀。复与方子元穉披衣夜坐,旬月得效甚速。……余谢方子曰:心力尚壮,欲殚精诗赋,……缅彼白云乡,桑榆收之未晚也。”至其壮年,“偶过孙定斋中,见旧所批《南华》丹铅,璀璨如新,覆读之,抑何与宗门语水乳交而空青转也。因随手所得,摘之于椠,得五十一纸,喟然叹曰:此书予幼既其华,壮既其实,于所谓‘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者,身亲[2]其事矣。迄今所得更有异,遂为《金刚》、《华严》引路也”(《南华泚笔自序》)。可见此书并非作于一时。宗璠历经世事变幻,见地更为精纯,不再停留于《南华》文辞的表面,而是深入到其义理之内核,并且更进一步看到了《南华》与《金刚》、《华严》的内在联系,将《南华》视作二经之导引。故书末《南华泚笔述言》又云:“《南华泚笔》者,以《华严》注《南华》也,以五经、二十一史注《南华》、《华严》也。诸经未到以前,晋道林、慧远不过向《南华》索义,而内篇亦已推论《人间世》、《应帝王》,岂无意世道人心者,……以此操政治之原,则平阳之清静也。……若作空门语录,虽入释藏、道藏,非阐扬意。予小子恐假道学辈,莫究涯涘,辄妄河汉,欲终秘之,乃请质王迈人、汪苕文两先生,皆留之久,而大此书。寄语亟梓,且曰:前辈柳子厚、李习之、苏子瞻兄弟,未尝不悟微言,畅宗旨耳。序中遂并及,于是诺诺,而公诸世。”依此意,此书则以《华严经》为宗批注《南华经》,再以世典作《华严》、《南华》之旁证,欲打通入世出世之界限,故此书可以“操政治之原”,亦可作“空门语录”入释道二藏。作者又怕世间假道学辈不明其旨,妄为河汉,不欲将其公之于世。友人以柳宗元、李翱、苏轼兄弟述圣先例劝导之,方将此书付梓流通,言辞间颇有佛门大德不轻易开坛说法之姿态。
那么,曹宗璠历经世事变幻,究竟悟到了什么高深的妙理,让他对自己的著述珍重如是、不欲轻出呢?通观全书发现,曹宗璠抓住一个“心”字,对《庄子》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诠释。而他的理论思维,的确受到了《华严经》的深刻影响。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包含之义;方,轨范之义;广,周遍之义。一心法界之体用,广大而无边,故称为“大方广”。佛,证入大方广无尽法界者;华,成就万德圆备之果;严,开演因位之万行,以严饰佛果,此为佛华严。如此“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气魄,使它成为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被大乘诸宗奉为“经中之王”,唐代甚至有以此经为依托,建立“华严宗”。故曹宗璠以《华严经》为底蕴来阐释《南华经》,无疑是占领了一个极大的理论高地。
《华严经》义理深微广大,曹氏主要发挥的是其“三界唯心”思想。《华严经·十地品》云:“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来于此分别演说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2]在小乘佛学,“三界”被视为实存的三种环境,而非一心所作;十二有支,亦即以十二因缘说明众生轮回的原因以及摆脱生死流转的方法和途径,并没有依于一心的意思。而《十地品》将“三界”、“十二因缘”归于一心,“心”不再只是个体内在的精神力量,而是具备了具体共相的时空感,这恰恰与老庄的大道本体论相通。曹宗璠遂以此说释《逍遥游》篇云:
真心无量,人好以知与物斗,小知大知相盖,得非有蓬之心乎?人而无有知也,则亦无有用也。无知为知,无用为用,岂翱翔蓬蒿间者耶?天池也,藐姑射之山也。江湖也,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也。观心者自遇之,出门迢递懒言心,留得烟波补劓黔。谁动心源蓬盖影,蜩鸠解上树头吟。(《逍遥游本文支节》)
《庄子·逍遥游》篇云:“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3]又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人间世》篇云:“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又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外物》篇云:“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人心最根本的弊病,就在于在种种境缘中,太迷信“已知”、“有用”,而不知任何“已知”、“有用”皆以无量的“不知”、“无用”为根基。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任何一次具体的“知”、“用”,皆是“已知”、“有用”与“不知”、“无用”的对立统一;只知“知已知”、“用有用”,而不知“知不知”、“用无用”,不仅仅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更会把“知”、“用”的源头活水堵塞了。既知此理,那就应该在任何一次“知”、“用”中,“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庄子·大宗师》)、“假不用者以长得其用”(《庄子·知北游》),即不把眼前的“知”、“用”绝对化,而是将“知”、“用”仅仅当作无量“不知”、“无用”的导引,智慧就必然源源不断地到来,人也就能进入“逍遥游”的“真心无量”之境了。故曹宗璠说:“无用为用,是逍遥真宰。《南华》直揭出‘心’字,点逍遥作结。(《瓠种樗树》)……逍者如春冰之就泮,遥者如飞鸿之若没。逍则无我,遥则无物,无己无物,而功名冥矣。游者,无所住也。逍遥游者,心之本位然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待西方圣人矣。”(《解题》)“逍遥游”就是“无知为知”、“无用为用”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4],佛与庄在这里连成了一体。
曹宗璠既以“三界唯心”说在本体层面连通了佛学与庄子,在解释《庄子》时,他就显得举重若轻、高屋建瓴了。他释《庄子·齐物论》篇:“《楞严》八还辨见,七结返闻。文殊指,而明月无留川影。迦叶舞,而大地皆作琴声。海天苍苍,山林翏翏,心境一如,固无心外之法也。”(《写意》)佛陀在《楞严经》里通过各种方便譬喻,揭示出“山河大地,无非妙明真心中物”的奥义;《齐物论》篇开头部分对“天籁”的生动描绘,亦是南郭子綦“丧我”之后对自己广大无比的心境的临摹,这正如曹宗璠所说:“人能见真心,方得丧我,步步不留踪,心心无处所。若只习静,鲜不为境风所飘者矣。”(《写意》)“真心”逍遥,无所不包,其中却没有一个“我”的歇脚处,既如此,那么,“怒者其谁耶?”曹氏自答:“只拈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便了真宰端的。《楞伽》偈曰:由自心执着,心似外境转。彼所见非有,是故说惟心。”(《大块噫气至可不谓大哀乎》)从“知无”一路深探下去,知无、无无、无无亦无,便找到“真宰”了;就怕在此过程中,心有执着,为境所转,“天籁”也就听不到了,故曹宗璠感叹道:
《南华》哀万物之各有其天籁,而莫知适其天也。哀之则必救之,救之则必示之以真心。真心者,内丧我,外丧物,遍天下不见一人为耦,一物足感。此日嗒然无始,不知始也;嗒然无无,不知无也。始不碍始,无不遣无,亦曰真宰存焉矣,岂待索之天籁而遇乎?言非吹也,窃吹之窍,好以坚白鸣,吾何择言乎?吾何遣言乎?当其有言,九年面壁不为寂;当其无言,无情说法不为喧。丧似则得丧之枢,化冥则司化之极而已矣。故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中者无始,物莫测其朕;中者无无,物莫启其门,我遇其天而万物遇其天也。籁曰天籁,钧曰天钧,府曰天府,倪曰天倪,其大觉者耶?无所谓觉也。无梦尔,梦不占梦尔。夫然后狙怒且甘,各安其性,鸒音蝶诩,各恬其知。是谓我丧而物会宗,物化而我命钧矣。故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以单提直指之旨,岂向物论索齐哉!(《齐物论本文支节》)
在曹宗璠看来,庄子作《南华》,正为哀叹人人皆丧失了自己生命本有的天籁之音的缘故;为了找回生命本有的天籁,必须揭破生命的本来面目,示人以“真心”。何为“真心”?对内扫除我相,对外破除法相,找到生命初始的“无”,走遍天下也是空空荡荡、无着无碍;再进一步把“始”、“无”也舍掉,浑浑沌沌,终身不离,也就找到“真宰”了。此时就不用执著于名言层面的“天籁”,亦不用“遣言”——万物的孔窍皆能说法,触境皆是妙义,还用得着刻意去“遣”吗?到了这种状态,就可以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真正回归自己的本然。我回归了自己的本然,亦即万物回归了自己的本然;我本在万物中,我放下了自我而回归万物,亦即万物本身找到了自己的宗本;而万物复归了其应有的存在状态,我自己的生命也就变得大通畅、大和谐;从此“天地一指,万物一马”,三界唯是一心,物论不用去齐,自己也齐了。这时便是:
参万岁而一成纯,且先参剎那。剎那无断,则万岁亦其本际。《法华》云:“我观久远,犹若今日。”“常在于其中,经行及坐卧。”苏子瞻月夜过白鹤观,访裴舜民,空庭竹柏影,如荇藻交横,此非他,步步蹈着心光耳,固是古今一照。(《齧缺问乎至寓诸无竟》)
停曦无恒照,玩义可忘年,声化相涵,犹色心不二,寸晷清思,尺锤长古。禅者曾问云:“毕竟如何?”答曰:“此中亦无毕竟。”闲垂一足,以谢桑阴。(《寓诸无竟》)
尽大地,明皎皎,无有一丝头可商。蝶耶周耶,一泓清碧,才涉伫思,便起现行,蠕蠕蝡蝡,欠伸已就。玄猿夜哭巫山月,客路原来不可行。(《问景梦蝶》)
按照经典物理学的时空观,宇宙是由一个硬邦邦的时空框架与一个个纯粹物质的星球所组成,时空本身是绝对的,人心只是物质星球形成之后的历史产物。可到了现代,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相对论揭示出时空是相对的,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更是对人心与外境的绝对分离提出了质疑。现代物理的最新发现无疑响应了古老佛学的宇宙观、生命观。佛学认为,宇宙——生命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空依心而起,只有相对的意义,只因为人对宇宙——生命系统的认识出现了误解,才使得主体与他的世界隔离了;只要觉悟,人依然能够回到时空俱泯、心境一如的本来面目。《庄子·大宗师》亦云:“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知北游》篇云:“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犹今也。’”通过一层层的“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不但可以进入“古犹今”的时空泯灭之境,而且能够领悟本无生死的至高奥义;此时所见,只是一片纯粹因缘的美丽,万法从心流出,不再有遮隔。曹氏所谓“步步蹈着心光”、“声化相涵,犹色心不二”、“才涉伫思,便起现行”,即是指此而言。
曹宗璠并没有停留在“色心不二”的见性境界上。在他看来,见性后通过反观人间的色法,可以使心体逐渐澄明。他说:“观色可以知心,以阳为充孔扬,中藏有盈亏,故采色不定,反求外感以容与其心,所积者销亡矣。若东郭顺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是何德也?又若壶子示渊而走,温雪目击而存,何可不置之心目间,与人间作镜。”(《庄子·人间世》)孔子云:“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5](《论语·雍也》)人之心不明,是因为中有积垢,遂遭扭曲,扭曲之心须遇善缘以化解。在曹宗璠看来,如壸子、温伯雪子这样的大觉,虽说也是“物”、“色”、“人相”,但怎可不放置心头以作觉悟之镜呢?曹氏这番言论明显是针对晚明学人一味师心自用而发。在论“心斋”时他又说:“诗云:‘奏格思成。’斋者,必思其祖父之形容、之笑语,见其人而后成享。在天地鬼神,思其情状,思其功德,亦犹是也。若心无体无方,亦必澄思真见无体无方,而后谓之斋,此正是守三日而忘天下,守七日而忘物,守九日而忘己事。”(《虚者心斋也》)在论“心止于符”时亦云:“符犹云心所。崔注符券,便有四至方隅,不若气之虚而待物也,此未必斋时事也。若心斋则心无其心,气无其气,何待哉?符亦何物?一条柱杖子。”(《心止于符》)按,在佛学,心分为心和心所两个部分,心是能知,心所是所知,两者名虽有二,实则绝对同一;每一次“心——心所”的变现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但此变现过程却是无穷无尽的。晚明诸人受心学末流影响,一味强调能知之心的与物无对、虚灵不昧,而忽略了能所不二的永恒变现,往往酿成沉空守寂之病。曹氏在此处即是强调,虽说山河大地无非妙明真心中物,但真心亦必显相为山河大地之“符”方才可知,不显为物相之“符”,“心”的一次运动就不完整。从曹氏的“物为心之符”再向前一步,即是王船山“师心不如师物”的唯物论[6]。曹宗璠并未跨出这一步,而是同时强调“符亦何物?一条柱杖子”。所谓物之“符”,不过是明“心”的一个拐杖而已,必须随立随破,方能保持心体的无着无碍。由此可以看出,虽说曹氏声称自己以《华严》来解庄,实际思路却颇得阳明心学的精髓。王阳明一生强调要在心体的“虚”与世事的“实”之间保持出入平衡[7],可惜其后学往往不是堕于虚,便是迷于实,失了心学的本意。故曹宗璠又感叹道:
夫抱虚而游,行天下不见有一人也。且离人独立者,又慹然入于非人也。何以标之曰人?爱恶攻取,利害斗争,亦曰人耳人耳。何以大力者挈而举之曰:世。或曰:有因果,斯成世,善恶酬报,本业如轮,三世毕具。或曰:有能所斯成世,根尘对触,惟力所造,遂起现行。或曰:有克治斯成世,净染差照,爰立剎土,克尽则销。于是揽宿业,如种生芽,起现行,如志动气,分净染,如形随影。三界惟心,觉王论之详矣。顾一心之清净,可以顿超,群心之积志,由乎曲牖,诚建出世之大觉,必提入世之精心。如怀婴儿者,燥湿以身代,如送亲丧者,踊躃不自知,此般若之门,即是慈悲之路。然岂智杜悲航,悲增智障,各相妨也哉!(《人间世》)
这段文字略有些费解,其意在说:真正能“乘物以游心”的人,天下一个也找不到啊!而刻意逃世者,又往往弄得自己人不像人。世间所谓的“人”,到底是指什么呢?爱恨情仇、打打杀杀罢了,这就叫做“人”吗?既然如此,为何大觉又如此强调一个“世”字呢?第一,“世”是因果造成的,善善恶恶的业力如同车轮一样旋转,三世就形成了;第二,“世”是能所造就的,六根与六尘相接,彼此激荡,世界就稳固了;第三,“世”又是被不断改造而变化的,觉心舍染趋净,五浊恶世亦可究竟涅槃。这三种“世”之成因,其实是一个过程:业力显发,变现世界,再以觉悟对治之,一切皆是一心之作用啊!只是一个人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悟性而顿超尘累,而群体的觉悟大业,就是一条无比曲折的道路了。所以,真正建立出世大愿的觉悟者,必然怀有入世度生的精志切愿。正如抱孩子的人,无论多么肮脏,皆以自身代之;为亲人送终的人,顿足捶胸大哭,亦必出于天然。真正的智慧,其中必含慈悲,悲智本来双运,为什么让两者各自相妨呢?曹氏这段文字,精细道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成因,并指出欲改造这个“世界”,必须把个人的觉悟与众生的业力结合起来。那么,这个“世界”,我们又如何具体转化它呢?曹宗璠接着说:
自藏识显为真如,真则一无所有,如则遍与之然,则虚之一言,印万法之宗。虚者,真如之性也。识受薰变,成根身器界,遇物现前,带影成相,亦即带如相而起,是在相而不离如也。由是暴人,亦吾心之暴人也;虎马,亦吾心之虎马也;山木膏火,亦吾心之山木膏火也;人道阴阳,亦吾心之人道阴阳也;名根争器,亦吾心之名根争器也。心与物如,物与物如。物与物如为如如,心与物如为如如智。以如如智入如如,如既浑融,智复何有?于是因果之世寂也,种子净矣;能所之世寂也,觉明净矣;对治之世寂也,变化净矣。世轴既隳,人相亦冥,惟一性光,结成法界。何漆园非给孤之园?何濠上非恒河之水?因缘既合,烛穗交光,泚笔兹篇,筦尔而笑。(《人间世》)
曹宗璠又以唯识理论解释世界起源,认为自从阿赖耶识变现为真如法界,一无所有的“真”就显相为普遍存在的“如”,一言以蔽之曰“虚”,此乃真如之性。阿赖耶识受到熏习而变现出六根、身体、器物、空间,由隐至显,而成物相;虽成实在之物相,实在之“物”亦有虚无之“如”相随。故暴人是我心中的暴人,虎马是我心中的虎马,山木膏火是我心中的山木膏火,人道阴阳是我心中的人道阴阳,名根争器是我心中的名根争器;物与物看似有僵硬的间隔差别,其间却有虚灵不昧的“如”一气贯穿,心与物之间亦然。万物一体即如如,心知此理即是如如智;以无遮隔的“如如智”进入无遮隔的“如如”,“如如”便与“如如智”浑然一体。于是扭曲的因果没有了,藏识中的种子也就清净了;虚妄的能所也没有了,也就无所谓觉与不觉;因果与能所消失了,也就无所谓改造世界。只有一片心光构成纯粹自然的“法界”,这样,庄子的漆园与佛陀的给孤园,又能有什么差别呢?曹宗璠的这一段话,明显发挥了《金刚经》第三品的思想:“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即是佛学的无为法,与儒家强调以身入世的有为法略有不同,但救世的根本目的则是一致的。《庄子》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在宥》篇写黄帝见广成子,寻求救世之道,广成子否定了黄帝的苦身焦思,对他说:“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广成子意谓,既然我与你黄帝皆是天地阴阳所化,本为一体,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身改变你与天地阴阳的状态;我只要守住我心的一片纯和,你与天地万物都会走向光明的前途。此即是道家的无为大用,是道家学说最深邃的地方。老子所谓“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8](《老子》第2章),也是这个意思,只是往往被后人看成有为法的政治策略罢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曹宗璠的确是一位对佛道学说有着深刻领悟的学者。其所著《南华泚笔》用《华严经》的“三界唯心”说巧妙地揭示出《庄子》最空灵阔大的一面,并且乘晚明儒释道合流之末运,阐明了佛道两家“无用之用”的化世大用。惜乎此书出世,已进入万马齐喑的清朝,时运既已过去,至言只好沉埋。
[1]方勇.子藏·道家部·庄子卷[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2]实叉难陀.华严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3]方勇.庄子纂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4]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王夫之.庄子通[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责任编辑:高建立】
2014-10-02
周鹏(1985-),男,安徽淮南人,博士生,主要从事老庄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B223.5;B94
A
1672-3600(2015)02-0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