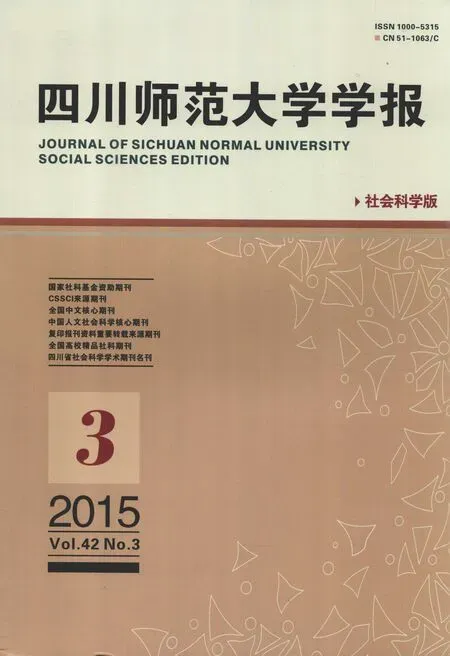职业重塑:民国旧式产婆训练班研究
朱 梅 光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职业重塑:民国旧式产婆训练班研究
朱 梅 光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民国旧式产婆训练班开启了传统产婆大规模近代职业重塑的历程,是落实产婆改良思想的一种制度性举措。以新代旧的职业重塑,主要通过技术置换来逐步展开,反映了接生手法医疗化的转向,同时又催生了职业资格化制度设计的进程,共同塑造旧式稳婆以西方为典范的职业形象和职业手法。早期作为先导的民间训练模式,与后来国家主导的普及化推行,共同构建起制度形塑时官民互动的发展态势,在其中,国家扮演着资源整合者和制度运行保障者的角色,民间医学和教育资源仍然发挥着促进作用。就制度实施的效果来看,职业重塑的历程不甚理想。训练方式上的“损之又损”以及“学”与“术”的训练难以兼顾平衡,这些自发生成的制度性障碍,对过渡时期产婆训练的整个行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产婆;职业重塑;产婆训练班;技术置换;制度形塑;制度反思
传统中国的生育观,向以胎产归之天然,将接生一门视为卑污下贱之行业,操其权柄者,多为旧式产婆。近代以后,本乎西医技法而养成的助产士兴起,在职业手法上与传统稳婆迥然有别,新旧两大产婆群体渐呈对立之势。但在新旧嬗变之际,近代国人经充分辩论,逐渐达成改良之议,对旧式产婆进行职业重塑,约于1928年后,她们以接受较为统一的训练班形式,被逐步纳入正规的助产职业教育的行列中。伴随医疗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学界对近代产婆的研究,也由过去蒋竹山所评论的“少有人碰触”向间有所论转变①,但相比而言,对其职业改造的研究,触论还甚浅。有鉴于此,本文拟借助于对旧式产婆训练班的制度检视,对相关问题作一专门探讨。
一 以新代旧的技术置换
产婆训练班中医疗化的分娩行为是如何展开的呢?就分娩行为的医疗化而言,至少有二重涵义,既有针对产妇分娩各阶段是否处于医疗“氛围”(而非迷信)中予以救助的一面,也有涉及接产人员是否能够医疗化“施行”(而非仅凭经验式)的另一面。具体到产婆训练班来看,以新代旧的职业重塑,核心是接生手法医疗化的转向,而这首先是通过技术置换来逐步展开的。
就技术而言,产婆拥有的“旧式接生方法”,属于传统经验的范畴,在新技术者眼中,这是典型的“非科学与没有前途”。因此,训练班的创设,就是要触及接生问题中的新与旧,即“新的医学的智识与技术如何在这新旧交替的社会中帮助和增进这些非科学的旧医药界人士”[1]100。“帮助”和“增进”的途径无他,唯有以新技术置换传统经验之一途。这种以新代旧,在时人看来,实乃时代发展的必然。但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自认为属于科学且有前途的一方,是如何“认定”旧技术的无效乃至危害性的呢?当时国人颇为推崇新医学,认为在医学上,与女子关系至为密切者,“莫如产孕小儿两科”,期待“医术昌明”,能成为当时“黑暗女界中之一服清凉散”,即使医学“现尚幼稚”,也“不可以其简陋而轻之”[2]9-10。 这种医学眼光与心态的养成,使得他们认识到旧式产婆连庸医也算不上,至多具备一些缺乏医学常识的经验。当时全国各地的稳婆普遍“生理不知,解剖莫晓”,仍强行收生与接胎[3]8。因此,这种分娩卫生,就其手法而言,更多属于一种社会行为,而非医疗行为。
约于1919年,毛子震从产科学的角度,建议将产婆的名字改为“护产医”,这是迎合社会心理尊崇医学的一种看法。而虞诚之也从医学的角度,对之“很表同意”,认为“中国的产婆向来没有医的知识,是无可讳言的”,若欲以“改良的动机”补救之,最切要的一点是产婆“万不能没有医的知识”[4]22-23。 由此可见,具体到产婆来说,学界言说中经常提及的“分娩医疗化”由来有自,并非专指蒋竹山先生所谓的“医疗化的分娩行为”。近代以来弥散于社会的崇医心态,远早于这种“施行”的行为,且形成一定的话语权势,解析并“认定”着旧式产婆及其传统经验。
其次,近代中国呈现中西医竞争的格局,竞争态势涉及面甚广,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产婆培训中。那么,谁能取得优势而成为培训的资源主体呢?其实,作为外来资源,早在19世纪末,已有人认识到“西法收生”能有“解产厄”的医疗效果。西方“收生诸事,皆藉医士取其谙识血脉子宫骨盘部位”,“故受胎成孕以及分娩产后各事,医士无不深明其理”;反观中医医史,“从来妇科书籍于胎产一门,大半专论气血,至胚胎分娩尤属模糊,大约因其近于狎亵,故从忽诸,无怪医家之梦梦,不得不以稳婆之言为圭臬也”[5]1-2。而到 20世纪初,中医形象益形毁坏,时人认为中医对于“吾国之厄于产事者”,“亦惟饰其按脉授方之丑态,此外更无所施”,而“教会医士及曾习西医者,能按医生之法则,拯之于危”[6]4,可见当时社会对西医的信仰有益形坚定之势。
1919年,在广东海丰产科学校的演说中,叶蔚文甚至认为,中国古代虽“有胎教之传,而保产则乏术,其载录于周秦古籍中者,几若昙花偶现,然又类皆散漫无序,实不足以言学也”,可见在叶氏眼中,传统资源实已被置于“不足以言学”的地步。何以言学呢?他认为,当然是西医资源,以此眼光视汉代以下妇科产科“专书”、“著作”和“胎产之方”皆为“古人之陈迹”,“其理论则与今之新医术不符”[7]55。这样一来,“新旧式接生问题”便转化成为“中西医问题的一部分”,在分娩医疗化的资源竞争中,中医与旧式接生法一样,被打上了“非科学与没前途”[1]100的烙印,从而退出竞争的行列。
随着社会的认可与接受,西医合法性不断增强,近代的外来资源也就成为改造传统的“当然”主体。1929年底,无锡市政筹备处社会科附设接生婆训练班,负责培训工作的王世伟主任与诸涵英教员,俱为拥有西医教育背景的产妇科开业医士[8]42,45。 全国其他地方性的“训练稳婆办法”中,俱明确宣示招集组织的训练班应“遴请当地西医或助产士义务担任训练”[9]12。至此,旧式产婆经由西方医学观念的冲击,再到被动“认定”,步步深入地受到西方医学的影响,开始进入医学体系并接受正规的医学训练。
医疗化要求产婆具备医学知识,产婆被纳入正规医学培训体系,同时也催生了职业资格化制度设计的进程。在虞诚之看来,过去被称为“有经验”的稳婆,获取旧技术的方式极为简单,他将这种旧式收生界定为“不合法”[4]24。从其观察问题的标准来看,实乃不合“西法”。由此可知,能否合于西法,已成为虞氏乃至时人思考分娩卫生如何建设的重要标准。进一步来说,合于旧法的稳婆群体,已没有维持这种职业的资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产婆训练班其本质实为构建一种新的职业资格的准入机制。
设置职业资格的新标准,早期明显受到日本及欧美各国产婆改良思想的影响。1907年,国人已注意到日本检定产婆职业资格的情况,“产婆技术之优劣,非得医师之确定者,断不可十分信任”,同时产婆“非经医师试验,予以免许文凭者,不准应用学识”[10]8。后来国人又认识到,不独日本如此,“考诸各国法律”皆然。产婆若要“营其业”,须经“试验及格”,登录名簿,方有营业资格。而在此之前,还须取得试验(即考试)资格。只有取得正规化的医学培训和学习经历,才能取得这种资格,“非入学校及养成所,修习产婆学术一年以上,得有修业证书或毕业文凭者,不得受产婆试验”[3]7。
因此,通过学习与考试,赋予旧式产婆法定的职业资格,这也成为创设产婆训练班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后来吴葆光仿照此例,拟定一份“中国卫生改良表”,主张设立“产婆养成所”,“凡欲谋生此业者,若非由所毕业,领有文凭,概不令其行业”[11]2。陈志潜也认定普通接生婆若没有相当的训练,就没有维持这种职业的资格,并主张以“训练所”的形式,提供给产婆操使职业所须具备的“训练的要求”[12]113-114。1928年8月3日,内政部公布的《管理接生婆规则》中明确规定:“地方官署应设临时助产讲习所,令核准注册之接生婆,分班入所练习”,在“练习期满成绩优良者”,由地方官署核给证明书;同时接生婆还须向地方官署“请领接生婆执照,未领执照前,不得开始营业”[13]95-96。
以新代旧的技术置换,最后落实到职业资格上,而以学习与考试为主要内容的职业资格化,又为近代以来分娩医疗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多一重的“物质”基础,从而也成为分娩医疗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医疗化还是资格化,其思考路径都是对传统分娩卫生社会行为的一种纠正。而具有法定意味的资格新标准的设定,从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理解为,是国家力量对分娩卫生进行控制的一种表现。
二 官民互动的制度形塑
与分娩“医疗化”相类,学界经常言及分娩“国家化”的概念,其涵义本身与界限也具有开放性与不确定性,但多将其表述为一种特征性的总结。其实,将之理解为蒋竹山所谓的国家角色的扮演,似更为合适。就以产婆训练班来讲,国家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对此问题的考察不能就事论事。因为早在国家力量统一推行之前,已有民间各种训练模式竞起,即使在所谓“国家化”主导之时,其情形也是颇为复杂的。
总体来看,1928年之前关于产婆训练的各种理念与模式,有两大特点。
其一,强调研究性。1907年,有人主张设立“产婆学堂”之前,“先设稳婆研究会,叫现在所有挂牌子的收生姥姥们,都入会研究生产的道理”,想要中国的“收生姥姥”都成为“有学问的人”[14]16。 虞诚之在1919年谋求补救改良产婆时,主张“各省各县须多设产科的研究所”,以使产婆具有“医的知识”[4]27。后来,北平市卫生局组织“产科筹备委员会,设立接生婆讲习所”时,另设“接生婆研究会”,专门对“受训练之接生婆”如何“增加其常识”加以研究[15]635。以上这些运作虽方式各异,但崇“学”输“学”的理念如一,而产婆的学术化也成为官方举办产婆训练班孜孜以求的目标。
其二,提倡速成性。20世纪初,杭州城内有“金绅高绅慨助经费,与英人梅滕更医士”商议,“组织一速成产科医学堂”,专收年长识字妇女入堂学习,“年半卒业”[16]6。 1916年,有人主张“养成产婆”,在探讨“养成之法”时,针对已经“悬牌之各收生婆”,提议“择各地善堂公所乡约之属,设数区产婆讲习所”,勒令其“每日以一定时间,入所肄业”,“仿速成科之例,以半载为期,试验合格,准其营业”[3]9。这种速成之例,对后来官方产婆训练班的制度创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早期形塑阶段,以民间力量为主。原因就在于,不仅“政府困于党争,酣战不遑,何暇顾及于此”,就是“所谓曾受新文化薰染之新女子”,惟以“解放改造”、“平等自由”为务,于“妇女健康,生育保障,则尚未尝一聆其高尚之建议”,因此,“欲行改革之方,惟在知识阶级”[17]110-111。 具体到产婆训练而言,以医界和教育界的职责为大。
而北伐后全国名义上统一,为分娩卫生国家化的转向提供了可能。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制定《训政时期卫生行政方针》,明确宣示各地“分班招集接生婆”,“授以简要接生学识及消毒大意”的必要性,并下发《接生婆须知》,制定《管理接生婆规则》,目的在于“取缔营业杜绝流弊之外,并授以必要之接生智识,以期适用”;同时编集《接生方法》,对清洁、消毒、接生、脐带扎切、假死初生儿苏生以及看护产褥妇等诸多科学方法,广为刊布[18]71-77,95,97-101。 至此,民间早期的制度形塑开始转向国家层面的制度构建,而这些法规文件的出台,也表明“国家化”程序的某种完成。
而官方主导下的产婆训练班中,国家也要借重民间资源来完成其角色扮演。《管理接生婆规则》要求地方官署设立“临时助产讲习所”,而此项讲习所“得委托医院或医学校、助产学校办理”[13]96。“委托”二字值得注意,表明不必非由政府机关直接办理,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专业性的社会力量来进行。
这其中,委托助产学校来办理,成为各地创班授学的一种主要方式。如当时杭州市政府就“会同省立助产学校迅即筹备成立”,并由学校先行调查本市散处各地的接生婆,并参与拟定了“杭州市训练接生婆办法八条”,编排班级,安排训练[19]26。30年代,“中央委员会”下级广西分会组织筹设“省立产科学校”,其中一个用途即为培养“各县村镇旧式稳婆训练指导所教员”[20]3。
其次,委托医院办理,成为另一种主要运作模式。如汉口市“接生婆训练班办法”中,明确规定将“接生婆训练班附设于市立医院,由市立医院院长主持办理”,训练班教职员“除有关法令一门由市政府派员担任外,余由市立医院院长就该院医师职员中遴委兼充”[21]33;福建省政府决定自1939年6月份起“分期由各县卫生院训练乡村接生婆”[22]387;而江苏省则计划“派新式助产士”往61县办理“平民产院”,“以救济一般胎产兼训练旧有稳婆”[23]70,但由于人才不足难以实施,故于“过渡时期”,先“由省立医院兼办稳婆训练班,藉求妇婴生命保障之普及化”[24]43。
两种模式中,政府作为“委托”方,并非直接创班授学,其职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间接的领导性。作为“受委托”方,学校和医院虽为国家所立,但毕竟属于社会性的资源,以其专业的学识与人才而被国家所推重,纳入训练体系,成为施学的直接主体。在这其中,国家扮演着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如整合专业人才资源以发展助产学校,整合专业设施资源以完善各类医院,整合各类民间理念以齐一所需传授的学科知识。当然,在整个计划中,国家扮演的角色并非一直如此,在某些方面适时凸显政府机构的相应功能,颇能弥合社会资源不能做到之憾。
如各级政府中的公安机关,在训练班的制度设计中,参与度很深。1930年,北平特别市规定,欲在“本市执行接生婆业务者”,应赴“公安局注册,领取执照,方得开业”[25]3。后来的福建省虽将执照发放权归于民政厅,但将招生资格审核权派发给各级公安机关,规定:“在省会经营接生婆业务,无论以前领有执照与否,应由省会公安局督饬各分局,限二十日内,调查登记,开列名单”,呈送民政厅[26]1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产婆群体特殊,不仅居住分散,而且大多思想顽固,拒斥训练。因此,不管是取缔还是训练,都带有强制成分,这就需要公安机关威权职能的介入。
1934年,江苏省立医院在“即刻可实行之改进计划”中,就希望:“由行政力量严格取缔,即日由公安局切实调查外来及旧住全数收生婆,勒令注册,立刻送由省立医院稳婆训练班训练,以免难产枉死。”[27]54更有甚者,直接将训练班附设于公安局。如甘肃省卫生实验处就与“公安局会同办理”,定名为“甘肃省会公安局附设接生婆训练班”,在筹备期间,由“省会公安局委任该处助产士陈怡迪为该班主任,以便负责进行”[28]6-7。这样一来,公安局也就相应地成为训练班的主管方之一,代表国家力量行使招集、监督与取缔的强制性职权,国家角色在此也就扮演着保障训练班正常运转之责。
就其所属来说,产婆训练为妇婴卫生的组成部分,约从3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全面推行公共卫生,以各地卫生实验区的成立与卫生事务所的设置为代表,卫生机关在训练班中的职能与地位日益凸显。继之推行的县政改革运动,对妇婴卫生更予以关注,至此,国家角色的扮演似有逐渐增强之势。与此同时,在多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民间的医学与教育资源利用这一契机,对农村产婆改造乃至妇婴卫生的推进表现得尤为活跃,这又说明某种程度上官民互动的态势依旧存在。
三 学术化的制度反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推行,国人对过渡期间产婆训练班的举措,呈现出某种反思的倾向。总体来看,时人对办班培训成效的评说,褒贬不一。有认为其效果不错,值得进一步推广。如上海产婆补习所的工作,其成效初显,通过训练,产婆渐成为“新法产科学术的宣传使者”[29]28。同时,也有人认为效果不甚理想。如黄胜白通过自己的观察,尤其对乡村训练稳婆之举,给出了“并非良好办法”、“成效至微”、“适得其反”等悲观评论[30]7-8。1934年,全国医师联合会也认为过去五年办理成效不甚理想,“接生稳婆,依然到处横行,有加无已”[31]27。
黄胜白将其咎更多归于顽固的产婆群体,这种消极观感的形成,明显受到新旧对立二分思维定式的影响,与近代早期新派人士对旧式产婆“污名化”之举有或隐或显的关联。全国医师联合会则将责任归于“地方卫生主管机关”奉令不力,揭示了国家实际扮演的角色在训练主导力量由民到官的转移中,与社会期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批评之声在举办后期颇为盛行,其实也体现出国人由效果看模式而产生的日渐增加的担忧心态。若以今日眼光回溯之,这种在事实和观念上俱有的不佳观感的形成,除了有产婆与政府之责外,其制度本身也值得我们去反思。训练班以灌输医学知识为宗旨,但又以“速成”为务,这就导致这种学术化的运作模式呈现“损之又损”的特点。
首先,这种特点体现在训练班的课时上。就训练时长来讲,异时异地的各种训练班都不甚统一。但大体上,早期民间培训机构学习期限较长。如上海产婆补习所不仅规定“以一年为度,以每六个月毕业一次”的学习期限,同时还规定“至少积至二百小时以上者始予参与毕业试验”的听课时数[29]31。而全国层面的各地训练班为追求“速成”性,专以压缩为务。《管理接生婆规则》中,将“接生婆练习期”统一缩减为“两个月”[13]96,表明其“速成”性的普及已占据上风。福建省会接生婆训练班,“每班以一个月为度”,每日授课时间,“自下午二时起至五时止”,其累计听课时数已不到一百小时[26]11。而河北清河产婆训练班,将“训练期暂定为两周,一日二时半”,“期于一年内,将划定区域内之产婆完全受训”[32]83。
其次,这种特点又体现在灌输产医科知识时的简约化上。如《管理接生婆规则》要求地方临时助产讲习所,对分班入所练习的接生婆,教以“接生上必要之知识”[13]96,“必要”二字,若以“简化”诠释,最能说明问题。1934年修正的“上海市卫生局训练产婆简章”,其课程安排中明确有“训练现有旧式产婆使于最短时间能了解简明产科学术及方法”的宗旨[33]166。 “最短时间”只能了解“简明”学术,“必要”之外的相关知识群只能囿于时长限制而摒弃。若要兼顾“必要”内外的知识,则只能如河北省产婆训练班的课程要求,对于相关课程以及“各种异常”只能“摘要教授”[34]6。摘要讲授虽能涵盖学科之全,但每门讲授的学科仍不脱简约化的处理。
学术化运作模式重在“学术”。从训练班的课程来看,“学”、“术”的指示层面似乎不同。姚燦绮就稳婆群体的落后性曾经批评道:“无所谓学识,无所谓技术,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生理和病理,什么叫做消毒和灭菌。”[35]33在姚氏看来,“学识”和“技术”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若说“生理和病理”属于学识范畴的话,那么“消毒和灭菌”更侧重于技术一类。高振之后来也认为,有经验的收生婆由于“熟能生巧的原则”,对收生是“相当有办法的”,同时也知道“脏污是要不得的”,并以新剪刀或火烧之后的剪刀“剪脐带”,“但不知剪刀要烧的原理,于实际也无大补”[36]14。此处实揭示出训练产婆时,如何构建“学(理)”和“术(法)”的平衡关系,至为重要。
但在实际操作中,此种并重原则有时实难兼顾。1928年,《管理接生婆规则》第五条在建议“接生上之必要知识”时,着重于教习清洁消毒法、接生法、脐带扎切法、假死初生儿苏生法、产褥妇看护法等科目[13]96,可见此一操作指南中规定的“必要知识”完全侧重于“术(法)”的传授。各地以此为标准的产婆训练班多数继承了这种倾向。1935年,江苏省立余塘民众教育馆举办的训练班,直接以“养成新法接生之技能为宗旨”,在其课程纲要中,除“人体简明解剖学”属于简明之学理范畴外,其他诸法的讲授皆为培养“技能”而设[37]85。 后来福建省会接生婆训练班,虽以增进接生上“必要之知识及助产能力”为务,但其课程与《管理接生婆规则》中的建议讲授内容基本无异,仍以术法为主[26]11。方法本简易可行,只要切实遵守即可,但之所以会出现有些稳婆囿于成见拒不执行的情况,其原因之一是作为方法层面的“术”本离不开理论层面的“学”的濡养,训练班若只是以授“法”为务,方法本身极有可能因孤悬于学理之外而失去其有效性。
同一时期,另有一些训练班的课程安排有变化,这实隐含着平衡“学”“术”关系的某种想法和努力。民间力量参与度颇高的河北清河产婆训练班,除继续讲授诸“法”的内容外,还增加了“产科生理解剖学大意”与“细菌学大意”等纯“学”范畴的科目;另外,在两周的训练期中,“一日二时半,以一时讲解解剖学,一时半表证手术”[32]82-83,就是平衡两者关系的一种表现。后来,广西各县接生婆训练班的办法大纲中,除“妇产科大意”科目授“法”外,特意开设“生理学大意”、“药物学”和“卫生学大意”科目[38]2,以满足学理知识传授的需要。
但现在看来,这种努力的实际效果颇可质疑。在传统改造中,以系统、逻辑性为特点的西方近代学理知识的普及,能为社会提供一种习以为常的新式观念,这种观念若能深入稳婆大脑,替代其固有思想,确能保障方法的施行。1934年,上海市卫生局在修正训练产婆简章时,就认识到使旧式产婆“了解简明产科学术及方法,增进其助产常识及能力”的重要,但由于稳婆自身基本条件的缺失,其对“学术”的培养,在课程中往往只能简化为“妊娠产妇、胎儿及新生儿生理与病理常识”的灌输[33]166,就是一种无奈之举。以常识灌输来带动观念变革,虽不失为一条实用化的路径,但“损之又损”的训练方式,又决定了即使将学理知识简化为常识传授,在训练学时上也不一定能得到充足的保证,这样一来,兼顾“学”与“术”的训练实难有效的平衡。
综上所述,产婆训练班开启了近代产婆职业重塑的历程,是落实产婆改良思想的一种制度性举措。以新代旧的技术置换,反映了广大基层接产人员分娩卫生医疗化的转向,与职业资格化一起,重新塑造旧式稳婆以西方为典范的职业形象和职业手法。在官民互动的制度形塑中,国家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其利用外部资源以达到改造内部的目的,而代表近代的新式资源又依托国家力量以达到置换传统的目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就举措效果来看,被重塑职业的对象似乎不愿完全“就范”,这虽与诸多外部因素有关,但以学术化为依归的制度本身在设计上自发生成的制度性障碍,似应更值得我们反思。
注释:
①蒋竹山《从产婆到男性助产士:评介三本近代欧洲助产士与妇科医学的专著》,〔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9年第7期,
第238页。关于学界对产婆群体的关注,其代表性的成果有:游鉴明《日据时期台湾的产婆》,〔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3年第1期;姚毅《产婆的“制度化”与近代中国的生育管理——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韩〕《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0辑;赵婧《西医产科学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产婆训练》,《史林》2013年第4期;朱梅光《取缔抑或养成:近代国人关于旧式产婆出路之争》,《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产婆改造》,《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6期等。
[1]日昭.谈新和旧的接生问题[J].科学与生活,1946,1(1-4).
[2]史宝安.河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训词[J].妇女杂志,1916,2(1).
[3]陈姚樨屏.中国今日宜养成产婆论[J].妇女杂志,1916,2(4).
[4]虞诚之.产婆能没有医的知识吗?[J].通俗医事月刊,1919,(2).
[5]请广行西法收生以解产厄说[J].万国公报,1898,(108).
[6]汪行恕.劝中国女子学医书[J].医药学报,1908,(11).
[7]叶蔚文.海丰产科学校演说词[J].光华卫生报,1919,(2).
[8]无锡县政府,无锡市政筹备处.第一回无锡年鉴[M].1930.
[9]湖北省训练稳婆办法[J].湖北省政府公报,1936,(224).
[10]沙世杰.育儿法[J].医药学报,1907,(1).
[11]吴葆光.论中国卫生之近况及促进改良方法[J].新青年,1917,3(5).
[12]陈志潜.接生婆[G]//丙寅医学社.医学周刊集:第一卷.北京:世界日报社,1928.
[13]管理接生婆须知[J].中华医学杂志,1928,14(5).
[14]稳婆[J].敝帚千金,1907,(23).
[15]王康久,刘国柱.远古—1948北京卫生大事记:第一卷[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16]誌速成产科医学堂[J].广益丛报,1906,(116).
[17]李瑞麟.产前诊查及其关系之重要[G]//丙寅医学社.医学周刊集:第一卷.北京:世界日报社,1928.
[18]训政时期卫生行政方针(附各种规则)[J].中华医学杂志,1928,14(5).
[19]布告本市各接生婆应遵照规定时间分班训练如有未领执照者并应即日来府具领毋得观望由[J].市政月刊,1930,3(3).
[20]龙秀章.目下旧式稳婆势力尚盛宜如何发展科学产科议[J].广西卫生旬刊,1933,1(23).
[21]汉口市接生婆训练班办法[J].湖北省政府公报,1935,(79).
[22]福建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卫生志[M].福州:福建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1989.
[23]江苏六十一县县立平民产院之计划[J].医药学,1932,9(10).
[24]汪黄瑛.江苏妇婴卫生实施概况[J].公共卫生月刊,1935,1(4).
[25]北平特别市接生婆注册领照规则[J].北平特别市市政公报,1930,(48).
[26]福建省会训练及管理接生婆办法[J].福建省政府公报,1936,(582).
[27]汪元臣.江苏省立医院四年来之工作[J].医药学,1934,11(2).
[28]甘肃省卫生实验处工作概况(自23年9月至24年4月)[J].卫生半月刊,1935,2(12).
[29]俞松筠.关于上海产婆补习所之事实报告[J].医药评论,1929,(5).
[30]黄胜白.平民产院之使命[J].医药学,1936,13(5).
[31]部咨饬属严格执行助产士条例并取缔接生婆暨设训练班[J].福建省政府公报,1934,(372).
[32]河北省乡村卫生工作鸟瞰[J].公共卫生月刊,1935,1(1).
[33]修正上海市卫生局训练产婆简章[J].上海市政府公报,1934,(143).
[34]民政厅令各县局抄发开办接生婆训练办法由(附办法)[J].河北省政府公报,1929,(496).
[35]姚燦绮.训练旧式产婆的困难及改善[J].医药学,1937,14(1).
[36]高振之.改良接生婆[J].现代农民,1946,9(7).
[37]一月来江苏省各种民众教育事业之进展[J].民众教育通讯,1935,5(9).
[38]广西省各县接生婆训练班及村街妇婴卫生讲习班办法大纲[J].广西省政府公报,1938,(178).
Remolding Career:On Traditional Midwife’s Training Schoo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U Mei-gu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Anhui 235000,China)
Traditional midwife’s training schoo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opened the process of mass remolding career on modern midwives.It was an institutional move which carried out improvement ideas.Remolding career which had been instigated by displacing old technology with the new one reflected medicalizational turn on delivering method,and ran up a process of designing institution about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Thus traditional midwife’s professional image and skill were shaped as following those of the West.The earlier training models being the precursor,together with the subsequent wide implementation sponsored by government,constructed the interactive trend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modeling institution.The government played a role in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safeguarding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while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mong the folk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Judging from the effects of the institution,the process of remolding career was not encouraging.The excessive simplicity in training mode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ly in balancing practice and theory were spontaneous 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 to hinder the overall midwife’s training act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midwife;remolding Career;midwife’s training schools;technology displacement;modeling institution;reflections on institution
G719.29
A
1000-5315(2015)03-0157-07
[责任编辑:凌兴珍]
2014-10-15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2014年一般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分娩卫生救助机制研究”(2014SK11)之成果。
朱梅光(1979—),男,安徽桐城人,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