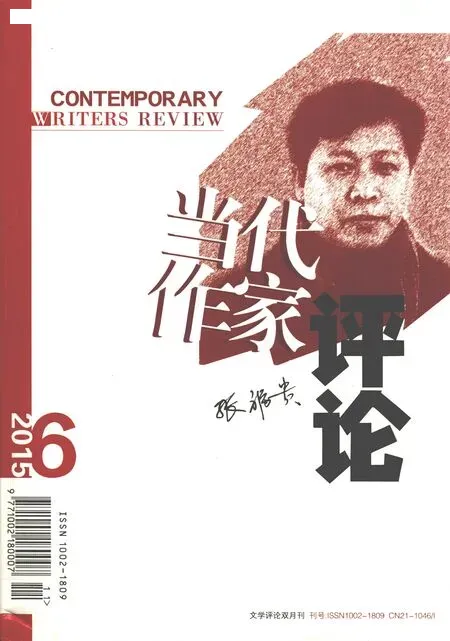网络空间的本土文学传统
黄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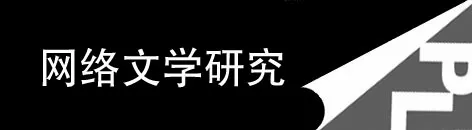
网络空间的本土文学传统
黄发有
网络文学作为新媒体技术与文学创作联姻的产物,研究者向来重视网络技术对文学写作方式、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影响。由于网络技术起源于欧美,从BBS到博客,从Facebook到微博,中国网络文化的繁荣在借鉴外来技术的前提下,其价值导向和时尚趣味也不能不受到外来文化的渗透。在文学写作方面,超文本写作的崛起打破了传统文本的封闭结构,其开放性、自主性、互文性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性。除此之外,外来的网络游戏尤其是美国暴雪公司开发的《魔兽世界》在中国的风行,使得越来越多以改编网络游戏为目标的玄幻小说写作,在情节模式、叙述结构、怪物系统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基于此,研究网络文学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学术取向,而网络文学与本土文学传统的关系往往被忽略。
一
新世纪以来,在产业化与娱乐化的潮流中,随着类型小说成为网络文学创作的主流。本土文学传统对网络文学的影响日益彰显。在某种意义上,玄幻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官场小说、历史小说等类型小说,都能从晚清至民国的文学史上找到对应的文体类型。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传统在网络空间中被重新激活,一些题材和故事也被重新讲述。
就单篇作品而言,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的影响不容忽视,众多网络写手竞相模仿。其“神魔大战”的叙事模式被玄幻小说和仙侠小说广泛采用,因此,还珠楼主常常被一些写手视为玄幻、仙侠和修真小说的鼻祖,像《诛仙》、《佛本是道》、《凡人修仙传》都闪动着《蜀山剑侠传》的影子。萧鼎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山海经》和《蜀山剑侠传》给《诛仙》带来了关键的影响:“《山海经》等古典文籍,我看过了不少,也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影响很深,比如《诛仙》中有许多细节,便是通过《山海经》的考证引申出来的。还珠楼主的《蜀山》是我从小比较喜欢的一部小说,对我写作《诛仙》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小时候看过《蜀山剑侠传》之后,虽然惊叹于其想象力的瑰丽雄奇,但却遗憾于其中人物情感形象的单薄。我始终认为,一个感情单薄的人物构成的小说,终究是不完美的,可以说我写《诛仙》是为了偿还这个宿愿。”创作于民国时期的《蜀山剑侠传》现在被反复改编成网络在线游戏,显示出其独特的生命力,《仙剑奇侠传》、《蜀山剑侠传》、《蜀山》、《新蜀门》、《梦幻蜀山》等让人目不暇接。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的《蜀山剑侠传》之所以能够在网络空间产生如此巨大的回响,和其作品的特点密切相关,其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思想和“修仙进化论”成为不少玄幻小说和修真小说的核心理念。正如叶洪生所言:“《蜀山》所描写的穷荒极地、山精海怪、灵禽异兽、瑶草琪花以及五金之精、上古神话,固多脱胎自《山海经》;而演叙降妖伏魔、玄功幻变亦近绍于《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引述飞剑跳丸、天府秘笈、修仙过程、考验道心则取法于《抱朴子》、《神仙传》、《平妖传》、《女仙外史》及《绿野仙踪》;至《野叟曝言》所造奇景与蛮荒异俗,毋论矣。同时还珠楼主更兼采清末民初以来的武侠先驱作品如《七剑十三侠》、《江湖奇侠传》、《江湖怪异传》及《奇侠精忠传》等志怪述异之素材,再参证《武术汇宗》所论道术、神通等奇谈,取精用宏,共冶于一炉。虽然还珠楼主之创作灵感得益于以上诸书,但其自出机抒、别开生面之想象空间则更为辽阔;在在皆能穷极幽玄,超妙入微;纳须弥于芥子,化腐朽为神奇!总之,其驰骋幻想,务求推陈出新,不落俗套,惊神骇鬼,自圆其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网络类型小说对《蜀山剑侠传》的借鉴与模仿显得生硬而浅薄,不少写手与其说从《蜀山剑侠传》中获得灵感,毋宁说是移植了蜀山题材的网络游戏的某些叙事元素。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引用古典诗词或以典雅的文字营造诗情画意,已经成为网络文学尤其是言情小说渲染气氛的重要手段。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就大量引用古典诗词和曲词,从《诗经》到唐宋诗词,作者信手拈来,或呈现甄嬛内心情绪的微妙变化,或咏物写景,或机巧应对,既增添了情趣,又使文字风格自成一体。在言语特征上,《后宫·甄嬛传》也有模仿《红楼梦》的痕迹,像普通话中间杂北京官话方言词、文言词汇的混用、儿化词的频繁出现。《红楼梦》的人物对话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媒介,鲁迅认为小说对话的绝妙之处在于,“并不描写人物的摸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显然,《后宫·甄嬛传》离鲁迅所说的境界还有很大的差距,作者在操练一些词语时过分随意,甚至不无鹦鹉学舌的意味。久久的《富贵繁花录》被网友视为女尊文的代表,表现出一种大女子主义的倾向,有网友戏称为“男版金陵十二钗”,行文半文半白,遣词造句和描写叙述均有《红楼梦》的鲜明烙印。湖月沉香的《折草记》作为《富贵繁花录》的仿作,更是无法摆脱《红楼梦》带来的“影响的焦虑”。匪我思存《寂寞空庭春欲晚》的小说标题取自唐代刘方平的《春怨》:“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这部小说在参考《清史稿》等史料的基础上,讲述了康熙、纳兰容若与虚构的女子琳琅之间三角恋情,作品对清代皇宫的建筑规制、宫廷礼仪和官员制度等内容津津乐道,并大量引用纳兰容若的词作,这居然还激发了不少网友对纳兰性德词集的兴趣。
就故事的选材而言,不少网络类型小说脱胎于古典文本或民间传说。像林寒烟卿的《春色岂知心》和《小狐狸遇龙记》,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聊斋志异》的花妖和狐仙故事;情随世迁的《白娘子养成记》和浪在心空的《穿入白蛇传》都是对经典民间故事白蛇传的另类重写;清代陈淏子的园艺书籍《花镜》触发了沧月创作《花镜》的灵感,编织了以花与美女为核心的悬疑情节和世情变幻。至于穿越小说的文体发展与变迁,网友一般会近溯到李碧华的《秦俑》、席绢的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和黄易的《寻秦记》。其实,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已经陆续构建了主人公进入别样时代或异度空间的叙事模式和情节框架。至于网络历史小说那就更无法割裂与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神联系,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空间的历史题材写作大多热衷于架空和戏仿,虚构历史时空和历史人物,像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和赫连勃勃大王的“中国历史大散文”系列,尽管也掺杂了虚构成分和娱乐元素,但历史的基本轮廓还算是清晰的。至于架空历史小说《新宋》、《浮生萦云》、《回到明朝当王爷》、《窃明》等等,这类作品是在历史的幌子下解构历史。
每个民族的神话往往保留着从蒙昧向文明过渡的原始记忆,其中天马行空的幻想给许多写作者带来灵感。网络幻想小说的作者也常常从中古古代神话中寻找素材。树下野狐的《搜神记》有较多追捧者,作品讲述上古洪荒时期的神魔故事,以奇幻的想象改写中国上古神话,作者对战火纷飞中的儿女情长的演绎,又明显受到商业化趣味的熏染。在江南、潘海天、唐缺等的“九州”系列中,“九州”幻境、夸父和羽人等魔幻神奇种族,都是直接来自《山海经》。网络文学中不少带有本土神话色彩的作品,像叶沧浪、藤萍、可蕊等写手的一些文字都或多或少受到《山海经》的启发。这些被一些媒体记者和学术圈人士贴上“新神话”或“新神话主义”标签的作品,基本上都以传统的神话文本作为母本,同时融入西方幻想小说如《魔戒》《纳尼亚传奇》《哈利波特》的审美元素,进行一种复合的仿写,它从不掩饰对商业利益的追逐,并以跨媒体传播和版权转化(图书、影视、在线游戏、动漫)作为核心的传播策略和盈利机制。
二
和网络文学相比,网络游戏的受众面更大,作为一种颇具规模的产业也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网络时代,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纸面读者日渐寂寥。但是,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网络游戏却长盛不衰,玩家络绎不绝。根据《西游记》《水浒传》改编的网络在线游戏《欢乐水浒传》《梦幻水浒传》《大话西游》《梦幻西游》《快乐西游》接踵而至,令人眼花缭乱。堪称奇观的是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网络游戏已经高达数百种,游戏厂商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竞争异常激烈。,日本光荣株式会社在一九八五年开发了第一款三国题材的商业游戏《三国志》,其后续产品《三国无双》也已经成为游戏产业界的范本,通过快速的升级换代来吸引源源不断的新玩家。韩国开发的《三国之天》《Action三国志》《三园志无限对战》《三国演义在线》等也在亚太地区风靡一时。而国产游戏《三国策》《三国群英传》《盛世三国》《热血三国》《卧龙吟》《天将雄师》等等,也希望借助自身的特色来抢占市场份额。魏、蜀、吴三国之间在军事、政治上长期争战不休,它们在战力、权谋、财力等方面的多重较量,既契合网络游戏崇尚实力、追求智慧的特点,又为开发者提供了开阔的想象空间。“三国”题材的在线游戏以《三国演义》的情节和故事为基础,模拟三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并将作品中的历史事件改编成游戏任务,让玩家在虚拟情境中去游历和体验。从桌面游戏到网络游戏的《三国杀》,让玩家以“主公”、“忠臣”、“反贼”、“内奸”等身份,扮演三国历史中那些武将,斗智斗勇。玩家中只有主公亮明身份,主公要杀死所有反贼和内奸;忠臣的任务是保护主公,反贼以杀死主公为目标,而内奸要消灭反贼再害死忠臣后,最后单挑主公,其胜利难度最大。尽管每一个文臣和武将的技能都参照《三国演义》而设定,譬如诸葛亮的技能为观星和空城,但这些历史符号都只是游戏的背景,玩家自身的选择才是决定游戏进程的关键,历史的进程往往被游戏进程的不确定性所颠覆。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游戏为了强化竞争性和娱乐性,玩家所拥有的城池、财富、武将、武器、坐骑、特性道具等都是争夺的对象。而且,在价值观念上,游戏遵循的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逻辑,强大的玩家可以雄霸天下,失败的玩家只能成为别人的俘虏、奴隶。玩家提升自己等级和战力的途径,无非是练级和花钱购买装备,这既要求玩家快速提升自己的游戏技巧,也要付出时间和金钱的成本。更为关键的是,在线游戏往往以玩家作为中心,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玩家可以自由控制整个游戏系统,体验和支配游戏中的各种角色。在网络游戏中,历史真的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一种消费和娱乐的对象。譬如《盛世三国2》中有一个“欢乐派对”环节,玩家随机变身成三国中的名将和美女,游戏系统指定武将和美女配对:吕布和貂蝉、诸葛亮和黄月英、周瑜和大乔、曹操和蔡文姬等等。台湾厂商开发的游戏《吞食天地》算得上是穿越版的三国题材游戏,玩家扮演的是一个当代的中学生,被仙人选中为结束三国之乱的英雄培养对象,因此进入虚拟的三国时空,误打误撞进入游侠、黄巾、曹魏、蜀汉、东吴等五大阵营中的一个,开始杀伐和争战,而曹操、刘备、孙权等都可以成为玩家手下的战将。《三国策》总体来说比较忠实于历史,但也曾宣称:“中国的历史将因每个玩家的加入而改变。”
三国题材的网络小说绝大多数都是粗制滥造,而且“穿越文”、“重生文”盛行。穿越小说的叙述模式是主人公从所处时代穿越到另一个时代,其作者、主人公大都为女性,但三国题材的穿越小说是一个例外,其作者、主人公几乎都为男性。在现实时空失意的少年穿越到三国的乱世,金戈铁马,血洒疆场,在虚拟时空中实现自己的英雄梦。《三国志之辅佐刘备》中的陆羽穿越到三国后,针对蜀国制度的缺陷,借鉴后世的一些政治制度,推行改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风流三国》中的张浪穿越到三国后,施展雄才大略,不仅广收谋士和战将,而且魅力超群,使得蔡琰、貂蝉、甄宓、大乔、小乔等美女都投怀送抱。重生小说的叙事模式是现代主人公意外死亡后回到过去,在另一个世界重新获得生命。《桓侯再生》中的于震触电死亡后附体到张飞身上,利用自己的现代智慧提升了张飞的境界,辅佐刘备统一了天下,立下不朽功勋。穿越文和重生文都是一种白日梦,其现实人生从头来过的愿望,既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慰藉。总体而言,三国题材的网络小说已经陷入一种怪圈,写手在开篇时还试图别出心裁,就像独自探险的旅人,走出不远就迷路了,只好原路返回,跟在人流后面,加入群体的狂欢。像《兵临天下》《三国董卓大传》《混在三国当军阀》《无奈三国》《三国厚黑传》《商业三国》《曹冲》《乱战三国》《三国突起》《三国战神吕布》《黄粱三国》《穿越三国做皇帝》《三国重生之公子刘琦》《重生之我是曹操》《重生之傲视三国》等等,叙述框架与文字风格都大同小异。
“古典”作为一个与现实疏离的世界,它可以摆脱社会规范和现实法则的束缚,成为现代人的一块精神飞地。现代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都可以从虚拟的“古典情境”中通过想象建构一个圆满的梦境,打造一片幻想的乐土,让空虚的内心获得一种仪式性的补偿。相对而言,在本土文学与文化传统中,表现民族忧患、治国安民、现实人生的文学传统往往被忽略,网络作者关注的往往是群雄逐鹿、权力搏杀、争风吃醋、妖魔鬼怪、奇门遁甲等可以带来心理刺激和感官享受的内容。面对这些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大都没有兴趣研究它真实的面貌,在乎的只是它可以带来暂时的愉悦,可以逃避现实的干扰,让人暂时遗忘包围自己的外部世界。在古典传统逐渐式微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古典知之甚少,这也为写作者的虚构和捏造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对新鲜的东西永无休止的追逐,使得流行元素迅速被淘汰,而古典元素的复出往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陌生化效果,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返回古代的倾向往往包含着对现实的一种不满和批判,就像老子对“小国寡民”世界的神往。现实大众在神游飘渺的古典空间时,也借此排遣在现实生存中积郁的不满和愤怒,通过虚拟的时空转换来获得瞬间的内心平衡。另一方面,退回到过去的愿望也是人性中的一种潜在倾向,未来充满变数和不可知性,而过去则是一种安全的庇护所,就像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西方文学中“失乐园”的母题,既是对基督教文化的审美阐释,也是不变人性的内在诉求。在回到人类童年的愿望中,也包含着现代人对飞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中物化生存状态的一种忧虑和反拨。而且,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历史景观,这也为选择“古典风”的写手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因此,网络空间的古典传统往往呈现为碎片化形式,古典与现代、历史与想象、梦境与现实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时空颠倒,真假莫辨。
综上所述,网络文化在借鉴本土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第一,网络写作的“复古”往往停留在表浅层次,生吞活剥,满足于移植古典的碎片,类似于戴着古典的面具的一种狂欢仪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鱼目混珠的“伪古典”恰恰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放逐和遗忘。譬如网络上风行一时的《见与不见》,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误认为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传世情诗”,以讹传讹,后来被证实是扎西拉姆·多多的仿作。以戏谑的形式改写古典文本的做法极为流行,比如网络小说《极品家丁》中的讨债人说:“风飘飘兮易水寒,借我的银子兮你还不还?”这种插科打诨本也无伤大雅,但是当低俗被视为高明时,这种碎片拼贴、类型杂糅的文风就不仅无法赓续文化传统,而且会歪曲、拆解传统。正如莫道夫所言:“把各式各样历史连根拔起,斩断所有牵绊拉到我们眼前,通过拼贴,随心所欲地把人们熟悉的那些历史符码置于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内,进行重新洗牌。”
第二,在商业诉求和娱乐风尚的推动下,以后现代主义倾向和消费主义趣味对传统历史文化和经典文本进行戏仿、篡改和恶搞,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尚。恰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言,后现代文化追新逐异,却流于平面,缺乏内涵,“在后现代主义中,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从林长治的《沙僧日记》和《Q版语文》,到十年砍柴的《闲看水浒》、成君忆的《水煮三国》,被商业动机激发出来的娱乐性的机智和标新立异的逆反,成了“违背原著”的原动力。“杜甫很忙”,“背串的古诗词”,以娱乐化姿态恶搞古典诗词,对古典文本进行任意的拆分重组,在网络空间中屡见不鲜。王维因“每逢佳节倍思亲”中有一个“亲”字,被网友们冠上“史上第一个淘宝店主”的绰号。这种混搭风以肤浅的创意哗众取宠,体现出的是对古典文学传统的不尊重。
第三,网络文学中的复古趋向,经常会演变为扎堆、跟风、起哄的群体行为,缺乏个性化的艺术提炼。在宫斗剧走红时期,宫斗题材的架空小说、穿越小说泛滥成灾,情节模式、人物关系和对话口吻都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陷入了低水平重复的怪圈。从玄幻小说、穿越小说、盗墓小说到职场小说、都市小说、言情小说,网络空间一旦有一种类型文学走红,马上有大批模仿者蜂拥而上,而且很快就形成一种固定套路,如同用模具制造出来的零件一样整齐。网络文学中呈现的传统元素,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复制,缺乏独立性和原创性,甚至是一种变相的抄袭。在网络成名的安意如,古诗词赏析是其成名利器,但是由于学养浅隘,经常会从互联网中获取知识和养料,没有经过充分的消化吸收和融会贯通,难免陷入穿凿附会和抄袭模仿的陷阱。对“卖点”的过分强调,使得文化传承的本意被扭曲。网络文学在对待本土文学传统时的偏食倾向。网络写手大多喜欢从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中的通俗小说中获得养料,对于相对小众的精英文学或小说以外的文体则较为隔膜,而且,不少写手即使在面对其模仿的文本时,也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缺乏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和融会贯通。
三
古典文化在“五四”以后走向衰退,而且这种进程难以逆转。正如王一川所言:“在作为实在的现代性进程中,古典文化并没有完全绝迹,而是作为古典残片生存下来,具体地说,是在现代因子的激活下生成为活生生的古典传统形象。这种现代性语境中的古典形象已不再是古代的古典文化本身,而是现代性中的古典传统,是现代性古典。”在白话驱逐了文言之后,古典传统的存在形态就变得封闭而破碎,和现实生活逐渐疏离。但是,中国文学如果抽离了自身的传统,将失去自身的文化记忆和审美特色,变成外来文学的复制品。
网络文学的发展与突破,要重视从本土文学资源中吸取营养,并以创造性的化用将其转换为源头活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写手们就不能满足于扮演搬运工,仅仅把古典元素作为一种粉饰的外衣和提味的调料。首先,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张爱玲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她曾经写过考论《红楼梦》的《红楼梦魇》,也曾将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翻译为国语。《金锁记》深得《红楼梦》的神韵,出身低贱的曹七巧被家人嫁给了大富人家的残废公子,从此便戴上了“黄金的枷”,“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在从卑贱到富贵的身份转换过程中,与此对应的是她的性格从质朴、野性转向冷漠、残酷。她眼睁睁看着大家庭支离破碎,亲手毁灭了儿女的幸福,也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张爱玲非常擅长表现危机四伏的时代环境中女性被外部环境和自身欲望所扭曲的悲剧,从那种钝刀割肉式的折磨中照见人性的脆弱与变形,进而生发出对社会退化的荒凉感和对文明衰退的忧患意识。张爱玲的写作有一种骨子里的悲剧意识,她善于从平凡人生中洞见平庸无恒的悲凉,如她所言:“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她的语言酷似晨霜里怒放的牡丹,远看雍容华丽,靠近了寒气逼人,在文字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对人世和人性的怀疑与不信任。而且,张爱玲的写法并不生僻,贴近时代和大众,走的是一条较为通俗的路线,她对鸳鸯蝴蝶派的写作套路就更是熟稔,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作家。张爱玲的不凡之处在于,她在兼收并蓄各种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并没有停留于简单的模仿,而是融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以个性化的思考进行创造性转换。作为一个集大成者,她从传统文化的母体中获得滋养,又以个人化的探索割断了依赖性的精神脐带,实现了对鸳鸯蝴蝶派和自我的双重超越。就网络文学目前的态势而言,在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环境中,写作者往往满足于名声和金钱,很难涌现能够破壁而出的集大成者。报刊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也曾经是新媒体,也曾催生出新的文艺形式,并逐渐孕育了一批文学大家。或许有一天,网络空间也会因为那些真正独立的创作主体的存在而呈现出新的气象。
其次,网络文学对本土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再创造,必须有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凤歌的小说《昆仑》中不少人一开腔就带“鸟”字,这无疑在向梁山好汉的满身匪气靠拢。网络游戏《水浒无双》官方网站的首页有显赫的字眼:“血战到底 抢钱抢粮抢女人”,尽管是在虚拟世界中,但对强盗逻辑的公然宣扬显然有不小的危害。从金子的《梦回大清》开始,穿越到古代的现代女子有不少都如小薇一样卑躬屈膝,低眉顺眼,言语中流露出一副十足的奴才腔,在四爷和十三阿哥之间的取舍,也只能听天由命,像一只小蚂蚱一样,被紧紧攥在皇权和男权的手心。在《梦回大清》中,主人公茗薇和四福晋有一段对话,常常被读者和批评家认为是精彩的片断,既表现了两个女人为争夺四爷的宠爱而斗智斗勇,又包含着无厘头的幽默:
“男人的事儿咱们女人不懂,都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衣服不穿也罢了,女人对他们而言,也不过如此,是不是?”四福晋面带笑意却目光炯然地看住了我,我用手指揉了揉耳边的翡翠坠子,若有所思地说:“是呀,所以我旱就决定做胤祥的裤子了。”
“什么……”四福晋一愣,不明所以地看着我。我呵呵一笑:“衣服可以不穿,裤子总不能不穿吧。”
其实,这些争风吃醋的机智恰恰折射出现代女性内心中主动依附男权的集体无意识。因此,网络文学对本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传承,也必须经历一种批判性的价值选择,而不是照单全收,以为只要是古董就能卖钱,而不考虑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
再次,精品意识是提升古典元素的艺术活力的关键。在网络文学写作中,多数写作者被潮流所裹挟,随波逐流,缺乏明确的艺术追求,无所适从,被文学网站的意志和网友的趣味所操控,灌水现象非常突出。就以三国题材而言,从网络游戏到网络小说,模仿乃至抄袭行为比比皆是。基于此,才会有网络游戏《三国杀》和《三国斩》的著作权纠纷。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起诉被告杭州趣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侵犯了著作权,意味深长的是,最终以原告撤诉结案。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在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过程中,被告的辩护理由是《三国杀》抄袭了意大利卡牌游戏《Bang!》(中文译为《呯》)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因而没有原创性,不受著作权保护。《三国杀》作为一款较为新颖的国产游戏,一度火遍大江南北,其原创性依然受到质疑,其它网络文化产品的艺术质量就可想而知。《悟空传》在戏仿经典的网络小说中,算是别具一格,最为关键的是作者抓住了孙悟空渴望自由的反叛性格,塑造了一个“宁愿死,但不肯输”的失败的英雄,葬身火海后回归顽石的原形。正如作者今何在所言:“如果我为了稿费或者发表来写作,就不会有这样的《悟空传》。因为自由,文字变得轻薄,也因为自由,写作真正成为一种个人的表达而不是作家的专利。”在本土网络文学刚刚破土而出的时期,文学网站的盈利机制还没建立,写手自娱自乐,也很少受到商业化潮流的侵蚀。到了现在,过度的娱乐化和商业化已经给网络写作套上了层层枷锁。今何在自己在《悟空传》之后,写出来的文字乏善可陈,这是否也因为难以抵抗日益强大的外部诱惑?如果网络写手无法进入一种自由的创作状态,而是时刻计算着回报,就很难写出真正的精品。如果还是片面追求数量,通过提高更新频率和拉长篇幅来集聚网络人气,网络文学对本土文学资源的搬用注定只能是粗糙的、肤浅的、碎片化的拼贴。当然,如果网络文学对本土文学传统能够创造性地继承和吸收,这既能利用网络媒介无远弗届的优势,激活本土文学传统的生命力,又能借助传统底蕴提升网络文学的境界。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文学传媒史料综合研究与分类编纂”(项目编号:14AZD08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韩春燕)
黄发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