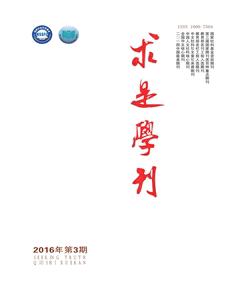生活即教育
侯晓颖+王志
摘 要 教化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强调的是无为而为的教育心态和教学方式。教师“教的心态”的固着,既阻碍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发展,又忽视了教学的教化过程,教学应该呈现的是教师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结果,而不仅仅是教导学生;教化人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生活是一切教育的发生场所。教育发生场所的固化,严重忽视了生活的教化功能,教化人生的构建需要的是真实的生活;教化人生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份永恒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需要更大的毅力和勇气去践行和阐发。
关键词 教化 生活 无为而为
教化人生,既是教化他人的过程,又是教化自身的过程,同时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时间范围上,它贯穿人的一生;在主体范围上,它既包含教育工作者,又包含着每一个生命个体;在客体范围上,它既指向教师,又指向学生;在影响方式上,它是无为而为,自然而然的;在教育效果上,它是化民成俗,不令而行的。
一、教化是一种“无为而为”的教育方式
如果教育被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培养人的活动”[1],那么这个活动的发起者不应只是教师,还必须包括学生。教育的结果是要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力量站立起来,这也是教化的本意之一。教化的过程就是活动者的本然生活——真实自然,毫无做作,而观察者也并非被有意地安排在那里,也没有被要求有所收获,他只是看到了一幕真实的生活,感而遂通,不令而行。
1.作为教育心态的教化:无为而为
人类总是预期通过教育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迈向一种更益于人类共同发展的趋势中,并最终实现“心灵的转向”[2]。可这并非一日之功,更非容易之事。正因为如此,教育更要谨慎行事。尤其在今天,干扰“心灵转向”的力量如此庞杂,教育就更应该走进学生的心里,从内而外地生发力量,让学生能够靠自力抵御外侵。
教育理应完成的就是让学生通过自力实现“心灵的转向”。这不是被告知、被教导所能完成的,外在的推、拉、催、压都是无力的。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后剩下的东西[3],剩下的是学生内在的学习力。所以,教育的影响是“无为而为”的,“无为”不是放弃主动权,而是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有为”的外在影响都是可以被忘记的,不是“我要”的东西都是走不进内心的。学习贵在“自得”,“自得之学可以终身用之,记闻而有得者,衰则忘之矣。不出于心悟故也。故君子之学,贵于深造实养,以致其自得焉”[4]。
教育也确实是一个“有意识的培养人”的过程,但这个“有意识”不仅仅指教师有意识的教。站在学生的角度,教育不是一种“别人要我”的过程,而是一种“我要”的过程,学习的主动权是教师无法强加的,教师应该变积极的主动为消极的主动。教育不需要带着“我来教育你”的心态,教师所要完成的就是把本真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效果呈现给学生,教学过程需要呈现的是教师的学习热忱。作为学习者,学生们自然能感同身受,因为他们就是带着求知热忱来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然有感而发,自己唤醒内在的学习力。心智是所有的自动化过程的结构,是生命进化长期形成的人类共有生物结构,如果共同激发,具有很大的能量。[5]
“无为而为”的教育心态,是要把反弹现象和负面作用减低到最小。今天的教育需要重新培养“师逸而功倍”的善于学习的人,不能再继续培养“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礼记·学记》)的不善于学习的人。“师逸而功倍”就是在“无为而为”的教育心态下产生的最好的教学效果。
2.作为教学方式的教化:从“有为”的“教的心态”走向“无为”的“学的心态”
好为人师是教育工作者一个突出的特点,尤其是当其面对“弱势”群体时,当教师意图明确地表达着他们的教学要求时,很容易忽视“有意识的教”带着一种先天的压迫,结束了应试教育后的学生们的很多表现就是这种压迫的结果。教师需要走出颐指气使的“教的心态”,“有意识的教”对学生“有意识的学”是某种程度的阻碍,很容易造成师进生退、师勤功半的困局。教师需要把这种“有意识”转而施于自身,以一种有意识的“学的心态”呈现于学生面前,而非是成人面对未成人的指教态度。“学为中心”的教育方式是中国古代的教学思想史浓缩概括,即为“以学为本,因学论教”[6];在古代的教学中,教师仅仅起着引导和监督的作用,学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自我学习和独自钻研[7];古代的教学原则,基本都是学习原则,教师的“教”基于学生的“学”,是为学生的“学”而服务[8]。今天,教师需要重新收回自身的教学主动权,把它交给学生,以退为进并非是一种教学策略,而是出于对学生自主性的肯定。在知识面前,教师也是学生,教学只是教师在汇报自己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结果,收回“教的心态”,师退生进、师逸功倍。教学只是在与学生共同切磋分享而已,又何必多一层或隐或现的颐指气使的指教心态。
教书育人在于成就自己的心性品行和智性德能,这才是符合人性的“为己之学”。中国历史上,自晋朝以来,作出杰出贡献的9997名人物中靠自学成才的占67.7%[9],历史证明,“为己之学”的成材率更高。自学不只是一种学习方式,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教学方式,教师需要做的是,时刻关注自身成长的步伐和空间,只有这份纯真的求学心态才能感化学生。“成己”才能“达人”,“成己”是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自我智性、心性的成就才是教育成功的最终证明,否则这样的教育又何以令学生信服和向往?
面对知识传播如此便捷的新时代,面对“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人类文明,教师需要走出“教的心态”。21世纪是学习型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是永远的求知者,求学之心应贯彻于生命始终,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教师应首先成为学习的专家,与学生共同学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把“有意识的教”转变为一种“有意识的学”,以自身的“学的心态”触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生发,学生的感同身受是不需要被指教的。求学在于自主,“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而因以教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无益”[10]。
二、教化人生: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
教育一定是在本然的生活中完成的,不需要任何激进式的催促。人类心灵的塑造如果不是内发的自我生成,就一定会导致并发性的后遗症。生活本身就蕴含着教育功能:生活中的每个个体都在给周围造成一种影响,无论大小,无论好坏,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无为而为”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事物,如杜威所言“环境(日常生活)的无意识的影响难以捉摸又无处不在,影响着性格和心理的每一根纤维”[11],所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教化,时刻在发生着,每个个体既是教化他人人生的一个参与者,也同时被他人教化着自己的人生。教育之中无小事,“凡是我们不经研究或思考而视为当然的东西,正是决定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和决定我们的结论的东西。这些不经思考的习惯,恰恰是我们在和别人日常交际的接受关系中形成的”[11]。
1.教化人生的本意是生活之外无教育
教育就是生活的全部,这是教化人生的根本信念,是每一个个体可以不断体知的生命实践。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不是回归,教育从来都是在生活中完成的,学校的产生是为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教育从来都是在生活中才最终得以完成。如果走出学校后,学生走向学校教育的反面了,这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学校教育呢?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学校教育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没有了真实的生活,教育还有何用?教育如不是真实的生活,学生走出校园的那一天,又该如何抉择?教师的言行如不是教师的真实生活,学生又该如何抉择?教化人生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完成的,无论是知识的学习还是品性的养成,只有真实的生活才能化育人心。
教育并非面对着生活,也不是回归“生活世界”[12],教育不是可以脱离亦或回归的部分生活,它与生活是一体的,不是“子归母怀”的母子关系。人和其生活世界是不可能被分开的,它们具有同时性和一体性。[13]教化人生既不需要回归生活,因为它本身就是生活,也不需要以“先验世界”为本源,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完成“下学而上达”的“不怨天,不尤人”之化育,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需要妄加一个意向。退一步说,无论“生活世界”作为一个原初的、先验的意识领域,其本身的实践性质蕴含着无限的能动力量。[14]教化人生就是一项生活实践,它是中国传统学问之生活实践属性的一个明证,中国的传统学问是一门生活哲学,一门实践哲学,是一门包含着生活任何所需的生命科学,精神的亦或物质的,经验的亦或先验的,意识的亦或感知的,这里面都包含着,而且这些和我们的生活是一体的,是生命个体可以践行体知的。所以,教化人生所要发挥的就是生活内在的教育力量,用自然纯真的生活构建“感而遂通”、“化民成俗”的一生。
2.教化人生是一种在场的“有感”
教化人生只是主体基于“素位而行”的生活状态,透射出的“无为而为”的场。人体是“形体-场-意识”三位一体的复杂巨系统[15]:宏观事物同时存在物质性和场性,前者与一定的实体对应,后者作为一种无形的(意识)场存在,概而言之,实在可见的事物与虚隐的意识场共同构成了生命世界。[16]
基于复杂系统学的人体科学认为,人的内层意识是发自内心的愿望、理想和人生观,是人体意识结构与广大生命空间中其他生命体的交汇处,是“良知”的所在,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15]人对专注力高的事情会形成固定的意识场,这个意识场既影响自身,又影响周围的环境。从开放性的角度来说,内层意识的开放度最大,能量最高。教化人生的专注力只是落实在教师自身,教学和生活都只是一个反求诸己的“致良知”的过程,这样的教学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在场“有感”的活动:教师专注在自身的“素位而行”,以“正己”为退,引导学生“有感”而进,学生在场的有感是自发的而不是被压迫的。在主动性的引发上,教师不再用外力要求学生,学生本身就天然地具备求知之心,师退生进,学生身处的是“不令而行”的“化育”之场,其主动性是“有感”而发。教育要完成的是主体自我掘汲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教育工作者应该审慎地考虑,是否因自己不信任学习者的“有感”而习惯性地用一种“你要接受并作出改变”的私意堵塞了学习者内心的动力源泉。
教育就是要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在“场”感触中,让每一个人不断地积蓄力量,使内在的智仁勇超越内外阻力。教育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唤起每个人的主体意识和内在动力,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的是有感而发,教育所能做的就是提供这种“有感”的“场”景,学习者的在场就足以保证他的感触,除非这个“有感”的“场”景是假的、被修饰的、意识涣散的“场”,自然也就没有能量。
三、教化人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永恒的力量
教化人生是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可以深度挖掘的宝贵资源,它不是教师的专属物,更不是教师的专职专责,“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大学》),这是求诸己而非求诸人,求自己是为与不为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这需要的是“独恭而天下平”的生活,“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诚实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我以为,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惟一可赖的力量”[17]。
1.教化人生:赢得一份社会力量
教育对于人类最本源的意义,就在于教育工作者通过个体的日常生活,赢得一种道德性的社会力量,这是社会和谐的动力基础。这种力量就时时刻刻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不需要任何的教学设计,也不需要特定的教学场所,更不需要所谓的“学生”这一特定的被称之为教育对象的人群。教化人生的主体未曾想过要通过他的言行去“教育”另外一个人,这只是他的生活,不这么做,他便不知道该如何生活,没有一种潜在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仅此而已,也唯有如此,教育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其“润物细无声”的“化育”功能,这也是《礼记·学记》乃至全人类教育的最高理想——“化民成俗”。教育可以是“如沐春风”的,春风并非有意要沐浴万物,这只是一种因外感而内生的力量,是生命主体因境遇的触动而生发的一种“我要”的生命状态。“无为”是个体全心全意地做着自己分内之事,并未盘算自此以外任何的觊觎之事,“尽人事”而不做一分一毫的分外营求。这是“独恭而天下平”的力量,是康德的三条道德律令的力量,古今中外都如此,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切己践行的问题,教化人生需要的就是这个“着陆点”。
2.教化人生:赢得一份个人勇气
教化人生对于个体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实践上的事,今天的教育理论多得似乎泛滥成灾,但真正能落实在生活和教学中的又少的可怜,一方面是它们本身就没经过实践,另一方面是它们经不起实践。教育人生的这份资源,既源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又源于人性之深厚的仁爱基础,它就在每个人的心中,“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区别只在于“为”与“不为”。
从教师的角度看,当教师把自己对待学问知识的那份热忱呈现在学生面前时,学生自然会被感染,这自然胜于让学生感到学习是被要求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这份热忱。教师不把自己视为教的专家,而首先要成为一位学的专家,教师的学带动着学生的学,教师学的热情带动学生学的热情,对于烂熟于心的教材,教师可以做创造性的转化,也唯有始终保持求学心态的教师,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教师的课堂很可能会走向一种习惯性的“表演”,为与不为,在于一念之间的心态转变。
从个体的角度看,生活与教育是一样的东西。教化人生的意义在于,个体充分感知自己每一刻的心念言语行为都在对周围造成影响,而且首先受影响的是自己的身心,人在改变周遭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他居留于其间的生活[18],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是“为己之学”,教育首先是为了成就自身的人格品质,唯有“正己”才能‘化人。对于一位教师来说,就更应该具备这种教育的敏感度,教化人生首先要端正的是自身的态度,因为这最终都不是为了他人,如果自身都还不够好,就希望为他人付出,这样的心态是有问题的,舍本逐末。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这份资源在历史中,在今天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在今天的科技文明中,一直都存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认识它,了解它,需要的是掘井及泉的功夫,得到的却是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不自具足,何须外求。
3.教化人生:从文化传统中汲取力量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教育以气质变化和心性养成为旨归,其指向的是“为己之学”,所以才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学生的“远怨”才是教化人生的开始。“正己而不求于人”(《中庸》)是教学的基本心态,也是生活的基本心态,教化人生是主客体都“无怨”的人生,这是“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礼记·学记》)的教育,今天的教育出现了太多的反弹,我们还是步入了“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礼记·学记》)的教育困境中。
教育的首要课题是要掘汲自己生命的源头活水,教育如果触及不到生命的源头活水,都将是苍白无力的。这份资源就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就在我们敢于践行的生活中。生活是自我教化的过程,即使一人独处,自身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在影响着自己的身心状态。“不欺暗室”并非是一句教条,而是个体善护自我心念以滋养心性气质的生活体验。生活需要的是务实求真的态度,古之学者之所以学为自立,是因为他们深知反躬自身的时光是永远都不够用的,又何谈“责求于人”呢。这才是最务实的生活态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为世范,“不令而行”的教化人生是这样完成的。
参考文献
[1] 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 柏拉图.理想国[M].张造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5] 佘振苏,倪志勇.人体复杂系统科学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6] 杨平,唐文中.试论“以学为本,因学论教”的教学思想[J].中国教育学刊,1994(6).
[7] 申国昌.中国学习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8] 刘秀峰.百年来中国学校自学思想的演进研究[D].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
[9] 刘宇庆.自学学初探[J].江海学刊,1982(1).
[10]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1] [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2] 朱刚.理念化、生活世界与先验生活—论胡塞尔的“理念谱系学”[J].学术月刊,2010,42(4).
[13] 石中英.教育信仰和教育生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2).
[14] 康永久.王雅薇.教育与生活:意犹未尽的对话——教育学分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J].教育研究,2012(3).
[15] 吴邦惠著.人体科学导论(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16] 佘振苏.复杂系统学新框架:融合量子与道的知识体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7] 钟兆云.解读辜鸿铭[J].书屋,2002(10).
[18] 刘良华.教育、语言与生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1).
[作者:侯晓颖(1989-),女,山东威海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王志(1988-),男,江苏连云港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
【责任编辑 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