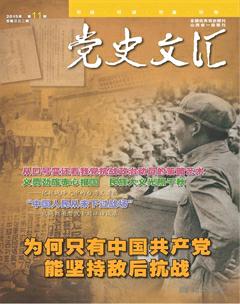党史军史工作者的责任、思维与著述方法
周健
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由胡乔木创意督导,胡绳担纲主编,集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名家之力而成,既有高度权威性又有一定普及性,到目前为止共印刷了10次。历史学家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为我们讲述了《七十年》的写作原则、方法和思路,回答了“这本书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的问题。掩卷遐思,我感到这本书至少在责任、思维和著述方法三个方面对党史军史工作者有所启迪。
党史军史工作者要有历史责任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改旗易帜。这时许多人在思考:那么多共产党都垮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垮?这就是《七十年》写作的历史背景。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有人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党,如何从艰难曲折中一步步走来,这个过程是多么不容易;党之所以能够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根本原因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种责任意识在胡乔木、胡绳、金冲及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胡乔木、胡绳关于《七十年》的谈话,并不是准备发表的,受职业习惯和长期训练的驱使,金冲及做了详细记录。在金冲及84岁的时候,感到这些记录如果成为废纸实在可惜,于是整天拿着记录本子读,让儿子录音、整理,再经他反复校对定稿。我感到,金老做的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三位大师的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确实值得我们敬佩,他们把这种意识上升到对党忠诚的自觉行动。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近年来,一些人为了吸引眼球,博取人们的好奇心,往往以历史研讨、网络文学、小报小刊、微博微信等形式,散布一些似是而非、颠倒黑白、漏洞百出、歪曲事实真相的东西。对于这种现象,如果听之任之、置若罔闻,“谎言就会变成真理”,从而损害我党我军的声誉,甚至动摇我党我军的根基。因此,党史军史工作者要有紧迫感、使命感,研究分析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与党史军史问题有关的动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在党史军史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党史军史工作者既要有科学思维又要有战略思维
所谓科学思维,一是必须真实,要“存真,求实”;二是必须从事实出发,找出党史军史发展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 “实事求是”。党史军史著作要坚持党性原则与科学精神相统一,用科学的态度来阐明我党我军历史,科学地论证我党我军所走过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和考察历史,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来考察,防止简单地用现在的标准去任意评判历史,或者随意裁剪篡改历史。运用科学理论深入研究社会关注度高的党史军史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令人信服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倡导严谨、求实、科学的精神,切忌赶时髦、凑热闹,追求轰动效应、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
所谓战略思维,是要注意官修党史军史不同于一般的党史军史研究。作为一部承担一定政治功能的党史著作,《七十年》的写作有其专门性和针对性。比如对“文化大革命”部分,胡绳一再强调,不要写成“文革”史,要写成党史中的“文革”阶段;书中既要写“文革”的错误,也要写“文革”中抵制错误的人们,要让人从党的失误中看到希望。这个思路提醒我们,党史军史的撰写和对党史军史纯学术化的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从党和军队的角度写党史军史可能是一种写法,从纯学术角度写党史军史则可能是另一种写法,在保持求真求实的基础上,前者重在资政育人,后者则重在还原史实;前者重在当下,后者重在长远,两种写作方式有可能长期并存。
党史军史工作者要讲究著述方法
我们要坚持党史、国史、军史和人民的历史、社会的历史相统一,勇敢捍卫党史军史的尊严和价值,使我们的党史军史著作导向正确、结构合理、史实准确、点评精当、逻辑严密、文字生动。
让历史说话,真实可信。要坚持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写历史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脉络清晰,有血有肉,在事实的基础上,展开必要的论证。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全大局。要用历史本身来说话,让群众自己去判断,通过党史军史著作,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产生信服感。比如,科学家竺可桢在上海解放时看到解放军夜里都睡在马路上,就在日记里中写道“国民党必然要失败,共产党必然要胜利”。把他这一段回忆写进党史军史,就很有说服力。
广征博引,客观详实。对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想,并且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包括已经发表的材料和没有发表的材料,党内外、军内外、国内外的有关资料;特别注意利用国外、国内中间人士乃至敌人方面的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评论,让这些证人参与到判断历史的过程中,来显示我们提供的见解是历史公正的证言。
措辞严谨,恰如其分。党史军史著述要特别注意表达的准确性。比如《七十年》原稿中有“‘文革造成更加广泛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这样的表述。胡乔木批注道:“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书稿中另一处的表述是:“文革”不是不可避免的,胡乔木认为:这样的表述“太软弱了,应该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对于“革命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党”的表述,胡绳认为:这就说得简单了。是不是有了这样的党就能胜利?至少得改成“革命胜利首先要有这样一个党”,不要说取决于有没有这样一个党。
既写大人物,也写小人物。首先,要在人民斗争历史的背景下写党史军史,写清楚党和军队是在人民中间奋斗,是密切地依靠群众才取得胜利的。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其次,党史军史也是党和军队的一切合作者、支持者的历史,对我党我军提供过帮助的人应当有所体现。第三,要有意识地多写一些党和军队的普通干部战士、各个革命时期的先进模范人物。因此,党史军史既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既要写领袖,也要写人民大众。
善于取舍,详略得当。要坚持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既呈现整体,又呈现局部,既合理布局又精雕细刻,把我党我军的历史画卷完整、生动地呈现出来。每个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要交代清楚,不要只叙述政治军事事件本身。要注意党史、军史和国史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些事情,现在还没有定论,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可以不写或者少写。简化不是平均用力,该详细的、有新意的就详说。
鲜活生动,波澜起伏。平铺直叙,像老的党史军史写法一样,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党史军史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能让人身临其境的材料,就得展开说。一些关键性的事情,要有特写镜头。比如四渡赤水、上甘岭战役等等。这样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鲜明色彩,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阅读价值。要写得让那些对党史军史没有多少兴趣的普通读者,读了也有所收获。让党外军外人士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夹叙夹议,平等交流。党史军史著作要有20%左右的议论,议论不能生硬,要不着痕迹、风生水起、画龙点睛,有时议论就在叙事中间。写历史不能像法官写判决词一样,好像读者不需要思考。夹叙夹议,并不是要你离开事实去发很多议论,而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事情本身的经过中引导出结论。这是一个平等的、商讨的过程,不是强加于人。
抓住读者心理,注重我党我军实践。过去有些党史军史著作中大量篇幅是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讲话、文章以及党和军队会议通过的文件,可谓“文山会海”。这样会让人看了眼花缭乱,毫无生气,原因是没有抓住读者的心理。其实,读者不只是要了解共产党、解放军是怎么说的,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比如,与其去写某位领导人在某次会议后做了哪些决定,倒不如说根据这次会议决定做了哪几件事情。
当我合上这本书时,发现有趣的是:封面上金冲及的名字后面没写“编”或“著”。媒体采访他时他说胡乔木、胡绳没授权他“编”,书中也没他自己的议论,当然谈不上“著”,所以只署了个名字,表示对此书负责。还有不能不提:在该书定稿过程中,金老特意嘱咐责任编辑到他的办公室来取稿子,生怕他精心修改过的书稿在快递时被弄丢。我想,这两件事体现了金老严谨的学风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一本书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党史研究中的背景或注释,使我们得以知晓那个年代是如何诞生了这样一部著作的。如果说还有些意犹未尽的话,从1927年国共分裂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这段时期的重要历史,两位大师不知何因都未过多言及。胡乔木和胡绳两位大师语重心长、点石成金,他们对于我党历史的认识和观察,代表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相信一定会为党史军史工作者提供丰富而有益的启示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