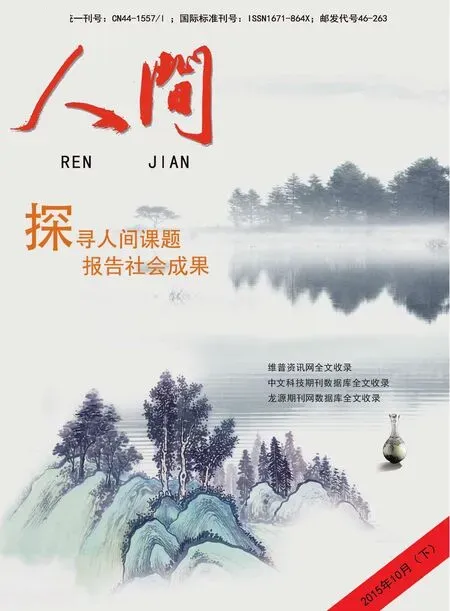浅析赛义德《东方学》的独到与偏颇
白雪松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浅析赛义德《东方学》的独到与偏颇
白雪松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阐述东方相对于西方而成立,是一种消极的概念。这本书的优势在于,赛义德打破知识和政治的边界,将二者相结合,通过旁征博引,进一步解释知识在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构建下,是怎样作用于殖民地并使其殖民合理合法化的。另外的独到之处在于,赛义德不讨论这种社会现象的影响,而是以寻根溯源的方式,探究产生的过程、途径及原因。然而,他的阐释只重视消极的一面,过于偏激,完全忽视由于这种东方、西方的观念以及殖民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另外,他只以远东作为讨论,没有涉及东南亚如中国、日本等例证及资料。事实上,这种殖民客观上对被殖民地的科技和人的思想解放产生积极作用,并对科技、文化、艺术、思想等多元化起到促进作用。从赛义德的论述和《东方学》的影响来看,其存在独到和偏颇之处。
赛义德;东方学;独到之处;偏颇之处;后殖民研究
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被公认为是后殖民研究的理论根基。赛义德东方学理论的形成,与其个人经历、知识水平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作为一个在西方学习、工作的巴勒斯坦人,赛义德切身经历了东西方之间差异导致的冲击和碰撞。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中,亚、非国家相继解放,取得民族独立,这导致西方国家权力缩水,全球范围内殖民体系瓦解。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用文学的方法,打破知识和政治的边界,进一步解释知识在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构建下,是怎样作用于殖民地并使其殖民合理合法化的。本文旨在分析赛义德《东方学》一书的独到之处与偏颇之处,有利于更客观地进行后殖民研究。
一、赛义德的东方学理论
东方不只是地理概念,它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综合意义。在现代社会中,东方学观点在跨文化的政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方学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赛义德创作的《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解释知识在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构建下,是怎样作用于殖民地并使其殖民合理合法化的。全书以寻根溯源的方式,探究产生的过程、途径及原因。赛义德写作《东方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至少从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对作为“他者”的“东方”的再现是如何被体制化的。在《东方主义》中他描述了多种学科、机构、调查研究的过程和思维方式,凭借这些学科、机构、调查研究的过程和思维方式,欧洲人在几个世纪中最终“认知”了“东方”。他用福柯关于权力话语的观念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来挑战“西方”认知“东方”的权威。另外,在该书中,他采纳了一种以欧洲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的西方人文主义观念。《东方主义》开创了“殖民话语”这一新的领域,使文学、文化和政治相结合,打破了学科界限,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视野,但赛义德在该书中同时使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的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和那种独特的西方人文主义观念则造成该书在方法论、理论阐述及价值方面的种种问题与缺陷,因而遭到了多种批评。(赵建红,2007)从赛义德的论述和《东方学》的影响来看,其存在独到和偏颇之处。
二、《东方学》的独到与偏颇
(一)《东方学》的独到之处。
在《东方主义》中他描述了多种学科、机构、调查研究的过程和思维方式,凭借这些学科、机构、调查研究的过程和思维方式,欧洲人在几个世纪中最终“认知”了“东方”。他利用知识谱系学的分析方法和福柯关于权力话语的观念以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来挑战“西方”认知“东方”的权威。另外,在该书中,他采纳了一种以欧洲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的西方人文主义观念。《东方主义》开创了“殖民话语”这一新的领域,使文学、文化和政治相结合,打破了学科界限,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视野。
因为对批评以及知识的世俗性的确信,赛义德得出了一个具有变革意义的结论:东方学是建构的,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其目的是凌驾于并且控制东方。东方被描述为低等的,而西方则处于一个优越的地位。赛义德主要是在批判西方,通过其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学术的力量、以及自身所规定的一套术语和规则来建立一套二元对立的话语,在这套话语当中,高高在上的西方对位于一个被规训的、沉默的东方“他者”。(何卫华,2004)
(二)《东方学》的偏颇之处。
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中的一些观点并不是正确的,如果完全采用赛义德的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几乎要遭到彻底的摈弃。他只以远东作为讨论,没有涉及东南亚如中国、日本等例证及资料。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因而,他认为,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赛义德的观点过于偏激,作为西方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东方学,它在知识上推动了人类对东方的认识。
赛义德《东方学》对中国的启示
赛义德《东方学》的理论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东方学现象是整个西方的隐喻或缩影,实际上应该用来代表整个西方”这是说西方为了确定自我,他们拿东方作为非我来作对照。在西方文化史上东方一直是作为西方确立自我的“他者”而不断变换着。
运用赛义德理论需注意,其一,西方人把中国当做“幻想”的对象是以中西双方实际历史的交流为基础的。尤其是大航海以后,西方人第一次走出狭小的地中海,域外的文明,特别是中国的文明对其实际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不需要用西方“幻想的矫情”来应证我们文化的合理性,但文化交往的历史至少可以说明多元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其二,虽然赛义德告诫我们,在东方不需要一个像西方的东方主义那样的“西方主义”,但实际上19世纪后的中国思想的确存在着一种“西方主义”,但它的历史正好和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历史进程倒了个个儿。在当前的西方形象学研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欠坚实的历史研究,在文化心理上走出“西方主义”是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赵建红. 赛义德的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研究[D].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2007.
[2]何卫华. 爱德华·赛义德:颠覆型的知识分子与对东方学的质疑[D].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2004.
I0
:A
:1671-864X(2015)10-0008-01
白雪松(1990.10),女,汉,辽宁,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在读),单位: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文学,比较文化。
——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