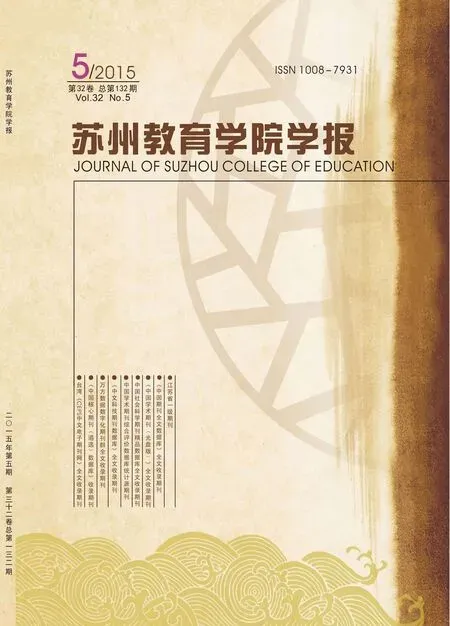金庸武侠小说自注中的自我经典化探析
—从“明河版《”金庸作品集》谈起
朱令军(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山东 青岛 266555)
金庸武侠小说自注中的自我经典化探析
—从“明河版《”金庸作品集》谈起
朱令军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山东 青岛 266555)
摘 要:金庸1970年至1980年对其小说所作的修订在其武侠小说自我经典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正文的增删改写之外,明河版《金庸作品集》的另一显著特征是系统的自注的出现。金庸小说的自注延续了中国古代文史著作的撰述传统,同时融入了现代的思想和理念,有效拓宽了小说的阐释空间,成为其自我经典化的重要手段。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明河版”;《金庸作品集》;自注;经典化
自1955年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极短时间内受到广泛的欢迎,获得了大批读者,成为影响报纸销量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人们多将其看作娱乐性的通俗文学,对其经典性并不认可。随着以陈世骧、夏济安和林以亮为代表的纯文学领域研究者的关注,金庸对自己的作品逐渐产生了经典化的期待。自1970年到1980年,他全面修订自己的作品,在正文的增删改写之外,辅以大量形式丰富的自注,有力推动了作品自我经典化的进程。金庸的作品进入了大学的讲堂,甚至进入了文学史,相关的研究日渐成熟。但值得思考的是,在金庸生平和小说研究成果累累的同时,最早系统承载金庸自我经典化期待的“明河版”《金庸作品集》(以下简称“明河版”)中的自注,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关注。本文拟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探讨“明河版”自注在金庸自我经典化过程中的意义。
一、金庸武侠小说自注的背景
自注是中国古代文史著作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存在,始自司马迁的《史记》。章学诚有言:“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1]238东汉王逸为自己的《九思》作注(文前有序,文中有注),则为诗文自注之始。自注的核心在于“恐后人不知其所云”,担心自己的主张历久失真,换言之,即希望自己的著作在后世得到更好的流传和更充分的理解。司马迁和王逸的自注皆有其特定背景,前者曾师从孔安国,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了解甚多,后者感于班固对《楚辞》解释的乖异而作《楚辞章句》,都对经典著述因历史隔阂而遭遇的阐释偏差有着切实的感受。进一步分析,自注的背后蕴含着对自己著述的强大信心,自信著述可以流传后世,并受到充分重视,具有相当大的阐释空间,至少具备成为经典的可能性。自注于文外体现为序、跋,于文中体现为注释,增益正文,导引阐释和批评的方向,作者往往具有深厚的学养和经典化的预期。这种经典化是自我经典化,是作者个人将其作品经典化的一种方式。
两汉之后,受佛经合本子注的影响,自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萧大圜《淮海乱离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和谢灵运《山居赋》。至唐代,自注已经成为学人的研究对象,《史通•内篇•补注》于此有专门论述:“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赅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2]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印刷和出版行业的发展,各种著作的积累日益增多,自注特别是文中注释往往会由于涉及文献考证,增加了写作的“麻烦”,而且“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某种意义上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哉?”[1]239更不用说有人有意轻视自注,为剽窃他人成果作方便了。虽然自注中的考证性和学术性受到了影响,但对作品能够流传后世的信心和对读者能够体会自己创作苦心的期待,依然驱动一代又一代的作者不但关注自己作品的当下影响,更关心后人对其作品的阐释和解读。在唐诗宋词中,自注拓宽了诗境,深化了诗意,已然成为重要的表达手段;在明清小说中,自注往往化身为“序”和“凡例”,而正文中“看官,你道……?原来……”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表达其实也有一定的自注功能。经过漫长的发展,自注已经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不但蕴含作家自我经典化的预期,更带有作品经典化的气息。当然,于一般作品而言,这种气息不禁一吹;但于优秀作品而言,这种气息增强了其生命力和影响力。
进入现代文学阶段,自注的形式更为多样,运用更为灵活。主要包括:序跋,如鲁迅的《呐喊》和曹禺的《雷雨》;注释,如卞之琳的《雕虫纪历》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封面设计,如萧红的《生死场》和张爱玲的《传奇》;扉页引语,如鲁迅的《彷徨》和曹禺的《日出》,等等。总体而言,有自注的作品未必能成为经典,但自注作为切入经典的重要途径,依然受到很多作家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有影响力的自注多出现在纯文学领域,而在通俗文学领域,作家在自注方面下功夫的并不多。商业化写作使得作家们更关注作品正文在当下的受欢迎程度,至于与正文在阅读上可以形成互文关系的自注以及其中蕴含的促进作品经典化的潜力,作家们一般有心向往,但也只好敬谢不敏了。来自纯文学的压力,也限制了通俗作家自我经典化的追求。以武侠小说为例,白羽在自传《话柄》里提到:“鲁迅先生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艺论。”[3]81“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我……可不负责。”[3]自序白羽在通俗文学创作方面的处境,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等人的武侠小说作品,封面或以书法为主,设计较简,或以绘画为主,意境较浅,多数没有序跋和扉页引语,更没有注释。作者本人似乎在经典化方面也没有什么预期。通俗文学领域能像张恨水那样在封面设计、插页、自序上下功夫并且产生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的作家,毕竟不多。
二、金庸武侠小说自注的内容和特点
1970年3月,金庸开始修订自己的武侠小说。1975年,《碧血剑》(修订本)由明河社出版,明报出版社发行,自此36册800余万字的《金庸作品集》以中国通俗文学史上罕见的姿态隆重登场。此前少有通俗文学作家将自己的作品大规模结集出版,因为大规模结集出版意味着典范化、权威化,对作家主观的创作成就和客观的出版条件均提出很高的要求。一生著述3 000余万字的张恨水,一部《蜀山剑侠传》即已500万言的还珠楼主,与金庸同为新派武侠小说大师的梁羽生和古龙,在此之前的作品均未大规模结集出版。而对自己结集的出版行为,金庸经过了充分的准备。除了全面修订(有时还在报刊连载修订后的作品,可以视为为试探读者的反应),亦即在主观方面努力外,他还为作品集的出版营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包括成立“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充分发挥明报的资源优势和个人的影响力。1981年8月,《鹿鼎记》(修订本)出版,至此,《金庸作品集》完整亮相。单从出版行为的角度,已可看出金庸自我经典化的努力,而作品集中的封面、扉页和封底的印章、插页、插画、注释、后记和附录,更在具体的层面丰富了通俗文学作品中自注的形式,即使在纯文学领域,这样的自注也是令人瞩目的。
(一)图文相生,以图说别构历史情境
“左图右史”是我国悠久的出版和阅读传统,元明以降,小说戏曲中的插图更是参与了叙事的过程。金庸本人对插图也非常重视:“我很喜欢读旧小说,也喜欢小说中的插图。可惜一般插图的美术水准,与小说的文学水平差得实在太远。”[4]727民国时期,通俗文学特别是武侠小说在封面、插页等涉及到图的方面大都做得比较粗糙,比如以画工简单的拿刀拿枪的侠客形象作为封面,直接点出作品所属的文类。新派武侠小说在报刊连载期间往往会有大量单行本出现,这些单行本的封面也很粗糙,“武夫”气质明显。在《金庸作品集》出版时,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金庸作品集》封面有名画,扉页、封底有印章,正文前有插页,正文中有插画,各处的图片均配有文字说明。其中,封面绘画说明36则,扉页印章说明36则,插页说明593则。封面和扉页的说明为小说找到了美术领域的“知音”,使得图解小说的意境成为可能;插页的说明则为小说找到了历史领域的“顾问”,增强了虚构的真实感。小说出入于历史、虚实之间变幻多姿,构建出既具有作者鲜明个人特色,又具有很大想象空间的历史情境。
关于封面和印章的说明着力为小说的意境别开生面,如同不同声部的合唱。封面均为绘画作品,多为名家名品,无名者亦堪称文物。比如《飞狐外传》两册的封面,用以喻人:《山茶水仙图》“山茶艳丽,水仙清雅”,象征袁紫衣和程灵素;《迎春、樱桃、望春图》以不能充分享受春光的三花象征“马春花与苗夫人,花开花落匆匆,却也有过一段凄艳的时光”。《天龙八部》五册封面的作品分别来自大理、契丹、吐蕃、西夏和宋的绘画,正与《天龙八部》中叙写的民族关系相应。《笑傲江湖》选用徐渭、傅山、八大山人、郑燮的画作封面,看重他们“为人重风骨节操,画画重自由发挥”,是“艺术家中极具‘笑傲江湖’性格的人物”。印章则因选择的恰切,但写出章刻文字,即有升华作品意境之功,如丁敬《长相思》之于陈家洛等对香香公主的思念,齐白石《吾草木众人也》之于狄云的性格,沈凤《当中和天,携乐易友,吟自在诗,饮欢喜酒》之于韦小宝的调侃,等等。
关于插页的说明虽看似繁琐,但其主旨在为虚构的故事营造真实的历史环境,为读者提供更加宏观的审视故事的角度。插页说明有三个特点:一是涵盖广泛,几乎涉及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金庸以小说家的身份选择历史图片资料,包括与小说有关的历史人物的肖像,元宝、钞票、年历、木碗、酒壶、经穴图、地图、御笔、兵器、官印、头盔、阵法、军旗等具体用品,诏书、实录、行稿、个人撰述等文献资料,以及景物、建筑等的照片,于读者而言有很强的代入感。二是与小说人物相联系,引导读者从历史的角度看虚构的人物。比如关于清皇贵妃冬朝冠,说明中有“这顶帽子,乾隆企盼能戴在香香公主头上,而终于无法如愿”的点评;关于郎世宁的《大宛骝》,说明中有“郭靖的小红马或仿佛如此”的提示;宋版《论语》,说明中有“黄蓉教杨过读《论语》,或许读的就是类似版本”的想象。三是具有结构性,与小说结构互相补充或互相对立。《碧血剑》的插页说明主要围绕两个人进行,一是袁崇焕,一是崇祯,而这两人的矛盾冲突正是小说情节发展的根本动力。《射雕英雄传》的插页说明一方面服务情节的发展,一方面分别重点介绍了宋、金、蒙古的有关情况,呼应小说中江湖人物在三国复杂的关系中命运沉浮的结构。《雪山飞狐》的插页说明主要在肯定雍正,从这一小说中没有的角度反映出胡、苗、范、田因反清复明而历代结怨的局限性。“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4]735,别蕴文心,是金庸现代武侠小说的重要特点,也是他非常擅长的结构故事的方式。
(二)小处考证,借注释道出虚构渊源
在小说的正文中设置注释,看似常见,其实多为他注,甚少自注。前文述及,明清小说中的“看官,你道……?原来……”和“且听下回分解”带有一定的自注性,但这种自注基本是为情节的发展服务的。在被视为典型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的行文中主动设置注释,而且是考证性的,绝对是一种冒险。对金庸而言,这些注释都是在修订作品的过程中加上的,是他的故事最初吸引的大批读者所未曾预想到的改变,亦即不是读者的必需和市场的必需。事实上,金庸也不是在所有的修订作品中都设置了注释,可见这种改变也不是修订的必需。但不管如何,金庸还是作出了改变,并且下了很大的功夫。这种考证性的自注很容易让人想起我国文史著作的自注传统。章学诚当年对学术性、考证性自注衰微的感慨居然在百年后的通俗文学领域得到了呼应,估计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金庸主要在《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鹿鼎记》三部作品中补充了注释。其中,《书剑恩仇录》是其开山之作,《鹿鼎记》是殿军之作,《碧血剑》则是“修订的心力” “付出最多”之作[5]864。细致的考证让人看到了虚构的历史渊源,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分量。
金庸的一些注释与情节的发展有着深层的关联,表现了作家企图通过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学范式去承担更高文学追求的愿望。《书剑恩仇录》通过两处共千余字的注释叙写乾隆在诗文创作方面的热情和才能之间的反差,其中有戏谑的用意,但乾隆若非如此,也不会被陷在玉如意的《桃花扇》和《少年游》中忽视了周边的危险。这部分注释于情节而言是有补充作用的,放在小说中则未免拖沓。同时,作者也指出:“乾隆诗才虽别具一格,但督修海塘,全力以赴,实令人心感……勤政爱民,似亦非虚言。”[6]427注释中的乾隆是个喜好作诗但水平一般的有点可爱的好皇帝的形象,与正文中的乾隆形成鲜明的对比。历史与小说在此形成了张力,给予读者更宽广的思考空间。《鹿鼎记》“连载版”的回目是四字短语,在“修订版”中则改成了查慎行的诗句。金庸详细考证了“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查家因为文字狱遭受的苦难,并以其中的受害者查慎行的诗句串联这部充满戏谑和讽刺的小说,知识分子的悲剧与江湖混混的喜剧相交织,真实与虚构相交织,已经远远超出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娱乐性、商业性的本质追求。
还有一些注释实际是金庸在历史方面的探究热情和解说兴趣的体现。为表明“五毒教”用蛊于史有据,金庸考证出袁崇焕的朋友郑湛若曾著《赤雅》一书,内有关于蓄蛊的记载。这种考证似乎意义不大。又如考证陈家洛之母“姓徐名灿,字湘苹,世家之女,能诗词,才华敏赡,并非如本诗中所云为贫家出身”[6]867,也略见多余,而且其中犯了一个重要错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徐灿并非陈家洛父亲陈世倌的妻子,而是陈之遴的妻子。陈之遴和陈世倌都是浙江海宁人,但前者生于1605年,后者生于1680年。算起来徐灿是陈家洛的祖母辈。《鹿鼎记》中的一些注释则尤其见出金庸结合现实解说历史的兴趣。在关于施琅功业的注释中,他评论道:“其时虽有不少人指施琅为汉奸,但于中华民族而言,其力排弃台之议,保全此一片土地于中国版图,功劳也可说极大。”[7]1949在关于韦小宝《尼布楚条约》签名的注释中,又跟当时的部分史学家开了个玩笑:“条约上韦小宝之签字怪不可辨,后世史家只识得索额图和费要多罗之签名,而考古学家如郭沫若之流仅识甲骨文字,不识尼布楚条约上所签之‘小’字,致令韦小宝大名湮没。”[7]2051类似的注释显出强烈的小说家言的色彩,也更能吸引普通读者的眼球,但若站在纯文学的角度,似乎有点遗憾。
(三)细道本旨,以后记阐述创作思想
从1975年1月到1981年6月,金庸为自己的12部作品撰写了后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和《越女剑》没有后记。表面上看,后记内容很散,包括创作缘起、修订过程、作品评论、历史考证、人际交往和人生感悟等,但综合来看,作者着力阐述的是自己的创作思想。虽然比起小说创作和社评写作,金庸的理论探究要逊色很多,但他至少触及了武侠小说的定位和人性的刻画两个于武侠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并且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关于武侠小说的定位,金庸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功能。在娱乐之外,它能否承担其他的功能?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武侠小说之前很少被理论界重视,在香港和科幻小说一起与“框框杂文”、爱情小说并称“三通”。前文述及,白羽一度为涉足武侠小说写作而痛心疾首。如果金庸本人也持这种看法,那么应该不会有后来对旧作的大规模修订。毕竟,单纯从娱乐角度来看,连载版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金庸在这方面非常在意纯文学领域的评价,换言之,定位武侠小说娱乐之外的功能不是武侠小说领域单方面的事,纯文学领域的认可更有象征性意义。因此他特意提到了陈世骧对武侠小说的认可,并附后者的来函(“印刷版”加“手写版”)作为证明:“我的感激和喜悦,除了得到这样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因之增强了信心之外,更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8]2125二是风格。武侠小说应当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金庸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一方面,他尊重传统,并且延续某些传统的手法:“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像样。”[8]2125为此,他专门翻阅王力的《汉语诗律学》补课,修改《书剑恩仇录》的回目,又用柏梁台体写了40句古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用五首词作为《天龙八部》的回目。在《射雕英雄传》增加说书作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9]1620。另一方面,他也很重视现代手法的引入。《射雕英雄传》“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当时只想,这种方法小说里似乎没人用过”[9]1620,字里行间不难感受到金庸对这种引入的得意。《雪山飞狐》没有一个肯定的结尾,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金庸的看法是“有余不尽和适当的含蓄,也是一种趣味”[10]245,在通俗文学领域非常现代。
基于对武侠小说定位的信心,金庸在人性刻画方面也试图超越通俗文学的范式限制。他将人性放在创作的首位。一般的武侠小说着力塑造的都是英雄豪杰,往往通过“巧” “奇”两字推动情节发展,但金庸认为应当把重心放在人性上:“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中心所在。”[4]658相应地,对于因为“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9]1619所以比较受到欢迎的《射雕英雄传》,金庸在艺术上并不是很满意。他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7]2132当然,对不完美的追求也不是刻意的。他又提出:“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11]1672性格的可能根本在于有现实基础,比如“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这样的人物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7]2132。金庸对人性刻画的思考涵盖性格与情节的关系、性格的复杂性和性格的现实依据等方面,实质体现了他对武侠小说经典化的追求,也可以说是自我经典化。正如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提到的:“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的价值。” “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会有,大概在别的国家都会有。”[12]1690这样能够跨越时空的典型人物,不正是经典小说的特质之一么?
(四)把玩学术,借附录提升作品层次
在《金庸作品集》中还有五篇附录,分别是《碧血剑》后的《袁崇焕评传》,《射雕英雄传》后的《成吉思汗家族》和《关于“全真教”》,《越女剑》后的《卅三剑客图》,以及《鹿鼎记》后的《康熙朝的机密奏折》。这些附录都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和考证性,除《卅三剑客图》外,皆以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的真实相映照,使得虚构的故事具有了史传的色彩,增加了作品的历史文化含量。同时,也要注意到,附录中的内容故事性更强,思辨性稍弱,和专业的历史研究毕竟不同,可视为一位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素养的小说家把玩学术的成果。
五篇附录中,《卅三剑客图》尤其值得分析。它以现代的视角和语言介绍33位剑客的故事,包括图33幅(任渭长所作),序1则,介绍33则,写于1970年的1月和2月,登在《明报晚报》创刊的最初两个月。33则说明中引出很多与小说经典桥段有渊源的古代小说和历史作品,趣味横生,意旨隽永。比如庾信有诗“授图黄石老,学剑白猿翁”,金庸“在《越女剑》的小说中,也写越女的剑法最初从白猿处学来”[4]732。白猿的形象一直流传到《绿野仙踪》和《蜀山剑侠传》,读者自然不难想到张无忌的《九阳真经》也是从白猿腹中取出的。绳技实为“群众催眠术,是一门十分危险的魔术。如果观众之中有人精神力量极强,不受催眠,施术者自己往往会有生命危险”[4]746,这又与丐帮彭长老的“摄心术”和杨过的“移魂大法”异曲同工。《唐书•高骈传》言高骈“不但是射雕英雄,而且是射双雕英雄”[4]808,自然让人想起郭靖。需要注意的是,说明不仅关注金庸本人创作与武侠传统的关联,更关注现代武侠小说的历史渊源。他将《虬髯客传》定位为“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4]735,认为其中的很多特点均在现代武侠小说中有所体现。《卅三剑客图》是中国版画艺术史上的重要作品,任渭长之画与蔡容庄之雕强强联合,使得以唐传奇为主的文学作品中的剑客形象跃然纸上。但世易时移,图画背后的故事却渐渐为人遗忘。金庸由画入文,详加考证,却在不经意间接通了现代和古代武侠小说的想象,从创作者的角度勾勒出了武侠小说发展的历史脉络。
三、自注和自我经典化的原因分析
通过图片说明,在小说的意境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意境之间、小说的环境和历史的环境之间构建桥梁,通过注释深化小说的意蕴和道出虚构的渊源,通过后记梳理自己的创作思想,给予武侠小说权威的定位,通过附录增加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金庸的自注系统地推动了个人作品的经典化进程,对提高武侠小说文类的地位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般读者可能不会很在意这些自注的内容,但其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比如读文和读图的关系、小说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武侠小说的定位和人物刻画、武侠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后来学者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关注。之后,金庸的小说进入大学讲堂,进入文学史,经典色彩逐渐浓郁。在新修版的《金庸作品集》中,自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见出金庸对这一形式的看重。金庸在旧版中已有自注,但并不多,自明河版起始成规模。自注源于自我经典化的预期,因此,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探究金庸如何产生经典化的预期并选择了自注这一形式,应当是有一定学术意义的。
(一)经典化预期的产生
连载期间,金庸大部分武侠作品的主要功能在于保证其所创办的报纸和杂志的生存和发展,娱乐性很强,既娱乐自己,又娱乐读者。但娱乐性之外的评判,渐渐对金庸产生了影响,使得他对自己的创作有了更高期待,促使他通过修改将自己的作品经典化。
一是来自武侠同行的影响。这里要提到两个人,一是梁羽生,一是古龙。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发表了《金庸梁羽生合论》。考虑到与梁羽生多年的共事关系,以及文章中对金庸个人和武侠小说文类的深刻认识,相信金庸不难想到作者是谁。其中一些观点对金庸影响很深,十年修订期间,他多次通过自注予以回应。比如梁认为金庸小说有时“为情节而情节”[13]320,《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即存在前后不照应的问题。金庸在《雪山飞狐•后记》中回应:“《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虽有关联,然而是两部各自独立的小说,所以内容并不强求一致。”[10]248梁认为金庸在刻画人物时存在“由于是非不分而消失艺术感染力”[13]325的问题,举的是萧峰的例子。金庸在《天龙八部•后记》中没有直接回应,但附上了著名学者陈世骧寄给自己两封信的手稿,其中是对《天龙八部》乃至金庸小说的高度肯定。至于梁对金庸古诗词方面的批评,金庸在自注中的回应就更多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从修订《书剑恩仇录》开始即翻阅王力的《汉语诗律学》。不能说梁的批评让金庸感到不愉快,毕竟比如关于诗词的批评金庸接受并且努力改正,而且梁谈到的情节、人性、侠义等问题都是武侠小说文类发展的肯綮,但两人创作方面的分歧实际上等于为金庸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自己的角度。也不能说梁的批评给予了金庸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动力,但在大规模的修订之后,金庸在武侠小说领域中的地位的确超过了梁羽生,不再是“合论”的对象了。如果说梁羽生直接的批评为金庸提供了重新审视自己的镜子,古龙则以创作给予金庸修订作品的动力。古龙虽是后辈,但身在台湾的他当时已经在香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多情剑客无情剑》1969年间开始在《武侠世界》连载,翌年年初金庸在介绍《卅三剑客图》时即已有这样的评论:“这十六七岁的瘦削少年名字叫做飞飞,真是今日阿飞的老前辈了。”[4]749从中可见金庸对古龙的关注程度之高。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在《明报》连载结束,接续的作品是古龙的《陆小凤》。《陆小凤》在《明报》连载到1975年春,是古龙的主要代表作。
二是来自纯文学的影响。通俗文学向夙难登大雅之堂,在文学研究领域,往往更多是批评甚至批判的对象,而不是研究的对象。到金庸,情况发生了变化。陈世骧对《天龙八部》的评价是“实一悲天悯人之作也”,“书中的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魑魍与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8]2127他认为金庸的小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不断克服文类与材料之困难”。[8]2129陈世骧的信中没有关于武和侠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认为金庸的小说至少克服了武侠小说文类的限制,这不但对金庸,而且对武侠小说文类,都是一种鼓舞。夏济安和刘绍铭也肯定过金庸的创作,前者曾有“金庸一出,自己不必开启打算已久的武侠小说创作”的戏言,虽是戏言,也含认可;后者则指出戏剧对金庸创作的影响,认识精准。对于这些于武侠小说而言难得的认可,金庸都在自注中予以记录。相对而言,1969年香港《纯文学》杂志对金庸的访问更有象征意义。这份杂志最初由林海音创办于台湾,香港版由作家王敬羲负责。采访金庸的现场,策划林以亮、记录陆离、列席王敬羲都可说是来自“纯文学”领域。访问中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金庸的小说,已经是文学作品了呢,抑或不是?”[14]318从访问的语境来看,在林、陆、王的意识里,一流的通俗小说才算得上文学作品。这里的“一流”除了“写得好” “言之有物”外,更有一个“超越它(文类,作者注)本身的限制”的标准。当然,这个标准不好界定,但“将来写文学史的人,总会知道的”[14]320。金庸本人坦言:“至于小说,我并不认为我写得很成功”,“将来有机会,真要大大的删改一下,再重新出版才是”。[14]311-312陈世骧、刘绍铭和夏济安对金庸的评价更多带有印象式色彩,《纯文学》杂志对金庸的访问实质上涉及了武侠小说的纯文学化问题,这对金庸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吸引。
三是来自传播的影响。这里主要谈两方面,聚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是跨文化传播。通俗文学作品被译成他国文字,实现跨文化传播,在金庸之前并不多。金庸本人曾提及,《射雕英雄传》被“译成了暹罗文、越南文、马来文(印尼)”[9]1619,《雪山飞狐》也“有英文译本,曾在纽约出版之Bridge双月刊上连载”[10]248。金庸作品在印尼的传播一度引起印尼语文当局的抗议,因为诸如“夜战九方藏刀”式的表达,用印尼语翻译实在困难,只好创造新字,“有碍印尼语文之推行也。”[15]如此的影响力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异域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对于有着强烈的历史政治情怀、常年在《明报》写社评的金庸来说,应当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更加完善的。二是华文地区传播。金庸的小说当时不但在香港大受欢迎,在海外华文地区也十分风靡。陈世骧到日本讲学,写信求金庸寄送《天龙八部》和《神雕侠侣》各一套[8]2128,夏济安到美国访学,托人每天从香港航空邮寄刊载金庸小说的《明报》。“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成立了金庸学会。”[14]314林以亮所言的“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14]298虽有夸张成分,但也距离实际不远。对海外华人而言,金庸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内容以及中国化的文字表达,具有相当的亲和力。这也给金庸带来了压力,“继续写下去,很困难”,“很难再想出一些与以前不重复的人物、情节”[14]314。在新作难为的情况下,修订、完善旧作似乎是更自然、更好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当时金庸的作品在大陆和台湾都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正式出版,在其作品已经产生很大影响的背景下,这种限制也许于作者而言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认可,促使他将作品打造到为后世文学史家认可的程度。
(二)自注的选择
来自同行、纯文学和传播的影响,兼以自身的艺术追求,促使金庸通过修订的形式推动作品的经典化,提高作品的传播质量,提升它们在文学领域内的影响力。修订的核心是内容的增删和改写,但再多的增删和改写,也无以改变作品武侠小说的身份。既要是武侠小说,又要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这真是个问题。你可以这么写,同时也要读者接受才可以”[14]319。换言之,处于香港商业文化的大环境,金庸作品的经典化不能以牺牲一般读者的认可为代价。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金庸真的将纯文学的内核植入武侠小说,他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研究价值。对金庸来说,吸引一般的读者已经不成为问题,吸引文学批评家的专业介入(无论是陈世骧的印象式批评还是林以亮的交流式采访)才是更有意义的追求。但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并不容易。笔者在网上搜索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从1955年到1970年,并没有发现关于金庸的研究成果。金庸当时虽然名气很大,因为武侠小说、《明报》月刊也与许多一流的文化人物(比如钱穆、余英时、牟宗三)有交集,但关于他的作品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经典化的进程需要权威的阐释,而在这些条件不充足的情况下,自注成为自然的选择,金庸在其中下了很大的功夫。自注总体上围绕着历史进行发挥,随处可见考证,所提到的问题多有强烈的学术性和思辨性,其实并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更多是为了吸引文学批评家的关注。自注以与小说迥异的语体风格,从历史(故事所处的历史和武侠小说发展的历史)的角度与小说形成文本“共建”的关系,拓宽了小说的阐释空间。“明河版”之后,关于金庸的专门研究逐渐增多,其作品的经典化顺利推进,自注中提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小说与历史的互动、武侠小说的定位和人性刻画)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但同时也要看到,作为对中国古代文史著作自注传统的延续,金庸的自注存在的一些问题更值得关注。一是部分自注至今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随文注释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现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但相关的研究不多。除《袁崇焕评传》外,学界对附录的关注也很少(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中用《卅三剑客图》作为插图,不经意间与金庸形成呼应)。二是部分自注存在过度阐释的问题。比如《碧血剑》的后记提出小说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5]864,《侠客行》提出“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中心所在”[4]658,都属于过度阐释,背景是袁承志形象塑造的不成功和对孪生兄弟作为情节动力的不满意,想将小说阐释成符合经典化期待的状态。这种过度阐释其实在纯文学领域同样存在,值得深入分析。三是部分自注存在撰述不严谨的问题。《袁崇焕评传》一些表达过于主观,如称努尔哈赤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5]758,《书剑恩仇录》关于徐灿的考证也出现错误,类似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庸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功力毕竟不同于写小说和社评,并不符合他对自我的经典化期待。简言之,自注虽是自我阐释,但因为牵涉甚广,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刘知几.史通[M].姚松,朱恒夫,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252.
[3]白羽.话柄[M].天津:天津正华学校,1939.
[4]金庸.侠客行[M].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77.
[5]金庸.碧血剑[M].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75.
[6]金庸.书剑恩仇录[M].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76.
[7]金庸.鹿鼎记[M].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81.
[8]金庸.天龙八部[M].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78.
[9]金庸.射雕英雄传[M].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78.
[10]金庸.雪山飞狐[M].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76.
[11]金庸.神雕侠侣[M].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76.
[12]金庸.笑傲江湖[M].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80.
[13]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M]//费勇,钟晓毅.三剑侠传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4]金庸.寻他千百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5]柏杨.武侠的突破[M]//柏杨,林清玄,舒国治,等.诸子百家看金庸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87.
(责任编辑:石 娟)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栏目特邀主持人:曹惠民
主持人简介:曹惠民(1946—),江苏南通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三度应聘赴韩国、台湾任专任客座教授。曾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等,应聘美国文心社顾问、日本华文文学笔会特邀顾问等。著有《边缘的寻觅—曹惠民选集》《出走的夏娃—一位大陆学人的台湾文学观》《他者的声音—曹惠民华文文学论集》《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主编《台港澳文学教程新编》《1898—1999百年中华文学史论》《阅读陶然》《台港澳文学教程》,另合著、参编10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比较文学史和国家级高校教材。1980年至今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新、马、泰、菲、印尼、韩、英、美、加等国几十种报刊发表论文近200篇。
主持人语:大陆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或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有37年的历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就连素以“苛评”“铁嘴”著称的著名批评家孙绍振教授,也“不禁惊讶其规模之大和水平之高,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二三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过,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草创时期,学科建构的定位似乎有了普遍的自觉。”(《刘登翰〈海峡文化论集〉序》)
华文文学这种“学科建构”的“自觉”自有多方面的表现,论题的不断开拓,研究的渐次深入,作者群的持续扩大,当属其题中应有之义,从本刊本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栏的几篇文章。虽然华文文学的研究边界至今也还有不同看法,比如外籍作家学者的华语写作,属不属于世界华文名为“世界华人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还是“华语语系文学”,抑或是“汉语新文学”?亦尚无定论。,越界跨国的华文文学这片文学的旷原就显出了她非同寻常的魅力,至今仍有很多课题在等待着研究者面对与深耕。
暨南大学是国内研究海外华人华侨、华语文学的重要基地,学术梯队也相当整齐,后起之秀池雷鸣博士对旅居加拿大20多年的张翎的小说代表作《金山》的评论,就是一篇富有新意的论文。论者以文化“涵化”这一概念介入加华文学的研究,又以人物形象的分析贯穿全文,对《金山》作出了精彩的解读。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既有话题场域引进新的话语,颇具别开生面的原创意识,给人启示多多。文化“涵化”的视角还值得、也可以进一步拓宽其覆盖领域。
韩国许世旭教授作为一位外籍人士,是中国以外极少数能娴熟地用华语写作的重要个例。他年轻时曾留学台湾多年(1960—1968),取得中国文学硕士、博士学位,中国传统文化学养深厚,华语创作与中国文学(涵盖古代、近代、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双管齐下,著述甚丰。韩国朴南用博士的论文在梳理许世旭这两方面成就的基础上,以他的《中国文学纪行》一书为中心,尤其突出了从文学地理学的学理视角观察许世旭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每有中肯、切近的见解,行文看似漫漶,其实,“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钱锺书《读〈拉奥孔〉》)。该文对许世旭学术理念的探讨,很值得关心华文文学发展的国内外同行了解,以便进一步拓展研究。
马来西亚华人女作家朵拉的创作富有创造力,常常能力避俗套,别辟蹊径,显示了她对人性和生活的自得的理解。论文在已有的朵拉研究的基础上,发掘出其小说的深层内涵,中心突出,条理清晰,诠释有理、有据、有力。此文的研究对象是马华作家,论文作者徐榛、郑有轸两位80后学术新人却来自中、韩两国,非常形象地佐证了华文文学及其研究的跨国界、跨族群乃至跨文化的重要特征,其间还有不少有待展开的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所论及的三位华文作家都曾造访过苏州,笔者也以“苏州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名义在苏大接待过他们。就华文文学研究而言,苏州虽然没有闽、粤或京、沪的地缘、语缘或学术中心的优势,似处“边缘”,但她开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的现代姿态,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心保存与良好传承,都对异邦人士(包括华语作家学者)别有一番引力。可以说,在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历来重视中外交流的苏州还大有用武之地和挥洒的空间。希望《苏州教育学院学报》本期本栏的设置,将带动本地华文文学研究开创出新生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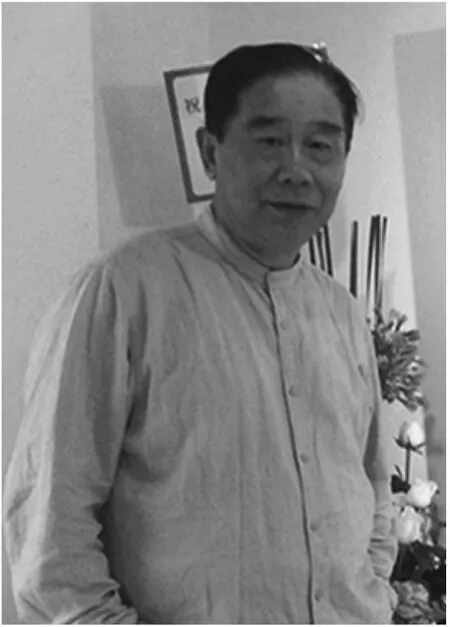
An Analysis of the Self-canonnization in the Self-notes of Jin Yong’s Wuxia Novels: A Discussion Based on Jin Yong Collection (Minghe Edition)
ZHU Ling-jun
(Journal Department, Qingdao Technical College, Qingdao 266555, China)
Abstract:The revision from 1970 to 1980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self-canonization process of the Wuxia novels by Jin Yong. In addition to the increase, deletion and revision on the text, the other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of Jin Yong Collection (Minghe Edition) is the appearance of systematic self-notes. His self-notes carried on the writing tradition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and historic works and contained the modern thoughts and ideas. It widened the interpretation space of Jin Yong’s novels effectively and became one important self-canonization method.
Key words:Jin Yong;Wuxia novels;“Minghe Edition”;Jin Yong Collection;canonization
作者简介:朱令军(1978—),男,山东海阳人,编辑,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青岛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度人文社科类立项课题(13-B-4)
收稿日期:2015-05-20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5-0044-07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I2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