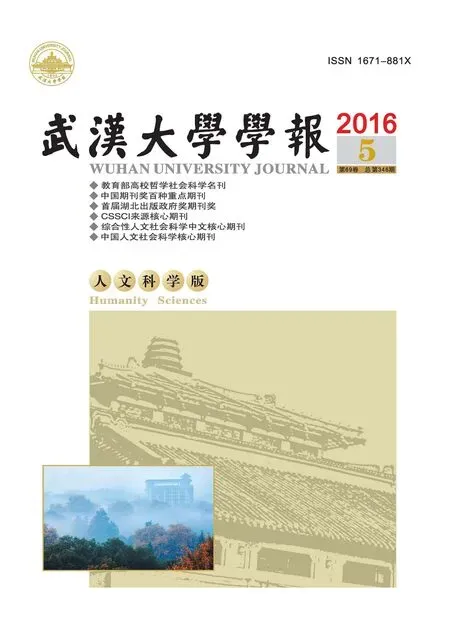车舆行进与生活政治
——以《礼记》为中心的考察
朱 承

车舆行进与生活政治
——以《礼记》为中心的考察
朱承
在《礼记》中,有大量涉及车舆、行进的礼仪安排,从中可以看出礼治传统中日常交通所承载的秩序关怀。贵族所使用的车舆往往体现着政治生活中的身份等级差异,车舆马具等成了政治身份差别的标志物。在日常的徒步行进中,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也有特定的礼仪要求,尊卑之别、长幼之序能从人们的道路行进中得到体现,道路行进成为社会秩序展现的场域。在现代社会里,交通问题依然体现着“生活政治”,传统的身份等级制虽然还有一定余绪,但不再是影响交通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公共理性以及现代性价值主导着现代交通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秩序。
礼记; 车舆; 礼治; 身份等级; 生活政治; 交通礼仪
车舆、行进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事情之一,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远或近,或利用交通工具或步行,或水或陆或空,或独行或结伴同行,或先或后,或疾或徐,这些都是司空见惯之事。但即便是这些寻常事,一旦放到人群社会中去考量,除了其自身的去远拉近的基本功能性意义外,往往也会成为政治、价值或秩序的表现。从大的方面看,类似于“车同轨”式的国家政策行为,自然是显在的政治行为,对共同体所有人的生活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小的方面看,个体的交通工具与行进表现,比如说,什么人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什么人乘坐的交通工具上可以有什么样的装饰和仪仗,在共同行进中什么人走在前面、什么人走在后面,行走时需要注意什么事项等等,在具体的活动中,除了要考虑安全、便捷等因素外,还需要结合礼制风俗等考虑嘉益分配、爵秩等级的因素,交通工具的资源分配、共同行进中的次序、特殊场合的行走仪态,往往涉及政治权力和身份秩序。在《礼记》的文献记载中,有大量涉及车舆、行走的礼仪安排,既能使我们了解古代交通生活的面貌,也能从中看出礼治传统中交通所承载的价值及其秩序性关怀。
一、 车舆礼仪与生活政治
车舆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战争、政务、礼仪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往往称“黄帝”或者“奚仲”制车*刘永华:《中国古代车舆马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页;葛志毅:《“奚仲作车”考论》,载《古代文明》2010年第3期。,因无确证可考,关于车之肇造者的考辨只能源于一些语焉不详的历史记载。但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一般都将制造交通工具的贡献算到圣人头上,以此增加圣人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所谓圣人“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易传·系辞下》)可见,“制牛马而用之”(《荀子·王制》),利用畜车来为人类交通运输提供便利,是圣人对生活文明的贡献,因此可以增加圣人的合法性。虽然从文献上看,中国古代车的发明权归属于谁这个问题不甚清楚,但随后而来的围绕“车”形成的礼仪却比较明确。
《礼记》中对古代祭祀时的车舆礼仪有过记述:“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骆马黑鬣,殷人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骍刚。”(《礼记·明堂位》)有虞氏以及夏商周时代的天子车马及其装饰都有明显的不同,这反映的是时代礼仪的不同,也说明每个时代的车马礼仪较为确定。当然,时代的礼节差异往往与生产技术、审美风尚等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天子、君主的车马一定要明显区别于其他人,一定是要具有独占性,以显示天子、君主的特殊权威。在《礼记》中,叙述车舆马具的差别主要是要运用到标志身份等级的差异上,也就是说,《礼记》中的礼仪规定,更多的是将车舆马具的功能从运载工具转换到礼仪制度、身份等级象征。在上述引文中,“路”(后世又称“辂”)是“乘车”中车主等级最高的,是天子的“乘车”,有时候天子也以之来赏赐有功诸侯。天子的路车之外,对于其他身份等级的人所用之车,也有专门名称“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周礼·春官·巾车》)从高等级的夏篆、夏缦、墨车,到低等级既载人又载货的栈车、役车,各有其特殊的称呼,从形制到名称,车舆马具与其他生活用品一样,是区分社会上各类人身份等级的重要载体。
在《礼记》中,车舆马具等关涉交通的用具和其他生活场景中的用具一样,往往用数量上的多少来标志政治身份的差别。在贵族群体中,为个人配备的车马仪仗数量上是依据身份等级来予以规定的,以地位尊卑来安排数量上的差别,特别是参加政治活动时尤其要遵守这些数量规定,如在朝觐祭祀时,不同等级的人的副车数量要遵守礼制,“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礼记·少仪》)郑玄注曰:“此盖殷制也。《周礼》贰车,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数也。”*《礼记·正义》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99页。按照爵秩等级予以明确规定,这即是一种差等的车舆秩序。丧葬礼仪中也需要注意在车马上的身份差异,“君之适长殇,车三乘;公之庶长殇,车一乘;大夫之适长殇,车一乘。”(《礼记·檀弓下》)从礼仪的角度,各种典章制度对不同身份等级的车舆有所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也有很多人僭越礼制,享受本不该享有的车舆待遇。在传统儒家看来,正是这种僭越败坏了礼乐制度,造成了“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
按照礼制,不仅在车马数量上能彰显身份差别,车马的装饰上也是如此。“君羔幦虎犆;大夫齐车,鹿幦豹犆,朝车;士齐车,鹿幦豹犆。”(《礼记·玉藻》)国君的齐车,麝皮为足踏、虎皮为缘饰,大夫的齐车和朝车则是鹿皮为足踏、豹皮为缘饰,强调用装饰的不同来区别身份等级。对于国君而言,在不同的场合,旗帜装饰也应有所不同,让观者能够一目了然,如国君打猎所用武车,要旌旗招展,巡守用德车,旌旗须要垂敛,“武车绥旌,德车结旌。”(《礼记·曲礼上》)这就说明,车舆的旗帜还发挥了信号的作用,用以区别政治活动的指向与目的。当然,对车的装饰问题,《礼记》中也有例外性规定,比如说在国家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对于车马就不应该装饰,如,“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縢,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屦,马不常秣。”(《礼记·少仪》)不仅不能装饰,连“造车马”也应该有所收敛,“年不顺成,君衣布搢本,关梁不租,山泽列而不赋,土功不兴,大夫不得造车马。”(《礼记·玉藻》)又如,“孔子曰:‘凶年则乘驽马。祀以下牲。’”(《礼记·杂记下》)当国家政治、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就要限制车马的规格,通过节俭装饰、减少数量等手段,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因此,车舆等的打造及其装饰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化,礼制也彰显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
众所周知,驾驭车马的“御”是传统六艺之一,是古代士人需要掌握的生活技巧。从“礼”的角度来看,传统“御”术不仅是对技术的要求,也还包括对“礼仪规范”的要求。在《礼记》中的记载中,驾车特别是为君主驾车有着严格的规矩。如《月令》中对天子的驾乘也有着明确的仪礼规定,“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礼记·月令》)“朱路”“赤骝”是天子的仪仗,与居所、服饰是配套的,标明天子的威仪。在驾车的具体技术性程序中,也有一套为君主定制的内容。在礼制安排中,为君主驾车,与其说是为了交通功能,不如说更像是一场礼仪表演,有着一整套程序性的完整安排,并以此来强调君主的权威性和礼仪秩序的重要性,既考虑驾车的安全、便捷,也考虑礼仪程序。《礼记》中记载:“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已驾,仆展軨、效驾,奋衣由右上取贰绥,跪乘,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左右攘辟,车驱而驺。至于大门,君抚仆之手而顾,命车右就车;门闾沟渠,必步。”(《礼记·曲礼上》)在这个一套完整的程序中,将驾、已驾、途中,对御者都有着较为细致的规定,一方面是技术性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礼仪性的要求。如,“凡仆人之礼,必授人绥。若仆者降等,则受;不然,则否。若仆者降等,则抚仆之手;不然,则自下拘之。客车不入大门。妇人不立乘。犬马不上于堂。故君子式黄髪,下卿位,入国不驰,入里必式。君命召,虽贱人,大夫士必自御之。”(《礼记·曲礼上》)驾驭技术的要求是为了安全和顺利,而驾驭礼仪的约束则是为了维护权威与秩序。可见,在《礼记》中,驾驭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有价值观念蕴含于其中,驾驭要体现权力的威仪和等级的秩序。
驾驭有一套规矩和要求,乘车的人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和礼仪。《礼记》围绕国君的乘车,做了很多礼仪性规定。就国君而言,不能与同姓共同乘车,如果和异姓同车,则不能同服,“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礼记·坊记》)对国君的同乘人做了排斥性的规定,尤其是不能与同姓人共乘。“同姓”是指那些具有继承人资格的同宗,郑玄注曰:“同姓者,谓先王、先公,子孙有继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则无嫌也。”*《礼记·正义》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59页。“不同服”是指同车的同乘之人不穿同样的服饰。“同姓不同车”的好处是防止同宗之人僭夺权力的可能性,“不同服”是为了人们明确知道谁是真正的国君,国君可以根据时令改变而变化,但同乘之人则需要穿着朝服,不过,这种“不同服”的情况在战争状态下是有所改变的,“仆、右恒朝服,君则各以时事,唯在军同服尔。”*《礼记·正义》下册,第1959页。大抵是为了安全考虑。国君在乘车时,同乘之人的选择以及同乘之人服饰的规定,除了人身安全之外,还要考虑政治安全、等级礼仪等,从而具有了附加的政治意义。另外,国君在车上据车轼行礼时,大夫要下车以表示敬意,士人见到大夫据车轼行礼,也应下车示敬,非如此不成差等式的礼仪,“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记·曲礼上》)国君乘车经过宗庙,必须下车,遇见用作牺牲的祭牛,要行轼礼,对于士大夫而言,更应如此,乘车经过国君门口、看见礼车用的马,都必须要行恰当的礼,以表示对车马之主人的尊敬,“国君下齐牛,式宗庙。大夫士下公门,式路马。”(《礼记·曲礼上》)另外,关于乘车时的礼仪,还有很多特别的具体要求,如,“苟有车,必见其轼。”(《礼记·缁衣》)“礼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车不式。”(《礼记·玉藻》)“仆于君子,君子升下则授绥;始乘则式;君子下行,然后还立。乘贰车则式,佐车则否。”(《礼记·少仪》)“车上不广咳,不妄指。立视五巂,式视马尾,顾不过毂。国中以策彗恤勿驱。尘不出轨。”(《礼记·曲礼上》)“介者不拜,为其拜而蓌拜。祥车旷左,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左必式。仆御、妇人则进左手,后右手;御国君,则进右手,后左手而俯。国君不乘奇车。”(《礼记·曲礼上》)“执君之乘车则坐。仆者右带剑,负良绥,申之面,拖诸幦,以散绥升,执辔然后步。”(《礼记·少仪》)对于乘兵车,也有明确规定,“乘兵车,出先刃,入后刃,军尚左,卒尚右。”(《礼记·少仪》)……从上所引,对车上的行礼、坐与立、左右方位、佩饰等等,都有着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足见在乘车礼仪上的繁琐仪节。这些仪节要求人们端庄、恭敬、规范,并以此来保证权力秩序、身份等级的全面展现,使人从外观上就能得到明确判断从而心生礼敬之意。
不仅国君、士大夫应该遵守驾乘之礼,连对待国君使用的“礼车”和“路马”,也要坚持驾乘之礼,前文已述,“路马”是天子礼车的马,是天子仪仗的重要组成部分,“乘路马,必朝服载鞭策,不敢授绥,左必式。步路马,必中道。以足蹙路马刍,有诛。齿路马,有诛。”(《礼记·曲礼上》)因为“路马”象征着天子的权威,因此《礼记》里规定,不能驱赶“路马”,不可授绥与人,牵行“路马”必走大道,甚至不能用脚踢“路马”的粮秣,也不可估计“路马”的年龄,总之,对待天子之车马仪仗,应该有着敬畏之心,必要时应该如同对待天子本人一样。对君主车马的礼敬,是“尊尊”之礼义的延续,更是对权力膜拜的具体体现。在“万物一体”的视角来看,我们对作为一种生物的“马”应该有同情之心,然而即便如此,那也应该是对普遍性生物的同情,而非对仅属于某个群体或个体的所有物的礼敬。因此,对君主车马的特殊对待,只能说明是对权力等级的固守和信念,这是礼仪秩序的要义所在,值得我们反思。
车舆制度作为先秦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与等级上的爵命制度密切结合。车舆制度和其他生活领域中的礼仪制度一起,构筑起古代贵族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既具有生活文明的意义,也具有政治文明的意义,后世历代也在有所损益的基础上予以延续。《汉书·成帝纪》上说:“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324页。《汉书·谷永传》中也说:“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制度。”*《汉书》第11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3467页。对于车舆不能逾制的要求,虽然在具体生活中未必如此,但在历代史书中的《舆服志》中还是多有记载,构成了历代典章制度的内容。后来出现的肩舆制度,也是参照古礼中的车舆制度,不同官阶、身份的人所乘肩舆也不能僭越,要按照国家根据礼仪制定的制度来予以安排,用以彰显身份等级上的差异,如明朝政府就规定:“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明史》卷六十五,第6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1611页。历代类似于皇帝、皇族、百官所乘交通工具的形制规定非常多,不胜枚举,名目和典章虽然繁多,但其目的大致一律,那就是为了明确等级、职级的差异。这种用外在显现的方式标示人的身份差异,正是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则,车舆制度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场域。
二、 行进先后与身份地位
如果说,车舆制度是有工具性载体的交通礼仪,那么徒步行走的礼仪则是不依托工具载体的交通礼仪,更具有直接性,也更为多见。正如现代人的道路行走需要遵守交通法规一样,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进在很多时候需要遵守礼仪规则,使自己的道路行进、朝堂进退合乎礼仪,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我们知道,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未必严格地按照礼仪规定来安排最具日常性、随意性的行走,但从《礼记》等典籍中还是可以看到与“行进”相关的礼义精神,这种礼义精神虽不是时时、人人都得以贯彻,但所蕴含的秩序原则还是值得注意的。
居处行走是正常人最为寻常的举动,居处有礼、进退有度,按照一定的礼仪来处置自己的举手投足,这是文明人在文明社会的应有品质,也是社会生活秩序的重要表现。《礼记》中关于这一类的规定也很多。以人间秩序的集中代表者“天子”的举止为例,就特别生动的说明了举止恰当对于秩序的意义,如:“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礼记·经解》)天子作为神圣意志在生活世界中的最高代表者,他的居处、进退不仅关乎个体的形象,还是礼仪的典范,百官、万事都从天子居处进退的合宜中,获得合理性、合序性。因此,天子的居处行进就不再是个人事务,而变成了政治事务。另外,为了彰显天子的权威与尊贵,在公共活动的时候,天子的出场应该有象征威仪的“警示”之声,而且也要在众人的恭候和瞩目中出场,如,“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礼记·文王世子》)而且,天子、国君不能不顾行走的礼仪,“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礼记·郊特牲》)由于国君拥有其治下所有的国土,因此国君到了臣子家中,臣子不应将自己当成主人并以客礼对待君主,国君应该从象征主人身份的东阶登堂。天子是天下共主,对于诸侯、臣子自有无上的威严,特别是在朝觐的场合,尤其要注重天子的行走礼仪,如果出现“下堂而见诸侯”那样的“失礼”场景,就表示天子的权威弱化了。而天子的失礼,将损害到天子威仪,祸及权力尊严,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影响甚远。
诸侯的居处行走也有一套礼仪,如在诸侯燕礼中,诸侯处于最高尊贵的位置,其行动也要显示其独特的尊贵,其他人都要来维护这种尊贵,“诸侯燕礼之义:君立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大夫皆少进,定位也;君席阼阶之上,居主位也;君独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适之义也。”(《礼记·燕义》)在国君饮宴群臣时,国君与卿大夫的行进、居停、方位,其核心只有一个,在国君出现的场所,其尊贵地位无人与之相匹敌,他是独尊的,这种独尊不仅是实质上的,也要体现在形式上。礼仪形式是保证实质性权威的途径。那么,用什么来保证这种形式得以不断巩固?在礼治原则下,只有繁琐的礼仪规定来保证这种权威,让人们通过规范自己的行止来强化对权威膜拜的心理。
大夫、士等人在特定的场合下,也有特定的行进礼仪予以规定。如在士、大夫等同为臣属的人员之间,按照等级,有一定的行进礼仪,“士于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于尊者,先拜进面,答之拜则走。”(《礼记·玉藻》)士比大夫的爵等要低,因此,士不能从门外拜迎大夫,只能在大夫离开的时候拜送。士去拜见卿大夫等位尊于自己的人的时候,要让尊者等在门内,自己在外面先行拜礼,如果尊者还礼,士还要避让以表示谦恭。又如,等到大夫退休的时候,国家应对给予礼仪待遇,很重要的一点礼仪待遇就体现在交通上,可以获得协助行走又象征身份的拐杖,还可以安车代步,行走四方,“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礼记·曲礼上》)这种待遇,是国家的礼仪规定,也是一种政治待遇,所谓“礼遇”。士、大夫等国家官吏层面的权贵者,虽是同僚,但因爵等有差异,因此即使在没有国君出现的场合,其行进也要按照尊卑等级予以礼仪安排,否则尊卑等级的秩序就不能贯彻到底。士、大夫等最为重要的行进礼仪是在朝堂上或者出入君主居所时的规矩,“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礼记·曲礼上》)士、大夫进出国君大门,得从门橛的右边走,而且不能踩着门槛类的门限,以示对君主的尊敬。《论语》中也曾记载孔子在朝堂上的举止行进状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试分析之:“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这里描绘了孔子在朝堂上行进的谨慎、恭敬之状态,特别是对具有国君独占性标示的位置格外恭敬,不走国君出入的“中门”,经过国君座位的时候面色端正、步履快疾,甚至也大气都不敢出,朱熹在解释时说道:“君虽不在,过之必敬,不敢以虚位而慢之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18页。而当走出来后,则神情放松、脚步轻快。这段描述很有代表性,展现了类似于孔子这样的士大夫阶层人士在朝堂上行进的礼仪和神态,朱熹称之为“在朝之容”。“在朝之容”反映了士大夫遵照礼仪规范在朝堂上的举手投足表现,将私人的举止习惯按照规范性要求予以校正,从而符合礼仪要求,并表达对于君主的恭敬,显示君主的至高权威性,李泽厚先生在讨论《论语》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将此称之为“来自父系家长制所建立的对氏族部落首领即部落国君的敬畏礼仪”,是“原始巫术礼仪的制度化理性化后之产物”*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也就是说,在朝堂的行止礼仪被制度化,以此实现对君主和最高权力的敬畏,是早期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实际上,稍微了解中国古代朝堂礼仪的人都会清楚,朝堂上行进有着一套完整的规范,这在整个古典社会是常态礼仪。从《论语》中的记载,我们可以认为,从堂上的“屏气不息”到堂下的“逞颜色”,说明在堂上举止行进一定是给个人的身体上带来不适的。既然不适,为何一定还要保持这样的一种紧张状态呢?因为这是礼仪,是表达对于君主权威的尊重,如果轻慢,就是对于君主权威的不敬,既不符合儒家对于君主的礼敬之情,也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正是如此,才会有各种各样、程度各异的“在朝之容”。“在朝之容”以尊重(甚至是膜拜)政治权力为前提和背景,以约束和压制个体的行动舒适为表现方式,传达了人们在政治权力面前的卑微和紧张,是传统“生活政治”的生动体现。因对权力膜拜而造成的道路行进时的身心紧张,生活文明的意义较小,而政治因素较强,随着权力的神秘性和人治的消退,这种“在朝之容”所体现出来的对人身心的压迫应该逐渐减小,庄重、严肃具有必要性,但身心的压抑则应该予以消除。
在军队或者其他事由组成的队列中,行进时也有着规定的礼仪。“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礼记·曲礼上》)队列前方的情况有变,队列中的旗帜则发生变化,以为信号,队列的前后左右均有着特定的安排,使得整个队列进退有度、左右得宜,极具秩序感。队列行进是群体活动,在等级制的视野里,群体活动要有权威性的指挥,由于队列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远,故而保证指挥有效的是各种信号,旗帜等仪仗因为其可以保证较远距离的人都能看到,正可以保证这种信号传达信息的准确。类似于这类传递信号的仪仗,是为了保证指挥的有效性,主要是一种指挥技术,但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礼仪秩序规则。
除了政治人物,在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人们行进举止的礼仪也表征了家庭权力和社会秩序。父子关系中,进退得当是展现子女对父亲及尊长的尊爱之意的重要表现,更是孝顺的具体行动。《礼记》中对于子辈在行进举止上的礼仪要求较多,如,“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礼记·曲礼上》)长辈是家庭权威的代表,子辈要服从这一权威,因此,子辈的进退要取决于长辈的意志,这才是符合礼仪的孝子行为。反过来说,如果子辈在行进上不如此,则有可能会承受不孝的指责。又如,子辈在家居生活中,不能占据尊长位置,不能坐在当中的位置,不能走当中的过道,不能站在当中的门口,以此来维护父亲的权威,“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礼记·曲礼上》)对于家庭或者家族中父子、长幼秩序的维护,需要借助各种生活场景,日常的居处、行走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未必能严格执行,但日常行走秩序常常还是以规范性要求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不仅是在较早的《礼记》类文献中出现,直到传统社会后期还有回响,如明末刘宗周曾制定《宗约杂戒》,对《礼记》中的道路行进秩序予以落实,“凡道路,祖孙行衔尾,叔侄行肩随,兄弟行雁序”*《刘宗周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74页。。不同的辈分的人走在一起,要呈现出不同的行进样态,用这些样态来表现伦理次序、长幼秩序。总之,在主张礼仪秩序的儒家那里,强调在一切生活场景中显示对尊长的礼让,所有的行动、言语都要念及尊长特别是自己的父母,以父母的意志为核心,这样,既能体现孝顺父母的情感,也能让自己远离危险的言论与行动,“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礼记·祭义》)这种对父母的尊崇,不仅是针对男性,也是针对女性特别是嫁做人妇的女性的要求。《礼记》中专门对家庭中女性的行进及举手投足做了很多礼仪规定。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主要活动场所并非公共空间,而是在家庭等相对私密的环境。但即使是这样,女性在日常的道路行进中也要遵照礼仪规定。特别当女性成年后,嫁做人妇,与其他生活场景中一样,要注意与公婆等人在道路行进中的礼仪秩序。“妇事舅姑,如事父母……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礼记·内则》)当女性走到公婆的居所时,要嘘寒问暖、要怡声低气,要关心公婆的身体状况。另外,在女性陪同公婆进出的时候,要注意在道路上予以扶持,以示恭敬,通过对女性生活仪节的具体要求,将“亲亲”的原则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可见,虽然在私人生活空间的家庭,也要处处恪守近乎苛求的行动规则,把公共生活空间乃至朝堂上礼仪秩序移植到家庭里,使得家庭也肃若朝堂,这是儒家生活政治的扩大化,对于一般的个体自由意志的生发具有抑制作用。
按照文献的记载,在整个家庭关系中,处处都能看到人与人之间行进次序的重要,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在各种礼仪场合中都有行进次序的要求。婚礼是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也特别能体现家庭生活秩序、家庭权力秩序的象征性活动。《礼记》对婚礼仪式中家庭成员的行止有所规定,如,“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礼记·昏义》)在婚礼活动中,父亲可以敬其子以酒,以发出迎娶新妇的指令,儿子受命往妇家迎娶。女方父母在家庙里设酒席,在门外迎接女婿,然后行置雁之礼。接下来,就是通过新婚夫妇在道路行进上的一些礼仪要求,来传达家庭生活中的秩序观念,如新郎将新妇的车驾好,把车上的引手绳交给新妇,引其上车,车轮象征性的转三圈,然后分车到达夫家,又是一番礼仪活动,等等。这些繁琐的程序,显示男女婚礼的隆重性,行进次序等表明男女的界限,夫妇间的关系才有正当性,夫妇间的正当性进而能保证家庭关系甚至君臣关系的有序,“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礼记·昏义》)婚礼活动中的举手投足,从礼治的立场上来看,其担负极大,被赋予了远远超出其本身的使命,也将日常生活与政治强行地关联起来,放大了私人生活对于公共生活的影响。私人活动被赋予重大的政治意义,即使是针对政治人物,也将导致公私之间的价值混淆,使得个人的私人生活不再具有隐私性和个体性,而通过风俗、传统等赋予了政治性价值。
师弟、乡里关系中,道路行进上的次序也要得到保证。行进次序作为社会交往礼仪,特别是要在行进中表达对尊长的敬意。行进与宴席等一样,强调次序,因为次序可以体现由于身份、年龄等造成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学生与老师就是一种身份差异,学生应该在各种场合体现对老师的尊敬,在跟随老师出行中,不能先于老师与路人交谈;在路上见到老师,要从体貌上表达恭敬之情,不能主动与老师交谈,要老师先言而后对答之,“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礼记·曲礼上》)这种礼仪要求学生在整个行进过程中,从属于老师,如果在行路中与老师并行,则会受到指责,所以孔子说:“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论语·宪问》)弟子对待老师应该“隅坐随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0页。,如果同座并行,那么这种学生在名利心上是值得怀疑的。就是在乡里关系中,长幼之间也应该如此,“行,肩而不并,不错则随。见老者,则车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达乎道路矣。”(《礼记·祭义》)“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可见,行进次序是落实长幼之别的重要落实手段之一。特别是在乡里的公共活动中,主客之间的行进、迎送活动,更要体现这种秩序性礼仪,“乡饮酒之义: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盥洗扬觯,所以致洁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让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絜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祸也。故圣人制之以道。”(《礼记·乡饮酒义》)乡里(一种人员相对互相熟悉的共同体)公共活动中的礼仪,主客之间在行进、迎送中的互相恭敬、彼此尊重,其意义在于让人们都领会君子之道,如是则可以消弭乡间的争斗与互相侵害。在《礼记》等礼仪典章制度看来,这是体现了圣人制礼的目的所在,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恭敬礼让,既是良善秩序的表现,也是形成良善社会的途径,好的政治,不是通过暴力强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日常举手投足的礼仪性规定就可以达到,这就是“不要政治的政治”,也即是儒家生活政治的理想性效果。这种“不要政治的政治”既是在等级话语体系里的表现,又是也在生活文明的话语体系里的表现。比如,在儒家看来,在一些场合,即使对方不是尊者、长者,也要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如“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论语·子罕》)对穿丧服的、礼服的以及眼障人士,孔子不论其身份等级,也会表示出敬让之意,这体现了儒家对于他人的尊重之意,是一种生活文明,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之心。
在《礼记·王制》里,还专门有对道路行进次序的一般性规定。“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礼记·王制》)这里,描绘了日常生活中道路行进秩序的清晰画卷,在道路上,男女之别、长幼之别、车马与徒步之别,一般性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都明确地展现在道路之上。另外,日常行止中的上下、左右、先后,是辨明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等社会关系的显在性标志,人们可以通过方位、先后的观察,来把握尊卑等级秩序。儒家认为礼乐可以为政,治乱与礼乐兴亡是关联的,孔颖达对此处所引的最后一句解释道:“涂,道也。道,谓礼乐也。言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使贵贱、长幼、远近、男女殊别,外内莫敢相逾越者,皆有此礼乐涂道出其此事也。”*《礼记·正义》下册,第1399页。道路行进、堂室进退的次序是日常行止的重要内容,车有左右,行有先后,一切都有法度,秩序才能得到保证,遵守了法度则治,违背了法度则乱,而这里所谓的“法度”就是礼仪。这种行进次序同方位等一样,不能够随便“相逾越”,否则,生活秩序的破坏即意味着将危及政教秩序。儒家认为,破坏道路行进秩序,意味着破坏身份等级秩序,损害儒家尊尊亲亲等核心价值原则,应该对这种挑战秩序的行为予以警惕,因此,在各种处境下要严格遵守行进秩序。
儒者的居处、行进礼仪,是儒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礼记·儒行》)在传统礼仪观念中,儒家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举止中,从日常生活中传递儒家的精神价值,进而养成符合礼仪规范的社会风俗,只有这样,儒家才认为是达到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成为好的社会。儒家对日常行进的礼仪要求,既作为一种生活政治保障了身份等级秩序,同时也丰富了儒家生活文明的内容,传递了儒家尊人、爱人、礼让他人的核心价值。
三、 日常交通与现代政治
在古代礼仪的文献传统中,日常交通体现了社会秩序,无论在政治人物之间,还是在家人父子和乡里关系中,车舆马具、出行仪仗、行进次序等等,包括后来社会上出现的肩舆、轿子等交通工具,在使用的时候大都反映着身份等级、长幼秩序等。“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礼仪规则如同现代社会的法律一样,对于划定群己边界、端正国家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礼以别异”,这种以外在标志物区分人物差别的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意义,同时也表示在共同体生活中,人们以约定的礼俗来展现共同体的秩序文明、生活文明。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车马与行进礼仪未必如文献记载的理想状态那样严格和细致,或常有僭越以及违背礼制的情况发生,但对交通工具、日常行进所体现的礼义大多还是保持尊崇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传统和生活文明,这些从现代生活中还能看到传统的影子。如前所述,交通、行进中的礼仪规矩等除了能参与维护一定的交通规则、保障交通便利之外,还能够体现权力关系、社会等级秩序,是政治权力、社会权力乃至家庭内部权力的重要表征,从而附加了政治功能,也能体现儒家对于日常生活秩序的高度迷恋与重视。传统交通礼仪担负了重要的交通规则和制度功能,虽然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治活动、公共交往活动的秩序,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规则意识,丰富了中国古代公共生活文明。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蒸汽机等能源传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交通工具日新月异,汽车、轮船、飞机、航天飞行器不断更新换代,取得了飞跃式的进展,跨越关山,一日千里,遥远距离的朝发夕至早已不是奢望,九天揽月、五洋捉鳖也不复是神话。罗伯特·路威说:“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比野蛮人的高出不知若干倍。但这是渐进而来的,其间也不知绕了多少冤枉路,和人心的惰性打过多少仗。这是人类进步的历史从头到尾一贯的特色。”*罗伯特·路威:《野蛮与文明》,吕叔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31页。人们在为了生活舒适和交流便利上,不断改造自然与改造工具,实现了在交通问题上的飞跃式进步。人与人的交往,随着空间距离上去远来近,也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从宏观上看,交通工具与现代文明构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交通工具的进步,促成了贸易往来、外事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为现代政治文明、生活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由于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扩大化,为了使这种交往放大至最大效益,为交通工具及技术的更新也提供了动力。从微观上看,在日常生活中,交通工具为现代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们的生产、生活往往随着交通的变化而变化,现代交通工具为人们的工作、人际交往、休闲旅游等做出了贡献,同时,人们对日常生活便利化的诉求,也对交通技术(包括道路、桥梁、隧道的修缮,航线的校正等)进步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现代文明与技术的关系来看,似乎交通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如道路设计、建造,动力、交通工具的技术革新,无一不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进步的,即使是交通的疏导,也涉及交通的调度管理技术,比如,红绿灯时长的设定、道路宽窄的计算、车辆行驶线路的划定等,需要根据人员流量、车辆流量等技术参数予以设计。但由于权力的分配、利益的纠葛等因素,现代社会的交通也依然和传统社会的交通一样,有着其政治性的一面,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日常交通依然是生活政治视域里的问题。政府如何统筹考虑国民的交通便利问题,稀缺性的交通资源如何分配,如何通过政策调控人们的交通出行,如何保障交通安全等等,都是政府公共性治理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社会大部分家庭因为逐渐成为核心家庭(即由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和居住空间的有限,交通行进主要指的是公共领域中的问题,是人们在公共性的交通工具、道路、航线以及公共活动场所的活动。公共空间、公共活动要求人们遵守交往理性和公共秩序,这类秩序往往不以身份等级、性别、种族(如有些国家曾经歧视有色人种,在公共交通工具中刻意隔离有色人种,这种情况也已逐渐消亡)作为前提,而是以如何保证人们的安全、方便、快捷作为制定公共交通政策的出发点。个体在这种公共理性的支配下,通过合作、遵守公共秩序来保证自己和他人的交通安全、便捷等要求得以实现。在一些公共活动中,人们的行进秩序也是如此,除了一些政治活动以及对特殊人员有专门性安排之外,如政治性的会议按照官职大小安排出场顺序,体育比赛为运动员专门安排出入通道,演出活动为演员们提供后台出入等等,其他大多数时候的行进都是在遵守利己利人的公共秩序下进行的,或者是按照商业规则(付出较多的经济成本获得较为优先的便利)来安排行进秩序,比如在乘坐飞机的登机活动中,付出较多金钱购买高等级舱位的人享受优先的行进礼遇。日常活动中的公共秩序有赖于政府的引导,更依赖于文明社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的形成,而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人们自发行为,都需要尊重公正、平等、自由等现代性价值,这些价值是秩序形成的基本依据,也是当代生活政治的主要内容。因此,现代社会的交通行进秩序与古典社会一样,也是在一定的政治价值和身份秩序主导下而形成的,现代社会人们普遍信仰的政治价值是自由、平等,主张人们身份上没有贵贱之分,我们在尊重自由、平等的原则下,对于传统的礼让、和谐精神也要继承发扬。同时,传统车舆、行进中的礼仪要求及其所反映的某些价值诉求,对现代交通文明有重要的启示,如从车舆、行进礼仪中抽象出来的礼让原则,对于现代人们的相互谦让、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照以及遵守秩序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现代技术不断前进,但交通工具和道路等等依然还是具有一定稀缺性的资源,这导致了现代交通行进中也依然存有传统的身份等级分配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是稀缺物总是被少数人所拥有,这些“少数人”,或是权力金字塔上的“少数人”,或是拥有巨大财富的“少数人”,对这些稀缺物的拥有、支配和使用,是身份、门第、地位、财富的标志。众所周知,不同社会形态的等级制结构是不同的,但正如戈登·塔洛克所言,尽管等级制的内在机理可能有所不同,但“所有等级制都是金字塔形的,少数人处于顶部,大多数人处于较低的各个层级”*戈登·塔洛克:《官僚体制的政治》,柏克、郑景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0页。。既然如此,只要有不平等的存在,基于身份、权力、财富等层级差异就会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因此由层级差异带来的分配差异就一定存在。由于交通工具不断更新,除了不断发展的公共交通以外,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现代交通工具,如私人轿车、私人船艇甚至私人飞机等。以更为常见的轿车为例,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私人轿车,但私人轿车的品质是有差异的,人们根据占有的财富情况和个人偏好等因素,拥有和使用不同品质的轿车。虽然更多的人拥有轿车,但在特别注重身份等级的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什么级别的人使用何种层次的车辆,什么时候能够使用,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时段使用什么道路,车子的安保装备、道路出行的安保级别,乘坐车辆时的座位安排等,依然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大小、政治地位的高低。不同级别的车辆,乘坐时的位置,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或许并不仅仅是增进乘坐时身体舒适和愉悦,更看重的是身份地位的差异。这种保证差异式的交通规定,往往还可能是国家的制度和规则,通过制度将人的身份差别用外在物规定起来,使得人们依然用外在形制来区别身份等级,熟悉内情的人可以根据外在性质来判别等级。
交通工具的分配、道路行进的优先权是日常生活中的嘉益,给人的生活提供便利,对人们拓展生活空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安顿,所以同样是生活政治发生作用的场域。在现代社会里,此类问题往往被归于民生问题。在和平年代,民生问题就是政治家应该最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如何分配车舆、安排道路交通、制定行进规则、保障交通安全和交通公平等民生中的嘉益,依然是“生活政治”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 结 语
通过对《礼记》所记载关于车舆、行进礼仪要求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在礼治的传统中,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一般平民,在使用交通工具或者安排特定场合中的步伐行进时,都应该符合各自的身份等级并且要根据情景来处置。就车舆而言,所拥有车舆的数量、车舆上的装饰、驾驭车舆的技巧、乘坐车舆的规矩乃至对待车舆的态度等等,都能体现身份等级秩序。尤其是政治人物乘坐什么样的车舆、如何乘坐、与谁一起乘坐等问题,成为了政治生活中间的重要事务,需要用具体礼仪规矩确定下来,以保证政治权力秩序、身份等级秩序的显在性。就行进而言,礼仪规则对天子、诸侯、士大夫等政治人物在不同场合下的步伐行进路线、快慢先后等都有着具体要求,不仅是政治生活的政治人应该如此,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普通人在家庭生活、乡里活动中,也要按照父子、师生、长幼、男女的伦理关系及其相应的尊卑原则来决定行进中的主次秩序、步伐节奏。从礼治的视野下来看,车舆、行进关涉着社会秩序的维系、政治与生活权威的维护、生活权益的分配,因此,它不仅仅是生活文明中的话题,更是政治之域中的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交通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与交通、行进有关的事务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同时,政治价值也通过日常交通而体现出来,实现了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的双向沟通。
牟宗三先生曾言:“分位等级保,则价值层级保。”*牟宗三:《历史哲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42页。这种具有“生活政治”色彩的礼乐制度,对于巩固儒家政治价值、维护传统社会秩序、推进国家治理、保障人际关系和谐等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历史地来看,包括车舆行进在内的日常生活礼仪,逐渐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对于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有所型塑。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来看,礼仪规则对于人们的型塑,既有积极意义,如能帮助人们养成礼让之心、规则之意;也有消极意义,如促成了身份地位不平等的固化、等级制度的弥散、混淆公私生活界限等。车舆、行进等交通问题依然是现代公共生活中的核心议题,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合理分配交通领域中的生活嘉益,形成适应现代生活的交通生活文明,要求我们发挥传统礼仪规范积极价值的同时逐渐克服其中的消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传统交通礼仪规范的研究仍然是有必要的。
●作者地址:朱承,上海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44。Email:zhucheng@shu.edu.cn。
●责任编辑:桂莉
◆
Vehicles,Walking and Life Politics: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TheBookofRites
ZhuCheng
(Shanghai University)
From the numerous recordings of etiquette arrangements inTheBookofRitesthat involved the use of vehicles and walking,we can find the concern of order within daily life commute of rule-by-rite traditions.Comparing the vehicles used by a noble to the standard of cart using,his level of nobility in his politic life could be distinguished.His cart and saddleries were his political identity.Even walking,the most ordinary means of travelling,when being of different position or being in different occasions,would be regulated by specific etiquette requirements.From the way one walks,things like one’s position,or one’s seniority,could be told.This made walking on his feet a demonstration of the order of society.Similarly,in the modern world,the way one travels still somehow reflects a certain degree of “life politics”.But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ource is no longer dominated by the old hierarchy system.It is now the public rationality and modern value brought by modern public life that dominate the modern communi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within it.
TheBookofRites; vehicles;rule-by-rite;hierarchy;life politics;communication etiquette
10.14086/j.cnki.wujhs.2016.05.0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X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