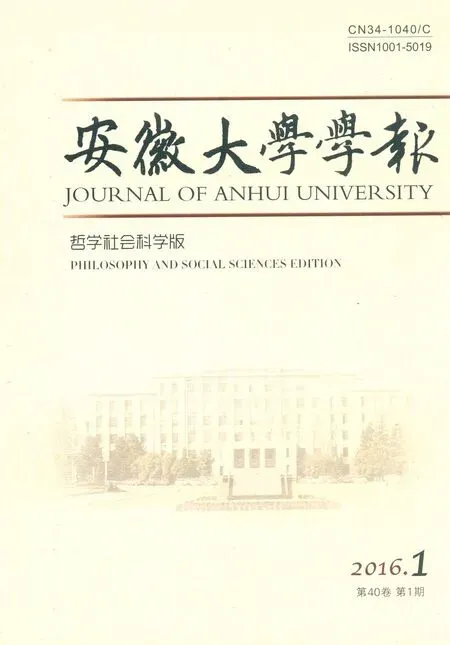新时期中国文学视域中“世界文学”图景的嬗变——基于对《世界文学》的考察
卢志宏
新时期中国文学视域中“世界文学”图景的嬗变
——基于对《世界文学》的考察
卢志宏
摘要:“世界文学”图景是建构的产物,依赖于文化历史语境,也因此会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产生变化。《世界文学》作为新时期主流翻译文学刊物,参与了“世界文学”图景的建构。和建国初期以及“文革”时期相比,新时期中国文学视域中“世界文学”图景发生了明显变化:就国别而言,从苏俄文学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各国文学的“百花齐放”;就文学类型而言,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化为“西方现代派”;就作品选择标准而言,从“革命”“进步”过渡到“经典性”。这其中有文学期刊内部的直接原因,主编和主办机构的专业化;有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双百”“二为”方针的提出;也有中国文学场域内部的要求。
关键词:期刊翻译;世界文学;新时期;《世界文学》
一、引言
以往的翻译史研究大部分注重单行本译介的研究,个别译者的个别译本所产生的突出作用在翻译史研究中被强化,翻译文学期刊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翻译文学期刊有一个单行本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翻译文学期刊通过节译、选译、全译等方式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呈现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世界文学”图景,透过翻译文学期刊可以考量中国文学场域对于外国文学作品如何选择性地进行译介,从接受维度洞悉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学场域中的传播。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已经逐渐注意到翻译文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就国外研究而言,Lefevere(1992)在谈及翻译文学系统的赞助(patronage)时,曾将期刊定义为作为群体出现的赞助人中的一种:“赞助人可以指个人,譬如中世纪意大利的美蒂奇家族、文学事业的资助者或是路易十四;也可以指一个群体,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社会阶层,皇室,发行商以及媒体,这其中就包括报纸杂志,以及规模较大的电视台。”*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15.报纸杂志是作为机构这一权力要素在赞助人体系中出现。Milton & Bandia(2009)将文学期刊视为“中介”(agent),在《翻译中介》一书中专门有两节针对出版机构在文化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探讨*John Milton & Paul Bandia, Agent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pp. 43-61,85-105.。就国内研究而言,谢天振、查明建(2004)对文学期刊对于构建翻译文学史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们指出:“如果说中译单行本的出版发行构成翻译文学史发展的躯干和动脉,那么这些分散在不同文学报刊上的译作和译介文章,就是血液、细胞和神经,使得一部翻译文学史真正鲜活、生动起来。这样我们在史述中国翻译文学时,就不仅能够回答‘是如何’,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如何是’。”*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页。除此之外,陈思和(1997)*陈思和:《想起了〈外国文艺〉创刊号》,译文出版社编《作家谈译文》,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王建开(2003)*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何云波(2005)*何云波:《换一种眼光看世界》,《世界文学》2005年第3期。也都注意到了文学期刊在翻译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本文主要探究《世界文学》这本刊物构建了怎样的中国文学场域中的“世界文学”图景,以及这种图景从建国初期(1953—1966)到新时期(1978—2006)产生了何种变化,并试图分析其成因。
二、《世界文学》构建“世界文学”图景的理想
就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而言,《世界文学》是和《外国文艺》以及《译林》齐名且贯穿新时期至今的代表性刊物。新时期的《世界文学》杂志的前身是1953年7月创刊的《译文》, 1959年刊物更名为《世界文学》。1965年停刊一年,1966年复刊时改为双月刊,出一期后即停办。“文革”期间该刊物一直处于停办状态。1977年《世界文学》内部发行一年,1978年10月正式复刊,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正式公开发行至今。
1959年,《译文》更名为《世界文学》,这一更名本身所传达的构建“世界文学”图景的理想在编者所撰写的《从译文到世界文学》一文中就可以得到验证:“我们的刊物今后主要将介绍反映现代世界各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作品。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尽可能要广阔而多样。”*编者:《从译文到世界文学》,《世界文学》1959年1月号。
1978年,该刊物在复刊后的第1期的《致读者》中明确提出了要“对全世界的文学”有全面的了解:“要在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前提下做到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尽可能使读者对全世界的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编者:《致读者》,《世界文学》1978年第1期。
2000年,《世界文学》前主编黄宝生在“主编寄语”中,更是明确地将办刊宗旨界定为打造一个“微缩的世界文学花园”*黄宝生:《主编寄语》,《世界文学》2000年第1期。。
细读1978年复刊伊始的《致读者》以及2000年的《主编寄语》,可以发现,这其中的核心词汇是 “全世界的文学”“微缩的世界文学花园”。由此可见《世界文学》一直是以构建“世界文学”的版图为己任的。
文学期刊的译介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功用,也是单行本译介难以企及的就是其译介覆盖面比较广,这主要体现在国别选择、文学类型选择和作品选择标准三个方面。
三、新时期“世界文学”图景的嬗变
(一)国别选择:从苏俄文学的“一枝独秀”到各国文学的“百花齐放”
就国别选择而言,可以通过如下的数据统计将建国初期和新时期《译文》和《世界文学》的“世界文学”图景做一对比:
新时期以来的期刊译介与建国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相比,就国别选择而言,有一定的连续性。建国十七年间,《译文》(《世界文学》)在译文的国别选择上,居前四位的分别是苏联(610)、法国(186)、日本(156)、美国(153)四国;“文革”时期,《摘译》也是以苏、美、日三国为主要译介对象;新时期以来,《世界文学》刊载的翻译文学,法(587)、美(517)、日(507)、苏(332)四国依旧占据前四位。

1953—1966年《译文》(《世界文学》)翻译作品的主要来源国* 卢志宏、王琦:《翻译文学期刊构建的“世界文学”图景——以建国初期的期刊文学译介为例》,《外国语文》2014年第3期。

1978—2006年《世界文学》翻译作品的主要来源国* 李卫华:《文本旅行与文化建构——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06页。
从整体来看,建国初期《世界文学》上刊载的苏俄文学的译介数量最多,占译介总数的22.2%;西方四国(法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和日本其次,占译介总数的26.6%;亚非拉四国(越南、古巴、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相对较少,占译介总数的10.9%。统计结果表明,苏俄文学译介是重中之重,西方四国和日本文学其次、亚非拉文学相对数量较少。
而到了新时期(1978—2006),苏俄文学已退居第4位,仅占总数的7.3%;西方国家的文学译介已经从原来的四国增加为6国(新增了加拿大、奥地利两国);另外两国罗马尼亚和波兰是东欧国家;亚非拉文学已逐渐淡出了文学译介的视野。从绝对数量上看,法国、美国两国的文学译介已超过了苏俄文学,英国和德国文学的译介数量虽然略低于苏俄文学,但差距并不大。中国文学视域中的世界文学,西方6国已经成为主流,苏俄文学的地位明显下降,而亚非拉文学也相对式微,已经从建国初期苏俄文学一家独大的状况转为各国相对均衡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新时期中国文学视域中的“世界文学”已经从建国初期的苏俄文学“独占鳌头”过渡到各国文学的“百花齐放”,真正做到了“多样化”。
(二) 文学类型选择: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西方现代派”
建国初期《世界文学》的译介重点无疑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到了新时期,译介的重点转变为西方现代派。西方现代派可以分为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类型。
新时期伊始,这种译介重点的转变首先体现在《世界文学》对于现代派文学兴起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世界文学》曾先于《外国文艺》刊载了西方现代派作品,这其中就包括象征主义作家瓦雷里的《诗四首》(1979年第4期),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1979年第1期),荒诞派作家哈罗德·品特的戏剧《生日晚会》(1978年第2期),超现实主义作家奥·埃利蒂斯的组诗选译《俊杰》(1980年第1期),意象主义作家H.D.的《诗五首》(1981年第5期)。除了“开风气之先”,《世界文学》还曾设立各个派别重要代表作家的专辑:该刊1993年第4期,为纪念卡夫卡设立了“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诞辰110周年专辑”;2006年第2期曾刊载有“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作品选”;拉美文学爆炸代表作家也曾设有专辑:“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专辑”(1987年第1期)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专辑”(1990年第2期)。
这一时期的文学场域中,现实主义的内涵更为丰富,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出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种派生派别。拉美文学热潮中诸作家都被冠以现实主义作家的头衔,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魔幻现实主义成功地将现实主义和现代派表现手法糅合在一起。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本质使得它的译介更为安全。拉美文学爆炸中另外三位作家的作品也和现实主义相联系。略萨被冠以“结构现实主义”作家的头衔*赵德明:《〈胡利娅姨妈和作家〉译作前言》,《外国文艺》1981年第3期。,富恩特斯被冠以“象征现实主义”作家的头衔*尹承东:《〈富恩特斯作品小辑〉译作前言》,《外国文艺》1982年第6期。,博尔赫斯的作品被定义为“超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另一种模式”*何榕:《现代作家小传——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世界文学》1981年第6期。。与此同时,除了现实主义而外,还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等诸多派别,已经发展成众声喧哗的局面。
(三)作品选择标准:从“革命”“进步”转化为“经典性”
茅盾(1953)在《译文》发刊词中明确指出:“今天我们不但迫切地需要加强学习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也需要多方面的‘借鉴’,以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因而也就需要熟悉外国的古典文学和今天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以及殖民地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茅盾:《发刊词》,《译文》1953年第1期。
在1978年复刊后的《致读者》中,编者指出:“首先当然要重视革命的题材,同时必须充分重视各种各样其他的题材。……此外,还要注意广泛介绍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作品。在古典文学方面,除了过去介绍得比较多和读者比较熟悉的现实主义文学之外,还要多多介绍其他各种流派和风格的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文学;在现代文学方面,也要广泛介绍各种各样流派和风格的文学,尽可能使读者对全世界的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黄宝生(2000)在《主编寄语》中则指出:“我们希望我们的选材能体现文学的‘经典性’,也就是在各国文学史上能占据一定地位的作家和作品。注重现代文学和大国文学,也不忽视古典文学和小国文学。”*黄宝生:《主编寄语》,《世界文学》2000年第1期。
细析茅盾(1953)的发刊词,不难发现,文学的类别不仅有现实主义、古典文学这种文学意义上的区分,同时也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地”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从重要性上来看,“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是“迫切地需要加强学习”,无疑是重中之重;而“外国的古典文学”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以及殖民地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则相对次之,也要“借鉴”。
到了1978年《世界文学》复刊时,措辞上有了一些变化:除了“介绍得比较多”的“现实主义文学”,要“多多介绍”“浪漫主义文学”,同时还要“广泛介绍”“现代文学”。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文学已经不再一枝独秀,“浪漫主义”和“现代文学”也逐渐进入中国文学的视野,之前那些加之在文学之前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殖民地”等对于文学类别的区分已经褪去。
黄宝生(2000)的《主编寄语》,重点译介的对象已经转变为“现代文学和大国文学”,选材的标准是“经典性”,即该作品在各国文学史所占有的文学地位。“革命” “进步”等字眼已经消失。就选材而言,建国初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一枝独秀”;80年代初期,除现实主义作品外,浪漫主义以及现代文学进入视野;世纪之初,现代文学已经占据主导。就选材标准而言,已经从建国初期的“革命”和“进步”过渡到“经典性”,意识形态标准已逐渐让位于诗学标准。
四、“世界文学”版图重构之成因
(一)主编和主办机构的专业化倾向
《世界文学》(双月刊)1953年7月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创办,刊物当时定名《译文》。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期刊的主办机构中国作家协会,并不是专业的翻译机构。茅盾和冯至两位主编,并非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只是名义上的主编,并不直接从事期刊的编纂工作,只有曹靖华专业从事翻译工作*详见崔峰《建国初政治文化语境下的〈译文〉(〈世界文学〉)创刊》,《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1期。。1964年承办单位由中国作家协会转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时任副所长的陈冰夷担任该刊物的主编。由此可见,在“文革”之前,从主办机构的角度来看,已经开始出现了专业化的倾向。但只可惜1964年出刊12期之后,这一刊物很快就进入了间歇状态(1965年停刊一年,1966年复刊时改为双月刊,出一期后即停办),“文革”期间则一直处于停办状态。
1977年,《世界文学》恢复出版,内部发行一年,刊行了2期。最终在1978年10月,《世界文学》正式复刊,出版机构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历任主编分别为:陈冰夷、叶水夫、高莽、李文俊、金志平、黄宝生、余中先。《世界文学》的主办已经开始由外国文学研究所这样一个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机构来实施,主编也都是专门从事翻译活动的翻译家,专业化倾向愈发明显。这种专业化倾向,直接促成了作品选择标准向“文学性”和“经典性”回归。
(二)从“文艺为政治服务”到“双百”“二为”方针
“文革”期间,据李景端回忆,“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出版全面停止,好多年,除了有本越南的《南方来信》和朝鲜的歌剧《卖花姑娘》以外,几乎见不到其他外国文艺”*李景端:《一次意义深远的学术会议》,《翻译编辑谈翻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世界文学》在复刊后1977年第1期上也有对“文革”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回顾:“在‘四人帮’大搞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不仅我国的优秀革命文艺作品横遭压制、摧残,外国的进步文艺、古典名著更是被一律斥之为‘毒草’,出版社不准出书,图书馆不予借阅,连外文书刊资料也概予查封。”*刘宁:《把外国文学工作中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世界文学》1977年第1期。正如佐哈尔所言,“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学场域“正处于转折期,经历某种危机,或是处于文学真空之时”*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awrence Venuti(ed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93~194.。
在经历了“文革”的“危机”或“真空”期之后,新时期“双百”“二为”方针应运而生。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迈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政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文艺界环境的改变。1978年5月,全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恢复中国文联、作协和其他的文艺家协会活动,《文艺报》等刊物恢复出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86页。。《上海文学》于1979年第2期刊载了题为《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文章,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大讨论。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时隔二十年后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祝词中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3页。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也从此被驳倒。“双百”“二为”成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双百”“二为”方针的确立,使得苏俄文学的“老大哥”地位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各国文学的平等关注,同时也让读者接触到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的西方现代派等多种文学类型。
(三)中国文学场域的内在需求
季羡林(1983)曾经指出:“我们研究外国文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借鉴,借外国文学之鉴,供我们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时的参考。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借些什么东西呢?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我的看法是,后者可借鉴的东西大大超过了前者。……真正要向外国古今文学借鉴的是艺术技巧。”*季羡林:《学习〈邓小平文选〉,努力开创外国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世界文学》1983年第5期。
新时期初的作者和人民大众一起,刚刚从“文革”十年压制下解放出来,分外深切地感觉到人的价值、尊严和“自我”丧失的痛苦,而进行反复的思考。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与该时期中国文学系统的需求刚好契合。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这种思考更加深长和沉重,愈益严肃地肯定了人的中心地位和文学认识人和提高人的职责*王铁仙等:《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这种文学内部对于人的中心地位的肯定客观上为存在主义提供了引入的文化环境。新时期初,“伤痕小说”最先鲜明地表现出对人的关注,对人在世界和文学中的中心地位的确认。
中国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学形式上的现实与神话交融在一起的表现手法更是成为新时期作家创作的范本。莫言就曾直言他曾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并将他和福克纳并称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百年孤独》不仅在艺术创造上给予他震撼,更重要的是让他意识到要“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寻找到自己的根。这些都成为这时期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重要的思想动因。
五、结语
David Damrosch(2003)曾借用Vinay Dharwadkera的比喻将“世界文学”界定为“由移动的地图相互叠加后产生的蒙太奇效果”*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77, no. 1, (Apr. to Jun., 2003), p. 13.,他进一步指出:“任何作品都难免被操控,甚至在外域接受中产生变形。”*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77, no. 1, (Apr. to Jun.,2003),pp.13-14.查明建(2011)也指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会因国际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读者接受视野等多种因素,而构建不同的文学经典谱系。”*查明建:《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
这里,Damrosch和查明建都强调了世界文学的接受之维,以及在接受中可能出现的操控和变形。“世界文学”图景的构建更多还是依赖于接受方,即目标语文化,是对“世界文学”的选择性呈现,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叠加。这种选择性呈现,一方面当然取决于译者,同时也取决于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如主办机构和主编),但最根本的还是意识形态和诗学这两个系统*翻译活动的三个外在制约系统,即赞助(patronage)、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具体请参见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赞助系统能够直接通过经济和文学地位等手段对译者施加直接影响,而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系统则通过赞助对于译者施加间接影响,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系统的角力,间接决定“世界文学”以何种面貌呈献给读者。
责任编校:刘云
作者简介:卢志宏,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翻译学博士(安徽 合肥230601)。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首批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资助经费(33010047);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02303319-33190122)。
中图分类号:I109;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1-0073-06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