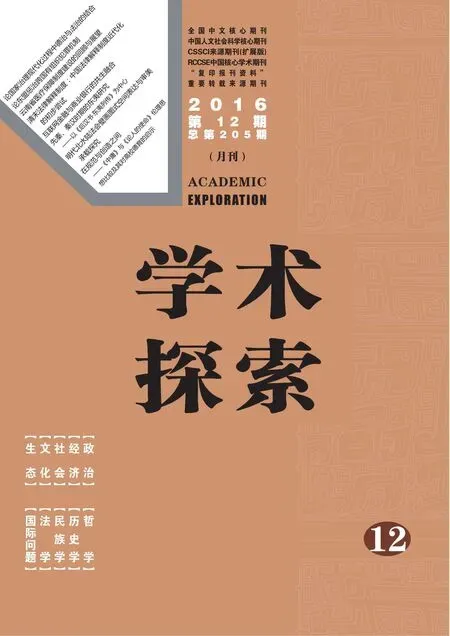论东盟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机制
张 屹
(外交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 100005)
论东盟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机制
张 屹
(外交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 100005)
在2004年中日韩与东盟“10+3”合作机制关于打击跨国犯罪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东南亚地区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被归纳为八个类别,而恐怖主义犯罪被界定为八种犯罪形态。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也“关切地注意到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目前在中国与东盟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恐怖主义犯罪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种种结构性阻碍。因此,在东盟框架内如何界定与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并且实施有效的国际治理将影响未来东南亚整体的经济、社会、政治协调发展,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战略利益,区域内合作机制亟待完善。
跨国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东盟;司法协助;次区域合作
一、东南亚跨国有组织犯罪现状
由于在历史上东南亚国家先后受到过英、美、法、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在文化、宗教方面遗留的历史问题比较集中且矛盾复杂,在这一方面可以与今天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对照。然而又由于东南亚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海洋资源优势,使得该地区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集中表现在毒品走私、贩运人口、海上犯罪等方面。而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也更多地与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相结合,以经济利益的榨取和物质资源的掠夺作为重要的犯罪动机和行为模式。
在2004年中日韩与东盟“10+3”合作机制关于打击跨国犯罪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东南亚地区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被归纳为以下八个类别,即:贩运武器、贩卖人口、贩毒、海盗、网络电信犯罪、洗钱与其他经济犯罪,以及恐怖主义犯罪等。
东南亚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该地区囊括了从最富有的新加坡到最贫穷的老挝、缅甸。贫富差距与区域内边境管制的松懈导致跨国有组织犯罪频率长期以来处于不断攀升的状态。[1]如果我们以《巴勒莫公约》(即《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定义作为认定标准,即“三个人以上作为犯罪主体实施的,作案范围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则为跨国有组织犯罪”,那么东南亚地区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无论从规模和地域来讲,都远远超出这一标准。
(一)主要案例与次区域合作机制
东南亚贩毒集团实施的湄公河惨案:在2011年年底,为调查处理湄公河惨案而设立了由中国、泰国、缅甸、老挝共同组成的湄公河联合执法行动机制。然而这一机制如何形成真正的常态化机制,并且通过机制的功能性溢出而增强地区间的司法合作深度,则应当引起各参与方的认真思考。
中国与东盟开展次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湄公河流域不仅是重要的合作平台,也是必要的贸易通道。在将近大约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澜湄地区性合作机制逐渐分化为包括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在内的多元机制,前者由于中国的积极参与推动而显得更具有国际影响力。
有些学者进而提出“那些不具有政治目的不是以胁迫国家机关或国际组织为目的而采取的暴力破坏或其他手段,造成一定范围恐慌的行为也应属于恐怖主义。”[2](P55)如果按照张杰的这一种定义,发生在泰国的湄公河惨案以残忍的方式杀害13名船员,其暴行震惊中国民众甚至国际社会,也当属恐怖主义犯罪之列,这样,恐怖主义犯罪与跨国有组织的犯罪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已经不存在明确的划分界限了。
以伊斯兰祈祷团为代表的东南亚恐怖组织犯罪:2002年在印尼巴厘岛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主义爆炸案,其幕后策划者就是广泛活跃在东南亚地区的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该组织与基地恐怖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将其定性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具有威胁性的恐怖组织之一。“伊斯兰祈祷团”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文莱等国家,其政治诉求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一个泛伊斯兰政权,称为“大伊斯兰国”。该组织不仅从事以爆炸袭击为主要手段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还在上述国家从事武器走私和贩运。因此,“伊斯兰祈祷团”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冲突,同时也在触犯着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底线。在从政治视角来判定其恐怖主义的属性的同时,也必须思考如何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属性上来进行惩治。
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犯罪都与武器贩运、军火走私密不可分,后者为前者提供必要的手段和利益链条,而东南亚的恐怖主义犯罪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菲律宾为例,其境内的恐怖组织多从事武器贩运,甚至与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本·拉登的嫡系哈拉克拉特-乌尔-穆加希丁长期进行军火交易,相互勾连。
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新形式的电信诈骗:2016年4月13日,包括32名中国大陆人与45名中国台湾籍在内的第二批67名犯罪嫌疑人被以电信诈骗罪名从国外押解回中国大陆。台湾方面认为台湾的电信诈骗集团已经发展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所有国家应该严厉打击的对象。甚至提到“我们治不了的骗子,让想治又能治的大陆惩治”。[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跨国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的东南亚地区,很多当地政府都存在着治理能力偏低,对待跨国犯罪捉襟见肘的状况,这必然需要借助于多种形式的合作,包括国际合作或境外区际合作。台湾电信诈骗犯罪集团不仅前往非洲、澳洲等地区作案,而且经调查发现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在马来西亚较为集中地从事电信诈骗。自从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在2009年共同订立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并提升了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的力度之后,电信诈骗集团大量转移到东南亚地区或者全球各地。
贩运人口:以菲律宾作为最典型案例,该国全国范围内都存在以大规模有组织形式从事非法移民的行为,据统计,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以人口买卖的方式输送至别国。菲律宾全国范围内的犯罪集团因从事贩卖人口而获取的利润接近200亿美元,已经成为仅次于武器贩运和毒品走私之后的第三大跨国有组织犯罪。[4]
毒品犯罪:菲律宾国家毒品执法预防协调中心(National Drug Law Enforcement Prevention and Coordination Center)有一项数据显示,菲律宾人口总数在2002年为7530万,在这样小国寡民的情况下,竟然有占5%的人口即大约370万人从事吸毒。菲律宾全国有将近300个贩毒集团,每年约有50亿美元的毒品地下交易额度。甚至有数据显示菲律宾每年的犯罪统计中有70%属于毒品犯罪的上游犯罪或者相关犯罪。*World Drug Report 1997”www.unodc.org/unodc/world_drug_report_1997.html有需要必然有供给,这一切使得东南亚地区的贩毒行为屡禁不止。菲律宾与东南亚臭名昭著的“金三角”地区临近,成为金三角的毒品中转站。
(二)恐怖主义犯罪与跨国有组织犯罪
恐怖组织如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一样,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往往借助于参与其他的社会活动或市场经营活动而获得表面上的合法性。也可能为了获取资金而参与其他性质的犯罪活动,比如贩毒、洗钱、邪教活动等。当然,在这其中,宗教的标签成为恐怖主义最青睐的隐蔽途径。
如同恐怖主义犯罪与各种上游犯罪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强导致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客观上的要求也更加强烈一样,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日益国际化在客观上也要求反恐工作的国际化,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反映和必然要求。然而后者不恰当的反应行为就可能被前者所利用。这种抽象的归纳很难理解,我们试以媒体作为案例,媒体对恐怖主义犯罪事件的过分渲染和没有尺寸地一味跟踪报道,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借以传播极端思想和制造社会恐慌的工具,被其加以利用。
安理会1373号决议中的第四条明确指出:关切地注意到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药物、洗钱、非法贩运武器、非法运送核、化学、生物和其他潜在致命材料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方面强调必须加紧协调国家、分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努力,以加强对国际安全所受到的这一严重挑战和威胁的全球反应。*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
(三)洗钱犯罪与跨国有组织犯罪
由于各类有组织犯罪行为都需要一定的资金基础作为支撑,尤其是大规模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从而使得金融犯罪,特别是洗钱行为成为其他相关犯罪行为的上游犯罪和关联性犯罪行为。而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最为令人棘手的当代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其与洗钱犯罪行为的关联则尤为密切。今天各国展开的针对恐怖活动的区域性司法合作必然要以打击洗钱犯罪作为重要手段和前提。
从“犯罪主体”到“犯罪行为”再到犯罪所得即金钱这整个链条中,金钱是一个薄弱环节,也是一个警务执法的突破口,通过这一个突破口,可以最终获得犯罪主体的线索。
当前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展开的国际执法行动,最为有效的往往都是针对洗钱犯罪展开的追查,即便是国际反恐行动,也往往以恐怖组织的融资行为作为侦查的突破口。因为,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恐怖组织以及其他犯罪组织借助多种手段使自身组织规模与实力迅速增加,单纯地针对其组织本身展开追踪颇为棘手,而犯罪资金作为犯罪行为的薄弱环节很容易遗留下追踪痕迹。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各国“有必要在其领土内通过一切合法手段,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和制止资助和筹备任何恐怖主义行为”。并且“禁止本国国民或本国领土内任何个人和实体直接间接为犯下或企图犯下或协助或参与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这种人拥有或直接间接控制的实体以及代表这种人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和实体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或金融或其他有关服务”。“毫不拖延地冻结犯下或企图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或参与或协助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这种人拥有或直接间接控制的实体以及代表这种人和实体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和实体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包括由这种人及有关个人和实体拥有或直接间接控制的财产所衍生或产生的资金。”安理会为了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专门对作为恐怖主义犯罪手段的金融犯罪做出明确规定。1373号决议还指出:“ 将下述行为定为犯罪:本国国民或在本国领土内,以任何手段直接间接和故意提供或筹集资金,意图将这些资金用于恐怖主义行为或知晓资金将用于此种行为”。*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
二、东盟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机制问题及其与中国的合作
东盟地区性公约立法解读。历史上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于1977年解散,有学者认为这一组织与东盟的历史发展有着某种关联,以反对中国、越南、苏联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使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消亡的十年前,也就是1967年,东盟就酝酿成立了。而后演变为今天与中国密不可分的东盟“十加一”机制的重要国际平台,根本原因在于彼此在全球化格局之下,经济贸易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
到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老挝等东盟国家订立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者含有刑事司法协助性质的条款。与除了印尼之外上述四个国家订立了双边引渡条约。这些成果,为中国全面展开与东盟国家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不仅如此,东盟国家司法部长会议与中国-东盟总检察长会议也逐步形成稳定合作机制,为各种形式的司法协助提供推动力和平台。
(一) 东南亚国家打击跨国犯罪合作现状
中国与越老缅三国边境线有四千公里之长。云南省深受“金三角”毒品走私之危害,因此在1996年,云南与越老缅三国相邻的地方省份共同确立了缉毒警务联络官合作机制,各国地方政府通过禁毒教育、警务信息交流等合作方式对该地区内的毒品犯罪进行严厉打击。在随后的5年内,该地区内的毒品加工窝点有10个被捣毁,包括海洛因、冰毒、鸦片等在内的近五百千克的毒品被缴获。当然同时也发现了贩毒者携带的大量武器军火。
至2001年间,中国已经分别与东盟陆上五国签署了有关禁毒合作《联合声明》及《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湄公河次区域内的双边禁毒合作得到有效开展。国家禁毒委员会还委托云南省政府与老挝、缅甸两国合作培训了大批专业缉毒官员。
此外,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签署了关于禁毒合作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的谅解备忘录,分别于上述三国开展了有效的双边合作。中国与菲律宾在2004年年初成功破获“九二”跨国毒品走私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缴获了将近300公斤冰毒,约合人民币1亿元。
1991年联合国禁毒署与中缅泰三国关于多边禁毒合作的高级禁毒官员会议在北京召开。1992年联合国禁毒署与中缅泰三国在第四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东亚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次区域内打击毒品合作的框架形成。1995年中老缅泰柬五国与联合国禁毒署《北京宣言》标志着次区域内打击毒品合作的框架完全确立。2003年10月8日《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在印尼的巴厘岛签署。2004年《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曼谷签署,2004年1月的东盟-中日韩第一次“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都体现了中国在东盟框架内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作用和话语权。
中国公安部从2014年开始展开“猎狐行动”,主要针对跨境金融诈骗犯罪进行追查行动,从境外追查遣返了将近百名金融诈骗犯罪嫌疑人。此次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涉及东南亚、北美、澳洲等地区的将近50个国家。堪称一次成功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案例。在2016年的台湾电信诈骗案的追捕中,中国司法部门成功将中国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引渡回中国大陆,这符合中国在国际法基本准则下的管辖责任和管辖权,也符合大陆与台湾在2009年共同订立的《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中所体现的双边司法协助精神。
以目前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机制来看,次区域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应该说次区域合作是全面推进东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途径和平台,这其中尤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间所开展的执法合作最为显著。以澜湄执法合作的发展历程作为纵坐标,可以发现,让公众记忆犹新的糯康事件促成了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的最终设立。
2011年10月31日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2011年12月10日中老缅泰举行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首航仪式;2012年1月14日中老缅泰四国开展第二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2012年3月25日第三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展开,从而实现湄公河联合执法行动趋于常态化。上述历程见证了作为次区域司法合作机制的“澜湄”成长经历。
澜湄合作机制在其任职周期内有两个主席国,即中国加上一个湄公河国家。澜湄合作以三个支柱“政治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全面、综合性地为合作机制做了铺垫,共同推动了澜湄国家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法律机制的快速发展。亚行出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GMS也从作为上述三大支柱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强有力地为澜湄合作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动力。
(二) 东盟框架内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合作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治理能力弱
在伊斯兰世界中,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可以说是世俗化程度比较高的,对多元文化也表现得相对包容,而东南亚国家间人员的流动性也是非常高的,这些特征都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然而正是较高程度的人员流动性使得东南亚地区呈现高犯罪率与政府的低治理能力并存。不仅东南亚很多国家的边境治理是滞后的,即使作为该区域内的重要国际组织东盟ASEAN对此问题也是捉襟见肘。[5]近年来大批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东伊运”“世维会”恐怖分子取道东南亚尤其是通过马来西亚中转至中东地区例如土耳其、叙利亚等国家参加国际恐怖主义活动。2015年共有一百余名“东突”恐怖分子在泰国被捕,并被遣返回中国,这个案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东南亚地区的边境管理松散与人员流动复杂给整个亚太地区的全球治理所带来的顽疾。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印尼作为一个地形支离破碎的岛国,却划分了33个行政省份。而印度尼西亚西部省份亚齐省则是地方政府瘫痪的典型案例了。地震、海啸、绑架、暗杀、战争、恐怖袭击、武装分离运动……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一块如此悲剧之地,那就一定非亚齐(Aceh)莫属了。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地理位置特殊,位于苏门答腊岛的最北端,马六甲海峡的入口,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同时这里又是活跃的火山地震带,所以无论是文化发展还是战争侵略或是自然灾难,亚齐都是首当其冲,财富的争夺、宗教的纷争和自然的灾难构成了一部沉重纠结的亚齐史。由于亚齐省地方分裂主义势力长期威胁着雅加达中央政府的权威,因此在雅加达与亚齐之间长期展开的拉锯战过程中,整个国家权威陷入了恶性循环的衰微之中。[6]
2.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犯罪的外延界定问题
从近几年中国贯彻实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司法实践过程来看,由于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其犯罪动机具有明显的物质利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犯罪由于其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甚或宗教、民族、文化权利诉求而不在此列,从而使得长期以来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代表的恐怖主义犯罪与跨国有组织犯罪被多数国际政治学者误以为是两个外延不相重合的犯罪概念。
然而,国内学界的大部分学者已经将恐怖主义犯罪明确列入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范畴中。此外,在2004年中日韩与东盟“10+3”合作机制关于打击跨国犯罪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也明确地将恐怖主义犯罪划分到八个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类别中去。
而在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犯罪与各类刑事犯罪在现实中更是相互勾连,呈现出鲜明的地区性犯罪学特征。由于东南亚地区长久以来存在着贩卖人口、贩卖毒品、金融犯罪甚至海上犯罪等现象,这些犯罪团伙在实际运作中往往采取点对点,化整为零的行为模式,因此将大规模的犯罪行动转化为更具有隐蔽性的零零散散的“个体”犯罪行为,使侦查和惩治都增加了难度,同时也使实质上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在形式上转化为传统意义上的个体刑事犯罪。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犯罪与跨国有组织犯罪,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是相互重合的。
执法合作由于上述原因(在中国,执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紧密结合)使之与政治外交层面的合作难以区分;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执法合作与司法协助体系(即司法合作)又有着诸多不同之处:
(1)合作主体不同。对于司法合作的主体《中国和罗马尼亚民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主管机关’系指法院、检察院和其他主管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机关。”而执法合作的主体则包括各个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政府机关;(2)合作针对的客体不同。司法合作一般是在确立管辖范围其间和其后进行;执法合作则可以是在前期预防、侦查到后期实施、执行等各阶段进行开展;(3)合作的程序不同。司法合作必须在尊重和符合合作各方即当事国的国内司法体制的基础上开展,须当事国的主动配合或至少消极默许;而执法合作往往是在情况紧急时运作,在治理突发事件的时候,只要不违法国际法律一般准则,即使没有确切法律依据,亦可开展。(4)合作所依据条约的生效机制不同。司法合作所要依据的国际条约必须经过各当事国的议会(中国的人大常委会)批准方可生效;而执法合作因其实质上具有政府部门间的行政合作性质,所以其依据的国际法律文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而是政府间的联合声明、共同宣言、互助协定等形式。对于此类文件,只要经当事国政府主管部门签字批准即可生效,无须经过议会。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区别可以看出,执法合作较之司法合作具有更加灵活、更高效率、实施范围更广等特点。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之容易蜕变为不受司法规则约束的傲慢的公权力。从而,我们不禁感慨安全问题考验着国际社会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考验着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民主与法治;正如安全问题如何考验着任何一国国内社会民主与法治那样。
集体安全合作是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一种形式,然而由于其带有军事同盟的色彩,往往侧重于军事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而且容易被非成员国攻击其带有军事扩张之嫌。例如上合组织的集体安全属性往往被西方国家指责为“东方北约”。以此为鉴,只有当东南亚国家在东盟组织框架内进行协商、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时,东南亚地区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反恐合作才能够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军事同盟容易受到国际社会利益冲突方的指摘,这一事实恰恰说明,军事同盟的敏感性和很多国家对军事同盟的神经过敏,以及军事同盟难以达成国际社会更大的一致性,难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普遍性国际合作。东盟区域内展开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合作应当以保护本地经济发展和区域贸易稳定为核心理念。
3.恐怖组织融资渠道与反恐怖主义融资
如果将恐怖主义犯罪认定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恐怖主义融资行为也必然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融资行为密不可分,或者说,两种表面上不同的融资形式本质上是同一种犯罪属性。正如赵秉志所主张的那样,恐怖主义犯罪与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最为重要的区别就是不以金钱利益为直接犯罪动机,当然,不能因此而认为恐怖主义与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具有本质区别,然而恐怖主义融资的确不以金钱的获得作为其犯罪目的,所以也就不能说恐怖分子所掌握的资金是犯罪资金。
恐怖分子的核心人物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高智商犯罪的特征,恐怖组织也往往具有出色的理财投资能力。有报道称,ISIS极端组织就将其从叙利亚地方银行劫掠的资金投向欧洲金融市场,从事各种金融活动,将“黑金”漂白。
首先,通过犯罪行为本身所获取的财产是恐怖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其大部分资金来源。在“金新月”地带,中东地区一些恐怖组织从这里的毒品交易中获取经济利益,在欧洲,历史上的民族分离型恐怖组织往往运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手段,如绑架、诈骗等方式获取钱财。而在我们所要关注的东南亚地区,则是囊括了以上两种“融资”形式,可见东南亚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更为复杂。
冷战时期,由个别国家出资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当地政府反对派往往以“代理人”的身份从事恐怖主义行为,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没有今天的恐怖主义手段极端,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今天的恐怖组织运作方式别无二致。只不过把今天的恐怖主义从法律意义上视为犯罪行为,是由于其去除了意识形态的修饰,特别是东南亚恐怖主义犯罪,表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其恐怖组织的架构体系已经超出了当今国际政治的传统行为主体范畴。从一个侧面来看,也正是因为今天的恐怖主义较少地带有意识形态特征,从而也就从“依靠政府”转型为“依靠市场”,更多地与跨国有组织犯罪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当然,今天仍然有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仍然具有官方背景,并且有某些极端色彩的政府出资支持其从事恐怖活动。
一个庞大的恐怖组织需要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体制架构和号召力,从而对其全部成员进行思想控制,一个有吸引力的谎言甚至可以让超越时空之外的非成员甘愿为其效忠,例如ISIS极端组织在欧洲近年来实施的恐怖袭击,实施者很多都是生长在欧洲当地的受到极端思想影响的居民。而同理,这些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极端思想“感召”的无知青年也会通过向恐怖组织捐赠财产来表现其认同。东南亚的恐怖组织,特别是带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色彩的东南亚恐怖组织也莫不如此。
固然国内很多学者强调经济利益的获取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唯一目标,而恐怖组织则不然,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恐怖组织的犯罪动机更为复杂,经济利益的获取虽然不是其唯一目标,但依然是其多种犯罪动机之一,或者是单一犯罪动机的间接动机。所以,我们才在司法实践中将洗钱犯罪和恐怖主义融资犯罪进行类比,并且在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中把反洗钱斗争与反恐怖主义融资斗争二轨并为一轨。
4.东盟框架内反恐立法进程
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三个国家于2002年5月在吉隆坡共同签订条约以应对本地区内部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尤其是加强三国在领海边境和陆地边境的治理,以利于遏制越境犯罪。
从2015年澜湄地区首次执法安全部长会议伊始,由地区内的各参与方组织实施的联合巡逻执法已经连续开展,并且日趋常态化。也只有依靠澜湄区域的相关国家联合起来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才能够实现边境地区的稳定,维护一个法治的次区域环境。以《东盟联合反恐行动宣言》为标志,东盟框架内的反恐立法不断取得实质性成效。
2009 年,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团参加了联合国第52 届麻醉品委员会高级别会议,再次重申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承诺。为减少“金三角”毒品危害,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率团赴泰国参加第八届MOU 签约国部长级会议, 签署了《MOU 伙伴关系补充文件修订版》,推进了东亚次区域禁毒谅解备忘录(MOU)机制发展。参加了在泰国、印尼举行的第32届和第33届亚太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HONLEA)等区域禁毒执法合作会议,广泛参与区域禁毒合作交流。[7]
东盟框架内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条约立法以及机构设置在近十年来取得了很多阶段性的成果。如2001年11月29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签署的《东盟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以及2002年东盟第八次峰会反恐联合声明,随后于2003年7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东盟反恐中心。2007年1月13日菲律宾宿务第十二届东盟峰会签署《东盟反恐公约》。“协助条约”不具有普遍性效力,近似于任择强制管辖权,而《东盟反恐公约》由东盟各国首脑签署通过,在东盟成员国之间具有普遍效力。随着这些区域内立法机制的不断完善,近两年来,东南亚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数量在总体上所有下降,甚至有西方媒体通过数据指出这一数字在2016年已经下降至上年同期的50%。*South East Asia crime at lowest levels in a decade, April 14, 2016, http://www.bairdmaritim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7609:maritime-crime-in-south-east-asia-drops-to-lowest-levels-for-a-decade
三、结语:中国与东盟联合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面临的机制问题及反思
如何对待一种法律机制,尤其是作为一个实体性国际组织所承载的区域性司法机制,归根到底,必然要面临着如何在确立一个高效独立而且坚实有力的司法体系之内依然保障各成员国家彼此之间的主权平等问题,特别在对于跨国犯罪的严重罪行进行起诉和执法的过程中,主权平等原则面临着考验。
对于国际上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学者往往对不同的特定地区采用不同的关注点。例如在美洲各国,贩毒活动长期成为该地区内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代名词。而近年来西非的海盗、东欧的枪支犯罪、人口贩运、中亚的贩毒和恐怖主义犯罪、东南亚的贩卖人口和贩毒、恐怖主义犯罪都成为本地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代名词。在整个地缘政治板块中,中国成为各地区有组织犯罪的交汇点。从而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参与引起相关各界的高度关注。
近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已经在立法实践与司法实践方面逐步进入机制化、常态化。2002年中国—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宣言》中谈到“为打击贩毒、偷运非法移民包括贩卖妇女儿童、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8]实际上涵盖了东南亚地区对于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目标和范围。
长期的合作实践证明,从外交领域、安全领域以及经济贸易领域而开展的双边关系合作是东盟与中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主要推动力。既有的双边政治磋商机制以及在司法层面开展的合作机制是中国—东盟成功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恐怖主义犯罪)的稳固基石。然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与东盟各国既有的双边引渡条约还存在着种种法律缺陷,例如在政治犯不予引渡和本国国民不予引渡这样的传统国际刑事法律问题方面都不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严重滞后于东南亚地区日益猖獗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现状,从而有很大的必要进行强有力的改进。目前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六种主要形式中,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边条约中大多都不具备,且条约内容单一,缺少执法可行性,而且还有一些东盟国家还没有与中国订立双边引渡条约,也无法援引国际条约进行有效的惩治,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进行协调、斡旋,今后中国与东盟开展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共同行动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机制化、常态化的办事机构,如秘书处这样的组织形式,并完善区域内的统一执法机制,共享区域内情报信息,以及建立区域内情报网络等等。
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全面合作的过程中,文化、宗教上的差异也会带来一些阻碍。例如中国在与澜湄流域国家开展合作过程中提出过“Shared destiny”(共同命运)的理念,而处在该地区的一些小乘佛教国家认为这个概念在其宗教信仰中是不能接受的,为此中方采用灵活的方式将这一说法改为“shared future”(共同的未来),从而得到地区内各国一致接受。
[1]Transnational Crime Booming Across South East Asia: United Nations[ED/OL].http://www.ndtv.com/world-news/transnational-crime-booming-across-south-east-asia-united-nations-1281092.
[2]张杰.反恐国际警务合作[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3]台湾反思“诈骗独步全球”之耻[N].环球时报,2016-04-14,3875.
[4]程琦.菲律宾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综述[J].犯罪研究,2007,(2).
[5] Roderic Broadhurst and Vy Kim Le:“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in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Andrew T H Tan, 2013. Routledge, London.
[6] Indonesia: Tension Over Aceh’s Flag,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Briefing N139, Jakarta/Brussels, 7 May 2013.
[7]2010年中国禁毒报告[ED/OL].http://626.cpd.com.cn/n2004620/c14748482/content_7.html.
[8]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N].人民日报,2002-11-14,(3).
〔责任编辑:左安嵩〕
On ASEAN Punishment of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Mechanism
ZHANG Yi
(Department for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Beijing, 100005, China)
In the first ministerial meeting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ASEAN“10 + 3”cooperation mechanism on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crimes in 2004, th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areas are grouped into eight categories, and terrorism crime eight kinds of crime form. Also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73rd“noted with concern that there is close contact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variety of structural obstacles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nd terrorist crimes at present. Therefore, how to define, punish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SEAN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will affect the future Southeast Asia as a whole in it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hina’s important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is region. Besides,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terrorism crime; ASEAN; judicial assistance;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张屹(1983— ),男,北京人,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安全,全球治理,国际人权与人道法研究。
D814.1
A
1006-723X(2016)12-0019-07